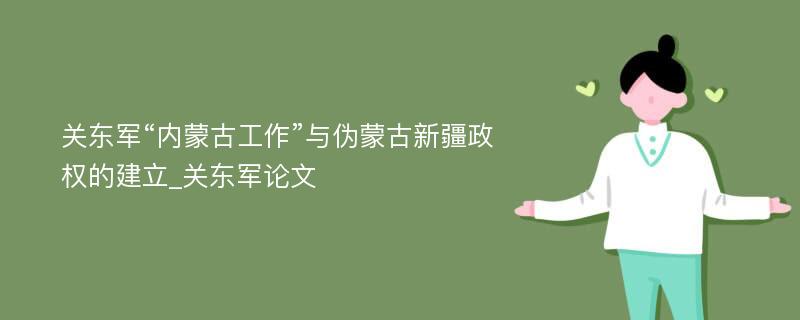
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伪蒙疆政权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东军论文,内蒙论文,政权论文,工作论文,伪蒙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1)03-0061-05
一、关东军的“内蒙工作”计划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即侵占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1932年3月,由日本侵略者策划操纵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完全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推行其“内蒙工作”。所谓“内蒙工作”就是日军在侵占热河和发动芦沟桥事变期间,关东军直接负责策划的以帮助蒙古民族“独立”为诱饵,将内蒙古西部地区(当时包括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部等)纳入日本侵略势力范围之内,扶植建立伪蒙政权,从而侵占内蒙古的阴谋活动。“内蒙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继续和具体化。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全境,并置于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关东军对“内蒙工作”之开端。同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政府订立“塘沽协定”,国民党政府不但正式承认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占领,而且进一步把绥东、察北等地划成了日本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这个协定打开了日军进而侵占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大门。其实,日本侵略军夺取热河后不久,旋即进犯了察哈尔地区。当时,东北军崔兴武旅的李守信投降了日本方面,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进犯了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次日,占领察哈尔重镇多伦,便在日本人的指导下,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自治区”,由李守信任行政长官。这样,与热河省接壤的察哈尔的一隅落入日本的统治之下,成为关东军“内蒙工作”的根据地。关东军参谋长在《并电第545号》(1933年5月5日)中对“内蒙工作”的初期意图做了如下说明:“以后指导该军,按照既定方针在察哈尔东境一带扶植亲日满势力,在建成对抗敌对势力的缓冲地带的同时,逐渐使其势力向乌珠穆沁方面扩张。”[1]同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又提出:“要指导和促进在内蒙古西部树立排挤苏联与中国势力进入的自治政权,使外蒙古逐渐摆脱苏联羁绊转为亲日满。”[2]对于紧连热河的察哈尔蒙古各部的方针是“主要依靠平和的文化工作,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密切使之自发导向亲满,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3]关东军这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方针,最主要的是由于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反满活动十分激烈。这时关东军的首要任务:一是尽快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二是保证与伪满相联的察哈尔地区的安定。“从整体上看,其内蒙工作的方针是消极的。”[4]特别是在西部内蒙古建立亲日的自治自权问题上,一方面想促进建立排斥苏、中势力的自治政权,另一方面又害怕自治政权建立后会导致东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兴起而脱离满洲国。由此可见,关东军的“内蒙工作”意图是巩固伪满洲国西南边境,形成对苏进行战争时阻止苏军由外蒙古向东北方向南下的形势,同时得到向外蒙古和华北扩张的立足点。
但是,当时在现地负责“内蒙工作”的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对关东军参谋部的以上方针不予理睬,而于1933年10月制定出详尽的《关于建立蒙古国的意见》,并开始实施。其中对于“蒙古国”的疆域,松室孝良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包括长城外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在第一案的基础上,增加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对于建立“蒙古国”的必要性,松室孝良认为:第一,可以使日本对苏或对华采取军事行动时更有利;第二,可以使日本经济圈扩大;第三,可以促进日本“大亚细亚政策”的实施,提出要建立“环绕中国外侧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西藏国的国家联盟,迫使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结盟。并且通过该环状联盟给以外蒙、中央亚细亚、波斯、印度、安南等政治上极大影响,促进全亚细亚民族的兴起,帝国成为真正的盟主”。[5]对于建立“蒙古国”的可能性,松室孝良提出主要有蒙古民族意识的复活与对汉族的反感,与清朝的历史关系和对溥仪的敬慕,蒙古族是天生的骑兵,西部蒙古是完整的蒙古族聚居区以及历史上大元帝国的传统和喇嘛教的影响等。按照松室孝良的计划,蒙古建国的时间用三年完成,行动从当年冬天开始,具体做法包括聚集蒙古人才、培养蒙古将校、培养优秀的日本人指导官、设置推动各蒙旗奋起的秘密联络机关等,所需经费为14.8万日元。甚至他对“蒙古国国家组织大纲”、“国号”、“元首”、“首都”等,都作了细致的说明。[6]松室孝良的“意见”得到了日本陆军参谋部和日本政府的确认之后,对李守信的旧东北军进行了改编,并且对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部的王公总管加以笼络。10月间,松室孝良招集蒙古王公,在多伦召开了蒙古代表会议,表示要支持内蒙古“建国”,帮助“复兴蒙古民族”,企图实现其分裂中国“以华制华”的罪恶目的。
松室孝良如此“过于深入的蒙古工作,特别是进行政治工作”,与关东军参谋部的上面所述之方针发生冲突,关东军参谋部害怕松室孝良的行动危及其巩固满洲国的中心工作,遂把他调离承德,转任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1934年1月24日,并东军参谋部制定《对察施策》,进一步强调:“力戒无视国际情势的露骨的活动和惹起内外视听的急进措施”,其方针是:“将来要准备和指导察东及锡林郭勒盟,使其首先在经济方面自发地成为与满洲国具有密切关系的行政区域,以利于满洲国的统治及国防;同时要使其成为对华北及外蒙古采取各种措施的根据地……,此外,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施策着眼点还放在“经济文化方面”,“军队工作要隐密进行”。但是,松室孝良于1934年2月又制定了“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工作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虽然松室孝良在“内蒙工作”上与关东军参谋部发生分歧,但他所制定的计划后来却由关东军的其他人实现了。因为这种分歧仅仅是工作步骤上的分歧而已。
二、关东军出兵侵入内蒙古西部地区
到1934年末,关东军在东北的治安基本得到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于同年12月新任关东军司令的南次郎大将与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便将主要精力用在对苏工作和对“内蒙工作”上。在关东军来说,对苏与“内蒙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当时关东军正专心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果苏军优势部队从库伦向察哈尔或热河方向南下时,关东军的左翼便暴露出重大危险。所以,关东军在西部内蒙古要求得到有力的作战根据地,以确保左翼的安全。
1935年以后,关东军进一步推进“内蒙工作”。同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了板垣征四郎为核心的幕僚、特务机关长、驻中国武官等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加强对华北及西部内蒙古的工作。关东军在板垣征四郎副参谋长、田中隆吉参谋的策划下,为了使西部内蒙古“从中国独立”,积极地鼓动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展开蒙古独立运动。当时,德王也见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举动置若罔闻、屈膝求荣,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竭力揭制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使他们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抛弃了在国民政府范围内实行内蒙古高度自治的主张,迈进蒙古独立之路,逐渐加深了与关东军的联系。
关东军与拥有政治号召力的德王、拥有军事力量的李守信以及察哈尔保安长官卓特巴扎布联合在一起,不断向察北施加影响力。当时,关东军在热察边境一带,多次蓄意制造事端,借以向察哈尔境内扩大其侵略范围。1935年6月,签订《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简称《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后,驻扎在外长城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决定撤退,向北平方向集结,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北部地区。《秦土协定》后,日本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和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代表张允荣即开始了有关细节的谈判。8月5日,划定治安界线,决定长城以北由蒙人保安队、以南由汉人保安队分别负责维持治安。此即所谓《松井·张允荣协定》,此协定强行将《秦土协定》所规定的日人活动范围扩展到察绥两省境的长城线。
《秦土协定》成立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于7月25日进一步制定《对内蒙施策要领》,明确规定其今后的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以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为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了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同时,还就控制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交通和经济等各领域作了细致的规定。政治方面强迫实行《秦土协定》,扶植德王、卓特巴扎布和李守信联合排汉,驱逐傅作义在内蒙古的武装力量;军事方面强调组建由日本军官做指导官的仆从军,给以武器和其它援助;文化方面要借助宗教与教育力量,灌输奴化思想;交通方面要以军事为目标全面规划,“以利于关东军将来的工作”;经济上则特别强调要由伪满洲国加以指导,展开物物交换贸易,使尽量“使之养成使用满洲国货币的习惯。”[7]日本在内蒙古推行的分离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是,使内蒙古地区与南京中央政府脱钩,成为日本的仆从国,要求其对日军和伪满洲国具有最大限度的依附性,并要担负日军对付苏联和外蒙古的战略任务。日军陆军中央从国际形势和全局战略出发,不同意关东军大力向西部内蒙古侵入的做法。8月28日,永田军务局长向关东军下达了《中央对华北及内蒙之指导》,指示关东军“对内蒙的政策依然要坚持以前的方针,不急于建立政权,在当前形势下,主要应以文化、经济工作为重点,这样也要达到目的”。[8]关东军对中央的指导并不理会,继续推进其“内蒙工作”。12月初,关东军空运约一个连队的兵力到达多伦,配合伪察东警备军李守信部,从多伦出发开始作战,相继占领了宝昌、沽源。此后,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达成协议,由李守信部借蒙古军的名义进驻外长城线以北的察东六县。至此日伪军控制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全部地区,为建立伪蒙政权打下了基础。
关东军并不以控制察东六县和各蒙旗地区为满足。1936年1月又通过了由田中隆吉参谋立案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规定其方针仍是:“关东军基于帝国陆军的形势判断对策,为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应当采取必要的对外蒙古的怀柔措施以及促进其反苏分离的气氛。同时为了有助于对华工作的进展,且巩固满洲的经济和国防基础的目的。要从实质上强化德王统制下的蒙古军政府,同时使其势力逐渐向中国西部地方扩大,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最终要使内蒙古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同时确定:“施策重点是将目前蒙古军政府管辖区域内各机关进行整备,以此为基础,将其势力渗入到绥远,然后扩大到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9]关东军的这一计划马上受到陆军中央的反对,陆军通盘考虑对华战备,兼顾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实施,遂制定《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的指示,对关东军制定的计划略加调整,指出:“关东军进行内蒙工作的范围应当在锡盟、察盟、乌盟,可能的话包括阿拉善地区,目的是使这些地区不执行中国政权的实质性命令”。还指出:“关东军对蒙古军政府的指导应以隐密的内部工作为主,通过特务机关实现以最小限度的日本人顾问辅佐之”,“对于军政府武力的充实应以提高质量为第一”。指示中最后强调:“关于关东军所领导的军政府管辖区域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绥远省、外蒙古相互间的分争的处理,要接受陆军的指示行事。”[10]在此之前陆军中央的《第一华北处理要纲》曾提出:“内蒙工作其范围应大致限定在长城线以北,且暂不波及绥远东部四蒙旗的地域”。[11]力图禁止关东军为内蒙工作冒险与傅作义军发生冲突。但是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对陆军中央的上述意图置若罔闻,继续独行,企图侵入绥远省东部地区。
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和德王分别从长春和西苏尼特旗赶来张北,与特务机关长田中玖计议成立伪察哈尔盟公署之事,以制造一个察北特殊化的局面,并为建立伪蒙古政权奠定基础。于是,德王以蒙政会名义决定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月10日,虽在张北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但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亟需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它各盟。2月10日,德王在西苏尼特旗建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按照4月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大会的决议,5月间蒙古军总司令部迁移到化德(嘉卜奇),并改称为蒙古军政府。之后,在关东军的援助下,努力扩充军队,极力着手准备建立蒙古国。在关东军的直接操纵下,德王与伪满洲国签订了“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军事同盟、互派常驻外交代表”为基本内容的“满蒙协定”。不久,又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提携”为要旨的协定。日本将伪蒙古军政府、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纠合在一起之后,更加猖狂地调动部队,加紧侵绥活动。11月,田中隆吉参谋和德王指挥伪蒙古军和大汉义军(汉族谋略部队)向绥东大举进攻,但遭到了绥远省傅作义将军率领的国民党部队的猛烈攻击,这次军事冒险行动惨遭失败。绥远抗战的胜利,使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内蒙工作遭到了挫折。
三、伪蒙疆政权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命令傅作义统一指挥进驻察哈尔、晋北及绥远的各部队,加强平绥铁路沿线之防卫。8月9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称东条兵团)进驻察北。20日,他们与从北京方面北上的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相呼应,由张北向长城线发动进攻。傅作义应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的要求,从怀来赴张家口增援,共同与沿平绥线西进的日军决战,但未能抵制日军的攻势。27日,张家口遂告沦陷。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此时,留守绥远的部队战斗力很弱。9月23日和27日,日军分别占领丰镇、集宁,转而向西攻占归绥,10月17日又占领了包头。至11月间,除伊克昭盟大部、河套地区及阿拉善、额济纳旗以外,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主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平绥铁路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
日本关东军在武装侵占察哈尔、晋北和绥远等地的同时,随军特务机关沿路扶植傀儡政权,企图使新占领区成为巩固的后方基地,并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加强殖民统治。1937年8月13日,关东军制定《察哈尔方面政治工作紧急处理纲要》,向陆军中央部提出了对新占领区政权的设想。纲要中说:“随着帝国军占领平绥路沿线,先要安定察哈尔地区的治安,以此来安定与满洲国接壤地区,并解除对平津方面的威胁,以有利于将来对内蒙古及绥远、山西工作的进展为根本方针,为实施上述方针由关东军及满洲国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援”。在上述方针之下,主张在张家口建立“统辖察北、察南的统一政权”,[12]将其置于直属关东军司令官的张家口特务机关及日本顾问的指导之下。接着关东军司令部于8月14日的《对时局处理纲要》中也规定:“成立察北、察南的统一政权……将来合并绥远省”。[13]
这些设想无非是企图首先把察哈尔省作为“第三满洲国”进行吞并,然后其活动范围扩大到绥远。但是陆军中央部对此予以反对,并在9月4日决定了《察蒙处理纲要》,指出的方针是:“目前关东军的政务指导地域范围为察北、察南,必要时可以对张家口以西平绥铁路沿线采取对策。将来由华北军担任察南政务指导及对平绥线地区采取对策。关东军实施对锡盟及察盟大部(工作进展后,要到乌盟范围为止)的工作”,“察南不要和察北的内蒙古政权合并……设立于该地方民众为基础的机关,担任维持治安,安定民心,开发经济等工作。”[14]此方针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想把关东军的行动范围限制在外长城以北的察哈尔、锡林郭勒两盟。其后,双方虽有若干交涉,但关东军对陆军中央的限制不予理睬,派出以金井章次为首的日本顾问团进入张家口,积极进行组织新政权的工作。9月4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杜运宇、于品卿为最高委员。同时成立张家口特务机关,吉岗安直大佐任机关长(不久由松井玖太郎大佐接任)。察南自治政府受吉岗安直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指导,管辖张家口市及察南宣化、怀来等十县。10月1日,关东军又制定了《蒙疆方面的政治工作指导纲要》,决定:“在已成立的察南自治政府之外,又组织内蒙古自治政府及山西省大同地区的晋北自治政府”。[15]《纲要》改变了先前仅在察哈尔建立政权的设想,拟从察南、晋北、蒙古之自治政府派出委员,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指出该委员会协商、管理有关三政权的重大政务工作。关东军占领大同之后,立即扶持汉奸夏恭、马永魁组织了“治安维持会”。10月15日,又策划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夏恭、马永魁任最高委员,前岛升任最高顾问;同时成立了大同特务机关,羽山喜郎中佐任机关长。晋北自治政府管辖大同市及长城以北沽源、左方等十三县。日军侵占归绥后,10月25日,关东军又制定了《对内蒙自治联盟措施》,提出了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施政范围内,以“防共”、“民族协和”为核心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大纲》。德王在关东军的协助下,于27、28日在归绥召开了“第二次蒙古大会”,决定将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937年11月22日,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上述三个自治政府的代表聚集于张家口缔结协定,成立协商性机构蒙疆联合委员会,金井章次任最高顾问兼总务委员长。该委员会统一管辖三个自治政府的有关产业、金融、交通、总务等重大事项,实际上成为三个自治政府的指挥机关。12月10日,关东军制定《关于蒙疆方面政治指导》,明确指出:“蒙疆联合委员会与各自治政府间的关系是,持续蒙古方面各种工作现状的同时巩固其基础。”这显然是将察南、晋北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使其作为特殊的防共区域的企图。1938年8月10日,在金井章次的操纵下改组了蒙疆联合委员会,使原先只是协商性质的机构变成了高居于三个傀儡政权的发号施令的机关。德王本想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强化,扩大职能权力极为不满。日本侵略者不可能同意德王的蒙古独立的主张,但如果没有蒙古的政治领袖德王的话,也失去强调蒙疆地区特殊性的依据。因此,只好把德王捧为蒙疆政权的最高政治领袖,并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使其接受“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控制。
1939年7月28日,日本兴亚院(日本政府设立的处理有关侵略中国事宜机构,1938年12月15日正式成立,日本首相兼任总裁,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兼任副总裁)提出《设立蒙疆统一政权纲要》,决定“合并蒙疆联合委员会和三个自治政府,建立统一政权,称之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采取高度的自治制度”。[16]经过日本军部和金井章次的精心策划,9月1日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成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推选德王为主席,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这样,关东军利用德王伪傀儡政权,达到了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控制内蒙古西部战略要地的目的。
标签:关东军论文; 伪满洲国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内蒙论文; 陆军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