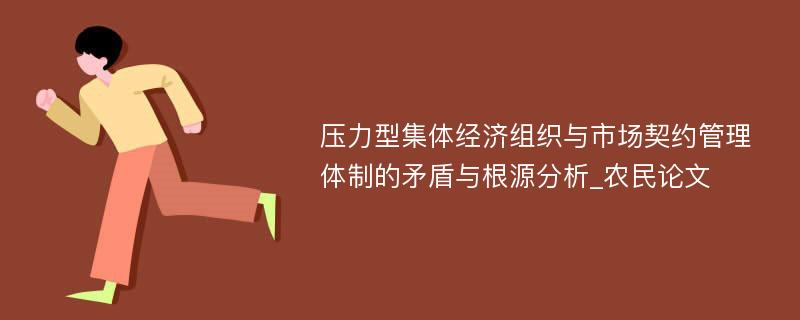
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的矛盾及根源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经济论文,根源论文,承包经营论文,体制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分”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农民重新取得了土地这一资源的支配权,并且获得了市场交换的权力,成了独立的市场微观经营主体,以市场为取向安排农产品的供产销,所以农业承包经营体制的改革,成功的把农民推向了市场。但是在“统”方面,却仍然保持了传统的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本文的集体经济组织是指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为,在目前实际操作中,两者是合二为一的),计划经济的惯性仍在左右着农民。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或者说农村经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体制外向体制内转移时,滞后的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以市场为取向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矛盾日渐尖锐,成了阻碍农业再上一个台阶的非理性制度安排。
一、 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矛盾的表现
表现之一: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对农产品产量的要求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在“销”方面困难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集体经济组织要求农户按指令生产某些农产品并达到一定总产量与农户对所生产农产品销售困难的矛盾。因为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是我国基层政权的延伸,承担着政府保证全国粮食供给的责任,特别是产粮区,这几乎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压给基层政权的代理人——集体经济组织,上级对下级规定各种任务和指标,然后把这种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依据。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一级一级下压,最后由乡村基层政权及其代理人落实,所以代理人只对上级负责,只负责总产量,不是对市场负责,不对农民生产后果负责。而市场型的承包经营体制的主体农民,按理说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供产销,但是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行政职能的存在,使农民生产决策上受压力约束,因此,在生产上是典型的命令经济,而在销售上是市场方式,农民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全责,产销的环境不同,权责不一致,必然使市场型的承包经营体制,出现诸如“卖难”、“买难”等无规则的振荡,而后果由农户单方承担。
表现之二: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在农地配置方面的调整压力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要求农地“稳定”的矛盾。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除了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能外,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具有资源优化配置(即“小中取大”模式配置农地,在均田制的前提下优化配置农地),追求利润最大的动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在社区内按“均田制”模式优化配置农地,而目前农地是人均分配,且流转机制没有完全建立,农地流转的内在动力不足,农地配置呈封闭性、凝固性趋势,承包地有强烈的排他性,但是随着农民生老病死,劳动力的变迁,人均承包的土地经过一段时间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经常出现“有地无人”,“有人无地”的状况;还有一些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户对农地的利润追求蜕变为自然经济,土地产出率极低,为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极少;有些甚至抛荒,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集体经济组织,便有了一种要因地制宜调整农地的客观压力。这种压力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地承包规定相违背。有些地方本着按人头优化配置农地的原则每隔3—5年普调一次,这虽然避免了自然经济和土地抛荒行为,但是承包期限短,农民的级差地租Ⅱ受侵蚀,造成了承包农户对耕地长期预期不够。
表现之三: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规模集聚及区域性流动的限制与市场型承包制跨区域、跨所有制和跨部门流动要求的矛盾。由于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在农地规模集聚及有效流转方面缺少必要的政策导向和政策扶持功能,对农户承包耕地仅仅满足于时间的单向延伸而忽视了部分农户对耕地的转移、转让和再承包的需求,忽视了部分农户对耕地规模集聚的内在需求。同时,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出于管理的目的,或者说出于直接干预的目的,或者上级压下来的生产任务和各种费用摊派的硬约束,农地成了社区经济组织的主要财源,因此,行政性的社区组织不允许农地在区域、部门、所有制之间的流动,而市场型的承包体制在规模经营、专业化经营等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驱动下则有跨区域、跨所有制、跨部门流动的内在动力,要求规模经营、要求联营、要求折价入股、要求再租赁、再承包、要求抵押、要求转让使用权等等。
表现之四: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惯性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主体依附惰性的矛盾。虽然法律规定农户是市场微观主体,但是农民对社区组织依附性依然很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户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但是中国封建传统既悠久又顽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在广大农村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再加上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熏陶,广大农民与基层干部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市场意识都不能与新体制相适应。一是农户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成为完全意义的微观经营实体,农户对集体经济组织依赖程度相当大,不能用市场经济的工作方式对其进行组织协调。二是很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观念没有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行政职能的角色,经营方向的选择、销售方式的确定,施肥、施药的指导等均带有很深厚的行政指令色彩。三是微观经营主体被掩盖或替代,农户缺少独立的人格,对“二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依附性强。
二、 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矛盾的根源分析
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矛盾的根源是主体目标的非一致性、利益的非一致性、地位的不平等性和权责的不对称性。
(一)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人由于是上级任命的,接受的任务是上级下达的,工作好坏由上级考核,干部奖惩由上级决定,因此,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人不是对社区内全体农民负责,而是只对上级负责,追求政绩最大。而市场型承包农户,是“经济人”,对自己经营成果负责,追求利润最大。目标的非一致性,使两种体制不兼容,磨擦成本高。
(二)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主体的目标非一致性。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接受了政府职能的“衣钵”,追求社区内公平发展,惟恐在当前二、三产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在农地配置上引入市场机制,会使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形成大土地所有者,造成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所以对规模集聚与农地的流动没有内在动力,而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下的农户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规模效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公平没有责任,目标的非一致性增加了管理成本。
(三)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下农户的权责不对称。由于农户对生产经营的充分自主决策权的归还没有一步到位,一部分决策权依然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对集体经济组织而言,农户仅有生产要素的组合权,即“如何生产”的权力,而“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的权力依然被集体经济组织牢牢控制,这就导致了主观臆想的粮棉价格;指令性的定购粮;刚性的农产品结构;扭曲的农业利润分割方式,脱离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加工项目。这种后果反过来又增加了两者的交易费用。
(四)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下农户的地位不平等。由于“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的权力不在农户手中,因此,农户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只能被认为是政策的执行者和被动接受者,农户在市场中的地位是从属的,缺少独立的人格,这就形成了集体经济组织有权但无责,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但是不对决策结果负责,如只对产量负责,不对农产品的销售负责;有生产成果分配权,但是不对分配结果负责。农户不能依据市场价格信息决策“生产什么”,但是必须对“如何生产”的结果负全部责任,而且对“为谁生产”也没有全部决定权,只有被动接受权。所以农民往往是“有责无权”。
三、 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场型承包经营体制协调运作的改革思路
要协调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农户的矛盾,关键问题是使两者的目标一致、利益一致、地位平等和权责相称,即如何使两者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上一致。
(一)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农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改革。农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改革关键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机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农民需要调整行为,政府也需要调整行为。基本准则就是要尊重价值规律,按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组织发展农业经济。政府对农业进行管理责无旁贷,但是要注意不要“重蹈覆辙”,回到扼杀农业生机和活力的老路上去,也不要“放任自流”,让“看不见的手”随意波动,应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在工作方法上行为要规范,不要“裁判抢球”;在对农业改革的态度上不要“叶公好龙”;在速度上不要“鞭打快牛”。农业改革开放要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宏观调控和市场导向是农业运行机制的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方面,宏观调控以市场导向为基础,市场导向又要依靠宏观调控,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把农业引向良性循环的轨道。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和基层政权的延伸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要在农业宏观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内运作,不能“越位”。
(二)政企分开推动集体经济组织向纯粹的集体经营组织和自治组织分离转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把当前压力型具有行政职能的集体经济组织“一分为二”,化解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职能,建立两套机构,一套为村级自治组织,以社区稳定为主要目标,专门处理社区日常事务和搞好土地的管理,不干预集体经营组织的经营管理业务,另一套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该组织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动力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同时,该组织的主要职责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为农户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服务,引导农民进入市场,保证集体积累保值增值。这种“分离”不仅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精简并行不悖,而且可以化解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职能,明确自己的定位。
(三)转变角色推动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从“行政式领导”向与农户平等的市场主体过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与村集体签合同,独立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是市场的微观主体,具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性。因此,这就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对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农户依赖集体经济组织,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充当龙头,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具有依赖性;另一方面,作为市场微观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我们必须尊重并承认这种两重性,压力型集体经济组织分为自治组织和集体经营组织以后,应打破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传统的上下级关系,村自治组织彻底与政府脱钩,成为真正的社区自治组织,由农民自愿组成,其代理人由全体农民选举产生,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的稳定,处理日常事务、传递和宣传政府的政策,集体经营组织应与农民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或“法人”,它释放的信息、提供的服务,不具有强制性,农户有选择的权力。
(四)转换职能推进集体经济组织由行政管理职能向“双层经营体制+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农业经济新体制发展。要使农民成为真正“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市场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必须从决策主体和管理主体的地位上退下来,向服务主体过渡。因为农民要求的多样化,必须要有多元化的服务组织为之服务,而集体经济组织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根据我国农村的特点和双层经营体制所处的历史阶段,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以国家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以农民自办服务为补充,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和特有功能,形成覆盖农村各业的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性、交叉性的专业服务化网络,建立“双层经营体制+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农业经济新体制,这种转换既转换了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又创新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内容,协调了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的矛盾,完善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五)加速民主化进程建立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要保证农民“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权利,除了推进农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改革外,还要在农村普遍推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推进村务公开,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使农村工作走上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上来。不仅可以切实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更重要的是使农民通过民主的渠道捍卫自己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彻底改变集体经济组织干预的惯性,扭转农民缺乏自主、民主意识的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