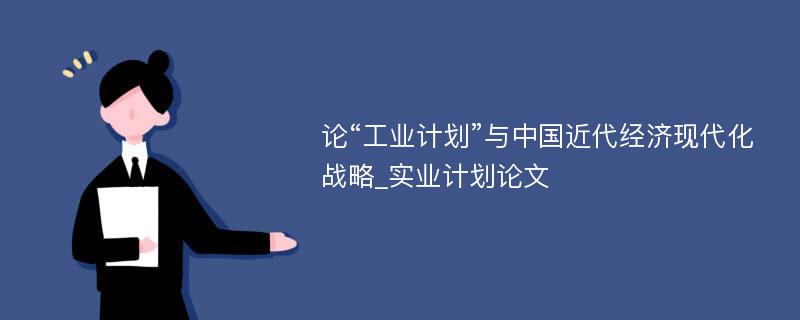
《实业计划》两议——兼论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近代论文,战略论文,实业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巨人孙中山秉承西方“民享”、“民治”、“民有”的基本原则,创立了“三民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并以之为终极理念。在“三民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是前提基础,民主主义是动力,民生主义则是目的和核心。诚如《东方杂志》所评:“革命不过为先生所采用之一种手段;至于先生终身所努力者,其目的全在建设。”〔1 〕对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且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实业计划。它似一幅理想主义的“完美”画卷,将经济现代化前景,直观、具体而又气势恢宏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实业计划》的出现,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毁者有之〔2〕,誉者有之〔3〕。但无论毁誉,基本上围绕着其可行性问题纠缠不休。 理想与现实原本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此类或褒或贬的评论,仅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对《实业计划》本身的认识,无助于对问题的深入研究。时至今日,其遗风流韵仍有未绝之势。
真正的评价,只能是按照孙中山的本意,去作更深层次的探讨。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开篇就告诫过:“余之所为计划,材料单薄,不足为具体之根据,……非待专门家加以科学之考查与实测,不可遽臻实用也。”实业计划只是国家经济之“大方针”、“大政策”。“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4 〕我们虽非“专门家”,但如果把《实业计划》放在从历史到现实的“长时段”中来考查,即可以用现实反观历史。纵观《实业计划》,不难发现区域经济和均衡发展的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对此,我们参照有关经济理论,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另一方面试图指出孙中山的理论偏差:其一,区域经济思想是“不纯粹”的;其二,均衡发展观是源于“逻辑推理的误导”。旨在“重构”近代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希望能为当今的经济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和印证。
一
孙中山经济现代化方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区域经济的梯度规划。他的区域经济,既打破狭隘的行政区划,也不是以人文风貌来划定的,而是以海港为轴心,由相关的交通网络为经,以资源、产业为纬,所形成的一个有利于经济沟通的空间辐射区。
区域经济第一个层次是分别以北方、东方和广州三个世界级港口为经济发展支撑点的经济区。在孙中山的设想中,三大港口都有密如蛛网的铁路系统和内河航运系统向内地伸延。北方大港与黄河及其支流、陕西渭河、山西汾河相接;东方大港通过长江与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鄱阳水路系统、汉水、洞庭湖水系相通;广州大港与广州河汊、西江、北江和东江相连。这样就形成了华北、华中及长江流域、华南经济区。区域经济的第二个层次是四个以二等海港为基点构成的经济区。四个二等港顺沿海岸线由北向南依次为营口、海州、福州、钦州。辽河与松花江之间开凿运河后,营口将成为吉林、黑龙江、蒙古内地水路系统之终点。海州将定为东西横贯中国中部大干线海兰铁路之终点〔5 〕;福州港之腹地,以闽江流域为范围;钦州将“定为通过湘、桂入粤之株钦铁路之终点”〔6〕。果如是, 四个二等港也将成为各自区域的经济杠杆。区域经济的第三个层次是以葫芦岛、黄河埠、芝罘、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电白、海口等三等港为中心的九个经济小区。不仅如是,孙中山还注意到了各经济区之间的协调,他希望通过交通使各经济区形成一个更大的互联网,甚至提出仅需要联络内地水路,即可使北京直达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7〕, 从而使全国经济区能够联手合作。由此可见,孙中山的区域经济,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所赐予的客观地理条件,藉开凿运河、疏通河道建成航运系统,并且与计划中的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构成纵横联系,使每个经济中心都据守铁路、水路的龙头地位。拟以港口为经济发展的“充电器”,为交通网所覆盖的地区“充电”、“加压”,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交通情况只是区域经济的最基本要素,孙中山更关心的是地缘性的资源和产业。《实业计划》不仅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分布的地域差异,而且主张依自然资源优势设煤矿、铁矿,建铁厂、钢厂,兴办水泥厂和毛纺织厂等各色企业。因此,经济区域间的协调与合作,也就是资源优势互补与产业优势互补。为了提高港口的经济辐射力,孙中山更主张把港口办成工业生产基地,如在广州设立铁厂。
在学理上,这种区域经济模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具有的推动力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有利于根据资源、经济技术的状况,发挥地区优势;其次,有利于较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沟通;再次,有利于打破地区和部门的分割,为经济发展松绑;复次,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化解由军阀割据造成的日益紧张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但如果较之于现代区域经济,孙中山的区域经济还存在着缺陷。现代区域经济,实质是一种生产结构型经济组织形式。经济活动所具有的较强的资源依赖性,决定了经济区域注重的是资源、行业的合理配置和调控,决定了它应该有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及辅助产业的协调发展。现代产业的显著标志,即是这种产业结构、部门的合理化。概而言之,经济活动的客观、自然联系与区域经济的制定、运作紧密相联。相反,《实业计划》注重的只是主导产业的发展,忽视了相关及辅助产业的同步发展。孙中山把矿业作为主导产业时,虽然提到矿业机械制造业,不过在主观上并没有把它作为矿业的相关产业,而是从纯商业利益角度考虑的。他认为,矿业日益发达,机械需要越多,“制造矿业器具机械之利益,已无可限量”〔8〕。他把冶金作为主导产业时,对选矿、 炼焦及化工业都缺乏必要的认识。产业结构失衡(只注重主导产业),势必造成重复投资(只投资于主导产业)所带来的生产结构的畸形发育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难以形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导致经济的低度发展和后劲不足,使产业自身丧失再生机能,不可能形成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故而,区域的整体优势也就根本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与之相应,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就不可能形成产业群之间的多层面的密集交叉,而仅局限于主导产业之间单一层面的沟通,实质上,这就把区域间的合作人为地限制在最低程度,以至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
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不能仅在一定程度上,而且应该纯然以经济活动的客观、自然联系为准绳,换言之,应该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经济决策与实践决不能疏忽这一点。但勿庸置疑,孙中山的区域经济思想毕竟揭示出,发展区域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出路。70年后,经过专家学者的充分讨论,中国的高层领导决定将区域经济作为“国家社会经济组织与规划的一个层次”付诸实施。为此,制定了区域经济规划的总方针和重点,并且“以经济的自然联系与资源区位优势互补”为尺度,将中国划分为七个经济区:一是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岸地区;二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三是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四是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五是西北地区;六是中原地区;七是东北地区〔9〕。 从中可以鲜明地折射出,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二
孙中山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全国“一体化”〔10〕的均衡发展观。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近代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传统与现代经济因素同时并存,主要表现为:近代性的工业部门与传统的手工业并存;超自然性“繁荣”的城市与衰败的乡村并存;经济较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并存。其中,如何消除地区间日益增长的经济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的同步发展,是近代以来一直拟以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追求高回报、高效益是投资的一个永恒的规则,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法则。落后地区的相对恶劣投资环境,难以吸纳资金,不可能引发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以致于较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仅未能弥合,反而不断拉大。在控制理论中,这一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现象被称为“马太效应”。更为复杂的是,落后地区又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民族关系举足轻重,关涉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在逻辑推断上,就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必要的政策干预为手段,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全国各地经济的平衡发展,才是寻求改变贫富悬殊、消除民族隔阂的唯一途径。我们称此为均衡发展观。
在孙中山的区域经济思想中,无论是规模宏大的交通网,还是地缘性的产业政策,都内在地包含和渗透着大规模开发落后地区、消除贫富地区差距的均衡发展观。落后地区经济上的贫困并不等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它恰恰是矿产蕴藏的集中带。为了与其所制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相配套,在孙中山的规划中也就必然加大落后地区的投资力度;他在谈到北方大港的建设时,十分强调对内地省份、贫困省份直隶、山西及黄河流域、西北、蒙古的开发〔11〕;在谈到铁路建设时,十分强调西南铁路系统“非特为发展广州所必要,抑亦于西南各省全部之繁荣为最有用者也”〔12〕。在论及西北铁路系统对蒙古、新疆开发的重要性时,特别指出“此两铁路系统,于中国人民为最必要”〔13〕。与此相关,孙中山还借鉴美国、加拿大、澳洲、阿根廷等国的经验,提出向蒙古、新疆等地移民,以此安置军队裁员,“消纳长江及沿海充盈之人口”〔14〕,同时又可以使移民成为“筑港、建路及开发长城以外沿线地方之先驱者”〔15〕。
应该说,孙中山的移民构想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自不必说,移民可以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更有意义的也许是与之相随的新观念的契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社会的变迁是观念的变革。观念更新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行政命令的强制下,骤然间一展新姿、跟上时代步伐,而需要新的因子的冲击和陶铸,以实现观念在更高层次的整合。人无疑是新因子的最有效的载体。如果可以把向落后地区投资比作“输血工程”的话,那么向落后地区移民不啻“造血工程”。与直接投资相比,移民见效要慢,却颇具潜力,它是把落后地区从“根”扶起的根本保证和最终举措。不过,孙中山有关均衡发展的整体构思有待商榷。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实现均衡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使国民经济的大系统有序地运转起来。事情(特别是近代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按逻辑常规却得不到预期的目的。根据中国经济起点低且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即使不考虑资金、技术等因素,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实现均衡发展的目的,必须排除均衡发展策略定式的干扰,代之以重点突破、倾斜发展的新思路。即首先要拉大不平稳,最后实现全国的共同发展。区域经济的重点,应该相应地放在较发达地区。我们可以把这一思路称为倾斜发展观。
究其缘由,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近代中国是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16〕。在此时期,摊子不宜过大,重在抓住主要矛盾。经济决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强经济发展的渗透力,培植坚实的生长点。较发达地区虽然与落后地区贫富悬殊,但并不等于说,较发达地区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事实正好相反。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异常缓慢,即使与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俄国相比,也难望其项背。1949年,近代生产设备(包括工矿、 交通、 运输业等)仅合人民币128亿元,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7%,而俄国1913 年的工业产值就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17〕。较发达地区经济作为近代工业化水平和方向的体现者,无疑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缩影。由此也就不难想见较发达地区的工业基础是如何的薄弱。较发达地区的发展都还是个未知数,遑论落后地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首先让较发达地区成为经济发展的样板和支柱。只有如此,较发达地区才有可能给予落后地区实质性的援助;只有如此,较发达地区才会对落后地区具有更大吸引力;也只有如此,落后地区才能对较发达地区产生更大的向心力。况且,落后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只是个时间问题。制定经济政策,不应仅注意解决眼前矛盾,以填平贫富地区鸿沟为出发点,而应关注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美国经济学家J.威廉逊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种倾斜发展观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他指出: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有效供给不足,加之追求全国经济最大增长,必然将资源配置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间的差异将会扩大。之后,随经济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程度趋于稳定,当达到成熟阶段,生产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有效供给过剩,国家为了发展,必然要把资源配置在落后地区,开发落后地区,因此,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趋于缩小〔18〕。
其二,中央政府必须依靠来源于地方的税收,维持庞大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各国政府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时,往往给予政策倾斜,实行极其优厚的减免税收的政策。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由较发达地区承担(并且随地方生产总值的递增,税收也有递增的趋势),必然有碍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严重影响了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积极性。因此,与其关注落后地区,不如更多地关注基础较好的发达地区,既可以保护难能可贵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发达地区经济爬坡,又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税收的稳定。
尚需强调的是,倾斜发展模式的前提条件:一是疆域广袤,二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三是处于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三者缺一不可。所以,该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的任何时期。倾斜发展观虽然以“牺牲”落后地区的发展为代价,但决不是抛弃落后地区,而是寻求近代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一种更有效的途径。政策上的倾斜发展观,也并不排斥在实践操作上对落后地区的某种形式的帮助。当然,倾斜发展观也有其副作用。如影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影响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但没有阵痛,也就不会催生出新生命。何况,经济发展自身的魅力会削减倾斜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中国中央与地方若即若离的关系,地方政府极尽所能地营造地方经济。因而,政策上的“牺牲”更不表明落后地区经济的停滞。
到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孙中山区域经济思想具有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仅局限于特定时空,它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也就不等于具有历史现实性。
40年代,工程精英承袭孙中山的均衡发展观,认为:“从前工程事业多集中沿江沿海,今后各地宜平均发展,尤其是西北的水利和交通应当格外注重。”〔19〕50年代的经济协作区的政策,仍然注意到了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60年代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把生产能力推进到大西南、大西北等内陆地区。无可否认,该政策也有着开发落后地区的意图。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基本走着倾斜发展的道路。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即是佐证:从1950—1980年的30年中,占国土面积60%左右的地区只花费全国几千亿基本建设投资中的700亿〔20〕。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均衡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如何加速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需要我们“两条腿走路”:一要建设好全国性的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进行经济试点、示范,并把它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二要注重全国共同发展,真正“把东部开放的区位优势向中部、西部延伸,与内地的资源优势和经济技术基础结合起来,按照经济联系和打通对外通道的思路,从较大范围和各自不同特点出发,对一个大区域的经济进行规划,从而增强中国经济活力”〔21〕。这是现代区域经济规划的一个基本原则。提请注意的是,开发落后地区,也不能齐头并进,应该以地方开发区带动全局的发展。惟其如此,才能逐步驱散笼罩在前人和今人头上的“贫富差”的阴霾。
收稿日期:1997—06—04
注释:
〔1〕 转引《以革命为手段建设为目的》, 三民编译部《孙中山评论集》,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版,第15页。
〔2〕 美国驻北京公使柯兰(R.C.Crane)认为,计划只是“不切实际的、浮夸的计划”。——转引[法]白吉尔《孙逸仙与〈实业计划〉》,《孙中山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 —196页;上海《大陆报》指出,孙中山“只是一个宣传家, 而不是行政家。因为他的理想,离实际太远了。”——《孙中山评论集》,第9 页。
〔3〕 胡适指出,孙中山是名不折不扣的“真实行家”, “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孙中山评论集》,第83页。
〔4〕〔5〕〔6〕〔7〕〔8〕〔11〕〔12〕〔13〕〔14〕〔15〕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8—249、326、328、300、393、255、 319、324、336、265页。
〔9〕〔21〕
详见《区域经济——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新框架——邹家华副总理访谈录》,1992年5月24日《经济日报》。
〔10〕 白吉尔在《孙逸仙与〈实业计划〉》一文中,简略提及“一体化”问题。
〔16〕 罗斯托把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从第七层楼上展望世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84页。
〔17〕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0、341页。
〔18〕 转引蒋清海《中国区域经济分析》,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19〕 《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1946年版,序六。
〔20〕王小强、 白南风:《富饶的贫困》,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
标签:实业计划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经济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经济学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孙中山论文; 铁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