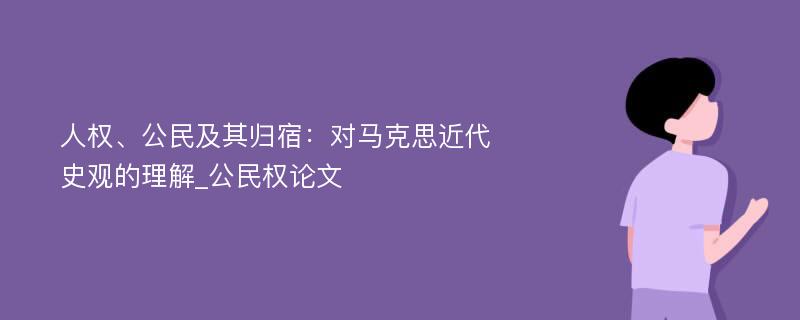
人权、公民权及其终结:理解马克思的现代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公民权论文,现代史论文,人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现代史观即马克思对于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看法,它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马克思的现代史观,人权、公民权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线索。在国内外有关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今天,从这一线索探讨马克思的现代史观的情况却并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一方面旨在系统清理马克思有关公民权和人权的思想,另一方面,则以此为基础廓清马克思现代史观的基本观点,从而抵制西方学术界对其思想造成的歪曲。
一、人权和公民权的兴起
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论述以对布鲁诺·鲍威尔有关“犹太人问题”的批判作为起点。通过《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等著作,鲍威尔对德国当时突出的犹太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要解决犹太人经济上富足而政治上无权的问题,首先必须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犹太教,从而要求德国相应放弃基督教偏见,这样才能实现其渴望的公民地位和获得政治解放。也就是说,宗教问题是横亘在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之间的最大障碍,只有让人们首先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们才能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对于这种颠倒宗教信仰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感到极为愤慨,他在《德法年鉴》上相继发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尖锐批评,并通过阐明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系统说明他对于犹太人问题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历史发展的看法,人权、公民权则在其中起着理解这些思想的核心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鲍威尔是把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对立看作是宗教上的对立,把宗教的统治当成前提,认为只要废除宗教,犹太人便可以作为公民而得到解放。“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①。因此,犹太人要在德国获得解放,就“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以便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②。但问题在于,公民解放、政治解放根本不依赖于宗教解放,前者可以与后者和谐共存,即个体即使仍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也可以获得公民解放和政治解放。同时,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可以存在,甚至还可能生气勃勃、富有生命力。这些情况表明,宗教存在和政治解放之间并不是彼此矛盾的关系。鲍威尔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宗教问题与世俗问题的关系,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前提。但问题却恰恰相反,宗教现象根源于世俗问题。马克思指出:“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来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③从这一立场出发,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倒转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犹太人以及现代社会问题的本质。
那么,什么是政治解放呢?政治解放就是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不再以任何形式的宗教作为国教,而只信奉自身。“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④但是,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彻头彻尾地摆脱宗教的束缚,政治解放只是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不以某种宗教为自己的国教,宗教仍旧是存在的,只不过宗教信仰经由国家的中介变成纯粹私人的事务而已。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所谓基督教国家,是基督教对国家的否定”,“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⑤,获得了政治解放的国家则是纯粹的国家、真正的国家。因为它宣布:宗教,与血缘、财产、出身、等级、职业等所有非政治因素一样,都属于私人的事务。从这一意义而言,政治解放就是传统以封建制为基础的旧政治体制的解体和现代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建立。因为封建政治体制建立在宗教、财产、家庭、身份等基础上。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宣布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私人领域的要素,资产阶级政治摆脱了这些要素的限制而完全以自己的原则组织起来,比如自由、平等、博爱等。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世界诸国中,英国、法国、美国等都属于已完成政治解放的国家。
政治解放的完成使社会个体的生活分割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并由此形成个体两种迥然不同的身份:“公民”身份和“私人”身份。作为私人,个体表现为自私的、利己的、具有各种欲望的个体;作为公民,个体以“类存在”的方式出现,他抹掉了市民社会中身份、等级、宗教、教育等所有差别,所有人都表现为平等的主体。“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⑥。“公民”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⑦,马克思有时候就简称其为“公人”;“私人”则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是活生生的个体。“公人”与“私人”的划分意味着政治解放的完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关系的确立。从此,宗教被宣布为与政治无涉的市民社会领域的事情,并形成政治解放与宗教信仰和谐共处的局面。马克思指出:“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⑧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有关公民权与人权的基本观点:“公民权”(droits du citoyen)是个体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成员的权利,这是一种抹掉个体的出身、财产、能力、教育、宗教等差别之后而形成的普遍性权利。比如,所有个体都被看作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所有个体在政治国家中都拥有平等的公民身份;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制定的权利;所有公民都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等。从这一角度而言,公民权表现为个体作为类存在的权利,这是一种脱离社会实在而虚构出来的权利。马克思指出:“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像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⑨与公民权相对,“人权”(droits de l'homme)则是个体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作为“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权是一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⑩。根据近代启蒙思想家确立的政治原则,它们表现在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等权利上。如果说公民权以相互结合为基础,人权则恰恰相反,它以个体之间的相互分离和孤立作为基础。以自由为例,自由作为人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内容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个体之间的自由界限有如田地之间的界碑,彼此不能重叠,通过划定彼此的边界,自由就是每个人退到自己的边界范围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
较之于学术界的普遍看法,马克思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观点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和实在性。首先,从产生时间上看,公民身份在西方普遍被看作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城邦国家的产物,雅典和斯巴达城邦最早创造了公民身份制度。德里克·希特也把公民身份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11)。较之于公民身份,人权的兴起则被追溯得更加久远。例如,近代启蒙思想家普遍从假想的自然状态出发追溯人权,把人权看作是“自然的”、“天赋的”。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完全把公民权和人权看作是现代的产物,它们以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确立作为前提。公民权承载了资本主义政治的基本原则,人权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缺乏这些前提条件,人权和公民权都不可能产生。
其次,从内容上看,人权在西方学术界一直被看作比公民权具有更加普遍和根本的内容。人权被当作人之为人的权利,具有普适性和道义性特征,比如生命权、平等权、人格权、发展权等。公民权则表现出明显的国家性和政治性特征,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劳动权和受教育权等。个体的公民权即使遭到剥夺,其人权依然存在。人权不仅仅局限于国家,而是以“类存在”的方式出现。比如,布赖恩·特纳认为,与公民权相对照,人权更具有普遍性(它为联合国宪章所载明)、更具有当代性(它不依附于民族国家)和更具有进步性(它更不考虑国家如何管理其人民)(12)。在马克思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超越于特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国家的普遍人权,人权和公民权都以特定的社会和国家作为基础,前者不过是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私人性权利,后者则不过是个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被虚构出来的普遍性权利,两者的差别反映了“商人和公民、短工和公民、土地占有者和公民、活生生的个人和公民之间的差别”,反映了“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13)。
回到马克思的现代史观话题上来,前文的分析至少表明了他对于现代历史的如下看法:首先,人权和公民权的兴起标志着现代史的开端。如果说前现代社会是一种为宗教神光所笼罩的社会的话,公民权和人权的兴起则表明,人们开始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开始“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14)。一句话,人们开始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构想幸福。其次,人权与公民权的分立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关系。人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状况,公民权反映的则是人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幻想出来的作为类生活的幸福。这种类生活想象尽管没有兑现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没有带来人的真正解放,但至少表明了人们在政治上所获得的解放,因此仍然具有进步意义。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人权、公民权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宗教统治的政治秩序的形成,这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又表明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二元化,即以人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与以公民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生活的二元分化,这种分化产生了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
二、人权和公民权的本质
人权和公民权的出现尽管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形成,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并不意味着人类从此就实现了自身的解放,就进入梦寐以求的自由状态。相对于传统社会,政治解放所催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不啻为一个巨大进步,在实现人类解放目标上迈出了一大步,但社会仍然被积重难返的问题所缠绕,尤其是以物的统治为表征的社会异化问题。“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15)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同样反映在人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可以通过它们而得到解释。
在马克思看来,公民权在形式上尽管表现为个体在国家中享有的一系列普遍而神圣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权利,为反映社会真实状况的人权所主宰,公民权屈从于人权。“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16)公民权与人权的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公民权服务于人权,通过前者作用的发挥,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更加稳固的基础,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目的得以实现。以财产权为例,财产权体现为“每个公民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的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财产权反映了人权的核心内涵,它表明,个人可以任意地、自私自利地、与他人无关地享用自己的财产,个人在财产上的这种自由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是,这种财产权不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领域,而且进入政治领域,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在财产私有这一经济基础之上,并把它具体落实到宪法、一般法律以及其他政治制度上。公民权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从而成为保护和再生私有财产权的政治手段。作为结果,如果说传统国家通过领主、等级、宗教以及同业公会等形式将个体整合进国家的话,现代国家则倒转了这种关系,它使“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17)。
在确立了公民权与人权的位序之后,马克思转而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表象上看,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犹太人的社会、基督徒的社会、清教徒的社会、商人的社会、短工的社会、土地占有者的社会,它表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但从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做生意”的社会、“金钱”的社会,归根结底,是“利己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倒转了金钱与政治、人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以前文刚刚论述的犹太人问题为例,犹太人经济富足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金钱势力同政治权力之间的矛盾,是前者征服后者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形与启蒙政治的观念追求从而是背道而驰的,即在观念上,启蒙思想家追求政治凌驾于金钱之上,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前者是后者的奴隶。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决定了人权和公民权的本质,即人权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公民权作为人类对于理想生存境况的追求,不但没有得到兑现,反而成为人权运作的外部支撑。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18)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权利反映的无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在做生意、金钱和利己主义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围绕利己主义而展开的金钱和贸易关系。“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19)这种自由贸易、自由买卖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私有产权尽管在前现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获得其“最完备的表现”。因为它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生活和政治关系都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对《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规定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四种人权进行了分析,认为财产权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其余三种人权的基础。财产权体现为个体可以任意地、不受他人干涉地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反映在其余三种人权上,自由相当大一部分的内容就体现在个人可以任意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上,平等则进一步将这种权利的范围扩大,使所有社会个体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同时,保障私有财产的安全也构成了安全权的最主要内容。
但问题在于,这种以财产私有和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在创造“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集中、还要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异化”。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它体现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与自己的类本质异化等方面。关于劳动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精彩的论述:“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20)人与自己的类本质异化则体现在人的类存在与现实存在之间的颠倒关系上。按照人的类存在要求,劳动对象、劳动产品以及人所创造的社会关系都应当是人维持自己类生活的手段,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类生活反而成为劳动对象、劳动结果和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手段。由此形成的结果是:“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类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1)由此形成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异化的社会。
较之于西方思想界有关公民权和人权的理解,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显示出明显的阶级性特征。在西方,不论是人权还是公民权,都被看作是“解放”的手段,公民权和人权都被看作高于政府而存在,政府有保护它们的义务,一旦违背这一宗旨,人民便有权改变它。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和《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等文献那里。比如,《独立宣言》开篇便对这一点进行了明确:“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有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者废除它。”(22)《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也指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23)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权和公民权与其说是解放的手段,不如说是将个体置于资本主义枷锁中的主要推手。人权就是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做生意、谋取金钱和利己主义的权利,公民权不过是屈从和服务于人权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两种权利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异化、阶级对立以及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等。总之,在西方学术界,人权和公民权被当作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自由屏障,而在马克思那里,人权和公民权被当作是维护资产阶级剥削的工具,后者的观点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性。
反映在现代史观上,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论述表明了他对于这一问题的两点看法:首先,公民权是维护人权的手段,两者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从表面上看,公民权与人权的分立确立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关系,国家毫无例外地服务于所有公民,人们普遍而平等地享有公民权。但那只是一种表象,公民权实际上服务于人权的需要,从现代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而言,人权和公民权又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以自由为例,马克思指出:“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24)其次,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人权和公民权是导致社会异化的主要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财产、安全等人权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服务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目的。但是,这种人权在促使资产阶级创造出比以前任何世代都要多、都要大的生产力的同时,却同时也使社会异化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严重、都要集中。从这一角度而言,人权、公民权不仅不是如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使人类遭受奴役的原因。人权与公民权的这种性质促使马克思思考如何超越它们,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
三、人权和公民权的终结
在马克思看来,催生人权和公民权的政治解放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它只不过是迈向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脚印和一个步骤。随着这一步骤的完成,政治领域中的类生活方式被系统地构想出来,并在社会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于,体现人们以类生活方式存在的公民权被置于人权之下,公民权成为服务于人权的手段,最终成为实现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目标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权不仅没有带来人类解放的结果,反而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异化。鉴于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25)要使个人真正复归于自身,使人类真正生活在没有异化的类本质状态下,人类解放的历程就必须再向前迈进一步——从“政治解放”迈向“人的解放”。
由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的解放呢?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前提。前文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表现在“做生意”、“金钱”、“利己主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本质是由于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造成的。因此,如果一个社会消除了私有制的存在基础,从而消除了做生意、金钱、利己主义的存在基础,那么,服务于它的人权也将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使社会真正成为自由、平等和安全的社会。这种社会也是公民权所承诺的理想社会,人权与公民权从而趋于一致。到那一时期,由政治解放所催生的“公民”与“私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差别将会消失,公民将复归于个体,个体将在自己的意识、经验、劳动和社会关系中以“类本质”的方式存在。随着公民权与人权之间差异的消失,它们也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人的解放”才告完成。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6)
我们可以再一次以犹太人为例来说明人的解放问题。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在犹太人身上和宗教维度上的体现,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还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家族、性别等各个方面。因此,不是犹太人的宗教造成了他们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造成了他们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产生了区分于他人的犹太人,而且产生了犹太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与所有其他问题一样,都根源于利己主义,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就这一意义而言,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不可能通过废除犹太教以及与之对应的基督教而得到解决,必须反过来,从产生犹太教的经济基础着手才能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也就是说,宗教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废除那需要依靠宗教来幻想的环境。马克思指出:“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做生意的前提,从而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27)如果社会不再催生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工人、资本家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那么,所有这些标志社会异化的范畴就将变得没有价值,人们就会从形形色色的社会异化中得到解放。
问题在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基础的私有制和利己主义如何才能被废除?这一问题耗费了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从无产阶级所经受的深重苦难中,马克思看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动力来源,并提出了实现这一解放的方案,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最终过渡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8)的共产主义社会。反映在历史维度上,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为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方案提供了现实范本。相对以前所有的政权而言,巴黎公社不是一次简单的政权转移,而是一次政权性质的根本改变。以前,“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29)但巴黎公社却是要从根本上废除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建立使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政权。公社不但要求在形式上用共和国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在性质上用“社会共和国”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马克思说道:“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30)
从与西方学术界有关人权和公民权观念比较的角度而言,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历史走向的观点体现出明显的对立性和历史性特点。所谓对立性,即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公民权的重要性将日益降低,人权的重要性则将日益凸显,公民权将日益融合于人权当中。例如,文森特认为,随着过去20多年全球化、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等彼此交织浪潮的发展,表示人类普遍性含义的人权概念将取代以特定成员身份为基础的公民权而成为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词汇(31)。索伊萨尔认为:“在战后时期,一种新的、更加普遍的公民身份概念已经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它的组织和正当原则建立在普遍个人身份的基础上,而不是以国家归属原则作为基础。”(32)福克斯也认为:“人权的语言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尊重个人的原则下,挑战国家对于公民具有至高无上主权,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无权干预的理念。”(33)从历史性的角度而言,鉴于民族国家的恒在性和世界差异的持久性,所有这些作者都没有预测过公民权和人权的消亡,相反,它们被看作是在差异和冲突的政治环境中保护个人的有效手段。马克思的关注点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而且侧重于人权和公民权的阶级分析。因此,在他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利己主义基础的消失,人权将从原来服务于它们的工具转变成促进个人自由的手段,人权从而将与公民权所承诺的类生活重合在一起,使后者不再处于虚幻的状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经由人权和公民权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对立关系和异化状态的消失,两者的差异也将消失,人权和公民权从而不再具有存在的理由。
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将走向终结的观点反映了其对于现代社会归宿的看法。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人权是服务于利己主义追求的手段,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公民权表面上赋予人们普遍平等的权利,但它只是“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34)。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异化形成了“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社会阶级、等级或者领域就是无产阶级。它的出现不仅表明“人的完全丧失”,而且表明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35)。从这一角度而言,无产阶级揭示自己存在的秘密,也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制度的秘密,无产阶级追求自身的解放,也就是追求整个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运动开启了超越特殊利益和权利的“世界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权、公民权等标志资产阶级法权和无视社会个体阶级差别、能力差别的权利范畴将逐步趋于消失,社会最终将“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而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6)。
由此可见,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观点既体现出与西方学术界的显著差异,又成为理解其现代史观的基本视角。从马克思关于人权和公民权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权、公民权既不是像大部分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也不是永远存在的,属于普世价值的范畴。相反,人权和公民权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们不仅反映了现代社会中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表象,而且遮蔽了彼此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追求的本质。从它们对现代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而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它们不仅不是人类解放的手段,而且沦为促进社会异化的推手。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加剧必将催生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将从根本上结束现代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使所有社会个体回归自己的类本质生活。伴随着这一生活方式的回归,公民权和人权也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这些基本观点表明,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思想不仅深刻揭穿了西方学术界或者政界制造的各种人权和公民权迷雾,而且廓清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就这一意义而言,理解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观点不可谓不重要。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9-17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1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2-183、183页。
(11)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41页。
(12)布赖恩·特纳(编):《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0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3、17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4-18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3-9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22)转引自格奥尔格·耶里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现代宪法史论》,李锦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页。
(23)转引自格奥尔格·耶里内克:《〈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现代宪法史论》,李锦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29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58-59页。
(31)Andrew Vincent,“Particularism,Human Rights and the Transnational Challenge”,in Wayne Hudson and Steven Slaughter(ed.),Globalisation and Citizenship:The Transnational Challeng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p.113-114.
(32)Yasemin Soysal,Limits of Citizenship,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
(33)Keith Faulks,Citizenship,London an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0,p.114.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6页。
标签:公民权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犹太民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