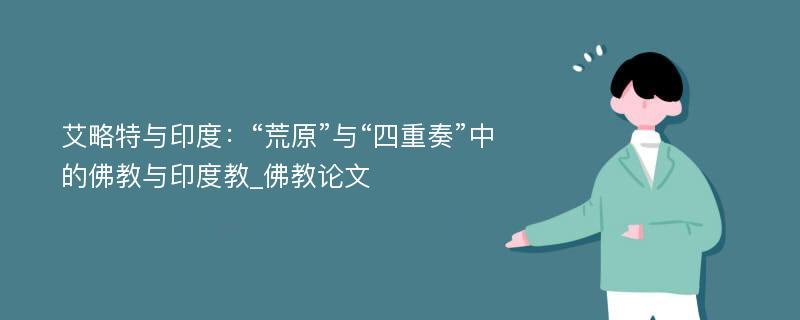
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教论文,艾略特论文,佛教论文,印度论文,荒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1-0039-09
根据斯蒂芬·斯奔德回忆,艾略特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说,写作《荒原》的时候,他曾经认真考虑想成为一个佛教徒。(Spender:20)这话可能有一定根据,因为《荒原》中充满了佛教经典的回响,第三部分“火戒”就是西方禁欲主义与东方禁欲主义结合的结果,最后一部分“雷霆的话”使用了佛教经典《奥义书》的结尾:重复了三遍的“平安、平安、平安”,艾略特说,是“一种超越理解的平安”。(Eliot,1969:80)《四个四重奏》也有基督教思想和印度教思想并置的情况,第三首《干塞尔维吉斯》就来自印度教经典《摩阿婆罗多》中的《福者之歌》,印度学者斯瑞说,其中一段几乎就是《福者之歌》第八章第五节的“译文”。(Sri:14)那么,艾略特与印度思想的关系到底如何?印度思想对艾略特到底有多么大的影响?
艾略特与印度的关系也许不算是一个未开垦领域。由于与印度有关,它曾经吸引了许多印度学者的关注。除了上面提到的斯瑞,还有《艾略特与印度哲学》的作者辛格和《艾略特的印度思想》的作者戈什等等。美国学者克利奥·克恩斯也写了一本《艾略特与印度学传统》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艾略特继承印度思想的事实的认识,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激发了我们对这个问题作更多的思考。比如,如果说艾略特的思想中融入了许多印度思想的成分,那么他对印度的认识从头到尾是一致的吗?他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影响他对印度的兴趣?印度教和佛教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几个问题的答案。
一、神秘感:初识东方和印度
在艾略特成长的年代,东方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到过印度和亚洲,多数人只是道听途说,或者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到一鳞半爪。东方是一个遥远、神秘的“他者”。在中学时代,艾略特喜欢阅读吉卜林的小说《吉姆》和菲兹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从吉卜林那里,艾略特了解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动物植物,地理特征。可以说,印度只是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地方,富有异域文化所具有的强烈吸引力。在史密斯学院,艾略特曾经创作过两篇故事,发表在校报上。一篇叫《鲸鱼的故事》,另一篇叫《做了国王的人》。前者是航海冒险的故事,与梅尔维尔的小说情节类似。后者有明显的吉卜林的痕迹,连题目都让人想起吉卜林。故事讲述了一次异域冒险的奇特经历。一个欧洲人(Macgruder)因海难而漂流到一个小岛,这里的部落以为他是上天派来的使者,而拥戴他为国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土著人发现他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救世主。上当受骗的部落决定惩罚这个冒牌货,最后他被迫逃离。(Sri:8)这样的故事情节不能不使人想起吉卜林的几乎同名短篇小说《想做国王的人》。艾略特的故事背景虽然是锡兰(Ceylon),但是与吉卜林的卡菲尔斯坦(Kafiristan),即阿富汗东北的偏远山区相差无几。这里的人们贫穷、无知、愚昧、落后、迷信、野蛮,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描述和报告的印度没有多少差别。可以说,这只是艾略特对东方的初步认识,并且这种初步认识还受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进入哈佛大学之后,艾略特对印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一次他更加侧重于思想层面和宗教层面的了解。艾略特在大学的专业为哲学和文学,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授中有好几位对东方哲学感兴趣,包括白璧德、兰曼、伍兹等等。在研究生阶段,艾略特开始选修梵文和兰曼开设的印度语文学,随后在第二年他又选修了伍兹开设的印度哲学,同时他还选修了一位日本教授(Masaharu Anesaki)开设的佛教课程。(Ackroyd:47)在这些课程中,他接触到了《福者之歌》等佛教和印度教经典,也正是在此时艾略特阅读了对他影响甚大的佛教读本:亨利·克拉克·沃伦主编的《佛教译本》。其中佛主的布道文《火诫》后来被用到了《荒原》之中。艾略特回忆说,他在哈佛的这段时光里对印度哲学和佛教的专研,使他产生了一种“具有启迪意义的神秘感觉”。(Eliot,1934:43)这时出版的“哈佛东方经典系列”丛书也说明佛教和东方对美国学术界的重要性,根据彼德·阿克罗依德的说法,这些哈佛教授对印度思想的兴趣具有一个特别的用意:即认为美国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无法在现代的基督教中找到西方问题的答案,而只能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宗教哲学中去寻找。而艾略特对印度和佛教的兴趣显然是在仿效他的哈佛前辈白璧德和莫尔。(Ackroyd:47)
二、幻灭:寻求拯救的良方
虽然艾略特否认《荒原》表现了“一代人的幻灭”,但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样的认识。(Eliot,1932:386)在《荒原》中,我们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的精神状况:颓废、绝望、精神支柱的崩塌。人们丧失了灵魂,丧失了信仰和精神追求。他们来去匆匆,犹如行尸走肉,像一个个幽灵。艾略特瞭望伦敦桥上的上班族,感叹道:“我没有想到死亡夺取了如此多人的生命”。伦敦被比喻为但丁的地狱。以这种心情和目光扫视欧洲大陆,艾略特看到的是一片荒原,“一堆破碎的图像”:这里只有石块,没有水;只有干旱,没有植物生长;这是一片不毛之地,大地已经死亡。这就是艾略特为20年代的欧洲描绘的一幅图景:一片精神荒漠。(Southam:81)在这样一个情境中,诗人作为一个灵视者和预言家,扮演了一个悲天悯人的角色。他的心灵比其他人更敏感,目光比其他人更锐利。他看到了他人看不到的颓败,感觉到他人感觉不到的痛苦,他因此而备受煎熬。在见证苦难的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付灵丹妙药,来医治欧洲人精神上的创伤,以拯救这片古老的大地,使之重新恢复其活力和生机。正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中,艾略特找到了印度和佛教。
欧洲文明的崩溃,“欧洲人感情和精神上的枯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感觉。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说,“文明陷入如此血腥和黑暗的深渊,是对整个悠久历史的抛弃,我们一直以为这个历史在进步,不管有多少坎坷,而现在必须接受目前的一切,将之视为这个历史的目标和意义,这太可悲了,无以言表。”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我曾经产生奇怪的幻想,觉得伦敦是一个虚幻之地。我在幻象中看见桥梁崩塌沉没,整个城市像早晨的雾气一样瞬间消失。”(Coote:9)为什么几千年的欧洲文明会导致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什么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科学、民主、进步等理想会导致战争、杀戮、强权、贪婪?如果以基督教和启蒙思想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那么与之不同的其他文明和宗教是否蕴含着恢复活力的灵丹妙药呢?
这样的思路不仅存在于詹姆士、罗素、白璧德等哲学家当中,也同样存在于艾略特、庞德、叶芝等现代诗人当中。我们应该记住,庞德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恰恰将他引向了东方,引向了中国诗歌和哲学。叶芝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将他引向了非西方的思想体系,即神秘教和他自己创造的《幻象》象征体系。并且,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局限于艾略特那一代人,在整个20世纪,西方的知识分子在重复着类似的思维路径。美国60年代的诗人金斯堡、雷克斯洛斯、斯奈德等对东方的兴趣也正是出于对西方工业化文明的失望。(钟玲:10)如果你自己的文明使你感到失望,那么你就有可能向其他文明去吸取营养。这也许就是艾略特走向印度和佛教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冲动。
三、人类学:东西方智慧的融合
在《荒原》的原注中,艾略特承认这首诗的题目、结构和象征体系都来自杰希·韦斯顿(Jessie L.Weston)的《从仪式到传奇》。韦斯顿探讨了基督教圣杯传奇的来源,认为它与古代渔王的故事密切相关:即荒原之荒,根源在于渔王身体之“荒”。要拯救荒原,必须寻找圣杯,医治渔王的疾病,使他从衰老和性无能中振作起来。艾略特还承认,他受到另一部人类学著作的重大影响,即弗雷泽的《金枝》:“任何熟悉这些著作的人会立刻识别诗中所提到的生殖仪式。”(Eliot,1969:76)在艾略特时代,人类学不仅是一门异常活跃的学问,而且代表着一种精神:即宽容、开放和平等的学术精神。人类学往往将不同的文化传统放置在一起,对它们进行平行研究,比较它们的异同,以及它们的传承关系。在以上两位人类学家的著作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基督教与其它东方宗教仪式的平行比较。艾略特在《荒原》中就是继承了这种人类学精神,以及人类学对东方的兴趣。
在圣杯传奇中,骑士寻找圣杯、以恢复大地活力和生机的故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故事。韦斯顿将圣杯传奇的源头追溯到渔王的故事,然后又暗示更早的源头是印度教经典《吠陀经》。在这部印度教经典中,王子(Bhagirath)为拯救他的家族和国家,历尽千辛万苦,登上喜马拉雅山,寻找恒河女神,以释放河水、拯救干涸大地的故事与艾略特的渔王的故事有诸多相似之处。格洛弗·史密斯认为,《吠陀经》中的这个故事通过韦斯顿的《从仪式到传奇》进入了艾略特的《荒原》。(Smith:90)印度学者辛格甚至认为,这个故事是“圣杯传奇的印度版”。(Singh:23)
艾略特的“荒原”不仅是西方衰落的象征,也是生动的现实:泰晤士河边的白骨在风中歌唱,似乎显露出死者狰狞的笑容。河上漂浮着空酒瓶、三明治的包装纸、丢弃的硬纸盒、烟头等垃圾,仿佛这是一个被人类抛弃的地方。老鼠在河岸的尸骨中出没,发出沙沙的声响。建筑物倾倒,“耶路撒冷、雅典、亚历山大、/维也纳、伦敦,/不真实。”(Eliot,1969:73)如果艾略特这片荒原有一个“渔王”,那么他应该是耶稣。按此推理,重新寻回“死去”的耶稣,就是拯救荒原的关键。然而,《荒原》并没有这样推理,而是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印度佛教:“给与、同情、抑制”三字箴言来自佛教经典《奥义书》中“雷霆”的故事,在此它被视为拯救人类的最高智慧。
可以说,艾略特的救世秘方是一个东西方智慧的混合物,一种东西方珠联璧合的古老良方。《荒原》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思想基石是一个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思想体系。用史密斯的话来说,“这个精神追求部分属于西方传统,部分属于东方传统。”(Smith:93)艾略特此时还不是基督徒,对于他来说,诗歌与信仰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创作的时候,他所寻找的是比喻,是可以表达他的思想的手段。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或者生殖崇拜仪式,只要能够表达“荒原”的意念,他都会将它为我所用。
四、欲望:东西方禁欲主义的并置
在《荒原》中,欲望是一个重要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西方文明的问题的根源。在诗歌的400余行中,我们多次见证欲望的火焰熊熊燃烧,以及在火焰中燃烧的男男女女:在德国阿尔卑斯山度假的贵族男女,在伦敦家中百无聊赖的中产阶级夫妻,深受性问题和生育问题困扰的下层女性,像野兽一样到妓院寻欢作乐的斯温尼,偷欢交媾的银行职员和女打字员,邀请同志到宾馆过夜的同性恋商人等等,而这些又与神话中夜莺遭到强奸的故事,以及瓦格纳歌剧中不该发生的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可以说《荒原》是欲望的众生相。作为诗歌的叙事者,诗人也是这些现象的见证者。他自比希腊神话中的先知铁瑞西斯,既做过男人,又做过女人,对欲望的两面都有过体验。然而他见证越多,他就越痛苦。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女性的形象常常激起“不快或恐惧”。(Ackroyd:44)美国学者米勒将《荒原》中关于女打字员的描写称为“反女性主义的段落”。(Miller:88)
欲望在东方和西方的宗教中都是邪恶的源泉,因此禁欲主义是东西方宗教的共同特征。由于欲望总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因此女性总是禁欲主义的受害者。女性被视为“祸水”,洪水猛兽。在基督教和西方传统中,夏娃和潘多拉的故事都暗示女性是万恶之源。(米利特:60—61)艾略特显然意识到禁欲的重要性,在《荒原》中,他搬出了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代表之作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希望能够浇灭这场欲望大火,同时他还搬出了佛主的《火诫》:在被欲望之火重重围困的情况下,他请求上帝将他从火中救出。“燃烧燃烧燃烧燃烧/哦上帝你把我拔出来/哦上帝你拔/燃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最后一句还没说完,他已经在烈火中殒灭。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基督教和佛教的并置,并且这种并置是一种有意的安排。艾略特在《荒原》的原注中说,“东西方禁欲主义的两位代表的结合,形成了这一部分的高潮,这并不是一个巧合。”(Eliot,1969:79)
艾略特这种平等地对待东西方思想传统的态度非常有趣,然而它并没有持续多久。1927年他在伦敦某教堂接受了洗礼,之后声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成员”。(Eliot,1928:79)伴随着这一保守主义的转向,艾略特对东方,及其他宗教文化传统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开始批评前辈诗人阿诺德用诗歌代替宗教的计划,批评他的哈佛老师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转而极力追捧英国17世纪基督教主教郎斯洛·安德鲁斯的宗教思想。他抛弃了先前对东方宗教和思想传统的人文主义关切和人类学兴趣,对这些宗教和思想传统少了一份包容和欣赏。在《追逐异教神》一书中,艾略特显然将基督教视为正宗,而其他宗教和思想则变为“异教神”的追逐者。他的思维中引入了一种二元对立模式,并且在这个二元对立模式中,主与次、正与邪、光明与黑暗、优越与落后的等级秩序异常突出。这一点我们将在《四个四重奏》中清楚地看到。
五、玫瑰花园:旋转世界的中心
《四个四重奏》是围绕几个宗教主题展开的一场哲学思辨。在诗中,抒情与沉思交织,感性与理性重叠:“时间现在与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未来之中,/而时间未来也包含在时间过去里。”(Eliot,1969:171)《四个四重奏》的开篇《烧毁的诺顿》让思绪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记忆中那个特殊的时刻:心灵豁然开朗,从而感觉到形而上的欢乐。欲望和记忆交融,显示出一个永恒世界。记忆中的玫瑰花园,百鸟歌唱,鲜花盛开。干涸的池塘在太阳光的照耀中奇迹般地充满的清水,碧波荡漾,水中还生长“莲花”。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艾略特在花园中安排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莲花”呢?面对那无以言表的神秘体验,语言的表现力,即使是诗歌语言,都显得苍白。这种体验的强度和深度超出了凡人的感知极限,人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无法确认它的真实性。这个无以言表的“真实”只能用喻说性语言才能表达,也许这就是神秘东方的“莲花”出现的原因。
《四个四重奏》的开篇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幻象。用诗歌语言来说,它是旋转世界的中心,或“旋转世界的静止点”。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它既没有运动,也没有停止运动;既不是肉体,也不是没有肉体等等,诗歌就是对这个“光的世界的悖论性体验”。(Moody:144)艾略特说它像一只“中国花瓶”,永远旋转,但又永远静止。在这里,人们又想起了佛教:佛教在描述“梵”时也是用一系列悖论:“既离我们很远,也离我们很近,既在这个世界中,又不在这个世界”等等。(Singh:29)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意象,不管是佛教的莲花,还是中国的花瓶,对这个神秘体验的描写似乎具有强大的表现力。不是因为它们比英语更加优越,而是因为它们产生的陌生化效果似乎超越了英语的程序化的思维和想象,从而得以让永恒的神秘感冲击读者的想象力,达到希望产生的效果。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穆迪说:“超越语言是《四个四重奏》的根本。”(Moody:147)
也就是说,虽然东方在艾略特的想象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不是因为它是艾略特信仰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它超越了西方的传统语言,超越了英语老套的、刻板的联想,从而能够起到激活思维的作用。在艾略特的思想中,东方充其量只是诗歌创作的一个语言资源。我们可以这样说,此时的艾略特延续了他前一阶段对印度哲学和东方的兴趣,但是这个兴趣已经与从前不同。他将会如何处理这个兴趣在他思想体系中的位置,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定位艾略特的信仰和哲学探索的方向。
六、轮回:合着四季的节拍
《四个四重奏》不是四首诗歌,而是一个相互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我们可以将这四首诗歌视为室内乐四个四重奏的四个乐章,可以将它们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也可以将它们视为气、土、水、火四大元素。如果我们仔细省视《烧毁的诺顿》和第二首《东科克》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发现:第一首写永恒,第二首写时间。两首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空气与土壤、天堂与人间、光明与黑暗的关系。东科克村位于英格兰南部,艾略特的曾祖父17世纪从这里移居美国。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少,数百年来保持着几乎同样的生活方式。生活就是一种重复,房屋倒了又建,村民死了又生,构成了一种人生的循环。用艾略特的话说,“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Eliot,1969:177)
四季更替、生死循环、艾略特的先祖离开英国去美国,而他现在又从美国回英国,这些都是循环往复的形象,类似于佛教的“轮回”。东科克村的人们曾经围着篝火跳舞,“相亲相爱,手挽手,臂连臂”,合着四季的节拍,“吃、喝、拉屎和死亡”。(Eliot,1969:178)这个篝火舞蹈仪式更加深了先前的循环意象。万物随时间而变化:人的生老和病死、植物的生长和枯萎、帝国的兴盛和衰亡、日子从白天到夜晚、季节从春天到冬天:人间没有永恒的生命,也没有永恒的荣耀。人生就像一个巨大的转轮,人们从最低点转到最高点,然后又从最高点跌落到最低点。辛格说,“《东科克》的土地就等同于羯磨……艾略特描绘了一幅完整的现世图景,其中的行为决定着行为的循环。”(Singh:66)
艾略特对人生的描述与佛教异常相似,他是否有意识这样做我们无法推断。不过,对艾略特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类学告诉我们,基督教和佛教,以及其他宗教在看待人生的方式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哲学家赫胥黎也曾经指出,在人类不同种族的原始神话中存在着一种“永在哲学”,这种“永在哲学”后来在世界几大宗教中都得到了发展,其主题包括时间与永恒、善与恶、拯救与永生、道成肉身、苦难修行等主题。在《永在哲学》一书中,赫胥黎在“印度的默祷僧人、伊斯兰教的苏菲派信徒、中世纪的天主教神秘主义者”以及基督教新教、佛教、禅宗等宗教圣人的思想中进行来回比较,梳理主旨大意,揭示共同特征。(Huxley:14)虽然艾略特并不相信“永在哲学”,并且批评过赫胥黎的普世主义思想,但作为一种哲学原型,“永在哲学”反映了各种宗教的共通之处,从而也为我们揭示了艾略特与印度思想的契合。
七、苦海:人世间的缩影
《四个四重奏》第三首《干塞尔维吉斯》描写了大江和大海,同时也描写了与航行相关的渔民生活。“哪里是终了,渔民在浓雾退去时扬帆驶入风尾?”渔民一代又一代在海上作业,出海后又返航,也构成了一个循环。“我们得想象他们永远在往船外舀水,/扬帆和拉网。”(Eliot,1969:186)“航海”是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运动,它本身就是人生的一种隐喻。对于渔民来说,“航海”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对艾略特来说,航海就是人间生活的缩影。用斯瑞的话来说,“现世的不断变化的表象在此被想象为波涛汹涌的大海,被描写成恐惧和绝望的深不可测的流动。”(Sri:32)
在这里,艾略特的想象又一次与佛教相遇。对于佛教来说,人间就像大海,人们只不过是漂浮在大海上的落水者。他们迷失了方向,不知哪里是陆地,哪里是海岸。他们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经受着无尽的煎熬。佛教的箴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但是对人间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对迷失的人们的召唤。对于艾略特来说,在人生的苦海上,只需要“一路向前”,而不是“一路顺利”。到达彼岸的人们将不是启航时的人们。他所说的“此岸”和“彼岸”可能也是佛教中所说的“此岸”和“彼岸”。航海者的“一路向前”正是为了离开欲望的苦海,到达天堂的彼岸。
在诗歌中,大海并不寂静:波涛声、风声和浮漂发出的声音代表了人间痛苦的“哀号”。然而,它们也在“宣告”人类的希望:耶稣的降临,这可能也是佛教的“回头是岸”吧。在宣布耶稣降临之后,艾略特紧接着将讲述了佛教版的“道成肉身”故事,即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下凡,化身为克利须那,去劝说英雄阿朱那参战的故事。辛格向我们展示,《干塞尔维吉斯》第三部分有多个段落直接来自印度学者斯瓦梅(Purohit Swamy)翻译的《福者之歌》,几乎“未作任何改动”。(Singh:63—65)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艾略特为什么要将耶稣降临与克利须那下凡进行并置呢?这对于我们理解印度对艾略特的影响提供了什么样的暗示呢?
应该说,克里须那的主要观点是:行动与放弃行动都是为了脱离人生的循环,对俗人来说,不必去考虑行动的后果,只需要去做应该做的事情。他的另一观点是:人在死时想到什么,来世他将变成什么,即他那时想到哪一个生命层次,来世就将进入那一个生命层次。史密斯评论道,艾略特的目的是想证明:过去、现在、将来同时存在,但是只有现在能够被体验到。印度教的故事使他得以强调现时生活和行动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影响到自由意志在将来的实施,而且决定着人生全部的德行,羯磨,产生的后果是天堂还是地狱。”(Smith:281—82)
八、玫瑰与火焰:超越历史和时间
如果《四个四重奏》的中间两首形象地展现了人间生活,那么最后一首《小吉丁》将实现对人间生活的“超越”。小吉丁是英格兰的一个小地方,但它的意义并不平凡。17世纪曾有一个虔诚宗教团体,通过苦行和修炼,超越了当时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实现了与永恒的交汇。因此,对于艾略特来说,小吉丁是一个“祷告曾经生效的地方”。(Eliot,1969:192)在他到此一游的隆冬季节,树上的雪花突然神秘地变成了鲜花。小吉丁的故事对艾略特来说是一个极富启示意义的寓言,它包含了指引人生冲出时间牢笼、奔向精神自由的教诲。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一场人类大灾难之后,通过虔诚和信仰来超越历史的是非,从而实现灵魂与永恒的交汇,不仅是17世纪的宗教团体的成功经验,而且也是艾略特所追求的目标。
“超越”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操练,它既是超越欲望和利益,但也不是完全与利益分离,它是通过记忆来达到灵魂的自由。艾略特说,它不是爱,而是“漠然”,是一种超出了欲望的“大爱”。佛教在修行方面也讲究一种超出人间欲望的境界,佛教的“四大皆空”与艾略特的“漠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这是否暗示艾略特又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呢?那倒未必。也许这就是赫胥黎所说的“永在哲学”吧:在各种宗教中,超越自我都是修炼的目标。“自我越多,上帝越少。神圣永恒和充实生活的获得,依赖于有意识地放弃欲望和私利,放弃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感情、愿望和行为,这些构成了不完整和使人分离的生活。”赫氏还认为,“苦行和有意识的自我泯灭在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世界的其他大小宗教的经典著作中都同样被赋予了不可妥协的地位。”(Huxley:106—07)
可以说,在《小吉丁》中,艾略特汲取思想养分的源泉是基督教。小吉丁的圣徒们的生活和言行为艾略特的“超越”提供了一种榜样、一种路径。艾略特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基督教圣徒的事迹充满了好奇,这些包括圣塞巴斯蒂安、圣那喀索斯、圣特利莎、圣十字约翰等。圣那喀索斯爱上了射进他身体的利箭;圣奥古斯丁请求上帝将他从火焰中拔出来;圣十字约翰的“灵魂的黑夜”和“否定的道路”都曾激发过艾略特的诗歌想象,使他兴奋不已。用默利的话说,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但对神秘主义有一种嗜好”。(Murry:2—3)在《小吉丁》中,艾略特的榜样是圣徒尼科拉斯·费拉和修女诺维奇的朱丽安。前者通过他的虔诚促成了“时间与永恒的交汇”,后者在《圣爱的启示》中主张“净化动机”,两者都成为艾略特在《小吉丁》中实现“超越”的基本手段。在《四个四重奏》的最后,在它的高潮,佛教和东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的玫瑰和火焰,以及基督教思想对整个诗歌意义的主导和垄断。
九、结尾:戴维的启示
在《基督教社会奏议》中,艾略特写道,“基督教处于腐朽状态时可以从东方学到许多东西。”(Eliot,1939:142)他承认,人文主义学者在促使人们意识到基督教需要理解和审视东方思想的必要性方面做出了贡献,认为“未来的基督教哲学不可能忽视东方思想”。但是,艾略特决不是一个普世主义者,也绝没有将基督教与东方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在同一本书中,他补充道,“没有基督教,智慧是一回事;有了它,智慧就是另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基督教,智慧将变成愚蠢,而且智慧决不能代替信仰。”正如默利指出,在《四个四重奏》的后两首中,“艾略特在使用东方材料时表现出更多的谨慎,在必要时还将印度教和佛教的哲学与经验转化为他起初的基督教意识。”(Murry:152)
英国批评家兼诗人唐纳德·戴维曾经撰文评论道,我们应该将《四个四重奏》视为一个整体,视为追求“永恒”的四个连续的步骤、一个完整的思想构架。根据他的观点,《四个四重奏》第一首是“天堂”意识的觉醒,第二首是“人间”生活的写照。这两首形成了天堂与人间的对立,同时也形成了永恒与时间、空气与土壤、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四个四重奏》的后两首则代表了艾略特为解决这个对立而寻求答案的尝试。不过第三首只是一个虚假的答案,第四首才是一个真正的答案。(Davie:198—200)戴维暗示,《干塞尔维吉斯》中的印度教思想仅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解决问题的真理包含在《小吉丁》的基督教思想中。
虽然戴维的观点听上去像是西方中心主义或基督教中心主义的结果,但是它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的作为。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足够地重视戴维的观点,因此也就没有对《四个四重奏》中的基督教中心主义产生足够的认识。在这里,我们重读戴维六十年前的一篇论文,不是为了赞扬他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而是为他揭示了艾略特思想中的这一倾向,而未意识到其中的问题而感到惋惜。作为结尾,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艾略特作为一名基督徒和西方传统的继承人,其思想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特征可以理解,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必须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并与之划清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