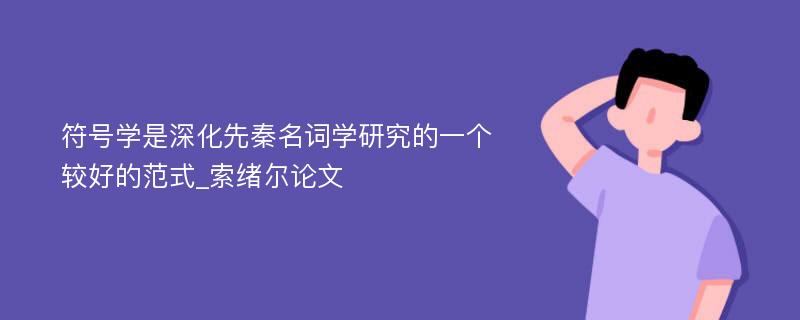
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范式论文,先秦论文,名辩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3)03-0044-06
“范式”这个术语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库恩(Kuhn,Th.)从语言学里借用来的,原意是语法中表示词形的变化规则,如名词变格、动词人称变化等,由此可以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序中给“范式”下的定义是:“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4,“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1]9。
20世纪初,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译介到我国后,当时的一大批名辩学研究者这一“实践共同体”就把它作为范式来研究先秦时期的名辩学。在这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进入新的世纪后,怎样深化先秦名辩学的研究是摆在当前中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研究我国先秦名辩学的得与失
我国先秦名辩学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统形式逻辑被译介到中国,这种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介绍到我国以后,立刻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兴趣,很多学者开始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这方面的思想资源。孙诒让第一个认识到《墨经》诸篇中有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和培根的归纳法。受孙诒让的启发,梁启超开启了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诠释《墨经》中名辩学的先河,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框架诠释《墨经》中有关名、辩的思想资料。梁启超之后,胡适、章太炎、章士钊、谭戒甫、沈有鼎、詹剑峰等学者继续沿用这种范式研究先秦名辩学,他们通过发掘先秦思想史上的资料,然后比照传统形式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辩的理论体系整理史料。从而把先秦诸子著作中的“名”解释成为概念;“辞”解释成为判断;“说”解释成为推理;“辩”解释成为论辩。通过这些学者的努力,“逻辑”思想资料的发掘更为丰富了,比较研究的视野也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春天,一大批学者投入到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成长起来了一批知名学者,出版、发表了大量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尤其是1989年至199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和与之配套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是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这一成果集中了当时20多位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的智慧,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种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诠释中国先秦时期名辩学的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有力地推动了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深入,极大地提高了名辩学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扩大了其影响。
这种研究范式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从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一出版,就有学者提出异议。1925年吴熙在《墨子的名学》一文中指出:“墨子的名学,在形式和理论二方面,都和西人的逻辑学完全相反,如果不悉心研究,强合西人的逻辑学,便要弄得十分的‘支离破碎’的。”[2]439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这种研究范式的批评更为激烈。刘培育先生曾指出:“……但以传统逻辑体系为范本去剪裁与建构中国名辩学体系,却发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1)扭曲了名辩学体系的原貌,或使其原貌变得模糊不清。(2)为适应传统逻辑体系的内容,而造成对名辩学史料的误解和强解。”[3]13曾祥云先生说:“我们看到,在我国近现代的名辩逻辑化过程中,研究者在‘吾国固有’这样一种狭隘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下,一味热衷于以西方逻辑诠释名辩、比附名辩。”[4]程仲棠先生进一步指出:“把墨辩过度诠释为‘逻辑学’,就无异于伪造历史。”[5]这些批评无疑是切中要害的,的确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参照系,对中国古代名辩学进行比较研究,造成了比附之风盛行和对史料的“过度诠释”。
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比较研究这种方法的问题呢,还是参照范式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比较研究方法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比较研究中选择的参照范式不恰当。就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特点来看,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符和它表达的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从汉字中抽象出一些符号做逻辑常项或逻辑变项,因此就不能对语言进行形式刻画。从先秦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像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形式”,就名辩学原典自身来说,既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变项,也没有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推理形式的刻画,因此,用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研究范式诠释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就必然会出现牵强附会的现象。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想深化先秦名辩学的研究,开创中国名辩学研究的新局面,就要寻找新的参照范式。我们认为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二、符号学概观
符号学(Semiotics)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符号学方法是一种当代思维方法,也是一种语言分析方法。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D.1857—1913)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Peirce,C.S.1839—1934)是世上公认的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
(一)符号
在索绪尔看来,符号不是别的,而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所说的“能指”(signifier),指的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signified)是它所表达的概念。索绪尔把它们比作一张纸,思想(概念)是纸的正面,声音是纸的反面,它们永远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他还认为,这是语言符号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索绪尔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至于‘符号’,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满意,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去代替,日常用语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术语。”[6]102
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理论,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因而也就澄清了两千多年来对于“符号”一词的混乱解释。其实,符号就是一种关系。索绪尔所说的“能指”是指符号形式,亦即符号的形体;“所指”是指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曰“意义”。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亦即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二元关系。
在索绪尔提出符号二元关系理论的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皮尔士把符号看作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和符号解释(interpretant)之间的三元关系。他说:“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真实的或塑造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本身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可以用另一个我称之为‘解释’的符号去加以解释,以转达在此之前还不知道的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这样在任何一个符号、对象与解释者之间就存在一个三元关系。”[7]2在皮尔士看来,正是这种三元关系决定了符号过程(semiosis)的本质。
由于索绪尔和皮尔士关于符号的定义是各自在不同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差别。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我们认为,索绪尔的“能指”相当于皮尔士所说的“符号形体”,人们通常称之为“符形”;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大体上相当于皮尔士的“符号解释”,人们通常称之为“意义”或“讯息”。索绪尔和皮尔士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和“三元关系”学说,奠定了现代符号学坚实的理论基础。
皮尔士之后的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Morris,C.W.1901—1979)给符号下的定义是:“如果某个东西A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控制了指向某个目标的行为,而这种方式类似于(但不必等同于)另一个东西乃在它被观察到的情况下用以控制指向这个目标的行为的那种方式,那么,A就是一个符号①。”[8]9莫里斯有时也将符号称为“符号媒介物”(sign vehicle),莫里斯定义的一个特点就在于符号不仅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以及心灵体现者的解释相联系,而且与解释者的行为相联系。
从上面几个定义可以看出,“符号”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某种事物、某个现象,而是体现解释者的心灵与所对应的对象的一种关系。“符号”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一种心灵的现象,它在人的认知和交际行为过程中产生。“符号是用甲事物表征乙事物,并且通过甲事物来传达关于乙事物的讯息”[9]8。
(二)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
在符号学的发展历史上,莫里斯第一次明确地把符号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语形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目前,莫里斯关于符号学三个组成部分的学说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且成为符号学基础理论之一。
1.语形学研究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
1938年,莫里斯在《符号学一般原理》一书里是这样定义语形学的:“语形学研究‘符号相互间的形式关系’。”[8]2611946年,他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对这个定义又作了一些改进:“语形学研究符号的种种联合,而不考虑这些联合的意谓,也不考虑这些联合和它们在其出现的那种行为之间的关系。”[8]262
莫里斯关于语形学的思想很快得到美籍德裔哲学家卡尔纳普(Carnap,R.)的积极响应。卡尔纳普在1942年出版的《语义学导论》一书中更加清晰地表述说:“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也不考虑所指谓,而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从事(逻辑的)语形学的工作。”[8]261
莫里斯说语形学不研究符号的意谓和行为,只研究符号的种种联合;卡尔纳普也指出,语形学不考虑符号的使用者,也不考虑符号的所指谓,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都非常明确地把语形学和语义学、语用学严格地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斯所说的符号并不是指符号的整体,而仅仅指的是符形,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能指”;卡尔纳普所说的表达式也不是指表达式的整体,仅指表达式的形式,即表达式的“能指”。通过细细评味这两位哲学家的论述,我们就能够非常明确地体会到:语形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符号系统内的符号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
2.语义学研究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研究符号的指谓意义(不依赖于符号情境的意义)。
莫里斯在《符号学一般原理》一书里关于语义学的定义是这样的:“语义学研究‘符号和其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8]261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他对这个定义又作了一些修改:“语义学研究符号所具有的各种方式的意谓。”[8]262
卡尔纳普在《语义学导论》一书中更加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而只分析表达式和它们的所指谓,我们就是从事语义学领域内的工作。”[8]261
莫里斯所说的“意谓”和卡尔纳普所说的“所指谓”实际上就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也就是说语义学是研究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意指关系是“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的,更明确地说语义学所研究的符号的指谓意义是不依赖于符号情境的意义,这是它和语用学最显著的区别。
3.语用学研究符号情境中的意义。
莫里斯在《符号学一般原理》一书里对语用学的定义是:“语用学研究‘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8]261在《符号、语言和行为》一书中修改为:“语用学是符号学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在符号出现的行为中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8]262
卡尔纳普在《语义学导论》一书中进一步清晰地表述说:“如果在一个研究中明白地涉及了说话者,或者换一个更为普遍的说法,涉及了语言的使用者,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研究归入语用学的领域中……”[8]261
从这两位哲学家关于语用学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语用学所研究的符号的意义不同于语义学,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和符号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要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与效果”,这些内容就是人们所说的“符号情境”。
关于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三者之间的联系,瑞士逻辑学家鲍亨斯基(Bocbenski,J.)在其著作《当代思维方法》一书中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句法(语形)关系、语义关系、语用关系以一种特殊方式交织在一起,它们的基础是句法即语形关系。语用关系以语义关系和句法关系为前提,而语义关系则以句法关系为前提。一个无意义的词对于人类理解毫无用处,而为了具有意义,它必须同其他词具有某种关系。另一方面,句法(语形)关系则并不以语义关系和语用关系为前提,语义关系也可以在不涉及语用关系的情况下加以研究。即使对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语言,也可以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句法。例如,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简单的语言,其中只出现符号P和X,并且把P永远先于X作为一条句法规则;并不一定要知道P或X实际意谓着什么。
作为符号学的一个分支,语形学同语义学、语用学之间的区分是比较容易的。然而语义学和语用学之间的区分就比较困难了,它们研究的问题有些是相互交织的。究竟怎样明确地把语用学同语义学区别开来,英国语言学家利奇(Leech,G.)在《语义学》一书中作出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认为语义学和语用学虽然都研究意义,但是语义学研究的是“sense”(字义),是语言片段的抽象和字面的意义;语用学研究的是“force”(用意),是语言片段在特定场合中的意义。前者为:X的意思是Y;后者为:通过X,S的意思是Y。利奇还对意义的某种讨论是否属于语用学的范围,提出四条区分的标准:(1)是否考虑了发话人或受话人(言者或听者);(2)是否考虑了言者的意图或听者的解释;(3)是否考虑了语境;(4)是否考虑了通过使用语言或依靠使用语言而施行的那种行为或行动。他说:“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是肯定的,就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在讨论语用学。”[10]455
我国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把语言表达式分为四个层次:抽象语句、语句、话语、交际语境中的话语,与此相对应的表达式的意义也分为四个层次:抽象语句的意义——命题;语句的意义——命题态度;话语的意义——意谓;交际语境中的话语的意义——意思[11]16~20。
根据利奇的四条标准,我们就清楚知道只有“抽象语句的意义——命题”是语义学的研究对象,其他三个层次的意义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三种意义都考虑了语言的使用者和语境。
三、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从上面对符号学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相比,用符号学做范式研究我国先秦的名辩学有更多的优势。
传统形式逻辑的主要内容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三大部分。“概念”用索绪尔的话来说是符号的“所指”,也就是说在传统形式逻辑中根本没有考虑符号的“能指”,而先秦名辩学中的“名”恰恰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是语词符号。“判断”和“推理”主要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属于语形学的研究内容,遗憾的是先秦名辩学中根本没有涉及推理有效的问题,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语形学的内容。名辩学中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又根本没有研究语用推理的问题。与此相反,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都给予了充分的研究,据此我们认为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下面我们以“名”的符号性质和“譬”、“侔”、“援”、“推”、“止”五种论式为例来说明符号学范式的优越性。
(一)“名”是语词符号
用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研究范式,把“名”解释为“概念”,我们通过阅读分析名辩学的原典,就会感受到这样解释太牵强。
首先,我们看看《墨经》中关于名的论述。《墨经·小取》:“以名举实。”《经上》31说:“举,拟实也。”“拟”的含义就是摹拟,即按照事物的样子画下来就像原物那样。《易·系辞》:“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这和许慎说的象形字如出一辙,许慎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出,日月是也。”《经说上》32讲得更明白:“名若画虎。”即写“虎”字,就像画虎一样。显然“以名举实”、“名若画虎”中的“名”不是概念,而是符号。
其次,我们再看看《荀子》中关于“名”的定义:“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根据许慎《说文解字》:“期”有约定之义,“累”有附加之意。因此我们可以把荀子的定义理解为“名”是通过约定,附加在“实”上的符号。《荀子》另一段著名的论述进一步证明了“名”的符号性:“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和“实”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和事物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某个“实”用什么“名”来表达,某个“名”表示什么“实”,既没有自然的法则,也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符号和概念的区别在哪里?概念是反映事物属性的思维形式,是思维领域内的东西,是索绪尔所说的“所指”。符号则是符形和符义的结合体,用索绪尔的话来说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它们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不能分开的。先秦文献中的“名”既可指文字符号,也可指声音符号。如果指文字符号,它就是字形和字义的结合体,如果是声音符号,它就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
(二)“譬”、“侔”、“援”、“推”、“止”五种论式都是语用推理
1.“譬”式推论。
惠施给“譬”下的定义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说苑·善说》)
《墨经》的定义是:“辟(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小取》)
《墨辩》的“譬”是作为一种推论形式提出来的。“举他物以明之”的“明”指明类。乙物与甲物本质(共性)相同,举乙物作譬,达到获得甲物与乙物为同类的认识的目的。涉及到论辩双方的背景知识,显然具有语用推理的性质。
例如《墨子·耕柱》说:“曰: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不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
儿童骑竹马,是一种白费力气,没有用处的儿戏,这和大国攻小国的“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墨子·鲁问》)在本质上相同,因而大国攻小国和“童子之为马”为同类,它们都是劳而无功的儿戏。
2.“侔”式推论。
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小取》)
“比”,“其本义谓相亲密也”(《说文》段注)。比的引申义有类等、齐等、同等。据此,“比辞”可以理解为两个命题相类、相等或相同。“比辞而俱行”就是比较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命题,并以其相类、相等或相同为根据而进行的推演,这也正是“侔”式推理的特征。这种推理涉及到上下文,是典型的语用推理。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
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
获,人也;爱获,爱人也。
臧,人也,爱臧,爱人也。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句话应译为“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是骑马”。这一推理的前提与结论均为直言命题,结论的主、谓项是由在前提中主、谓项上附加相同语词而构成的复杂语词,表达这些复杂语词的是由若干词构成的词组(“乘白马”与“乘马”均为动宾词组),而不是句子。这些实例表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齐等之处不在于具体内容的无差别,而是它们的主、谓项之间均具有属种关系,即主项包含于谓项。就这点而言,作为前提与结论之间的两个命题可视为类同,这种“类同”正是“侔”式推理的根据。
3.“援”式推论。
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小取》)
“援,引也”(《说文》)。“援”式推理的特点是:引述对方的论点与自己的论点进行比较,以双方论点属同类为根据,驳斥对方对己方所持观点的否定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特点被孙诒让概括为“引彼以例此”[12]380。这种论式是通过指出对方所赞同的观点与其企图反驳的观点是相同的,从而说明对方是自相矛盾的。它依赖于语境,是语用推理。
《小取》的一段论述可以作为“援”式推理的例子,世人有“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的论点,墨者有“盗人,人也;杀盗,非杀人也”的论点,“引彼以例此”,二者同类。因此,“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就站不住脚了。这个例子表明“援”兼有证明和反驳的作用,反驳是主要的。“援”是十分有力的论辩手段。
4.“推”式推论。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小取》)所谓“推”式,就是揭示对方所否定(“所不取”)的命题和对方所肯定(“所取”)的命题为同类,从而推知其结论只能是要么都肯定,要么都否定,而不能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这也和论辩的语境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属于语用推理。
“推”式推论既可用于证明也可用于反驳,更多是用于反驳,例如:“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墨子·公孟》)
“是犹”,即《小取》“是犹谓也者,同也”的“是犹”。“执无鬼而学祭礼”和“无客而学客礼,无鱼而为鱼罟”也是“是犹”关系,即同类关系。按“法同则观其同”,两者要么同真,要么同假,而不能一真一假。
5.“止”式推论。
“止”式论式是《墨辩》在《说》中明确总结了的一种论式:
止,因以别道。(《经上》99)
止: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经说上》99)
止,类以行之,说在同。(《经下》101)
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们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经说下》101)
“因以别道”是指把不同的、别的情况(这儿是指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指出来加以反驳。但这个不同情况的命题必须限于同类(“类以行之”),即命题的主宾项同一。比如对方举出一个正面事例,得出关于这类事物都是这样的一个全称命题(“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这是由个别到一般的类取,是简单归纳。我们只要举出这类事物中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例子,就可以推翻对方这个全称肯定命题。这就是“止”式推论。又如,对方举出这类事物都是这样(“彼以此其然也”),推出这一类事物中某物也是这样(“说是其然也”),我只要举出这类事物并非这样(“我以此其不然也”)的一个全称否定命题,就可以证明对方那个某事物是这样的特称肯定命题为假(“疑是其然也”),这同样也是“止”式推论。可见,“止”式推论是利用命题之间矛盾关系进行的推论,这也是和语境密切相关的,因而也是语用推理。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用符号学作范式研究先秦的名辩学,能够对“名、辩”问题作出更加合情合理的阐释。由此我们坚信: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注释:
①符号(sign)原文译为“指号”,下同。
标签:索绪尔论文; 符号学论文; 范式论文; 逻辑符号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墨经论文; 逻辑学论文; 形式逻辑论文; 语言学论文; 语义学论文; 语用学论文; 推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