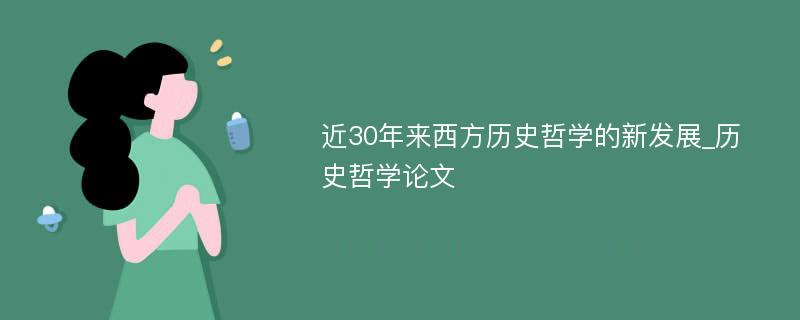
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哲学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哲学论文,近三十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08
一、历史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历史哲学(指西方历史哲学,下同)迄今为止的历史,大致说来可以概括为思辨——分析与批判——叙述这样一个三部曲。思辨历史哲学是关于历史本身(历史总体进程、历史意义等)的总体性哲学话语,其标准样本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马克思、汤因比及斯宾格勒是这一家族为人们所熟知的基本成员。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在时间和逻辑上均代表走出此前思辨历史哲学的范式转换,二者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不再试图操思辨的口吻讲述关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哲学故事,转而对历史学作二阶的认识论分析,这与历史哲学之外西方哲学由自然哲学到科学哲学的转向完全异曲同工。贯穿这一思潮的深层精神焦虑是确定史学在西方学术中的地位,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史学始终存在的身份确认问题。对此的回答则大致可以分辨出向科学靠拢的一元论倾向和努力论证史学独特性的自律论立场。分析历史哲学阵营中的人大致具有一元论倾向,而自维柯开始,下至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等则为史学自律辩护。20世纪统治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历史哲学,其核心论题集中在历史认识客观性及历史解释模式这两个方面。在分析潮流之后出现的就是作为本文论题的历史哲学的当代叙述主义转向,其标志性事件是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的出版。
史学文本的叙述特征并非新奇之事,但此前关于历史的理论反思视野所及,至多只是丹图(Arthur Danto)、加利(Gally)等人将叙述附属于历史解释(独特样式)的认识论探讨。自怀特始,叙述之为史学文本的话语维度成为史学理论的中心话题,在此,语言从长期以来我们习焉不察的透明物(something to be looked through)转变为被注视的焦点(something to be looked at)。① 历史哲学中这一叙述主义的思想转向与当代哲学中著名的“语言转向”可谓是不谋而合,这应该是更大范围内时代精神与学术转型的共同哲学表现。② 当代思想的基本共识是,此前人们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问题均具有内在的语言维度,甚至本质上就是语言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历史哲学的叙述主义转向与主流哲学语言转向在具体的理论背景、问题意识与致思取向等方面均迥然有别。后者的重要背景之一是现代哲学寻求自我转型,其灵感和思想资源主要来自逻辑学以及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的语言学理论,其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句子意义及其与实在的关系(指称)。反观叙述主义,其语言意识表现为对史学叙述修辞和美学维度的文本自觉,其相应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文学批评理论,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罗兰·巴特、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观点是怀特、保罗·利科、弗兰克·安柯斯密特(Frank R.Ankersmit)等人借鉴的对象。总之,在统一的语言范畴下,语言转向涉及的只是句子水平的精细分析,给人以实验室工作的印象,叙述主义处理的则是文本,所展开的可以说是话语的现场作业。这两种不同的语言分析应该说具有广泛的互补性。例如,语言被突显之后其与存在的关系是双方最终都要面对并且事实上已经触及的共同问题。
伴随着叙述主义的范式变更,历史哲学的学术旨趣由此前认识论范围内的历史解释和认识客观性问题转向对史学文本叙述模式及“叙述逻辑”的关注,这种关注突显了历史叙述的语言学(修辞学)与文学(诗学或美学)维度,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话题,如史学与文学的关系、故事与实在的关系,以及叙述与意义建构和理解的关系等。
二、叙述与表现:史学文本的文学及语言学维度
史家从来都在叙事,但是,直到怀特的《元史学》对历史作品作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的文本特征的系统分析,史学之为叙述文本这一简单事实背后的理论涵义才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怀特指出,在整体文本层面上,历史写作中可以分析出各种不同的“情节化模式”(悲剧、喜剧、反讽)、“形式化论证手段”(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情境论的)、“意识形态蕴涵”(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及修辞学特征(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并且将19世纪诸多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著作一一对号入座。
《元史学》的开创性意义在于,它扭转了分析历史哲学的思想范式,使“历史哲学终于赶上了自从奎因、库恩和罗蒂以来哲学上的发展”。③ 这本书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的形式刻板特征,怀特后来对这一方面亦有悔意。④ 但是,就其所揭示的史学与文学文本享有共同的话语符码与赋义手段而言,怀特的观点已经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者,如柯纳尔(Hans Kellner)的《语言与历史表现:将故事说圆》和古斯曼(Lionel Gossman)的《历史与文学之间》等等,均是对怀特观点的呼应和推进。
通常,史学与文学间的界限是依(原子)事实层面上的纪实或虚构划定的,落实在语言层面上就是陈述句子的指称问题,史学句子无一字无根据,而文学句子所涉及的人和事均无实在指涉对象。然而,叙述主义的观点是,“历史叙述是历史叙述,只是在于历史叙述的(隐喻的)意义在其整体性上是超越其单个陈述的总和的(字面的)意义”。⑤ 一旦越过单一陈述句进入整体叙述文本层面,史学文本不只是其中所包含着的实指陈述句及其逻辑联系的集合,在关于事件的“编年”层面之上尚有故事“叙述”结构的层面,⑥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情节编排”及故事风格(悲剧、喜剧等)等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法亦为史学文本基本的叙述符码和手段,由此赋予所描述事件以特定意义。
关于历史叙述的文学维度,最为极端的表述莫过于怀特那篇以《作为文学虚构的史学文本》⑦ 为题的论文。应该注意的是,一方面,文中所用的“虚构”(artifact)一词在英文中的本义是人造物品,在引申的意义上它亦含有虚假的意思,但虚构并不必然等于虚假(在中文中,“虚”“实”相生和相通,与“真”、“伪”对立不同)。在准确的意义上,怀特在此所表达的意义略近于康德对于知识的先验主体性因素的强调,强调叙述并非单纯由客观陈述内容构成,其中包含主体性叙述形式的建构成分,并且,这样一种“虚构给予我们有关(历史)实在的隐喻性真理”。⑧ 另一方面,我们亦应消除认为文学作品只是单纯的情感表达或美学愉悦的偏见。怀特指出,只有当我们把文学当作丝毫“不教诲我们任何关于现实的事情,才会因将历史和想象相连接而损害历史”。⑨ 历史哲学领域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法国的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敏锐地观察到文学与史学间的“相互赈欠”关系:“小说从历史中借来的东西与历史从小说中借来的一样多”。⑩ 当然,归根到底,史学与文学虽非壁垒森严、不通骑驿,其固有界限亦无可抹煞。句子层面上史学的纪实性质毕竟对历史叙述构成了基本的理论约束。
如果说怀特关于史学叙述的理论灵感主要来自文学理论,那么,同为叙述主义阵营中的当代荷兰历史哲学家安柯斯密特(F.R.Ankersmit)强调,对于史学理论来说,更为迫切的问题毋宁是语言哲学层面上关于历史文本(而非历史研究)的分析,其成名作《叙述的逻辑》的副标题“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明确标示了这一点。
在语言哲学的层次上,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属于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安柯斯密特认为,史学文本作为关于“法国革命”或是“冷战”的言说应该理解为是某种“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叙述语言没有透明性”,(11) 换言之,它不是描述外部实在的透明语言工具,而是体现了对过去的综合性视角的语言实体。尽管一项叙述内所包含的单个陈述作为历史研究的成果的确指涉过去,但文本层面上的“叙述语言并不根据指称或符合过去的部分或方面来表现过去”。(12) 严格说来,历史叙述是“关于”过去的语言阐释,它给出如何理解过去的“建议”,如从“冷战”的角度考察和理解美苏对抗:“提议可以是有用的,富于成果的,也许并不这样,但既不能是真的也不能是假的”。(13) 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叙述与艺术表现有相当的相似性。事实上,在安氏后来的著作《历史表现》中,问题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上被提出和讨论的。
安氏通过叙述实体的表现性来对抗描述性或指称性。“表现”英文为representation,有“代表”的意思,是对不在场者的替代。例如,在代议民主制中,议员是民众的代表,律师是当事人的代表等等。在同样的意义上,史学文本是不在场的过去的语言替代者,在此,“被表现或代表者与其表现或代表之间享有同样的本体论地位”。(14) 表现并不以指称的方式描述现实中的对象,相反,被表现者反倒总是要依附于表现者才得以存在。以绘画为例,即便是描述表象最强的肖像画,尽管它是“关于”模特的,但却不可以说是“指称”模特的。(15) 我们不假思索地肯定一幅画总是在画些什么,却往往忘记了画家也许首先是在画画,“这里绘画本身就是被意指的东西”。(16)小说家弗吉尼亚·沃尔芙(Virginia Woolf)说得好:“艺术不是世界的摹本,烦人的东西一个就够了”。(17) 同理,“历史表现跟过去的特定部分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也许最好这样说,历史表现是‘关于’过去的特定部分的——不要将这种‘关于’(aboutness)归结为指称”。(18)在此,叙述具有明显的隐喻性质。
安柯斯密特清楚地意识到,在他关于历史叙述的语言哲学处理中,史学文本与过去实在之间所有的认识论链条均告断裂,(19) 这意味着,在认识论中作为核心范畴的真理对历史叙述而言并不具有传统上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意义。“一个对历史的写作维度缺乏敏感,宣称关于历史著述的所有理论问题最终都可以被重述为关于真理的问题的史学理论是残缺无用的,就像声称为了判断博物馆中我们所欣赏的表现现实的绘画作品的优点,摄影式的准确性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美学理论一样”。(20)
和一切观点一样,安柯斯密特对史学叙述语言文本的“表现主义”理解未必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例如,他关于“叙述实体”的理解建立在过去(如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均不再在场的直觉虽不无道理,但却需要更多的论证。但这不能掩盖其思想的敏锐与新意,它超越了关于历史理解的天真实在论和简单反映论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历史叙述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三、历史之超越语言的经验维度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理论动向,就是以安柯斯密特为代表的历史经验的理论,其集中论述就是那本书名意味颇难传递的《崇高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
经验范畴的提出,反映了理论内外一系列因素的交汇:一方面,它是历史哲学理论内部为寻求自身的理论突破与发展的反思结果,具体来说,就是试图从语言进至先于语言的层面,从文本叙述进到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代史学发展各种趋势与关注的理论回应,包括微观生活史、心态史的崛起,关于“创伤记忆”、“浩劫”与“大屠杀”的思考等等。当然,它与对历史表现的美学维度的思考亦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是核心范畴由“表现”转换为“崇高”。
后现代历史编纂学最为特别之处,就是《蒙塔尤》、《马丁·格雷归来》和《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这样一批所谓微观生活史和心态史著述的出现。它们所代表的学术趣味、研究题材与风格的转变是一目了然的,而其精神底蕴则更为深刻。首先,它们共同体现了关于历史断裂、偶然与零碎化的后现代史观。以往一切史学理解与描述都以某种关于人类历史的整体观点为出发点,历史学家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存在分工,但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学术理想,相信各处的工作最终将汇成历史的完整图景,即所谓的“大叙事”。新的史学著述的出现表明,“历史学家不再能有意义地向自己提出其研究成果如何与历史整体的画面相吻合的问题。过去不再被看作是一张世界全图,其中有许多空白点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依次填补。它不再被看作是关于已经由非人的巨大力量勾勒出大致轮廓的草图,只需由历史学家进一步弥补细节。相反,过去已经成为巨大和无定形的块面,每个历史学家都可以在与(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同行不照面的情况下各自为政,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和‘整体历史’(就此事仍然被当作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而言)有什么关系”。(21) 如果说过去历史被理解为是一座每个历史学家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之添砖加瓦的“大教堂”,现在,它被代之以“大都市”的形象,在这里,每个人走自己的路,操心自己的事,不太关心其他人在干什么。
从语言向经验的回撤的另一个动因,是面对20世纪纳粹集中营之类的“创伤记忆”时人们在感受到通常语言的苍白无力时出现的普遍失语现象。“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化简的已知实在,或是依此我们可以澄清大屠杀?是否存在着我们所熟知或是完全建立起来了的人类行为的模式,由此可以解释大屠杀?”(22) 答案是否定的。换言之,大屠杀这类的创伤经验向传统史学叙述的适宜性提出了挑战,它没有办法被放进任何现成的叙述模式中获得理解和表达,为此需要的是“记忆”话语为这样的历史悲剧提供“见证”。因为“记忆话语是‘索引性的’,它指向或指示过去,将过去固化从不指望穿进它”。(23) 此外,记忆之为见证与史学叙述的区别是,后者是非个体化作者对匿名读者说的成型套话,而见证则是人对人的倾诉。“在作为听众的言者和旁观者面前提供见证不仅只是报告一个事实或事件,或者讲述曾经经历过的、被记载下来和记得的事情。在此,记忆被唤起在根本上是为了向另一个人倾诉,让听众印象深刻,对公众呼吁……见证因而不单单是叙述,而是将自己交付出去,将叙述托付于别人”。(24)
“创伤经验可以看作是崇高体验的心理对应物,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哲学对应物。”(25)面对个体性和极限经验,原本出自美学的“崇高”突显为重要的理论范畴。崇高指的是我们在面对巨大、壮阔或强有力的现象——如高山大川、狂风暴雨——时所产生的体验。这种经验一方面是不愉快(震惊、恐怖)的,另一方面又曲折地包含着特殊的审美愉悦(对自身心灵力量的信心)。如果说优美感的产生与可把握的形式有关,崇高感往往与无形无序、难以把握有关。进而言之,优美感是对已经被我们“驯化”了的现象的通常体验,而崇高则是面对我们理性及语言尚未驯化的狂野现象时的感受。驯化是必要的,可是,驯化了的也就是被掌控了的,我们获得的是掌控,失去的是本真。正因为如此,安柯斯密特认为,有必要突破“语言的囚笼”,将被语言和文本所摧毁、被语言的先验性所“驯化”与“挤占”的关于实在的前语词经验释放出来。(26)
经验维度的开启在理论反思的层面上是对语言学转向的超越。鉴于语言维度内含着与康德先验知性范畴的对应性,二者本质上仍然属于同一的先验主体性哲学范式,或者说,都仍然是现代性哲学思维的产物。而对先于语言的经验的强调,试图让经验外在于先验语言的努力,则完全是后现代式的。在这一意义上,后现代在哲学上即后康德的。
正如先于和外在于先验语言模式不等于抛弃语言一样,简单地写下经验二字毫无意义。关键在于,这是什么样的经验:作为历史或者存在经验的经历不同于直接的感官经验,后者只是认识原料的提供者和“真理温顺的仆人”,是真假语言游戏的成员,而在诸如心态史与大屠杀所指向的历史经验方面实质上是一种生命经验(lived experience,德文Erlebnis)或者说存在体验,是人们全身心沉浸于特定情境产生的体认性感受。这种经验先于且超越真假。(27) 在某种意义上,两种经验的区别是认识论与美学的区别,前者是主客二分的,而后者则是物我交融的。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经验隐喻地说与其说是被看到的,不如说是被听到的:“看”总是拒之所见物于一定距离,而在“听闻”中我们与所经验者无缝对接。(28) 更准确地说,存在在此被体验或体认。与“眼”相比,“体”不但是全方位的,并且,所体验到的事情——如维特根斯坦爱举的例子“疼”——与体验者是内在一体的。值得注意的是,安柯斯密特明确提到亚里士多德《论感觉》中对触觉比其他感觉优越的观点的重要性,(29) 暗示的就是这层意思。此外,审美与历史经验只有在对象与主体双方没有哪一方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平衡状态下才成为可能,这保证了存在的真正在场性与我们的经验体认的真切性。
历史经验维度的提出显示出明显的超越此前语言分析进路的理论态势,对其中可能蕴涵着的历史哲学未来新的学术生长点值得关注与期待。然而,经验与文本对立所包含着的后现代特征亦令人不无疑虑,包括人类历史意识是否以经验实感为对象以及经验与语言的关系,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理论问题。
注释:
① Brian Fay,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Vann (eds.),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1998,p.3.
② F.R.Ankersmit,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63。另参见Brian Fay,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Vann,1998,pp.2~3.
③ [荷] F·R·安柯斯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④ [美]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中译本前言,第1页。
⑤ [荷]F·R·安柯斯密特,2005年,第48页。
⑥ 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1,trans,by K.McLaughlin and D.Pellau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⑦ Hayden White,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in Brain Fay,Philip Pomper and Richard T.Vann (eds.),History and Theory:Contemporary Readings,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8.
⑧ Ewa Domanska (ed.),Encount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8,p.86.
⑨ Hayden White,1998,p.33.
⑩ Paul Ricoeur,1984,p.82.
(11) [荷]安柯斯密特,2005年,第45页。
(12) 同上,第44页。
(13) [荷]安柯斯密特,2005年,第44页。
(14) F.R.Ankersmit,2001,p.81.
(15) 同上,p.41。
(16)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卷,第181页。
(17) F.R.Ankersmit,2001,p.81.
(18) 同上,p.13。
(19) Ewa Domanska,1998,p.74.
(20) F.R.Ankersmit,2001,p.44.
(21) F.R.Ankersmit,2001,p.1。
(22) 同上,p.177。
(23) 同上,p.1。
(24) S.Flelman and D.Laub,Testimony:Crisi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 History,New York,1992,p.204.转引自F.R.Ankersmit,2001,p.163。
(25) F.R.Ankersmit,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338.
(26) 同上,p.4,p.116。
(27) F.R.Ankersmit,2005,p.9.
(28) 同上,pp.123~124。
(29) Ewa Domanska,1998,p.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