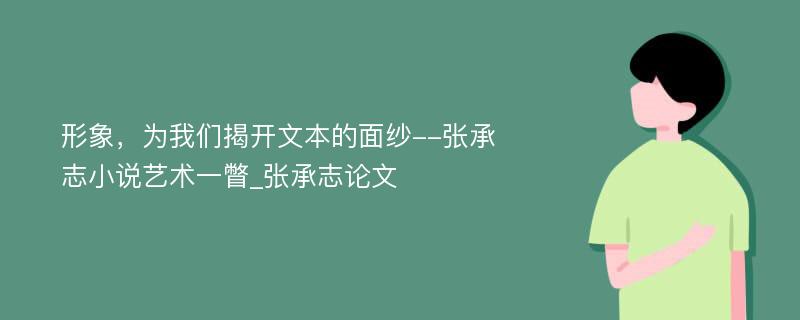
意象,为我们掀起文本的面纱——张承志小说艺术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面纱论文,文本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当我们从“意象”的角度切入张承志的艺术世界时,他所坚持的规避艺术观便由“意象”在他的“诗性小说”中得以充分显示。意象便为我们深入他的小说天地而掀起了“规避”的面纱;张承志视“意象”为自己的小说创作的特殊手段。或用来淡化、消褪乃至代替故事情节,或用来结构全文,或用来塑造人物,达到了通常使用的小说营构手段所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张承志选择了意象,同时意象也适应了张承志情、智相兼的创作个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意象同时又选择了张承志。这不仅表现为意象在某种情形下成就了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又表现为张承志在创作实践中扩拓了意象的使用功能。不仅如此,借助“意象”的探寻,我们又意外地梳理出张承志的两次艺术转向,并对他今后的艺术跋涉仍予以关注并寄厚望!
关键词 意象 文本 诗性小说
作为一名小说家,张承志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位已由他十几年来的丰硕创作实绩而确立。他的小说又因始终与同仁取了“别一种样式”而独存。当我们细究这独存的奥理时,分明感到:意象似乎比人物、情节等更能凸现其小说固有的文本内涵。之所以如此,或是因“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出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1〕; 或是因作家本人更精心于营构意象所透出的丰富象征意味与文化内蕴等对小说中人与事的高屋建瓴般的穿射……无论如何,在张承志的小说世界里,意象,无疑具有意味深长的勘探价值与启迪意义。
意象之于张承志的艺术观
只要归拢张承志小说的题目,我们就能触到他小说的意象群。他拥有着山、河、大坂、泥屋、太阳、草地、骏马、雪路、绿夜、血衣、拱北及残月……这样一个完整的且经严格挑剔而构成的宇宙世界。而这个宇宙的贫旱而壮美、严酷而倾心、惨烈而神圣,便拥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与颇具深意的蕴味。令我们特别应该领悟的则是:一切倾诉的表达只是意象。
从内容上划分张承志小说的意象,大体有五类:(1 )是由桥(《老桥》)、马(《黑骏马》)、河(《北方的河》)和绿夜(《绿夜》)等组成的“青春见证”型的意象:它们均是作家那段无悔的青春岁月的见证者。其中,“老桥”上的诺言、骏马前的爱情、“北方的河”边的壮勇、“绿夜”里的豪情等均成为主人公日后久久难弃的精神财富与源源滋生的生命元气;(2)是由雪路(《雪路》)、 太阳(《凝固火焰》)与落日(《辉煌的波马》)等组成的“人生启示”型的意象:生命途中往往阴晴难测、多舛多难。有时如“雪路”般峭寒难熬、有时如烈日般酷烤难忍……但无论有多艰辛,人生应当如日中升般地执著、激进、热烈,永远澎湃青春般的生命激情。即便是人之暮年也应当如波马的落日那样辉煌一番;(3)是由“黄泥小屋”(《晚潮》)、 九座宫殿(《九座宫殿》)、黄泥小屋(《黄泥小屋》)和金草地(《金草地》)等组成的“生之念想”型的意象:无论是平平淡淡地还是轰轰烈烈地,只要是实实在在地活,“生之念想”就应当是生命存活的强有力的支撑:庄稼汉们心存的老婆、孩子与炊烟的“黄泥小屋”式的平常梦、甚至探寻“九座宫殿”的痴妄梦与额吉一生念念不忘的“金草地”的人生宿愿等均是芸芸众生生之目标、活之渴盼的确确实实的价值显现;(4 )是由大坂(《大坂》)、烈马(《春天》)和顶峰(《顶峰》)等组成的“征服对象”型的意象:仅有“生之激情”和“生之念想”是不够的,更应当有征服生所遭遇的勇气和胆略:在妻子越过生命大坂的感召下,“他”也终于越过了事业的大坂;为保住畜群、更为赢得姑娘的芳心,乔玛以年轻的生命驯服了烈马;为虚荣也为回报姑娘的痴爱,铁木尔勇敢地向顶峰挺进……无论成或败,征服者均在这不凡的征服过程中认清了自我、成熟了生命;(5)是由“血衣(《西省暗杀考》)、残月(《残月》)和“拱北”(《心灵史》)等组成的“宗教情怀”型的意象:伊斯儿这个血泊中的幸存者,生命的全部目的只有一个:为家为族更为教复仇,求一件“血衣”进天堂!杨三老汉急急奔寺做晚祷,而清真寺顶那弯高悬着、残缺的铜月牙则是苦难深重的独存中,仍持守宗教信仰和人生信念的穷山沟回民生之态的逼真写照;而七代宗师生命璀璨的显示便是舍命争得的、辈辈奇迹传诵的拱北……执著的精神追求与不息的生命挣扎均又掠过俗界、跃入了圣域,生之旅也因此涂上了挥之难去的宗教情怀。
显然,这五类意象构成了张承志小说意象群的基本骨架。此意象群也便具有了独特的征貌:(1 )这五类意象在内容上具有内在的层递性与逻辑制约。因此,这个意象群也就成了一个严密有序的大系统; (2)此意象系统的母题是:俗界里的圣域般的精神追求与九死不悔的生命挚爱!(3)是理解蒙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之一;(4)借助意象群的层层推进而昭示出了母题,更是张承志的规避艺术观的一次出色演示。
张承志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一惯坚守“艺术即规避”的艺术观。审视这“规避”,恐怕起码该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对政治、潮流等非文学因素的规避;二是对直白、浅吟等文学忌疾的规避。而在文学的最基本体样中,诗歌当属最讲究本真、最切近含蓄,因而也最能逼近文学自身的一种。所以,张承志便认定:“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2 〕而要达到这“诗的境界”,也就离不开意境的营造与意象的构设。亦即在“象”中透“意”,在“意”中蕴“象”。而张承志本人则舍弃了诗人表层操作方式,却赋予了小说一种诗的内核与本真。这种对小说和诗两种文体的双重整合与运用,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诗的境界”。我们不妨称之为“诗性小说”:由于小说家本人的“全部体验都过于私人和神秘,全部体验都过于沉重地负载着巨大的意义和命题”,〔3 〕这“诗性”的显示便由意象来承担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象之于张承志,是一种特有的倾诉方式,亦即情智相兼的艺术符号与表现载体。正因为他是借“意象”来表现与诉说的,连他自己也知道,读他的小说,“哪怕是极其亲密的朋友也可能读时感到艰涩和陌生”。〔4〕但是, 当我们抓住了意象,尤其当意象为我们掀起了他小说文本的“规避”面纱时,“艰涩和陌生”也随之消减,一个意味深远的艺术世界便徐徐向我们展开了。
意象之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
张承志曾坦言:“我发现真正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是一定程度的冷血动物。他们能旁观,能调和,能冷静和冷漠,能热衷于布局和故事,能专门关心他人。而我很难如此。”〔5〕实际上, 张承志视“意象”为自己小说创作的手段来“布局和故事”,甚至于塑造人物的。具体表现如下:
(1)意象几乎淡化、消褪乃至代替了故事情节:
这主要体现在《北方的河》、《老桥》、《绿夜》、《凝固火焰》和《辉煌的波马》等作品中。其中又以《北方的河》最具代表性:“河”是小说的中心意象,也是情节主干线,几条北方的河则是此干线上的情节点,这点与线便形成了此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框架。此小说主要讲述主人公的察河、考学与恋爱的故事。而这几条河又牵制着故事的发生与推进。亦即:不仅人、事、情都与河有关,更重要的是,每条河都曾予以主人公精神的启迪和情感的慰藉:他在额尔齐斯河边插队、初恋。这条“自由而宽阔的大河重新塑造了”他,叫他切身懂得了“意志、热情和诺言”。额河支撑了他那几年底层的艰苦生活,又帮他忍痛埋葬了初恋,更启悟他立志从事北方诸河的研究。他曾两度搏击黄河,但心境迥异:昔日的黄河只留给他一个珍存的纪念;十几年后的黄河便成了他心目中的父亲——给他安慰、理解与护卫的精神巨人。他从这“虽饱经沧桑但仍奔腾不息”的大河中汲取了迎击人生的勇气和力量,同时,在黄河边听到的“十二岁小姑娘”的勇敢故事,又激发了他对生活的责任与热情,并因此而对她萌生了真挚的恋情。湟水边“彩陶碎片”如同试金石般测出了他与她不同的人生观,这为他们日后的分手埋下了隐患,也为她与徐华北的结合做了某种暗示。永定河以“坚忍与宽容”启发、安慰了他那颗屡遭坎坷而狂燥不宁的心。冷静之余的他不得不承认:“这不是我渴望的爱情”,毅然与她分手,从容赴考场了。出现在梦中的黑龙江以轰然炸响的“黑龙”开冻的壮举鼓励并感召他奔向宏阔的未来,同时,理想中的爱人也正向他走来……可见,由于人与河的精神同构关系,便由几条河演绎、罗织出了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反之,若没有额河,便无他报考人文地理学的原初动机;若没有黄河,便无父爱的鼓励与恋情的萌生;若无湟水边彩陶碎片,也无两人的日后分手;若无永定河的启发,更无断爱与全心赴考;若无梦中的黑龙江的“开冻壮举”,主人公连同小说的精神气韵都将黯然失色。可见,作家是借几条小河来写主人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并由此勾画出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历史。这位“被那些河惯得太野”的河之子的故事就是他与河的故事,甚至就是河的故事:额河是故事的开端、黄河是故事的高潮、湟水是高潮之后的发展、永定河是情节突变前的缓冲、黑龙江则是又一更大的情节高潮。整个小说的情感流程也一波三折、波澜起伏,在“银瓶乍破水浆迸”的高亢中戛然作结,留给读者撼动心魄的启悟。
(2)意象用来结构全文:
这主要体现在《黑骏马》、《晚潮》、《残月》、《黄泥小屋》等作品中。其中又以《黑骏马》最具代表性。张承志曾回忆:那首著名的蒙古古歌《钢嘎·哈拉》(即《黑骏马》)是他“青年时代学会的最美的一支歌”。他的“胸中从此增添了一支神奇的诱惑了”他“长达十多年的深沉旋律”。他甚至许诺:“将来要写一篇小说,它的内容不管是什么,题目都叫《黑骏马》!”于是,在创作《黑骏马》时,他便“决定了用民歌来结构它——每节歌词与一节小说呼应并控制其内容和节奏”。〔6 〕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在多年后发现自己居然“亲身把这首古歌重复了一遍!”实际上,小说八节全由古歌八段引启。小说的旋律便依次而成,形成一唱三叹的悠长之调。小说的内容也与古歌基本内容相近。在古歌中,“黑骏马”这一中心意象结构了全诗。在小说中,古歌里的黑骏马此时虽已被虚化,但这一虚化了的意象仍贯穿全小说始终且又结构了全文:古歌主要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基本情节的安排线索是:相恋——离别——寻找——失落。重在咏叹“寻找”之艰辛。而小说则扩写为北国底层的“一些平凡的女性的人生”,重在抒写白音宝力格与草原三代女性的命运纠葛及由此而生的愧疚、悔恨之情。实际上,若无黑骏马这一实写意象,这三位女性的不幸故事仍会发生,只不过有了骏马的见证与目击,便为她们的命运悲剧又涂上了一层人生的沧桑与民族文化的幅射。因为在游牧民族内心深处,他们总认为:“骏马集中了一切生物(他们觉得包括人在内)的优点,牧民们觉得有朝一日骑上一匹神奇好马的愿望是那么珍贵。这样的心理积蓄沉淀了多少个世纪。也就在这样一个历史中,骏马的形象和对骏马的憧憬,构成了游牧民族特殊的审美意识,骠悍飞驰的骏马成了牧人心中的美神。”〔7〕同样, 在小说中,主人公也和三位女性一样视黑骏马为“一种实在但又比生活好些的希望”与寄托了。但现实却将他们心存的些微希望都一一揉碎了。就连其其格这个不幸的小姑娘也在“巴帕骑着黑骏马来看我们”的梦想兑现的瞬间,心中储下了更深的人生苦痛。索米娅未能摆脱奶奶的人生悲剧,其其格就易避免索米娅的不幸吗?对此,就连与人异境的黑骏马也对她们的不幸遭际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只不过这同情却无法言说。可见,“黑骏马”这一实写意象的设置,加重了小说悲剧的份量。更为重要的是,实写意象虽没有象虚化意象那样直接结构全文,但却对结构线索的合理性提供了间接性的规范与指导,即实写扩延了小说的情节内容,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又完善、补正了小说的情节结构。虚、实意象相辅相成,共同实现了小说的艺术构想。
(3)意象用于人物塑造:
这主要体现在《心灵史》、《西省暗杀考》、《雪路》、《春天》、《大坂》、《顶峰》、《九座宫殿》及《金草地》等作品中,其中又以《心灵史》最具代表性了:“拱北”(即圣徒墓)是《心灵史》中贯通全文的潜意象。回民对拱北怀有图腾崇拜般的情愫。实行薄葬的回民,“藉此拱北看守着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财富、历史。”现实也往往是这样的:有了祖先拱北,便在墓旁盖房、娶妻、生子、聚众、建寺,一个回民的“小聚居”便形成。因此,对于失乡丧语的回民来讲,拱北便是他们的无根之根;对圣徒们而言,有了拱北也便有了被崇拜与被追随。因此,七代宗师和白彦虎、杜文秀等人的生命价值的最高显现也便是为自己争获一块圣洁的拱北;对哲合忍耶来说,拱北更集中显示了他们所遵循的“束海达依”(即殉教)的精神实质:惟有得了舍西德(殉教)的高品才配有拱北。哲合忍耶的辈辈宗师的墓均遭挖坟扬灰被再毁的厄运,这便使他们的拱北成了血泪历史的见证者与罹难者,也成了声讨血腥镇压心灵自由的控诉者。正因此,《心灵史》中令人过目难忘的那些人物都由“力争拱北”这一潜念来显出人物的血肉与立体感的。
作家在“拱北”这一主意象的指导下,又借许多次意象所形成的意象群来塑造众多的人物。
马明心的口唤(即使命)是传教。作家塑造此人物的重心便是什么人传什么教。据载:马明心曾受教于也门苏菲派的一个道堂,十五年后奉也门导师之命回国传教,创建了哲合忍耶学派。而“起源于中西亚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叫做苏菲主义。苏菲,意即羊毛衫。古代那些神秘的行吟诗人、修炼者、追求着爱主接近主的私人体验的隐士,都穿一件羊毛衫袍。”马明心生前也穿一件妻子手织的羊毛衫传教的,以此向人们表明该教派的“苏菲”特征。这件羊毛衫便成了最直观、具体的象征物了。作家便借“羊毛衫”这个意象来塑造马明心这一人物。同时,作家又为我们安置了一个“羊毛衫散香、发光”的故事,意在突出“穷人宗教”是哲合忍耶教派的本质。不仅如此,作家又特意强调这位苏菲老人是“穿着这件衣裳上路,直至牺牲。”于是,一个“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的从容赴难者形象,从此便在多斯达尼(教友)的心中植下了无法剪除的追随、效法之根壤。于是,他们代代舍命、辈辈流血都为成就自我生命的“这一刻”。这也便播下了“束海达依”的种子。马明心殉教时穿的那件浸血的羊毛衫便成了该教派所坚守的“束海达依”的原初注解物了。于是,穿着羊毛衫传教、殉教的马明心便成了哲合忍耶心目中坚不可摧的道祖、圣徒了。马化龙的口唤是卫教。作家在塑造此人物时,将重心放在此人“如何卫教及卫教的程度如何”上。一切有信仰的人都该熟知易卜拉欣曾把独子伊斯玛仪勒举意做古尔邦的羊那个著名故事。这是对人类信仰的一次残酷考验。人类则经受住了此次考验。于是,被感动的主允许用羊来代替其子。古尔邦节便成了宰牲节。同样,作家便选了“古尔邦的羊”这一意象来塑造此人:“十三太爷马化龙为着换回多斯达尼,把自己一家人举意当了古尔邦的羊了。”这是一件信仰、心灵、神圣的历史上的罕见大事,“标志着中国人之心灵追求的程度,更说明在中国社会中宗教存活的艰难。”对他这一舍家弃命的壮举,教内辈辈以屡生的奇迹传颂而予以代代的肯定与回报。马化龙这位坚决的卫教者如同当年替代伊斯玛仪勒的那只羊而永驻人心。马进城的口唤是忍辱。作家以“瞬忽的弦月”这一意象来塑造此人:因他是马化龙的孙子而关狱、押京受阉割苦刑、被贬为异族家奴、仅25岁亡于他乡且以汉俗入葬。可见,此意象便是他短暂多难命运的某种暗示;同时也是他冷硬、倔犟个性的写真:这位年轻的冷面人拒绝教内营救,至死不露身份。白天当奴伺奉异教徒的主人,夜晚熬夜修炼侍奉真主。短暂的一生竟在受难忍辱中熬度的。“哲合忍耶把一位事实上并未掌教,而且终生受辱的刑余之人尊为自己的一辈宗教导师”,其根本原因恐怕在于“马进城的故事抽象了这种被迫的罪人感,并且以自己冷冷的对自由的摒绝,向人们显示了哲合忍耶作为宗教的成熟和深刻。”这便是忍辱者的生命价值所在;杜文秀这个人物的使命是献身。作家用“孔雀胆”这一意象来塑造此人物的:孔雀是美丽的,掺毒的胆则是残酷的。而杜文秀吞咽的那个孔雀胆便是美丽而残酷的象征物了。献身者服用的毒药既然是一服孔雀胆,死便是一个美丽的梦。正因这美丽的死而使献身者的人格、心灵得到了灿烂的升华。这位云南回民代代引为骄傲的民族英雄便与云南的至美而长留人心了!总之,《心灵史》中几位过目不忘的人物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准确、贴近的相应意象的选择运用。这是通常使用的人物塑造手段所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
可见,张承志是借意象来营构他小说的情节、结构与人物的。当然,这几方面是互渗互透,各有侧重,相互交叉的。绝非割裂难容:如《大坂》中“大坂”意象既代替了情节,又塑造了人物;《黄泥小屋》中“黄泥小屋”意象既结构了全文,又塑造了人物等等。
意象之于张承志的创作个性
曾治史务哲的张承志终因诗人的天性而弃史从文。作家的他既有诗人情怀又有理辩头脑,这便形成了情、智相兼的独特的创作个性。《心灵史》之所以令行家很难划归派属,就是因那亦史亦诗、亦文亦理的文本实为既主情又主智的独特创作个性的最集中的显现。
张承志认为:“形式从来只有在真正艺术的气质和血肉中才能诞生,形式没有搜索枯肠的投机和赶潮头。”〔8〕综观他的小说, 最突出的文本特点是倾诉。他又特别强调:“倾诉在本质上只能是诗。”〔9 〕他之所以极喜爱自己的那三首长诗,是由于“它们给予我倾诉和表现的原野,给予了我的无拘无束地用中文汉语指点江山、发掘和丰富这美好文字的喜悦。”另外,张承志所谓的“诗”,显然既含有诗的激情又含有史的思辩,意象便是这“诗眼”。他那“诗性小说”之所以选用意象作为主要的倾诉方式,就是由于,从某种意义上讲,意象最能负载激情与哲理,情中蕴意,象里喻征。张承志选择了意象,同时意象也适应了张承志这种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因此,也可以说是意象同时又选择了张承志。正因为如此,意象又在某种情形下成就了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借助于意象的选用,使他扬长避短成功地推出了自己的“诗性小说”。人们往往不更多苛求他小说中人物的细腻与情节的曲折,人们对他的小说记忆更多的是“意”与“象”而非“人”与“事”。这恐怕是由于特殊的接受背景遇合了他这种独特的文本了:八十年代是个全民狂热之后,人们不想再被激情愚弄而缺乏激情的时代,张承志则以历经坎坷仍引辔长啸的黑骏马的嘶鸣与饱经沧桑仍奔腾不息的黄河的燃烧而激发人们重燃生命的热情与欲望;九十年代是个全民信仰萎顿甚至丧落的时代,张承志则以“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五十万人”的母族血泪秘史而揭示出:宁肯有信仰而死,也不无信仰而生!以雄辩的历史事实来呼唤荒芜了的信仰之路上的后继者!如果说,他八十年代的诗性小说以“情”打动了人们那颗冰冷的心,他九十年代的诗性小说又以“理”撼动了人们那麻木的灵魂。他小说中的意象之所以易与读者在“情”与“理”上产生强烈有效的对立与共鸣,就在于他在选用意象入创作时,意象迫使他跳出既定的人、事纠葛,跃出时代冲击圈之外,能高瞻远瞩地把握生活表象与时代脉搏。同时,意象又为接受者留下了艺术想象的空白,意象的处处暗示更易引起人对于生活的反思与内省。
就文本表象特征而言,意象的选用,的确适应了他这种“倾诉式的创作”实际。同时,就文本内容而言亦如此:张承志历来以“塑造清洁的人物心灵历史”为文本的主要内容。他避开了传统的“灵魂拷问式”的基本写法,而是坚持:“正确的方式存在于被描写的人们的方式之中。”在创作人物时,他更清楚:“历史全是秘密。偏执地追求历史而且企图追求心灵的历史,有时全靠心的直感、与古人的神交、以及超验的判断。”〔10〕因此,在刻划人物心灵时,他尽可能以一颗清洁的心灵去感应湮没了的另一颗心灵,在“神交”中碰撞出赞美的诗情,再借“超验的判断”予以深远的表征。一个个意象的设置或为情节或为结构,最终都归向清洁之心的塑造。尤其是这个“心灵历史”的启悟意义更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内心塑造了。而意象的选用则又成就了张承志“刻画人物清洁心史”这一创作目的。
不可否认的是,张承志携意象入小说创作时,因其驾驭意象的娴熟能力而灵活选用了意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大了意象的实用功能。当我们细究张承志小说中的意象,就会发现有表意象与潜意象、主意象与次意象、近意象与远意象、实意象与虚意象等等之分。当然也是互有交叉与渗透的。
《西省暗杀考》中的“血衣”、《晚潮》中的“黄泥小屋”和《心灵史》中的“拱北”均属潜意象:伊斯儿毕生渴求一件血衣进天堂,以兑现17岁时接下的复仇口唤。但他却复仇总无门,在89岁时空叹而亡。而与妇人合葬时,“染红白布”的奇迹则是对他血性生命的肯定。只是这种“兑现”整整折磨了他一生。可见,若抽去“血衣”这一潜意象,主人公遭遇的坎坷、磨难便失去了价值与意义,此人物将因失去灵魂而坍塌;《晚潮》中的母与子心中时时涌动的是对“娶妇生子”、搭一个亲情弥漫的“黄泥小屋”的渴求。整个小说的结构也由母子心中的渴求情潮而演绎的;“拱北”这一潜在意象对七代宗师数百年的心灵历史的刻画是不可或缺的生命结。不同人物的心灵也因此而气贯一致,他们的生命也因此而抬升了品级。
《心灵史》除“拱北”这一潜在的、中心的意象外,还有“羊毛衫”、“古尔邦的羊”、“瞬忽的弦月”和“孔雀胆”等次意象。它们都与主意象“拱北”形成精神主旨的同构关系而使人物的人格气韵浑然一体,组成了一个具有宗教血亲联系的精神家族。在“死亡”及“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上,次意象便通过各自所塑造的不同人物来对主意象“拱北”进行烘托与诠释。
“九座宫殿”、“黄泥小屋”和“金草地”等属远意象:它们终因难以企及,便可望而不可及地时常萦绕于主人公的心头而成了一种生命企望。它们便因此而影响、左右了人物的命运抉择:韩三十八曾因股心劲而探“九座宫殿”,虽失败而归,但却从此凭这股心劲硬将自己的根扎在了荒瘠的红胶土上了。因为他终于懂得了:“人哪怕真的到了绝境,只要心劲不死就有活路”。苏尕三时常远眺的“黄泥小屋”的几次隐显,一次次地感召他由躲避、认命到挣扎、反抗,最后带着自己的女人去寻那安身又安心的泥屋了,小说的结构也由此而得到了推进与完成。额吉因“金草地”的念想而迁徙了一生,而额吉迁徙的人生又帮“我”完成了由红卫兵向人民之子的蜕变过程。当然,可触能见的意象则属近意象。而近意象又分为两类:如“大坂”、“太阳”、“顶峰”、“烈马”及“雪路”等往往以主人公要征服的对象而出现;而“北方的河”、“黑骏马”等则因与主人公形成精神或情感上的同构关系而成了主人公倾诉的主要对象了。
《黑骏马》里,古歌中的“黑骏马”与主人公骑的“黑骏马”构成虚、实意象的对应关系;《大坂》中“我”要翻越的冰山大坂与妻子已跨过的生命大坂也形成实、虚意象的对应关系。虚与实互衬互托,相得益彰:前者因黑骏马的虚化,而为实写的黑骏马所目击的命运悲剧涂上了人生的哲理色彩;后者在妻子越过的生命大坂的感召下,征服了困难并成熟了自我。
张承志曾声称自己“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也“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更“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11〕事实上,“诗性小说”也已成了他艺术探索之途上的一个足印了。他先是由小说而转向诗与散文:如三首长诗和一系列散文的结集出版,尤其是将《金牧场》改写为《金草地》,“就是删掉了原作的结构和情节;保留并在思想上坚持了原有的抒情和独白。”〔12〕而后又由文转向了画:如果说,在他的“诗性小说”里,意象是画面,小说本身是这画面的文字提示,此时他连这“提示”也取消了,索性完全走向了色彩。显然,张承志的两次艺术形式上的转向,即由“意象”的小说规避到诗歌的直抒胸臆,再到绘画的色彩沉默,“把可读的小说诗歌干脆变成沉默的色彩”,由此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艺术探索过程。无论如何,独自跋涉在艺术坎途上的张承志也渴望有朝一日能像凡·高与冈林那样拥有自己艺术上的“色”与“歌”。为此,张承志正以自己不懈的努力,追求着他心目中应有的张承志!
“方式的选择可以或是绘画或是文学或是作曲吟唱,但关键只在于表现这种美好的灵魂。”
——张承志
如同我们欣赏他的“诗性小说”、宽待他的不分行的长诗,我们也能容忍他始于绘画的艺术新探索。只要他在形式迥异的艺术外壳下仍表达、倾诉着那颗清洁的灵魂,那就不失张承志之真我,也不枉我们对他仍寄寓的厚望!
*收稿日期:1997—5—21
注释:
〔1〕韦勒克·沃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2页。
〔2〕〔3〕〔4〕〔5〕〔6〕〔7〕〔8〕〔9〕〔11〕《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20—221、342、342、342、33、284、223、341、392页。
〔10〕《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长篇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22页。
〔12〕张承志:《金草地》,海南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