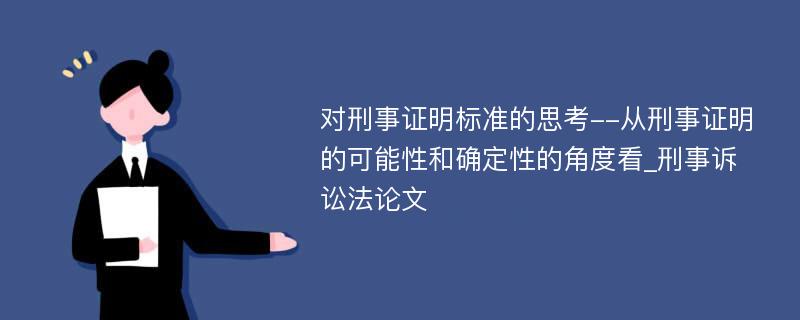
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以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可能性论文,性为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贯穿整个刑事证明过程始终的一根主线。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进行实体处理的活动均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在证据制度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复杂的、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在我国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讨论中,存在着诉讼证明应当追求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绝对真实还是相对真实、实体真实还是程序真实,证明标准应当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排他性、确定无疑还是确信无疑,证据制度应当以认识论为基础还是以价值论为基础的激烈争论。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对刑事证明标准的分类、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刑事证明标准的实践价值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与确定性问题展开探讨。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分类
刑事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证明要求,是刑事讨论中证明主体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需达到的程度要求。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以可能性或确定性的不同程度来划分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如在美国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这一标准无法达到;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做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以及做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做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可能的原因,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注:参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这里,证明标准不仅包括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标准,而且包括检察机构起诉的标准,此外,还包括侦查机关采取重大侦查行为应当遵循的标准。可以说,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上呈递进的态势,对被告人作有罪判决要求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排除合理怀疑。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奉行自由心证原则,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未作类似英美法的严格划分。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将刑事诉讼中的待证事实分为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并以此区分刑事诉讼中不同的证明标准。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87条规定:“证明的对象:(一)与控告、可罚性、刑罚或保安处分的适用有关的事实均为证明的对象;(二)与适用诉讼规范有关的事实也是证明对象;(三)如果设立了民事当事人,与因犯罪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有关的事实也是证明的对象”。日本学者认为,需要证实的事实由实体法上的事实和诉讼法上的事实组成。实体法上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构成要件事实、处罚条件事实)和犯罪事实以外的事实(影响法律上构成犯罪的事实、法律上加重减免理由的事实、酌情减轻处罚或缓期执行条件的事实)。诉讼法上的事实包括:作为诉讼条件的事实、作为诉讼行为要件的事实、证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事实和其他诉讼法上的其他事实。对于实体法事实中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倾向于从重、加重被告人刑罚的事实,要进行严格证明,其他的实体法事实则可进行自由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只需进行自由证明。(注: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严格证明指依据诉讼法规定的有证明力的证据并经适当形式的证据调查程序得出的证明;自由证明系指依据证明力不完全充足、调查证据的程序不严格所得出的证明。(注:参见[日]松岗正章:《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法学译丛》1981年第5期。)在德国刑事证据理论中,区分“证明”与“说明”两个概念,前者用于对实体法事实的要求,后者则用于对程序法事实的要求。此外,涉及对定罪量刑有意义的情节,需要进行“严格证明”;对于不涉及定罪量刑的情节,可以进行自由证明。(注: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诉讼制度中,有证明与释明之分。“得生强固之心证(信其确实如此者),谓之证明。仅生薄弱之心证,亦即发生低度之确信(信其大概如此者),谓之释明”。(注:《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六册《法律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9月第3版,第452页。)须释明的事实,多为程序法上的事实。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将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表述为“内心确信”。(注: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04条,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61条,李昌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关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中刑事证明标准的划分,我们大致可作如下比较分析:其一,英美法系中的证明标准偏重于从诉讼阶段上进行划分,证明标准成为不同诉讼阶段的主导者对案件进行实体处理——逮捕、搜查、起诉、定罪等的尺度;大陆法系中的证明标准偏重于从证明对象上进行划分,在理论上不同诉讼阶段遵循不同证明标准的观念并不十分明确,(注:我国有学者从《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的相关规定推导出德国、法国在不同诉讼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结论。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李学宽、张小玲:《关于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问题的探讨》,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证明标准的划分主要立足于审判程序。其二,从划分证明标准的依据看,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根据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划分;而在大陆法中,主要根据证明的方式及法官心证(确信)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其三,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庭审判阶段,对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均要求达到诉讼证明标准的最高程度,尽管前者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后者表述为“内心确信”。其四,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中,对证明标准的关注一般以陪审团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裁决为终结;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不仅关注法庭定罪的证明标准,而且关注量刑的证明标准。其五,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中,对于控辩双方的证明程度有着不同的要求,控诉方的有罪证明需达到“
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被告人关于正当防卫、精神错乱等方面的辩护获采纳只需达到“优势证明”的程度。在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举证责任的规定不如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明晰。如在法国,对于被告人是否负举证责任问题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从法院的判例看,在涉及行为人不可归罪的原因时,将举证责任加在受到追诉的一方。(注: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以下。)日本将举证责任分为客观的举证责任(实质的举证责任)和主观的举证责任(形式的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原则上检察官负有客观的举证责任,这种客观举证责任不能转移给被告人。在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检察官也有举证责任。但是,被告人有责任形成上述事由存在的争点,即被告人负有主观举证责任。此外,即使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检察官认为这种事实不存在时,负有客观举证责任。但是,在例外情况下,客观举证责任也可以转移给被告人。在被告人负有客观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被告人不必证明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只需达到证据优势的程度即可。(注: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综合英美法与大陆法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可以说,证明标准的分类主要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等三个方面得到了体现。我们可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略作分析。
第一,关于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立案的证明标准表述为“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86条);逮捕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第60条);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均表述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62条)。可见,英美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第二,关于不同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未对证明对象做出明确规定。从理论研究方面看,通说认为,刑事证明对象的基本部分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实体法事实;同时,从广义上说,某些程序法事实如关于管辖、回避、强制措施、诉讼期限、违反法定程序等应当作为证明对象。(注: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以下。)《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对案件中的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至于诉讼程序上的某些事实,立法则未作如此要求。(注: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可见,大陆法中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在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得到了承认。实体法事实包括定罪的事实和量刑的事实,定罪的事实需要严格证明,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于量刑情节,也须进行严格的证明。(注:参见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页。)日本学者认为:“量刑情节只通过自由证明即可。但是,倾向于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节事实需要进行严格证明”。(注: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笔者赞同日本学者的解释。因为刑事诉讼中所奉行的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原则,在证明要求问题上体现为: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实体法事实需要进行严格证明,而有利于被告人的实体法事实只需自由证明即可。
第三,关于不同证明主体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证据理论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举证责任)。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的例外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除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外,我国刑法中是否还存在着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其他情形?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如果提出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他是否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他对有关事实应当证明到何种程度?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在英美及日本等国家,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根据是:在某些情况下,由被告人举证更为方便。(注: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贯彻有程度上的差异。在举证责任问题上,法律关于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例外规定意味着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某种减损。但是,司法实践中有时存在着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更为方便也更为合理的情形。比如,为了惩治腐败,在此类诉讼中颠倒举证责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实践。(注:第8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反腐败的实际措施》第70条指出:在反腐败的斗争中,颠倒举证责任这项程序性办法可能在本国内具有巨大的重要意义,它不公正或犯错误的可能性很小。)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中,运用推定原则来确定环境污染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从而将推翻这种推定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被告人。(注:如日本1970年颁布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规定:“如果某人由于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致使公民的生命或健康受到严重的危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地域内正在发生由于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生命和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总之,在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显然需要对被告人举证的证明标准做出回答。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作为定罪标准的“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起诉标准的“可能的原因”以及作为辩护标准的“优势证明”。在大陆法中,将证明分为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严格证明要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自由证明要求“低度的确信”(相当于英美法中的优势证明)。“内心确信”与“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大体相似。从目前的情况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不仅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适用,它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越了英美法系国家,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1984年通过的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一般性意见中指出:“有罪不能被推定,除非指控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注:CCPR General Comment 13.)“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被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形成于17世纪末期,它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从其形成的理论背景来看,宗教和哲学中的认识论起了重要的作用。17世纪的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博物学家对可能性、确定性、真实的本质、知识的来源等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一些神学家和博物学家将“知识”分为三种:物理知识,源于直接的感性材料;数学知识,建立在逻辑证明基础之上,如几何学中的证明;道德知识,建立在证言和第二手的感性报告基础之上。(注:CCPR General Comment 13.)以洛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则将人类知识分为两个领域,认为在第一个领域可能达到数学证明的绝对确定性,如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之和;在另一个领域,即对事件进行实证证明的领域,达到绝对的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在关于事件的领域,正因为绝对的确定性不可能达到,我们不应将每个事物仅视为一种猜测或者一种意见。在这个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可能性。当我们所得到的证据的量和质增加时,我们达到越来越高的可能性。在实证领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确定性,在这一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可能性,称之为“道德上的确定性”,一种没有理由怀疑的确定性。洛克关于可能性问题的论述,为刑事诉讼中区分不同程度的证明标准提供了主要的认识论基础。在刑事诉讼中,从逮捕、搜查和扣押,到起诉、审判,随着证据的质和量的变化,可能性的程度发生着移转,从而在人的内心形成不同的判断,法律上将其表述为怀疑、可能的原因、排除合理怀疑等。作为实证证明的最高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强调有罪结论的可靠性、确定性,只不过它将这种确定性称之为“道德上的确定性”,以区别于数学证明中的“绝对的确定性”。洛克的实证主义哲学与修谟的怀疑主义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怀疑主义认为,无论有多少证据,都不能排除怀疑。
长期以来,我国有不少学者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对英美法系国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批判,认为它是“相对真实”的证明标准的法律表述;它允许法官在不完全或不绝对确定的情况下,判定被告人有罪;这种确定性不高的证明标准是导致英美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错判的原因之一;“排除合理怀疑”不承认“排他性”要求等。(注:参见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此外,他们还认为这一标准“是哲学上不可知论的反映,为法官的主观随意性开了方便之门,理论上是错误的,对实践是有害的”。(注: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笔者认为,这种批判有过于简单化之嫌。从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合力的作用,宗教、哲学、修辞学、历史学、决疑论、大陆法传统乃至政治方面的因素等对证明标准的形成有着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单纯地将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归结为哲学上的不可知论,遮蔽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背后所隐含的丰富的智识背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成为英美刑事司法制度的特征已逾200年,它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所根植的带有综合性或普遍性的智识土壤。“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非不追求诉讼证明的“确定性”、“排他性”,相反,它十分强调诉讼证明的“确定性”,只不过它将这种确定性称之为“道德上的确定性”。在英美法律史上,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旨在为刑事司法中发现事实真相的假设建立一种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使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得到法律的保护。(注:See Barbara J.Shapiro,"Beyond Reasonable Doubt'And'Probable Caus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glo-American Law of Evid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252.)为法官擅断开方便之门、允许法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判定被告人有罪,这些恰恰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极力想避免的情况。我国奉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司法人员只要依法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事实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注:参见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这里所说的“客观真实”的含义是一种“绝对的确定性”。在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基础问题上,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英美法系的学者认为,在进行实证证明的领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确定性”;而我国现行证据理论则认为,在进行实证证明的领域,能够达到类似于数学证明的“绝对的确定性”。而且,我国立法本着对刑事证明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规定刑事诉讼三阶段均要遵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如果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绝对的确定性”、“客观的确定性”,那么,要求在审判前的程序中就达到这种最高程度的证明,显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既然侦查程序、起诉程序就要求结论绝对正确,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审判程序呢?我国在证明标准问题上过分强调“绝对的确定性”,忽视了司法人员对案件认识的“渐进性”和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未能将认识论中的“可能性”范畴纳入研究的视野,因而得出了诉讼三阶段证明标准同一的结论。相比较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证明标准中所体现的可能性与确定性思想为刑事证明过程——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过程提供了较为恰当的理论解释。
三、刑事证明标准的实践意义
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探讨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证明标准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于事实的审理者而言,证明标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另一方面,对证明主体而言,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法定标准是其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前提。英国证据法学者摩菲认为:“‘证明标准’术语,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中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或是他为获得有利于己的认定而对某个争议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标准。所以,从卸除证明责任的角度看,它是证据的质量和说服力应达到的尺度”。(注:转引自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英美法系国家对刑事证明标准作了不同层次的划分,在法律上作了不同的表述。然而,证明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对证明标准的适用牵涉到对可能性或确定性刻度的具体把握。如西方学者所言,排除合理怀疑“表面上简单,实际上却是一个复杂、微妙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于那些必须向陪审团解释其含义的法官来说尤其困难”,“证明标准是那种容易识别、难以解释、更难以适用的法律概念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注:[加拿大]阿兰·曼森:《加拿大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2002年北京刑事证据法国际研讨会论文。)
在美国存在大、小陪审团制度,大陪审团适用“可能的原因”作为起诉标准,小陪审团则适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定罪标准。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的发展与陪审团制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法官面临着向陪审团发出司法指令、向他们解释证明标准的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定罪标准的表述经历了“令人满意的良知”或“令人满意的相信”、“令人满意的认知”或“令人满意的理解”到“道德上的确定性”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变化过程。早期将证明标准表述为“令人满意的良知”,因为在当时,“良知”被认为是理性司法的重要特征。后来,在美国的许多司法区,将“道德上的确定性”和“排除合理怀疑”放在一起使用,但是,也有一些州考虑到“道德上的确定性”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再使用,外行陪审员对其含义难以有统一的理解,因此,在法官的司法指令中删除了“道德上的确定性”一词,只保留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注:See Barbara J.Shapiro,"Beyond Reasonable Doubt'And'Probable Caus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glo-American Law of Evid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274.)应当说明的是,无论对定罪标准如何表述,其基本的含义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要求陪审团对证据进行合理考虑,在“确定”或“确信”被告人有罪后,才能做出有罪裁决。
与定罪标准相比,对起诉标准的把握更加困难。“可能的原因”是一个介于“怀疑”与“确信”之间的概念,其可能性程度高于“怀疑”、、低于“确信”,具有某种游移性。这种状态使起诉标准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导致实际适用上的两难处境:假如滑向小陪审团的定罪标准,结果将是两种陪审团程序可以相互替代;假如滑向“怀疑”的证明标准,将会削弱其对不当指控的控制功能,因而不能对被指控者提供现实的保护。在这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停靠点——一种明确的、中间程度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可能的原因”失败于解决起诉标准所面临的困境,却又假定这种困境已经获得解决。(注:See Barbara J.Shapiro,"Beyond Reasonable Doubt'And'Probable Caus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glo-American Law of Evid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前言”部分。)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起诉标准的这种不稳定性曾经引起政党间的纷争,导致大陪审团地位的动荡。后来,作为妥协的结果,将起诉标准表述为“表面上证据确凿”,试图描述一种中间状态的可能性。但它所采用的方法不是对“可能性”一词增加限制语,而是规定一种法律程序,以达到中间程度的可能性,即大陪审团通过听取单方意见做出起诉决定,它也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相信,这种相信高于“怀疑”和“优势证明”,但低于小陪审团通过听取双方意见后所达到的“排除合理怀疑”的相信。(注:See Barbara J.Shapiro,"Beyond Reasonable Doubt'And'Probable Caus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glo-American Law of Evide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113.)英美国家在起诉标准上的探索,是为了使大陪审团在理论和制度层面上获得一种稳定的地位。
在我国,首先需要承认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与确定性理论,在此基础上区分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并在立法上做出相应的表述。在笔者看来,所谓“道德上的确定性”与“绝对的确定性”的分歧与争论在法律规范层面上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实际上,无论在英美,还是在我国,法律均要求有罪证明要达到一种最高程度的“确定性”。“道德上的确定性”和“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国家的学者对实证证明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一种表述,我国学者将这种确定性视为“绝对的确定性”,并不意味着证明标准的实质性提高。从理论上看,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并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关键是,我国如想移植英美国家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表述方式,不能不考虑其存在的语境。英美国家的定罪标准、起诉标准在表述方式上所经历的变化本身说明,刑事证明标准的表述应当考虑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比如,关于定罪标准,我们需要通过一种表述,传递有罪证明要求达到“最高程度的确定性”这一信息,同时,又要做到容易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笔者认为,“确定无疑”、“确信无疑”等表述就能满足上述要求,而引进“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方式,则可能导致实际把握的证明标准的降低,因为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下,人们对“何为合理怀疑”难以形成一致的认识。关于起诉标准,仍旧可以使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表达一种接近于定罪标准但又略低于定罪标准的证明要求,类似于英美国家的“表面上证据确凿”。至于对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标准及被告方举证的证明标准,则可以借用英美的“优势证据”的表述。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对证明标准的表述是一个问题,在实践中如何把握证明标准则是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可以说更为复杂,也更具有实际意义。在何种情况下、依据哪些证据就可以认为达到证明标准,如何防止“理论上的高标准、执行中的低标准”是我国今后在研究刑事证明标准时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