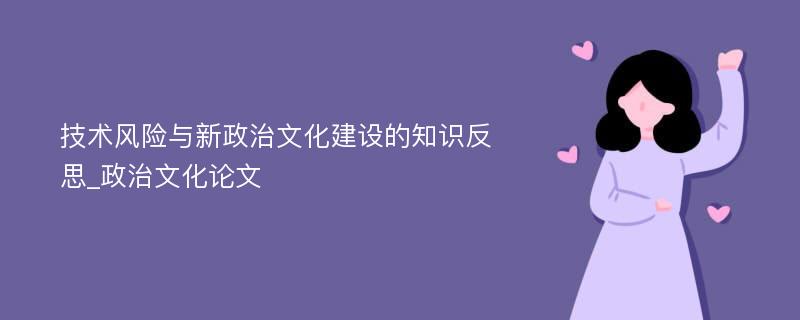
技术风险的知识反思与新政治文化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政治论文,知识论文,文化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20-05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使我们深刻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即科技给我们带来财富、安全、健康等的同时,也带来了副作用,如生态恶化、核危机、高科技犯罪等。科技发展问题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家普遍关注的问题,风险社会理论即是对科技(当然不仅仅是科技)风险进行研究的一种理论。“风险社会”是当代社会理论家贝克、吉登斯等人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风险”就其词义来说,意味着机遇与可能的危险并存,意味着不确定性。既然存在着可能的危险,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去尽量降低风险所带来的可能危害,这是如何规避风险的问题。
一、技术风险的特质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出版德文版《风险社会》(Die Risikogesellschaft)一书,首次使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中所出现的人类危机,思考关于人类的生存、生态启蒙、社会结构等问题。而安东尼·吉登斯也在《现代性的后果》(1990年)中从现代性的视角同样思考了风险社会议题。此后,风险社会相关研究得到了不断拓展,就贝克而言,后来他侧重全球风险社会理论,而斯科特·拉什等则提出了风险文化的概念,如此种种,风险社会理论也成为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至于何谓“风险”,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表述,例如,卢曼认为“风险”是由高技术及其决策(计划)的累积效应引发的,是“计划的复杂性产生新型的不安全”,“这种计划含有很高程度的技术上显著的不确定性”。[1](P21)可见,风险含有“不安全”、“不确定性”的意思。经济学家奈特(Knight)在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对“风险”与“不确定性”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他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代理人面对的随机状态可以用某种具体的概率值表示,那么,这种随机状态就称为风险;如果一个经济代理人面对的随机状态不能够(至少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以某种实际的概率值表述出可能产生的结果,这种随机状态则称为不确定性。[2](P11)贝克认为,“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他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3](P19)而贝克、吉登斯同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强调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即风险“是人为的不确定性”。可见,风险与现代化相关,是现代化的风险,是与“危险”、“不安全”、“威胁”、“不确定性”等相关的一个概念。其实,风险按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有学者按现有的研究,概括了四种分类标准:按分布的领域来分,风险可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个人的、道德的等;按来源来分,可分为自然具有的风险、技术引发的风险、制度引发的风险、政策或决策引发的风险及个人引发的风险;还有是从认知程度及风险的历史形态来划分等。[2](P19-22)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培罗(C.Perrow)所言:“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创造了前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却掩盖了社会潜在的巨大风险;而被认为是‘社会发展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的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当代社会最大的风险源。”[4](P25)笔者以为,这是风险社会的实质所在,换言之,风险的关键是由于技术而引发的不确定性,具有“不安全”、“恐惧”、“危险”等具体特质,如核危机、生态危机、伦理危机等,当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同样喻示着克服和规避风险的可能。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风险正是由技术引发的风险。
技术风险的提出及其对策性反思应该是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的根本旨趣,而“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日益变得自我批评的现代性知识的政治理论”。[5](P106)因此,笔者认为,对技术风险问题的研究,应该从知识与政治的角度展开。
二、风险的现代性知识反思
风险理论的提出使人类惊愕,也使人类开始了一种自身生存论的反思。固然,人类的自我反思古已有之,哲学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一典型例证,但贝克指出:“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差别首先在于知识的差距——那是说,对于发达的工业现代性之危险的反思的差距。”[5](P106)这表明,知识的意义在于反思,反思是基于生存论意义上的,是生存方式的反思。19世纪的社会理论将自然与社会置于对立之中,因此当时工业社会的知识之思就集中于如何使生存工具(科学技术)向外(自然界)延伸与扩展,集中于生存工具自身的自我扩张之中;而风险社会的知识反思则是基于工业社会的恶果上之集中于生存工具与人类的未来意义,集中于生存工具的发展对人类与自然之(未来)存在意义和价值上的思考。由于“‘反思现代化’在本质上(保持这个词的原意)与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础、后果和问题的知识(反思)紧密相关”,[5](P142)因此,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知识的反思集中于风险产生、感知和规避三个层面上。
1.风险产生的知识反思。贝克认为,“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不再是那些脱离了人的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3](P225)在风险问题上,知识的本质应得到必要的追问,我们人类所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在其构成要素和实际作用上必须进行反思。
就大多数人而言,对知识的理解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命题所预示的就是,只有自然科学才能体现人类的力量,体现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此说明现代社会的建构力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知识观在现代技术社会被进一步强化,有如利奥塔所言,“知识只有被转译为信息量才能进入新的渠道,成为可操作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一切构成知识的东西,如果不能这样转译,就会遭到遗弃。”[6](P2)这可谓是利奥塔所批判的当今人们对“知识的划界”准则,似乎知识的建构成了一种工具操作及其复杂化过程。人类知识的工具化趋势和可操作性诉求使得知识缺乏一种必要的自我反思能力,这样的知识体系不断庞大,指向自然的目标日益明显并日益微观,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这一过程似乎标识着人类的发展与文明的程度,其实这正是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技术知识成为知识的唯一形态,成为人类看待世界的唯一“世界观”,似乎世界就是一种技术要素的构造。因此,贝克指出:“文明的危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这是些采取化学公式、生物语境和医学诊断概念的危险。当然,这样的知识建构并不能使它们减低危险性”,[3](P59)这就是说,风险来自于诸如化学公式的科学思维模式,来自于缺乏对科技自身发展的审视、评价等反思的思维,同样也来自于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审美追求,此类的知识体系建构并不能减低危险的存在,其实这正是风险的重要成因。
2.风险感知与判定上的知识反思。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的现代文明社会也将风险锁定在专业知识的封闭和局限中,广大民众只能在生活中感知到风险的存在。“风险就是知识中的风险,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3](P64)在民众的生活中,茶叶中的滴滴涕,蛋糕中的甲醛,食品中的苏丹红,牛奶中的三聚氰胺,甚至一片绿叶的枯黄和一棵小树的垂死,都是风险存在的直接证明;而原本被看作财富源泉的化学,现在成为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毒物,原子能技术和基因技术,现在都成为不可预测的危险源泉而间接地渗入我们的生活。然而,这些风险只能由科学家和专业知识来揭示和解释,它们超出了广大民众的知识范围,人们只能感到害怕和威胁,只能感知风险的存在。
人们对技术风险的感知包括两大类问题。第一,是我们的生活风险加剧了,还是我们对风险的敏感度增加了?是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还是我们的(风险)观念变化了?面对以上列举的广大民众生活中的各种风险,我们应该感觉到,是风险的技术化程度在增加,是我们借助科技在催生着产品的数量或改变着产品的性质,而科学技术的这一动力与方向又是在资本利益的趋势下进行的。于是,“风险不仅仅能被(广告或类似的东西)唤起,而且能够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简言之:被操纵。”[3](P65)这种由资本利益驱使的风险在生产,也在产生,它不断侵蚀着我们的生活,加剧着生活的风险化趋势,使得当代的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贫困化”中,它不是物质财富的贫困,而是生存的威胁、恐惧的贫困,是人类生存上无“根”的恐惧,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海德格尔),一种关涉人的“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吉登斯)。大多数人依靠科学家或知识专家对种种风险的揭示和解释,自己在各种风险的专业知识上一无所知。第二,我们该如何看待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专业知识的封闭性使风险超越了民众的知识范围,民众只能依赖科学家或知识专家对种种风险的判定和解释,于是,风险的界定、风险程度的判定都取决于他们,如对于食物中的农药及其他化学产品和杀虫剂在多大程度上被判定为污染?对于牛奶中三聚氰胺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人体而导致疾病?毒素对于人身体的“可接受程度(值)”是一个科学事实,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定心丸或是一个伦理问题、社会政治问题?农药和三聚氰胺对人体的危害是否还有其他潜藏而尚未被检测和发现的因素?这些都是科学知识问题,都在科学家和知识专家的话语权的掌控之中。“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3](P82)人成为科学的实验品,成为科技风险的承担者。显然,在风险社会中,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与知识的可靠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成为我们不得不关注的焦点。因此,科学家在他们的新成果中应该具有一种长远的社会考虑,知识专家对新产品的研制或检验应该负有社会责任,广大民众对风险的感知与理解也应该突破自身的知识局限,并超越专业知识的界限。诚然,广大民众需要新的知识结构,更呼唤对科学家或知识专家之科学行为和科学评价的制度建设和伦理建构。贝克认为,“对风险的处置促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一种横跨并超越了所有精心设计并加以维护的边界的协作。”[3](P84)这是在风险社会下现代性反思之后对知识发展的要求。
3.风险规避的知识反思。贝克的风险理论显然包含着对当前知识体系建构的批判,它促使我们对知识的辩证性思考,以寻求风险规避的知识途径。伽达默尔认为,“辩证法并不是那种能使某个软弱东西成为强大东西的论证艺术和讲演艺术,而是那种能从事物本身出发增强反对意见的思考艺术。”[7](P472)换句话说,辩证法是探究对立的东西,是在对立的意见中寻求另一种可能,是在社会的强音中倾听弱音,以寻求和谐的社会音符。在当今技术时代的强音里,经验性的科学技术似乎就是“科学”的代名词,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它是人文与社会科学效仿的对象,直至借用或移植,似乎唯有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建构才是“客观的”和“科学的”,才被纳入“科学知识”的体系之中,冠冕堂皇地“出场”在公共领域。知识体系的建构成为经验材料的堆积。然而,如上所述,贝克认为,“文明的危险只在科学的思维中存在,不能直接被经验到。”化学式的自然科学思维正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产生出的风险却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风险的存在跨越了理论和实践的区别,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专业的能力和制度化的责任,跨越了价值和事实的区别(并因此跨越了伦理和科学的区别),并且跨越了似乎是由制度区分开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的领域。”[3](P84)风险问题的跨越性,促逼着我们对知识的科技性和工具性进行反思,促逼着我们对知识话语体系建构的宽容性与多样性的期盼,促逼着我们对风险规避的跨越性追求。“为了避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破坏,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不只是技术的外部影响,而且也包括无限制的科技发展的逻辑。技术的人道化包括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8](P149)因此,“技术的人道化”呼吁根本地改变了技术时代对知识的片面认识,知识的标准“划界”应该拓展,应该更具全面性、反思性、伦理性乃至审美性,在技术时代的强音中奏响呼唤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动心音符,让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成为一门科学的经典论述,再一次成为我们知识建构和发展的指南针。
三、走向新政治文化的建构
技术风险的规避究竟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技术专家与政治家的对话平衡问题?或者是他们之间角色的融合?这或许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但或许更是一个政治文化的建构问题。假如风险是全球性的,那么风险社会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意义上,在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意义上,政治文化的建构应该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有效方法之一。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事实上,技术问题很难同政治问题分开,而进入政治舞台的科学家们必须既是鼓吹者又是技术顾问。但是这一方面不能掩盖另一方面。……都必须在公开和详尽的政治辩论后才能作出技术决策。”[9](P438)作为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描绘者,丹尼尔·贝尔把高新技术看作后工业社会最重要的轴心,而将其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诉诸政治论辩,这就使得技术问题向政治问题转化。
在贝克看来,风险是依赖于政治决策的,是以决策为前提的。他说:“全球风险社会各种灾难在政治层面上的爆发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全球风险社会的核心涵义取决于大众媒体,取决于政治决策,取决于官僚机构,而未必取决于事故和灾难所发生的地点。”[10](P72)“在全球风险社会中,风险定义的政治学和亚政治变得特别重要。……它强调风险的新的权力博弈(power game)和它的元标准(matenorm):谁,以及在一个人为不确定的时代基于社会来定义一种产品、一种技术的风险?”[5](P5)风险依赖于决策,这预示着一条解决风险的路径,一条对话的政治路径,于是,“风险社会的理论是日益变得自我批评的现代性知识的政治理论”。[5](P106)因此,应对风险社会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对话的政治问题。贝克的“亚政治”概念就是一个全面对话的政治概念。“亚政治”是相对于“政治”而言的,它是指超越了政府的、议会的和政党政治的形式;它走出了政治家的活动场域,将风险问题变成由大众关心的社会生活问题,一个人类的生存问题;它是现时代的人们在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展开对话的政治活动。在贝克那里,亚政治意味着民众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社会政治,塑造社会;它是建立在个人积极参与政治的基础上,是一种自觉的大众政治,是一种平民政治;它是民众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与关切活动。这种亚政治之所以是“新”的,原因正如贝克所言,面对全球风险,“新就新在这种全球联盟处于超议会力量和议会力量之间、市民和政府之间,为的是一个具有更高合法性的理由:挽救世界环境。”“全球威胁产生全球风险社区——至少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的产物。”[5](P52)因此,这种新的政治文化建构就是力图构建一个全球化的大众政治,而在多角色中展开的多角度对话是其宗旨与核心。
面对风险社会,贝克寻求的是政治道路,以政治意识来规避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选择一条以建构政治文化的道路来规避风险。所谓的“政治文化应当被理解为不同向度之间的一种平衡互动”,这种“平衡互动”建立在全方位人员之间,这种“政治文化”所培养和塑造的人民大众应该具有这样的关键能力,即“能够明智地评价什么是足以维持和改进各向度之间平衡互动的”。[11](P71-22)这就需要人们在对话、商谈和沟通的实践中来培养和塑造。这种政治文化的追求被哈贝马斯称为建构“世界政府”,而罗蒂2004年在复旦大学做过题为“哲学家的展望:2050年的中国、美国与世界”的报告,其中,他说要有一个新的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就是他所说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最重大任务是维护世界和平,这个“和平”包括人类对风险的规避。可见,政治文化的方式可能是当代众多社会理论家面对风险危机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
总之,为了规避技术带来的风险,人类需要全面反思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全方位地关注风险的产生及其知识背景;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人类选择某种新政治文化方式也是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政治文化之路又可以维护和创造新的人类合作形式和可能;风险是危(险)也是机(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技术风险的产生意味着人类曾经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分离,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而今风险的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威胁的同时,也促使人类不得不消除他们之间的分离和与自然的分离,去实现人类共同合理性的探求,并共同承担社会责任,即实现人类风险的共同承担和共同规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