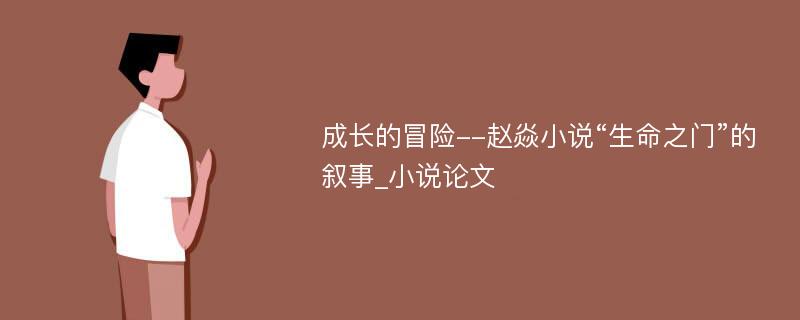
一场成长叙述的冒险——评赵言长篇小说《生命之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之门论文,生命论文,评赵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众多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农村题材、都市题材,还是颇为流行的农民工进城题材,大都存在着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文化视野,也就是说,它们大都以城/乡、城里人/农民及其文化心理冲突为故事展开的推动力。在这一视域之下,现代与保守、文明与愚昧、中心与边缘、道德与欲望等诸种矛盾乃至断裂得以展现,人性在现实面前的种种困境和悖论由之被凸显出来,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也许忽视了在20世纪末以来的文化转型中,许许多多的生存形态背后还有着突破上述二元结构的生命轨迹。就人的存在而言,生命感受的整体性与生命之流的连续性,较之突出人性的断裂或矛盾也许更能接近这个时代的生存本相,更有利于展现生命的深度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赵言长篇新作《生命之门》(《钟山》2007年长篇小说专号B卷)为读者制造了一场不无惊心动魄的叙述冒险,并通过这场冒险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敞开理解某一种人生的生命之门。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杭州东北郊一个叫乔司的小镇上,主人公则是一个从13岁成长到17岁的“小帅哥”。时间上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空间上是各种生存形态最为集中的城乡结合部,心理上则是生命感受最为敏感和人格定型最为关键的青春期,在这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样的三维审美结构无疑为小说叙述平添了几分难度、深度和重量,也预示着在这块值得开垦的时空区域读者必将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悟。
诚如人所言,小说可贵的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而是一场叙述的冒险,《生命之门》的叙述冒险不在于制造复杂的人物冲突与人性悖谬,而在于抛开道德困境的思考拟或人性标准的使用,竭力将人物置于生命流程本身,缓缓地展现生活状态的面相。小说叙述者声明,当站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上,无论是回头看还是朝前走,人生的道路都是注定的,命运就在那里。“所以说,我所知的一切,正如柏拉图所说的,只不过是来自于别的地方先期存在的记忆。我正在付出的劳动,并非人们指责的那样是为了表达自以为是的道德困境,而是通过回忆把记忆中的‘真实’事件还原并重新呈现给读者。”也许,这里的意思是要于叙述的无声处让人们听到生活本身的惊雷,或者还要反过来,当惊雷存在于平淡的叙述中时,生命才回到真实,也回到真实的重量。
于是,在小说平静而不无压抑的叙述中我们认识了主人公阿凯及乔司小镇上的众生群像。如果没有叙述者在“真诚”上的积极甚至刻意的努力,读者也许根本无法承认阿凯的故事有多大的可信性:从读小学五年级开始到读高中后被开除,从一米六五长到一米七五,这个人见人爱的小子竟然先后与五六个女性发生了关系,而且使她们其中的三个生出了四个孩子。小说没有回避性描写,但是似乎并没有吸引读者眼球的嫌疑,性在故事中总是那么“自然地”就发生了,是那么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符合人物关系及其环境。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筒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他们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总起来看,阿凯的性格特征在于既懵懵懂懂又自以为是,既散漫无知又活跃可爱,既不求上进又自视甚高,既敏感冲动又似乎提前看透了人生,既缺乏自律与道德意识又良心未泯。平时他热衷于与网友在电脑上玩网络游戏“理想帝国”,在虚拟的世界里设计理想的王国,在现实世界中则毫无理想可言。
无疑的,小说完全可以从堕落变态的角度理解和塑造阿凯,从性滥交的角度批判阿凯及其周围的人生形式,然而小说的叙述者无意于也“无力用我的人性的卷尺来丈量阿凯的人生”,“俗世的道德准则均是陈词滥调,而我所作的努力仅仅是借助文字的力量,来引导读者对生命进行严肃的思考而已。”这种努力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回到阿凯的生命视角,回到他身心的混沌状态,从本能来感受自我、他人和生命。13岁的阿凯本能地“喜欢小悦身上草莓的香味,喜欢和小悦一起躲在被窝里,喜欢吃小悦的奶头。每每想起春节和小悦睡在一起,阿凯总心跳加快满脸发热手心出汗,还慌张地探视着周围,生怕被人发现了他的秘密。”大他十岁的小悦唤醒了阿凯朦胧的性意识,而对于一个近乎早熟的少年来说,性意识一旦被唤醒,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再加上周围应接不暇的诱惑,那么就会毫无遮拦地疯长。
根据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在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能量转移就是心理学上的所谓“移位”。小说就描写到了父亲张志强(名义上的父亲)的意外死去给阿凯带来的压抑及其“移位”:张志强的死如同夜色中的一排路灯突然灭了一盏,虽然眼前的路还在,可是阿凯总觉得路灯有一天会全部熄灭的,这让他非常害怕。“阿凯需要有人来安慰,需要有人贴在他身边,也需要释放悲伤的情绪。”于是,就在父亲刚死的一天晚上,阿凯与小悦隆重而成功地完成了交媾。此后,风流寡妇徐丽萍的“诱奸”,妓女灵灵的调戏和“犯贱”的投怀送抱,语文老师李老师顶在阿凯肩膀上的胸脯,大二女生童童对他开放的性行为,等等,这些无疑都构成了阿凯生命感受的根本。“童童姐姐让自己懂得了什么是性高潮,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男人,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女人喜欢的男人”。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陈上尉(李老师的丈夫)走后,阿凯嘴边常挂着一句话——“李老师真漂亮,李老师,你的身材和皮肤真好看”。因为与小悦与童童,尤其是与徐丽萍有过肌肤之亲,阿凯什么都明白了。所以,每次跟李老师单独在一起,手拉着手的时候,阿凯就会用这样那样的俏皮话,逗得神色沉闷的李老师开心起来。这样的话李老师想听也喜欢听,陈上尉不肯说,阿凯就是要说,就是要说得李老师开心起来。可见,人小鬼大的阿凯过早地就成了情场上的老手。
然而,以身体和性为根本的生命感受占据了阿凯心理空间的同时,也挤走了他本应有的精神空间的扩大。这位情场老手的思想意识却始终是混沌和麻木的组合,似乎离开身体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小说通过一个对话场景展现了这一状态:“……钟大树沉思了半分钟,然后说,不光光是练肌肉,要练好身体,你说说练好了身体有什么用,我告诉你练好身体的用处大了去了。比如说……阿凯抢着说,比如说,做爱……大家面面相觑,又都睁大了眼睛盯着阿凯。”小说将阿凯的麻木刻划得淋漓尽致,当听说因子被查出怀孕引起轩然大波的时候,阿凯也不过是“心里还是有点出乎意料地紧张,总怀疑这件事多少与自己有点牵连,甚至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即使当因子的爸爸冲到家里来要打死这个“小死尸”的时候,他还不忘“用冲动和激情来淡化紧张的气氛,用欲望和疯狂来填充空洞的内心”。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经历了这么多的惊吓后,他在出逃的时候还不忘给远在美国的“老板爸爸”发短信:“美国好玩吗/大西洋飓风味道好极了是吗/呵呵!”麻木的快乐与快乐的麻木几乎构成了阿凯生命意识的全部内容。
用情欲泛滥以及物欲膨胀来形容乔司的生存形式似乎是多余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这个地方的生命常态,成为一种自然,我们也可以说阿凯的个性被扭曲了,然而在某种典型环境之下,扭曲的成长同样也是一种必然,一种“自然”的生长。惟其如此,典型的环境对于像阿凯、因子这样的少年来说,不只是一种影响,更是一种渗透,一种深刻的对于生命本身的渗透,这也许是作者极尽平静之叙述而又不乏伤感的动因之一。小说写道,“爸爸说这个世界变坏了,妈妈说这个世界让人提心吊胆,因子则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不仅对于因子来说,这个世界不再有标准答案,对于整个乔司镇的人来说,这世界也没有了标准答案;不仅人们的社会行为、社会身份失去了依据,人们的生命本身也失去了根本。更大的问题在于,对于因子或者阿凯的爸爸、妈妈一代来说,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动,但对于阿凯们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说爸爸、妈妈一代毕竟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人性的异化,那么阿凯们的真实感受则是这就是人性;换言之,上一代人经历过道德的冲突,至少知道从善到恶的无奈或者认同,而阿凯们一开始就处于道德冲突之后的道德真空地带。因此,对于阿凯来说,几乎不存在道德堕落与否的问题,不存在善与恶的冲突问题,在其生命词典里没有这些概念,也就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的能力和意识。堕落或者变态,对阿凯来说不过就是自然生长,是阿凯的自在形态的人生形式。
无疑,这是一个可怕的发现,也是一个令人惊心的命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宁愿将此作视为一部从生命之门入手的“成长小说”和“社会问题小说”。既然触及到问题的这些层面,我们不由要追问的是,到底是谁造成了阿凯的生命形式?这一切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呢?
其实在小说叙述者即到乔司挂职锻炼三年的“我”向领导提交的报告名称中,就流露出作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旨趣之所在。报告名为《关于城乡结合部青少年生活及家庭与性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叙述者告诉我们,调查报告惹恼了领导的政治嗅觉,被勒令修改,不但因此失去了前程,连妻子也义无反顾地离婚他去。该小说便是由此报告修改为“轻松愉快的文字”所得。这一设计使得《生命之门》不但呈示出多视角叙述的特质,而且也似乎暗示作者对自己所取题材所作思考的自信。
继小说第一部各种人物出场和各个线索缓缓铺开后,小说第二部一开始就转入经济问题的叙述。信用社的沈主任被检察院带走的消息不胫而走,乔司街上一夜间流言四起。有人幸灾乐祸,有人坐立不安,也有人四处奔走打探消息。很快读者就会发现,在这个被人称作“小上海”的地方,每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背后都有一部被遮蔽的发家史,他们无一例外地在犯罪的边缘上走着钢丝,进行着各种黑暗中的交易或者欺骗。这是一个失去秩序的时空,但他们仅凭着这个地界和诸种关系网,空等着或者仅凭机遇和钻营就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小说描写道:在这里,原来的水稻田里都长出了高楼大厦,原来骑摩托车的人都开起了小轿车,原来做小裁缝的现在是服装公司的大老板,原来的小木匠只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工程一夜之间就成了什么装潢公司的董事长,原来“濒临破产”的乡镇企业厂长在政府官员面前算盘子噼里啪啦乱拨一通,一分钱不出集体的资产就转资成私营的了,年年亏损的企业马上就扭亏为盈了……张志强对这样的局势很不以为然,他接着说,乔司人只知道自己拼了命地赚钱,盖房子,办工厂,开超市,造宾馆,什么生意来钱就做什么生意,就连被抓住要坐牢要枪毙的假烟走私也做得红红火火。二十年来,乔司人的心思都放在了钞票上,再也不愿去留意青石板老街了,再也不肯提起千人坑是怎么回事了。乔司人都忘本了,开始跟日本人合伙哄抢自己人的腰包了。
当年,钟大树与张志强是一对亲密的战友,转业后,钟是邮电局的电报员,张在村办企业做财务,二人都做着本分的工作。漂亮的吴秋娣嫁给张后,几个月未见怀孕,便诱惑钟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阿凯。吴秋娣达到目的后再也不出轨,并要求钟坚决保守秘密。本来一切是平静的,但在迎来了商品经济改革的大潮后,一切都变了样,一切都被裹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潮流之中。在万富公司董事长的女儿高素珍的帮助下,钟大树摇身一变成了副总经理,后来又独自打天下,成了大树集团的老总,也成了乔司这个城乡结合部偌大的权力金钱网络的一位活跃人物。
尽管小说将这些内幕描绘的有声有色,但揭幕经济或者政治问题显然远远不是作者叙述的目的,他试图逼近的真实在于:一个失去历史的时间,和一个秩序不再的空间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经济动物主导的世界里,精神和生命何以安放?又何以成长?起初,阿凯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干爹肯为他的挥霍无条件地埋单,“他又何必去打破那只魔瓶呢,真要是打破了,他还能吃到牛排吗?阿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阿凯的语文老师与丈夫的一段对话尤其富有意味。“李老师说,老公,你爱我吗?陈上尉说,什么年代了,还说这种笑话,你以为你还是从前的小女生啊!这世上人们谈论的是做爱,而不是爱。”由此,我们不难进一步发现,乔司的那些女人主动向阿凯献身,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帅,也不仅是出于她们的“犯贱”,更是因为他的不成熟,他的懵懂,他的天然和无功利,而从成人世界,或者从自己的丈夫那里,她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爱,得不到真诚。小悦拒绝过庸俗的厨师,也讨厌那位虚伪的卖手机的小老板,但“乔司给了小悦一个阿凯,一份从未有过的好心情,她想说,乔司真是个好地方,她已经从心底里喜欢上乔司了。”而李老师似乎也是因阿凯一句“李老师,你老公真是个大傻瓜”被彻底征服了。
乔司的时代潮流对人裹挟力量是如此的强大,那些“走钢丝”的人只要能够脱险就活的有声有色、如鱼得水,而那些落伍的尚存留历史负重的人则处于被命运抛弃的边缘。爱上阿凯的女人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玩弄阿凯的女人也许毫发无损。不无落魄的张志强死了。吴秋娣死了丈夫,儿子令人担心,后来又被流氓李建中强奸所惊吓,精神失常住到庙里不复出来。李老师生下阿凯的孩子后,被丈夫识破,不堪负重,终于跳进了黄浦江漂着油腻的水里。小悦则无怨无悔地坚守在阿凯的家里,抚养着这个少年的四个孩子。……如果说他们都去了该去的地方,那么阿凯该何去何从呢?前面说过,作者似乎想暗示一种叙述的自信,然而这种自信最后仍然被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未来和无限的可能性击垮了。小说的最后部分,当叙述者边与徐丽萍做爱边听她讲述阿凯并没有死去而是去了南京这一结局时,读者与叙述者一同陷入了“茫然与无所适从”之感。生命之门到底在哪里?这尤其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作者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交给读者去参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