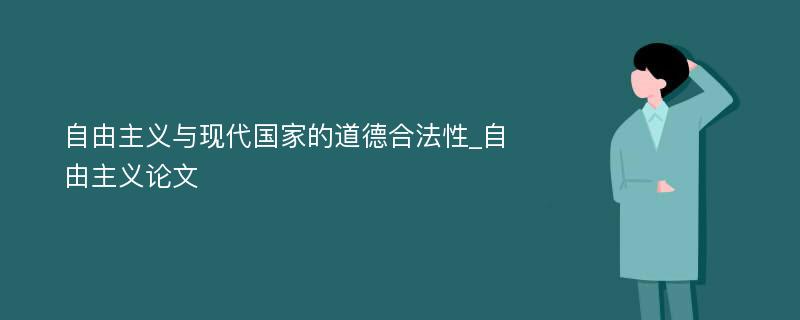
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性问题论文,正当论文,道德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 言
晚近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国家和国家主义的讨论渐有热烈之势。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讨论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一场针对国家的堂吉诃德式道德审判。事实上,国内学界对于国家的这种道德义愤,正如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主义一样,原本不是中国本土的自生自发之物,而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当今西方世界,甚至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主义早已成为一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甚至是唯一“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信奉的是十九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倾向于败坏,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败坏”。①尽管自由主义也承认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认为需要国家来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但是无论如何,“必要的恶”仍然是“恶”(evil)。只要国家是一种权力,哪怕是一种公共权力,那么对自由主义来说,国家就必然是一种“败坏”,一种道德上的“恶”。
自由主义对于国家的这种道德批判和否定,来自于它对国家与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区分。这是它的基本原则。它所预设的基本事实是,包括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在内的一切善(goods)或价值都是主观的和相对的,并且都是完全不可通约的。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因为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分歧而产生政治和社会冲突,自由主义的策略是将国家“去道德化”。具体地说,自由主义把一切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等都划入私人领域,并且将这一私人领域同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或国家分离开来。相应地,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必须保持道德的中立性:它仅仅关心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保护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却不能、也不应该干涉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
但是,一旦国家被“去道德化”,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纯粹的权力,甚至是一个赤裸裸的暴力机器,也就是霍布斯所谓的“利维坦”。对于个人来说,国家的这种强大权力首先并非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保护,而是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持久威胁和侵犯。在自由主义那里,保持道德中立性的国家本身恰恰因此失去了道德的正当性,无法在道德上为自己辩护。
自由主义的犹豫或矛盾在于,它一方面要求国家最大程度地保护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自由,为此必须赋予国家强大的权力;但另一方面,又基于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反过来否定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的道德正当性,甚至批判国家是一种道德上的“恶”。问题是,倘若国家失去了道德的正当性,倘若它在道德上被判定为“恶”,哪怕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它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个人的服从?但是,假如没有个人的服从,那么国家又如何能够反过来为个人自由提供保护?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自由主义陷入了两难。
一、现代国家的“神学政治”起源
在西方前基督教的古代时期,也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家都认为国家是一种高于个人的真实存在,都将国家看成是个人的终极目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城邦类比成“大写的人”,认为城邦作为整体比个人更高、更真实。②当亚里士多德说“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动物”时,他的意思显然不是对城邦或国家的道德批判,而是对它的完全肯定。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在城邦或国家之中做一个公民,才能培养自己的德性,实现自己的人性,并且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③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总结了古代哲学家对于国家的一般看法。有人问一位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家如何教育自己的儿子,他的回答是,“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法律的国家的公民”。④——黑格尔举这个例子当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他是极少数高度肯定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的现代政治哲学家之一。
然而,古代政治哲学对于政治世界和国家的肯定在基督教那里遭到了决定性的挑战。基督教的非政治性和反政治性就体现在它的二元论教义之中。它不仅在“上帝”与“恺撒”、精神与世俗、彼岸与此岸或“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进行了严格的二元区分,而且设定了前者相对于后者的绝对统治和优先地位。一方面,基督教从根本上排斥和否定世俗政治的地位,将它贬低为一个堕落和原罪的世界,认为真正的荣耀属于彼岸的精神世界。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认为自己担负了拯救世俗政治的使命,因此必须引导、监管进而控制世俗政治。
与这种二元论的教义相对应,基督教的教会作为一种“政体”也表现出独特的二元论色彩。教会将所有的世俗政治或国家贬低为一种世俗权力,同时将自己看成是一种精神权力,并且认为任何世间权力都应该受到精神权力的统治和领导。一方面,教会宣称精神权力高于世俗权力,对后者表不极端的鄙视、拒斥和否定,所以它拒绝将自己看成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另一方面,教会又认为自己作为上帝在世俗政治世界的代理者,因此不仅能够、而且应该甚至必须干涉世俗国家。从世俗权力的方面来看,教会似乎显得软弱无力,因为它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通常意义的官吏和臣民。但从精神权力的方面来看,教会的力量却是非常强大,因为它控制了人的精神思想和信仰,因为只有教会有权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获得拯救,是在死后走向天堂还是被罚进地狱。
恰恰由于基督教对于世俗政治的这种悖谬态度,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中世纪一千多年漫长的世间里一直陷入政治上的混乱、无序和战争。在《社会契约论》的结尾,卢梭简洁而准确地总结了基督教的政治后果:⑤
既然永远都只能有一个君主以及公民的法律,结果这种双重权力就造成了一种法理上的永恒冲突;这就使得基督教的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政体,而且人们永远也无从知道在主子与神父之间究竟应当服从哪一个。
这里,卢梭清楚地指出了现代国家的思想渊源。从根本上讲,现代国家就是为了解决西方基督教世界自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政治危机”,消除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毫无疑问,这一点既构成了现代政治哲学革命的内在动力,也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域和思想背景。
二、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国家学说
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位先驱——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他们的政治哲学思考,首先并且主要针对的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神学政治危机”。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整个基督教世界之所以长时间地陷入内乱与战争,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会对于世俗政治的干涉。诚如他在《论李维》中所说,“教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让这个地域保持四分五裂的状态”。⑥为了解决这一“神学政治危机”,马基雅维里首先将政治“去宗教化”。他认为,政治本身是一个与宗教无关的纯粹属人世界,是一个由生存、安全和荣耀的欲望或必然性主宰的世界。不仅如此,他还反过来将宗教本身“世俗化”。对他来说,宗教不再意味着一种超政治的精神力量或神圣信仰,而是一种纯粹世俗的权力欲望,因此它完全从属于政治世界。马基雅维里不仅将政治同一切超政治的道德和宗教划清界限,而且提出了独特的“国家理由”思想。他毫不隐讳地宣称,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是政治世界的最高原则,甚至是唯一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君主或统治者必须抛弃一切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考虑,即便是作恶也无所顾忌。⑦
与马基雅维里类似,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考同样具有明确和具体的现实针对性——他所针对的是英国当时的政治危机。在他看来,英国内战在本质上是一种“神学政治危机”,因为冲突和交战的各方都是以上帝的名义争夺世俗政治的统治权。这一危机的思想根源是基督教关于精神与世间或彼岸与此岸的二元论教义,而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是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冲突。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这一神学政治危机的实质:⑧
在基督教体系国家中,引起叛乱和内战最常见的借口,长期以来一直是当上帝和人的命令互相冲突时,两面同时服从的困难;这一困难迄今尚未完全解决。十分明显,当一个人接到两个互相冲突的命令时,如果知道其中一条是上帝发布的,他就应当服从那一条;另一条即是他的合法主权者(不论是君主还是主权议会)或他的父亲的命令,他都不应当服从。
霍布斯政治哲学思考的根本意图,无非是要克服宗教权威与世俗政治权威之间的对立,实现政治世界的统一与和平。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清楚地指出了霍布斯的这一意图。他说:“在所有的基督教作家之中,哲学家霍布斯是唯一一个能很好地看出了这弊病及其补救方法的人,他竟敢于提议把鹰的两个头重新结合在一起,并且重建政治的统一;因为没有政治的统一,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就永远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⑨卢梭这里所说的“鹰的两个头”,显然是指宗教权力与世俗政治权力。对于这两种权力的冲突和对立,霍布斯的解决方式是将它们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开端——人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之中,每个人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教会,而是完全属于自己,也就是说,他在自然上就是一个完全自足、排他和独立的个人。
基于“自然状态”和个人主义的哲学假定,霍布斯重新解释了国家的起源与目的。他完全拒绝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政治哲学家的目的论,否定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动物”。他认为,国家对于人来说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仅仅是一种人为的创造。人之所以建立国家,并不是为了实现他的德性完善或追求“至善”,而是仅仅为了防止最糟糕的状态或“至恶”,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在霍布斯看来,包括宗教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都可以追溯到人的自然本性。从自然上说,每个人都本能地寻求自我保存。这是他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自然权利。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每个人必须尽一切努力追求权力或力量。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和战争。就此而言,人的自然状态必然是一种战争状态,甚至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⑩置身这种极端的战争状态,每个人都随时感受到不安全、死亡甚至暴死的恐惧。出于恐惧,人与人之间订立契约,决定将除生命之外的所有自然权利都授予或让渡给国家。这就是国家的起源。
不过,霍布斯再三强调,国家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并没有参与契约的订立,因此它既不受契约的约束,也不存在违反契约的可能。就这一点来说,国家本身拥有绝对或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主权。这就是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国家观念。在他看来,国家只有拥有这种绝对的权力,才能对个人和私人团体产生威慑作用,才能保护每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安全,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反过来说,一旦国家的权力或主权受到制约,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国家的分裂或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退回到自然状态,甚至退回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在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国家之中,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不再产生致命的政治后果。一方面,宗教被“去政治化”了:宗教完全变成了一种个人或私人的信仰,不再具有干涉世俗政治的权利和权力。另一方面,政治也完全“去宗教化”了:国家作为一种具有绝对权利的公共权力,在面对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的“诸神之争”时也完全保持中立,保护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不会支持或倾向于任何一种宗教或教派。这就是霍布斯对于“神学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就这一点来说,无论霍布斯是否可以被看成一位自由主义者,但他的确是自由主义“政教分离”原则的真正奠基人。
但是,霍布斯的解决方案并非没有代价。他的“政教分离”策略固然消除了宗教对于政治的干涉和威胁,但却同时将国家本身也“去神圣化”了,或者借用韦伯的话说,将国家“去魅”了。无论国家被命名为一个“人造的人”,一个“有朽的神”,还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利维坦”,其本质都是一个纯粹属人的世俗之物。霍布斯认为,一个人服从国家,要么是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因为他觉得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和平与安全的好处;要么是出于对国家的恐惧,因为倘若他不服从国家,那么他就会受到惩罚。但是,这两点并不足以使个人在道德上服从国家。因为在霍布斯那里,个人在道德上显然比国家更具有优先性。他虽然再三强调国家具有绝对权力,但是严格说来,这种绝对权力本身并不是无条件或绝对的。因为归根到底,国家不过一种人为的创造或建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尤其是个人的生命。倘若二者发生冲突,那么一个人为了捍卫自己的生命而反抗国家,无论如何都是正义的。(11)但这样一来,国家本身的权威和道德正当性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辩护。
因此,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国家包含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道德困境。他无法说服人们相信:国家的绝对权力并不是对个人自由的威胁或侵害,而是对它的保护。事实上,这也是洛克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批评霍布斯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讲,自由主义恰恰是利用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前提去反对他的绝对主义结论,也就是说,它站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立场对国家权力进行道德上的限制和约束。
三、洛克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
洛克向来被看成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对国家的起源与目的的看法,已经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的经典表述。人们通常认为,洛克的主要批判对象是霍布斯。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流行和典型的误解。正如拉斯莱特所说的,洛克的真正对手并不是霍布斯,而是费尔谟(Sir Robert Filmer)。(12)作为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费尔谟极力捍卫“国王的神圣权利”,宣称包括英国国王在内的一切君主的统治权都来自于上帝的授予,都是承袭自人类的始祖亚当。他把君主或国王比作人民的父亲,认为一切政府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家长专制,没有人在自然上是自由的。(13)在《政府论》中,洛克对费尔谟的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他看来,每个人在自然上都是自由的,都是自足、独立的个体,并且拥有完整的自然权利,这就是人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之中,既没有国家或政府,也没有统治和被统治;国家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契约和同意,来自于他们的自然权利的自愿让渡或授予。就这种个人主义的哲学前提而言,洛克的同霍布斯并没有根本区别。(14)
但是,恰恰基于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前提,洛克反过来批评他的绝对主义国家思想。按照洛克的看法,个人之所以同意或愿意订立契约并且建立国家或政府,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但是,在霍布斯式的绝对主义国家之中,个人虽然可能不受其他人的威胁,却受到国家权力的更大威胁。洛克认为,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和不可理喻的。从洛克的立场来看,霍布斯的错误是没有将个人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因为,倘若每个人在自然上都是自由和独立的个人,那么自然状态就不可能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是一种受理性或自然法约束的和平状态。用洛克本人的话说:“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5)
问题是,倘若自然状态是一种和平状态,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离开自然状态,建立国家呢?洛克的回答是,自然状态本身非常脆弱,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很容易受到威胁。这一点多少体现了洛克对于自然状态的两难态度:一方面,他不能把自然状态描述得过于美好,否则他就无法解释建立国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把自然状态说得过于糟糕,否则他就不得不接受一个霍布斯式的绝对主义国家。为了避免这两个极端,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中庸的态度,认为自然状态包含了某种根本的缺陷: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来评判每个人的行为,也缺乏公正的裁决者和执行者,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在洛克看来,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克服自然状态的这一弊端,更好地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与霍布斯类似,洛克把国家的建立理解为契约的结果。(16)但不同于前者的是,洛克明确地区分了政治社会与政府,尽管他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社会并不能脱离政府而单独存在。(17)因此在洛克那里,国家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和政府共同构成的,而狭义的国家则特指政府。从逻辑上说,国家的建立过程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多数人达成契约,同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治社会”,也就是所谓的“人民”;第二个阶段是人民委托少数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并且授权给他们,让他们建立政府。在洛克看来,政府具有两种主要的权力,一是立法权,二是执行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因为它负责制定成文的法律,以便明确地规定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界限;而执行权作为一种具体执行法律的权力,当然从属于立法权。
为了防止政府本身蜕变或堕落成为一种霍布斯式的专制或绝对权力,洛克对政府的权力进行了双重的限制。首先,政府的立法权和执行权必须被区分开来,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因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18)这就是现代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权力分离”原则。其次,更重要的是,立法权虽然是一种“最高的权力”,但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受委托的权力”,而真正的“主权”或“最高的权力”仍然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19)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者,还是执行者——滥用了自己的权力,侵犯和损害了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那么人民就可以废黜政府:“人民享有恢复他们原来的自由的权利,并且通过建立他们认为适合的新立法机关以谋求他们的安全和保障,而这些正是他们所以加入社会的目的”。(20)一言以蔽之,人民拥有革命或反抗暴政的权利。
与霍布斯相比,洛克对国家的“去道德化”更为彻底,或者说他在道德上把国家贬得更低。尽管他承认国家的必要性,认为需要国家来克服自然状态的缺陷、保护个人的自由,但是他对国家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他反复强调要对国家或政府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防止它变成一种绝对或任意的权力。因为对洛克来说,国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一种“恶”。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里,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似乎不仅超过了其他的个人或团体,而且超过了没有国家存在的自然状态。他在《政府论》中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如何使国家更好地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如说是如何防止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可能威胁和侵犯。
由于洛克强调了个人在道德上相对于国家的绝对优先地位,他几乎不可能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事实上,洛克的国家学说几乎没有为爱国主义、公共精神和对他人的关怀等传统美德留下任何余地。对他来说,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才是终极目的和唯一实在,而国家不过是一种外在和派生的东西。因此同霍布斯一样,洛克也认为,个人之所以服从国家,要么是出于理性的利益计算,要么是出于对于违反国家或法律之后果的恐惧。问题是,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或内部叛乱等危机时,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军人,是否有义务牺牲自己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去保卫国家,保卫他人和同胞的财产、自由和生命?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洛克,还是在其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那里,都不可能找到答案。而真正认真地思考并且回答这一问题的,恰恰是被现代自由主义所批判和排斥的两位政治哲学家——卢梭与黑格尔。
四、卢梭与黑格尔对现代国家的道德辩护
卢梭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分水岭。他既是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继承者,又是它的激烈批评者。他接受了霍布斯与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的哲学前提,认为国家既不是作为一种终极目的隐含在人的自然本性之中,也不是来自于上帝的神圣启示,而是一种人为的契约创造。但是,他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按照这种社会契约所建立的国家在道德上非常脆弱,因为它仅仅外在地保护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却不能满足个人更高的精神和道德追求。进而言之,这种社会契约思想一方面造成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导致个人作为私有资产者和作为公民这两重身份之间的分裂和冲突,使个人丧失了自身的完整性。
与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不同,卢梭版本的社会契约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向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整体或国家无条件和无保留地让渡自己的全部权利,否则就必然会出现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以及个人作为私有资产者与公民的自我分裂。卢梭虽然继承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但却抛弃了他们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学说。他认为,人的自然作为开端只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不包含任何权利与法。任何权利和法都以人的理性或理解力为前提,但人在自然状态中却并不拥有理性能力。因此,真正的权利不是自然权利,而是理性权利;真正的法不是自然法,而是理性的道德法。就这一点来说,真正的让渡并不是自然权利的让渡,而是一种理性权利的让渡,或者说是一种意志的让渡。作为意志让渡的结果,国家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普遍意志”。这种“普遍意志”不仅高于任何“特殊意志”,而且高于作为“特殊意志”之总和的“众人意志”。对于卢梭来说,恰恰是这种“普遍意志”构成了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基础。(21)
在国家之中,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不是人民受国家统治,而是人民自我统治。换言之,人民才是真正的主权者。对个人来说,国家和法律不再是一种外在、异己和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他的自我立法;服从国家就等于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服从自己。因此,真正的自由既不是单纯的自我保存,也不是对于国家和法律的外在服从,而是一种道德意义的自我立法或自律。换言之,人的理性不是发现并服从外在的法(自然法),而是体现为自我立法。正是通过这种自我立法或自律意义的自由,个人才从一个动物式的欲望和利益主体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如同卢梭所说:“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22)
卢梭不仅为现代国家重新奠定了道德正当性的基础,而且同时肯定了个人的道德自由。他希望由此消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恢复人自身的完整性。正是由于这一点,卢梭成为德国唯心论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从政治哲学上说,德国唯心论代表了现代性和现代政治哲学的最高成就,它的根本意图就是在卢梭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个人与国家的真正统一,使国家成为个人自由的最终实现。这个意图,在德国唯心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就现代政治哲学来说,黑格尔是极少数高度肯定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甚至或许是唯一的一个。他一方面继承了自笛卡儿以来的现代主体性(我思或自我意识)原则,尤其是卢梭和康德的道德主体性(或自由)原则,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回归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也就是说,他在肯定现代性的前提下返回古代,将被早期现代政治哲学所批判和否定的传统宗教和道德再次激活,使之成为现代政治世界的真实内容。他重新肯定了国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拥有的崇高地位,认为国家是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是“伦理性的整体”和“自由的现实化”,是“地上的精神”和“地上的神”。(23)他反对将政治与宗教完全分离,反对将国家彻底“去宗教化”或“去神圣化”:“当我们说,国家是建筑在宗教上面——国家的根是深深地植埋在宗教里面的——我们主要地说,国家是从宗教产生的,而且现在和将来会永远如此产生的”。(24)
基于对国家的这种道德肯定,黑格尔明确将国家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他对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后者把国家误解为市民社会,抹杀了二者的本质差别。在黑格尔看来,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是抽象、片面和不真实的,是一种纯粹外在和否定性的自由,只有在国家之中个人的自由才获得了伦理性的客观内容,成为真正的自由。(25)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言简意赅地肯定了现代国家的原则:(26)
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体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体性的原则本身中保存着这个统一。
因此,现代国家在现代的主体性原则前提下回归古代的实体性,由此消除了个人与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自然(必然)与自由、政治与道德的对立和冲突,实现了主体性和实体性的真正统一。当然对黑格尔来说,这种统一并不是像古代世界那样简单、直接和无差异的统一(同一),而是基于个人意志、自由或自我意识前提的统一,因此是“差异中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将现代国家看成是“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
五、黑格尔之后的国家虚无主义
但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除了在少数新黑格尔主义者(如鲍桑葵)那里获得少许正面回应之外,几乎遭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内的所有现代思想流派或意识形态的一致批判。马克思主义或更宽泛意义的左翼激进主义同自由主义虽然看起来势如水火,但在批判黑格尔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奇特的共识,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现代国家。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谓的现代国家不过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其本质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暴力机器。推而广之,一切国家在本质上都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工具,都是一种人的异化。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真正自由和解放意味着国家的彻底消亡。当代左翼激进主义和文化左派甚至将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从阶级扩大到宗教、种族、族群、性别和性取向,似乎国家是导致人世间所有冲突、不平等和灾难的万恶之源和罪魁祸首;只要消灭了国家,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现代自由主义那里,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同样是名誉扫地。在以霍布豪斯、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看来,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代表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是“开放社会”和个人自由的死敌。
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罗尔斯的努力,自由主义的思想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尔斯抛弃了低俗的功利主义,将自由主义回溯到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社会契约思想传统。他试图由此建立一种正义理论,为自由民主社会奠定“最恰当的道德基础”(27)。他从一种类似于“自然状态”的“原初状态”中,推导出“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但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洛克、卢梭和康德等社会契约论者为之殚尽虑竭的两个主题——宗教和国家——几乎消失了。首先,他对洛克的“自然宗教”、卢梭的“自然宗教”与“公民宗教”以及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等不置一词。对他来说,正义似乎与宗教完全无关——而在洛克、卢梭和康德看来,正义必然最终指向宗教。其次,罗尔斯的正义仿佛只是人的一种理性自觉选择,无需作为“正义之剑”的国家来保护。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进一步认为,他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自由主义”,不需要任何道德哲学的前提。因此,他将正义同一切形式的宗教和道德学说划清界限,并且把国家看成是一种市民社会意义的“民主共同体”。只有这种与任何“整全学说”都无关的正义理论才能满足人们对公平和平等的追求,才能最大程度地尊重人们在宗教、道德、文化、种族和性别等方面的差异性。(28)
人们通常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方面是对自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新政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总结,另一方面是对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的道德辩护。但是历史的事实清楚地表明,无论是“新政自由主义”的推行,还是“民权运动”的进步,都是以强大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很难想象,倘若没有国家权力作为前提,那么单凭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尤其是其中的“差异”原则,我们如何能够说服那些地位最有利者(强者)自愿地放弃自己的利益去补偿“地位最不利者”(弱者)。就这一点来说,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说服力远远不如洛克、卢梭和康德,甚至不如霍布斯。
结 语
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范围越大,他就越需要国家的保护,相应地国家的权力也就必然会变得越大。进一步说,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在道德信念、宗教信仰和价值偏好方面的差异、分歧和对立越大,就越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事实。但托克维尔似乎没有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国家在现代社会逐渐被“去神圣化”或“去道德化”,它在道德上越来越不能自我辩护。无论对左派激进主义,还是对自由主义,甚至对保守主义来说,国家都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利维坦”。如果说在保守主义和罗尔斯式的温和自由主义那里国家还是一种“必要的恶”,那么在左翼激进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那里,国家甚至连“必要的恶”都不是,它成了纯粹的“恶”。国家拥有的权力越大,它就越缺乏道德的正当性;它越是缺乏道德正当性,就越需要用更大的权力来弥补这种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现代国家的道德困境。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自冷战结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非西方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同样普遍弥漫这种反国家或国家虚无主义的情绪,甚至比西方世界有过之无不及。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说,引发这种反国家情绪的具体原因或许非常不同,但最终的结果都是对国家的道德否定。国家虚无主义者热衷于在道德上批判国家是“恶”,但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国家这种“恶”之所以是必要的,恰恰是为了对抗人性本身的“恶”。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美国联邦党人的警世名言:(29)
政府本身若不是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
在现代社会或现代性的前提下,我们是否能够基于可取性的更高理由为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进行辩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去神圣化”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宗教和道德在内的一切传统权威都受到彻底的怀疑、批判和解构,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左翼激进主义,都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典型表征。
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想要为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辩护,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在根本上来自于现代性自身的危机。思考和探究现代国家的道德正当性危机的第一步,就是获得一个超出现代性的更广阔视野,并由此反思现代性自身的逻辑前提。
注释:
①这句话中文通常译作“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与阿克顿的原意稍有出入。参见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2页。
②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132—133、197页。
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9页。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2页。
⑤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4—175页。
⑥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⑦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5章。
⑧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473页。中译文根据霍布斯的英文原著有所修改,以下同。原文参见:Thomas Hobbes,Leviathan,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Edwin Curley,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Indianapolis/Cambridge:1994.
⑨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76页。
⑩霍布斯:《利维坦》,第94页。
(11)霍布斯:《利维坦》,第147、170页。
(12)彼得·拉斯莱特:《洛克〈政府论〉导论》,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87—89页。
(13)Robert Filmer,Patriarcha and Other Writings,edited by Johann P.Sommervil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6—7,11—12.
(14)麦克福森将霍布斯和洛克的个人主义称为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其核心是认为个人是其自身人格和能力的绝对拥有者,只有个人自己才能自由地支配和使用他的拥有物或财产,而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社会和国家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参见:C.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263—271.
(15)(16)(18)(19)(20)洛克:《政府论》,第6、59—60、89、81、134页。
(17)洛克指出,应该“把社会的解体同政府的解体区别开来”。在他看来,政府的解体不等于社会的解体,因为这只不过是回到了政治社会的状态,也就是说,人民重新获得了授予政府的权力;但是反过来说,社会的解体必然意味着政府的解体,因为这等于是完全退回到自然状态。参见洛克:《政府论》第80、91—92、128—129页。另可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下),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6—577页。
(21)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3—25、39—40页。个别术语根据英译文稍有改动,英译本参见: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49—50,59—60.
(22)卢梭:《社会契约论》,第30页。
(2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24)黑格尔:《历史哲学》,第53—54页。
(25)(2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3—254、200页。
(27)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
(28)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61—67、165—166、302—306页。
(29)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4页。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自然状态论文; 卢梭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道德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 政治学论文; 法律论文; 洛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