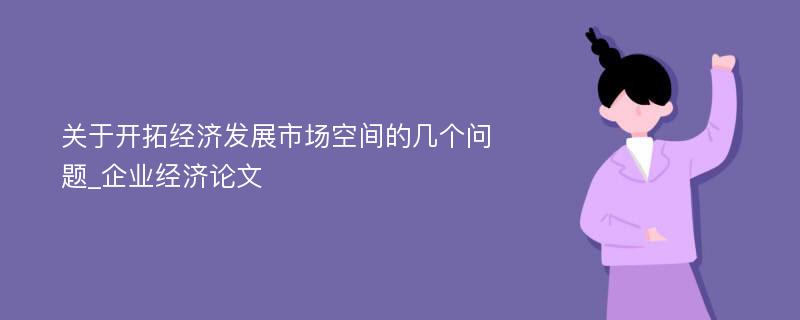
关于开拓经济发展市场空间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市场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单纯运用扩张的财政政策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
在有效需求不足条件下,拓展市场空间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而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上下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就业问题解决得如何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确保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路支配下,政府发行国债的规模不断扩大。财政预算支出增加显著。尤其是在1998年7、8月我国遭受洪灾后,1998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议案,及时决定财政部增发1000亿元10年期限、年利率为5.5%的国债,定向向国有银行发行,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笔国债,又使银行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试图通过这样的办法,总共2000亿元的建设资金所形成的最终需求可以拉动GDP增长两个百分点,并创造就业机会。因为统计表明,1979-1997年,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新增城镇就业人员80万人。在通货紧缩时期,实施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是有助于增加投资需求,并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的。但是同时也应认识到,单纯运用财政手段是不能完全解决就业问题的。
要逐步解决目前日趋严重的就业状况,一是应启动各种有益的经济政策,放松对建立企业的控制,逐步缩小企业审批制的范围,使企业登记制有序地成为主导制度;二是鼓励国内各种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实行收购与兼并,在资产的重组中开辟新的就业领域与就业机会;三是应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在失业问题严重的地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借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员;四是积极开拓和发展新的产业和技术,提供更多的非传统行业的新就业机会。
当然,在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时,要摆脱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有目的地吸引外资是必要的,但那种试图依赖外资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早在1996年时,我们做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单纯依靠外资来解决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通过对1984-1994年期间的我国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如下:
Y=52715.6+2.97FI
(3.58)
R=0.5869 D.W=0.361 S.E=2952.9
(Y:就业人数,单位万人;FI:外资,当年价格,人民币亿元)
上述数据告诉我们,在1984-1994年期间,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外资,平均会增加2.97个单位的就业机会,但是数据也表明,外资与就业的相关程度较低,因为两者之间相关程度的判定系数仅为0.5869。而且通过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就业人数对外资的弹性值很低,仅为0.065。这些都说明,外资增长对就业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似乎我们把解决就业问题的重点放在内资身上更现实一些。
二、单纯运用扩张的货币政策不能如愿刺激消费需求
从我国1998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的确有些不如人意,特别是在刺激市场需求方面。但有的人把这种格局简单地归咎于是货币扩张程度欠缺,是不能苟同的。
回顾1998年,货币政策的扩张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为增加消费需求,提高消费信贷力度,商业银行从1998年下半年相继推出贷款买房、买汽车业务就是如此。二是适度放松银根,扩大货币供应,以期全面刺激内需。这突出表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加快了降息的频率,1998年的一年内分别在3月21日、7月1日、12月7日前后三次下调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在前两次调整中,贷款利率的下调幅度要大于存款利率的下调幅度,例如,3月份贷款利率下调0.6个百分点,而存款下调0.16个百分点;7月份贷款下调1.12个百分点,存款下调0.49个百分点。到12月7日后,除了活期、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保持1.44%和2.79%外,其他各个档次的利率都作了调整。例如,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降为3.78%,一年期贷款利率降为6.39%。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准备金存款利率由3.51%下调为3.24%;再贷款利率由5.61%下调为5.06%、再贴现利率由4.32%下调为3.96%。这对于增加消费信贷,刺激国内需求,降低企业成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据有人估计(林晖,1999),仅三次降息就可使企业每年减少880亿元的利息支出。但是尽管如此,在中国市场经济框架不完全的背景下,利用以降息为主要手段的扩张的货币政策仍然显露出了它本身的局限性。到1998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1亿元,增长15.5%;全部各项存款余额为95697.9亿元,增长16.1%;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5亿元,增长17.1%。可见低利率走势并没有改变人们的传统消费行为方式。探究原因,或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不明确,或是由于各种改革措施出台,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等等。但是当人们在“生产过剩”背景下探讨刺激市场的消费需求时,不能忘记真正能刺激人们消费需求的是人们的收入水平。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的历史教训,那就是,造成其“生产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的低下的收入水平无法大量消费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产过剩”也同样潜藏着类似的危险。例如,如果从吉尼系数来看,根据有关报告(世界银行,1996),中国1992年的吉尼系数为37.6,低于1989年的巴西(63.4)、1989年的马来西亚(48.4)、1992年墨西哥(50.3)、1992年的泰国(46.2)、1993年的俄罗斯(49.6)。似乎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并不严重。实际上如果再细化一下,就会看到问题的潜在的严重性。例如,在关调查结果表明,如果按五等份的方法衡量,1992年在中国两极分化的格局是,最高收入的20%的人占全部收入或消费的份额是43.9%,*
而最低收入的20%的人占全部收入或消费的份额是6.2%,两者之比是1∶7.1,远远高于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为1∶4.3(1979年);瑞典为1∶4.6(1981年);德国为1∶5.8(1988年);意大利为1∶6(1986年);加拿大为1∶7.1(1987年)。如果按十等份的方法衡量,在中国两极分化的格局是,最高收入的10%的人占全部收入或消费的份额是26.8%,而最低收入的10%的人占全部收入或消费的份额是2.6%,两者之比为1∶10。可以看出,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仅是最高收入者的十分之一,也可以说,对于最高收入者来讲是属于“更新换代”的产品,可能对于最低收入者来讲还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行列,而这10%的人口总数就相当于一个日本。因此,人们的收入差距过大是阻碍市场发展空间扩展的重要因素。
三、单纯运用退税手段不能有力提高出口竞争能力
在开放型经济中,开拓市场发展空间的手段之一是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以说,在1998的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中,对于刺激出口需求是做了一些准备的,但措施是比较单调的,似乎只能实施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在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分4次小步分别提高了纺织品、煤炭、水泥、钢材和部分机电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退税率水平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两个百分点,即由9%提高到11%。例如,1998年1月1日起,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由9%提高到11%;1998年6月1日起,钢材、水泥出口退税率由9%提高到11%;1998年9月1日起,7种机电产品和5种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由9%提高到11%;从1998年9月1日起,铅、锌、铝的出口退税率由9%提高到11%。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国内的增值税是17%,所以11%这一退税水平并未达到出口产品“零税(ZERORATE)”的国际惯例。因此国外有些人说中国在搞倾销是站不住脚的。虽然提高出口退税率对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的作用明显,但出口产品的高度化还有赖于企业的创新能力。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在全球竞争中普遍被视为企业创新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维护企业竞争力的有力手段。这是因为当前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人们的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如果一个企业不能把研究与开发经费提高或保持在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上,那么这个企业就会丧失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观察,无论是国有企业的现状,还是“三资企业”的现状,都是令人担忧。
例如,据国家统计局前几年在福建和甘肃两省的企业调查表明,432家大中型企业里开展R&D的占82%,1515家小型企业里开展R&D的只占41%,两省企业的技术转让率仅为4.7%。企业普遍认为“资金缺乏”是阻碍R&D开展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样必然阻碍企业的创新。
再例如,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三资”工业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平均水平为0.4%。结果:一是新产品销售收入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过低,“三资”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为5.2%;二是高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在销售收入中的比重过低,“三资”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为3.2%。造成上述状况的基本原因,是许多“三资”工业企业根本不存在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在59311个“三资”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中,有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企业仅258个,存在的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只有660个,其中有327个机构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有196个机构没有经常性的开发任务,有251个机构不具备一定试验测试条件。按照一般经济理论的共识,企业应是技术创新的载体,而被取消了研究开发机构的某些企业还能被视为“企业”吗?这种企业的产品会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吗?
四、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是开拓市场的基础性工程
在市场开拓的实践中,一般在各国的市场需求中都倾向于假定主要受两类因素即质因素和量因素的影响。所谓量因素主要是指人口规模,所谓质因素主要是指各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当然,在选择质因素的指标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偏好。似乎在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一般能反映各国经济发展及生活水平的因素包括人均电力产量、就业人数、每千人拥有的电视机数目、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目、每千人拥有的收音机数目、人均汽车拥有量、可支配收入等。但是不管如何看,衡量市场规模大小的主要标志是制成品的产量。但是所有这些人均指标的测量都需要以准确的统计数据为依据。但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实在不小。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我国GDP增长7.8%,对于这个指标,不少的人根据直观认为有水份。但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1998年年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却表示这一数字是实实在在没有任何水份的。他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全国的经济统计数据经过了认真的审查和复核。(国际金融信息报,199-1-1)”但是似乎这些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的疑问。因为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统计数据实在与之差距甚远,根据各地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的GDP的增长速度从高到低排列如下:福建11.4%,江苏11%,山东10.8%,河北10.7%,湖北10.3%,上海、浙江、广东、广西分别为10.1%,西藏10%,北京9.7%,内蒙古9.6%,陕西、天津分别为9.3%,甘肃9.2%,山西、湖南、四川分别为9.1%,安徽、青海、吉林分别为9%,河南8.7%,贵州8.6%,黑龙江、重庆、宁夏分别为8.5%,辽宁、海南分别为8.3%,江西8.2%,云南8%,新疆7.3%。根据以上这些数据,无论是用算数平均法,还是用几何平均法,都无法得出全国GDP增长7.8%的这一指标。
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实践活动,还发现在制成品与能源消耗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在市场秩序混乱、弄虚作假成风的环境里,以各地的统计资料为基础而汇总的数据往往失真。以电力弹性系数(发电量增幅/GDP增幅)为例,1994年,GDP增长幅度为11.8%,电力弹性系数为0.85;1995年,GDP增长幅度为10.25%,电力弹性系数为0.84;1996年,GDP增长幅度为8.8%,电力弹性系数为0.74;1997年GDP增长幅度为8.0%,电力弹性系数为0.58;1998年GDP增长幅度为7.8%,电力弹性系数为0.32。也就是说,在1998年GDP增长7.8%的情况下,发电量只增长2.5%。显然,如果没有显著的普遍的技术发明应用,如此低的能源消耗是支撑不了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的。
可见,要想真正开拓市场,如果没有真实的数据为依据,那么,任何市场预测都是扭曲的,也无法高效地配置资源。
五、开拓市场空间过程中应正确看待政府干预
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各国(地区)的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管是香港政府的入市以阻击对冲基金的袭击,还是美国政府的介入以挽救长期投资管理公司的崩溃,都表明了政府干预起着重要作用。当然,中国也不例外。由此而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对于政府干预的争论又重新热化。但此次争论的中心是,政府如何和怎样干预,才可以使公众受益。理想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中心问题是何日官僚将会允许市场运行不受约束。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在政府干预问题的探讨方面,应该破除两种迷信。
一种是要破除对纯粹经济自由理论的迷信。很长时期以来,有些学者一味为了单纯追求经济自由理论上的完美,通过各种不同的曲线或理论模型来论证纯粹自由经济可以产生各种好处,但是实际上,从地球上诞生市场经济以来,大概还没有真正产生过不受政府任何约束而运行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因为,政府是国家、民族、利益集团意志的代表,排除这些利益主体存在的实际而完全按市场力量自由运作的经济模式,实在是过于理想化了。
另一种是要破除对强化政府干预的迷信。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化需要逐渐有序地放松政府管制,而不是相反;另一方面,在目前投资机制、软预算约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如果过分强化政府的干预作用,大量动用财政力量去刺激经济增长,不仅会妨碍企业制度的改革,而且会降低投资效益。
在政府干预问题的探讨方面,“互补互济论”是值得注意的。这种理论认为,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应该是互补互济的关系,其中较为重要的事情是划定领域,明确哪些事情应由政府管,哪些又应该由行业公会去协调,哪些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而形成一种整体有序的状态。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创造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
六、刺激市场需求的短期措施应与长期发展利益相一致
在1998年,政府动用财政力量,不断拓宽投资领域,在加大对农林水利、铁路、公路、通信、环保、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的同时,增加对粮库、农村电网、城市经济适用住房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应该说,这种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一种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手段。但是,如果政府一味地偏好使用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也会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构成威胁。因此,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出了某种担心。例如,政府投资支出未必全部进入能最有效抵消通货紧缩的部门和地区;投资支出一旦投向亏损企业,则会对金融系统的财产质量形成压力;在法治软约束背景下,过分依赖由政府负债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易于出现效益问题(例如“八五时期”项目);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易于形成新的经济过热。因此,从长期利益来看,能够支持我们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在微观,关键在企业,仅靠扩张的财政政策,效果难免长久。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94年克鲁格曼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克鲁格曼是在全世界都为“亚洲奇迹”而感到惊讶时,惊人地指出,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是“纸老虎”,他认为,今日的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奇迹与30年前的苏联的“经济奇迹”一样是“谨慎的寓言”,西方国家不必为其崛起而恐惧。为此,他先回顾了一段他认为是重要的蛤却大部分被人忘记了的经济历史—即在60年代由于苏美的增长速度的差异所引起的争论。接着,他把90年代的新加坡与50年代的苏联做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分析后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经济增长主要靠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资源投入(如资金和劳力),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却近乎于零。这种只靠投入品增加的经济增长绝不会持久,因为这种只注重投入品扩张、而不注重单位投入品产出增长的经济必然是损失收益。现在看来,不仅克鲁格曼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而且是应该使我们引以为戒的,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被克鲁格曼称为“纸老虎”的新兴工业国家是相似的。如果我们只注重投入的规模,而忽视产出的效率,那末,相似的增长方式必然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总之,只有把以上6个方面的问题逐步解决好,中国经济才能从不断市场化、国际化的环境中开拓发展的无限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