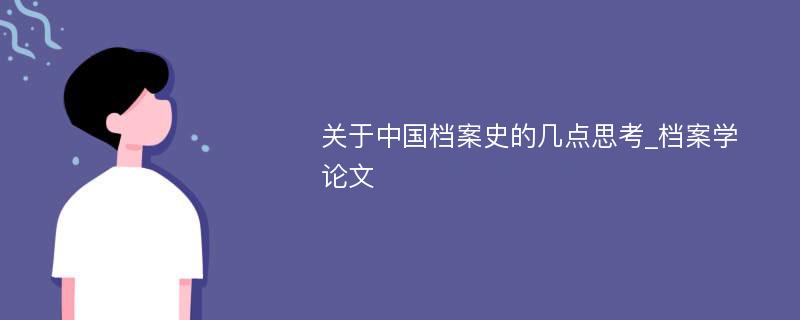
关于中国档案事业史的若干问题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中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事业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名称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档案事业史一直沿用“中国档案史”名称(现在仍有不少人用此称呼)。但如今看来,这个提法似乎太狭窄了。因为这门课的内容包括两大部分,即一方面是档案的历史,另一方面是档案管理工作及其延伸的历史,这部分的内容在这个名称上没有体现。
在中国古代,文书与档案、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往往很难作泾渭之分。至少在隋唐以前,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是无法作严格区分的。档案工作大多作为文书工作的后缀部分,由文书工作人员或广义的秘书工作人员甚至是官员本人从事并完成的。在叙述这一时段档案工作的时候自然要把一部分文书、文书工作史的内容掺入。进而言之,古代“文书”一词与我们今天“文书”的含义也并不完全一致或重合,有时“文书”的含义恰恰涵盖我们今天“档案”的含义或指称,如《汉书刑法志》曰:“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此“文书”即今天之所称之“办理完毕已转化为档案”的“文书”。当然,隋唐以后,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逐渐有了区分,文献史料中也有恰如其份的反映,最典型的莫过于《隋书刘炫传》的记载,其中提到的“今之文簿,恒虑复治”一语。这里的“复治”,即对办毕文书的“第二次加工或整理”,这无疑就是今天所称的档案工作的内容了。但这种区分也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或阶段都十分清楚,而是时隐时显,直至国民党时期还在搞所谓的“文书档案连锁法”,观念上似乎反而倒退了,档案工作在文书承办之前就开始了。此乃其一。
其二,还需说明,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内容基本上限于文书档案事业史的范围,所以也许直称“中国文书档案事业发展史”更名符其实;虽然古代也存在如今天所称的“科技档案”、“技术档案”、“水文档案”、“天文档案”、“建筑档案”、“病历档案”等专门档案,只是不像如今这般普遍。笔者曾经收集到一则有关宋代病历档案的史料。
宋代有各类医院,名称有广惠坊、“安济坊”、“养济院”、“病囚院”、“医药院”等。其中一所是大文学家苏轼在杭州为官时“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设立的“安乐”医院。这所医院的病人管理“以轻重而异室处之”,实行以病分室制度,而且“医者人给手历,以书治愈失,岁终考其数为殿最”;“三年医愈千人,赐紫衣、祠部牒各一道”(类似今天常见的奖状或荣誉证书,材料见《宋史食货志》)。这里所谓的“手历”既是必要的病人病情记录,也是主治医生施治用药的原始凭证,还是对医生进行定期考核、奖励的依据,当为病历档案无疑。而“赐紫衣、祠部牒”则是国家对恪尽职守、做出成绩的“医者”的奖赏。明代著名的建筑师蒯祥建造紫禁城时没有各类设计、营造图纸(即如今之基建档案)是无法想象的。长江三峡等地也有古代的水文记录保存下来。但是这类档案在所有档案中的比重有限,能历尽劫难、保存至今更为罕见也是可以肯定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这些属于古代技术档案、专门档案范围的理应包括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之内的内容,在本学科基本处于空白。
二、中国档案事业史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档案事业史的主体内容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档案的历史,包括档案的起源、产生、种类、制成材料在历史上经历的若干阶段及其演化与特点,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这些问题,需要把它们放到相应的历史阶段中去考察,同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及制度完善结合起来。另一部分是档案管理工作的历史,隋唐以后,这部分内容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的主体部分,即客观地介绍并准确地描述历史上的档案机构及其人员是如何从事档案的收集、保管、立卷、整理、鉴定、销毁或修缮等一系列具体工作的,用刘炫的话说就是“复治”。
档案管理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有一个总结、提高及理论化的内在要求,这是学科产生的内在规律,此时档案学就应运而生。档案学诞生于何时?一般认为,我国近代档案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标志之一是1935-1938年间周连宽、程长源、何鲁成等学者分别公开出版了各自的档案学著作:《县政府档案处理法》、《县政府档案管理法》、《档案管理与整理》。但现在有人认为,档案学中国自古有之。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内有相当数量的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著作和文集中,收入了一部分涉及这一特定内容的著述。这些著述中或多或少包括了一部分的档案学思想与内容成份。如宋代曾巩的《隆平集》、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元陈旅的《安雅堂集》及宋李大异的《六部架阁库题名记》、陈晦《六部架阁库续题名记》、明何乔新《江西布政司黄册库修造记》、林钺《太平府架阁库记》等相关记载。但是具有学科形态和独特研究对象的独立档案学则是不存在的。与此相类,颇具学科形态的清代“幕学”也不是现代秘书学。
众所周知,文书、图书、档案、文献同源。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文献是甲骨卜辞。它们是商王及奴隶主贵族在占卜活动中(《左传》有曰:“古之大事在祀与戎”)形成并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记录。它在实际事务活动中形成,又以实际事务活动为内容,当是文书无疑。甲骨文书又是集中存放的,甚至在外地——殷都以外的地区形成的甲骨也需向殷都“归档”。因此甲骨文书又是典型的档案材料。但是秦汉以后,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后世人们对书籍的需求与其实用性、重要性的认识要比档案来得更深刻和迫切,从而使图书事业的发展大大超前了。这可以从与中国书史的比较中得出结论。作为图书馆学专业学科单元的《中国书史》,其研究对象是不包括书籍整理与管理工作的历史的。单纯的书史内容就涵盖历代的书籍制度、书籍的制作工艺、生产流通、历代官府及私人藏书、纸的发明、利用与传播等都是书史研究的内容。相对说来,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内容要单薄一些。如古代档案管理中同样使用目录形式,其普遍性与系统性则远远比不上图书管理那样广泛、深入。但古代档案与档案管理工作也有其鲜明的特色,如丰富多彩的档案载体形式、演化规律及受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甚至是观念因素的制约关系,从宋代肇始直至民国还沿用的千文架阁法,从唐代甲库开始的、包括历代架阁库在内的大批具有独特收藏范围的档案机构,王朝更叠之际“一成不变”的档案收集工作,独步于世界各国档案立法制度,生生不息的档案工作整顿与改革,处于封建专制下的档案工作御用性、垄断性、封锁性与档案利用的矛盾等内容,无一不是中国文化史的有机构成。
三、档案利用是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相关教材与著作已有多种。1994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周雪恒教授主编的《中国档案事业史》新教材。与以前的多种著作相比,本书的章节结构作了较大调整,不再羁泥于古代、近代、现代各占三分之一的不成文约定,而是根据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实事求是地安排全书篇幅。全书内容详实,重点突出,史料丰富,观点平允,确实反映了学术界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的研究最新成果,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但是作为中国档案事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历代档案利用的有关内容则稍显薄弱,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
中国古代的档案利用虽然不能与我们今天的档案开放同日而语,利用者的范围(个体利用以各类史官与学官为主)与频率也有限,档案保管与图书收藏、文献庋藏相似,或多或少存在重藏轻用的倾向。但是,历史上的档案,从保存目的说,归根到底与我们今天的目的并无二致,还是为了利用,如无利用目的,则不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将数以千万计的档案材料保存下去。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档案事业史中这一部分的内容还是相对见弱的,甚至是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同类著作中叙述档案利用部分,尤其是古代,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讲汉代的档案利用是编史修志,述宋代的档案利用也是编史修志,介绍清代的还是编史修志。内容显得较为空泛,叙述时又不便于深入展开,如展开那将是史学史或史籍编撰史的内容。
我以为,描述历代的档案利用情况,不能把眼光仅局限于这一个方面,而更应该把视野扩展到广阔的领域:政治斗争、经济建设、文化繁荣、对外交涉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有档案利用的事例。如从这一角度作深入开掘,古代的档案利用内容将是丰富多彩的。这里稍举几例:
1.汉代外戚争权斗争中档案利用及其结果。
汉朝的制度规定,皇帝驾崩须向中外发一遗诏,主持者是最亲近皇帝的高官,发出的是文书的正本,但还需在宫中的尚书官署备有副本。武帝初年,爆发了一起外戚争权斗争,敌对双方是窦婴与田蚡,两人分别是汉文帝窦皇后的侄子与汉景帝皇后的弟弟。窦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因军功受封魏其侯,而田则出身低微。等到窦太后一死,窦婴随即失去位极人臣的地位。而田蚡却因汉景帝皇后田氏取代窦太后而得势,当上丞相,并受封武安侯。势利之徒纷纷去窦走田。在平定七国之乱中与窦婴一起出生入死的灌夫颇为窦婴不平,以为身无寸功的田蚡不当位极人臣。而此人此时正炙手可热,顺其者昌,逆之者亡,好事者遂将灌夫羁押治罪。窦婴完全处于下风。他觉得只有利用先帝的权威,才能重新夺回自己所有已失去的权势,遂向汉武帝上书,说自己曾在景帝临终前“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想以受先帝遗诏这一非常之举来压到田蚡,号令天下。遗诏一出,马上有人对此遗诏的真伪提出质疑,但也有人指出:如此诏是真,宫中尚书当有此诏之副本。于是朝廷决定“案尚书”。朝廷检索了尚书所藏的所有文书档案,但结果是,“尚书之中无此大行遗诏”。既然宫中尚书并无此诏之副本,那就意味着此诏本是子虚乌有,所谓的正本完全是窦婴伪造的。为此,汉武帝大怒,下令将窦婴处死。这场旷日持久的外戚争权斗争以窦婴被斩而告结束。但是左右这场斗争的关键是档案利用的过程及结果(事见《史记窦婴传》)。
2.宋代外交斗争中的档案利用及其结果
北宋建国以后,虽然陆续消灭了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但北方却不断受到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和骚扰。太宗时期,几次伐辽战役失败后,北宋政府不得不改变了它原来的对外政策。
北宋中期,辽国派出了以萧惟辅为首的使团,来宋朝进行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宋朝方面派出了以判三司都磨勘司程师孟等人与之交涉。萧惟辅提出:“白沟之地(今河北南部)当两属,今南朝植柳数里,而以北人渔界河为罪,岂理也哉?”师孟答曰:“两朝当守誓约,涿郡有案牍可覆视,君舍文书,腾口说,讵欲生事耶?”惟辅乃服(见《宋史循吏传》)。
仁宗朝,庞籍出镇河东道(今山西),郭逵知忻州(今忻县)。契丹欲求天池庙一带土地,庞籍身为边关大臣,竟束手无策,擅自把与契丹的交涉责任全部推给了下属郭逵,让其与之周旋。幸好,郭逵在宫中“访得太平兴国中故牍,证为王土;檄报之。”辽国代表在档案文献所陈述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次的领土要求(见《宋史郭逵传》)。
有宋一代,类似的材料特别多。在谈判桌上,宋朝方面往往仰仗档案文献(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签定的国书、誓约、协议等外交文书)出奇制胜,维护了宋朝自己的有关权益。
当然,历代的档案利用也不是任何时候总是铁板一块,没有一点差异。相反,作为档案利用两大领域之一的学术利用(另一方面即上文所举的政务利用一类)却差异度极大。如在宋代,因国家实行“右文”政策,对文人士大夫比较优遇和宽容,历来为统治者视为禁脔、绝不能让外人染指的皇家档案,如实录、日历、时政记等允许臣僚阅看,甚至抄录。私人撰修当代史,政府也采取鼓励政策,给编撰者提供在宫外无法接触到的国家档案和秘籍,从而达到了专制社会档案利用史上最大程度的开放。然而,到了元朝,非但官府公文档案私人不准查阅,就是经官方编纂过的史料利用限制也极严。到了清朝,则“虽九卿翰林不得窥见一字”保存在内阁大库数以千万计的所谓“大内档案”。一般说来,少数民族政权对档案的控制要比汉族政权严,档案利用的范围与频律更小、更低。
四、中国档案事业史的学科建设状况
最早开设中国档案事业史课程的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以后一直作为档案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许多高校在人大档案系的帮助下,开办了档案专业,中国档案事业史也皆作为专业主干课程开设。作为大学四年制的档案专业学生,对祖国自己的档案事业发展历史,从古至今的相关情况有所了解并掌握,既必需也完全应该。但近二十年来,尽管档案学的整体研究状况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就中国档案事业史这一学科自身来讲,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它的学科进展与整个档案学成长并不完全同步。虽然也有如郑州大学王金玉教授那样在宋代档案管理工作史断代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例子,但这还毕竟是个别例子。许多重要历史时期的内容如唐代、汉代、明代等断代专业史研究尚无史料扎实、内容观点堪与王教授比肩的成果。什么原因?我以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在档案学界研究史的风气相对见弱,绝大多数的研究力量集中在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学概论及外国档案管理等分支学科上,现在又有档案法规学、电子文件(档案)等新兴学科,从事中国档案事业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数较少,又没有形成合力,更谈不上规划,基本处于凭各人兴趣、各自为政的状态。有的学者,原来主要力量搞档案事业史教学和研究,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转行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从事中国档案事业史研究需过“两关”:一是古代汉语关,二是史料积累关。如档案利用的史料发掘与积累,就会涉及这两只拦路虎,难度较大。据我所知,王金玉先生原来是搞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对他来说这两个关都不成问题,其他人(如不是大学中文或历史专业甚至研究生毕业的)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总之,现在这门课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还有大批的重要史料沉睡在图书馆及各种史籍中,未被发掘和利用,许多重要的课题还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正如图书馆学界的老前辈刘国钧先生20世纪50年代在批评书史研究的状况时说的:“只是收集了、堆积了许多史料而没有予以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这能说是史料集而不能说是发展史。”这席话,刘先生是针对书史研究说的,但对于我们中国档案事业史教学和研究同样也不无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