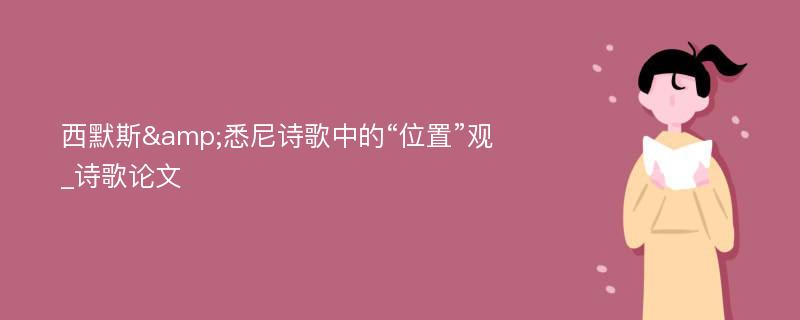
论谢默斯·希尼诗歌的“位置”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位置论文,论谢默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6)02-0105-10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dney,1939-2013)堪称继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之后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希尼出身于爱尔兰北部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其家庭出身及教育背景注定了他复杂的文化身份建构。从他不同创作时期寓于诗歌的“地域”意象即可略窥一二。在早期作品中,希尼有意将其生活过的地名融入诗歌中,此举绝非仅仅为了抒发对故土家园的眷恋,更是表达早年生活对他未来文学创作深刻影响的重要手段。 希尼在随后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愈发关注对隐于北爱尔兰“地域”中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元素的挖掘。例如,《进入黑暗之门》中对黑暗沼泽地的描写,《在外过冬》中盖尔语文化游移无根的重复申诉,无不体现出诗人对家园传统文化的关注。在英国历史上,爱尔兰无论在疆域归属还是社会政治等方面都饱受争议,而希尼在诗歌中频繁引用爱尔兰地名,这无疑引发了诗人对自我与家园关系以及爱尔兰传统与社会政治现实关系的思考。 然而,希尼后来离开故居阿尔斯特,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人诗歌创作风格转变的分水岭。例如,希尼在后期诗歌创作中提及的朝圣遗址斯特森岛,亦成为评估诗人诗歌创作特点的恰当“领地”。诗人最终超越了家园“疆域”束缚的狭隘观念,在保留对爱尔兰性探讨的同时,更注重挖掘诗歌的社会功效,逐渐意识到,诗人和艺术家应通过诗歌创作,尝试在创造性思辨能力和社会现实冷暖真实之间架构桥梁,并主动承担起彰显文学内省性特质与文学良知功效的责任。如他曾说,诗歌“不管属于古老的政治制度还是渴望表达新的政治制度,都必须是具有包容意识的一种工作楷模。它不应该简单化。它的投射和创造应该与一种围绕着它并产生它的复杂现实相称”(希尼,2003:284)。形形色色的“地域”贯穿希尼诗歌创作始终,无论是以实际地理位置为蓝本,抑或借助自我丰富想象力而建构,希尼都得以反思其与爱尔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且,他不断地开采、拓展自己的诗歌创作领地,进而对个人与集体身份“位置”不断反思,进一步取得对艺术家身份地位的思量。本文试图从希尼不同创作时期的诗歌作品出发,探讨贯穿希尼诗歌创作始终的“位置”观,即“地域”与诗歌的关系、诗歌的地位以及诗人甚至艺术家在社会中的定位。 一、对故土家园的艺术“挖掘” 在希尼早期诗歌作品中,“位置”这一概念频繁出现。例如,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中的系列“地形”诗歌突出体现了诗人意欲为纪念爱尔兰文化传统另辟蹊径所面临的困境,体现了诗人在寻求诗歌创作独立与传承家园文化职责之间的矛盾。尤其,希尼在该诗集的开篇之作《挖掘》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主题。《挖掘》是对爱尔兰古代历史的真实写照,体现了诗人从爱尔兰历史中寻求灵感的努力。作者笔下的挖掘“不仅是一种日常的劳作,它更是一种对爱尔兰本土历史的挖掘和寻求”(章燕,2008:333)。希尼笔下老一辈的风霜史成为整个爱尔兰民族历史的缩影。 在《挖掘》中,希尼尤其注重对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细节描写。在诗人笔下,诗中的“父亲”被刻画成为一个永远肩扛铁锨的老农形象,倾其一生都在与土地打交道。甚至,“我”对“祖父”的回忆亦跃然纸上,“他直起身/一口灌下,又立刻弯下身/继续利落地切割,把草皮/甩过肩,为得到更好的泥炭/越挖越深”(希尼,2003:8)。祖祖辈辈都在这方土地上“挖掘”,但这日复一日的日常劳作,引发诗人对爱尔兰传统的深思,“挖掘”的象征之意不言而喻。而“马铃薯地里的冰凉气息,潮湿泥炭沼中的/咯吱声和拍吼声,铁锨锋利的切痕/穿透生命之根觉醒着我的意识”(希尼,2003:8)。希尼将祖先的农耕劳动等同于自己借助想象、运用笔杆来“挖掘”爱尔兰祖先“传统之根”的脑力劳动,因而模糊的记忆变得有形,进而警示人们关注过去、注重历史。尽管诗人对祖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工作的场景从小耳濡目染,但是,希尼没有借助真正的铁锨(如其父辈和祖辈所为),而是通过笔杆来“挖掘”,思考隐于其中的爱尔兰传统文化,唤起人们对爱尔兰性的思考。如希利(Healy)所说,“当希尼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祖辈们的体力劳动等同看待,并乐意如祖先们泥泞的双手般奋笔疾书,这一‘挖掘’类比从哲学层面将文学书写与缺乏文化认识的过去联系在了一起,而这样的认识恰恰掩饰了诗中所描述的将‘观察者’与在田间劳作的‘被观察者’分隔开的文化鸿沟”(Healy,1997:32)。身为一名爱尔兰诗人,希尼在开篇之作《挖掘》中为自己寻求诗作创新、探寻爱尔兰传统文化提出了意蕴深刻的比喻——用笔杆“挖掘”。希尼“与乡村农夫一样,脚穿平头钉靴、徜徉在典型的英式草坪上,因此,他对原本充满异域风情的英国诗歌有了更为细腻而智慧的见解,同时,诗人得以重新发现并纠正文化的不平衡性”(Foster,2009:207)。希尼在诗歌中所援引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爱尔兰本土历史与文化对作者的深厚影响。诗人将祖辈们用铁锨对爱尔兰土地的“挖掘”与作者用笔杆对爱尔兰文化的“挖掘”相类比,旨在证明,写作不仅仅是学术范畴的纯粹理论研究,更是切切实实感受生活、打开观察世界大门的钥匙,是融合体力劳动与心智思考的双重体验过程。 评论家布兰德斯(Brandes)称,“表面上看,《挖掘》反映了诗人对家庭以及社会传承责任的担当——‘我’的祖先曾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所以‘我’也应该沿袭这一传统——同时诗人逐渐意识到,对爱尔兰过去的‘挖掘’亦逐渐使他与传统农耕文明渐行渐远”(Brandes,2009:21)。诗人没有选择跟从自己祖父辈从事农耕、在田间默默耕耘,并摒弃先人世代沿袭的苦力劳作方式,一定意义上,这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僭越;但是,诗歌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对祖先农耕劳作细节的观察和仿效,看似平凡的劳作场景成为诗人获取创作灵感、激发作者深入思考的源泉,因而,诗人选择用手中的笔杆耕犁这方承载北爱传统历史的热土,亦是一种对祖父辈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是保存爱尔兰文化之根、避免其遭受殒萎的手段。可以说,《挖掘》是希尼第一首“用文字来表达思想”(希尼,2003:41)的诗作。 二、承载历史与现实的沼泽地 如果说,希尼的《挖掘》表现了诗人将承载爱尔兰历史的家园诉诸笔端,进而记录爱尔兰民族传统文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在其沼泽系列诗歌中,诗人借助沼泽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存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关切。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政治风云变幻,英国与北爱尔兰之间政治冲突异常激烈。随着爱尔兰独立意识的逐渐增强,希尼诗歌创作凭借其对爱尔兰历史与现实的深邃思考而贏得关注,并使爱尔兰诗歌传统屹立于文坛之上。“希尼的作品标志着英国诗歌传统中英国性的全面崩溃和瓦解”(何宁,2006:90)。 希尼致力于重建爱尔兰诗歌传统,并在凝练诗歌语言、挖掘主体意识以及民族精神等层面不遗余力。希尼借沼泽地系列诗歌,成功地展现了爱尔兰独特的语言、文化与神话传说。希尼创作沼泽地系列诗歌的灵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希尼于1969年阅读了丹麦考古学家格罗布的著作《沼泽地人》,它主要讲述远古时代人们为保丰收而进行活祭、尸体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沼泽地中的故事。这为希尼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他开始通过沼泽地形来探讨爱尔兰掩埋的历史,借助死尸意象唤起民族遥远的回忆。沼泽系列诗歌的创作正体现了诗人努力重建爱尔兰传统,唤起整个爱尔兰民族历史与文化认同,进而建立爱尔兰民族意识的愿望。另一方面,北爱尔兰与英国之间不断深化的冲突成为另一激发诗人创作灵感的源泉。鉴于沼泽地实则象征了爱尔兰深受英国残忍殖民统治的境况,因而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成为联系爱尔兰过往历史与当下社会现实的枢纽。诗人通过将现实政治议题诉诸爱尔兰传统历史遗址,生动彰显了爱尔兰主体意识与民族精神。 在希尼沼泽地系列诗歌中,《托兰人》是彰显爱尔兰祖先奉献精神的典型代表。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名托兰男子为了社族利益而被族人当成新郎祭献给女神的悲惨故事,成为传统社会体制与宗教制度的受害者。这首诗是希尼沼泽地系列诗歌“对格罗布《沼泽地人》——对铁器时代掩埋在日德兰半岛沼泽地中尸体的考古研究——中死尸意象充满想象力的第一次回应”(Johnston,2003:117)。希尼有意识地将古代的祭祀活动与当时爱尔兰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如其所说,“从爱尔兰政治殉道的传统中寻求灵感……这不仅是一个古老的野蛮祭祀仪式:更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受害者的照片时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不禁使我联想到爱尔兰过去与现在政治和宗教斗争的残暴”(Heany,1980:57-58)。因此,希尼的沼泽地系列诗歌突出了爱尔兰政治冲突的残暴性质,同时也表明,身为诗人,应主动承担不断反思、不断表现社会政治现实的责任。更广意义上讲,它使读者不断反思诗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在该诗的第一节,诗人首先做出承诺,一定要在某天亲自去看看被挖掘出土的托兰人,“有一天我要去奥尔胡斯/看他那炭褐色的头,/他那温柔的豆荚形眼睑,/他的尖顶皮帽。”其中,“豆荚形眼睑”表明这则男尸实际上是祭祀的牺牲品。此外,诗句“他最后喝下的冬麦种做的粥/已在他的胃中结成了饼”(希尼,2003:58)暗示了托兰男子的非正常死亡。接着,诗人便将其不幸遭遇和盘托出,“新郎祭祀给了女神/她收紧了套着他的项圈/张开了她的沼泽”(希尼,2003:59)。尽管,该男子被称为女神的“新郎”,但“项圈”一词不仅反映了男子脖颈被绳索紧紧扼住并强勒至死的惨状,更暗含了英国在爱尔兰进行殖民统治的残暴。实际上,托兰男子是宗教残暴统治下的无辜受害者,是宗教祭祀仪式的替罪羊,是“远古愚昧暴力的牺牲品”,它唤醒诗人内心深处的爱尔兰意识,成为“激活诗人爱尔兰民族记忆与苦难历史的活化石”(章燕,2008:339)。 然而,诗人并没有止步于仅对远古时代宗教残酷迫害事实的揭发与控诉,同时,传统宗教的残暴也并不意味着暴力行径在现实社会的结束,相反,希尼成功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对远古宗教祭祀的残忍揭露转移到对爱尔兰当时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思之中。在诗歌第二节中,希尼将铁器时代掩埋在日德兰半岛沼泽地中的托兰男子与当时爱尔兰教派冲突下的受害者联系了起来,“那些在伏击中死去的/劳动者的死尸,/有袜无鞋躺在农民院子里/等待殉葬的尸体/四个兄弟的皮肤和牙齿/斑斑点点洒在枕木上/泄露了暴力的真情,/他们被沿线拖拉了四英里”(希尼,2003:60)。其中,“四个兄弟”是在一次宗教派别纷争中遭新教徒杀戮的受害者,他们的尸首被信教暴徒沿铁路轨道拖拽示众。在宗教教义谎言掩盖下,宗教活人祭祀被美化成结婚典礼,因而,远古时代托兰男子的死亡越发神圣而受人敬重。同时,在当时的爱尔兰,宗教派别争端依然猖獗,一些极端宗教分子借宗教名义对异教徒展开大规模疯狂屠杀,并美化其极端暴力与恐怖行径,称之是对宗教纯洁性的绝对忠诚与维护,是每一个信仰者都应遵守的法则。福斯特曾这样描述希尼有意将爱尔兰过去历史与现实社会问题联系的初衷,“(希尼对托兰尸体)无意的发现与(诗人对承担责任)必要性的思考,在托兰男子这一形象中得到集中体现,他成为人类为满足社会大众现实需求而沦为宗教神秘势力牺牲品的象征,并成为希尼诉诸笔端而不断反思的意象之一:暴行,过去与现在,不仅是当代野蛮行径的真实写照,更是现代暴行的范例”(Foster,2009:33)。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诗根据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再现了四兄弟的悲惨遭遇,揭露了爱尔兰当时借宗教名义肆意枉杀民众行为的残暴,并通过古今元素的衔接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环境的愤慨。 第三诗节是建立在诗人丰富想象力基础之上的,希尼穿越时空界限,转向关注另一北方民族,并探讨在那个地方挖掘出的沼泽地人。尽管诗人面对不同的语言和习俗倍感陌生,他还是从中发现了自己与那方领土密切的关系,“在迦太兰/在古老的行刑教区内/我将感到迷惘/悲伤,就像是在家乡”(希尼,2003:60)。希尼再次将远古时代女神神圣的沼泽地与北爱尔兰当时的杀戮战场联系了起来。同时,“教区”一词为他的诗注入了天主教宗教元素,这便突出了遇难者的身份特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是为了集体利益而受宗教信仰束缚的受害者。因此,希尼借助托兰男子,通过将爱尔兰过往历史与社会现实相融合,生动再现了诗人欲借助诗歌来挖掘爱尔兰性、唤起爱尔兰民族记忆文化之根的目的。 希尼在中期诗歌创作中,致力于寻找一个能够给予诗歌权力的“地域”,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诗人艺术创作与政治权力管控的矛盾性:诗人在一方土地遭受流放,同时也是这方土地历史变迁的见证者;诗人不信任任何“地域”的政治权力,但是又不得不与之时刻保持密切联系。“管控”一词意韵深远,令人深思,不但突出了艺术表达的权威性,而且揭示出艺术创作权力被认可、被行驶的“领地”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希尼诗歌中的“地域”并不直接干预社会政治制度,诗人只是借助地名的象征隐喻表达自己对历史、对文化、对社会现实等的思考罢了。他在诗歌中辗转于不同的“疆域”,从不驻足流连某处,从不对某处投入一成不变的认识。正如希尼的沼泽地系列诗歌,不但承载着爱尔兰过往的苦难历史,更体现了诗人对当时爱尔兰宗教派系争斗与政治暴力冲突的深切关注。鉴于此,诗歌等文学创作,应该立足于对本民族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挖掘”,同时,亦应对当下社会现实给予关注;而对诗人或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借手中之笔,用文字记录供后人不断回忆、不断反思的重大事件。 三、探寻自我艺术创作“领地” 希尼早期诗歌创作灵感多源于对家园领土象征意义的挖掘,无论是对过去历史的回忆,还是对当时爱尔兰社会政治现实的关注,无不注入对“疆域”指涉意义的思考;而希尼在后期诗歌创作过程中,其艺术追求、创作素材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诗集《斯特森岛》即标志着诗人在诗歌创作主题表达方面的重大突破,从先前侧重从承载故土家园深厚历史传统的空间地域取材,并融入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关切,继而试图“挖掘”诗歌艺术更为广阔的“领地”,探讨艺术创作的真谛。朝圣遗址斯特森岛位于爱尔兰遥远的西北湖中地区,与希尼在诗歌集《斯特森岛》中提及的自我冥思忏悔圣地不谋而合。希尼最终赋予该爱尔兰传统朝圣遗址更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在此过程中,希尼不断反思诗歌创作的社会功用以及诗人或艺术家在社会中应有的位置。然而,希尼一直对文学创作本身与政治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充满焦虑,从希尼与想象中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斯特森岛》第十二首中的对话可见一斑。乔伊斯鼓励希尼从更广的时空中发掘诗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进而使诗歌叙事更为宏大。为此,希尼后期的诗歌创作更具批判意识,他并非教会等正统思想的支持者,也并没有对之全盘接受;对希尼而言,摆脱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忠实于艺术创作本身才是他最需要的。 诗集《斯特森岛》的最后一首主要讲述了诗人与想象中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之间的对话。诗人站在朝圣遗址前进行自我忏悔,达3天之久,最后,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庇佑下,回到岸边。乔伊斯反对希尼遵从天主教否定自我的主张,他告诉希尼,身为诗人、艺术家,不应受困于民族的和世俗的束缚,“作家的责任/不允许你顺从惯例习俗。无论你做什么都要独立自主”(希尼,2003:150)。继而,乔伊斯鼓励希尼张扬个性,寻找真正的自我,“你失去了更多的自我。/为了做好事救赎。背离原来的路径。/当他们把圆圈扩展开,就是你该/自己游出去之时,把你自己的频率/写满元素回声探测仪,/寻找,探查,诱惑,/小鳗鲡在大海的黑暗中微弱闪光”(希尼,2003:151)。其中,“鱼”和“雨水”两意象的使用尤其值得深思。诗中的鳗鲡,象征诗人对精神自由世界的向往,渴望在文学艺术创作的领地自在游荡,亦即,真正的艺术家,不应替特定政治言说,应该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与羁绊。此外,“水”的意象在诗中也具有象征隐喻意义,“水”在希尼早期诗歌中多指涉束缚或羁绊(如:一个水汪汪的沼泽坟墓),而在本诗中,“水”是宗教洗礼的圣洁之物,一个人接受宗教洗礼,能够得到灵魂的救赎与提升,因而变得神圣而永恒——是获得灵魂宁静的源泉。如本节诗中,尽管“水”以“暴雨”甚至“骤雨”的形式出现,并猛烈地袭击着海面,但水是鱼儿生命的源泉,诗人借雨之大表达自己终于摆脱束缚,重获新生。 希尼渴望在自由的领地天马行空、自在游弋,但亦不能完全脱离世俗的影响。思想的羽翼在高空自由翱翔,同时肉身为尘世所牵,因而,诗人或艺术家,应该在感性冲动与理性思考之间、在艺术创作自由与尘世束缚之间寻找平衡。《斯特森岛》标志着希尼诗歌创作主题思想的重要转变,希尼终于摆脱前期诗歌创作中深受民族义务与职责困扰而不得不圈囿自己思想的羁绊,逐渐意识到,“诗歌绝非政治的附庸和机械的传声筒,它必须坚持其对于生活和现实的诗性思考”(李成坚,2003:57)。同理,诗人、艺术家不应为现实社会政治争斗言说,成为宗教矛盾与冲突的代言人与牺牲品。身为一名爱尔兰诗人,“为获得认同与追求进步,(希尼)对时间、历史、地理位置与精神凝聚力的感知,成为他诗歌作品创作的动力”(Healy,1980:162)。诗人在朝圣遗址的自我反思使他获得了艺术救赎。希尼逐渐摆脱宗教教义的强压性影响以及爱尔兰充满争议的历史说教传统,并成功地重新建构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因而,希尼在对当时爱尔兰传统历史文化与现实英爱政治问题进行言说的背后,饱含着他对“爱尔兰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态度:在‘既定’的英国文化影响的事实下,保有爱尔兰性,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与共存中,形成一种‘双向的忠诚’”(李成坚,2003:57)。这种“双向的忠诚”态度,不是诗人对现实政治矛盾问题的逃避,亦不是对两种政治文化归囿选择的妥协,更非一种不偏不倚、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相反,它超越了现实政治矛盾的束缚,不拘泥于成为某一宗教派系或政治力量的喉舌,从纯粹文学创作的“高地”反思艺术创作的真谛。纵然,诗歌创作的素材与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诗人或艺术家绝不应沦为政治现实论争的傀儡,希尼借想象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之口重新诠释了诗人在社会中的真正位置、诗歌的地位与作用,并最终主动承担起诗人在文学创作中应彰显文学良知特性的责任。 纵览希尼早期诗歌创作,可以发现,诗人已经寓自我诉求于字里行间,借不同“地域”行使自己的诗歌创作特权,但是,诗人诉诸文学而发言的权利一直受到自己居无定所、不断遭受流放现实处境的摧残。似乎,希尼诗歌中不同“地域”“管辖权”的潜在威胁削弱了诗人对寻求艺术家真正身份认同的信心。在诗歌《挖掘》中,诗人徘徊在实际民族家园与自我想象的“避难所”中。接着,在诗歌《托兰人》中,诗人内在的归属感受到沼泽地系列意象与神圣不可定义“地域”的冲击。然而,自己理想的“避难所”依然无法使诗人获得自我归属感的慰藉,因为诗人所构想的“避难所”是建立在希尼对民族家园必须承担的义务之上的,为确保艺术创作的纯洁性,他深陷诗人、艺术家内在需求与外在社会公民职责义务的“囹圄”中无法自拔。最终,诗人在《斯特森岛》中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家与社会间矛盾性问题的独特见解。实际上,诗人通过内心流放、挣扎重获新生,于家园中得以摆脱现实羁绊、表达艺术家内心真实的想法,对诗人和艺术家在社会中的“位置”有了更为鞭辟入里的认识。 希尼在诗歌创作中不断背离自己的家园“领土”,同时又始终没有完全与之割舍,表达了诗人由于深受北爱尔兰传承思想的影响,而对艺术权威的不确定性表示焦虑。诗人逐渐意识到将自己诗歌创作注入社会政治现实氛围之中的必要性,不断思忖着艺术语言在社会现实面前的效力问题,并提供一个极具建设性的视野,或者唤起人们对现实的再思考。在艺术创作领地,希尼始终在寻求爱尔兰民族传统与英国文化的平衡方面不遗余力,如其所言:“当我的根和我阅读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时,我就成了一名诗人”(Foster,1989:14)。即便如此,希尼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爱尔兰民族身份,他曾经告诫欲将其诗歌收录于爱尔兰诗集的编辑说,“我们都从不曾举杯/为女王敬酒”(Johnston,2003:122)。希尼从未放弃自己的爱尔兰民族身份,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自我艺术追求立场;诗人所处的无形“位置”不应局限于自我民族家园的狭小“疆域”,相反,诗人、艺术家应该对整个宇宙万物投入普遍的人文关怀。 总之,希尼在生养自己的那方热土上,运用笔杆不断“挖掘”,将爱尔兰性、爱尔兰民族记忆注入自己的诗歌创作。早期诗歌故土家园情结浓郁,大大小小的地理空间是爱尔兰悠久历史的符号象征,形形色色的实际地名是爱尔兰民族传统文化的隐喻,诗人视之为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唤起爱尔兰遥远民族记忆的纽带,诉诸笔端,以不同的“位置”为创作蓝本勾勒爱尔兰历史图景,传达对爱尔兰传统历史文化的关切,这是对爱尔兰祖辈传统农耕文明的僭越,更是发扬与传承;随着英爱冲突的加剧,希尼逐渐陷入公民社会义务与艺术诗学责任担当相矛盾的两难境地,希尼逐渐摆脱民族“疆域”的有限限制,在“挖掘”爱尔兰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唤起爱尔兰民族意识与民族性的同时,亦寄寓诗人对当时爱尔兰社会现实矛盾与宗教冲突等问题的关切,并能够跳出自身在面对爱尔兰民族传统意识与英国文学滋养相矛盾、英爱冲突的社会义务与艺术创作的诗学责任背道而驰时的藩篱,依靠想象,借古喻今,通过远古时代掩埋下的泥沼反观社会现实矛盾与冲突,并在不断地反思中摆脱艺术家政治身份的归囿,从纯粹文学创作这片净土中关照诗人或艺术家创作的伦理向度,“提出多元平衡、坚持双向度思维的诗学主张,实现了从文学创作到参与文化建构的飞跃,履行了当代作家的责任感,发挥了当代文学的社会文化参与作用”(李成坚,2005:126),到达更为广阔的文学创作“领地”。 在当今社会,全球文化交流进程加剧,各国文化传统碰撞交织,族裔文学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希尼的诗歌创作哲学必将给后起文坛新秀以深刻启迪。他善于从自己最为熟悉的地理“疆域”获取创作素材,借助想象,融古通今,既有对历史过往的追思,亦有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虑。面对自我身份归属的困境,在社会现实义务和自我艺术追求相矛盾时,希尼始终保持中立,没有沦为政治说教的喉舌,并主动承担起彰显文学内省特性与文学良知功效的责任,从纯粹文学创作的高度对社会现实寄予深思。同时,希尼诗歌创作的“位置”观,亦必定会为广大读者解读文学作品给予点拨。正如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颁奖词所言:“他的诗作既有内在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希尼,2003:2)。诚然,纵观希尼近一生的诗歌作品,“不论是对古代经典、北爱历史,抑或社会现实、英国与爱尔兰文学传统的认识,还是对诗人身份独到的见解,实际上,无不证明(希尼)借助诗歌‘韵律美’进而彰显‘伦理思考深度’”(O' Donoghue,20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