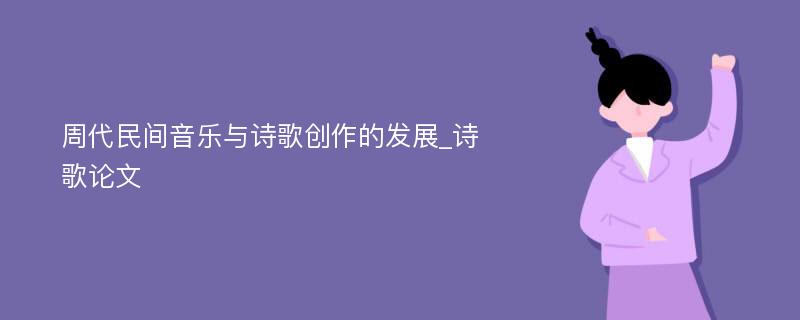
周代俗乐的发展与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代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149-04
原始社会时期的诗、乐、舞本是合而为一的,也没有所谓的雅俗之分,它与原始宗教活动、生活方式等一起构成了一个氏族的原始文化。至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随着氏族的分化,阶级的出现,很多权利为上层阶级所垄断,而用于各种仪式的乐、歌也随之被垄断,于是诗歌、音乐也出现了雅俗之分。据《汉书·礼乐志》等典籍记载: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①,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时代的雅乐。夏商时期,雅乐得到了快速发展,舜之《大招》、禹之《大夏》等乐舞被保存下来而且得到流传。到了周代,为了适应礼乐的需要,诗歌创作进入繁盛期,且诗歌文本通过结集的方式也得以保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在雅乐兴盛的同时,俗乐也得到长足的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甚至可以达到与雅乐分庭抗礼的地步。随着俗乐的发展,一大批官方倡优应运而生,民间的专业歌手也相继出现。俗乐的发展与专业歌手的出现大大推动了周代诗歌的创作与流传。
一、周代俗乐产生与发展
在周代建国之初,周人便着手建立自己的一套礼制并创作与之相适当的乐歌。周成王“兴正礼乐”②,康王“定乐歌”③。通过这两次大型的制作乐歌的活动和后来代代君主的增益,使周代的雅乐得以快速发展,且进入鼎盛时期。
进入周人雅乐系统的乐歌也并非全是由上层贵族所创作,其中不少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风诗。如产生于豳地的《豳风》用于各种祭礼活动之中,其中的《七月》或称为“豳雅”,或称之为“豳颂”④;产生于江、汉与淮河流域的《周南》和《召南》,既用于各种大型的仪式,也用作房中乐。而更有些产生于民间的诗歌直接被编入雅诗之中,所以陈子展《小雅·我行其野》注说:“《采薇》、《鱼丽》、《杕杜》、《祈父》等篇皆似民风。……其实《大雅》、《三颂》何尝不间有类似民风之作乎?”⑤这说明,今本《诗经》“二雅”中的一部分诗歌原本是各地风诗,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得以进入雅诗系统,其乐曲经过改造也进入到了周王室的雅乐行列。
这种风诗入雅的过程可能与周王室乐官对风诗进行过筛选的工作有关,而更多的则是周王朝专门掌管四夷乐舞的旄人和鞮鞻氏的功劳。据《周礼·地官司徒》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⑥“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⑦旄人的职责是教导散乐之舞和四夷之乐舞,鞮鞻氏主要掌管四夷之乐歌,一掌舞,一掌乐歌。这些乐舞不仅可以作为用于日常生活的燕歌而存在,同时也可以用于祭祀和娱乐宾客,从而进入雅乐系统。正因如此,旄人和鞮鞻氏所掌的乐歌既可以作为俗乐,也可以作为雅乐,因而他们具有将俗乐提升至雅乐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由于后天大量的风诗进入雅诗和颂诗系统,导致《风》《雅》《颂》相错。孔子极力想恢复周乐的本来面貌,到晚年终于成功,所以他自豪地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⑧朱熹注曰:“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阙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⑨
西周时期,周王朝具有节制诸侯国的强大功能,王朝礼制得以顺利实施,雅乐兴盛。各地方乐歌被诸侯国的乐官所收集整理,除少数乐歌进入雅诗系统之外,大多数风诗依然以地域性诗歌而存在,其乐歌也只具备所谓的俗乐身份。至东周以后,礼制崩坏,音乐制度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概括这一时期的礼乐崩坏情况时总结说:“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⑩用于宗庙祭祀及国家典礼的雅乐强调教育意义、道德观念,突出平和中正、庄严肃穆、雍容华贵,而世俗的新声显得生动活泼、旋律自由,所表现的内容也更加接近世俗的生活,所以与雅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郑风、卫风为代表的世俗之乐的流行,既反映出人们对娱乐的需要,也反映了时人对新声的渴求。所以,从东周至战国时期,俗乐发展成了可以与雅乐分庭抗礼的大众乐歌,上至王侯、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对它情有独钟。《礼记》中记载魏文侯语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11)
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新声的流行也有着地域的差异。郑、卫之地为春秋以来新声的发源地,其柔美的情歌被孔子视为乱雅乐的靡靡之音;齐鲁大地后为居上,齐都临淄更是歌舞盛行,所以《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12)而处于燕赵之间的中山之地,素有一种剽悍之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13)。这种民风民情培育了燕赵之地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
而地处南方的楚国,其俗乐的发展更不让于北方。楚国之俗信鬼而好祠,常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故其世俗之乐也尤为发达。宋玉《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14)这说明,《阳春》、《白雪》之类的雅乐受众远远少于《下里》《巴人》《阳阿》《薤露》之类的俗乐。
随着俗乐的发展,春秋战国之时,被视为周王朝礼制有机组成部分的音乐元素走下神圣的殿堂从而落户于寻常百姓之家,用来演奏雅乐必备的钟、磬等乐器为普通的竽、瑟、琴、筑等常见的乐器所替代。喜欢音乐的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凭借手中的一件简单的乐器或慷慨高歌,或低呤浅唱,流行的俗乐就成了世俗的人们表达情感、娱乐心志的重要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俗乐的兴起也正是原始时期音乐文化功能的复归。
二、俗乐的流行与倡优、民间歌手的出现
在歌舞艺术发展史中,倡优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低下,但是却对中国古代的音乐、舞蹈、杂技等表演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据相关文献记载,早在夏代便有了倡优这一称谓,据《事物纪原》卷9“俳优条”引《列女传》曰:“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而为奇伟之戏。”(15)可见,倡优、侏儒在夏代就以宫廷的“奇伟之戏”的表演者而出现。至西周时期,由于礼乐制度森严,从周王室至各诸侯国蓄养倡纳优的现象并不多见。而至春秋以后,各诸侯国在邦国的重大礼仪场合虽然也以所谓的雅乐来装点门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争相养倡优、纳侏儒,供自己观赏娱乐。这些倡优们或以活泼动听的俗乐刺激统治者的听觉,或以美色满足统治者们的视觉需求,或以各种新奇的杂技表演来代替传统的程序化的舞蹈,或以讲故事、说笑话的方式取悦于他们的主人。由于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是当时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自然而然地把诸多民间俗乐和民间表演艺术带进了宫廷;随着民间艺术大量步入上流文化圈,上流文化对这些表演艺人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于是一种新型的演艺群体——倡优也随之出现。这些倡优不再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者,而是从事歌舞、说唱、杂技表演等的专职艺人。在倡优所精通的诸多技能中,最为普遍和擅长的还是歌唱,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原本是乐人出身。
先秦的倡优因为天天在君王身边,有时也会卷入政治漩涡之中,甚至参与改变诸侯国历史走向的政治谋划。如春秋时晋献公时的优施,私通于骊姬,施优多次献计,骊姬顺利地除掉了申生,逼重耳、夷吾外逃,使自己如愿以偿(16)。还有些倡优以自己的杰出的表演天赋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以艺术方式微言劝谏当政者,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的楚国的优孟和秦国的优旃便是典型代表(17)。
当一大批男性艺人以倡优的身份进入宫廷,将民间艺术带入上层社会的同时,民间长于歌舞的女性艺人们也不甘寂寞,纷纷以各种方式展现其才艺,或求平步青云,或以闻达于世。如以俗乐发达而闻名的燕、赵、郑、卫等地之女,以其超凡的技艺与美色,游于富人之家,进入宫廷之内。所以,《史记·货殖列传》说中山一带的女子“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18)。而李斯的《谏逐客书》更以“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19)来形容秦国的众多外籍女子。《楚辞·招魂》中大写楚国宫廷乐舞之盛况,所歌之乐有“吴歈蔡讴”,表演之人有“郑卫妖玩”(20)。楚国宫廷里所歌的吴歌、蔡乐固然可以由楚人自己来表演,但也不排除是吴地、蔡地艺人所为。而“郑、卫妖玩”一语则表明楚国宫中有大批的以来自郑地、卫地为代表的民间女性倡优。
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倡优之性别不限男女,大凡除表演雅乐之外的以从事专职歌舞、说唱艺术的男女都统称之为倡优,他们以歌舞表演为职业,并以此谋生,游走于上流社会和富贵豪门,被特定的人群所畜养、宠爱,有较为固定的服务对象和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与此同时,民间的专业歌手也相继出现。《宋书·乐志》载:“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若斯之类,并徒歌也。”(21)《宋书·乐志》中所的提到的秦青、薛谈、韩娥、王豹、绵驹等,都不同于供职于宫廷或富贵之家的倡优,他们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间专业歌手。从《乐志》“《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的评价来看,是将这些歌手所演唱的歌曲视为与雅乐相对应的俗乐。这些民间歌手与倡优的主要区别是:他们的服务对象不是王公大臣,也不是富家子弟,而是普通的百姓;他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有些甚至靠卖歌为生。为了提高演唱技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师从前辈歌手,且一旦成名之后,又会有很多追随者,使自己的演唱技艺得以广泛流传,甚至形成一个流派。
三、俗乐对周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早在史前时代出现的民间乐曲,是一种纯为抒发情感而随机创作的作品。其演唱者既没有功名目的,也不带任何经济目的。而夏、商、周时期的宫廷雅乐工作者则直接供职于王室,服务于王室的礼乐制度与政治教化,也并不考虑经济效益。当历史发展至春秋时期,雅乐衰退而俗乐代之而起的时候,它带来的不仅是人们礼乐观念的改革、欣赏品味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诗歌创作的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雅诗创作进入尾声,而民歌创作方兴未艾;宫廷正统诗人退出历史舞台,而倡优抒情之作兴起;诗歌的教化功能衰退,而媚俗、合俗的消费型诗歌大量产生。
随着一批专业歌手的出现,乐歌便与经济价值联系在一起了,而诗歌和音乐的创作也就具有了经济目的。因为这些歌手们需要将自己的技艺传达出去并且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名声与相应的报酬,一是为了扩大影响,二是为了保障衣食。于是歌手与听众之间便有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这些歌手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听众,除提高演唱技巧之外,还要大量创作新歌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这无形中会推动诗歌创作的发展。
可惜的是,由于春秋后期的战国之际各邦国没有专门人员来收集和整理诗歌,也许曾经整理过而不像《诗经》文本一样得以保存和流传,这些歌手们所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今天已不能看到了。但从零星的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精品,以汉代流行的《薤露》、《蒿里》二诗为例:
崔豹《古今注》卷中《音乐》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故用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滋,人死一去何时归!’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摧促,人命不得少踟躇。’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22)
说此诗原出自田横门人不可考,但它是齐人创作的诗歌应当是可信的。因为这与春秋至战国之际齐鲁之地的音乐传统有关系。《宋书·乐志》说,韩娥到齐国城门雍门一带以卖歌为生,其长调悲歌声使附近的大大小小悲愁垂涕,三日不食;又作轻声长歌,使老幼喜跃不能自禁。所以后来这一带的人擅长悲歌,是受了韩娥的影响。《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一年》曰:“(鲁哀公)会吴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23)杜预注曰:“《虞殡》,送葬歌,示必死也。”(24)这说明,在齐鲁一带,早已流行一种送葬的歌曲,虽然我们不能了解春秋时期鲁国丧歌《虞殡》的内容,但一定是有歌辞的,其内容当与人们对生命的思考有关。韩娥之悲歌能够在齐鲁大地有一定的市场,这当与它的文化背景有关。至战国末期,齐人田横的门人也许是采用了原本流传的歌辞,或许经过一定的再加工。但《古今注》中所录的《薤露》《蒿里》也许非先秦齐地丧歌的原貌,但透过它,我们依然可以窥视战国丧歌的大概内容。
由于一批民间歌手的出现,专门送葬歌的产生,也出现了为了谋生而专门为别人唱丧歌的歌手,《薤露》《蒿里》则是专为送葬所创作的。
同时,先秦时期,还有另一种称为“成相”的说唱艺术广为流传。所谓成相就是当时盲人拿着小鼓到处演唱的一种歌辞,其形式正如后天流行的莲花落、凤阳花鼓之类的小调。这种民间歌曲在先秦时有很多种,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有:成相杂辞十一篇,而歌辞今已不传。这些歌辞也是艺人们为谋生所创作的消费品。后来荀子依据这种民间短歌创作了著名的长诗《成相篇》,流传至今。
总之,周代俗乐的兴起与发展,在中国的音乐和诗歌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打破了西周时期雅乐一统天下的局面,对推动音乐朝着多元化发展、丰富音乐表现技艺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俗乐的发展,专门从事演唱、各种技艺表演的倡优产生,民间的专业歌手也应运而生。俗乐的兴起和专业歌手的出现推动了民歌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同时又为传播民间乐歌做出了巨大贡献。
①⑩班固:《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8、1040页。
②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0页。
③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77页。
④⑥⑦贾公彦:《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第801、801、802页。
⑤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29页。
⑧⑨《论语·子罕》(四书集注本),岳麓书社,1987年,第163页。
(11)孔颖达:《礼记正义·曾子问》(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97页。
(12)《战国策》,上海书店,1987年,第76页。
(13)(18)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63页。
(14)吴广平:《宋玉集》,岳麓书社,2001年,第88—89页。
(15)高承:《事物纪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5页。
(16)《国语·晋语一》,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17)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14页。
(19)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44页。
(20)洪兴祖:《楚辞补注·招魂》,中华书局,1983年,第209—211页。
(21)沈约:《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548—549页。
(22)崔豹:《古今注》(百子全书本),岳麓书社,1993年,第3672页。
(23)(24)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74、17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