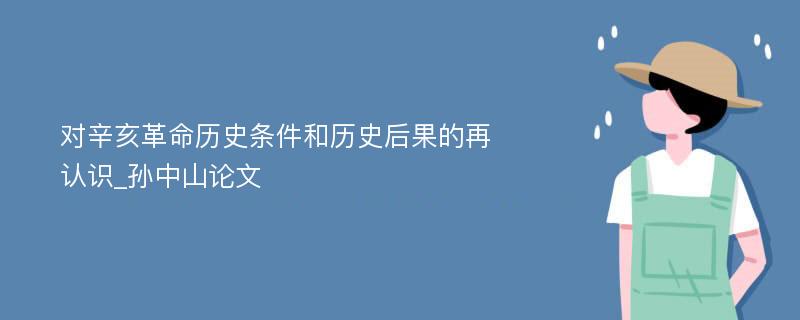
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再认论文,结局论文,历史条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For a long time it wa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inhistorical circles tha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s a greatsuccess.At the same time.however,it was a failure as well.At first sight this conclusion seems dialectical and dual-sided.But in my opinion it is parodoxical.
As far as overthrowing the Qing Dynasty is concerned,theo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Revolution were mature while thesubjective ones comparatively immature.As far as establishingthe republican politics is concerned,neither the objectivenor the subjective conditions attained their maturity.Apartfrom that,the outcomes of the Revoluton shows that the QingDynasty was overthrown indeed and the republic politics began.So the revolution can't be oversimplified in such a simpleword as"failure",unless it is compared with Dr.Sun Yixian'sidealized promise"accomplish the whole revolutionary task atone stroke"
一
任何革命运动都不是凭空发生的,既离不开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摆脱不了革命者自身主观条件的规定性。辛亥革命无疑也不例外。无论就推翻清朝而言,还是从建立共和政治而论,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并不十分理想。
一、就推翻清朝而言,客观条件比较成熟而主观条件并不成熟。
客观条件相对成熟的主要表观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清朝统治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险象环生。
自乾嘉以降,中国社会经济受自身所固有的周期性发展规律的制约,就已相对停滞。随着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人民饱经战争创伤,原有的生产生活条件都已无法保障,目不暇接的巨额赔款又铺天盖地而来。据不完全统计,迄至1909年上半年,清政府所欠战争赔款和外债连本带息多达1.3622亿英镑,折合银两为9.08163933亿两〔1〕, 即使统治者大肆搜括,当时的年国家收入也不过2.9696亿两,而岁出多达3.3865亿两,不敷为4169万两〔2〕。固然,在晚清新政施行过程中, 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应有所增加。只因原有的经济基础过于薄弱,积重难返,国家经济命脉又已为列强所控制,地方督抚分享中央财权已成惯例,加之新政项目一哄而上,开支浩繁,清朝财政的困境不但未曾有所改观,反而每况愈下。
新政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倒是基本形成了。广大资本家已不满足于清王朝对自身经济活动的提倡和奖励,也不满足于撤冗衙、清吏治之类官样文章,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实行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尽快建立君主立宪制、他们同袁世凯、张之侗、端方、锡良等开明官僚达成默契,要求速开国会,从根本上杜绝反清革命运动的发生,避免内乱和列强干涉。他们在精心实业建设,倡导和组织一系列抵货、保矿、保路运动的同时,还充当着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后盾或主导力量。慈禧太后于1908年一命鸣呼后,资本家阶级要求速开国会的心情就越发迫切,其政治态度也日趋强硬。
清朝统治者曾经异想天开地指望通过官制改革和预备立宪,收回自湘军问世以来旁落地方督抚手中的那一部分中央集权,尤其想削弱比曾国藩的湘军强悍数倍的袁世凯北洋新军势力,结果也是适得其反。殊不知,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相适应的还有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及其社会影响。它们借助于洋洋大观的直隶新政和沸沸扬扬的预备立宪而迅速扩大,尤其是袁世凯那“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3〕的姿态和决心赢得资本家阶级和社会舆论的好评。无怪乎, 当载沣以“足疾”为由罢免袁世凯时,引来的却是社会舆论对袁氏的普遍同情。满汉矛盾实际上是在朝着有利于袁世凯的方向激化着。
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封建统治者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却不顾“民力已岌岌不支”〔4〕的事实, 把大批新政费用强行摊派给超负荷生存的下层人民。加之连年灾荒,天怒人怨,下层人民的自发反抗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自发性抗粮、抗捐和抗税斗争每年均在100次以上,1910年还增至266次〔5〕。 忍无可忍的下层人民纷纷捣厘卡,惩税官,驱污吏,烧衙门,形式多样,起伏连绵。如此频繁的自发性群众反抗尽管还不足以给手操国家机器的清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却逐渐摇憾着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历史总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遭到这样的事情”。〔6〕跚跚来迟的清末新政不但没有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反而带来了清王朝的覆灭。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新政本身招惹所致,还不如说是清末预备立宪政治遗产的继承者载沣之流并不懂得现代化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正是由于他们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强行镇压下去,资本家阶级及其君宪党人才被迫同反清革命战士握手言欢,站在同一战壕并肩作战。上述没落王朝所固有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就迅速表面化,并且陡然加剧。
倘若威镇群臣的慈禧太后和颇得士人拥戴的光绪帝不是在两天之内奇迹般地死去,以谘议局为据点的君宪党人和资本家阶级能否越发措辞强硬地要求连开国会?倘若天假以年,慈禧太后能于两年后目睹震天价响的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她将采取什么举措?我们已不得而知,因为历史无法假设。而问题在于,既然载沣之流愚不可及地把积诚罄哀的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那么,所谓“铁道国有”政策和“皇族内阁”公布之日,便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苦心倡导十余年的反满民族主义声势空前高涨之时,这是因为,以重新出卖路权为核心的“铁道国有”政策既羞辱了以资本家阶级为主体的路股集资者的爱国热情,也触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皇族内阁”的出台既嘲弄了充满政治激情的资本家阶级和君宪党人,激化了满汉矛盾,也导致了满族内部一般成员的不满,增加了皇室成员同一般成员的矛盾。此时此刻载沣之流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曾经孤身抵抗反清革命浪潮而不遗余力的君主立宪运动代言人梁启超也开始对黄花岗起义的将士们公开表示敬慕,并且慎重声明:“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7〕。如果说1903 年的拒俄运动横遭清廷镇压是许多留日学生纷纷转向反清革命行列的一个契机,那么,载沣之流将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就成了清王朝自取灭亡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载沣所把持的清朝政府日形孤立,一向嗅觉灵敏的西方列强也决定不再扶植这个“洋人的朝廷”,这也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还在1911年2月,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同日本公使加藤会谈时就明确表示:“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8〕格雷的态度在西方列强中是颇有代表性的。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列强各国就纷纷表示中立,已不再为清王朝撑腰助威了。
尽管如此,反动统治者总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革命胜利的获得离不开革命者自身的努力与奋斗。相对于渐趋成熟的客观条件而言,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却还不尽人意。
首先,革命党人缺乏一定的群众基础,革命的声势大于革命的力量。
如所周知,任何革命斗争都是千百万人的事业,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远非少数人的奋斗便可竟功,然而,面对阵阵紧逼的民族危机,孙中山等人似乎还没有想到必须耐心细致地发动人民群众,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他们从容发动之。同他们那炙手可热的革命激情相适应的是急功近利的躁进心理。象黄兴那样温文尔雅的革命元戎,最使他所赞叹的也是“能争汉上为先著”的革命首功。他自己最能使后人铭记于心的,除了其笃实谦和之为人外,便是那屡败屡战的戎马英姿。
在近代中国异常艰难的历史环境里,作为有产者的广大资本家一般都不赞成暴力反清,只希望通过和平请愿,祈求清廷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在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象沈缦云、龙璋等人那样热情支持同盟会反清活动的资本家还寥若晨星。资本家阶级充当了君主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却并未同时充当反清革命运动的阶级基础。孙中山等人过多地强调反满同请愿立宪的政治界限,很少在牵动千家万户的君主立宪运动和抵货、保路、保矿运动中切实扩大自己的影响。对于下层人民自发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他们也基本上不闻不问,我行我素。这些缺陷反映了反清革命者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也体现了以“中等社会”自居的革命知识分子对“下等社会”的政治偏见。
在历次武装起义队伍中,高举反满旗帜的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知识分子,起而应之者主要是临时联络仓卒策动的会党和清军。会党固然也来源于社会底层,且不乏反满传统,只因习气使然,易聚易散,颇难领导。孙中山等人带着海外华侨的捐赠前往发动时,常常不得不以厚饷相许,俨然一雇佣军。结果,会众因饷银不至而临阵解散者有之,饷银到手后一去不复返者亦有之〔9〕。 会党的革命精神及其战斗力显然并不如有些学者所估计的那么可观。就拿曾经领导萍浏醴起义而名震遐迩的洪江会首领龚春台来说,起义一败,他就迅即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及至清朝覆灭,他才从民间冒出,而且表现平平,锐气远逊当年〔10〕。
革命党人联络清朝军队时,多赖军官倒戈,或策动防勇哗变,也往往不可靠。黄兴谋划防城起义和上思起义时,就寄厚望于颇有乡谊的巡防营统领郭人漳,结果也是大呼上当,黄兴等人还差点遭到暗算。究其原因,此类军队“实未受革党主义之陶熔,其变而来归,虽受党人运动,但只因其乏饷与内部之不安而煽动之,其军官向来腐败,尤难立变其素质,而使之勇猛进行”〔11〕。1909年后,有的同盟会员把联络重点转向新军,也多属仓促发动,起义之火燃得快,灭得也快。象刘复基等人那样注数年心血,默默无闻地发动新军者似不多见。反清革命队伍似乎并未通过历次武装起义而直接获得量的积累。
其次,同盟会内部长期四分五裂,削弱了原本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自1907年3月始,章太炎同孙中山交恶,互相攻击,闹得不可收拾。宋教仁同孙中山之间,陶成章同孙中山之间也是矛盾迭出。连黄兴也因国旗式样问题同孙中山吵得面红耳赤,颇伤和气。虽因黄兴主动让步,两人和好如初,而争吵本身的消极影响并未由此而日出冰融。当章太炎等人提议改选黄兴为同盟会总理时,黄兴竭力维护孙中山的威信,果断拒绝此议。至今为止,学者不察,把黄兴拥护孙中山与顾全革命大局同日而语,异口同声地强调黄兴顾全革命大局的历史功绩。其实,在同盟会内部已经一盘散沙,连孙中山本人也抛开同盟会而另有他图的情况下,黄兴一味拥孙所顾全的大局不过是个空局〔12〕。君不见,自章孙纠纷发生后,同盟会总部就已名存实亡。不仅张百祥、焦达峰等人以“共进会”名义另树一帜,而且孙中山于1909年11月宣称,他已在南洋“从新组织团体”,“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13〕。次年2月,孙中山还首次打出“中华革命党”旗号,并且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稍作改动〔14〕。在此情况下,章太炎和陶成章也不甘示弱,重新挂出光复会招牌,争相发展会员。
平心而论,具有“协理”之称的黄兴虽然为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和威信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也不过是以“免陷兴于不义”为前提,自己考虑最多的主要是他和孙中山的个人关系这个小局,并不是同盟会的整体建设这个大局。同盟会章程中所写的“四年更选一次”领导机构的规定只是一纸空文,黄兴并没有对整顿同盟会发挥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同盟会的瘫痪状态一直维持到革命高潮的到来,接着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二、就建立民权政治而言,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还不完全成熟。
千百年来,无论是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是自然经济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地主制经济,都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坚实基础。“民主”一词虽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里早已有之,那也不啻是“人主”、“君主”、“民之主”或“为民作主”之代名词,它同西方政治学说中的“民主”(Democracy)即“人民当家作主”之义隔若霄壤。 风尘仆仆留学归来的革命党人平时所接受和宣传的民主思想都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留下的历史遗产中挑选出来的,并不是中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下层人民长达十余年的自发性抗粮、抗捐、抗税斗争为何大都只是以合法形式展开,却不见洪秀全那样的“奉天讨胡”者,再试做一次“汤武革命”?那些走投无路的饥民捣毁县衙甚至堂堂抚署的激烈举动为何只是针对地方污吏,而不是顺水推舟地指向腐败无能的清王朝?个中原由,似乎还有待专题研究。本文因篇幅有限,姑置不论。而问题在于,既然在为数众多的下层人民中连推翻没落王朝的“汤武革命”都还难以产生,倘若要引导他们从事超出“汤武革命”范围的民主革命,推翻帝王制度,无疑更不容易。同为广大人民,即使是一字不识的劳苦农民,他们大都是在世代相传的君臣父子主义的薰陶中走向人生的。即使曾经驰骋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将士,他们也从未祈求过一种既不需要爱新觉罗之皇恩,又无需向“天王”洪秀全跪叩的新生活。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甚早的英国,那里的人民就对君主制有着某种特殊的感情。“当国王在白金汉宫时,全国人民睡眠得更安静,更和平。”〔15〕英国是如此,曾被马克思比喻为“木乃伊”的古老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固然,自戊戌维新运动发生以来,特别是经过历时数年的清末立宪运动,部分有识之士办报刊,兴学堂,作讲演,大量出版《公民必读》、《议员要览》、《地方自治制纲要》等宪政书籍,在民权启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也产生过一些社会影响和效果。只因民权启蒙任务本身的艰巨性所在,国民的整体素质还很难迅速改观。“誓起民权移旧俗”的梁启超认为国民的素质不足以行民宪制,只能行君宪制〔16〕,以反满为前提的革命党人在论战中却用推测性的语言回答说:“中国国民,必能有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17〕。没有也不可能理直气壮地用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已有为共和国民之资格。他们心底里对国民素质的估计同自己的论战对手梁启超的观点并不矛盾。关于这一点,他们在字里行间时常有所流露。
当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美国《独立》周报的社论就发出疑问,一个习于墨守成规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可以成为一个共和国吗”〔18〕?另一家报纸也认为,“中国的皇帝是天子,与日月星宿同辉,在这样的观念下根本不存在共和制度滋长的土壤”〔19〕。
革命党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观条件也并不十分理想。尽管他们在高擎反满大旗的同时,难能可贵地把民主共和旗帜紧握在手,但他们宣传得最多,也最有影响的还是前者。究其原因,他们不仅缺乏象国内君宪党人那样合法宣传民权思想的诸多便利,而且自身的民主素质并不很高,对民权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作者章太炎那样误将“民主”理解成君主之意的革命党人固然并不多见,不过,正如有的当事人所回忆的,“关于‘建立民国’这一条,当时大家所了解的就是以后将以法兰西、美利坚那样的共和国来代替大清帝国,谁都没预料到几年后就出现了辛亥革命那样迅速推翻清朝统治的局面,心目中总觉得新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是比较遥远的问题,何况有法、美等国的现成模样,可以依样画葫芦,不必多费精神,因此对民主、共和缺乏真正认识,也说不上早具信心”。〔20〕宋教仁曾在留日学生中强调:“四川、两湖、两广、云南各省同志,都积极进行,大约一两年中,一定有大举。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21〕如此真知灼见,也不过一如空谷足音、应者寥寥无几。
有的学者也承认革命党人整体上的民主素养和思想水平不高,认为革命领袖孙中山同一般党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应该说,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是相对有限的。
诚然,孙中山作为近代民主革命领袖,是它为这场革命提供了比较系统的革命纲领,影响了几乎整整一代革命者。他的民权主义思想水平自然比一般同志要高些。不过,相对于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这方面也还不是他的强项。他把那些本质上属于改造封建专制制度之同路人的君宪党人斥为“汉奸”,并且同吴三桂、洪承畴等人相提并论〔22〕,就是因为他十分看重反满民族主义。在他亲手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里,这位民主革命领袖就虔诚地祈求“我汉族列祖列宗神灵默佑相助,使恢复我中华祖国”〔23〕。及至溥仪退位,清朝皇统结束,他还特意驱车前往明孝陵,向明太祖的亡灵祭告自己的“光复”之功,可谓有始有终。
对于反清革命,孙中山有过一段著名的解释:“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24〕在这里,孙中山无疑把反满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紧密结合起来了,但并不等于说他的民权主义思想内容就已十分丰富。他在这里所针对的主要是君主制政体,并不同时针对以汉族官僚地主占多数的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在他的革命纲领里,除了极少数所谓“汉奸”外,多数汉族官僚地主均可在政治革命的风暴中秋毫无损,甚至还很容易引为同志,一同建设新生的民国政权。毫无疑问,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纲领“没有一个贵族阶级……需要废除,也没有被禁闭着的社会阶级需要解放”。“革命取代了王位,但它却不具有如同法国革命、19世纪革命或以后的俄国革命所经典地规定了的其他那些革命目标”〔25〕
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方面的上述缺陷,既源于自身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也同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密切相关。如同他的民族主义只局限于满汉矛盾的小圈子,不厌其烦地宣称一律保护西方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一样,既有认识上的失误,也苦于自身反帝力量的不够。耐人寻味的是,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民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战略上的某些缺陷,却曾在反清革命实践中奇迹般地转换成某种策略功能,在相应的时空里显示出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互补性。
孙中山一代人在民主素质方面的不足还时常体现在革命准备时期的具体组织活动中。
同盟会章程明确规定,总理“由全体社员投票公举”,而当时众望所归的孙中山之总理一职却只是由黄兴提名,然后大伙举手通过。这桩小事表明,以民权政治为主要目标的反清革命政党同盟会一开始就不是严格按章行事,不是采用有助于建立民权政治的有关民主程序开展活动,对干部和会员进行基本的民主素养训练和培养。较之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等君宪团体,同盟会都还显得逊色三分。同盟会的领导机构虽然仿行“三权分立”原则,也只是形同虚设,执行部、评议部和司法部从未独立开展活动。即便集中活动,也缺乏制度性和经常性的民主协商。孙黄之间的国旗之争,孙章之间的经费问题之争,都主要因为孙中山事先不同大家通气,事后又不能冷静地对待不同意见而骤然迸发。
对于同盟会的一会之首孙中山来说,这倒是非同一般的毛病。他虽然不难使为人谦和宽厚的黄兴及时退让和服从,但要团结和领导好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谭人凤、张继、焦达峰、孙武等同样个性较强的各路骨干,步调一致地完成近代民主革命大业,显然就不容易了。
革命领导者自身民主观念和组织观念的相对淡薄,直接影响到同盟会的团结和发展,其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不说别的,当反清革命高潮到来时,西方列强之所以只保持中立和观望态度,而不愿再向前跨一步,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们认为“革党亦派别纷岐,显无真正领袖”〔26〕。美国驻华外交人员甚至视孙中山为“来自广东省的地方性政治人物,并不是受大家支持的全国性领袖人材”〔27〕。列强的偏见同事实交织在一起,怎不令人遗憾!
笔者无意于非议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开山者和奠基者,只想说明,他在民主观念和民主作风上的某些缺陷,既是他不曾很好地团结同志,共创伟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同他分道扬镳的关键所在。
孙中山是如此,多数革命骨干也是如此。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事实是,象宋教仁这样始终兼顾民权理论研究,不乏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却始终曲高和寡,甚至为同志所不容。在宋教仁倡导的民初议会斗争期间,袁世凯的帮闲攻击他有自任总理野心,无疑出于前者的险恶用心,不足为训。而在此之前,革命同伴给宋教仁以类似的打击,就未免令人心寒。例如,在讨论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方案时,宋教仁根据自己对国情和革命形势的认识,提出设立内阁制,不赞成总统制。基于此,党人中讥讽他图谋自任总理者有之,挥拳殴击者亦有之。如此闹剧,显然有失民主革命者之身份,有悖民权主义之本真。
革命党人民主素质方面的相对不足,同样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历史土壤和环境相关联,无需过多地追究他们个人的历史责任。不过,如实地指出这些不足,对于了解辛亥革命的全局是必要的。这同某些苛求革命党人的做法不是一回事。
综上所述,及至辛亥革命高潮来临之前,革命党人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都不完全成熟,尤其是自身的主观条件还不够理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并非单凭敢拼的革命勇气便可一扫而光。然而,在民族危机的阵阵紧逼中匆匆踏上民主革命征途的先驱者不可能等着这些条件全都成熟后再来革命。诚如孙中山在1905年回答严复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28〕孙中山一代人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推出了彪炳史册的反清革命高潮。
二
对于反清革命的先驱们来说,正因为推翻清王朝的主观力量不够强大,难以单枪匹马地走向预定目标,就只好通过争取已不愿为清廷冒险效死的袁世凯、黎元洪等新军将领,逼迫清帝退位,从而推出一台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位的政治三角戏。尽管孙中山等人曾经尽情地描绘过中华民国的美好蓝图,并且以此许诺国人,只因建立民权政治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并不完全具备,在新的历史环境里,财力、物力和人力均显得捉襟见肘,因而,在新生的共和政权建设过程中,难免出现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不足为怪。既然历史并没有赐给辛亥革命的先驱者足够的创业条件,欲期后者于一夜之间在封建帝制的废墟上建成无懈可击的民国大厦,确立完美的民权政治,一洗专制王朝所遗留的污垢和耻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的过渡,决不能一蹴而就。”〔29〕
窃以为,就推翻清王朝而言,辛亥革命无疑是胜利了,清王朝的命运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实实在在地结束了。就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来说,尽管不能说辛亥革命已取得彻底胜利,但也不能说它的结局就意味着失败。如果我们不是误步孙中山等人当年的思路和承诺,以为只要腐朽王朝一垮,就能建成理想的中华民国,从而在主观臆想同客观历史结局的反差中产生失望和晦气;如果不是因为民初社会的若干弊端而一叶障目,代替对革命结局的全面分析和客观评价,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用巨人之手挂起中华民国的招牌之际,就同时树立了民主共和制的尊严——一种既不能漠视又难以侵犯的尊严。前人建设近代民权政治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尽管远离于后人的要求,但毕竟不能以“失败”二字来否定它的存在,采取不承认主义。正是通过辛亥革命,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政治近代化方有了良好的开端。透过政治斗争的云雾,后人从先驱者那筚路篮缕的历程中,不难看到历史前进的足迹。
且不说民国初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空前发展的,仅以民权政治而论,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已明显打破。民初政党林立,“殆达三百有余”〔30〕。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并非毫不管用的橡皮图章。从中央到省级政权,都是实行三权分立。“各省议会,掣肘行政,已成习惯”〔31〕。至于民权基础较弱的县级政权,固然有不少地方的议会机构不起实际作用,但也有一些地方的议会“确非虚设机构”,“凡是县政的预算决算及地方兴革各事均须由议会通过”〔32〕。民权政治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之下,多少还有些实际内容,它较之“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政治,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进步。倘若中华民国果真只是一块可挂可摘的招牌,那么,人称“强人”的袁世凯要扯下这块招牌,岂不比当年程德全在高高的抚署屋顶上凿烂几块玻璃瓦片更容易?为何偏要等到4年之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出“洪宪”旗号? 而且当相距数千里的云南护国军一声断喝,为何又立即化为灰烬?
我们不妨听听曾经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不无成见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回首往事时的一段演讲:“中国以四五千年的君主国体,一旦改为民主,在世界新趋势虽顺,在世界旧观念则逆。况以一二人为之,则因逆而更难。而孙中山不畏难,不怕苦,不耻屡仆屡起,集合同志,谋举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辛。至辛亥年,事会凑合,率告成功。以历史上看来,中国革命之第一人要推商汤。其后因君主之昏聩,或其他原因,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33〕
辛亥革命之于中国思想文化变革的贡献尤其值得注目。当辛亥先驱们把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打倒在地时,其解放思想的作用及其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封建帝制的覆灭,意味着对儒学三纲之首和封建等级制的彻底否定,意味着芸芸众生那些整天忙于磕头的脑袋和应酬跪拜的双脚同时得到解放,让它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和走路。正如有的当事人所回忆的,尽管革命党人被迫失去了政权,“但封建帝制被推翻了。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减少,有些完全消灭了。……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所换得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34〕。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使命,即变革文化之制度层面的最大制度——国体、政体的使命,变革文化之理论层面的最顽固理论——名教观念的使命。辛亥革命成功,中国政治由此进入共和时代。辛亥革命的伟大,在于它不仅仅推翻了一个王朝,而且在于它使得一切恢复帝制的尝试,都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丑剧,并由此得到启示,把向更深层寻求文化现代化的任务,提到了人们面前”。〔35〕
至今为止,学术界之所以比较一致地强调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仍然遗留下来;第二、新生的民国政权旁落他人,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去;第三、民初社会黑暗,民不聊生,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有过真实的描述和揭露。尤其是革命先烈的尸骨未寒,帝制复辟就接踵而来。
窃以为,以上论据都还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就已失败了。
首先,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内涵及其变化过程还属于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至少应当考虑到,既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民国政权,那么,就很难说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仍无变化可言。那种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就标志着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形成的观点,那种断言只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才算改变了近代社会性质的观点,都是值得重新推敲的。
其次,以革命发动者的政权转移为依据来断定革命全局就已失败,其说服力也显得不够。孙中山等人失去了政权,充其量只能说革命发动者和领导者在这场革命中遭到了失败,并不等于就是整个革命全局的失败。应当将二者稍示区别。
长期以来,人们一边说孙中山让位,一边又说袁世凯“窃位”,这本身就显得自相矛盾。“窃”者,盗也。既然有让在先,何“窃”之有。〔36〕其实,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往往受诸种政治力量的制约,并非政治家的人品优劣所能左右。本文第一节已谈到,孙中山等人推翻清王朝的主观力量是相对不够的。奉旨南下督师的袁世凯能否为革命党人所争取,就显得至关重要。倘若袁世凯不是停停打打,最后偏向革命党人,而是甘当曾国藩第二,反清革命的结局还不堪设想。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革命党人以民国总统职位相许来争取袁世凯,并非错误。至于袁氏后来把革命党人抛在一边,实行专制独裁,甚至搞“洪宪”帝制,那也不必过于丧气,不能由此逆推出当初让他上台就是错误,不能断定辛亥革命早已失败。“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37〕
只因后来袁世凯把已经为人民所唾弃的黄袍龙旗翻出,开历史倒车,人们就说当初让他上台便是历史性大错,好象他的上台就注定了他在数年后必然要搞帝制复辟一样,这种以事物的结果来代替其过程分析的方法不啻是宿命论和历史功利主义方法。后人所了解的历史都是已经凝固而且再简单不过的既成事实,而某些既成事实的原型在凝固成历史之前,往往是错综复杂和变幻多端的。后世学者即便有必要以历史结局为前提来重新设计历史过程,也应当同时注意到,历史主体对客体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8〕。
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无疑是历史的罪人。但他沦为历史罪人前那段有功于直隶新政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应当予以客观的评价。如同汪精卫堕落成民族败类前那段曾经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纲领主要阐释者和执行者的历史,应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样。唯其如此,方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宽怀大度和科学精神。历史科学那扬善击恶的社会道德功能不应靠任意剪裁历史来体现,而应当通过公正地评价一切过去了的人和事展示出来,在历史评价标准面前人人平等。
至于孙中山事后谈到自己当初让位拥袁乃“巨大的政治错误”〔39〕,往往也成了一些学者断定辛亥革命早已失败的一个力据。窃以为,孙中山后来固然经常反省让袁是个“错误”,但他当初让位时的认识却恰恰相反。那时,他只是觉得,如果能把袁世凯争取过来,便可马上结束战争,避免内乱和列强干涉,那将是“一圆满之段落”〔40〕。应当说,就让位而言,身临其境时的切身感受似乎比时过境迁后的历史总结更实在,也更具有说服力。孙中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让位问题的不同认识,与其说体现了这位革命领袖的思想认识水平之升华,还不如说主要反映了他的主观历史总结同当年客观历史环境之间的时空差异。
再次,封建帝制推翻后,旧的腐败还没有来得及根除,新的腐败却应运而生,人民的生活环境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是事实。鲁迅笔下那为非作歹的绍兴都督王金发确有其人,《阿Q正传》中赵秀才一班人的假革命也不难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不过,凡此种种,也还不足以证明辛亥革命已经归于失败。自从洋务运动发生以来,在中国近代特殊环境的制约下,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水平往往不能充作测量社会改革或革命运动之成败的晴雨表。尤其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民主革命运动过后,必然产生社会动荡,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并在一定时期影响人民生计。然而社会的进步伴随着新的历史代价的付出而悄悄来临。“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41〕
至于鲁迅等当事人对民初黑暗面的揭露和抨击,也不等于就是对辛亥革命的全面总结和科学评价。因为无论是哀叹“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或革命征途的颓废者,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般民众,他们最能感受到的主要就是革命政权的旁落,以及社会的动荡与腐败,既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去冷静地估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成就。
身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以“国情”为由,打出以立宪为名君权为实的“洪宪”旗帜,“辫帅”张勋导演丁巳复辟,似乎也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已经失败。袁世凯之流玩火自焚,两次帝制闹剧也不过如昙花一现,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何况,即使具有“世界革命”之称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其吵吵闹闹和反反复复的历史场面中,那里的民主共和制也经过了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费时近百年才最终确定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封建专制主义笼罩了数千年的国度里,共和制的威力还能迅速粉碎袁世凯之流的倒行逆施,堪称难得。历史展示给后人的显然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恰恰是这场革命的不朽功绩。
注释:
〔1〕《中国洋债一览表》、《东方杂志》第6年第13期。
〔2〕参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4页。
〔3〕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9页。
〔4〕胡思敬:《退庐疏稿》卷一。
〔5〕参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6〕《列宁全集》第2卷,第459页。
〔7〕梁启超:《粤乱感言》、《国风报》第2年第11期。
〔8〕P·洛:《英国与日本人(1911—1915),英国远东政策研究》,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第91页。
〔9〕田桐:《革命闲话》,《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9页;熊克武:《辛亥革命前四川历次起义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等等。
〔10〕萧汝霖:《浏阳烈士传·龚春台传》。
〔11〕《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版。
〔12〕拙稿:《孙黄关系再评价》,1988年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长沙)论文,载《近代中国》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年版。
〔13〕〔14〕〔22〕〔23〕〔24〕〔40〕《孙中山全集》第1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439、260、310页、325页。
〔15〕张金鉴:《欧洲各国政府》,台北版,第19页。
〔16〕梁启超还一度强调当时实行君宪制的条件也不够,只能实行“开明专制”。
〔17〕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 《民报》第4期。
〔18〕[美]《独立》周报1911年10月18日,转引自薛君度:《武昌革命爆发后的美国舆论和政策》,1986年广州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19〕[美]《环球商业报》1911年12月27日,同〔18〕。
〔20〕吴弱男:《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21〕景梅九:《罪案·与宋钝初谈话》。
〔2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26〕〔27〕转引自薛君度前揭文
〔28〕王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4—75页。
〔29〕《列宁全集》第3卷,第161页。
〔30〕谢彬:《民国政党史》,第4页。
〔31〕顾敦鍒:《中国议会史》,第168页。
〔32〕费璞安:《吴江光复前后回忆》,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280页。
〔33〕张謇:《追悼孙中山的演说》,《张季子九录·文录》。
〔34〕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68页。
〔35〕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36〕参见:《郭世佑就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等问题答记者问》,《社会科学报》,1991年11月28日。
〔37〕〔38〕〔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 页; 第602页;第606页。
〔39〕《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5页。
标签:孙中山论文; 黄兴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袁世凯论文; 宋教仁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