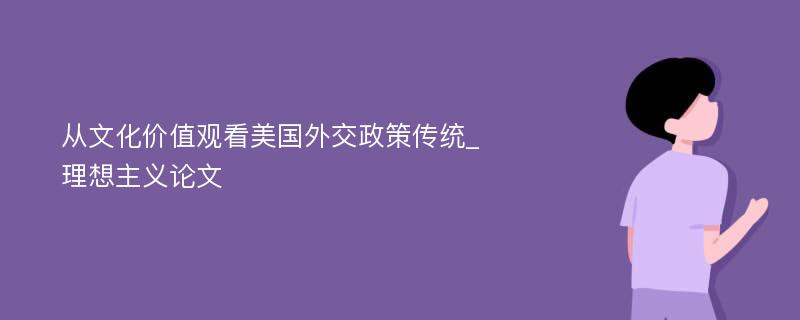
从文化价值观透视美国的对外政策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价值观论文,透视论文,传统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是受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等条件的制约的。在学术界人们通常习惯于从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层面等来研究一国的对外政策,而对于文化层面的研究却忽略了或者重视不够。其实作为一种历史长期积淀的文化具有极其深刻和丰富的内蕴,对公众舆论、思维模式、甚至领导人的行为模式都有深远影响。尤其是近来亨延顿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这更加坚定了人们从文化层面来研究对外政策的信心。本文拟从文化价值观这一视角来透视一下美国的对外政策传统,可能会给研究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及其形成传统
文化价值观主要是指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及与行为相关的信仰、思想、习俗、准则、惯例等,是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及他们与世界其它相关国家的观念倾向。由于文化是历史积淀下来而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中的观念性东西,因此其深刻内涵也主要反映在心理—价值层面。从这一层面上看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有:
(一)上帝选择的“使命观”
“使命观”指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对人类的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落伦·巴里茨在《逆火》一书中认为,有三个关键性的特征说明了美国是怎样看待自己及其余的:“山巅之城”的概念、理想主义和传教士精神以及战无不胜的美国技术。[1](p.373)使命观隐含着丰富的内容,主要有:美国清白无罪、美国乐善好施、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ism)以及天定命运观(manifest destiny)。并且使命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
首先,在美国这个特殊国度里,存在着主流文化盎格鲁—萨克逊文化(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1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一场以新教伦理为导向的宗教改革运动,其主要的理论体系之一是“因信得救”的“预定论”,即上帝以其绝对的意志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则为弃民。由于人们无法改变早已由上帝预定的自己的命运,所以只能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由此引发出新教徒在尘世的天职观。因此,“对热衷宗教的人来说,世界是他的责任。他有按其禁欲理想改变世界的义务。”[2](p.542)这种宗教上的价值取向便是使命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其次,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大批清教徒移居北美大陆是为了信仰。北美大陆“由于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在这些清教徒看来北美洲就像上帝隐藏起来的希望之乡,现在即将由上帝的选民所占据。在神的指导和保护下,他们将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地区。”[3](p.30)早期移民领袖约翰·亚当斯在1765年宣称,人们总是把具有尊严和奇迹的北美殖民地看作是在天意下开始一项宏伟的计划与设计,以启示无知者和解放整个地球上人类被奴役的部分。[3](p.11)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指出,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的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5](p.177)
由此可见,美国的“使命观”在美国的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上帝的选民”、“希望之乡”、“山巅之城”等说法便是他们特殊使命的生动表达,并且成为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区并把他们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主要标准之一,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观,成为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主要标准之一。正如莫雷尔·希尔德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中所写:“考察美国外交义务的出发点是这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6](p.4)
(二)美国心理的偏执狂心态
文化价值作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及其余世界的一种价值理念,它必然涉及到心理层面。阿尔蒙德在其所著的《比较政治导论》中,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层面,指出“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指的是专门化的政治导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方面的态度和对于自我在这个体系中角色的态度,”[7](p.13)而布朗(A·Brown)将政治文化理解为:“历史与政治的主观感知、基本信念和价值观认同感与忠诚的积聚,以及作为特定民族或团体的历史经验的产物的政治经历和知识。”[8](p.1)
由上述可以看出,心理层面的要素在政治价值观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反映在美国文化价值观中就是美国民族心理的偏执狂心态。
美国人从立国之初由于历史及地理因素诸方面的影响,即形成美国人与众不同的心理,认为美国处处高人一等,形成美国的例外观。美国这种强烈的与众不同心理必然导致心理偏执,这种偏执狂心态充分体现美国民族心理的不健全或不成熟。我们知道,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反映在国际关系方面就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的产生,可能与美国政治体制有关联。法国阿历克斯·托克维尔便从美国的政治制度上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必然性。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不可否认的是,民主制度很容易促成人类的嫉妒之心,固然,这是由于民主制度提供了使人们上升到同一水平的途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制度意味着永远让人不满足。因为民主制度唤起和助长了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但却不能让人完全满意。”[4](p.201)
美国民族心理偏执的第二个重要体现是强烈夸张敌国的阴谋和危险性。霍夫斯塔特认为,政治上偏执狂心态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将“庞大阴谋理论系统化”,总是认为敌对的方向正对本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巨大威胁。[10](p.4)霍氏这一见解为美国历史所证实。19世纪,美国总是担心欧洲势力侵入美洲,颠覆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20世纪,特别是大萧条后,害怕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等威胁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身生存的心理影响到美国生活的每一方面,特别是在外交上。20年代美国出现的“红色恐怖”,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等,都是美国民族偏执狂的明显体现。
由于理想与现实很不一致,从而很容易导致美国人的心理危机,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进程。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看上去自相矛盾,但却是美国民族心理在其外交政策中的体现。美国历史上几次重大外交事件如美西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战等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危机有关。美国民族心理的大起大落及多变不仅贯穿在本世纪,而且贯穿了美国整个历史。
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
文化价值观作为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它一旦影响外交政策,这些特点就会在外交政策上反映和折射出来。但是综观美国的对外政策,却并不像文化价值观那样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而是易变和多样的。比如,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并不是始终指导美国外交的两大对外政策传统,并且两者常常相互交织,交替指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总结一下,美国对外政策传统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反共主义等。这样看来,其文化价值观与对外政策之间似乎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文化价值观始终深深地影响着对外政策传统,其对外政策的每一步变化并未与文化价值观相矛盾,现逐一进行分析。
(一)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
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总统在其告别演说词中,就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一套被称之为“孤立主义”的准则。其要点是保持美国的“超然地位”,不卷入欧洲旧大陆的纷争。在发展商业关系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同外国发生政治联系”、“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性同盟”,以保持美国的选择自由。[11](pp.223-225)孤立主义在很长时期中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指导原则。其实作为美利坚民族意识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孤立主义始终受美国使命观的影响,“美国例外论”和“美国清白无罪论”是其深刻的心理基础。美国人不认为自己喜欢操纵别人和具有侵略性,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厚的防御型民族和国家。根据这种看法美国人不是一个向外寻求的民族,相反,他们一直在自我反省,关心国家建设以使本民族作为让其他国家和民族竭力仿效的“山颠之城”而屹立于世界。乔治·华盛顿1789年4月30日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称:“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11](p.257)1847年共和国创建时期的最后一位政治家埃伯特·加勒廷告诫国人,“你们的使命将是为所有其他政府和所有其他不幸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发挥你们的所有才能,逐渐改善自己的制度和社会状况,靠着你们自己的范例,带给人们最有益的道义影响。”[12]
这里须着重指出的是,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它的内容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孤立主义最初是针对欧洲国家,当时的美国刚刚建国,羽翼未丰,力量薄弱,无力向外扩张,此时其核心思想是美国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欧洲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务。这里除了自己力量不足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鄙视心理,认为欧洲在堕落,在沉沦,而对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却感到自豪,因此他们在感情上不愿与欧洲为伍”。[13](p.93)并且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相对的含义,美国只想利用此原则来束缚欧洲国家的行为。因此孤立主义与对外扩张并不冲突,当扩张局限在美洲大陆时,孤立主义就成为大陆扩张的一种理由。美国统治者一向宣称,大陆扩张是美国摆脱欧洲邻区威胁的一种手段,从而把扩张和维护独立密切联系在一起。如保罗西伯里认为,“在美国的统治中,孤立主义并不代表对政治的一种消极态度。相反,它是美国侵略性的领土增加和其文化与经济扩张的一个方面。”[14](p.47)因此,1823年颁布的门罗宣言实际上是孤立主义在空间上的延伸,除了把美国要在西半球实现的国家利益包括在内外,也反映出与孤立主义相同的价值取向。
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一根主线,扩张意识从一开始就成为美国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正如朱利叶斯·W·普拉特指出的那样,“认为有一种天命主宰和指导着美国的扩张,这种思想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简直很少有不存在的时候。”[15](p.23)但是须指出的是,同欧洲的赤裸裸的殖民扩张不同,美国的扩张却具有独特的特点,被称为“美国式扩张”。在美国人看来,“扩张”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同“进展”和“增长”是同义词。富兰克林认为,“进展、扩张和增长都是美国生活的必然规律”,[4](p.179)它是美利坚民族开拓和冒险精神的体现,是上帝赋予他们在尘世履行的一种特殊使命的具体化。也就是说,美国的扩张主义的深层次基础是“使命观”,传播文明是美国对外扩张所体现的一个重要内容。诚如J·斯帕尼尔所言:“美国人从其国家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引导到世间新的耶路撒冷。”[16](p.10)这样,美国外交决策者把美国外交政策的私利说成是维护了弱小国家的利益,“天定命运”被解释成把文明带给了未开化的地区。比如美西战争1898年刚一爆发,艾伯特·贝弗里奇就宣称美国人民是“一个进行征服的民族”,按照上帝做出的深谋远虑的计划,“没落的文明和衰败的种族”应该“在更高贵和更年富力强的那些类型的人所拥有的较高文明面前”消失。[17](p.137)
由此可见,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共同的心理基础是“使命观”。当美国力量不够或所发生的事情对美国利益不大时,“使命观”驱使人民选择孤立主义,而当美国实力充足或事情涉及重大利益时,“使命观”就要求美国依照自己的政治特性进行干预,即在干预的过程中依照“天定命运”的信念,向外推广美国文明或美国生活方式。
(二)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是美国学者站在维护本民族角度用来说明美国一种外交方式的术语,旨在表明与其他国家外交的区别,以显示美国外交的特征。“理想主义”的提出首推威尔逊总统。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们同时见到了丑陋、虚假和邪恶,它们与美好、真实和善良共存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使命是清除、反思、纠正前者,同时却丝毫不削弱、不损伤、不危及后者。”[18](p.53)话语之中使命观溢于言表。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美国都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马歇尔计划、卡特的人权外交、克林顿的“民主、人权、价值观”等无不反映了这一点。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对一种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但理想主义的背后却掩盖着现实主义的欲求,即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受美国的国家利益制约的。堂而皇之的马歇尔援助计划的背后隐藏着美国控制西欧的现实考虑,人权外交的实质却是以“人权”为幌子来侵略扩张、干涉别国内政,推行民主和价值观等实质上也是搞文化扩张。并且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美国必然向外扩张,这是美国外交的一个根本目标。在此情况下,纯粹的“理想”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其宣扬的“理想”能在某些方面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找到它的历史渊源,但当这种“理想”援引到国际事务中时,就会成为服务于私利的工具。完全以本国的利益为圭臬的“理想”和“自由”只是对外交的一种粉饰,带给被干涉和兼并国家的则是“灾难”和“压迫”。由此可见,理想主义的外交只不过为美国的侵略扩张披上一件颇为诱人的外衣,它往往成为现实主义者实现其现实欲求的工具。难怪现实主义者经常对理想主义赞赏有加,其实它有现实主义的欲求。
(三)反共主义
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社会随即出现了强烈的反共思潮。二战之后,反共主义更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经常性内容,并且是其对外政策中的基本指导原则。从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一诞生,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就视她为洪水猛兽,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帝国主义包括美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无疑是严重威胁。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兰辛向威尔逊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19](p.24)威尔逊在1919年说:“莫斯科的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24](p.167)由此可见,当共产主义的幽灵真正出现在美国统治阶级面前时,它们既恐惧又仇恨,美国民族的偏执心态暴露无疑。此外,反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有关,即:由于美国社会是由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和地域团体组成的复杂拼合体,而且历史短暂,没有时间从容消化差异因素,维系社会学家所谓的“一体化”功能主要依靠政治上的共识。于是美国主流社会一方面容忍各种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极端坚持为维护社会统一所必须的起码的一致性,任何对基本一致性的威胁,都将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坚决反对。这种反对的动力发自潜意识,具有不可言喻的非理性特征。而共产主义正属于可能破坏美国意识形态一致性的“非美因素”。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美国会对共产主义如此恐惧,并且在反应上经常如此歇斯底里。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艾森豪威尔主义等反共产义政策的出台正是这种民族偏执狂心态的真实写照。
三、几点启示
(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中隐藏着公众的简单化的和乐观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美国人易于漠视历史和政治因素。
美国公众大部分是清教徒,“预定论”和“天定命运观”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头脑中,而正是这种观念又加深了美国人“清白无罪”的理念。例如“西进运动”被认为是边疆精神、个人主义和艰难生活的体现,而忽略了另一种说法,即强调向西扩张的残忍性以及对土著人和墨西哥人土地和生命的掠夺;美墨战争被描述为一场美国进行的防御性战争,并且还夹杂着向“未开化地区”推进的道德说教,它忽略了这是一场美国人发动的领土扩张的战争。这就使得美国人难于接受那些与它们乐观主义的想象不相符合的历史真实或模式,也就是说,这种简单化的和乐观的观念使得美国人易于漠视历史和政治因素。
(二)美国领导层有借文化价值观利用和愚弄公众之嫌,其文化价值观不会超越美国的自我利益。
美国对外政策的实际举措常常包含着对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的追求,它意味着政策制定者运用秘密交易、威胁、武力等与“实力政治”有关的手段来成功地促进它们所界定的国家利益。但是这种非道德的和实用主义的行为与美国人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例外论的概念是一致的。正如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说的那样,在1947年要赢得公众支持向希腊、土耳其的军事援助,唯一的途径就是用共产主义对自由、民主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来“竭力吓唬美国人”。威廉·富布赖特曾指出:“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讨论理想,却很少描述它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它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21]
(三)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正遭受挑战
美国的使命观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民众意识之中,而它在冷战期间又演变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世界舞台上肩负着共产主义暴政下拯救这个世界重任的唯一净土。因此冷战期间美国的侵朝、侵越战争等都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但是侵朝战争尤其是侵越战争的失败引发了公众对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的怀疑。在越战中,美国使用了凝固汽油弹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并最终失败,这与美国人的清白无罪、乐善好施和例外论不符,因此,许多美国人开始认为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它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民族,美国爆发声势浩大的反越战运动正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标签:理想主义论文; 孤立主义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