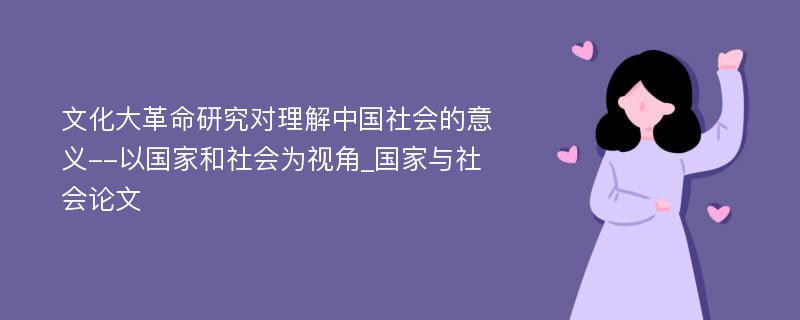
文革研究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意义———种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革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视角论文,意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英国史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m,Eric J)将二十世纪称作是“极端的年代”,而如火如荼地展开于神州大地上的文化大革命(下文简称为“文革”)无疑是这一“极端的年代”中的极端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文革不仅是一个可供研究的学术领域,更意味着刻骨铭心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文革是多重经历的重叠,是多重情感的交汇,是中国现代社会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1976年文革终结以降,大陆有关文革的描述与回忆性文章呈现汗牛充栋之势,但具有理论分析的研究性论文并不多见。学术界对文革研究的缺失,主要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定调,屏蔽了学术界对于文革的言说和表达的空间。中国的学术界所面临的困境是——文革是一个不可涉猎的禁区,但又是认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学术界有关文革的研究似乎在逐渐放开,在坚持意识形态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学术界有了更多与国外进行学术对话的机会,使得研究逐渐从政治导向转到了学理导向。
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每至文革的十周年纪念年都会展开文革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有一批著作译为中文。如Franz Schurmann所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非比寻常的事件,这对于与之相关的研究领域,的学者都是一次惊人之举,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许多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和分析的有效性,也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Schurmann,1968 p.504)
这意味着诸多在文革前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中的种种预设随着文革的爆发而呈现出新的形态,成为西方学界寻求重建理论的一种努力。而这些努力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理论、数据与资料的公开程度及学界的关注度等差异而呈现出了各异的学术成果。
1993年,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一书中指出了西方在文革研究对象选取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领袖取向和群众取向。这意味着在文革中,在上层领导的争权夺势之外,还存在着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借用Lefebvre的“平行革命”的概念,作者认为文革也同样是一系列的“平行运动”,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和基层的造反派在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的得益是平行的。这种判断暗合了“两个文革”的提法,意指文革是同时在上层领导和基层群众中展开的。通过对于文革时期武汉地区的个案性的地方经验的描述,王还指出了原先比较盛行的假设——毛的超凡魅力(charisma)对于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主导性影响的不成立。王通过一些个案访谈得出“(个人)在文革前社会中之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文革中参加哪一派”,并且大多数人在运动中其实是扮演了“逍遥派”的角色。同时由于四点原因,即(1)不一致的目标;(2)不适当的纲领;(3)畸形的传播媒介;(4)靠不住的执行机构,从而使得毛对于文革的发展完全失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毛和群众之间“偶像—崇拜者”的平衡关系,还群众以历史运动的主体性位置。通过将群众视为能动的历史行动者,作者强调了运动本身的逻辑,也完成了这样一种预设——对毛泽东的“超凡魅力”(charismatic authority)的正当性的批判。(Wang,1993)
本文将王绍光的“两个文革”的思想拓展为“国家与社会”视角,关注国家权力及其这种权力与其影响下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更扩大至关注国家领导人、权力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关注文革研究便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从这一视角出发,文革研究可有三大部分,一是对国家层面上权力精英,特别是毛泽东的研究;二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群体影响的研究;三是对社会群体能动性的研究。本文将沿着这三条线索展开梳理。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革成了一个标杆,可以接通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以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变,值文革开始四十周年之际,写作本文,也是为了深入的了解文革前的三十年和文革后的三十年。
二
从国内外的研究看,“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对新中国的认识,西方学术界常常会将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与伟人“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从这—意义上看,对毛泽东的研究就是对一个“领袖魅力型权威”社会的认识。
(一)极权政治与个人权威
早期的文革研究很多集中于对毛泽东与新中国政权关系的理解上。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预设:一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二是毛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渗透。就文革研究而言,其基本认识是将文革视为领导人理念的一种展示,赋予了毛泽东对文革的决定性作用。哈里·哈丁的观点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这场运动影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在于一个人。没有毛泽东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Harding,1992,p.20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一书较早地体现对毛泽东的重视,成为费正清的历史主义观点的典型表现。费正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的《美国与中国》中将毛泽东研究规范化。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概念,凸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独创性”仅成为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而且是早期文革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此后的研究出现了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符号化的情形,并使毛主义成为了一种“类意识形态”话语。(Xiao,2003)
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的第四章《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中,将毛泽东自身思想的演变和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和元素进行交叉讨论,从而将文革的过程看作是政治的王朝更迭(接班人问题)和毛思想的展开(毛主席逻辑的铺陈)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套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虽然强调了综合因素对历史嬗变的作用,本质上依然是“英雄史观”和政治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变体。其研究方法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在这一叙事下,文革变成了一场封建式的“宫廷战争”,成了“帝王将相”同场竞技的舞台。(MacFarquhar,1992)
中国明清史专家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在《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中,尝试综合运用王阳明玄学、公羊学说、黑格尔哲学等一众的中西方哲学思潮来透视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元素。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影响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思潮之一,而没有将其视为其中最关键的要素。(Wakeman,2005)。
施拉姆(Stuart R.Schram)的《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一文,试图将毛主义归纳为辩证法和阶级斗争这两个理念;同时,他肯定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式的道路”的求索,这使得他在评价毛时采取了二分的态度。他依然具有一种历史视角的学术关怀,从中国历史传统中寻找文革的资源,他甚至将毛与秦始皇相提并论。(MacFarquhar,1992)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毛的一生,认为毛是一个“粗莽的哲学家”,“推动毛前进的内在力量是对最残忍的家伙们的憎恶,它出自毛个人的反抗意识”。提到文革时,作者同样坚持毛“在解放人民方面是光辉的,但在管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方面则是不成功的”。作者力图向我们呈现的仍然是一个中国旧式君主的形象,只不过这个君主刚巧又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哲人而已。毛虽然试图建立平权,带有民主的端倪,但却具有基督教式福音主义的霸权特征。(Wilson,1993,p.494,p.499)
上述种种研究还有很多,国内有不少译著出版,但有两点倾向值得注意。第一,有些作品带有比较的、甚至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以妖魔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对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形象进行污名化处理;第二,有些作品强调中国政治体制的前现代特征,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神圣化。前者丑化了中国历史,后者则简单地将中国现代历史回归到“农耕文明的乡土皇帝”时期。
(二)精英群体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类研究开始将视野从毛泽东的身上扩展至其与上层精英的关系。英国学者克莱尔·霍林沃思的《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着重研究并叙述了中共党史上“十次路线斗争”。在她看来,文革是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及中共党内实际情况的认识有误,在于由此错误认识产生的善良而又根本不着边际的使命感”。(Holinworth,1995.p.4)她开始将文革原因置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去思考,而不是简单地诉诸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权力意志,虽然作者仍然强调了毛泽东复杂的人性特质和超绝的政治手腕对于文革发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本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界逐渐摒弃简单的政治话语叙事和个人权力意志说的思维模式。
李泽厚认为,不能简单把文革视作是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是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夺势,“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的情况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两者是混在一起的”(Li,2003,p.189)。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史料翔实,试图理解毛泽东“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主张,并强调正是这一理想最终形成了毛个人对抗中央集体的态势。而种种问题的衍生,例如武断专横、批反党集团、重用奸佞小人,都是基于这种“孤胆草莽似的悲情英雄”情结。作者观察到了文革发动的原因和其实际后果之间的落差,强调了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支配,淡化了个人对历史的决定性力量。(Wang,2005)高皋和严家其撰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是文革研究领域重要的论著,它最后将文革发起的根源导向了中国对于一个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缺失上,从而将历史动因的探究对象由个人转向了制度,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跳出单一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桎梏,寻求制度漏洞和缺陷的努力。
三
随着对文革的深入研究,出现了一种以文化和制度为纽带的,强调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分析框架。
(一)通过国家力量重构社会的努力
对文革的研究,许多学者对文革当中毛泽东推行的“反官僚制度与反不平等体系”等有广泛的兴趣,因为这些努力意味着通过国家或政党力量来重构社会。
首先,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摈弃了科层制的官僚体制,在运动中,所有级别的国家机构都遭到了清洗,大量的国家干部被迫劳动改造,专业技术人员受到控制;所有规章制度被取消,取而当之的是政治忠诚。此时,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参与式民主,大众有权来批评领导,实施了由革命委员会代表大众来行使权力的体制革命。这样的一种社会实践,吸引西方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研究围绕着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一个大型的行政机构能否只靠少量的正式规定和专业人员就能有效地发挥功能?第二,有效的科层制与大众民主的实践是怎样的关系?中国的制度变革的实践挑战了现代管理体制中科层制的必要性。(Nee,1973;Whyte,1973)
但文革结束后的社会变化使对科层制有效的研究和思考具有新的空间,学者们看到“反官僚体制”的努力只是暂时的。在政治上积极和忠诚的同时,官僚机制更加庞大,大众民主成为空洞的形式,专断权力更加集中在各级组织的官僚手中。对这一现实的反思表明,毛泽东创立的替代科层制的大众民主的政治模式,不是什么新的模式,而是一种“家长制”或“新传统主义”。(Walder,1986)
其次,文革中实施了一系列的平均主义的社会政策和分配模式,这引发了学者们对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学术兴趣,但学者的研究结果却令人吃惊,那就是毛泽东式的发展模式加剧了多种不平等。
从城乡差别看,一方面,是城市内和农村内存在明显的收入平等,但区域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却显著扩大。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从五十年代的大约二比一扩大到三比一,甚至是六比一;这种差距取决于国家对城市住房和食品消费的补贴程度。(Parish,1981;Whyte,1986)
从性别差别看,一方面,妇女被动员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社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妇女就业并未降低两性间的不平等,反而产生了新的更复杂的问题,妇女依然要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问题的关键是,不是革命提高了妇女的就业,而是对家庭结构的改造,如以户为单位的居住制度、从夫而居等使男性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强化了传统家庭制度。
从代际流动看,文革期间,学校的学制缩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政策使地位获得机会完全平等,被称为是一种“去分层化”,但这种中止年轻一代地位获得的状况是在关闭学校、冻结工资和停止职位提升的状况下发生的。(Parish,1984)但也有学者看到,在文革期间,按照政治标准划分“出身”的办法全面影响了不同群体对各种生活机会的分配状况,血统上的政治身份导致了那些父辈是被剥削的阶级、党员等在招生、分配工作和提升上的不同优先权;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等属于中间地位群体;而以前的剥削阶级、国民党分子的后代们则受到歧视。(Kraus,1981;Whyte,1975、1985)学生和工人们强烈地意识到这些人为的地位标记,并对友谊以及红卫兵运动中的政治派系形成重要影响。(Chan,1985;Unger,1982)
刘小枫认为,“文革的实质是,政治不平等的制度中,各阶层之间或阶层之内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斗争符码的政党国家一体化结构的内在冲突。”(刘小枫,1998,第430页),因此“文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众运动,而是政党运动群众的运动”。(刘小枫,1998,第398页)
(二)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
有学者注意到文革中精英集团或党组织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李鸿永指出,文革中精英集团企业动员和操纵群众,但党组织的控制力一旦削弱,社会中所有潜伏的力量和矛盾就会表面化,这使得群体运动依靠自身的力量前进。群众组织把官方意识形态和政策当成追求小集团利益的工具,合则拥护,不合则抛弃。严重的官僚化使党和群众的关系疏远,并淡化了人们对平等的要求。在组织上,激进的群众组织主要是由无特权的社会集团组成;保守派主要由那些出身优越的成员组成。(Lee,1978)
White在分析文革中的暴力问题时,将中国社会的矛盾模式引入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暴力反映了中国社会三种主要的矛盾,在这三种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文革,这些矛盾是:第一,身份的认定,如扣“帽子”(工人、干部、地主、反革命)的做法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的划分赋予了人们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第二,组织内部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这种关系依然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第三,周期性的群众运动,正是这种周期出现的群众运动使得暴力合法化。(White,1989)
Whyte的《中国的小群体和政治仪式》一书较早地分析了中国国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改造民众的艰难程度。他用“遵从结构”的概念来分析中国民众的力量。从服从的类型看,有三类服从,即基于威逼和强权的强制性服从、基于奖惩的功利性服从、基于信仰的规范性服从。不同的服从类型需要不同的组织形式。毛时代的国家目标是通过广泛的小群体组织制度使国民达到很高程度的规范性服从;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国家不得不对一些重要的组织中的人实施奖罚制度,以增加服从程度;同时,对于奖罚较少的地方,如农村,服从程度则大为降低。对于城市中的工作组织来说,国家只能通过强制的或功能的手段实现民众的遵从。(Whyte,1974)
有学者认为,文革时期的中国文化系统绝非浑然一体,相反,它包含了许多不协调、有时甚至矛盾的部分。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的务实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多层面而不单一的儒教传统。有些文化主体被国家全力推广,但其他的则得到农村社区机构,特别是家庭和亲属关系的支持。如在广东农村中,干部和群众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文化重新组合。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文化构件的重新组合的互动,发展出各种影响到干部或普通公民的行动方式。农村干部的行为表明,国家深受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而社会亦被国家所改造。国家和社会都不是西方模式的“现代”政治组织或“传统”意义上乡村社区。但两者都极具中国特性,是一种独特的、不断变化的、包含昨日和今日的中国文化的各种成分混合体。(Madsen,1984)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强调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相互渗透,传统文化和社会已经以许多方式在中国国家结构中自我再生,尤其表现在国家是部分建立在庇护与受护之间的个人关系之上,而并非是普遍性的行政系统规则。新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任何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都会存在改变原有的某些传统,同时保持某种连续性,这种转型就是一种“新传统”。华尔德提出了“庇护关系”的概念,在中国单位组织的制度文化中,核心特征是一种庇护关系网络的存在,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工厂领导与各级分子之间。这种关系在西方也存在,但相对来说并不普遍,人们往往将其归于正式组织中的非正式结构,而不是正式结构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单位中,这种庇护关系系统是不能离开正式组织而单独存在的,这种关系受到官方的支持,是其组织角色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关键点在于,个人忠诚、制度角色的履行和物质利益是联系在一起。华尔德通过对中国单位制的研究提出,单位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庇护者—受庇护者”的庇护关系所形成的基本单元,其中领导处于绝对的权力地位,而职工或是争当积极分子,或是发展与领导的私人关系,以争取由单位配置的有限资源。(Walder,1996)
四
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帕森斯理论的终结,这意味着社会学者再也不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整合的、自我平衡的体系,而是将社会看作是各种社会结构形式的混合体——包括家庭、当地社区、利益群体、地位群体等。它们由某种权力结构组合起来,这些权力结构不具有普遍性,而是在对各个历史环境的因应中发展起来。如果没有大体系的瓦解,则“传统”的、前现代社会不会因革命性变革而消失。由这个理论角度出发,中国研究就展示出一幅社会群体的组合图景,一些旧社会的残余仍然存在,并且与现代国家的权力相抵触。(Madsen,1999)
以毛泽东作为研究对象反思文革是文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文革毕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尽管其是由毛直接发动的,然而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纷纷参与其中,并且直接改变了运动的方式和进程。就文革研究而言,最初受到关注的社会群体仅仅局限在党和国家干部、人民军队、红卫兵以及工人造反派,承认这些群体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政治叙述的意义上成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一些学者反对将这些社会群体作为上层领导人争权夺势的注脚和投射,而是将其看成是重要的社会行动者,由此开辟了文革研究的另一路数。
(一)大众利益与大众运动的自我逻辑
李鸿永(Hong Yung Lee)1975年就注意到,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运动”中,一些社会集团发现了他们的利益诉求,并激烈地要求改变中国政治体制;而另一些社会集团则力求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生了激进派与造反派的分化。其基本的区别是:前者认为运动的对象是“走资派”,后者认为运动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的问题突出了出来,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对于工人来说,经济因素对其派别的形成很大的作用,一般来说,地位较低的合同工、临时工、小厂工人等构成了激进派的主力。(Lee,1975)
陈佩华(Anita Chan)提出一种“社会冲突模式”来理解文革。她认为,如果将文革说成是一场以老干部为一方,以毛和四人帮为一方的权力斗争,根本就是抹杀了人民,尤其是抹杀了红卫兵青少年在文革中的作用。她强调,在文革中群体分裂为严重对立的两大阵营,即保守派和造反派,这种对立反映了文革前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矛盾。(Chan,1992)
有学者则认为,在整个文革运动进程中,中国的普通民众所展现出的惊人的政治行动能量使得我们绝对有理由舍弃原本占有主导地位的解释路径——极权主义模型而转而寻求其他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性力量的新的诠释方法。(Perry & Li,1997)这些研究是以红卫兵群体和工人群体的研究为主要内容。
(二)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分析
Elizabeth Perry和李逊合著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一书力求人性化地对工人运动进行解读,并寻找一种对工人行动的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方式,那就是要分析工人分化的基础,探讨工人运动与同期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行动间的关系,以及解释中国社会主义体系内部变化的潜能。该书通过对上海工人的分析来讨论“大批判”(popular protest)的本质,作者放弃了从宏观的角度整合各种因素的努力,而是遵循就事论事的原则,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解释文革中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暴力冲突。作者认为,即使是在国家的威权之下,大批判的行动也并非是以无定式和无组织的状态进行,而是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更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纽带,呈现出多样性。虽然文革一直被称为“大乱”,但是它同时也孕育了一大批自下而上的组织。毛泽东思想主导下的国家,与其说是压制了群众,不如说是催生了“集体性意见分歧”(collective dissent)的可能性,这种具有集体性的不同意见,在地方领袖的主导下,大众无组织的行动转变为清晰可辨的不同的社会联系,并实现了大众行动的组织化过程。作者强调,文革中所出现的真正了不起的并不是压迫性政治氛围自上而下的渗透,而是自下而上的有组织的大众的政治反应,以及这些政治反应表达出来的多样性(Perry & Li,1997,chpt.I)
该书将上海工人分为三种类型:造反派、保守派、经济主义派,并应用不同的解释框架,辨识出三种不同的行动取向。造反派意在挑战党内的某些权威;保守派则极力维护那些权威;而那些经济主义派的组织则渴求社会经济中正义的实现。工人们各有各的目的并且为此而苦心钻营:造反派、保守派、经济主义派分别效忠于不同类型的领袖,他们的行动分别建立在相异的动机之上。这些明显的差异性,正如我们之前所阐述的,只有依循不同的分析传统才能够得到最佳的解释。
作者特别强调在1966年至1967年中国城市中刮起的“经济主义风”,这一风潮在地域上的差异正表达了中国普通民众中社会经济状况断裂之大的现实。民众的分化一部分是被国家政策生产出来或加以恶化的。普通市民明显的区隔表现为:阶级出身的好坏、城乡户口的差异、正式工与临时工的差别、国有制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相对的分化,这些分化明显是社会主义者们倡导的产物。不管怎样,即使这些对立项都是国家强制的结果,但上述类别的划分确实生产出了互相对抗的利益诉求,而这些诉求便构成了一种群体政治格局的基础。在文革期间,受惠于国家的分化策略的群体渐渐趋向于形成保守的组织。对此他们使用Walder所强调的庇护与忠诚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关系,强调保守派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文革之前与党内的庇护主义的非正式网络有着紧密的联结。他们是典型的激进主义分子,团体中领导人和副手、普通党员、劳动模范、共青团员和其他一些公认的积极分子。”(Walder,1987,p.82)这一群体尽管明显地被国家规则所形塑,但利益群体这样的“委托-代理”的网络结构在其他的政治体系中也可以找到。造反派是文革中最复杂且事后证明最有影响力的工人行动派的一支,作者使用了与传统分析相去甚远的分析框架,强调了中国政治格局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一直存在着一种对抗的亚文化,一些胆大的个人会跃起挑战权威人物,反映了政治大环境中的个人雄心和智谋的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些并不是“心理依赖”的人格特质——渴望臣服于上级领导所能够解释的。那些奋起挑战权威、批评党委和工作队的工人是一群不同寻常的、无畏大胆而且雄心勃勃的工人,他们精力充沛同时又暴躁易怒的人格特征往往脱胎于他们艰苦的家庭状况,滋养于经营在正统的党组织生活边缘的暴徒无赖的亚文化。北方籍贯人士、贫民区的童年生活以及青年时代的帮派经历都为造反派领袖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Perry延续了她的地缘政治的理论,强调地缘性的身份认同在造反派的派系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作者关注社会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图景:一些工人深陷党内庇护网络中,他们倾向于采取服从的策略,成为保守派;一些工人从那些与正统的政治网络不相适宜的亚文化中获取了力量,挑战党内权威的霸权,成为造反派;还有一些工人表现出对于物质补偿的极大的关注,要求获得收入补偿、改善工作环境等等,他们对捍卫或是打倒党内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游戏并不感冒。也就是说,单位制所诱导的绝对不止是顺从和依附,还有挑战和抗衡,两种态度都指向了个体的工作场所中的权威人物和体系自身的结构性特征。(Perry & Li,1997,chpt.Ⅶ)。
在注重群众运动的能动性的方法论基础上,Perry进一步引入了一种“情感模式”。Perry认为,在文革中,原本存在的劳动人民与地主、资本家之间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冲突已然不存在了,所以不得不生产出主观定义的阶级敌人,以此催化情感革命,在群众运动中,“文革不过试图再一次证明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可能的”。情感工作在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新活力,只是到了文革的批斗大会的形式,情感工作才真正达到了它的极限。虽然此时所依赖的是早就存在的大众反抗的传统,但却更进一步将这一实践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情感模式”的讨论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强调:情感不应该简单地作为非理性的和残余的意识被舍弃;相反,情感的姿态和表达方式,却具有独一无二的改变言说者的能力。(Perry,2001)
五
今天研究文革,应当更重视其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的意义,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国现代历史,虽然有许多的反思性文章看到了文革带给中国的“灾难”,但是也应当通过研究文革了解中国社会,以防止更多的社会危机。文革应该成为研究的模本,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中介,这是我们在从事文革研究时应该致力的一种观念。美国学者德里克在强调要重新恢复对文革的研究时指出:
正因为出现这种历史被抹杀的情况,所以有必要重新恢复文革的历史事件地位,这不但是为了让我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正视它,也许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我们的批判自觉,好让我们亦能以批判的态度正视那些因为抹掉革命历史而被束之高阁的现代问题。(Dirlik,1996)
这需要从几个方面对历史的反思。
第一,需要多元的理解分析框架。在这一点,Perry强调的不同的群体应当应用于不同理论来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社会下的个体绝不可能是些“原子化”的个人,中国社会在表面的同一性之下隐藏着各种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这将成为中国社会向一个现代性国家发展的原动力。这种情形在各种政治事件中都会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现。
第二,要看到文革的破坏力,也应看到文革在大破坏的同时产生的正面影响,即不仅看到文革的失败与弊端,也看到文革前的弊病;看到文革带给中国人对暴力和“动乱”的拒绝姿态。文革促成了中国人反思中国政治制度,并改革中国制度的愿望。正是经过文革,人们政治觉悟和以前大不一样。人民在文革中享受过空前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组织,利用大字报等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希望。这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经历,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Meisner,1986)文革虽遭否定,但却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持久的东西,反官僚、反权威的精神是人们的宝贵经验,青年一代学会了独立思考。
第三,需要去魅化地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追溯文革研究的变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西方在文革研究中都遇到了自己的困境:中国不断压抑,而西方不断窥视。文革对中国是个禁区,于西方则是个黑洞。我们的确无法将历史和政治截然分开,历史叙事的权力一直都是政治威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但是,认识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真正认清我们自身,以明确我们的历史境遇和责任担当。
从全球看,对文革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承认中国的文革已超出中国国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并特别深入地影响全球各地的政治运动。从法国的林荫大道到秘鲁的贫苦乡村,文革不仅在理念上提供了反抗不平等战略的原则,同时在实践上也提供了激进变迁的经验。我们只有把文革理念和实践看作是二十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中政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才能更好地判断其理念、价值和实践意义。
标签:国家与社会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毛泽东论文; 造反派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