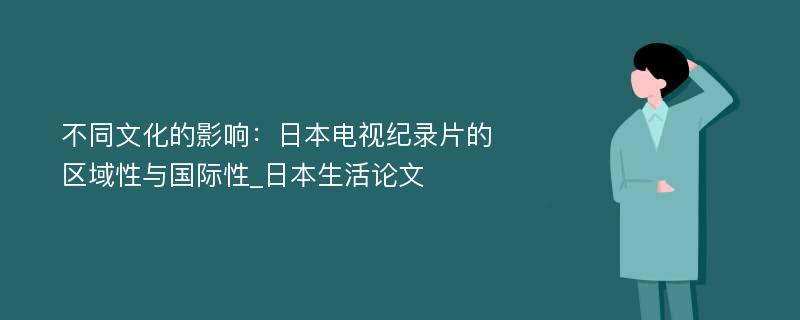
异文化的撞击——日本电视纪录片的地域性与国际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地域性论文,日本论文,纪录片论文,国际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这一术语在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被普遍使用。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给了文化一个简明而又意义广泛的定义:文化是人类环境的人造部分。文化应该包含这样几方面的因素:1.它指的是一个群体或社会的信念和知觉,价值观和准则,习俗和行为。2.文化用来表示认识、知觉和行为,以意见一致的方式为某一群体的人所共有。3.文化意味着把人们共有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样式传授给其他人,尤其是儿童;以及对该文化新成员的教育,使之适合社会的需要,有助于一代一代地保持意见一致。4.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信念和习俗,涉及到的不仅是“内心的”和“行为的”过程;文化出现在物和物质环境中。[1]
电视是否是文化我们姑且不论,无庸置疑的是电视与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反映在电视纪录片中的地域文化。
电视纪录片是记录人类以及自然界的一切在他(它)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如何生存,如何生活的过程,并将它传达给不了解这一切的人们的一种手段。所以,电视纪录片离不开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影响、制约着文化的的形成与发展,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又作用于电视纪录片。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两位女人类学家之一的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
人类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指出,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自然大致有3种一般的取向:1.人屈从于自然;2.人凌驾于自然;3.人是自然固有的一部分。[2]以日本为例,日本民族从整体来看更趋向于第一种取向,即:人屈从于自然。
一、岛国地域及文化与日本纪录片
原美国驻日本大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Edwin O·Reischauer在自称是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撰写的《THE JAPANESE》一书中指出:“空间是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点而言,日本人是贫穷的”。[3]在四面环海,缺乏自然资源,又多火山、地震和台风的小岛上,日本人对于自然的威力持有宿命论,从自然灾害中站起来重新再出发的能力极强。也因此,日本人更崇尚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勇敢地坚韧地生活着的人们。中日合拍的大型纪录片的日本版本《万里长城》中,日本对于游牧民族——内蒙古人的家庭生活、习俗的讴歌,正源自于这种立脚点。
由于日本岛内没有肆虐的大江河,只能是小集团间共同利用水资源,所以必须齐心协力。这种协力持续了若干世纪,导致了日本人的集团志向,集团行动的性格。[4]为了集团制,他们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公司’对个人来说,在认识上不是客体,不是与个人订立一定契约关系的共同企业,而被认为是主体,即我的或我们的公司。并且在多数场合,它浓厚地搀入了感情因素,即它是自己的社会存在的一切,是全部生命的依据”。[5]日本人“要让集团的力量不仅介入个人的行动,甚至也进入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中”。[6]当我们在《望长城》中受到了更多的英雄主义的教育时(无论是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是唱民歌的王向荣,他们都不再是平头百姓,而是多寡不同的人心目中的英雄),《万里长城》却给我们讲的是实实在在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国人的故事。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凝聚,这些普通人的顽强,才能够为更多普通的电视观众提供一种生活的参考,因为英雄毕竟是少数。也正因为此,很多中国人认为,《万里长城》不如《望长城》的立意深刻。
日本人在分析问题时,与明晰性相比更注重微妙的感受性;与理性相比更重视直觉;与理论相比,更重视实用;与概念相比更重视组织力量。[7]鉴于日本的民族性,所以,他们用电视来反映生活也许比用文字来表现更显得得心应手一些,因为电视更多地需要的是感受、直觉和实用。纵观日本TBS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万里长城》,可以说对于日本的这些民族性或者是日本电视纪录片的这种风格能够一览无余。他们在纪录片中,特别是反映长城这个中华民族文化的题材时,并没有去挖掘它的文化与历史厚重的一面;而是像不经意般信手拈来素材,从前期采访到拍摄完成,历时三年多。那么,他们又把重点放在了什么地方呢?岛国意识决定了他们心胸狭窄的一面,同时,也造就了他们善于从小处着眼的拍摄手法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中国人大概不屑于为了一只挂钟去召集钟表的制造专家们聚会;不会为找到了一位合适的采访对象而再度回访(石佛寺村的姬广印;内蒙古的司旗、扎布)……而日本人却不厌其烦,尽力拍好每一项内容。
二、不同地域的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是平等的
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大师牛山纯一先生认为,从本世纪的7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地把纪录片的焦点对准了民族问题以及人类全体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纪录片的内容更多地渗透了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方式,发达或不发达国家的电视纪录片更多地关注所谓的文明社会以外的其他文化、社会形式。因此,这种风格的纪录片被称作“映像民族志”或“映像人类学”。也就是站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的高度来记录世界,反映世界。
翻开最近几年来我们的获奖电视纪录片的目录,不难发现其中在选择题材上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就是反映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外国人所不熟悉的社会形态,反映都市以外的文化,反映远离我们文明的文明。藏族人的生活,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目光很难注意到的人的、动物的生活以及环境……这些纪录片的出现绝非偶然。因为纪录片是我们时代的见证,它将作为被记载的历史而流传。
再例如牛山先生所拍摄的若干部系列反映海外独特的民族风情与文化的纪录片,向世界展示了那里民众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价值观念以及他们的荣誉观。有一部片子描写地处巴布亚新几内亚以东的索罗门群岛中一个名为托罗普里安的小岛,岛上至今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态。在这个岛上,种植着一种当地人作为主食的土豆白薯(味道和形状都介于土豆与白薯之间),他们称这种食物为“亚姆”。每年的收获季节,种植“亚姆”的男人们把它们挖出来以后,全部送给自己的姐妹、自己母亲的姐妹以及侄女们,因为她们都是他们所爱戴的人。同时他们可以从自己妻子的兄弟以及自己岳父的兄弟那里得到“亚姆”。每年的收获季节,都是送“亚姆”的季节。他们认为,自己种的粮食自己享用是很可耻的一件事,他们是为了姐妹们而辛勤劳动的,这样他们才能够赢得人们的称赞。
就这样年复一年,托罗普里安的男人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的姐妹们劳作。收获上来的“亚姆”大约要被展示一个月左右,用来接受往来人们的赞赏。通过赠送“亚姆”,女人们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誉;而男人们则为此感到无比自豪。谁又能用我们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在这个群岛上生活着的人们呢?
牛山先生强烈反对把这种母系氏族社会制度称为“原始的”或者是“落后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那只是一种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制度的另一种社会制度而已。在文化范畴里,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并不比他们先进,而他们也并不比我们落后。[8]我们与他们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就比他们的更高级。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念,有他们自己对待爱情、婚姻的独特方式,有他们所信奉的神灵。他们并不比我们的文明社会更应得到同情或叹息,我们的生活也并不比他们更幸福。
于是,我想到了在我们国内的影视界经常可以听到的议论。有人认为我们在国际影视节上的获奖作品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把我们的落后的东西展示给世人。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不同的地域,必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不同的文化发生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念发生撞击,是我们进行国际交流或者进行大众传播所必然面临的。我们不能以我们的价值观念去衡量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或评价他们的价值观念,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别人只欣赏我们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里有猎奇的成分。同样我们也应该知道,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科学的方法解释世界时,是没有我们所理解的“先进”与“落后”的,而完全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我们的“家丑不可外扬”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在进行国际间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时,必然会滞后。因为我们认为的“美”与“丑”,完全是以我们的文化为背景,以我们的价值观念为基准所作出的判断,而并非站在社会科学的高度来审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
在今年5月北京国际电视周的“纪录片走向世界”国际研讨会上,费海丽女士讲到中国应该与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中国人不了解外国,外国人也不了解中国。中国若想使自己的电视纪录片走向世界,不了解外国人不行,同样,外国人若想在中国做生意,不了解中国人也不行。倘若我们还坚持以我们的价值观念为基准去衡量世界的话,我们只有被碰得头破血流。我并非认为我们应该持别人的价值观念来做我们的事情,而是认为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差异,并且本着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同样,在关注反映不同地域文化的电视纪录片时,我们应更多地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角度来审视摄像机所记录的一切。出任ABN行政总监的保尔·佛朗斯认为,在制作国际性纪录片的过程中,必然要碰到文化冲突的问题。如果国际合作的纪录片能够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并带有国际感,那么,它就容易被广大观众所接受。[9]
由此,我想到了我的一段亲身经历。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我走上讲台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外纪录片比较”。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中日纪录片比较”。当我把日本TBS电视台拍摄的《万里长城》放映给学生看时,我们电视专业的学生对于外界事物的感受力以及对于本民族事物的理解力使我震惊。当我们的学生看到片中拍摄的反映内蒙古风葬习俗的镜头时,他们的惶惑、他们的愤怒、他们的难以言表的眼神至今我还历历在目。他们要问我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要拍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在随后所赋的《风葬》一诗中到底表现了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拍我们的这些落后的东西?
为什么学生们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呢?因为日本人拍摄的是我们的鲜为人知的一面,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我们所谓的“不能见人的东西”,他们担心日本人在嘲笑我们的这些“陋习”。
我很遗憾我们的学生没有就片中的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风葬习俗提出质疑,诸如:内蒙古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俗?他们为什么要风葬?我告诉他们,主持人所赋诗的大意是:
“茫茫原野,
栖息着白骨;
有个刚刚化作新土的男人,
寒风中、瑞雪中,
正在午睡,
只有他的头发随风飘逸。
他们把这里称作‘黄色的斜面’,
从太古遗传下来的习惯——野葬。
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来,
却可以赤条条地选择‘黄色的斜面’;
内蒙古男人魂灵如此升上了九天。
茫茫原野,
栖息着白骨。”
尽管如此,我知道很多学生仍然不能明白风葬意味着什么——对于内蒙古人意味着什么,对于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我们所论证的是每一个我们熟悉的原动力的必不可免性,因此就总要把我们自己的局部行为等同于一般行为,把我们自己的社会化了的习惯等同于人类本性”。[10]
《万里长城》的主持人是日本著名的影视男星绪形拳,他不仅具有卓越的表演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所具有的文学、历史以及书画等多方面的深厚的功力,才是他能够承担起包括《万里长城》在内的一系列日本诸家电视台的大型文化系列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要因。当绪形拳来到黄河边时,他掬一捧黄河的水,感叹道:终于见到黄河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的摇篮。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捧起黄河的泥沙,要把它作为礼物带回日本,送给自己的夫人和女儿。看到这里时,我们的学生又感到了不可思议。一个外民族的人怎么会对中国的文化摇篮,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感兴趣呢?我不是绪形拳,我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为什么会对黄河如此发生兴趣。我只清晰地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小说《司巴达克斯》时所受到的震撼,以及对古罗马文化的向往。虽然这一切促使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却并未动摇我对华夏文化始终如一的追求。所以,我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理解绪形拳的某些感受。人,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对于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尊崇,在某种意义上是共通的。正如同当我问及《万里长城》的总制片篠崎敏男为什么要拍长城时,他告诉我:“长城是人类的文化遗产。长城周围的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就是我们所要表现的对象。”我们试图向观众说明:“什么是活着?”这也许应该是一切人文纪录片所要表现的主题。
不同地域的文化对于电视纪录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许是一个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但是,我认为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心境去面对它。我们不应该按照别人的口味去拍我们的纪录片,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当我们以一个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以及我们自己时,也许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我们拍的片子是要给外国人看的还是要给中国人看。因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电视观众,他们都需要一个用科学的态度解释世界的电视纪录片。
注释:
[1]《文化与环境》P4欧·奥尔特曼、马·切默斯著,骆林生等译,东方出版社
[2]同上,P23
[3]《ザ·ッャパニ一ズ》P236,EDWIN O·REISCHAUER著,国弘正雄译,株式会社文艺春秋
[4]同上,P29
[5]《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P14,中根千枝著,陈成等译,商务印书馆
[6]同上,P18
[7]《ザ·ッャパニ一ズ》P231,EDWIN O.REISCHAUER著,国弘正雄译,株式会社文艺春秋
[8]1996年北京国际纪录片研讨会上的发言
[9]《纪录片走向世界》研讨会上的发言
[10]《文化模式》P9,露丝·本尼迪克特著,王炜等译,三联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