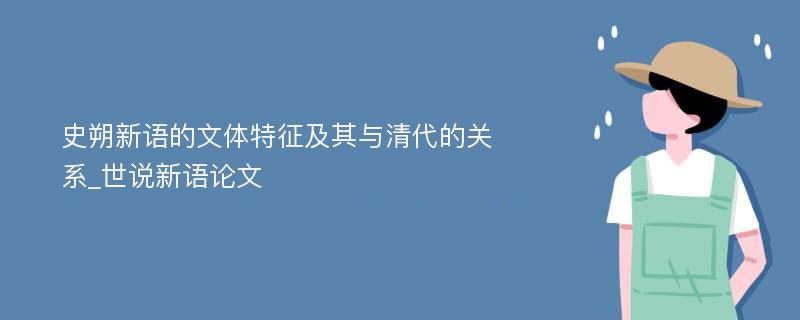
《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特征论文,关系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清人刘熙载论文风之变,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艺概·文概》)虽然没有具体描述《世说新语》的文风特征,但将其与《庄子》、《列子》及佛经并列,这实际上已暗示了《世说新语》的特征与传统文章不同,它别有一种特殊魅力。同时,此种特征又不同于《庄》、《列》、佛书,否则不得谓之变。
《世说新语》的确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它之所以在后世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士大夫案头必置之书,固然可以归因于该书记载魏晋名士言行这一特定内容,同时也与其特殊的文体相关。自《世说新语》问世,后代仿其体例续作者代不乏人。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辨,唐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焦竑的《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的《廿一史识余》、郑仲夔的《清言》等。清代仿作者更多,有梁维枢的《玉剑尊闻》、吴肃公的《明语林》、章抚功的《汉世说》、李清的《女世说》、颜从乔的《僧世说》、王晫的《今世说》等等。尽管这些仿作远不能与《世说新语》同日而语,但这一现象的存在,无疑表明《世说新语》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二
那么,《世说新语》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著录大多将其归入子部小说类,如《唐书·艺文志》、《通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均是。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世说新语》应属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则以之为志人小说,以区别于《博物志》、《搜神记》一类的志怪小说。直到今日,一般的文学史都承此说,明确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类来讨论。
这当然不能算错,但问题在于:第一,古人所说之小说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第二,就算《世说新语》属小说之一种,它也应该有其自身的特征。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一概以小说视之,则不但混淆了《世说新语》与一般小说的重大差异,而且很难真正把握《世说新语》独有的文体特征,从而使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流于一般化。所以,若要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其与小说的差异便不能不首先加以辨析。
按照一般的理解,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应该具有三个要素,即:人物、情节、结构。粗略地看,《世说新语》似乎也满足这个要求,尤其是第一和第三两个要素,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虚构性应该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因此,虽然《世说新语》记述的对象是人,是魏晋名士的生活,但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现实中的人物,并不真正具有虚构性。诚然,《世说新语》中的某些描写或许不无虚构的成分,然而严格些说,这种虚构并未超出史传文学所允许的范围。比如: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伯仁弟)。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迳便出。(《方正》)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自新》)此二例为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书中所举,意在说明《世说新语》不乏虚构成分。王能宪认为:“周仲智问病与周处斩蛟,作者不可能目睹其事,但都描写得十分细致、生动,活灵活现,如在目前。这样的细节描写,显然有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创造成分。”[1]说此二例的细节描写有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创造成分,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小说所要求的虚构,小说之为小说也不由这种虚构成分来决定。小说和人物传记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作品中人物的虚构性,而非若干合理想象的成分。其实,不要说小说家,就是史家,也不可能完全目睹他所记载的史实。王能宪谓书中类似的虚构成分不在少数,这是必然的。因为《世说新语》所记,几乎都不是刘义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以他当然免不了会用想象去弥补材料的不足。然而,又有哪一位史家不是这样做的呢?翻开二十四史,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显然,此类虚构成分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将《世说新语》定为小说的依据。
另外,作为小说重要因素之一的情节,在《世说新语》中也颇为鲜见。小说本由故事发展而来,因此情节便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现代小说中有淡化情节的趋势,但就总体而言,情节仍被公认是小说的基本要素。而且,情节的复杂性、曲折性往往是小说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的关键之所在。而《世说新语》所记,除少数略有情节外,绝大多数皆无情节可言。上引周处斩蛟事算是略具情节之一例,再如: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雅量》)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悦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已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惑溺》)
较之周处斩蛟事,此二则更近于小说。首先是情节相对完整,有一定的故事性,尤其第二则,已粗具唐传奇乃至宋元话本雏形;其次描写较为细腻,如第一则写沈兴对褚季野前倨而后恭,以及褚季野之宠辱不惊,笔简形具,不异小说家手笔;第三则是在记叙中突出人物个性,此点殊可注意,我们下文再作详论。不过,类似的情况在《世说新语》中并不多见,而且《世说新语》最为人称道者亦非此类。
相应地,《世说新语》的结构也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就是说,不是沿着故事线索展开,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对《世说新语》的结构特征,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着眼于它按内容分类编排的网状结构。这种结构的叙述描写中心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类人,其结构方式则是围绕这一类人组织相关的故事群,再由若干类人的故事群缀合成书,从而具有一种分类世态百科全书的性质。《世说新语》作为一种文体所以对后世产生影响,以至仿作不绝,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二是就书中每一则记载而言,多为生活中某一场景、某一片断的叙写,不作纵向展开。或是一则传闻,或为一段对话,要言不烦,如绘画中之写意,虽略有情节而不求曲折,虽偶用描写而不为工笔。《世说新语》的艺术魅力,实得力于此种安排不少。有人认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所谓“世说体”,就在于它这种按内容分类的结构方式,[2]这不错,但《世说新语》被视为志人小说的代表并非由于分类结构。从其效用来看,分类结构只是便于编排和检索的手段,而不能使《世说新语》更具文学性。这也说明为什么后世虽然仿作不少,却鲜有以小说见称者。事实上,如果说《世说新语》的成功多少与分类结构有关的话,那也只能从编撰者分类的指导思想方面去寻找原因。总之,《世说新语》的结构不类小说,这是没有疑问的。
三
那么,是否因为我们以近代小说的标准来衡量《世说新语》,才得出如此结论的呢?假如我们遵从古人的意见,是否又会有别的理解?这也不尽然。其实,直到现在,对小说的界定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中称小说为“文学领域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有成百条小川流灌着,有时还变成一片沼泽。”诗人固然不免偶尔置身其中,历史家有时也会失足陷入沼泽。福斯特认为没有一句话能把这片沼泽描述清楚,“我们只能这么描述: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而第三边却面向海洋”。[3]福斯特是明智的,他深知小说处于诗和历史的夹缝之间,而且小说与诗、历史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他形容那代表诗和历史的山脉“连绵但并不陡峭”)。“第三边却面向海洋”一句尤可玩味,这似乎表明小说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如此,在小说与诗、小说与史的结合部还有大量的边缘地带,其性质往往不易确定。所以,严格些说,《世说新语》应该正处于这样的边缘地带。
在中国,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说的“小说”,意思是琐屑不足道之言,与名言至理相对,并没有文体的意味。到了汉代,小说才开始成为文体之一类,西汉末年的桓谭在《新论》一书中写道:“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甚理家,有可观之辞。”其后班固作《汉书》,将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其中诸子类共十家,小说家居末。班固认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庄子·外物篇》所言,“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之语,“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至于班固的见解,“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4]当然,鲁迅这样说,不等于他认为桓谭、班固所言小说与后来小说毫无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不会在书中辟出专篇来讨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小说,也不会给予《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特殊的注意。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鲁迅称《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他并没有将其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因为按照汉人的观点,《世说新语》正是这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丛残小语”,而《隋书·经籍志》所以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类,依据的也就是班固的分类标准。
《汉书·艺文志》对小说的界定在后代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仍从此说。所以,古人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类,并不能成为我们今天赞成《世说新语》是小说的依据。
事实上,在古人观念中,小说一词还兼有野史、外传的意味。《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武帝时人殷芸所撰《小说》十卷,清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道:“按此殆是梁武帝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外乘即外传,亦即正史所不载之轶事传闻。这类轶事传闻未必皆出于虚构,虽然不入正史,仍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为后来修史者所重。宋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便主张“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进资治通鉴表》),因为在他看来,“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
《世说新语》自然也可以归入这一类。我们知道,唐人修《晋书》,就有不少材料采自《世说新语》,后来研治魏晋史者,不论是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还是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等等,也都极为看重《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可见,史家对《世说新语》的重视,决不在文学家之下。宋人秦果序孔平仲《续世说》便说:“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之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要而不烦,信而可考,其《世说》之题欤。”他认为《世说》既如诸子小说之具有可读性,又如史书之真实可信,介于小说和历史之间。也许正是有见于此,《世说新语》除了入子部小说类之外,还可入史传类。例如清代的《孙氏祠堂书目》,便将《世说新语》归入史学传记类。
就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的意图而言,应该说是尽可能追求真实的。这从书中两处有关裴启《语林》的记述不难看出。一是《文学》第九十则: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王东亭作《经王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二是《轻诋》第二十四则: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曰:“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
裴启的《语林》,是一部记述汉魏至东晋士人言语应对之可称者的专书,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由于谢安认为所记不实,于是废弃。刘义庆既知此事,并写入书中,当然会尽可能避免讹误,力求真实。鲁迅在讲六朝小说与唐传奇的区别时曾说:“六朝人的小说是没有记叙神仙或鬼怪的,所写的几乎都是人事;文笔是简洁的;材料是谈资、笑柄;但好像很排斥虚构,例如《世说新语》说裴启《语林》记谢安语不实,谢安一说,这书则大降声价云云,就是。”[5]至于刘孝标作注不乏纠谬之处,并不足怪。一则刘孝标所纠之谬不到百分之一,此种情况任何史书在所难免;二则所纠之谬误在所据材料,而非刘义庆有意虚构。最主要的,是刘孝标本人并不将《世说新语》看作道听途说的轶事传闻,他之所以广征博引,详为注释,正表明在他心目中,《世说新语》有着与正史同样的价值。对上引《轻诋》第二十四则,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谓:“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表达了他对《语林》因谢安批评而废弃的不满。可想而知,对《世说新语》,刘孝标也不会因为偶有失实便否定其价值。
不过,正如我们没有因历代著录多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类,便等《世说新语》同小说一样,我们也不会由于《世说新语》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就将它认定为历史。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世说新语》异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而在此,我们同样可以指出《世说新语》与传统的史籍不类。
最明显的差异无疑表现在体例上。首先,和正史关注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世说新语》只关注这一时期某些人物的言行,而且不是有闻必录。其次,即便是和史籍中的人物传记相比,二者也有很大的差异:史籍中的人物传记,一般总免不了介绍传主的出身故里、生平仕宦,以传主的主要业绩为中心,按时间顺序来展开;而《世说新语》所记人物,往往只撷取人物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一件琐事,着眼于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长短不拘,意尽即止。尽管我们也可以将书中所记某一人物的全部材料综合起来,从而对其有更多的了解,但这种了解仍是片断的,与正史要求的完整、系统不同。第三,在表现方式上,正史讲究所谓春秋笔法,客观叙述,突出的是事件的因果关系;而《世说新语》则不乏形容,颇多细节,看重的是事件的发展过程。所有这些,不但和正史相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野史、外传。
综上所述,无论将《世说新语》划归小说抑或划归历史,其实都不确切。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来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
四
但《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也就在于此。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它正是在这种两可之间呈现出独自的个性,具体些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内容的纪实性。《世说新语》所记为真人真事,这在上文已经论及,此不赘述。有必要说明的是,《世说新语》在材料的选择上有自己的标准,刘义庆并非有闻必录,而是将范围限定为汉末以来名士的特定言行,这就和一般的史书区别开来。
二、篇幅短小。这本是汉人眼中小说的基本特征,如桓谭所谓“合丛残小语”,“以作短书”。《世说新语》此点尤为突出,其长者不过二百余字,短者甚至不到十字。如果稍作划分,《世说新语》所记大致有三种类型:1.偏于记言者,如《言语》、《赏誉》、《品藻》中的大部分。此类大多较为短小,盖编撰者的兴趣只在人物的语言,因此可将人物语言单独抽出而不显突兀。其中极短者如: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赏誉》第五十六则)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赏誉》第七十八则)2.偏于记事者,散见于各门,以记品行、个性者较为集中。此类较长,如前引周处斩蛟事、韩寿与贾充女通事,皆是。然亦不乏短小者,如:
郗嘉宾得人以已比符坚,大喜。(《企羡》第五则)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栖逸》第三则)3.记事兼记言者。此类数量最多,长短不一,但一般不作铺陈,叙述多于描写,场面重于情节,故篇幅多在数十字到百余字之间。后人称道最多的,主要就是这一类。大概因为过短则难显人物个性,过长又不免流于史笔,所以长短适中,言行兼具的这一类,更符合编撰者的意图,也更能体现《世说新语》的文体特色。
三、清通简淡、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陆机《文赋》论文,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虽然此“说”非《世说》之“说”,但他明确指出不同文体都有各自的文体风格,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世说新语》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当然也有自己的风格,即清通简淡,空灵玄远。前人论《世说》多有见于此,如南宋刘应登《世说序》道:
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谓:“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
《世说新语》不像正史那样典雅凝重,也不像《国策》那样炜晔飞动,而表现为雅淡闲远,意余言外。如果说,史家追求的是事理,纵横家追求的是气势,那么《世说新语》的编撰者追求的则是韵致。刘熙载所谓文风至《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应该说主要是就此而言。
我们知道,一种新文体的出现,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原因:一是外部的影响,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定时期社会的政治状况、学术风气、文化氛围,会对该时期的文学范型乃至文章体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使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不难由整个文学史得到证明。二是内部的作用,亦即《文心雕龙·通变》中说的“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应,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也就是说,文体的发展演变,一方面是对前此相关文体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适应当前的需要而有所变化。那么,具体到《世说新语》,情况又如何呢?
就外部影响而言,《世说新语》文体个性的形成,无疑和魏晋清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清谈既由人物品评发展而来,则《世说新语》以名士言行为记述的主体,正可视为清谈风气的影响。而且,由人物品评的性质所决定,这种记述必然追求尽可能真实。《世说新语》文体特征所表现出的内容的纪实性,应该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事实上,刘义庆所以采取纪实的编撰原则,倒不完全是因为有裴启《语林》的前车之鉴,而是由于谢安的批评代表了当时士人对此类文体的要求。或许谢安此举不无私心,但平心而论,谢安一句话便使《语林》废弃,除了谢安特殊身份地位的影响之外,还因为谢安所说的确抓住了裴启的要害,从根本上否定了《语林》的价值。篇幅短小与文风新变亦然。明人袁褧《刻〈世说新语〉序》说:“尝考载记所述,晋人话语,简约玄淡,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叙,明畅不繁。”清谈崇尚简约,以语少意深为佳。在这方面,东晋乐广可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世说新语·文学》称其“辞约而旨达”,《赏誉》记王夷甫语:“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从清谈的影响看,《世说新语》篇幅短小,一方面是由材料本身所决定,即清谈家言语尚简,如刘应登序《世说新语》所说:“盖于时诸公专以一言半句为终身之目,未若后来人士俯焉下笔,始定名价。”另一方面,则是清谈风气对刘义庆本人文风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材料的选择、处理。所以,尽管清谈中不乏长篇大论者,但不论是呈口舌之利,非理中之谈如许掾与王苟子之争高下,或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如支道林对王羲之之论《逍遥》,其具体讲谈内容均不为刘义庆所录。而那些简短精绝,易于口传者,才是刘义庆着笔最多的。
《文学》第二十五则记: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南北学风,固自不同;江左清谈,尤贵精简。相应地,才情、捷悟、以精敌博、以少胜多便成为两晋名士的一致追求,而作为“清谈之全集”的《世说新语》,其文风自然会与此相吻合。
就内部作用而言,《世说新语》当然也不免受此前相关文体的影响。较早一些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论语》,尽管《论语》的篇章划分并未依从孔门四科,与《世说》不类,但在记载人物言行及偏于语录体等方面,或许对《世说》不无影响。其实,玄学既然兼综儒道,则《论语》虽不入“三玄”,仍不失为魏晋士人之谈资。而既为谈资,耳濡目染,影响便在所不免。如果比较一下两部书记叙人物言行的角度、手法,乃至语言,不难看出其间若干共同之处。着眼于分类结构,则有汉代刘向的《说苑》。《说苑》是一部分类著录先秦至汉遗闻佚事,借古喻今的杂书,全书分为二十门,即: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理政、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谋权、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由于带有明显的政教劝戒意味,史籍不入小说,而归入子部儒学类。刘向另有《世说》一书,已亡佚,但据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考订,《世说》与《说苑》实为一书。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则认为:“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又据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引日人古田敬一自类书统计,《刘义庆说苑》亦为《世说新语》之异称。总之,无论刘向之《说苑》是否就是《世说》,其与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关系当非同一般。除了书名之外,更重要的是体例的相似,亦即记述遗闻佚事和分类编排材料。
不过,这些都还只是“通”的一面,如果没有刘义庆的“变”,《世说新语》不会形成自己的文体个性。实际上,刘义庆并非完全援用刘向《说苑》的体例,只要稍加比较,便可看出两书在分类原则上的明显差异:《说苑》分类以政教为依归,《世说新语》则着眼于人物才性。相应地,刘向所记,较重故事的完整性,且带有强烈的议论色彩;而义庆所记,则只取场面片断,作者的主观态度隐于记叙之中。在文风上,《说苑》仍承先秦论说体,不无策士、纵横家习气;《世说新语》则自成一格,简约玄淡,与魏晋名士之清谈相近。显然,上述差异较之一般说的分类结构更能体现《世说新语》的文体个性。
在《世说新语》之前,文体相类的还有西晋郭颁的《魏晋新语》、东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这些书的性质应该更接近于《世说新语》,就是说,它们都是清谈影响的产物。但也有不同,虽然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时有不少材料取自它们。据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考辨,[6]刘义庆从它书辑录材料时往往予以简化,如《言语》第二十则: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语林》作:
满奋字武秋,体羸畏风。侍坐晋武帝,屡顾看云母幌,武帝笑之。或云:“北窗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答曰:“臣为吴牛,见月而喘。”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御览》卷七○一引)
《郭子》作:
满奋字武秋,高平人,畏风。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问之,对曰:“臣若吴牛,见月而喘。”(《御览》卷一八八、八九九引)
再如《容止》第二则:
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语林》作:
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驸马都尉。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遂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
从这两例可以看出,与它书相比,《世说新语》文字更为简练,刘义庆略去了与事件无关的一般性介绍,如字号、籍贯、官职之类,从而使主旨更加突出,特征更加鲜明。[7]《语林》、《郭子》等书的亡佚或许不是偶然,因为《世说新语》既后出转精,它们便不免相形见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终被淘汰。客观地说,《世说新语》的流行固然有编撰者刘义庆的皇室身份、刘孝标注等因素的作用,但《世说新语》自身的艺术成就,其独特的文体风貌,才是它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因为清谈影响的产物,较之《语林》、《郭子》等同类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无疑更充分、集中地体现了清谈精神,其不同于刘向《说苑》之处在于是,其超出《语林》、《郭子》之处亦在于是。
五
所以,从根本上说,《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形成,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这就是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划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
名士意识并不就是个体意识,然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我们甚至可以说,个体意识是名士意识的内核,魏晋间名士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突出一个我字,以自我为中心来行事处世。谈玄也罢,任诞也罢,名士们追求的不外乎是展示自我,呈现个性,越是高自标持,不同流俗,便越能显示名士派头。《世说新语》所以不同于《说苑》,根本的区别即在于刘义庆关注的是人而不是事,是人的活动所显现的才情、个性、风致,而不是事的因果所昭示的规律、经验、教训。因此,同样是撰录史实佚闻,同样是分类编排材料,两书取舍不同,分类不同。《世说新语》三十六门的划分,如果说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的话,那就是以人的活动为着眼点,而在所记人的活动中,最突出的即是人的才情个性。从人物的姿容、言语,到人物的品性、情感,以至人物的才艺、专长,不管是否出于自觉,刘义庆的确展示了魏晋间丰富多彩的人性,《世说新语》也因此成为展示各类人物的艺术长廊。后人读《世说新语》,每每于此叹为观止,称誉良多。如:
竹林之俦,希慕沂乐;兰亭之集,咏歌尧风;陶荆州之勤敏,谢东山之恬镇;解《庄》《易》,则辅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则道林、法深领其乘。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奥,风旨各殊,人有兴托。(明袁褧《刻〈世说新语〉序》)
晋人雅善清谈,风流映于后世,而临川王生长晋末,沐浴浸溉,述为此书。至今讽习者,犹能令人舞蹈,若亲睹其献酬傥在当时。聆乐、卫之韶音,承殷、刘之润响,引宫刻羽,贯心入脾,尚书为之含笑,平子由斯绝倒,不亦宜乎。(明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序》)
临川变史家为说家,略撮一代人物于清言之中,使千载而下如闻声欬,如睹须眉。(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可见,《世说新语》的人物描绘的确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成为它得以流播后世的重要原因。进而言之,《世说新语》和一般记叙人物生平业绩的史传的不同,就在于从人性的各个侧面分类,从而极为鲜明地刻划了人物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一点,使它从根本上远于史传而近于文学。就是说,不是虚构,不是笔法,而是对人性的描绘使它更具小说意味。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的确如此,超越实用功利而追求赏心娱乐,正是《世说新语》在编撰动机方面的重要特征。刘义庆既非受命而作,也不是为了有所劝戒讽喻,他所以编撰这样一部“名士的教科书”,“清谈之全集”,应该说只是为了自娱和娱人。尽管身为皇室贵胄,然世路艰难,刘义庆未必不想置身事外,在对汉末以来名士清言逸行的把玩中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脱。
当然这仍与名士意识相关。汉末名士,最重德行操守,故于时清议品鉴的标准,实为传统儒家之道德规范,李膺、陈蕃之能领袖群伦,为一时楷模,原因即在于此。而魏晋以降,由清议到清谈,风气亦为之一变,德行操守虽不废弃,但已让位于姿容言行,风神韵致,如李泽厚《美的历程》所言:
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气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愈来愈明显和确定。《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轶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尘拂,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
魏晋的人物品评已带有较为明显的审美意味,已不似汉代清议那样单纯作为进身致宦的依据。在魏晋时期,即便是探讨抽象玄理的清谈,也有意追求辞令之美,至于山水赏会,托意艺林,更是以对美的领略、表现为依归。与汉末名士相比,魏晋名士对于美的事物可谓情有独钟,而此时的名士风度,名士意识,便不能不包括了这种对美的倾心。因此,《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论刘义庆是否有意为之,的确成为远实用而近 娱乐的赏心之作,体现出与名士审美追求相一致的旨趣。
注释:
[1]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18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宁稼雨《“世说体”初探》,《中国古典文学论丛》1987年第6辑。
[3]福斯特《小说面面观》第3—4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4]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卷9第3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鲁迅《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
[6]《魏晋新语》、《语林》、《郭子》诸书皆已亡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有若干则,是为王能宪考辨所据。
[7]除简化外,刘义庆也不乏增补之处,但目的仍在于突出人物个性特征,更显生动。如王蓝田食鸡子事即为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