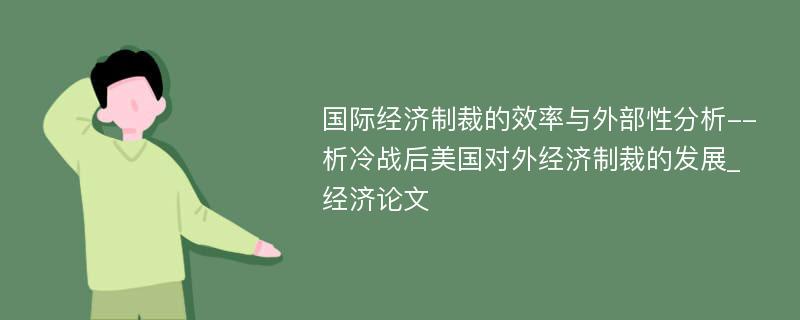
国际经济制裁的效率与外部性分析——兼析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后论文,对外经济论文,效率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经济制裁及其效率的有关认识
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对外政策工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432年,雅典运用贸易禁运打击麦加那。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据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尔(G.C.Hufbauer)对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发生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50多件[1](P.403)。
对经济制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效率上。一般而言,国际经济制裁就是通过限制经济往来给对方造成一定经济痛苦,从而达到特定的政策目标。因此,人们往往结合中介目标、终极目标及其相关性评估其效率,即经济制裁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对目标国经济产生影响;经济制裁的各种影响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终极目标。前者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取决于目标国对外依赖程度和调整能力;而后者则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取决于政治认同和抵抗意志对持续制裁的承受能力。由于经济制裁所需要的条件比较复杂,较能完全满足,因此许多学者并不看好其效率。伊利沃特等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2](P.110),即使在90年代,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约1/4[1](P.403)。
在影响经济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标国所承受的经济成本。伊利沃特的统计发现,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过目标国GDP的2%,而失败的案例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2](P.109)。目标国所承受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转换成本。直接成本受目标国的对外依存度等因素的影响。目标国对与发起国经济交往的依赖越大,制裁的影响越大;转换成本在目标国内部经济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受国际社会对制裁合作程度的制约。国际上参与制裁的国家越多,制裁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越小。直接成本与转换成本与目标国对外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相联。敏感性主要取决于一国对相互交往的依赖程度,而脆弱性则是从动态角度反映其寻求替代的调整能力。尽管有些国家对进口某种商品的需求比较大,即其敏感性高,但如果在进口中断后能够迅速从新的地方获得替代,则脆弱性并不高,制裁所造成的影响不会有多大。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如果调整成本太高,则敏感性也会发展成为脆弱性。从根本上讲,一国对经济制裁的脆弱性取决于其资源能力、政治意愿和政府能力。
在实际经济制裁中,对外依赖与国际合作并不是确保经济制裁成功的充分条件。“以资源类型为衡量标准的权力与对结果的影响为衡量标志的权力之间很少出现一一对应关系。”[3](第12,13页)。坎波菲(Kaempfer)和罗温伯格(Lowenberg)以及罗伊(Rowe)清楚地意识到制裁的效率不能仅仅参照它对目标国人民所造成的经济打击程度。巴德文(Baldwin)认为经济制裁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手段,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本质上是政治的。仅集中于经济成本,就忽视了实际迫使目标国领导人屈服的因素[4](P.18—19)。特别是以威胁目标国国家安全或颠覆其政府为目标的制裁,必然遭到其殊死的反抗,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1990年以来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的多边经济制裁,无论国际合作程度还是对伊拉克的打击程度都是空前的,但最后还是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推翻萨达姆政权。
摩根(Morgan)和舒巴赫(Schwebach)从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将效率问题转变为“制裁什么时候起作用”,而不是“它们是否有效”。他们认为,制裁给目标国所造成的成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才能起作用。而制裁成功的条件十分复杂而且较少能够完全满足,因而效率低下。正如戈尔唐(Galtung)所言,“经济制裁最初可能是导致政治整合,稍后可能更后才会导致政治瓦解,或许永远也不会……制裁创造了一种能够容许更多牺牲的社会条件,从而使政治瓦解的极限需要更晚才达到”[5](P.378—416)。
在效率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如何理解经济制裁被越来越多使用的原因呢?许多保守派认为经济制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其政府,缓和其内外政策,阻止其军事冒险,即使没有达到所宣称的目的,但也避免了不作为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更糟糕局面,并为进一步的行动创造了条件。还有人认为,经济制裁是在软弱的外交交涉与后果严重的军事行动之间的一种相对廉价而有效的选择,当面临非致命挑战时,“制裁能够在战争与漠然处之这两种可怕的选择之间提供一种非军事的替代办法”[6](P.75)。
二、国际经济制裁的外部性与效率
经济制裁必然会对目标国产生消极影响,但未必能够或者马上达到目标,还必然会经历一个消极影响的累积过程,即经由物质损失到利益分化加剧、认同破裂,再到抵抗意志的崩溃,才能够最终实现经济制裁的终极目标。在这一累积过程中,经济制裁的外部性对其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外部性实质上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与个体成本收益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经济制裁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使财富和权力不仅在发起国和目标国之间,而且在国际第三方行为者之间,以及各国国内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必然引起他们对制裁的不同态度,从而影响到经济制裁的效率。
经济制裁在国际层面的外部性,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无论理论推导还是经验直觉都认识到,国际制裁的效率与国际合作的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了各国对经济制裁的潜在脆弱性,同时也增加了规避制裁的机会[1](P.403)。面对发起国经济制裁所造成的资本、商品或技术的中断,目标国在进行国内调整的同时,必然要寻求国际替代。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多边合作,是确保制裁成功的必要前提。鉴于参与合作的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必将因经贸转向或失去制裁所创造的获利机会而在经济上受损,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国际共识,并提供必要利益补偿,是获得国际合作的关键。随着制裁的推进,参与合作的边际收益不断减少,与其机会成本之间的矛盾会不断激化甚至影响政治共识。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长期对抗中,美国一直以经济和军事援助迫使西欧和日本加入到对他们的经济制裁中来。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欧日逐步要求恢复与东方的经贸往来,以解决日益突出的市场与原料问题,与美国在出入管制的范围和程度上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的冲突不断。
经济制裁在目标国的外部性表现为目标国内不同的反弹。从发起者的角度来讲,经济制裁就是要给对方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迫使其改变不受欢迎的政策,或通过民众的不满改变政府。然而在面临外部强制时,目标国无论是出于政权利益的需要还是民族国家利益的需要,都会进行抵制,并加强政权控制。这种抵制的程度和决心依各国的体制和民众的凝聚力而定。同时,由于经济制裁首先打击的是目标国社会的下层和对外联系紧密的部门,结果往往首先会加剧民众对外部强制的反对,并削弱了外部力量借以影响目标国的渠道。在有些情况下,制裁还会在目标国内部产生一些受益于该政策的利益集团(从事走私或进口替代的行业等),他们会为延续其既得利益而支持政府的抵制政策。但是在制裁持续的情况下,如果目标国政府缺乏强有力的公正干预,不断加剧的利益分化会破坏国内认同,削弱政府动员基础,从而使外部矛盾内部化,最终导致政府更迭。
对于经济制裁在发起国内的外部性,许多传统的相关文献重视不够。它们大多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上,即国家作为一个单一意志的理性行为者,经济制裁是其单一意志的体现。实际上,经济制裁必然也会在发起国内造成受益者和受害者,而且受害者的成本分担也是不均匀的。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与深化,经济制裁所造成的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一般说来,与进口竞争的行业会从中受益,而依赖进口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以目标国为市场的生产者则会受损。利益受损者必然要寻求突破。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粮食制裁,还是80年代的油气管道禁运,在与扩大此类贸易有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最终主动放弃了制裁。美国七八十年代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资产冻结,既包括保存在美国本土的两国资产,还涉及到美国银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中的资产。其实施不仅引起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的法律冲突,损害到该地的主权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金融界的利益。一些美国专家指出,这将导致大量的外国政府储蓄从美国银行逃离,“从更广阔视野看,更重要和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的是,客户对美国银行服务能力的信心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类顾客离开纽约或美国其他市场,到诸于伦敦这类被认为能够提供比较公平环境的外国市场”[7](P.143)。据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在1995年的报告称,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在150亿到190亿美元之间,并且影响到约20万工人的就业问题[6](P.75),其结果必然引起相关行业的不满。
经济制裁的外部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还体现在道义上。道义是凝聚共识获得内外支持的重要无形资源,没有道义合法性的政策不可能得到持久广泛的支持。随着制裁的推进,对其道义性的质疑有可能将各自运动的国内外外部性整合为一种反对制裁的共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各国不仅在增进物质利益的方式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而且在一些基本价值观上也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些都将对各主体处理相互关系和共同问题的原则和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美所主导的对伊拉克的全面制裁,首先导致妇女、儿童以及老人等社会最下层的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引起国际社会对制裁的强烈批评。
三、冷战后美国经济制裁的发展特点及影响
20世纪以来,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使用经济制裁最多的。据统计,从1914年到1990年间的116起经济制裁中,美国发起的就占有77起[2](P.97)。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更加频繁地使用经济制裁,推进其战略目标的实施。在冷战后新增加的50多个制裁案例中,美国主导的就占到36个以上,涉及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1](P.403)。
(一)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主要特点是辅助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和针对性制裁(Targeted Sanctions)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制裁主体和客体的非国家化
辅助性制裁是90年代以来美国为了迫使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主导的制裁,以进一步强化对目标国寻求国际替代的打击而采取的一种带有治外法权性质的政策,它不仅要打击目标国,而且还要打击与目标国进行经济交往的第三方国家的公司。他们认为这些经济交往支持和帮助了这些政府,因而同样负有责任。在对参与缅甸经济活动的尤诺克(Unocal)公司的起诉中,原告认为,参与被证明虐待人权的缅甸军政府的商业活动,就足以证明尤诺克公司对缅甸军政府违反人权负有责任。1995年所颁布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禁止不合作的外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美国进行商务活动。2001年初通过的《苏丹和平法案》,禁止参与苏丹油气资源开发的外国公司在美国获得资金或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市场交易其证券。这与冷战期间美国以取消援助来制裁拒绝合作的盟友相比更具进攻性。
针对性制裁主要是针对目标国内特定的集团或个人。由于国家不再被看做一个单一意志的独立行为体,而被看做是由不同意志和利益所组成的地理范围,相伴着更加强调掌权者对国家行为的个人责任,以及对经济制裁的人道主义后果的关注,导致了针对性制裁的兴起,它是为了将其影响集中于领导人、政治精英和被认为应对不受欢迎的政策负责的社会成员身上,以减少国际舆论的谴责和目标国抵制的民众基础,分化和转移矛盾。90年代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小国家的一系列制裁中,不仅特定物资的进出口受到禁止,而且制裁还直接对准执政集团的成员及其家属,他们的海外银行账户和其他金融资产都被冻结,签证被取消,来往海外的个人飞行也被禁止。
对外经济制裁的频繁实施及其方式的演变与美国国会的干预有着密切联系。冷战后,国会越来越深地参与到经济制裁的发起和实施中,这反映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不断增加的活动,因为议员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国内选区和利益集团的支持。在冷战时期,制裁所导致的国内利益分化被对苏联遏制的政治需要所掩盖。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外交政策的目标次序,在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缺乏明确共识的情况下,国内利益集团获得了相对更大的影响,纷纷要求就其各自所认为的优先问题采取行动。
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制裁动议不仅来自于国会,而且来自于州和地方政府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从80年代开始,美国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利用退休基金和政府购买,抵制与某些政府做生意的公司。在80年代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运动时,有23个州和80个城市采取经济抵制的方式。90年代又转向缅甸、尼日利亚和印尼等“违反人权”的国家。1996—1998年间,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等7个州的12个县、市共13次宣布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1996年瑞士银行隐藏大屠杀受害者秘密账户的集体诉讼被提出,纽约市和纽约州的官员威胁要禁止瑞士银行承担市政养老金业务或在该市进行商业活动,以迫使其处理纳粹抢自犹太人的黄金和大屠杀受害者秘密账户。
此外,美国司法机构的司法实践也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产生影响。1999年11月,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对马萨诸塞州要求其州政府机构联合抵制在缅甸做生意的公司的法令提出诉讼。最高法院虽然认为联邦法律优先于马萨诸塞州法,然而其判决却没有宣布这类行为违宪并禁止州和地方政府单独采取对外经济行动,因而使得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够自由地运用不同手段对目标进行制裁。在尤诺克案件中,州地方法院在2000年最初判决是支持该公司的,但2002年第九巡回法院又要求进行重新审理。
(二)辅助性制裁和针对性制裁的兴起及其主客体的非国家化,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国内外外部性,进而对其效率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美国经济制裁所呈现出的这些特点首先反映了苏联解体后美国推进其战略方式的变化。这些制裁的综合运用强化了对中小目标国的压力,大大压缩了其生存资源和对抗潜力,同时分化和转移了矛盾,减少了目标国内的外部性;在对付大国方面,冷战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美国更多地使用针对性制裁而不是辅助性制裁,这样在推进其战略的同时可以避免双方关系的全面对抗,减少其外部性。美国曾多次以扩散武器为借口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相关企业进行制裁。美国政府认为这样可以一方面用制裁打击他们,另一个方面仍保持在其它领域磋商的余地。“9·11”之后,美国将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其主要威胁,通过国际合作实时监控和冻结其资产,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必要手段。
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制裁的国内外部性,而一些具有治外法权性质的制裁也增加了国际层面的外部性,甚至与美国的对外战略相冲突。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在20世纪的外交政策越来越由经济和种族利益集团所决定,而不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因此,更容易损害美国的其它外交目标。亚美尼亚裔犹太人集团所推动的对阿塞拜疆的制裁,严重损害了美国在阿塞拜疆石油的战略利益。古巴裔美国人社团所支持的具有治外法权性质的《赫尔姆斯—伯顿法》,不仅遭到了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盟友的强烈反对,还遭到国内其它行业的反对。作为反应,欧盟威胁要向WTO起诉《赫尔姆斯—伯顿法》,还和日本要求WTO专家委员会裁决马萨诸塞州惩罚在缅甸经商的外国公司的法律。在国内,除了农产品生产者等相关行业外,以前不受制裁限制的美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也受到该法的限制。国内外外部性往往相互作用,损害美国的长期经济利益。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国内各部分与国际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扩大了经济制裁的外部性;但同时,经济制裁作为美国推进对外战略的一种非军事替代手段,仍将被长期广泛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