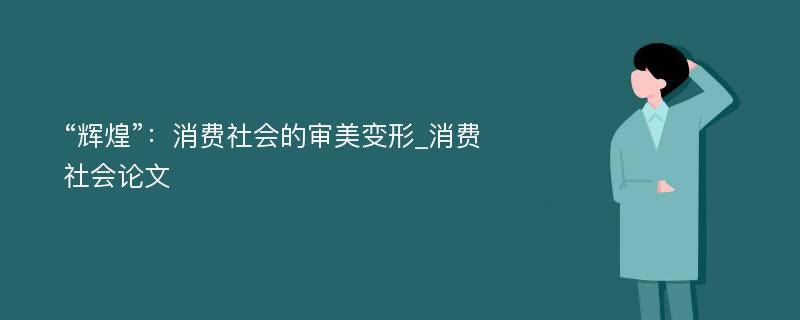
“漂亮主义”——消费社会的审美变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漂亮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丹尼尔·贝尔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 当下,视觉似乎已经具有一种本质主义的特征,视觉冲击力这个词描述的不是对对象一种无功利的赏玩,而是对人的眼球毫无掩饰地剥夺和占有。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审美文化中,催生了一个新的语词“唯漂亮主义”。这个肇始于电影评论的美学用语,是郝建先生对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一些商业影片和一些带有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片的风格特征的界定。虽然从语词上只是将“唯漂亮”置换“唯美”,但是其内涵却发生了重大的移位。这种由“审美”过渡到“审漂亮”,究竟是一种语词的游戏,还是审美在深刻且复杂的文化背景下的新呈现?本文试图从“漂亮主义”的内涵和特征入手,分析审“漂亮主义”为何盛行,以什么样的方式盛行,审“漂亮主义”究竟和传统经典“审美”有哪些不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置换,在消费社会下这种审美文化的出现对传统审美产生了怎样的一种影响。
一、“漂亮主义”的内涵和特征
关于张艺谋系列影片的探讨催生了一个所谓的新的美学术语,就是“漂亮主义”。郝建先生认为,以张艺谋影片为代表的,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些申请片都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点,“纯净、明亮,这是唯漂亮主义一眼看上去的明显性质。画面要求色彩的饱和,画面中的空间呈现、大气透视都要求很‘透’。这类作品的画面和音乐有一种光滑而明亮的华丽”。② 这种唯“漂亮主义”强调“视觉和听觉呈现方法是逐步规范化、定型化、程式化的”。但是,却缺乏“那种天马行空的飞扬感和真正的浪漫性”。③“漂亮主义”强调视觉的绚丽和灿烂,强调视觉的冲击,这种对“漂亮主义”的特征的概括,是比较具体鲜明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所有的定义都只具有微小的价值。”“漂亮主义”作为一个命名,其意义可能是微小的,用这个语词为一种新的美学趣味命名,无非就是寻求一个概括的方式,用以揭示其存在的意义。而所谓“漂亮主义”,在笔者看来,就是以明亮绚丽的色彩,精致的构图为主的意象形态组合,以视觉冲击力为主要指向,以消费“漂亮”符号为旨归的一种所谓的美学趣味。“漂亮主义”就是要形成一种虚拟且完美的意象形态。强调视觉冲击和视觉快感的第一性,并且要完成一种消费逻辑建构的实际功能。米兰·昆德拉说,意识形态再有力,总敌不过现实,可是意象形态却超越了它,意象形态比现实更强大。“漂亮主义”所形成的意象形态正在悄然改变人们对于审美的理解,重新格式化人们的审美感知。“漂亮主义”集结了各种功能性的元素,比如明亮对于视觉的刺激,比如精致完美的细节给予视觉的享受,比如放大或放慢了一些常态下视觉不可见的东西对视觉产生的陌生化的效果(比如张艺谋电影《英雄》中水珠的放大性效果,以及《十面埋伏》中对飞刀的慢镜头展示),这些都具有某种仪式化表演的特征,形式大于内容,甚至压倒内容。“漂亮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一种仪式化的视觉冲击来实现所谓的意象形态的美感,并且以虚拟符号的形式建构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人们创造并且享受美轮美奂的日常生活的意象形态,正是“漂亮主义”的世俗化呈现。
当“漂亮主义”走出狭义的影视美学趣味的域界,进入到更广泛的审美文化视域,它逐渐成为消费社会中“审美”的一个变形。因此,笔者认为“漂亮主义”还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不能忽略。
第一,图像至上的视觉完美主义。“漂亮主义”追求的就是图像和影像形式的视觉冲击力,并将此置于逻格斯中心地位,对此关注的结果就是人们从理性的“文字崇拜”过渡到了感性的“图像崇拜”。“漂亮主义”和仪式化的视觉审美效果是相关联的,这些图像要的就是“好看”的效果,要的就是人们“震惊”和“惊艳”的感受,至于“好看”之后有什么,是否导致意义的缺失和陷落,并不重要。迈克·费瑟斯通说:“观众们是如此紧紧地跟随着变换迅速的电视图像,以至于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联结成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他(或她)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叠连闪现的屏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和感官刺激。”④ 美是一种形式,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说美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如果缺失了意味以及深沉的人生和情感体验,而只流于视觉的肤浅的快感,那么审这种“美”,无疑失去了审美的真正意义。“漂亮主义”更多地停留在视觉刺激上,这种貌似精美的图像形式,不能掩饰缺乏“韵味”之后的意义的苍白和粗糙。
第二,“漂亮主义”的意象形态特征。意象形态(imagology)是米兰·昆德拉在其长篇小说《不朽》中使用的概念。昆德拉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由于意象设计师的大量出现和其对传媒的控制,人们通过亲身体验把握现实的机会被剥夺了,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广告宣传、政治口号、民意测验、流行趣味共同编织而成的意象形态之网中。意象形态放大了一种假想的现实却遮蔽了真正的存在。“漂亮主义”所呈现的恰恰是一种对于意识形态柔媚化的表现。精美时尚的杂志,明亮绚丽的电影,包括以“品位、格调”定位的室内空间装饰都成为一种意象形态,人们在一种氤氲气氛中寻求到了一种幻象所带来的快感。与此同时,视觉的挑剔性和疲劳性使人们不断去追逐更新更异更漂亮的符号,“美的整体只是变成了漂亮,美学化的意象形态,只不过是从艺术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然后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⑤
如果说审美给人的感觉是“陶醉”,那么“漂亮主义”给人的感觉只是一种“解渴”。审美可以反复地回味,可以经过多次体验之后依然如初见;而“漂亮主义”的“与大多数当代文化生产者有关的‘无深度’,紧紧盯住外观,表面和瞬间冲击力,都毫无随着时间推移的持久力量”。⑥ 图像和瞬间的视觉冲击无法提供给人们语境,“漂亮主义”的意象形态特征使得“漂亮主义”观赏者把幻象当作真实,把想象当作体验。“漂亮主义”的视觉旨趣,难以成为人们心灵深处深沉的审美体验。
二、“漂亮主义”盛行的原因
“漂亮主义”的流行和消费社会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个术语最初只是以小众的方式呈现,但却以大众喜爱的方式扩散到社会文化中。“漂亮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传媒致力于谋划的形式元素。在消费社会,美丽不再单纯用来观赏,而是作为重要的消费内容成为了大众乐此不疲的趣味。美也沦为时尚的符号,在传媒的世界中以简单且媚俗的方式稀释着美学所能够承载的意义世界,传媒所宣扬的大众文化“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麦克唐纳语)。房地产商宣传自己的住宅是“美学生活蓝本”,用漂亮的意象形态直接表明自身的审美精神,实际上,这和真正的审美精神没有多少关系,只不过打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幌子假装美学而已。媒介成为消费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手段,人们对于“漂亮主义”的渴求,表明媒介已经成功地以某种隐藏的方式,将“漂亮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置入人们的内心。电影、杂志、购物中心、家居装饰等等,几乎在整个日常生活领域,“漂亮主义”已被演绎成为一种全民的游戏。那么“漂亮主义”为何如此盛行?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消费社会逻辑所贯穿的对符号意义的消费。波德里亚认为,符号的区分逻辑使得人们通过消费符号以表明自己超越原来的群体而晋升到更高的群体,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远远大于对商品自身的消费。消费“漂亮”本就是“漂亮主义”的符号旨趣,人们通过符号确证自身身份,以此获得社会意义的认定。当T型台上的模特,极尽奢华和绚丽地展示人们对于“漂亮”的不断地寻求,那些绚丽的漂亮的“梦”,会在后工业社会下被制作成为一种现实,只不过这种现实,是伪审美意象与大众传媒共同拟造的幻象。和“漂亮主义”有关的一切,都注定和消费结合,然后合谋,去瓜分审美的世界,并一步步蚕食人们心灵中对美的悸动和无目的的美好,“漂亮主义”最后演变成一种“象征性资本”。所谓象征性的资本,并不是实存的,而是通过意义的显示,所具有的可以增加自身价值的一种资本。这种资本被界定为“聚集证实拥有者之趣味与个性的奢侈品”。⑦ 趣味和个性奢侈品,这个符号的典型作用就是证明拥有者自身的层次和品位,虽然只是在一个小众的范围。事实上,“漂亮主义”就是从小众开始,然后从个人趣味转型为一种大众的诉求,“通过获得身份象征的一切方式而追求社会差别的沟通,一直是都市生活的核心方面”。⑧
第二,媒介文化所带来的视觉化和形象化的转型,促使人们对“漂亮主义”的热衷和追逐。在这个讲究速度的时代,人们对于文字远不如对于图像的喜爱,人们对带来视觉冲击的东西更感兴趣。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文化的盛行营造了一个后文字时代的图景,这种以技术媒介为特征的新世界,实现了更为迅速的观念、态度和形式等多方面的交流,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甚至一些更高端技术的新媒体,共同构筑着一个崭新的令人震惊的时代。喧嚣的迷乱,嘈杂的热闹,眩晕的斑斓,这让人们不知不觉中对视觉冲击力迷醉。媒介以其独特的力量为大众制造了一个电影般虚幻的“漂亮主义”传奇,人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意象形态来完成自身对于现实的想象。媒介制造了“漂亮主义”,人们已经习惯并需要“漂亮主义”来填补心神涣散之后的“震惊”。“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艺术和传媒也在做同样的事情”,⑨“漂亮主义”就是在这种专注于表演和媒介形象的文化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
第三,文化生产者对于大众的引导。大众随波逐流的特点是工业化社会造就出来的群体特征的突出表现。大众的喜好究竟是自己真实的喜好,还是在文化生产者的引导下的一种虚假的表现?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如果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说明了人们是在一种虚假的形式下建构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并且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内化,并认为这是自己真实意图的呈现,那么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就是在文化生产者图谋之下大众不知不觉形成的一种非真实意图的体现。文化生产者与大众之间有很多联结点,比如建筑、广告、时装、电影、筹划多媒体事件等。那些时尚的发布者的趣味,那些斥资巨额的国产大片所呈现出来的趣味,那些杂志策划者在杂志中所表现出来主导性的个人趣味,无不是“漂亮主义”的始作俑者。以精英为代表的小众操纵以草根为代表的大众,然后与之愉快地结合在一起,共同上演了“漂亮主义”的审美文化的饕餮盛筵。“大众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它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数量比例,但却不拥有大多数的话语权、决策权和支配权,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小众,他们可能只稍稍触碰了一下自己的思维,却可以让这个世界更具风格”。⑩ 文化生产者是属于“小众”的一些人,正是这些文化生产者引导了大众,把“漂亮主义”营造的绚丽和消费社会的符号逻辑结合起来进行社会区分,使得较低群体希望通过这种符号所营造的虚拟的漂亮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群体。所以说,“漂亮主义”不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么简单,而是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只不过这种建构是以意象形态的方式完成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且“获得了串通一气的沉默的效果”。(11)
三、“漂亮主义”的样态呈现
美是人类自由、超越、无目的和非功利的一种理想的形式。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体现人类自身全部丰富性和自由性的“美”遭到了解构。美体现了人的全部自由自在的感觉,但是“漂亮主义”却切割了人的整体性感觉,突出人的视觉性。那么,“漂亮主义”究竟以什么样态呈现出来?
第一,以静态图像表现出的“漂亮主义”。这突出体现在时尚杂志对于身体的完美再现,对各种品牌商品的精致呈现。人们看到的是化妆品修饰下漂亮的毫无瑕疵的美女的脸,看到的是氤氲在诗意中的各种品牌产品美学化的表达。“那流畅线条的机械质感,那发动机的轻微轰鸣,都被赋予了一种性灵,一种性感,一种美学的优雅甚至德性”。(12) 在诸如《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瑞丽》等女性时尚杂志,和以《男人装》为代表的男性时尚杂志,无不倾心地去制作漂亮、性感和时尚,这种虚拟制造出的完美和漂亮降低着人们对于现实的自信,增加对自身不完美的恐惧,“应该警觉,不是缺陷本身,而是对缺陷的遗忘”。(13)“漂亮主义”集结着品牌的社会认同、意义的完整统一、绚丽的色彩和明丽的质地等元素,给人们虚拟的美的形式和意象,通过静态画面所呈现出的炫目的“漂亮”,再配上一些符合受众趣味的所谓的“诗意”表达,经过视觉和听觉双重渗透,“漂亮主义”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一切皆漂亮的恍惚和眩晕。“广告传媒与视觉美学联姻,引导着人们进入流动奔腾的读图时代,空灵轻盈,没有重力的形式幻觉取代了实在性的笨拙和沉重。在越来越快的感觉里,生命也越来越具有了某种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14)
第二,以动态影像表现出来的“漂亮主义”。“漂亮主义”原本就是对电影美学趣味的一种解读,只不过现在被普适化了。“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文化。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5) 电影和电视,包括新媒体,以动态影像的方式进行着“漂亮主义”的演绎。张艺谋《英雄》、《十面埋伏》等影片中所呈现出的那些绚丽明亮考究的画面,曾经“震惊”了很多欣赏者。如果说商业影片对“漂亮主义”的诉求还带有对艺术形式的刻意努力,那么电视广告呈现出对“漂亮主义”的追逐更多的是物质利益的优化实现。消费社会的符号逻辑使得广告更注重这种区分,精致、漂亮、唯美都表明一种趣味、一种追求、一种品质。这些无一不体现消费社会中人们对于符号的价值渴求。由于媒介,尤其是广告不再参照真实的物品和世界,而是依据自身的信息系统来制作画面,所以人们生活在一种“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的世界之中。“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16) 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影像的“漂亮主义”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渗入,于无形之中将人们符码化,使其成为符号区分之后的类群体。
第三,以空间形式表现出来的“漂亮主义”。空间是人们延展自身的一种方式。“漂亮主义”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进都市人的生活之中,那些优雅、舒适、明净的购物中心,那些在灯光晃动下闪耀的商品,无不展示着“漂亮主义”的细节和内容。人们既可以自由地游走在购物中心漂亮的空间里,享受视觉的美感,同时也在消费自我的一种趣味。这种空间的“漂亮主义”形成某种暗示:这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有能力消费,消费将带给你们满足感和自信力,你们将因此晋升到一个更有品位的高层级群体。这是典型的购物中心所传递的内在旨趣。
还有一种空间是不容忽视的,就是街道。虽然街道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的载体,在这个载体中漂浮着各种趣味和各个阶层的喜好。但街道是“人与物之间的中介:街道是交换,商品买卖的主要场所,价值的变迁也产生于这里”。(17) 因此,“漂亮主义”的渗透绝不只是在购物中心狭窄的空间里,街道同样上演着“漂亮主义”。当然这种注解脱不了和广告的干系,汪民安说:“广告的色彩,就是街道的色彩;广告的形象,就是街道的形象……广告不是布满了街道,而是占领了街道。”(18) 广告在街道上既可以一种静止的方式呈现,比如耸立在街边炫目亮丽的广告牌,也可以流动的方式呈现,比如各种交通工具上的广告。所以,在街道这个空间里,上演的“漂亮主义”是多层次多棱镜的,时刻让人们的视觉经受着不可拒绝的冲击。
不仅仅是公共空间,当室内装修成为人们乐此不疲的一种爱好,表明着“漂亮主义”正从公共走向私人。人们对于精致生活的寻求和对日常生活“美学化”的向往,再次证明“漂亮主义”已经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自觉。如果说,静态的图像和动态的影像都是人界于外部的一种“看”,空间的“漂亮主义”则是人们以行走的方式由外部介入到内部。“漂亮主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盛行,并且贯穿了人们动和静的双重状态中。
四、“漂亮主义”与传统审美的区别
电影、电视、杂志、互联网,包括购物中心等空间以及借助这些媒介形式的广告,都将审美逼向了一个“去自由”的境地。审美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是以变形的方式适应新世界,还是继续固守传统保持自身的纯洁和自由?“美”,“这个以最切近而又最神秘的方式伴随着人类精神的历史;以最明显的表象和最莫测的本质挑战人类的智慧;以最崇高的承诺和最艰苦的承受塑造人的心灵”的存在,面对新的时代特征,传统审美所具有的经典的内蕴,是不是在消费社会已经成为明日黄花?
第一,“漂亮”和“美”在很多时候表达的是同样的含义,但是,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这又是两个有着清晰区别的语词。漂亮表现出了对视觉的强大的倚重和偏爱,对视觉的占有性和冲击力。这种对视觉的侵略性不仅和媒介有关,在消费社会里,消费符号逻辑命定性地主宰了以审美为名义的多种噱头。在这个华丽、漂亮,甚至奢侈的表象下,传统的审美偏安一隅,甚至被盗用,被重新组装意义,以证明我们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当代社会对‘形象’的过量生产使人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强大的视觉之流,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面对汹涌而来的视觉之流,人们根本不可能再以静观、冥想等方式去细细体悟对象”。(19) 消费社会消费了“漂亮”,将后工业社会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斑斓炫目的“漂亮”抬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并进行着形而下的诱惑和吸引,使人们越来越给予其前所未有的关注,只不过被抽干了意义内蕴之后的“漂亮”总显得那么的干瘪和无味。
第二,审美注重感官愉悦和生命体验的双重境界。“漂亮主义”强调快感冲击。审美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一种本己性的自由的无目的精神交流,是主体自身自由以及主体对于世界的超越性表达。人用自己全部的自由自觉的本质观照对象,对象也向主体敞开其最本质的方面,不是目的,不是限制,而是自由和超越。审美不是表演,是体验,是感受,是人们从日常生活走向自由生活的一种可能性途径。审美带给人们的是游戏的忘我,超越的自由,精神的想象,并且以这样的方式获得对于世界的真理性的体验。海德格尔对梵·高《农鞋》的读解,就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的精神性的交流。“漂亮主义”并不看中审美所具有的精神意义和人的自由追求,更注重酣畅淋漓的快感冲击,让人耳目一新的视觉彰显。但是“漂亮主义”往往是昙花一现的视觉撞击之后生命体验和意义的全然不顾,不呈现审美的意义和精神指向。
第三,审美感知的过程是人用自己的全部感官与对象交流和沟通,“漂亮主义”凸显视觉的根本性。作为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本领,审美能力是审美知觉力、感受力、记忆力、想象力、理解力、判断力、选择力和创造力等方面的统一;“漂亮主义”则是基于对于视觉的偏执性的爱好,将人的全部的对于对象的欣赏能力完全的集中在视觉,且仅仅止于视觉。印度诗人泰戈尔说:“颜色吸引眼睛,但要懂得和谐的美就需要用心,需要认真的观察……因此,光通过肉眼,而不是同时通过心灵,就不能真正地看到美。”(20)“流动的画面给观众带来震惊,但这种震惊却指向消遣,指向一种感性的愉悦,这使得观众最终归于一种心神涣散的快感”。(21)“漂亮主义”过分强调视觉,从根本上撕裂了原本统一的人的丰富多重的审美感觉,视觉成为审“漂亮主义”最本质的感官存在,审美感觉被肢解得七零八碎。
第四,审美对象是有机完整的系统构成,而“漂亮主义”却片面地倚重符号形式。如果为审美对象完整的系统做一个层次划分的话,应该有这样三个层次:物质材料层、符号形式层和意境世界层。在审美活动中,这三个层次是统一的,是浑然一体的,审美主体可以通过自身的身心统一来完成对于三个层次的贯穿性的理解和体验,最终实现物我交融,神与物游。但是“漂亮主义”过分地注重对象的形式特征,强调对象的视觉效果和视觉感受,因此,突显的是符号形式层,并且停留在符号形式层,最终削弱了人们深度理解和体悟的可能。“我们已经约略有所领会,视觉文化的美学究竟是什么?高科技制作出来的电影是一种反抗意义中心的美学,一种把智力降低到儿童和原始人的美学,一种拆解深度的美学,一种感觉驱逐理性的美学”。(22)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审美构成形式。“漂亮主义”或许只是一个不成熟的术语,对消费社会下的审美变形的概括可能显得还不够周延;但是,审美在当下社会的新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容置疑的。“漂亮主义”让人们体会到视觉震撼和冲击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生命深沉体验的缺失。在传统和新变之间,审美和“漂亮主义”之间,究竟应该怎样选择?笔者认为,理性看待“漂亮主义”这个新的变形,同时我们似乎也应该坚持,“恢复和培养个体的生产性人格,使其真正进入一种把自我从种种束缚限制中解放出来的领域——即审美的自由境界”。(23)
注释: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56页。
② 郝建:《将唯漂亮主义推向世界》,《南方都市报》,2004年7月20日。
③ 同上。
④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⑤ 吴志翔:《肆虐的狂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⑥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1页。
⑦ 同上,第108页。
⑧ 同上,第111页。
⑨ 波德利亚:《完美的罪行》,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页。
⑩ 《新周刊》,2007年5月1日出版,第42页。
(11) 同⑥。
(12) 同⑤第61页。
(13) 同上,第40页。
(14) 同上,第93页。
(15) 同①第154页。
(16) 同⑨第8页。
(17) 奈杰尔·科茨:《街道的形象》,选自约翰·沙克拉编:《设计——现代主义之后》,卢杰、朱国勤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18) 朱大可、张闳主编:《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0页。
(19) 孟建德、Stefan Friedrich主编:《图像时代:视觉文化传播的理论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20) 泰戈尔:《泰戈尔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21) 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
(22) 同⑤第223页。
(23) 李西建:《重塑人性:大众审美中的人性嬗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