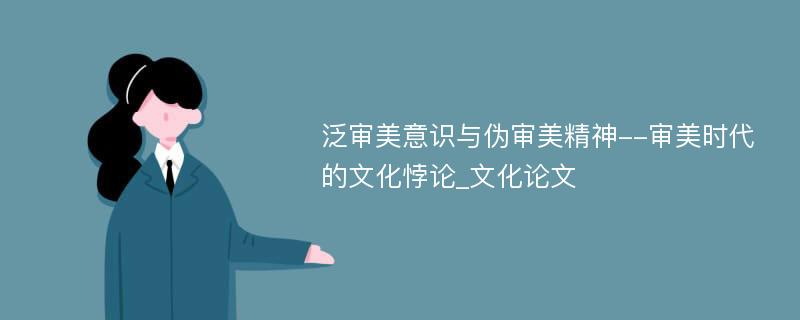
泛审美意识与伪审美精神——审美时代的文化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意识论文,精神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审美文化对形象游戏的无意义追求,在“美化”生活的普遍欲望中,表现了一种泛审美意识。这种泛审美意识,一方面是在现代化运动中个体自由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包涵着自我意识的丧失和审美理想的落空,因此,它实现为一种伪审美精神——审美活动失去了超越力量,沦为纯粹形象的物化追求。为了保护和发展审美精神,必须揭示这一当代文化悖论,批判这种形象的物化无意识,在现实和精神的两个维度的对立统一中重建审美精神的人学意识和理想。这乃是当代美学的首要任务。
一、文化的审美时代:形象游戏的二律背反
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悖论来自于现代化运动的无限发展过程全面展开所产生的自由的失落意识,并且渗透了世纪之交的瞻前顾后的情怀。一方面是挣脱了传统束缚之后的解放,自由因为现代化的无限发展要求的内涵而具有绝对的价值;另一方面是无限发展的未来指向所包涵着的对个体性的必然的否定和对自由的自我价值的消解,自我必须承担的选择的无根据和判断的无标准——个性存在的根基失落。反正之间,福祸相依,是非莫辩,妍媸相混,生死同一,因此是大悲恸,也是大欢喜;是大失望,也是大希望;是大意义的创造,在跨世纪的举措中接近于无限崇高,也是大无奈的熬煎,在天地悠悠之间独怆然无依。悖论的普遍性带来了普遍的游戏意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游戏的时代,人生是游戏,世界是游戏,宇宙是游戏。因为无家可归而乐不思蜀,当代悖论把20世纪末表演为一出人间喜剧。
在游戏的普遍意义上,悖论并不是单纯的拒斥,而且也是诱劝,甚至是安顿。也就是说,通过游戏,当代悖论以全面的逆反律拒斥了人们向终极回归的希望,同时又把人们安顿在塞壬女妖的魔境中,成为忘归的俄底修斯。因为失去了意义指向,悖论的游戏使当代人在成为游戏主体的同时,成为一个彻底的他者——纯粹的观赏者。“做”就是为了“看”,这是无家可归的当代人的无辜的欲望。在这个欲望中,古老的神话在游戏中复现了,或者说,游戏本身就是神话的复现——出埃及后,当摩西在西乃山上受戒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子民因为害怕被主遗弃而恐慌,他们倾其所有铸造了一个金牛犊,向它顶礼慕拜。对金牛犊的偶像崇拜转化为迷途者忘忧的狂欢庆典。(《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正是狂欢的必然结局,揭示了偶像崇拜的原始冲动——形象的欲望满足。当代人重复了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的游戏,不同的是,金牛犊崇拜的一神论原则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形象的标新立异。因为上帝已死,关于摩西的神话自然破灭。游戏取代了神话,成为当代人的福音。西乃山下偶像崇拜的狂欢的歌唱已经暴发成当代都市通霄达旦的形象夜宴。
在游戏与形象的普遍联系中,当代文化滋生着一种泛审美意识。这种泛审美意识不仅对审美形式表现了特别的需要,而且表现了把整个生存审美形式化的欲望。对审美形式的普遍欲望是泛审美意识的基本特征。由于泛审美意识的漫延,在这个全面物化的世界,人们转入了审美形象的全面增殖,在其中,曾经落空的浪漫的自由理想化成无处不在的形象的轻歌曼舞,似乎,席勒所展望的审美文化的时代正在到来。然而,当代生存并没有因为审美意识的泛化而上升到审美之维。把整个生存审美形式化的欲望,在审美形象的全面增殖中,不仅没有成为对物化世界压力的真正反抗,相反成为又一次更根本的物化——形象的物化,也就是说,形象,在一切物之后,成为一种新的物;旧式的商品拜物教,转化成新的拜物教:形象崇拜。
形象,成为当代人在无归之旅的宿营地;当代人在形象中栖居,但是不能构成诗意。在对审美形象的全面欲求中,泛审美意识阻止了自我与世界的历史性关联,从而放弃或拒绝了对审美表现的追求,不仅没有再创性地形成审美转化力,而且在对传统的对抗性承续中,全面消解了传统或经典的审美转化力,使艺术下降到生活的境地,审美形象物化为物质对象。泛审美意识的形象崇拜表明了审美精神的心理残余,包涵着否定现实的乌托邦情调。但是,由于这种意识是以对当代悖论的失败主义认同为基础的,对现实的否定已经包涵在对现实的屈服的前提中,因此,泛审美意识对现实的否定不仅只能在抽象的意义上,即纯粹形式的意义上进行,而且,这种否定必然采取与它所否定的现实相同的手段来进行否定——“以物化反对物化”(阿多诺)。由于意义的根本性缺失,泛审美意识在对形象的贪婪追求中最终必然丧失判断力和选择力,放弃形式主义的美学原则,陷入无原则的形象的标新立异,甚至是媚俗的“畸趣”。在这种注定失败的反叛中,泛审美意识把失败直接等同于胜利,而它的伪审美精神实质表现在对这种反诗意的结局的喜剧式的诗意狂热。这种诗意是虚假的,因为它只是关于形式或形象的——在根本上,它没有意义。所以,泛审美意识实现为伪审美精神。
诗意是审美精神的真正表达。正如席勒所言,“对于美,人却和它游戏”(参见《美育书简》,第89页),审美精神首先是一种游戏的精神;但是,它不归结于游戏,也就是说,审美的目的不止于对物象的迷恋。游戏对于审美的意义,在于游戏本身必须是审美的。一方面,游戏必须实现美的形象(有生命的形象)的创造,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成为人和世界的双重扩展;人和世界都在自由的无限意义中来展示。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游戏的审美特性在于它构成了“向创造物的转化”,即把一个实在的物象转化为一个艺术品,一个审美经验展示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游戏的意义整体,也就是在世界中的自我表现。“游戏在某种杰出的意义上就是自我表现。”(《真理与方法》,第156页)因此,无目的的游戏就有一个内在的目的:表现。表现对游戏的内在规定,同时也成为对游戏所包涵的自由原则的限制,这一限制是:游戏的自由不是一种“空虚的无限性”(席勒),或一种拘于外在形式或边缘现象上的“随意性”,它“应使形象达到表现”(伽达默尔)。表现既形象的完满实现,同时也是对形象的超越——它把形象转化为“真实事物”,一种在可能性的未来视野中的人与世界的统一体。在表现的意义基础上,游戏的虚构,不但不是一种作假,相反是向真实性的深入和发展。所谓进入真实性,是在形象的表现中达到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的解释性重建。正是在自由与真实,形象与表现的必然联系中,审美精神才在游戏的封闭体系中,构成了一个解放的国度,一个超越的诗意的境界。
泛审美意识实现为伪审美精神,是一种逆转,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当代文化本身的悖论。所谓“归根结底”,因为当代文化在总体上的悖论意识和游戏原则必然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形象欲望。这种欲望把形象作为无根基的,同时也是无归依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存在的可能。对这种可能性的认同,把游戏扩张为一种反表现的绝对价值。因此,不仅是审美游戏的意义表现被消解了,而且文化整体的意义也被消解了。换言之,在当代生活中,审美意识的泛化,同时就是文化的审美化。文化的审美化,即当代文化在泛审美意识的追求中,经过意义整体的消解和价值尺度的削平,而片面发展为以形象为主体的文化,平面化、形象化、表演化是其基本特征。由此,文化进入了文化的审美时代。文化审美时代的本质是,代替哲学和宗教,“美学成为生活的唯一证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98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文化就是审美文化。而作为审美化的当代文化的悖论,正是泛审美意识逆转为伪审美精神。
二、形象的增生与物化:形象的本体论
当代文化被指认为审美文化,是以普遍性的形象增生和物化为根据的。在这里,形象的增生和物化并不是特别意味着,当代文化具有空前的形象塑造力和表现了强烈的形象欲望。不容置疑,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重重形象包围的环境中。形象的增生和物化对于当代生活的特别意义是:形象的超额生产不仅导致了以意义消解为代价的形象过剩,而且导致了过剩形象对生活的超现实重构。形象,并且只是作为形象,构成了新的现实,一种“复数现实”(realites)。过剩的形象转化为实体,形象增生的意义必须在形象物化的意义上来理解。由于形象的物化,形象不仅改变了它与现实的影象和本体的关系,因为它本身已经是本体了;而且改变了它与人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因为现在它不再是作为人的作品,而是作为新的现实,与人对峙。形象现实的复数构成,既表明了它是无限增殖的,也表明了它对于人的不可超越性——超越的行动必然归结为新的形象增生。由于不可超越性,形象成为人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在整体上规定了当代生存的游戏情景,并且把泛审美意识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植入自我意识。因此,在当代文化被审美化的同时,当代生存也被审美化了。
形象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在于,形象不仅包围了人,而且形象改变了人。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广告作进一步的研究。广告的文化本意应当是“信息”或“信息传播”。但是,广告的运行却必然是增殖活动,即实现为“超信息传播”。广告的增殖机制来自于它的基本载体——形象。没有一个广告不是由形象构成的。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由于形象的增生和物化本质,它在成为信息载体的同时就转化成广告主体。广告的秘密是,形象的构成代替了信息的传播。当人们自以为在接受商品的信息的时候,实际上获得的是“关于”商品的形象——包装。正如包装必然大于内容,形象是必然大于商品的。而一个接受了广告去购物的当代人,他如愿以偿地买回来的,并不是商品,而是那个被称为商品的“形象”。只有对形象的买卖才是与现代商业化社会相称的。把商品销售转化为形象销售,广告不仅极大限度地带来了商品增值,而且在刺激超额购买的同时,成为对当代人的形象欲望的满足。当代人怀有一种对形象的根本性欲望,这种欲望把形象直接认同为存在,存在的欲望被代换为形象的欲望——存在就是形象的出场。在谈到为什么各家公司只是为了得到一张漂亮脸蛋作广告而不惜血本时,一位美国广告商说:“你买一只唇膏,因为你认为这姑娘看上去真棒;你买一件衣服,因为你想你会看上去和这个模特儿一样。你明白,这是一个梦:而且女人总是追逐一个梦……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一处,那里出售的是唇膏,那里形象是被卖的东西。它说的是‘你也可以进入这个花花世界’。”(《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在对形象的根本性欲望中,形象是大于存在的,因为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关于存在的形象成为“你也可以进入这个花花世界”启示和可能。商业的广告操作把握了这种启示和可能,而它表达的商业野心是,把每一种有限使用价值都扩大为对形象的根本性欲望的满足向买主倾销。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广告成了唯一的艺术品”,就是指出了文化在整体上成为过剩形象的生产和倾销。
对形象的购买是超需要的,因此是超额的——这就是“时装革命”。时装革命的意义超越了服装业而对于当代文化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当代文化的隐喻。在商品与广告的二元对立中,时装更是广告。它把商品生产彻底转换为形象生产。这种转换的彻底性在于,形象的时间性压迫了空间性成为构图的主体因素——流行是时装的第一要素。在流行的强制力下,不仅商品作为物质对象被消解了,而且形象也被抽象削平了。形象的意义就是它的无意义,而形象的价值是时间的“时新”和“过时”对立的虚构。这种虚构性在于,由“时新”到“过时”的转换,速度之快,已经脱离了现实文化情景而成为一种无文化前提的机械自动化运作。无疑,时装革命是一种商业操作,但这种操作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却是植根于当代文化的审美化品质。在这种加速度的迎新换旧中,时装不仅改变了服装的原有属性,而且也改变了人与形象的审美关系。泛审美意识的追求成为关于时装形象的非理性冲动,对审美形象的意向不仅因为规范和标准的丧失而必然丧失了,而且怪异猎奇的欲望把无趣味的“畸趣”确立为唯一的形象趣味。“畸趣”是无趣味的,因为它不仅不是一种趣味,而且是对一切趣味的破坏和变态。畸趣在根本上是趣味的丧失和缺失。面对时装的超前变异,更多的人,甚至时装设计师本人,都感到它的异己性(即时装的纯粹表演性)。畸趣破坏了一切趣味,最后它是针对趣味和人本身的。时装的意义最后体现在设计师和模特儿溶为一体的现场表演。设计师在模特儿身上的即兴制作,不仅把手中的布料变成了阿拉伯飞毯,而且使模特儿的存在,也就是人的存在,在这块飞毯的变形魔术中被彻底割袭和抛弃了。因此,时装革命是把人的形象游戏发展到了这样的极限,在这个极限上,形象成为一种超人的形象游戏。
时装的时间性是同现代生活的加速运转相联系的。生活变换之快,也许,只有时间本身才能成为当代生活的说明。因此,时间必然成为当代生活的第一要素。在低节奏时代,时间提供给个体的是一种整合力量,也就是说,个体可能努力而从容地把自身实现为一个完整的存在体;而在现在的高节奏时代,时间成为自我存在的无意识,它给与个体的却是一种自我分裂的冲动,因为时间的绝对命令把个体自我完成的愿望转换成了对时间的本体欲望。当这种欲望进入游戏世界,它就必然把形象分割为瞬间的对等物——片断。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当代生存是一种瞬间性的、片断式生存。泛审美意识的伪审美精神就表现于它是在根本上丧失了人类自我形象的整体性的前提下进行形象游戏的。支持着这种形象游戏的是自我分裂的无意识冲动,而它的结果必然是形象的分裂物——片断和片断的游戏。MTV在把音乐转化为形象的同时,进行了对形象的无意识分裂。在画面分割和镜头闪回的节奏化交替之间,人被强制地束缚在形象分裂的狂欢中。正是在与形象的片断的关系中,而不是与形象的整体关系中,当代人遭到了形象物化力量的打击,并且因为这种打击而迸发出无限制的形象欲望。可以说,MTV的煽情力量就在于这种分裂的打击力量——它通过形象暴力传达一种自由的幻觉。由于人对形象的关系局限于一种片断关系,因此,在形象游戏中,关于整体性的瞻望就具有根本性的喜剧意味,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反讽。自我反讽的风格无疑是当代游戏的基本风格,游戏者通过失败主义的自我戏耍来获得一种空洞的自我意识。表演,而不是对某种东西的表演,被绝对化了。MTV既不是听觉艺术也不是视觉艺术,而是表演艺术——它只是表演。在这里,表演的意义是对被表演者的彻底否定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这里,自我不仅被认为只是一种可能,而且被认为必然是一种危险的可能。成功的希望就是在尝试这种可能的同时逃避或毁灭这种可能。因此,现代形象游戏在反讽表演之外,必然包涵着一种疯狂的意志。片断内在地具有复归于整体的欲望,而时间把这种复归转化为更深的分裂,并从相反的方向驱迫这种欲望走向分裂。
在形象增生和物化的时代,包围着当代人类的,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或无数多种,而是实体化的形象本身。正是这形象本身,可能或者危险,打击或者慰藉,成为人类个体的当代命运。这种命运,注定了形象对当代生存的替代,也注定了个体对形象的根本性欲望。正因为如此,当代生存是根本性无根的,而寻根的热情必然性地转化为无根形象的无意识表演。这种表演的无意识特征是,它只是生存的表演,而不达于生存的根本和意义。当代文化的泛审美意识游戏,在与审美精神的审美游戏的形式同构关联中,对形象的游戏是封闭在这种无意识表演中的,而放弃了对审美精神(意义整体)的表现。
三、当代形象:市场与技术联姻的自我幻影
前面对形象的本体论阐释已经在形象的增生和物化的统一性中揭示了形象构成了对人的异己的存在。现在我们要在生成论的分析中来阐释为什么形象成为一种对人的异化对象。我们将会看到,当代人对形象的绝对认同,是现实的强制力作用的结果。现实的强制是以对自我观念的转换为核心的,即把自我的现实的平等、自由和个性的观念,转换为形象的平等、自由和个性的观念——表演。自我观念的核心转换,形成了一种虚假的民主意识——形象的民主。关于形象的民主原则是,在人人都具有平等自由地选择和享受形象的权力前提下,根本上确定了形象的无规定性和游戏的无规则性,也就是说,形象游戏在其无意义的纯粹性上必然地是符合民主精神的。形象的民主原则是以大众的名义提出来,并且由大众来维护的。在自我扩张的时代,只有大众构成一种保证——它保证了自我,也保证了对自我的否定。
形象生成的第一个前提是,大众保证了民主——自我。兴高采烈迫不急待地进入晚会现场的观众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种先在地保证,并且由于这种保证,他对自我满怀信心。但是,大众是什么?如果大众没有特别的名字,他就只是众多的个人。多数与个人是一种对立。问题是,这种对立怎样在大众的名誉下被消除了?换一个问题就是,众多的个人怎么聚集成为一个大众?假如不用神秘主义来搪塞问题,在进一步地追问中我们会发现,大众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这是一个更真实的名字——市场。市场聚集了个人并构成了大众。形象生成的民主原则作为一种大众保证,是在市场交换的普遍性中完成的。当形象生产商在呼唤大众的参与的时候,他无疑要求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等价交换。因此,当代形象游戏必然是以广告为先导的。广告不仅向大众宣传,而且广告直接作为大众向个人宣传。大众的市场本质保证了大众对个人的无意识权威,市场借广告之手以大众的名义把握并且控制了个人。在这种控制下,大众只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而个人则成为市场运转的一个中介或符号。当然,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只是一个市场的受骗者。或者说,这与商品交换中的智力高低无关。更实质的意义是,在现代社会,商品交换的普遍原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乃至于交换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市场不仅是提供商品的地方,而且是提供存在的地方——个体的存在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即形象的交换来实现。在根本的意义上,各种形式的晚会是最典型的形象交换市场。
在形象生产和交换中,当市场原则代替了民主原则的时候,技术就代替了人在操作——机械的自动化制作和复制。今天,大众传媒对当代生活的全面渗透,作为工具的信息技术变成了对于人的替代性主体——技术代替人成为形象的制作者和享受者。技术的本体化对于人的否定意义在于,不仅形象的制作,而且形象的享受都离不开技术,并且完全由技术的性能确定——比如音响设备之于音乐欣赏。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不是一些由于新技术的开发而出现的形象制作手段,如电脑动画;我们关注的是新技术正在进行的对传统创作手段的替代,如电脑写作,电脑制片。无疑,电脑是不具备原创力的,它必须能提供信息元素,提供操作程序。但是,制作者已经广泛地利用了电脑来代替自己的构思,并且获得了在一个平面上无限复制和改写形象的超额利润。新技术不创造形象,但是它制作形象,也就是说,机械的非理性把形象转化成为无限增生的物质产品。当我们感到被形象普遍地包围着的时候,首先是因为大众传媒的新技术在操作。面对大众传媒的成批量的过剩形象生产,自我个体即不能拒绝、也不能选择。形象的物化力量,是在新技术对形象的全面操作中形成的。新技术在对形象的无限增生性制作中,使形象达到了抽象的极限,转化成为纯粹的直观景象,并制作了纯粹技术的辉煌效果,构成了一个纯粹“为了被看的世界”。因此可以说,泛审美意识是新技术的胜利,在这种胜利中,我们看到,大众本身就是由大众传媒的新技术制作的一个幻影。就此,电视的本质(如果电视有本质)就应当理解为关于这个幻影的无情节(即无发展)的连续剧,它向个人展示一个关于大众的无意识幻梦。
在当代形象游戏中,个体对大众的无意识幻想是以他的自我形象的欲望为目的的,而对大众形象的欲望,是基于自我意识的根本性危机的。这种危机感使个体对大众形象怀抱着一种本能的期待和依赖。但是,大众不能为个体提供保证,因为大众只是无名的个人的虚幻的聚合,它本身也是无名的。个人在对大众的本能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依赖中,并不能摆脱自我危机的压力。对于个人,在大众中的生存是一种焦虑的存在,他在彻底的依赖性中感到极端的孤立性,或者说,大众对于个人是无可把握的,正因为必须依靠自己无可把握的大众,个人在大众中感到了自己的孤独或处于危机中的独立性。明星就在这种危机感中被制造出来。明星是以大众的名义被制造的个性形象,它处于大众与个人之间,作为中介,它是大众和个人的双重保证。一方面,它是被大众“认可”的形象,从而赋与崇拜者以大众的确证;另一方面它是关于个性或个人的形象,从而消除了大众的无名的虚无。明星的意义就是,在成为个体自我幻象的同时为大众命名。但是,由于名星的被包装性,即名星作为一个形象是大于承担这个形象的名星本人的,对明星的崇拜包涵着双重危险。一是名星本人的存在被形象替代,甚至粉碎的危险;二是崇拜者的自我彻底丧失,或被引入虚幻的形象癔症的疯狂追逐的危险。两种危险都将归入自我在形象崇拜中的丧失。而自我在形象中的丧失,由于商业主义的利润原则,由于技术本体化的物化力量,乃是形象游戏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当代形象的增生和物化形成了对个体存在的替代,那么,这种替代是在当代形象的最后生成中,即在明显崇拜中完成的。
明星崇拜把形象游戏实现为当代生存的神话仪式,明星就是这个神话仪式的神学主体。那种保护当代人,而把形象的危险转化为形象的慰藉的力量,是仪式的力量。在形象游戏中,当代人抛弃了古典仪式的膜拜内容,却保留了膜拜的形式。然而,仪式的真正意义恰恰是存在于形式中的。正是游戏的仪式性,提供给了当代人一种整体性的庇护,并且使他在片断中产生完整性的幻象。当代游戏仪式是以晚会为基本形式的。与古典仪式相对,晚会给人以自由、随意、尽兴之感。但是,最随意的晚会,也包涵着特有的规则和形式。晚会作为当代游戏,其根本意义不在于规则的有无,而在于它把古典的单向膜拜用双向式参与的形式来实现。膜拜者同时也是被膜拜者,在其中,形象的意义就是被膜拜的意义——因此形象本身是无意义的。现代晚会是化装舞会的变种,而化装舞会在煞有介事的形象表演中所追求的只是参与这个形式本身。游戏的绝对原则在游戏的仪式中体现了,可以说,游戏仪式所保护的就是游戏的绝对原则,而作为游戏者的个体,只是为了这个原则被保护,他所获得的慰藉,是自我和游戏直接认同的自以为是的假想。在假想的慰藉的必要性的意义上,当代人对形象的欲望是归结于对仪式的欲望的。仪式用吞没个体的形式保证了个体,形象的异化力量和形象对于人的可能和慰藉,都在仪式的吞没的保护的二重性中被解释。这也是晚会对于当代生存的绝对意义所在。流行艺术就是一种晚会艺术,一种仪式艺术。摇滚音乐的魔力应归解释为这种晚会仪式的魔力,它所煽起的类宗教狂热,是在歌手与歌迷的双向式参与的音乐晚会仪式中形成的,而盒带和音碟的巨额畅销,不过是对这个仪式的延时反应。形象游戏是在游戏的仪式中完成的,形象归于这个仪式,因为它本身就属于这个仪式,因此,形象是无忧无虑的。但是,人类个体再次成为一个弃儿——如果他侥幸没有被吞没。所谓慰藉,不过是投入下次遗弃的诱惑。
四、反批判时代的批判的可能:突破形象与开放游戏
把当代文化指认为审美文化,就已经承认了一个反批判时代的文化前提。因为,在泛审美意识的普遍渗透中,对形象的欲望已经成为当代个体的存在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包涵着把一切对象转化为纯粹形象的非理性冲动。正是这种非理性冲动,封闭了当代文化的形象游戏,并且预定性地拒斥一切批判。形象,并且只是形象,在当代游戏的无意义的纯洁性中被伪审美主义的虚幻的审美理想做了免疫保护,也就是说,抽象的审美化原则把形象铸造成同样抽象的审美民主的建筑材料。
但是,形象并没有成为坚不可入的阿喀琉斯之盾。在当代文化中,形象所抗拒的只是柏拉图式的元形象批判。这种批判基于形而上学的实质主义观念认为,形象只是事物(物体)的影子,因此是虚幻可疑的。实质主义已经被近代哲学的怀疑主义所动摇,因为除了通过形象(现象),人类是不可能认识世界的。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形象批判,应当是一种非相拉图主义元形象观念的批判。因为元形象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是不具有可批判性的。新的批判,应当基于当代形象的生成(或构成)性,在形象生成的运动力学中来阐释形象的结构力学。这种批判,可以称为对形象的生成本体论的批判,它是超越于形象之外的,也就是说,它在对当代人存在的现实和可能的整体性审视中来反观形象的活动。面对这种批判,形象的拒斥力量就化解了,而被必然性地溶入批判所引入的存在之流。
对形象或形象游戏的批判必须达到对现实的批判。形象的物化力量根本上是对理实的物化力量为基础的。现实的物化力量来自于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意义。现代化对技术扩张和财富增殖的无限要求在极大限度为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现实前提的同时,包含着对人的自我关怀和自我肯定的消解和否定,因为它所包含的普遍交换原则和技术优先原则,在削平一切价值的同时,也必然包含着对人自身的价值的削平。这就是现代化运动所包含的普遍的物化力量。当代生存的悖论情态就是这种普遍的物化力量意识形态作用,而当代形象游戏在文化层面上展现了这种力量。
批判不是别的一种活动,它是形象的突破和游戏的开放,是被落空的审美精神的批判性重申——因为审美精神在根本上就是一种现实的批判力量,而泛审美意识的形象游戏所放弃地正是审美精神的现实批判力量——形象游戏用一种表演的否定(纯粹形象的否定)与现实同行一道,并且遮蔽了现实。对形象的生成现实的批判,就是要深入对这种现实的物化力量的揭示和批判之维,从而解放被异化和束缚在形象中的人的主体力量和自我意义,使对形象的游戏在同现实的深刻关联中达到人自我表现的意义整体。因此,对形象的批判不是否定形象的意义,而是相反强调形象的意义——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指认形象是有意义的;也可以说,通过批判,不是抛弃形象,而是保护并且发展形象,使之在意义整体的表现中达到自身内在的完满性。批判的结论是关于形象的诗意的结论,也就是审美精神真正确立在形象游戏中的结论——作为一种存在,形象的游戏是关于人的,并且必然是人的。这个结论超越了当代悖论对人的纯粹喜剧的游戏意义,它重新启示了一种存在的悲剧意义。在这种悲剧意义中,悖论不是结论,而是创造的起点,确定无疑的是,在与自然的世界性统一中,人因此是必然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