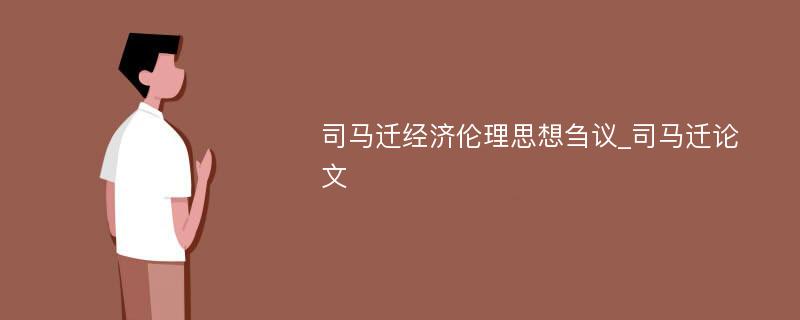
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司马迁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汉代以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重农轻商的儒家经济伦理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最终被确立为正统思想,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与此相对应的是,民间经济伦理、商业伦理则被视为异端,备受轻视和限制,其生存和发展步履艰难,历尽坎坷。尽管如此,民间经济伦理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渗透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关的记载也不绝于史书,它们闪耀着我国民众的智慧之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不仅开创了史学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而且堪称反映当时民间经济伦理的代表作,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支奇葩。挖掘和发扬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司马迁的经济伦理观是建立在其人性自利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
应该看到,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儒家思想虽然已经开始确立其官方正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对时人的影响并不那么深刻,百家争鸣的遗风犹存。因此,在司马迁的思想源渊中,既接受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推崇诗书礼义,又崇尚道家的无为和法家的功利思想,具有融合儒、道、法三家思想的特点。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司马迁深受黄老学派和荀子的影响,认为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好利求富。他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百姓,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其目的都是逐利求富,“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骞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推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同上)这段议论是奔放而深刻的。抑制人们的物质欲望,要求人们安分守己、安贫乐道,是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学说的一贯主张。司马迁视这种主张为虚伪的说教,充分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从普遍人性的高度加以论证,为普通百姓的求富行为寻求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在司马迁这里,追逐富利的行为是直接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人性自利论也不只是单纯的哲学人性论,而是作为一种经济伦理思想贯注到了人的行为中。因而,不可将其与一般的人性论等同视之。
人们追逐富利的天性不仅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杠杆和动力,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司马迁考察“古今之变”得出的结论。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社会上农、虞、工、商的形成和发展,人们各自勤勉其业,并非圣人实行政治道德教化所使然,而是由人的自利的天性所推动和驱使的,即“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是一种“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史记·货殖列传》)
既然趋利逐富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么,应该怎样对待人们的这种自利行为?如何把人的自然本性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呢?司马迁提出了“善者因之”的经济伦理观。他指出:“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按照司马迁的逻辑,既然趋利逐富是“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的自然本性,那么,人的自利行为也就不是恶的,相反,它还应被视为社会经济、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有力的动力机制。因此,司马迁从自利的人性论出发,必然得出“善者因之”的经济伦理观。他的基本主张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使之各任其能,竭其力,人们就会各得所欲,民富而国强,这种放任自由的办法,是最聪明,也是最好的办法;其次是因势利导,进行教育,而加以人为的压抑、限制,并与民争利,损害人民的利益,则是最不可取的,必然导致人民怨声载道,社会动荡,历史倒退。他还批评了輓近之世的做法,认为“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同上)激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与民争利的禁榷制度。
可以看出,司马迁在人性自利论基础上提出的“善者因之”的经济伦理观,具有许多合理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在我国古代的伦理学说中,达到了对历史发展动力的最深刻的了解,充分意识到了利欲、个人利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二
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一个根本问题。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经济与道德的关系是头足倒置的,不是经济决定着道德,而是道德准则决定和制约着经济,它坚持以伦理道德准则来规范人们的经济生活,倡导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思来者”而为现实服务的气魄,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颇具叛逆色彩的观点。他认为,物质财富、经济状况与国家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社会的道德状况、风尚习俗也有极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可以做到致富成仁。
首先,在社会变革时期,经济财富的作用远比道德教化的作用强大。司马迁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兼并的时代,人们“贵诈力而贱仁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仅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国民财富的状况直接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前途,其作用非道德教化所能比拟。齐国在齐桓公时期的强盛和秦后来统一六国,主要是依赖其经济优势,而非道德教化。“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史记·平准书》)也就是说,通过发展生产而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是齐、魏国力强大的基础。同样,对于秦统一六国,人们多是从政治上的合纵连横考察,司马迁则指出其深刻的经济原因: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移风易俗,兴修水利,使关中成为沃野,民富国强,所以,“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其次,经济状况、地理环境对道德状况、习俗风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司马迁曾游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对各地的风俗人情有广泛的了解。《史记·货殖列传》中,他列数各地风俗民情的特点和差异,认为这些特点和差异的形成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任何政治的和道德的教化都难以使其改变。
他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贷物而多贾,……孝、照治咸阳,固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未也。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刃事。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为什么关中地区民益玩巧而事末?为什么三河地区民俗纤俭?为什么齐地民俗宽缓阔达且足智多贾?为什么好儒备礼的邹、鲁后亦转而趋利好贾?司马迁都从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予以分析和回答。这种分析和回答是建立在一种经验性的观察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十分深刻的观察,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经济发展状况与道德风尚之间的内在联系。
再次,致富可以成仁。也就是说,道德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是能够一致的。司马迁非常赞同管仲对经济与道德关系的看法,完全接受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命题。在他看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是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就好比“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阐明了,经济财富决定着人们的道德观念,是道德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史记·货殖列传》中,他还列举了诸如范蠡、卜式等“富而好行其德”的楷模。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第。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三
自古以来,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财富这个轴心旋转的,关于财富的道德观念自然也构成了经济伦理的主要方面。把财富与道德(利与义)对立起来,视财富如祸水,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也提出了一些“颇谬于圣人”的观点,他重视社会的经济活动,关切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财富状况,热烈地赞美财富。
西汉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物质财富骤增,并随之产生了一些富贾大户,他们富比封君,奢侈逾制。对此,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如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极为忧虑,依据其等级制的道德观念加以谴责。司马迁却不以为然,他虽然也倡导礼义,但更崇尚货殖,赞美财富。他反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认为“素封”是令人羡慕的,更是值得称道的。他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三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傜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姿所好美矣。”(《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激烈抨击了安贫乐道、甘于贫贱的生活态度,认为“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渐耻,则无所比矣”。而且,即使是“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同上)对于司马迁的这一思想,班固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应该承认,班固的指责把握住了司马迁思想的基本特征,只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却不是其蔽,恰恰是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的独到之处和精华。它表达了汉初社会变革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对当时民间经济伦理的反映。
肯定工商货殖致富是正当的行为,提倡竞争致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工商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民富裕的作用和意义。他认为,“富无经业”,农、虞、工、商,四者皆为民众的衣食之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商业的发展使得“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因此,治国之道必须“本”“末”并重,他说:“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致富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富总比贫好,但是,致富亦需要才智和方术。工商“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推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白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史记·太史公自序》)由此看来,“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肯定了人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竞争致富的合理性,这一思想在今天也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重农轻商、崇本抑末,是战国至西汉的传统思想,也是两千多年来我国的文化传统。受此影响,工商业者被视为逐利的小人,历来遭受贬斥。据《史记·平准书》载:“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这里的“困”和“辱”,实际上表明封建国家和正统思想对于商人的态度。司马迁则对工商业者深表同情,并为他们辩护。他以鸟氏倮、寡妇清为例指出:“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抗礼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史记·货殖列传》)拥有财富的工商业者不仅可以与王者同乐,而且同样受到了人们的尊重、礼敬。司马迁还为先秦至汉初的一大批工商业者树碑立传,总结他们致富的经验谋略。这些经营之术包括:运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策略,不失时机地利用行情来吞吐商品;“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加速资本周转;“务完物”,讲求商品质量;赢利适度,“无敢居贵”;节约个人消费,“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经营者应具备“智、仁、勇、强”等方面的素质,等等。在司马迁看来,应把大商人同大政治家、军事家等同视之,认为治生之道亦需要智谋权变,犹如政治家治国、军事家用兵。
值得指出的是,司马迁在赞美财富,肯定富比贫好的同时,对致富的方式和途径也作了阐述,提出了对人们致富的方式和途径进行道德约束和道德评价的观点。根据孔子致富须“以其道得之”的思想,司马迁也强调生财、聚财应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不应贪求不义之财,以防止单纯追利逐富的危害性。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感慨:“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防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因此,“以礼义防于利”,这是人们追利逐富时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对于人们致富的方式、手段,司马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所谓“本富”就是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末富”则是指通过工商业活动致富,而依靠诸如盗掘坟墓、拦路抢劫、私铸钱币、私刻假印及贪污受贿、欺行霸市等卑劣手段发财致富,是属“奸富”。在司马迁看来,“奸富”最下,最终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本富”和“末富”是应该肯定的。但他还是以“本富”为上,所谓要“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表现出他在“本”“末”问题上的思想局限性。
有的学者曾论证指出,我国古代民间商业伦理内在地催育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而且与现代商业理性精神具有机理会通性格。司马迁的经济伦理思想作为一家之言,虽然不可能包纳民间商业伦理的全部内容,但也颇具代表性。他所推崇和信奉的追求富利、放任自由、本末并重、致富成仁、以义取利等价值观念,都符合经济生活运行的客观规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