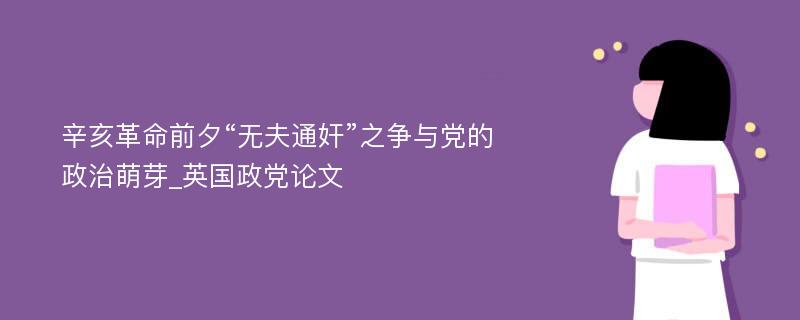
辛亥前夕的“无夫奸”论争与政党政治萌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萌芽论文,政治论文,无夫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9-0106-10
晚清最后十年的修律事业带有“意在法外”的时代特质,主要回应靠拢西法和收回治外法权①的朝野共同诉求,导致中西法律思想和制度的全面转型,直接牵动背后的礼教观念和思想基础,因此相关争议持续不断。比如删改亲属容隐、存留养亲、干名犯义和十恶等传统法律的规定,特别是“无夫奸”(孀妇或处女与人和奸)等条文是否进入新律,以及以何种方式进入,更成为新旧双方争持的焦点,即所谓的“礼法之争”。以往的研究多从法制史的视野对其加以论述,②实则“无夫奸”争议与清季政党政治的发生关系密切。③“无夫奸”本是无足轻重的法律议题,且不具实践性,但经过报刊传媒的推波助澜以及对西方消息的无知想象,“无夫奸”被赋予采用西法和收回治外法权的象征意义,后更因各方政治势力有意无意间的操作,使之成为区分政党的标准,西式政党最终瓜熟蒂落,得以结成,颇能揭示出辛亥前夕舆论注重外交和趋新的时代风向,以及西方政党政治落地中国的原生态与复杂性。
一、“无夫奸”背后的“主义”之辩
认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启动的修律事业,不能脱离庚子以后收回治外法权的时代语境。四月初六日朝廷发布修律上谕,明显受到商约谈判关于法权问题讨论的影响。传媒亦注意到:“虽修定呈览,候旨颁行尚须时日,不能就现在改订商约之际收回治外法权,然而蓄艾以治病,今日之改订律法,即可为他日挽回张本。”④初时删除重法、改订旧例尚算一帆风顺,众论翕然;当进展到预备立宪、制订立宪刑法典的阶段,朝野各方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起草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几乎全依西法,军机大臣张之洞认为违背礼教,以学部名义弹劾,并引起众多部院督抚群起反对新法案。后经刑部司员吉同钧主持修订,在不变动正文的前提下,别创附则五条,规定“十恶、亲属容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以及亲属相奸、相盗、相殴并发塚、犯奸各条”因为“关于伦纪礼教”,中国人“应仍照旧律办法,另缉单行法,以昭惩创”。⑤此草案后交宪政编查馆审议,遭到参议劳乃宣的反对,要求把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修入正文。他认为,新刑律主要为立宪时代的国人而设,如此重要的条文不宜列于附则,且不会妨碍收回治外法权的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劳氏并不完全反对新刑律草案,“新刑律中保存家法之处甚多,特尚未能尽善耳”。而其要求增加或修改者仅六条: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亲属相奸、亲属相殴、犯奸和子孙违犯教令;所增改的条文也按照新律“主于简括,每条兼举数刑以求适合之审判”的体例增入,而亲属“等差应依据旧律逐加分别,于另辑判决例内详之”。可见其对法律中的礼教问题有其缜密思考,并不主张全盘推翻新律。
稍后修律大臣沈家本撰文回应,部分承认了劳乃宣意见的合理性,包括干名犯义、亲属相奸、亲属相殴等条,只是主张用制订判决录(例)的方法去解决,即不修入草案正文,以案例办法临时解决。这样既可避免外人的指责,达致收回治外法权的目的,同时又可以维持礼教,可谓一举两得。劳氏也同意此办法,但是对于删除无夫和奸有罪等条文仍感不满,最终相持不下。背后则牵涉两个根本性的修律议题而无法让步:其一,法律与礼教的关系如何,传统的礼教因素应否被排除在公布的法制之外,就像“无夫奸”有罪只见于案例,而不列入新刑律正文一样;其二,中律条文若没有西法的呼应,如西法没有类似“无夫奸”条文,可否有独存的价值,是否有必要一律改同西法,以作为收回治外法权的代价。为此,劳乃宣与馆中杨度、吴廷燮、汪荣宝等人颇多辩论。
宪政编查馆乃是清末推行新政的中枢,政治作用极为重要,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传媒的关注。劳氏的主张从一开始就被京师多数传媒视做保守之举。上海《神州日报》的“京函”指出:“京各报记者对于此案皆诋劳而助杨,以《帝国日报》为尤力。其两袒者惟《北京日报》,中立不赞一词者惟《中国报》。《北京日报》为政府机关无论矣。《中国报》记者则谓于法律素乏研究,兹事体大,不敢盲从,是非自有定论,黑白终无久淆。此数语虽似模棱,尚有见地。”[1]其中《帝国日报》办报方针颇为激进,既以革命党人宁调元为总编辑,周震鳞为记者,又与立宪派领袖杨度关系密切。据御史胡思敬奏参,《帝国日报》之前身《中央大同日报》为杨度所经营,主笔陆鸿逵也为湖南人(留日学生),而两广总督袁树勋“投赀本其中,藉以掩盖赃私,诛锄异己,俗所谓机关报者是也”。[2]此外,不少传媒支持杨度,是从西方优越的思维定势出发的。如《时报》的作者“天池”虽然“无由得知”新刑律的内容,却能从“劳乃宣之所訾为过宽者思之”,“想亦与各国大同小异”,与旧律残酷之法不同。“今日既欲跻为法治国,则不得不改习惯,屈道德而伸法律。此迨近于偏宕之言,然亦实鉴于时势之必要,不得不如此者也”,否则就无法收回领事裁判权。[3]从其“不得不”的语气不难看出,“天池”其实并不太反对原有的道德,只是为“时势”所迫,才根据尊西趋新的思路去判断像新刑律这类并不熟悉的法律问题。
其事后交由馆中枢臣决定,将“无夫奸”列作新刑律的暂行章程第四条,并作为议案交资政院审议,为论争提供了更开放且引人注目的平台。杨度受宪政馆的委派,到资政院解释新刑律案之“主旨”,却别出心裁地阐释“新刑律与旧刑律精神上、主义上之分别”:“现在国家改定法制,总以国家主义为宗旨,既然以国家主义为宗旨,则必要使全国的孝子慈父、贤兄悌弟都变为忠臣。……但要使孝子慈父、贤兄悌弟都变为忠臣,不可不使他的家人都有独立之生计与独立之能力,既然要他有独立之生计、独立之能力,国家就不能不与他以营业、居处、言论等等之自由,使其对于国家担负责任。……此二主义是相冲突的,不是相连合的。……亦即新刑律、旧刑律根本上之区别所在也。”[4]言下之意,一向被视为人生温暖港湾的家庭(家族)要为国弱民穷负责,新法制需要破除家庭(家族)的桎梏,使个人直接对国家负责,国家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支援,其实正反映近代以来公权力向私领域的侵蚀之势。教孝、保家本是官方标准的意识形态,身为政府特派员的杨度居然在资政院公开反对,确实令我们对于晚清朝野互渗的多歧性有了更多的认识。
杨度的演说过程与演词内容被传媒广泛报导。不少报刊如《北京日报》、《帝国日报》、《申报》和《法政浅说报》都登载了演词全文,其他报刊也多有摘要刊登。其内容更是得到众多的好评,具有日本背景的《顺天时报》称,“议长与特派员以及全体议员百数十人皆肃静无声,以共听杨君之雄论,拍掌之声更番造起。议场中一种欢怡景象,实为开院以来所未有之大特色”;反观其后劳乃宣等人的辩驳,却是“毫无价值”。[5]此前吴廷燮与劳乃宣等人所争持的是“无夫奸”等具体法律问题,讨论未免枝节,加上后者似旧还新的立场,两者比较之下就显得有些纠葛不清。此时杨度首次将法律问题上升到“主义”之争,不再纠缠于具体问题的讨论,而把问题直指中国传统礼教,更能激发传媒原有的西方优越的潜意识,收获到更多的舆论同情。
二、外力内化:对于西方消息的想象
庚子以后西方在华的影响力日益深入,不止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有形压力,甚至得自西方的片言只语都可引起时局的变化。《帝国日报》注意到,“新刑律提交资政院以来,外人视为中国一绝大问题,数日之间电报络绎不绝”。⑥同日《国民日报》也报道了“外人注目新刑律”的消息,认为“撤退领事裁判权在此一举”。该报并揭载所接到的“英京友人专电报告”:“中国资政院提议新刑律问题,英国各大报均得有北京专员之电告,一时哄动全欧社会,均集视线于此问题。其国中舆论皆谓中国刑法向守残酷主义,今新刑律纯以崭新之学说编定而成,可知其所注重者在于撤退各国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本系为对待野蛮国主义。今中国果能改良法律,吾英人亦不惜以全力协助之云云。并闻各国政府已纷纷电致各该公使,询问新刑律之内容若何,及能否通过。”报道者甚至进一步解读,各国之所以如此“关切”,就是因为“各国将以刑律之能否通过决将来放弃(领事裁判权)与否之从违”。[6]稍后数日该报告也出现在《申报》、《民立报》和《盛京时报》上。[7]
当时报纸的编者和读者重在阅读新闻,而非时事评论,⑦尤其对于这条来自西方中心伦敦的消息,重视有加,并多有引申和想象之处。笔者检阅当年该时段的《泰晤士报》,只有两则关于中国法律改革的报道。一则是9月22日,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徐谦在伦敦仲裁法院举办的午餐会上发表演说,讲述中国改良监狱、修改刑法和商法的进展;另一则是12月17日,赞扬中国在改良监狱方面的进步。[8]即便其他英报有论及取消领事裁判权的相关报道,能否达到所谓“英报无日不议论此事”、“一时哄动全欧社会”的景象,似乎不无疑问。退一步而言,即便欧洲的传媒报道是真的,列强政府也不会轻易放弃领事裁判权。西方虽然一直关注中国的修律进展,但是不大满意。以英国驻华公使馆对于1910年中国实施宪政的评价报告为例。该份报告已经注意到新刑律草案由资政院审议,并由朝廷正式颁布;但是却质疑实施的成效,“法律改革已经制定出很多重要的纸上条文,但它们是否真的有助于改善司法审判的情况却很令人怀疑”;省会和商埠审判厅的建立,加剧了外国领事和地方官员的冲突。报告虽然肯定清廷实施司法独立的努力,认为这会缩短中国收回法权的时间,“然而没有人能够伪称我们距离那个时间并不遥远,或者过去一年中沿此方向有任何实质的进步”。[9]
然而,未悉内情的国内传媒却根据这条伦敦消息,对收回治外法权寄托了过高的期望。《帝国日报》“时评”的论调因此变得激烈,认为“此次新刑律法案之会议通过与否,实吾民生死关头,即吾民四万万生命托于二百议员之手矣”。因为此事关乎法权,“刑律不改良,领事裁判权万不能收回,议员苟反对新刑律,是又以个人私意,实行断送国权也”。该文甚至还威胁,若议员持“乡曲陋见”加以反对,“吾民即当设法取消其代表资格”。[10]后来果然组织团体,实践如其言。数日后,《帝国日报》又为此事发表“社说”,并特别注意外人的态度。“各国新闻记者争欲探视其内容。而《伦敦时报》至谓中国律例果能改良,英国有履行条约之义务”,可见“各国皆注意此次之新刑律矣”。因此将新刑律放在国家存亡的高度上加以看待,“此次刑律能否通过,将来国家存亡系之”,“使改良刑律之目的不能达,致国家从此永不能称完全,且或因是以归于灭亡”。[11]
立宪派主持的《宪志日刊》则藉此批评议员反对新刑律为不爱国:“今乃享有领事裁判权之利者,闻我有新刑律之订,无不代为欣喜,深愿此案之通过。英人之言至欲协力以助我,而实受领事裁判之祸者,反死力反对,惟恐此案之成立。呜呼,抑何我学士大夫谋国之忠,曾不外人若也!”[12]就在几天前,该报还特别引用了议场中某“西友”之言:“资政院议员中,赞成新律者固有其人,然当反对派发言时,鼓掌者亦不少,吾恐其卒无成也”,要求议员想清楚再鼓掌,“四万万人之生死从违,实决于我两掌之一鼓”。[13]作者似乎已把这位“西友”当做是全体西人的代表,而西人又决定了“四万万人之生死从违”,这样无限放大西人言论的威力,大致反映出当时思想话之语权已在西人一边。
连在上海一向立论稳健的商业报纸《申报》“时评”也激动起来,“新刑律方在资政院讨论耳,而外人舆论已惊天动地如此,设竟实行,不知其影响于国际上者更何如也!”外人注目新刑律,“亦惊中国断行轻典之决心,而喜一扫从前惨酷无人理之旧习耳”。由此反观“硕学通儒”中的反对者(暗指劳乃宣),可谓“不仁亦甚矣”。[14]其后的“时评”又认为,新刑律案的争论其实是“主权”和“亲权”之争,“欲主权则不可不减削其亲权,以希冀其挽救之一日;有亲权则无日可希望其主权,而外人裁判权永永恭让,莫可如何”,“此固不必齗齗争辩也,但熟审其利害之大小焉斯可矣”。[15]
康梁一派的《时报》也针对此事发表《论新刑律》一文,指出“外人之注重此事”,“欧洲各报无日不议论,有谓中国刑法向主残酷主义,今改用新律,志在收回领事裁判权,如果实能改良,我英国当先撤去领事裁判权,以为诸国倡。又有谓资政院议员程度不足者多,恐难通过,各国政府宜审慎从事。”因此“他日之能否收回领事裁判权,又在乎此举”。[16]同样以欧洲关注新刑律的消息为收回法权辩护。
各报之所以会如此兴奋,其实表明他们本来就相信劳乃宣等人所提出的劝告,即修律未必就能收回法权,还需要本身的国力和兵力去支援;只是默认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目标始终会达成。现在欧洲居然传来列强肯主动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消息,难怪他们会欣喜若狂。而传媒舆论对于西人消息之敏感及赋予丰富的想象,正反映出西方在中国权势结构中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足以影响国内舆论的走向。
三、成立团体:新律维持会之干预
既然认为西人“重视”新刑律,传媒开始将之视做关系立宪成败的重要关键。与此同时,由于有了“主义”之争的认识,新派舆论多以劳乃宣修正数条,即是反对新刑律全体。署名“隐讨”的作者投稿《帝国日报》,认为新刑律“主旨正确,计划详密,条文简要,精神统贯,万万无可搀杂之处”,“劳乃宣而敢主张废弃也则已,而曰保存礼教,真是海外大奇谭”。又谓“劳乃宣欲支支节节而为之,非惟不知法律,并且不知礼教。其所知者,但有章句而已,吃饭而已”。显然,作者厌恶的是折衷调和的改革思路,“从前之学务计划,近年之筹备宪政事宜,种种秕谬,至今为梗,何莫非劳乃宣辈自雄予智,强作解人之戾,今更欲为害于大清新刑律,孔子所以恶乡愿者在此!”[17]
虽在日本却能领导舆论潮流的梁启超也承认,劳乃宣将旧律的思想羼入新刑律有误。“新刑律者,一种之法典也。法典与单行法异,全部皆为有系统的组织互相联属,若欲以门外汉而妄改其中一二条,此犹以不知画理之人而欲强画师惨淡经营之画幅,令其改削一水一石,必至全幅不复成片段而已。”[18]晚清以来风行一时的“中体西用”语境氛围,到辛亥前夕似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双方相持不下,只能在资政院议员中争取支持者,以图将来的表决优势,孰料由此走出了一条组党之路。被舆论视做守旧的劳乃宣似乎先走一步,以宴请为名,聚合议员同志。有传媒批评为“酒食征逐”和“酒食响应”。[19]其实劳氏的宴客之举,在西方不过是议员间联络公关的常见之事。就如汪康年所言,“今世发明之新法,凡议员以酒食招集人而运动之,乃为普通应然之事,则各报之对于劳君应责其吝酒食之费,不应诮其以此为运动之资也”。[20]揭示出新派传媒除了党同伐异的心态外,可能对西方议会政治的运作方式不甚了然,才会以鄙视酒食贿赂的传统思路待之。
《民立报》则注意到:“劳即邀是日会场为之赞同者小饮聚谈,如湖北陶峻、四川万慎、江西闵荷生皆在其列。一时众论哗然,翌日外间即有所谓新律维持会者发现,扰攘数日。其实新刑律之主义专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而设,与国内政治、教育本并行相辅,并非除刑律外无他法令也。劳固一迂曲之士,无纤毫世界观念,而维持会亦不知资政院提出之本意,视为一种政党竞争之事,皆可谓庸人自扰。”[21]该报因为革命的立场,不大注重新刑律问题,甚至冷嘲热讽,不过正可跳出立宪派内部相争的局限,提供了第三方观察到的历史情况:“政党竞争”的苗头已然出现。
所谓“新律维持会”之成立,最早见于《京津时报》的报道:“都中政学界志士”为防止“顽固卑陋、无法律知识之议员挟持私意,运动反对,致不能通过”,决定创立新律维持会。签名之发起人不但有《帝国日报》记者周震鳞,而且还有钱维骥、张嘉森(君劢)、张嘉璈等康梁门人。[22]另据《时报》消息,新律维持会实际上是周震鳞和陈佐清发起的。[23]据周震鳞在1950年的忆述,他在庚子年参与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后加入同盟会,宣统年间在京与吴禄贞等人“专力联络布置北方各省实力”。其担任《帝国日报》编辑,乃是应主编陆鸿逵之邀;自举荐宁调元入报后,只是“星期暇日作社论、短评而已”。[24]该回忆竟忽略不提创建新律维持会一事,不难推知其事与周氏自我定位的革命者形象不甚合拍,当中提示出的历史信息值得重视。另一发起人陈佐清为《神州日报》记者,[25]在宣统元年正月,与黎宗岳等人号召各省发起国会期成会。[26]两位发起人皆身在传媒,但各有政治背景和立场,可见此会发起之临时性。
综合各家传媒消息,新律维持会初十日开会,到者300余人,会议由周震鳞、陈佐清和钱维骥等人主持。周氏说明“新刑律在实行立宪时代对外对内之必要,所以吾辈对于反对新刑律草案者不可不极力设法取消其阻力”。钱维骥则“演说礼教不可牵入法律范围,驳倒劳乃宣所据之意见”。[27]最后由陈佐清说明“迅速维持之办法”,请会员自愿“直接往晤资政院各议员谈判”,谈判结果无论赞成与否,“皆随时函达各报登载”。当时自愿签名者约有40人之谱。十三日又再行开会,商议具体事宜。“决定将反对较力者先向质问,当即配定五股,随分配随起行,颇有秩序”,对于“反对新律议员之最著名者,则由周君震麟[鳞]、陈君佐清等于十五日前往质问,必使反对者词穷理屈始已”。[28]由此发端,开启了院外势力干涉资政院议员言行的系列进程。
当十五日资政院部分议员在全蜀会馆商讨新刑律案,周震鳞和陈佐清“特蒞会与各议员直接谈判”。议员刘景烈报告汪荣宝主持的法典股审查结果,主张删除被视做旧律残余的暂行章程,引起了陈树楷、高凌霄等议员的反驳。在会议结束之后,周震鳞对陈树楷、陈佐清对高凌霄进行了一对一的劝说。《帝国日报》消息指:“周君将陈疑难之处一一解释,陈本精通法理者,立时省悟,并谓高议员凌霄肆口发言,殊多不合,即劳乃宣之说亦甚不当。”但是高凌霄与陈佐清“反复辩论,约有两时之久,高始恍然。是时周君震麟[鳞]与各议员谈判已毕,见陈、高二君尚在争执,复大声峻驳高之误点。陈谓伊疑窦现已尽释”。高凌霄最后也表示“决不反对”。[29]逼迫之情已跃然纸上。两日后,资政院议员在财政学堂再次商讨新刑律案,“议员到者约六十人,旁听者约七八十人”,高凌霄、万慎等议员仍出言反对法典股的修改意见。[30]新律维持会成员不但在旁听时故作噪声,而且在会后与高凌霄、万慎等人发生肢体冲突,彼此互控对方殴人。当时大多数的报章都指责议员殴人,但相信这并非实情。议员胡骏对于新刑律并无固定立场,亦与论争双方瓜葛不深。其日记显示,次日他到资政院开会时,见到高、万二人,方“知报章故意颠倒是非”,真相原来是周、陈二人被捕,外省议员也因此“辄抱不平”。胡骏因此感叹,“足见报馆之无价值,而报律不得不严。从前院中为报馆出力,转觉无谓”。⑧
有意思的是传媒如何报道这条新闻,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媒体生态。《帝国日报》报道,“高凌霄因附和劳乃宣、沈林一受嗤,恼羞成怒”,对周震鳞、陈佐清“肆口谩骂”,后又呼万慎前来,“围殴周君”。陈“大声质问高凌霄何以如此野蛮,高反诬周君欧[殴]人,周君更怒,遂由章君宗元呼巡警前来,并扭高凌霄、万慎同到内城右二区”。区官询问时,“忽有多数旁听人前来作证,证实高凌霄、万慎殴人”。最后区官“叫车将高、万二人送总厅”。[31]周震鳞身为《帝国日报》中人,将此事报道成议员殴人的事件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同日发表的《京津时报》和《北京日报》报道该事的内容文字,竟与《帝国日报》几乎完全相同(除了标题和副标题)。[32]十九日的《顺天时报》、[33]二十六日的《申报》[34]和二十八日的《时报》[35]也刊登了同样的内容。十九日的《大公报》也是根据该篇报道略作删减而成的。[36]可知各报在私底下应该有沟通的管道,而且彼此立场接近,才会达成默契,形成众口铄金的效果。
直到二十二日,似为铁幕一般的传媒界才透出一缕亮光。《国民公报》以“议员来函”的方式,稍为透露真情。该来函称:“前日开会时情形与散会后冲突之事,当日曾经目睹”,“先是旁听席中有嗤叱之声,高起喝之。迨散会时虽有二人扭高,欲行殴打。经万慎告知本堂监督章君。章因呼巡警将殴人者送厅,高遂归寓云。将高、万送厅者,实系传闻之误。”[37]但到二十四日,该报又刊登周震鳞的启事,指二十二日所刊“实于情形不合,请为更正”。[38]新派试图掌控传媒舆论的意志由此可见一斑。
《刍言报》的汪康年对于议员斗殴之事颇有质疑,直指各报“最为颠倒黑白”。汪氏考其原因,“以周震鳞为《帝国日报》主笔,《帝京新闻》本与相联,于报亦存同业相护之心。《国民公报》虽据函更正,而题目亦不敢显揭,后又登周辨正之函。”汪氏更直指,“新律维持会辄于资政院议新刑律之前一日,每议员处以二人往胁,令明日至资政院必须赞成新刑律,否则不相宽假”,不由感叹“国家大事而伊等乃敢以把持恫嚇行之”,传媒却不加过问,真“可怪孰甚”。[39]汪氏敢于报导真相,并指斥同业之思出其位,显见《刍言报》并不在传媒界的主流之中,经营困难也是意料之中。⑨
高、万殴人事件的影响持续,发展成召开大会驱逐议员的局面。熊煜、欧阳煦等人,以“川省同乡”名义,开会对付“玷污全省名誉”的高凌霄。其公启指高凌霄“所主张之议论,与原始时代人民之口吻无异,不惟不知领事裁判权之必待改正条约而后撤去,且不知新律上原则、例外之用语”。“该议员荒谬绝伦,惟存一自己之目的,始而反对新刑律,继而诬人殴打,大为吾蜀之羞”,因此开会“质问该议员,并筹保吾蜀名誉之方法”。[40]
《京津时报》记者在报道开会详情之后,加上按语称:“新刑律已为一般心理所欢迎,倡议反对最为不名誉,川人之对待实亦当然之结果,深愿议员诸君各自宝贵其人格,而勿步其覆辙也。”[41]此语不无恐吓议员的意味,新刑律草案俨然变成不可修正之定案。部分议员在此气氛下,也不得不向传媒表明态度。《帝国日报》报道,湖南和浙江两省议员较支持新刑律,“湖南籍议员除黎尚雯、易宗夔、罗杰、席绶赞成最力外,闻曾侯爵(指曾国藩之孙曾广銮)并主张将暂行章程五条一概取销,免与新刑律主旨冲突。外有反对者一二人,闻湘人已预筹对付之法。浙江议员亦多半是赞成派,以邵羲、王廷扬、余镜清诸君为最著。”[42]“直隶议员如李榘、刘春霖、胡家祺诸君,均力主从新,而李君搢荣则谓中国果欲实行立宪,则不能不步趋各文明国之通行刑律,以为收回领事裁判权之地,如劳乃宣、高凌霄辈所主持,实根本错误。鄙人决不与之表同情云。此外,奉天议员孙以芾、陈瀛洲、书铭、王玉泉,吉林议员庆山、徐穆如,黑龙江议员桂山,湖南议员李子爵等,业已一律宣言,祝新刑律早日通过。”而郭家骥则说“我于法律无丝毫阅历,不敢妄言”。[43]
另外,“如刘述尧谓广东议员全体对于新律均表赞成,所以日前未登台发表意见者,因言语隔阂,诸多不便之故。安徽议员如江谦、江辛、柳汝士诸君,亦系新派中人”。而理藩部郎中、议员荣凯也说,“和奸与违犯教令二条,皆是道德及教育范围以内问题,非刑律所应规定”。林绍箕的主张更形激进,“新律旧律不可混杂,欲行新律则不可参以旧律,欲参用旧律则不如并新律而不议,宪可不立,国会亦可不开”。记者称赞“其言可谓透辟矣”。[44]然而,在最后阶段的无夫奸投票,江谦和林绍箕不知何故未有投票,荣凯等人反而支持劳乃宣。不排除有议员在外界压力下被迫表态支持的可能性,或者新派报纸故作烟幕,误导舆论。
值得注意的是,传媒大力攻击不同意见的高凌霄、万慎等人,主要在于其“民选”议员的身份。《时报》的社论便认为,“民选议员,其程度宜高于钦选议员,乃对于新刑律一问题,其智识反在钦选议员之下,窃不禁为民选议员羞也”。[45]而且舆论最初是以西方朝、野政党对立的眼光去看待资政院的“钦选”、“民选”阵营,⑩现在却因为新刑律的争议而趋于混同,政党政治受挫的责任自然要归咎于附和劳乃宣、陈宝琛等“钦选”议员的高、万等人。
四、因法律异见而组党
新律维持会以传媒势力干涉议员的投票意向,加剧了议员间的意见对立,事实上打破了资政院之中“民选”与“钦选”的政治阵营的分野。《神州日报》指出,“资政院自开院以来,民选议员与钦选议员政见往往不合。初八九两日议新刑律第二百八十八、九两条,钦选党自起冲突,民选党亦自起冲突,两党合观,则昔之互相冲突者,皆化为今之互相融洽。”[46]所谓第二百八十八、九两条,即无夫奸罪应否入律及如何入律的问题。当日新旧双方在议场内就此问题进行激辩,当时竟然有十八次因议员争抢发言而出现“声浪大作”的情形,不难想见辩论的激烈程度。辩论终结后,会场(在场议员共119人)以投票作决定。结果支持无夫奸定罪(投白票)得77票,反对者(投蓝票)只得42票。新派不服,又进行第二次投票,表决无夫奸罪是列入刑律正文还是暂行章程,“白票党”仍得61票险胜(3票的优势)。
投票结果反映颇多的事实:首先,认为“无夫奸”有罪者要远多于反对者,彼此距离有35票之多,表明在场的大部分议员支持劳乃宣适当保存少数礼教条文的做法,而新派传媒所大肆宣扬的新派占优的前述报道并不确实,甚至可能因此促进了劳乃宣一方的团结。其次,在第二次的投票中,投白票议员有所分化,导致支持正文和支持暂行章程者大致旗鼓相当,证明折衷新旧的取向在议员间还有相当的吸引力,甚至有时成为关键的少数,也不排除某些白票议员愿意屈从于外交需要而作出让步。第三,白票议员中“民选”、“钦选”议员各半,蓝票议员中“民选”、“钦选”的比例为二比一,突破了“民选”(“民党”和“钦选”(“政府党”)的分野,呈现出“民党大为分裂,而政府新进与民间新派乃不期媾合”的现象。事后,蓝、白票的议员各自加紧联络,商讨应对新刑律案的后续事宜。汪荣宝在十月本有组党行动,而且跨越“民选”、“钦选”的界限,意图为政府施政保驾护航。不过,汪氏对于“无夫奸”条文与政府的折衷立场不同,而力主从暂行章程中删除之。此时眼见资政院表决受阻,遂决定联络蓝票议员,退而求其次,重新支持政府原案,终获得成功。[48]白票议员一方似乎也有所行动。《时报》消息指:“白党要求伦议长勿奏新律总则,枢臣联络白党,皆是附和劳乃宣之顽陋一派,近且运动白党,早日组成政党。”[49]
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度为了鼓吹组织政党,致信梁启超时便提出:“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人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摇动而可与言结党共谋,以弟思之,所谓简单之事,莫开国会若也。”[50]果然政党之议渐兴,不过召开国会迅速成为朝野共识(差别只是迟早的问题),因此难以据此成立政党。加上中国传统本有“君子不党”的古训,政党实践从一开始便颇有阻力。[51]直到辛亥前夕才找到此题以作政党政见之区分。
有意思的是,这一轮行动使部分传媒看到了政党政治的曙光,新刑律的争议也变得不那么重要,反映出所谓“礼法之争”不过是“功夫在诗外”,重点本不在法律问题。《国民公报》开始用“蓝票党”的称谓,报道他们在十二日开会,“其目的在于研究以后议会中各种重要法案,如商律、民律等必须预先研究,庶议决时不生他种困难”;而且“有人主张以此次赞成新刑律之人,组织一新政党”。[52]该报同日还报道,“白票党”也组织团体,“以为政党之预备,其目的注重在地方之发达”。该报评论说,“中国有主义政见之党派,自蓝票、白票两党始矣”。[53]
《国民公报》对蓝、白票议员组党抱持欢迎态度,“其对于新刑律之是非姑勿论,而能以主义政见互相角逐者,则自兹役始也。夫蓝票党主义微近进步,白票党主义微近保守,二者皆有成立政党之要素,且将来对于他种问题一取进步,一取保守,亦各国议会中常有之事,而亦我国所不能免。故记者对于两党之发生,取绝对的乐观主义。”这是因为“较之昔日之以钦选、民选分帜者,更促进一阶级,于议事之前途增无限之融洽。故此次之结合主义的也,政见的也,而非个人的也,感情的也”。[54]该报以为据政见而组党,当可改善资政院的议政效率,故而乐观其成。[55]
《帝京新闻》似乎也改变了对旧派的谩骂姿态,报道立场转趋中立。(11)“自新刑律提出之后,议员中党派分立,今遂有蓝票、白票两大党发生。汪荣宝、陆宗舆、雷奋、籍忠寅,蓝票党之钜子也。劳乃宣、许鼎霖、于邦华,白票党之钜子也。闭会之后,两党各标旗帜,双峰并峙,作将来政党之预备。”[56]该报转向的原因与《国民公报》类似,“(蓝、白)两者主义,一近于平和,一邻于激进”,即如“立宪政治之国家,必有两大政党,以相对峙”的“通例”。并表示“某等决不能于此有所轩轾”,特别是“两者能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以政见主义相争竞,此则吾人所最欢迎者也”。[57]
然而也有人看法不同,认为缺乏政党才是新派失利的主因,而不是应由此事而组织政党。远在英伦的章士钊认为新派表决失败,“实由于无指挥员之组织”,因为两派票数相距甚远,“似非侥倖之胜负”,新派事前未能预知胜负,也不能确保己方人员全部出席,甚至不能确保无倒戈现象的发生。可见“当局者未能先事罗致同志,或临时取径他法,以图迁就吾之目的,此失败之所由致也”。[58]梁启超也观察到正因为缺乏政党,民党议员才会因新刑律案而分裂。“如新刑律之争议,持反对论者本毫无价值,稍衡以法律之性质作用,则其说不攻自破,然院中有民党骁将,为举国所崇拜者,或乃反辩护彼说,而与同志相冲突,甚可痛也。脱有政党,则全党对于此刑律之方针,必先协议决定,党员若有怀疑,则当开党议时,反复辩难,必能相说以解,而安有临时参商之为病耶?”[59]
显然,章、梁二人并不同意《国民公报》和《帝京新闻》提出的以法律意见异同区分党派的主张。章士钊指出,因为该案并非纯为“党派问题”,而“杂有社会问题”。“凡政治问题之含有风俗礼教种种性质者,乃政家之所视为最棘手者也,故非必不得已,万不可以此列入政纲。苟列入之,其党未有不起内讧者也”。因此新刑律案“断断不当付之党争”,“一时以袒新刑律袒政府者,固不必袒政府之政纲者也,而反对新刑律者,又不必不能与赞成之者同最大之政纲者也”。换言之,两派并未对政纲有“政治之原则”,即不足以划分政党。[60]著名报人黄远庸虽然相当肯定组党的必要性,“以为中国存亡之先决问题”,[61]却也极力反对以蓝、白票党为将来政党之基础,“自有政党以来,未闻以法律上一部意见之异同而分党者”,“以政党之生命,在对于立国之宗旨,在对于现实之政治”。据其理想,组党须“与现政府或类似现政府绝缘”,依靠民间势力。因此劝告“民选”议员抛开“区区法律意见之异同”,组织真正的政党。[62]此说表面上仍是以政纲作区分,但实际上却以朝、野对立的思维,作政党之分野。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章、梁、黄等人法律异见不足以组党的看法。虽然蓝、白票党在宣统三年演变成政学会和帝国宪政实进会(后者的势力稍大),但是内部的组织建设实不如人意。[63]到清帝逊位、资政院解散以后,两党便迅速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融化于民初众声喧哗却政见雷同的政党政治之中。可见,清末民初借镜西方、以政见区分政党的思路,往往纸上谈兵,难于实行,最终还是落实到援助政府和反对政府的两大党,进步党和国民党即其明证。
注释:
①所谓“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原义指到访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官和经允许进入的外国军队,不受所在国法律管辖的特权或豁免权。初时本是国家间相互给予,慢慢演变成国际公法。然而西方国家在殖民扩张的进程中,单方面将此特权扩展到旅外的本国普通民众,使之仅受本国领事根据本国法律作出的裁判,故称为“领事裁判权”(consular jurisdiction)。在近代中国,外人在华的实际司法特权,远远超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而时人多将两名混用,本文亦从之。参见Shih Shun Liu,Extraterritoriality:Its Rise and Its Dec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5; G.W.Keaton,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New York:Howard Fertig,1969.
②如黄源盛的《法律继受与近代中国法》(台北:黄若荞,2007年,第200-283页),李贵连的《沈家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310页),以及[日]小野和子:《清末の新刑律暂行章程の原案について》,《柳田节子先生古稀纪念·中国の传统社会と家族》(東京:汲古书院,1993年)。
③张玉法已注意到“最足刺激政党发生者为新刑律之争”,但未悉此事之内、外语境,且不免有事实之误述。参见氏著《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4-327 页。
④《论参改律法》,《新闻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九日。该报不分版次。
⑤《修正刑律案语》,清末铅印本。详情参见李欣荣:《吉同钧与清末修律》,《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期。
⑥《外人注意新刑律之一斑》,《帝国日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该报不分版次。
⑦晚清报人包天笑注意到:“大概普通读报的人,一份报纸到手,翻开来最主要的是要闻与专电。……到了最后,或者读读论文,事忙的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简直干脆不看论文。”见其《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第322页。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当此各报竞争之时,必以消息灵通,新闻最多,方足以立于不败之地。”见其《告列位同志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7页。
⑧胡骏:《补斋日记》(宣统二年十月十八日),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423页。趋新的汪荣宝在日记中则说双方因口角而致“互殴”。见《汪荣宝日记》(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719页。
⑨比利时远东通讯社的王慕陶致信汪康年,称赞《刍言报》“实为朝阳鸣凤,读之如嚼橄榄,苦涩中有回味也”,实则暗讽该报不入主流。见《王慕陶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2页。
⑩就如《国风报》的观察:“大抵资政院议员中,隐分两派,一为政府党,一为民党。若满汉王公世爵,及蒙古王公世爵,则持中立态度。”见《资政院议事摘要》,《国风报》第1年第26期,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第97页。
(11)该报两周前还在痛骂:“劳乃宣反对新刑律,不恤百万运动,乃至收外人贿赂,亦所不辞。其丧心病狂于此已极。呜呼,硕学通儒而为此丧失人格之事,吾为中国羞。”见秋心:《卮言片片》,《帝京新闻》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第7页。前后转变未免过于急速。
标签:英国政党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法律论文; 北京日报论文; 劳乃宣论文; 申报论文; 领事裁判权论文; 神州日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