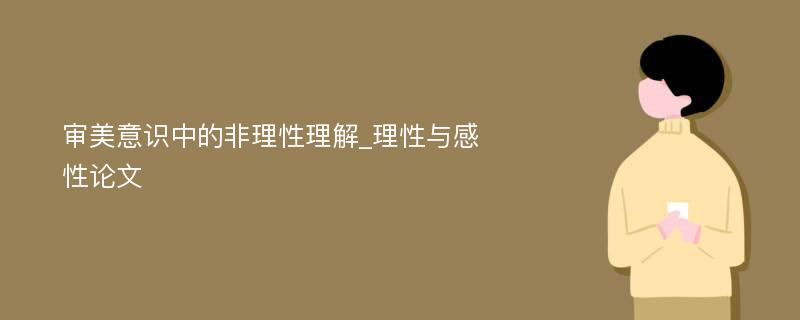
审美意识中的非理性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0)02—088—04
从非理性的层面去透视西方哲学即可发现,科学主义在热衷于理性分析之后不得不回到人本身,回归到人的情感以及能体现这一情感的形而上境遇;而人本主义则更是将情感体验视作人的生存方式,认为情感是“此在”在世的安身立命之地,又是“此在”体验自身把握世界的绝好途径。美国思想家宾克莱在论述海德格尔的思想时就曾指出:海德格尔认为,人是用他的整个“有”,并不单用他的反省意识来理解他自己,人是被突然抛进了一个世界,他必须在这个世界里创造自己的命运,他的哲学试图揭示出人的生活界按其实际显现于人的样子。所以海德格尔主张,“我们对世界的知觉,首先是由情绪和感情揭开的,并不是靠概念。这种情绪和感情的存在方式,要先于一切主体和对象的区别。”无疑的,这种把握世界的情感方式就明显地表现在人类审美观照和非理性体验活动之中。
一
审美直觉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建立在审美观察和审美体验之上的高级的审美感知能力,是一种以主观的情感体验去观照自然和现实,让审美对象激发主体的情感,又将主体的情感溶入审美对象之中的表象运动。这就是说,审美对象的某些特征诱发了主体的特定情感,而主体又在情感体验中不断强化对客体的感受,使从物象得来的表象依照主观的情感体验的逻辑和审美理想规定的方向进行变异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情感化意向。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这种相互作用、有机融合,就展示了审美认识的发生、演进的动态机制。
具体说来,审美直觉一方面强调情感体验性主体的存在,没有主体,或者说没有主体的感受体悟能力,审美直觉就不可能存在。同时,它又肯定审美客体或审美物象的重要性,认为审美直觉是不可能脱离审美物象的。即使没有外在的、可感知的“景象”,也必须有想象联想的虚象或心象(心理表象)。也就是说,在审美非理性认知活动中,不仅不舍弃具体的景象,且在思维过程中必须重视可见可闻和可想象的景象。它至少以三种方式与景象相关:其一是以具体的事物和事物间的关系同抽象的审美概念或审美学命题进行比附,用前者推绎出后者;其二是引用有象的典故或事例去解释无象的理论,以前者印证后者;其三是通过写景状物将深奥的道理隐含于浅显的景物之中,使前者(景状物)暗示后者。这样,审美主体以审美观察活动为中介,就与审美物象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非理性认知结构。
审美直觉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常被称作“味”或“体味”。例如,老子的“味无味”(《老子》六十三章),王弼释为“以恬淡为味”(《老子注》),这个命题曾影响了古代文艺美学中关于审美观照、审美体验和文艺的审美本质,以及二者之间关联性的讨论。在这里,“味”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审美主体的审美活动,其中又主要指审美观照与审美体验;二是指审美对象的审美特征与美感力量。当然,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与欣赏过程中,这两层涵义又是缠结难分的。文艺创作必须通过审美观照与体验获得审美认识,才能将这种认识物化为文艺作品,而文艺欣赏也只有通过审美观照与体验,才能感受和把握审美对象的审美特征和美感力量。
我们说审美直觉是一种观照和体验,是为了标识出这一活动与科学认知活动以及伦理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异,是为了标识出它把握世界并因此而进行文化创造的独特方式。在这里,它是一个由观照而体验、体验中蕴涵观照的过程。观照是审美直觉的起点与基础。文艺创作不可能以抽象概念的形式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而只能通过审美观照才能把握审美对象的审美特征,才能充分发挥审美想象,并在此基础上酝酿、组合、凝聚成审美意象。同样,文艺欣赏对作品也不可能以意志实践的方式去改变对象的性质与形态,而必须通过审美观照才能将文艺作品的艺术形象转化为欣赏者的审美意象,从而领悟到艺术形象的审美意蕴和艺术家的审美情思。审美观照的结果便是审美体验,便是审美主体在心理内界所呈现的某种特定感受。只有进行深入的审美观照和情感体验,才能领悟和把握作品的审美特征和美学意义,这也就是“书亦国华,玩绎方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内在意蕴。
从不同的视角去考察,审美直觉就有着不同的具体形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具体的审美直悟,均由感性之悟和理性之悟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例如,若将审美之悟区分为形式性直悟、图式性直悟、象征性直悟和内省性直悟,我们就不难发现,每一种具体的审美直悟形态都内在地包蕴着感性之悟和理性之悟两个要素,只是这两个要素在每一种审美直悟中的构成比例有着量的差异而已。
二
简单地说,审美感性之悟是指观照审美对象的外在现象、形式,即通过对物体的形状、体积和造型的富有个性色彩的情感体验,达至对蕴涵有生命和活力的形式的感知。在这里,审美视野中的物象能够产生特定形式的幻象,即主体通过对对象形式的感受而被激发出意味深长的情感,对有意味的形式实现带情感色彩的感性把握。例如,形式性直悟就是这样一种非理性活动,它力求超出对物体的几何学概念的认识和实用价值的评价,通过对对象的形式作审美观照和体验,将对象本身当作目的来欣赏和享受,并赋予对象以某种特定的审美意味,虽然并不可能排除其中所存在的理性之悟的因素,但它主要是一种感性之悟,或者说,其中的感性之悟成分远远地多于理性之悟。在书法、绘画、雕塑、建筑、陶器以及纺织品的美的创造与欣赏活动中,就融贯着这种感性之悟意义上的形式性直悟。
当艺术家描画时,不管它是一个有生命的物体还是一块石头或一片云,总是在内心中寻求自己的直观感觉,即形式性直觉体悟。就山水画而言,由于画家能“以形写形,以色貌色”(宗炳《画山水序》),即以艺术形象生动地描绘、表现大自然山水的物象及其内在生命,故能达至“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宗炳《画山水序》)的境地,这是一种因酷似所致的出神入化之境,哪怕是再求得真山真水,也无法胜过绘画作品。为使山水画达到这样的境界,就要求画家亲历名山大川,获得对审美形式的感受,实现审美体验;就不仅要“身所盘桓,目所绸缪”(宗炳《画山水序》),反复观察、体味,而且要“应目会心为理”(宗炳《画山水序》),用目感知,用心溶冶,以把握山水的内在本质和生命,从而塑造出具有美感力量的艺术形象来。正如我们所论及的,要对审美对象进行审美观照和体验,以把握审美对象的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蕴,就要求审美者能摆脱人世间的一切利害欲求,不将审美对象视作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具有一种虚空明净、自由愉悦的审美心境,而这也就是宗炳所说的“澄怀”。在他看来,山水画家要“凝气怡身”,山水画的欣赏者要“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回荒,不违天励之丝,独应无人之野”(宗炳《画山水序》),以便具有一种能进行审美观照的审美心境。
王维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承接。在《绣如意轮象赞》的序文中,他提出了“原夫审象于净心,成形于纤手”的观点。这里的“审象”就是对审美对象的感性形象进行审美观照,“净心”则是一种经过净化、排除了各种世俗欲求的审美心境;“审象于净心”,就是要审美者以一种高洁的审美心境去对审美对象进行审美观照,从而既肯定了审美形式感知的基础性,又默示了审美心境这一形成形式性直觉体验的前提的存在。
在这种基础上,沈括要求人们既要着眼于感性的形式,又要突破物理时空的限制,追求一种心理的时空。在《新校正梦溪笔法》卷十七《书画》中,他认为,中国山水画并不单纯追求形似,并不拘泥于物理时空的等同。如果画山要酷似真山,从下望上就只能见一重山,画房舍亦不可见中庭与后巷。可是,中国画却能见重重山,能同时看到山顶、溪谷、庭前、屋后,“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这“以大观小”的“妙理”,就是要求山水画法不受固定透视法则(焦点透视法则)的约束,突破物理时空的限制,追求心理的时空,“以主观心灵之大,观宇宙山川之小。”换言之,艺术家以一种无限宽广的审美心境去观察、体验大自然的万千景象及其内在生命,从而酝酿、凝聚成为鲜明生动、意蕴丰富的审美意象,这意象既是艺术家的心灵的活跃,也是大自然的生命力的象征。这种审美之悟与柏格林所说的那种将材料与想象力加以综合,即通过艺术家对外界的体验和艺术家向内心的自我观照而实现物我相融的感性直觉,无疑是大同小异的。
三
西方体验美学的偏颇就在于,它将审美之悟与理智完全对立起来,排斥艺术的客观源泉和理性内容,将审美与艺术创作的客观源泉和理性内容,将审美与艺术创作的全过程归结为感性直觉,无限夸大审美感性之悟的功能,过分放大了审美之悟中的感性要素,漠视理性因素的存在。事实上,只要我们将人看作是感性与理性有机结合的整体,将直觉放到审美活动和艺术思维的整体中去进行探究,就可在发现审美感性之悟的同时,亦能窥见理性之悟的存在。
与感性之悟不同,理性之悟是审美主体从自己内在精神状态,包括主体在自身所感到的企求、理想、欢乐、活力等出发,情不自禁地捕捉与此相对应的情绪化的外在对象即美的情景,探求和开掘观照对象所外化的情感价值,即将自我感受和体验假托于对象之中,并借助感性之悟发生升华,使特定的审美体验上升到以形象来表述的哲理之悟。例如,内省性直觉虽然内含着感性的东西,却主要地是一种理性之悟。小说、戏剧、绘画等艺术作品的作者无不主要通过理性之悟意义上的内省性直觉去组织情感逻辑和生活逻辑,进而表达对人生的看法。有人分析指出,李商隐的《乐游原》就体现了这种内省性直觉。“向晚意不适,驱车向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短短的一天之中,无情的时间老人已经把太阳从清晨的朝气蓬勃变为落山时的温柔倦怠,还要将它掩埋在漫漫的长夜之中。诗人惆怅的心情因夕阳悲凉的境遇而陷入更深沉的悲哀之中,并凝结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哲理化悲剧意识(见谭容培《论审美直觉》,《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第15~21页)。这种因目睹夕阳所致的哀愁和失落感,就将自我感受和体验假托于对象之中,并藉助感性直觉实现了理性之悟的升华,以外在的形象表述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感悟和体味。
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审美理性之悟:
首先是主体审美经验的承继性。为了能在艺术构思和审美活动中较快地获得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象,就必须重视对前人经验和优秀作品的总结、学习、体验和领悟,以提高自己的审美理解能力,丰富自己的审美经验。汤垕就曾说过:“仆十七岁时便有迂阔之意,见图画爱玩不去手,只鉴赏之士,便加礼问,遍遍纪录,仿佛成诵,详味其言,历观名迹,参考古说,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过为听声随形,终不精鉴也。”(汤垕《画鉴》)清代一画家说:他“自龄时搦管,仡仡穷年,为世俗流拘牵,无繇自拔。……复于东南收藏家纵揽右丞思训荆董胜国诸贤,上下千余年,名迹数十百种,然后知画理之精微,画学之博大如此,而非区区一家一派之所能尽力。由是潜神苦志,静以求之,每下笔落墨,辄思古人用心处,沈精之久,乃悟一点一指,皆有风韵;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阴阳之辨,傅色有古今之殊。于是涵泳于心,练之于乎,自喜不复为流派所惑,而稍可自信矣。”这就表明,总结、借鉴、玩味、领悟前人的创作经验和成功之作,能有效地扩展主体的审美经验结构,因而对于作为理性之悟的审美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艺术情感的逻辑性。艺术情感虽以个体的形式表征出来,确是一种具有共通性质的情感,它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功利,浸透着理性内容,并由此导致审美判断,以经过作者理解后所产生的自身逻辑力量去感染和说服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和共识,达到对作品的审美理解。曹植的《七哀》诗便是如此。“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云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人们不难从诗中人物情感发展的层层深入而领悟出某种理性的东西,不难从这种情感逻辑的层层剥开而领悟到忠良之士那种怀才不遇、抑郁不得志的凄苦灵魂终日沉溺、无所归依的境遇,理性之悟之光就将诗中的情感逻辑推到了一个理性的高度。
更进一步地,理性之悟还通过观照和领悟情感逻辑中所暗含的生活逻辑而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当审美者与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有相似或相同的生活经历或心境时,就更能深入领悟和把握艺术的审美特征,获得深切的审美体验与感受。一宋代学者曾深有感触地说:“李咸熙作营邱山水图,写象赋景,得其余胜。溪山萦带,林屋映蔽,烟云出没,求其图者可以知其处也。余去国十年矣,官系于朝不得归。每升高东顾,想在家山,而神驰意到,自有见闻。宾想既悟,而悲悼随之。及观正夫所示图真得乡路矣。反若不敢识者,亦似失其悲心者矣。咸熙画手妙绝今世共知之。至于营邱之寓于画者,余独知之,他人恐不能尽识也。”他之所以能“独知”,就在于他有“去国十年”的游子思乡之情,与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有共通之处,能获得强烈的审美体验与感受。
最后是与人的审美实践息息相关。说到底,人的审美能力、审美经验结构的形成与积淀与人的审美实践密切相关。宋人吕居仁指出,只有进行辛勤的艺术实践,才能达到“悟入”、“顿悟”的境界。“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能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吕居仁《童蒙训》)清代书法家吴德旋也说:“余学书几二十年,所历皆世人嗤笑唾弃之境,而又不肯安于小成,故数数从业,至今日乃觉有悟入处,倘亦禅家所谓‘渐修顿证’之候乎?”(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看来,瞬刻的审美体悟是以长期的审美实践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基础,就无法获得深刻的审美理解。
从总体上来看,两种审美之悟是有所区别的:感性之悟主张融情于景,而理性之悟则主张融理于情。但是,在现实的审美非理性认识活动中,二者又总是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的,感性之悟以理性之悟为前提,理性之悟又以感性之悟为基础。一方面,正如高尔基所说的,“直觉的东西不能理解为某种先于知识的、‘预言’的东西,它只在作为假说或作为形象组织起来的经验缺乏某些环节和细节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经验。”(引自《文艺理论学习资料》(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页)感性之悟虽未达到理性的高度, 但主体过去的审美经验和理智仍无意识地蕴涵于感性之悟的情感体验之中,帮助情感实现对表象的选择、变异和组合,决定着意象化情感或情感化意象的酝酿及形成,从而为审美认识定向。另一方面,理性之悟又是感性之悟的升华,没有感性之悟作基础,理性之悟就不可能实现和完成。可以说,不存在离开理性之悟的感性之悟,也没有离开感性之悟的理性之悟。这种审美直悟的“‘敏感’一方面涉及存在的直接的外在的方面,另一方面也涉及存在的内在本质。充满敏感的观照并不想把这两方面分别开来,而是把对立的方面包括在一个方面里,在感情直接观照里同时了解到本质和概念。”(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7页)这样, 感性之悟与理性之悟就相互包蕴、缠结在一起,贯穿在审美认识的全过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