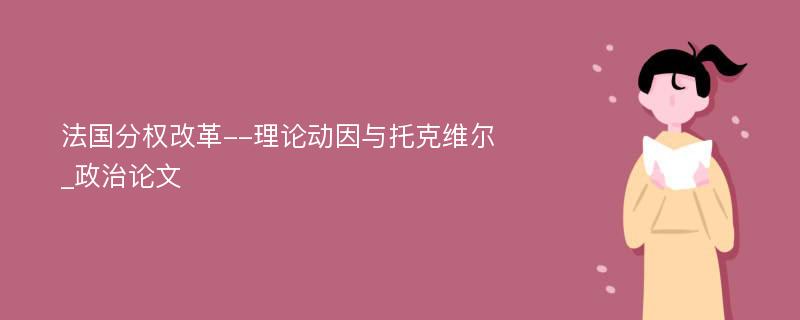
法国的地方分权改革——理论动因与托克维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法国论文,维尔论文,理论论文,托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法国1982年以来进行的地方分权改革的理论动因:提高效率、促进民主、保障自由;论证了托克维尔对这个改革的理论基础的贡献;探讨了托克维尔有关平等、民主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有关代议制民主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病的思想及其在今天的意义。
1981年5月10日,密特朗在第二轮法国总统选举中,以51.75%的多数票击败右翼候选人——前总统德斯坦。5月21日,密特朗解散国民议会,重新进行立法选举。在6月21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左派联盟再次获胜,在国民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6月23日,以莫鲁瓦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派政府宣誓就职。这样,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见到了一位左派的总统,一个左派控制的国民议会,一个左派的政府。左派的这个被称之为“法国政治的伟大转折”①的胜利,虽然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法国的政治制度,但确实反映了大部分选民对右派及其政策的失望和厌倦,反映了他们对政治、社会进行某种变革的要求。而以“改造我们的生活、改变社会的航向“为口号,以旨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对法国进行深刻改造的《共同纲领》及《110条政纲》为指导方针而取胜的左派,在这点上也确实没有让选民失望。在新议会的第一个5年里,特别是在1981-1983年间,左派通过立法手段,在法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国有化、地方分权,选举制改革、司法改革、社会改革……。一时间,法国的政治乃至社会真正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13年过去了。法国两次出现了左派的总统与右派的议会、政府“共处”,而实则是右派主政的局面(1986-1988,1993-)。当前各种迹象更都表明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右派获胜的可能性极大。1981-1983年间左派通过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已为右派取消。即以国有化改革为例,通过1986年和1993年右派政府实行的两次私有化,不仅大部分在左派执政期间国有化的企业重新变成了私有制,甚至连一些1981年之前的国有企业也被私有化了。而在这种右派对左派政策的一片否定中,唯有被密特朗评价为他第一个“7年任期中的伟大事业”②的地方分权改革是一个例外。
一
在这里,我们无意详细回顾法国中央集权制的历史,而只想指出:法国行政中的中央集权制,早在王朝时代即已形成。而法国大革命,尤其是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则将它推向了高峰。另一方面,虽然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的正式起点是1982年,但事实上这种尝试早在1871年便已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尽管1982年前的法国行政已与第一帝国时截然不同;尽管行政地方(collectivitesterritoriales)特别是公社已经有了一定的主权,但从总体上来看,法国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而要求进行地方分权改革的呼声也一直很高。
何谓地方分权(decentralisation)?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定义:即中央将一部分涉及地方利益的行政权力及行使这些权力的必需物质手段转交给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地方行政机关。与联邦制国家中各州所享有的较大权力不同,它是单一制国家中的一种独特的现象。分权的范围严格限制在行政权之内,而不涉及立法权及司法权。另一方面,它又区别于简单的权力下放(deconcentration)。法国政治学家吕歇尔父子(F·Luchair et Y·Luchair)在他们的《地方分权法》中指出:“权力下放是将中央的一部分权力转移到一些中央在地方的官员手中。地方分权则是将这些权力由中央或在地方的中央官员手中转移到独立于他们的行政地方的代表手中。”③魏德尔(G·Vedel)和德尔沃夫(P·Delvolve)则在他们的《行政法》一书中写道:“权力下放与地方分权有一个共同点:决策是在地方而非中央做出的。但它们在政治上及实际上的意义则大不相同。权力下放只是一种管理技术,本身不具有民主价值。因为它把全部国家行政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及其在地方的代表手里。地方分权则具有民主意义:它的目的是让当事者及其代表尽可能多地管理自己的事务。”④而法国左派政府在1982年所着手进行的,正是地方分权改革。
这项改革以1982年3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大区、省及公社的权利与自由》法案为开始的正式标志。它扩大了公社、省及大区的自由和权利。而1983年1月7日的另一项法案成为了它的重要补充,该法案重新划分了公社、省、大区与国家之间的权限、职责,扩大了地方事务的范围。在1982-1986年间,国民议会就地方分权问题通过了共26项法案,政府也颁布了近200项行政法规,以利于这些法律的执行。1986年3月16日,首次举行了各大区议会的直接普选,这标志着法国地方分权改革初步任务的完成。正如法国1993年出版的《地方分权史》中所说的那样:“在1982年到1986年间我们走过的路是令人难忘的。法国很少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如此紧锣密鼓的立法工作。”⑤而1992年2月6日通过的《共和国地方行政法》则可被看做是有关地方分权的一项最新的重要法案。这场地方分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大区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地方。省及大区的地方事务的决定权由中央任命的省长及大区长官手中转到了民选产生的省或大区议会的手中(在此之前各市市长便须对市议会负责,因此不构成这项改革的主要对象)。此外,中央及其在地方的代表对地方议会决议的监管权也被取消。
2、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许多过去由中央负责的涉及地方利益的事务改交地方管理。
3、向行政地方提供了行使其新职权的必要物质手段,特别是在财力及人力方面。
自1992年地方分权10周年时起,法国政治学界已开始探讨它的实际执行情况及得失。他们的一致意见是:这场被称之为法国“行政及日常生活中的静静的革命”⑥的改革虽有尚待改进、完善之处,但总的来看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进行了10年的地方分权改革……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的传统。……它深刻地改变了决策及行政系统,……并构成了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⑦事实上,它不仅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变了法国行政及政治生活的结构,还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文化。
尤其应指出的是,在当代法国国内政治中,地方分权是少有的几个(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为各派一致接受,不引起争论的口号。地方分权改革的必要性在全社会中已成为一种超越于党派斗争之上的共识。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指出的右派没有否定它的原因。戴高乐将军在1968年说道:“我国在向一种新的平衡演变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央集权,为实现和维持国家统一所必不可少的中央集权……,今后不再是必要了。”⑧(我们知道他曾在1969年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地方分权法案)而密特朗则在刚上台时即宣布:“法国过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以便她建立起来,她今天需要一个地方分权型的政权以便她不致分裂。”⑨正如法国政治学家梅尼(Y·Meny)所指出的那样:“对中央集权制的谴责和对地方分权制的鼓吹不再是一个党的专利,而是所有党派的口号了。……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中央集权主义者。”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社会的共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为何要进行地方分权改革。长期以来,法国政界、政治学界对地方分权的理论动因的探讨可谓卷帙浩繁。人们从各种角度、各个侧面说明了地方分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第一个完整、准确、深刻地论证了这个问题的,当属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他在其两部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的地方分权的3个理由:效率、民主、自由,为以后的理论家们普遍接受、反复引用并不断补充,至今仍为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的指导方针。可以这样讲,不认真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就无法真正理解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的理论动因。而托克维尔提出的这3项理由,特别是自由与民主,是当今法国任何一派政治力量所不敢反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地方分权的理论动因使它成为了各派的共同认识,或至少是共同口号。
二
为什么要实行地方分权?一个最浅显的理由是:要提高行政质量及行政效率。在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下,由于一切重要决定都须由中央做出,地方行政没有必要的决策权,因此必然造成大量的公文往来,层层审批的繁琐手续,行政机构的臃肿,官僚主义习气的蔓延,行政人员责任心的丧失以及整个行政机器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由于在中央进行决策的官员不可能对地方事务的详细情况及当地人民的利益有真正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他们做出的决定也不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中央集权制对这种弊病早已为托克维尔指了出来。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是这样描写法国的情况的:“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书面文件已经十分庞大,行政程序慢得惊人。我从未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获得批准,最通常需要两年或3年才能获准。”(11)“要想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屋顶,或重建本堂神甫住所坍塌的墙垣,必须获有御前会议的裁决。……我曾看到御前会议批准它们有权开支25里弗。”(12)对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文牍主义和令人发笑的低效率,司汤达做过同样精彩的描述:“在1811年,一个小的农村公社想花60法郎来修补一下它的人行道。这需要省长、地区长官、工程师及部长们的14个批文。这个公社在经过了11个月千辛万苦的努力后终于得到了批准,但此时这段坏了的人行道已被工人们拆掉,用来填补公路上的几个洞了。一个低级的官员,在巴黎的一个部长办公室的角落里花费大量的经费来决定800公里以外的其于公社中的一件小事。而这件小事其实只需要3个村庄代表便能在两小时内处理得更妥贴。我们不能再对这种如此明显的事实无动于衷了。特别是要知道这种事实一天会重复500遍!”(13)对于托克维尔来讲,在这种事无巨细都由巴黎来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我们很难期望采取一个比较高的行政效率和质量。因为“一个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它办不到这一点,因为这样的工作超过了人力之所及。当它要独力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它们发动的时候,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劳无益地消耗自己的精力。”(14)这个结论也完全适用于当代的法国社会。1970年《法国笔记》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写道:“法国行政机器的运转缓慢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受其危害最大的是外省。……中央行政机构过分臃肿。一个对某地方采取十分重要和急迫的,并被地方迅速而严肃地处理过的计划,会在巴黎的某个办公桌上放几个月,因为这张桌子可能同时有十来份同样急迫的计划。地方上要盖一所医院,经常要等10年才能得到中央的拨款。这种低效率的原因不在于行政官员们的不负责任,而在于行政程序的过分复杂。行政运作,特别是财务行政越来越复杂。一个简单的计划会牵涉到许多中央部门。……但是中央集权制的最恶劣的后果在于它所引起的不负责任的精神。当一个决定是由很多层次的很多人共同做出的时候,谁也就都觉得它的正确和现实与否已与己无关了。……这些事实上的不负责任与法律上的不负责任结合在一起,便扼杀了一切人的被动性和效率感。”(15)对这点,即便是对地方分权一直执反对态度的戴高乐的内政部长德伯雷(M·Debre)也不得不承认:“中央集权是昂贵的、低效率的、无力的。官员太多,决策及执行缓慢,责任感的缺乏,这一切使国家印上了软弱无力的标志。”(16)而要改变这种情况,提高行政效率并使决定符合实际情况,就必须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将地方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到当地人民及其代表的手里。托克维尔的这个观点,为以后法国的地方分权主义者所一致接受。当代政治学家巴格纳(J·Baguenard)在他的《地方分权》一书中写道:“我们认为决策中心的多元化是行政效率的保证。我们期望权力的适当分散能引起责任感的发展。……对于一个行政地方来讲,……决策机构对环境的了解越详细,行政效率也就越高,就越能迅速地调动一切物质手段。”(17)魏德尔和德沃尔夫也指出:“分权后的行政可以与有关的居民取得更密切的联系,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愿望。”(18)
应当承认,这种从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防止官僚主义危害的角度出发对地方分权的必要性的论述是有道理的。这些论点为支持地方分权的人共同接受,并成为这项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的动因。但这里有一个尚待解决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些论点及其论据是否足够充分、足够有说服力?中央集权制是否与高效率绝对不相容?地方分权是否必然导致行政效率的提高?对这个问题,许多人,特别是一部分专家治国论者是执否定态度的。法国《权力》杂志1981年第19期的一篇文章认为:“实际上,行政效率的低落是许多因素的共同结果,与行政区域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这些因素有:工作人员的素质、行政问题的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等。那种认为引进地方分权政策便可以消除这些因素的想法是幼稚的。……在紧急情况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能够比一个地方分权的国家更快、更有效地解决问题。”(19)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上,社会事务日益繁重、日益专业化,并经常要求做出快速反应。这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那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相应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缺乏全局观念的地方民选代表能否比中央集权型的行政机关更好地处理这些事务。很多人干脆认为真正的地方分权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化、集中化趋势背道而驰。即使是赞成它的人,有的也怀疑会不会“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决策错误的可能性越大。”(20)中央集权制可能有种种不足。但如果我们能够适当简化行政程序,明确行政机关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提高行政人员的责任心及职业道德,我们是否也可望拥有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行政效率?特别是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其在行政部门的广泛应用,更为这种假设增添了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否应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只局限在提高行政效率这个层次上是难以令人绝对信服的。提高效率是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但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理由。对这一点,托克维尔早就做过十分雄辩的论述。实际上,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地方分权的行政效果,而是这种分权的政治效果。”(21)他完全承认,如果单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地方分权常常不如中央集权,甚至不如专制政体。但他之所以仍要不遗余力地宣传地方分权,是因为它是促进和实现一个国家的民主,特别是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途径和保障。也就是说,地方分权的理论动因中,虽然有行政效率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政治因素:民主与自由。而如果别无选择,如果确有必要,那么我们宁可牺牲效率也不能放弃自由。
三
托克维尔的这种将民主与自由放在效率之上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当代法国政治学家的赞同。早在1921年,巴黎大学法学教授奥户(M·Hauriou)在谈到地方分权的真正意义时就曾指出:“如果这只涉及到行政,那么中央集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习惯、更全面、更公正及更经济的解决办法。但是一个国家并不是仅仅需要一个好的行政,它还需要政治自由。”(22)社会党前总理、前第一书记罗卡尔在1981年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当然,在要求地方分权的运动中有提高行政的经济效率的考虑存在。但还有比它更深刻的原因。……对法国左派来讲,是要借此将社会主义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纠正斯大林式体制的错误。”(23)或更明确地,如密特朗在1990年的一次讲话中所总结的那样:“地方分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也不仅仅对曾长期支配我国的中央集权传统的否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自由的支柱,因为它是民主的一个工具。”(24)
我们知道,按照民主的字面含义和原始含义,它意味着人民的权力,即全体人民都应拥有参与对公共事务、国家事务即政治的讨论及决定的全权,这种直接式的民主在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曾经部分地实现过。它也是一切民主主义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权形式。但对于国家面积较大,人口众多,国家事务头绪万端且日趋专业化的当代世界来讲,每天为无数件公共事务将全体公民召集在一起做决定是不现实的。目前真正具有可行性的,只能是代议制民主,即理论上拥有国家主权的人民将该权力委托给自己选择的代表,由这些代表来表达他们的意愿,替他们做出决定。这便是西方目前所实行的制度。抛开它的虚伪性、阶级性不谈(因为最终拥有权力的只不过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会是全体人民的代表),这种制度在理论上也是很不完善的:它只是一种间接式的民主。尽管代表由选举产生,并受到选民的监督,但他们能否真正反映人民的意愿意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很难完全保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不过是古代原有意义上的贵族制——少数优秀分子的权力而已。因此,从民主的角度来讲,代议制民主或曰间接式民主永远不如直接式民主那样彻底、权威、具有合法性。
既然在目前世界上,由于技术原因我们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直接式民主,那么我们能否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实现它?一个公社或一个市镇的事务,只与当地的居民有关,也只有他们有权决定如何处理。这个框架相对于国家来讲很小,居民们对自己身边的事务也比较了解,他们完全可以直接发表意见,亲自做出决定。即使有时仍需选出代表来执行决议,他们也更容易对这些代表进行监督、控制。这就是人们将地方分权与民主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对地方分权与民主主间的关系,托克维尔并没有做更多的阐述。他只是指出,地方分权有助于培养公民对公共利益、公众事务的关心,有助于提高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它就象一所学校,训练他们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这种培养和训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小事情上都没有学会使用民主的老百姓怎么能在大事情上运用民主呢?”(25)为了进行这种培训,他认为即便是降低一些行政效率或质量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一开始必然要付出的学费。“人民插手公共事务,往往会把事情搞得很糟。但是,不扩大人民的思想境界,不让人民摆脱陈规旧套,他们就参与不了公共事务。”(26)就永远不会拥有行使民主权力的能力。不过,托克维尔在地方分权与民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的论述也就到此为止了。法国真正就此大作文章的,是当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梅尼在他著名的《法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一书中指出:“1871年和1884年通过的关于地方自由的法律,在政治界中引起了民主概念与地方分权概念的混同。”(27)“在自由主义、共和制哲学旗帜下的对与其他自由同样重要的地方自由的呼吁,逐步形成了地方分权概念与民主理想的同一化。”(28)莫克里(J·M·Moeckli)认为:“在一个行政地方内,当每一个人都能决定与他及他所属的行政地方有关的问题时,这就是民主。而如果是由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来做决定的话,这就表明民主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所谈的民主,是要把决策权地方化,使当地的公民及其团体真正能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事务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29)艾茨曼(Ch·Eisenmann)提出:“在中央集权制与地方分权制之间,后者是更为民主的方法。因为比起中央集权制来,它使行政与更多的人的意志相吻合。”(30)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总报告人则在议会中宣布:“我们强调:公共权力包括地方权力;我们强调:民主的地方权力是民主的政治权力的基础。”(31)在地方分权改革进行了十余年后的今天,政治学家们更是到处将它与民主相提并论。萨当(P·Sadran)宣称,不论在公民学习直接管理地方事务方面,还是在他们选举地方官员方面,“地方分权所引起的地方民主都是完全真实的。”(32)而波尔多政治学院地方政治研究所主任马比罗(A·Mabileau)更是将地方分权列为民主制发展的第三阶段。在他看来,法国民主制的第一阶段是雅各宾式的民主。此时尽管国家权力是民主的,但它强调的更是统一和中央集权。民主的第二阶段是代议制民主。与第一阶段一样,虽然它在理论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人民在选举之外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是一种“没有人民的民主”。而地方分权导致的则是民主制的第三阶段:参与制民主。它使每个公民都有可能学习和参加地方事务的直接管理,最富有民主精神(33)。
为什么当代政治学界对地方分权的民主运动倾注了比托克维尔大得多的热情?我认为这是由民主这个概念在西方20世纪的模糊化和神化所决定的。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从纯理论角度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即直接民主的优越性是肯定的。但问题是欧美17-18世纪民主革命后所实行的政治制度不过是代议制民主。在这种民主下,人民除选举外并不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西方的普选制也只是在二战后才基本实现)。而掌握国家权力的,是一个代表着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阶级。这种制度,与政治学经典意义上的贵族制毫无两样,或如一些西方理论家所承认的,至少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波利比笔下的一个“混合制政体”——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议会是民主制和贵族制因素的代表。我们完全同意,这种代议制民主比起专制制度来是一大进步。我们也可以同意,在目前情况下,它是最具有可行性、最接近于民主本意的形式。但毕竟应指出这两者间的区别,毕竟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在西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宣传中,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理论界限被巧妙地模糊化了。好象代议制民主便是真正本意上的民主——无人敢反对的、象征着全体人民权力的民主;好象代议制民主从来就是这样,没有经历过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好象这种民主的原则已有百分之百地成为了现实;尤其是好象这种民主没有任何弊病、从来不会失误。这种代议制民主的神话使西方在宣传战中取得了莫大的好处。也使得任何思想或政策如不和它自动挂钩便无法证明其合法性。它成为了一个图腾:谁来对它稍有非议,谁便是在反对民主,反对人民的权力,谁便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一个恶棍。这种简单化、概念化、条件反射化、非此即彼的美国式思维方式或毋宁说宣传真正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一大灾难。而我们看到,法国政治学界对地方分权的理论动因的探讨也没能逃避这种影响。
四
但对于托克维尔来讲,地方分权的主要理由并不在于增进民主,而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他赞成代议制民主,但并不迷信它。相反,他还在这种民主制中看到了巨大的潜在危险,看到了它对公民自由的可能威胁,并把地方分权做为一项防止这种危险、抵御这种危险的重要手段。
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与自由是有着明确区别的。民主制的主要内容是平等,是人与人之间身份的平等。它既是民主制得以诞生的条件,又是民主制带来的结果。它是民主社会中的“一件大事,而所有的个别事物则好象是由它产生的。”(34)民主社会就是“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35)
但是这种民主,特别是这种民主制下的平等,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自由。“虽然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把两者区分开来。”(36)因为自由并非某一特定的社会,包括民主社会的专利,而民主制虽然完全可能导致自由,却并不能保证自动导致自由。处理得不好的话,它甚至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一种相对高度的平等,可能与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度,或与完全没有自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37)而“在任何时代都是危险之物的专制,在民主时代尤其令人可怕。我们不难看到,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最重要的是自由。”(38)因此,在托克维尔的心目中,民主有别于自由。而对西方民主革命后的代议制民主的迷信也不存在。
为什么民主,特别是民主制下的平等可能构成对公民政治自由的侵害,甚至导致专制和暴政?托克维尔认为,简单地讲,是因为平等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似及相互隔绝,人民力量的分散及自然而然的软弱。个人变得日益渺小无力,只重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不再关注社会事务和全体的幸福。而另一方面,社会中政治权力迅速单一化、集权化并迅速扩大。在平等的民主社会中,过去贵族的特权消失了,地方的自治权让位给了中央的统一管理;旧制度下的司法相对独立不见了;行会也被取消了。因此,一切在旧制度下中央与人民之间的次级权力,这些虽然本身可能不平等,但却可以构成对专制的抵制及对人民自由的某种保障的次级权力都不存在了。我们只能见到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全能的、无处不在的、集权的中央权力。总之,“在民主国家,每个个人都是非常软弱的。但代表众人并统治众人的国家却是非常强大的。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会象民主国家的公民那样看来渺小。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象民主国家那样显得强大。”(39)这种民主的,这种因代表了多数的意愿而显得天然合法、不受限制的权力,完全可以导致自由的毁灭。在托克维尔看来,“政治自由来因于国家弱小,而非来因于国家本身。”(40)而本身过分强大的民主权力倒可能成为“多数的暴政”。他认为,一切权力只要过分强大,只要没有限制,就必然会变质。在这点上,代议制民主并不例外。“如果你承认一个拥有无限权威的人可以滥用他的权力去反对他的对手,那你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多数也可以这样做呢?许多人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改变了他们的性格了呢?……我反对我的任何一位同胞有权决定一切,我也决不授予某几个同胞以这样权力。”(41)“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42)因此,当务之急不在于探讨一个过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权力的性质,而在于对它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为此,托克维尔设计了种种措施:司法的独立,人民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而尤为重要的是地方自由。这也是他大力鼓吹地方分权的根本原因。
托克维尔谈道:“我认为地方分权制度对于一切国家都是有益的,而对于一个民主的社会更是最为迫切的需要。……没有地方分权制度的民主政体,不会抵抗这种灾难(指暴政)的任何保障。”(43)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既限制着多数的专制,又使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习惯和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44)而“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45)这也就是他那著名的“地方分权是人民自由的学校”的命题的由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他来讲,政治自由的价值远远高于代议制民主。而他主张实行地方分权的核心理由,既不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也不在于促进民主,而在于保障自由。
法国当代政治学界,尽管未必同意托克维尔对代议制民主的不信任感,但在地方分权可以保障自由这一点上是继续了他的思想的。梅尼指出:“地方自由已经与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一样,成为自由这个概念的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成为共和制对君主制的胜利的一个象征了。经过一个世纪来的混合,地方分权与政治自由之间已经建立了紧密的、明确的联系。”(46)巴格纳希望“地方分权能够通过对多元化倾向的加强而深化我国的自由。”(47)吕歇尔父子则指出:“地方分权是对国家的无限控制的一种抵制。托克维尔及蒲鲁东已经注意到地方自由的发展是对国家的过分权力及社会的齐一化倾向的宝贵的解毒剂。在今天,在公共权力已经干涉到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情况下,这种解毒剂就更是不可或缺的了。”(48)而1982年3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决定开始地方分权的法案也就被顺理成章地冠之以《大区、省及公社的权力与自由》法。
五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托克维尔对我国地方分权改革的理论贡献:这场改革的3个理论动因都是他首先提出,并加以令人信服的论证的。他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已成为一切地方分权主义者的理论经典。地方分权在今天能成为法国社会中少有的一项共识,也是因为各派都无法否认他提出的那两条理由:民主,特别是自由。而他从地方分权出发,对平等、民主与自由的关系,对代议制民主的弊病所做的论述更显示出他天才的预见性、正视现实的勇气和科学、客观的精神。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仍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现在谈论法国1982年以来的地方分权改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自由和地方民主还为时过早。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各级行政地方的自主权确实是扩大了。但这些权力真正落到人民的手里了吗?法国地方生活中真正出现了“参与制民主”吗?从目前能够观察到的事实来看,实际上是那些经常身兼数职的地方官员——市长、省议会议长及议员们从中得到了好处。他们利用地方权力的扩大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而绝大多数选民仍被排斥在地方事务的决策过程之外。梅尼在1992年的《权力》杂志中尖锐地批评道:地方分权改革十年后的法国成了一个“领主共和国”。地方官员们已经很象过去的封建领主了。洪丹(J·Rondin)则认为地方分权不过是新贵族们的加冕仪式。“它所创造的形势的特征便是权力在一个人手中的积聚和广大群众对地方事务的毫不知情。”(49)
但是这些批评都只说明了地方分权改革仍需改进和完善。没有人试图否定地方分权的理论动因,更没有人要否定托克维尔对它们的论述。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能在100年之后仍得到各派的肯定,能够如此完整地成为法国地方分权改革的理论基础,确实证明了它的价值和生命力。
注释:
①马比罗(A·Mabileau):《法国政制》(Le Systeme Politique Franfais),1985年法文版,第137页。
②雷米松(E·Herichon):《地方分权》(La Decentralisation),1983年法文版,第56页。
③吕歇尔父子(F·Luchair et Y·Luchair):《地方分权法》(Le Droit dela Decentralisation),1983年法文版,第18页。
④魏德尔(G·Vedel)、德尔沃夫(P·Delvolve):《行政法》(Droitadministratif),1984年法文版,第849页。
⑤包迪诺(P·Bodinean):《地方分权史》(Histoire de la Decentralisation),1993年法文版,第111页。
⑥[法]《世界报》,1986年3月20日特刊,第15页。
⑦《地方分权的回顾与展望》编写组:《理性时代:地方分权》(Decentralisation:1'Age de Raison),1993年法文版,第5页。
⑧戴高乐:《讲演及书信集》第5卷,1970年版,第271页。
⑨见密特朗1981年7月15日在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⑩梅尼(Y·Meny):《法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Centralisation et Decentralisation dans le Debatpolitique francais),1974年法文版,第51-52页。
(1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1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0-91页。
(13)司汤达(Stendhal):《拿破仑的生活》(La vie de Napoleon),1958年法文版,第233页。
(1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00-101页。
(15)奥尔曼(D·Hodremann):《权力下放与地方分权》(Deconcentrationet Decentralisation),载《法国笔记》(Cahiers Francais),1970年7-8月号。
(16)德伯雷(M·Debre):《共和国的覆云》(La Mort de 1 ECat Republicain),1947年法文版,第42页。
(17)巴格纳(J·Baguenard):《地方分权》(La Decentralisationterritoriale),1980年法文版,第75-76页。
(18)魏德尔(G·Vedel)、德尔沃夫(P·Delvolve):《行政法》(Droitadministratif),1984年法文版,第864页。
(19)怀特(V·Wright):《一个英国雅各宾党人的问题》(Question d'un jacobinanglais),载[法]《权力》(Pouvoirs)杂志,1981年第19期。
(20)吕歇尔父子(F·Luchair et Y·Luchair):《地方分权法》(Le Droit dela Decentralisation),1983年法文版,第23页。
(21)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05页。
(22)奥户(M·Hauriou):《行政法细节》(Precis du Droit administratif),1921年法文版,第109页。
(23)罗卡尔(M·Rocard):《大区:左派的一个新见解》(La Region une ideeneuve pour la gauche),载[法]《权力》杂志1981年第19期。
(24)转引自萨当(P·Sadran):《地球村时代的地方民主》(La democratie locale o Lege du Village Planetaire),1992年法文版,第55页。
(2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07页。
(2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279页。
(27)梅尼(Y·Meny):《法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Centralisation et Decentralisation dans le Debatpolitique francais),1974年法文版,第30页。
(28) (Y·Meny):《法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Centralisation et Decentralisation dans le Debatpolitique francais),1974年法文版,第33页。
(29)莫克里(J·M·Moeckli):《权力与责任的结合:地方分权与计划》(Le Mariage de La Decentralisation dans le Partage des Pouroirs et des Responsabilites),载[法]《为了》(Pour)杂志1979年1-2月号。
(30)艾茨曼(Ch·Eisenmann):《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Centralisation et Decentralisation),1948年法文版,第228页。
(31)[法]《政府公报》,1946年4月号,第1922页。
(32)转引自萨当(P·Sadran):《地球村时代的地方民主》(La democratie locale o Lege du Village Planetaire),1992年法文版,第56页。
(33)见马比罗:《迟到了的地方分权》(La decentralisation en retard),载[法]《法国笔记》1992年5-6月号
(3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4页。
(3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59页。
(36)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621页。
(37)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621页。
(38)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630页。
(39)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573页。
(40)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179页。
(41)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288页。
(42)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289页。
(43)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106-107页。
(44)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332页。
(45) 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第67页。
(46)梅尼(Y·Meny):《法国政治辩论中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Centralisation et Decentralisation dans le Debatpolitique francais),1974年法文版,第30页。
(47)巴尕纳:前引书,第75页。
(48)吕歇尔父子(F·Luchair et Y·Luchair):《地方分权法》(Le Droit dela Decentralisation),1983年法文版,第21页。
(49)洪丹(J·Rondin):《贵族的加冕礼》(Le sacre des notables),载《地方分权的法国》(La France endecentralisation),1985年,第299页。
标签:政治论文; 代议制民主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中央集权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分权管理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行政效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