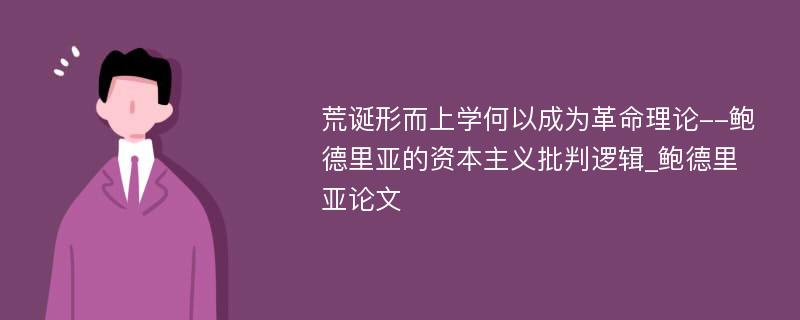
荒诞玄学何以成为革命的理论——鲍德里亚的资本主义批判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玄学论文,荒诞论文,资本主义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活在我们这个矛盾已达极限的时代,何妨任讽刺、挖苦成为真理的代言。
——罗兰·巴特[1]3
巴特《神话学》初版序言的这个结语预示了一种批判策略,鲍德里亚后来为之提供了一个难以模仿的范例——以象征暴力为旨趣的“知识恐怖主义”。这种“知识恐怖主义”既以向死而生姿态激发着人们从文化根源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釜底抽薪式批判,又以犬儒主义姿态回避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物质暴力从而使批判面临丧失意义的危机,加之其他的内在理论张力,这种策略本身也引发多种争论。在我们看来,作为整个资本主义批判史上的又一次激进转向,鲍德里亚是“68”传统的一种延续,他的策略产生过程独特地表现为各种新旧批判资源之解释力和批判力的再检验过程,“知识恐怖主义”的产生最终见证了传统批判的失败和今天批判理论所面临的基本难题。
一、理论家,或为什么是革命的知识恐怖主义者?
即使在后现代知识氛围中,鲍德里亚给人的印象也是极为震惊的,他集中了拉康的隐喻性写作、麦克卢汉的寓言式写作、德里达的自我擦除式写作以及巴特以消灭符号为旨趣的絮语式写作等多方之长。其离散的身份、碎片化话语打破了理论写作的通常逻辑形象;对理性论证的摒弃,各种修辞的大量堆砌,各种异质性话语不加协调地并置等,也给人们的阅读带来巨大的挑战。一句话,他不仅超出了批判理论家的传统形象,而且超出了批判理论的传统界限。这使得,集中面对他的文本时,我们往往只能médusée。① 甚至,正是这些东西逆反性地使得他的话语具有巴特所言的可写性与吸引力。
当他以“知识恐怖主义”、“荒诞玄学”、“病毒”、“诱惑”等等各种术语来描述自己的论述,只是通过反讽、比喻、寓言等形式喋喋不休而不期待着什么,他到底要干什么呢?他的惊世骇俗难道仅仅是为了某种médusée效果,就如今天中国市场上每日都重复着的那种明星效应?
答案既是又不是。这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他的奇异之处。在不同文本中,鲍德里亚曾经反复论及现代市场的眩晕,甚至将眩晕看作体系(即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例如,他指出,今日世界处在生产力崇拜的眩晕之中②,从交流来看,眩晕正是世界游戏的一个部分。[2]26 既然眩晕是其批判的对象的特征,那么他就不应该把眩晕效果作为一种理论的追求。然而,他确实追求那种眩晕效果。在《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中,他便将涂鸦形式的写作看作是对体系的反抗③,后来则大谈“诱惑”策略和虚无主义,直接赞扬以象征暴力而非真理为目标的知识恐怖主义④。眩晕正是这类策略实践的外在目标和效果。
如何理解以上那些术语描述的策略,它们的操作方式、性质和效果?这正是鲍德里亚给出的难题之一。从这个难题出发,我们不得不深入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不得不提出自己的分析,从而为评判提出合理参照。在此,我们不得不穿越他的身份离散性,那只是其理论的甲胄。用他的术语来说,这种甲胄是借以“消失”(disappearance)策略逆反性地获得的“露面”(appearance),同时就如这种策略所模仿的体系本身一样,它是一种没有任何外在参照的封闭的表皮(appearance)。用传统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形式。作为现代社会本身的特性,它表明现代社会“在场压倒存在”的性质。⑤ 鲍德里亚自己曾经用“表面的深度” (the superficial depths)、“表面的深渊”(superficial abysses)、“恶之透明”(the transparency of evil)等不同术语来描述这种特征。在更大范围中,对现实的这种描述,并非鲍德里亚独有,拉康—齐泽克谈论“深度与表皮之间的张力”[3],布迪厄曾以“自指性”(self- referential)来描述“新闻场”[4],都是在同一层次上按照同一逻辑来进行的。他们都共同地依赖由拉康揭示的“镜像”理论,并且更为有趣的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通过模仿这种逻辑来实施自己的批判。鲍德里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仅如此做了,而且公开强调,除此而外没有别的选择。在直接的意义上,这是愤世嫉俗的“向死而生”的战略,是一种“致命的战略”。⑥
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策略缺乏严格的定义,也不可能严格的定义。他曾经说,这是:“缺席的战略,逃避的战略,移影换形的战略。替代的无限可能性、没有参照物的串联的无限可能性。转移视线和设置圈套,这样就取消了迹像、拆散了物之秩序和欲望的秩序……这是东方战争艺术的策略:绝非直接瞄准对手或者他的武器,绝不直接看他,而是看他的两边,看那些他发动攻击的空白点并打击那里,看行动的空白中心、武器的空白中心。这就是庄子提到的庖丁:为了把握空隙——这些空隙把牛的器官联系起来并且是你的下刀之处——,他绝不看牛的身体”[2]68。这种可用中国传统智慧描述成“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这种通过加速体系来反体系的策略,这种用死亡来反死亡的策略,确实超出了传统理论的限度。但是,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却是一种“比体系本身的劝诱要强大许多”的诱惑策略。[2]75
《象征交换与死亡》曾为这种策略的起源提供过合理性论证。不过,我们可以撇开鲍德里亚本人的解释而直接从其理论深化轨迹来把握这一策略的实质:在看不到革命前景条件下,这是一种受到媒体交流实质性激发的挑衅性写作姿态。这种挑衅性姿态既批评了马尔库塞在体系内部寻找革命主体的“大拒绝”策略,又以“大消失”(Disappearance)在形式上将之进行到底。
20世纪70年代之后,鲍德里亚不止一次强调过,体系已经接近它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使得历史地出现过的对资本主义的最激进批判——马克思和精神分析等——无一例外地成为体系自我繁衍的资源。⑦ 当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无须他的指点,我们自己也严肃地面对迄今为止批判理论失败之事实。只是极少有人像他那样,在宣布没有革命的背景下,为了保持一种革命的姿态,挑衅性地在理论上成为一名自我标榜的恐怖分子。在“恐怖分子”成为全球“政治上正确”语境中一个令人难堪的“术语”这一背景下,鲍德里亚确实提出了许多批判需要直面的问题。在逻辑上,鲍德里亚既是从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恐怖主义”批判中走出来的“以恐怖主义对恐怖主义”奇特思路,又是结构主义之“理论上反人本主义”之别样升华。⑧
这一切都与其对当代西方社会性质的判断直接相关。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最终进入以代码统治为标志的“模拟”阶段和以价值不规则碎片化为特征的分形(fractal)阶段或病毒阶段,传统批判理论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在他定义的代码统治中,文本和话语都表现为信息在自我流通过程中的短路效果,理论生产也不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来保证,即“理论生产之镜也破裂了”[5]7。他断言,从今天以后:“我们只为将来某一天发现我们——我们和我们的‘实在’的那些人工作,他们把我们当作一个神秘或怪诞时期的遗迹,当作皮尔丹人的颅骨:一个尼安德特人的颅骨和一个南方古猿下颌骨的混合体——这就是一个纯粹精神时代的考古学家们不久将要认出的东西。”⑨ 鲍德里亚借由“皮尔丹人的颅骨”这个伪科学例子所说明的工作,在多大的意义上,这是对包括理论在内的全部活动的真实描述或预言,这个问题可以存而不论。⑩ 可以肯定的是,这也是他对“知识恐怖主义”所做的一个辩护。
这种“知识恐怖主义”,恰当地说,是在预言(乌托邦)耗尽自身符号能量之后作出的一种不再承诺的反预言写作姿态。(11) 我们在齐泽克等人那里也会看到它的变体。也正是在这种反预言写作中,批判不再需要任何证明合理的动机,也不再强调对任何(理论的和现实的)资源的本质性运用,甚至不再要求任何逻辑上一致的话语。至少,就鲍德里亚来说,他到底是一个荒诞玄学家、境遇主义者、乌托邦人、TOE分子、病毒和隐喻高手,还是什么都不是?(12) 这个问题不再重要。因为,身份的离散性,正是今天后现代作家们的关键性政治诉求和写作特色,借以此,他们试图打破拒斥接近完美的体系本身。
二、消费社会,或为什么要告别马克思?
如果像上述解释的那样,鲍德里亚的恐怖主义是理论上的革命,那么它给我们提出的真正问题是:在今天,为什么革命只有通过理论才是可能的,更进一步,为什么理论必须走向零意义的重复才是革命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包含在鲍德里亚对现实的判断中。正是那种判断清晰地勾勒出他的知识路径的偶然性,从而使得它的高度异质性和离散性可以理解。
无须强调,鲍德里亚大谈资本逻辑的时候,与其他激进左派一样,他把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作为自己进攻的对象。特殊的是,在理论起点上,他受列斐伏尔影响,直接瞄准的是作为这个一般逻辑之具体表现的“消费社会”。这个特殊的起点对于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正如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之日常生活》(与《物体系》同期)详尽阐明的那样,这是对人们普遍感觉到的“新资本主义”的一种定位努力,包含在这种努力中的是一种理论的漂移,而漂移又是传统(包括批判理论)失败的见证。(13)
20世纪70年代初,“红五月”的旗帜已经开始褪色;“东方”的曙光也不再耀眼;加之老一辈左翼理论家或凋零或沉寂,左派处在一种严重的理论困境之中: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庭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极刑宣判已经成为一种无意义的重复。一方面不再能够像马克思时代那样容易地找到判决的执行人,另一方面宣判本身已经因为证据不足和量刑失当而在合法性上遭到质疑。因此,深深蕴含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的“告别”(无产阶级)、“转向”(新社会运动)、“重新定向”(资本主义危机)等等萌芽开始绽开出新的枝叶。列斐伏尔这些老将,鲍德里亚、哈贝马斯等一批新秀几乎同时在不同领域和方向上提出新的见解,这绝非偶然。无论什么理论,它们的发展都高度依赖于对现实本身的判断。因此,新的方向都是从资本主义的重新理解开始的,这种重新理解恰恰包含了“致命的逻辑”: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适应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偶然的是不同理论家之特殊视角的选择。例如,列斐伏尔把空间作为新的起点(《空间的生产》,1973年)与他对资本主义残存(即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重要性认识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从社会进化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与其对现代资本主义危机认识直接相关(《合法性危机》,1973年),鲍德里亚热衷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则与其对消费替代生产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后果的重视一致(尽管这受到了列斐伏尔和巴特等人的直接影响)。
我们不必细究这种偶然逻辑的路径起源,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结果。在此,真正的问题在于,从起点到结果之间的逻辑是如何过渡的?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早期是否站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是否忠实于导师列斐伏尔,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因为,列斐伏尔等传统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在自己的主题中表明,现代分析的逻辑(消费)已经与马克思(生产)相反。重要的是,当他采取精神分析和符号学视角来揭示消费本质的时候,试图通过发展一种(普遍的)消费社会学来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的时候,要么失败,要么回到一种以主体平等为内容而否定形式的纯粹交换(意义的生产)。因为,在一般理论逻辑上,只有基于这样交换,才能够提出对消费社会之拜物教或物化的批判。这个问题实际通过参照马克思从生产出发的批判逻辑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马克思对那种以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生产的“辩证扬弃”不正是为了实现“为生产而生产”吗?
悖反性地,不只是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着这种要求,而且正是资本生产的当下现实似乎为实现这种要求提供了真实可能性。因为,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的那样,在今天的消费模式中,“不再存在什么超验,甚至也不存在商品之拜物教的超验。今天,只存在无所不在的符号秩序。……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秩序”[6]192。这是对消费社会批判的制高点。不过,这个制高点并没有多少原创性,因为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列斐伏尔等人早已得出类似的结论或直接就是从其出发进行批判的。不同的是,鲍德里亚走向符号学分析(这是列斐尔伏尔不愿做的)时,在形式上完成了对马克思逻辑的颠倒。这种颠倒具有逻辑上的推动和拉力。推力是,在这个制高点上,除非把交换本身(消费只是特殊的或异化了的交换)视为社会构造的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力量(或者用传统哲学语言来说,把消费视为社会结构的本体),并且把消费视为现代社会之“普照的光”,从而把现代消费建构的符号秩序视为历史的物化,否则缺乏理论的冲击力。这种推力与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分析资本生产一样。这说明,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建构的一般消费社会学理论是个失败,因为这个制高点正是在其失败中诞生的。(14) 拉力是马克思的逻辑。尽管鲍德里亚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的《资本论》说成是内容分析,但正如拉康等人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其直接就是形式分析。因为,马克思强调,正是在资本生产中,生产丧失了其历史内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变成纯粹的形式(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甚至物也丧失了其使用价值而作为纯粹的交换价值而存在)。这是黑格尔意义上目的与手段的颠倒,即异化,也是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内容。德德里亚后来通过马克思有关交换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描述而颠倒马克思分析的时候,他实际上借助的正是这种逻辑本身。只不过在《消费社会》中,他通过指认马克思在消费形式也没有看到了资本逻辑的发展,开始转向对马克思本人的批评。
《消费社会》之后,鲍德里亚在理论上首先是按照推力的方向本能地前进的。所以,他开始对包括马克思在内在的传统批判理论进行清理,并建立起批判所需要的一般交换理论。《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其成果,亦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理论高峰。在其中,他借助于结构主义理论和以莫斯为突出代表的人类学理论(15) 建构出以交换作为社会本体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此替代马克思以生产作为社会本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但,这注定也是一个要放弃的计划。因为,这部庄严的学术著作提出的那种为超越使用价值而设计的价值换算公式最多算是无害的娱乐。(16) 当鲍德里亚把拜物教的形成原因从生产过程移到交换过程之中时,他依赖于交换—消费—指示作用(signification)三种不同层次的意义活动之间的还原操作,也依赖于对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符号价值三种递进的意义属性之间的区分,以及在对象定位上则诉诸原型(实体)—体系(关系)—模式(结构)之间的深化过程。尽管鲍德里亚在这里恰当地描述了现代消费的特征,但并没有在更长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或人类全部历史中说明它的历史形成,而这需要对交换的本体论地位及其历史变化的进一步说明。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莫斯象征交换的本体地位出现了,在其后的《生产之镜》中,交换的历史变迁也出现了。但遗憾的是,由于前一文本聚焦于在共时性结构中阐明交换的形式变换,而后一文本聚焦于对马克思的外在批判,上述理论任务恰恰被压抑了。所以,这一任务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才得以完成,而一旦完成,理论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有趣的是,尽管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生产之镜》,其理论主题有一个跳跃,但并非不自然(17),并且正是必由《生产之镜》才能走向《象征交换与死亡》。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消费定义(18) 出发,能够在交换问题上指认马克思的不足,而对马克思不足的指认将直接掀开生产——再生产问题的认识。这样,他实际上就理解了马克思以及列斐伏尔等人正是从“资本主义是通过资本把自己生产的条件再生产出来而得以再生产的”这一思想出发的。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无法从生产方式的自我循环中走出来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理论,这是一种失败。与之相反,以莫斯为前提从交换角度来讨论文化的生产从而为穿越资本能够提供更加普遍化的理论,就如萨林斯所做的那样。在这里,隐含在《消费社会》中的逻辑推力就达到了顶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恰恰从马克思关于交换历史发展的说明,不仅能够为其从意义生产(交换)角度来进行历史分期并定位“模拟”逻辑打开大门,而且可以摆脱从交换角度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的那种本体论依赖。因为,只要承认象征交换曾经是历史地出现过并且也是消费逻辑无法彻底消除的从而困扰着消费自身的逻辑,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承认,在《消费社会》所描述的那种消费的制高点,符号秩序对物的消灭恰恰为象征交换的回归提供了客观条件。这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矛盾,也如马克思所言的资本界限——正是在资本生产中出现了否定资本私有制的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趋势。所以,在形式上,鲍德里亚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实际上是同构的。当然,他不再需要谈论马克思,客观的现实也出现了仅从马克思出发无法分析的新内容。因此,在《生产之镜》及其后的理论发展中,他的焦点是:如何通过象征交换来打破资本的统治?
从上述分析看,《生产之镜》不是一个突兀的主题,而是鲍德里亚逻辑进展中必需的对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后一方面没有展开)为代表的全部资本主义批判话语的清算,在这种清算中,他才能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新定位和开启新的批判方向:正是在社会关系直接生产的层面,资本主义是脆弱的,并处于毁灭的途中。因此,资本主义致命的毛病并不是它不能经济地和政治地将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它不能将自己象征地再生产出来。[7]129 再强调一次,正是借由马克思的交换分期理论,鲍德里亚指认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想理解它。……这种突变涉及从形式—商品到形式—符号、从一般等价规律下物质产品交换的抽象到符码规律下所有交换的具体实施的转变”[7]107。这种突变即是价值的结构形式对商品形式的替代。《象征交换与死亡》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他后期的全部重复性论述也都是围绕这个中轴展开的。在那种重复过程中,他先后又采纳过“模拟逻辑”和“病毒扩散模式”这两种递进的描述方式,并最终依据“病毒扩散模式”而展开分析。从鲍德里亚整个风格和逻辑看,术语问题恰恰并不重要,对术语的过度迷恋正是“模拟逻辑”的阴谋。在此,我们也就不展开讨论了。
三、革命,或为什么走向象征暴力?
既然传统革命不再有效,革命本身就需要重起炉灶。但鲍德里亚的难题是,在其定义的价值的结构形式支配的当下资本主义阶段(即模拟阶段),恰恰是革命已经不再可能。所以,他便讨论支配着象征交换过程的死亡的物质性,提出唯一能够对抗代码结构暴力的象征暴力问题。不过,这是其第二个理论高峰,并且这一高峰随即被其后加速的理论发展所覆盖和加倍。因此,我们不再从其理论的实际进程出发一一地详解他曾经提出过的全部战略序列,而是简述其最终形态——“病毒模式”,这是对网络模式的模仿。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鲍德里亚越来越偏爱当代信息技术,将最新的交流模式视为现代社会的纯粹模式,并由之定义出价值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分形(fractal)阶段,这当然也是一种比喻说法。(19) 这个阶段,“即价值之不规则破碎的(或病毒的、辐射的)阶段,根本没有任何参照点,价值不参照任何事物而只根据纯粹相邻性向四面八方辐射,占据全部的空隙。在不规则破碎阶段上,不再有等价性,无论自然的还是一般的。更确切地说,今天不复存在价值规律,而只有一种价值的流行、一般性病毒转移和偶然的增殖或弥散。实际上,我们真的不应该再谈论什么‘价值’,因为这种蔓延或链式反应使所有的评价都不再可能。再一次,这使我们想到微观物理学:不可能在美与丑、真与假、好与坏之间做出评价,这就好像计算一个粒子的速度和位置那样。好不再是坏的对立面,今天我们不能把什么东西绘制到地图上,或者根据纵横坐标来分析它们。就如每个粒子都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每种价值或价值的碎片也都从模拟世界中断断续续地发散出来,然后沿着一种弯曲的路线消失在空洞中,那种路线只是在极少情况下才与其他类似的路线发生交叉。这就是分形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fractal)——并因此是我们文化的当前模式”[8]6。到这种程度,对现实的判断可以说终止了。因为,尽管我们还可以说很多,但不会有更新的。在这个阶段,鲍德里亚的批判怎么都行了。甚至,象征都失去了暴力。正如今天艺术所表明的那样:在此背景下,我们今天能够做的只是模仿放纵,模仿解放。至此,我们似乎也可以不必认真对待鲍德里亚了,就如其《终结之幻象》等著作表明的那样:对现实的判决也只是一种语言游戏。他似乎留下了一种深刻的悖论:揭示了代码统治之事实,但是却只是以话语的方式宣布话语之终结,而从根本上回避了对代码统治之机制的挑战,从而不仅没有走出自己批判的逻辑,而且在更深层次上使批判成为一种自指的言语活动。
在确切的意义上,如果继续把鲍德里亚视为一场理论上的革命,从上面的讨论看,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这种革命都是对话语的话语革命。这种话语革命并非与现实无关,其意义必须在结构主义语境中来理解。因为,在那种语境中,话语不是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与社会存在相对的社会意识,相反,它是社会存在得以结构的原则,就是社会结构本身。在鲍德里亚以及巴特、拉康等人看来,现代社会本身就是形式的,即结构压倒了实体。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应,需要在更大的理论空间中进行。本文的基本目标不在于此,我们希望强调的是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无论如何极端与难以理解,鲍德里亚的批判都是后68时代形成的一种新激进主义,它与整个激进主义传统有着不解的联系。尽管在其先前出现的批判家极少有逃出其批判之锋的,但他却在《忘却福柯》一文中非常直截了当地指出自己战略与传统批判理论终结之间的关系。他说:“全部唯物主义的批判思想都只是企图以阻止资本、冻结其经济和政治合理性的要素。资本的‘镜像阶段’被辩证法这个妖妇所欺骗。当然,在这一点上,唯物主义思维同样也冻结了全部在这个阶段上抵抗资本的东西。……一旦批判思想的保守障碍被克服,死对头们便最终面对面。不只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冲突(尽管被一个单一的巨大的社会化模式所支配),而且形式也处于敌对之中——资本的形式、牺牲的形式、价值形式和挑战形式——伴随着社会死亡之危险。必须把社会自身看作是一种拟真模式和要推翻的形式,因为它是由资本粗暴地决定并因此由批判思想理想化的战略性价值形式。”[9]52 如果说鲍德里亚最终采取了与社会(权力统治策略)一致的策略,就如《黑客帝国》之三“革命”中Neo(以及Oracle)所认识并实际所为的那样,那么这种认识并不只是因为迄今为止的革命逻辑的失败,而是别有原委。拉康为这种原因提供了解释。借由拉康,人们将看到:权力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位置。这一点正是另一个比马克思更激进的齐泽克的全部出发点,与鲍德里亚不同的是,齐泽克以一种矛盾修辞法(这种修辞法正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策略)把“不可能性”作为一个正面目标从而摆出一副真诚的革命家形象,反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姿态。在鲍德里亚看来,“权力背后,或者正是权力和生产的中心,是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在今天给予它们一点微弱的实在迹象。如果不颠覆它们、取消它们和引诱它们,它们就绝不会成为现实”[9]45。从这里出发,他把全部传统的真诚性革命家都作为残余给打发掉了,代之以对斯多葛学派的赞扬。他与齐泽克的不同,正如人本主义者萨特与布洛赫不同,两个前者都以“绝望”为出发点,而两个后者则把“希望”本体论化,但实质上他们不又都构成一种“颠倒的两面性”吗?反人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不也是一种“颠倒的两面性”吗?所以,在此,真正的问题并非辨别孰是孰非而是理解从萨特/布洛赫这种人本主义的两面性到鲍德里亚/齐泽克这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两面性的过渡,鲍德里亚本人的知识路径精确地演示了这种过渡。
第二,鲍德里亚本人的转变无疑预示了激进理论的一种转向,前面阐明了这种转变的偶然与必然,但我们还需要问:从一个激情的批判家走向一个无情的叙述者,其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鲍德里亚自己多次解释过(例如在《交流的狂喜》和《冷回忆Ⅱ》中)这个问题。在《交流的狂喜》中,他强调:“世界正变得无情,并且,越是无情,它似乎就越来越接近于一种超人类的事件、在我们不断增长的不耐烦中反映出来的例外结尾。不只是我们,而且历史和事件,似乎都是渴望不耐烦和无情之复杂结果的牺牲品。无情的或不耐烦的并不是我。世界自身似乎渴望加速、加剧自身的烦躁,失去了对物之迟缓的耐心,而同时陷入了无情。在超越或反思它的过程中给世界以意义的,不再是我们”[2]94。有趣的是,这种辩护恰恰与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完全一致。比如,在谈到李嘉图的时候,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句子!”[10]94 并且他在《资本论》中强调自己不用玫瑰色来描述资本家和工人,是出于同一逻辑。当然,这里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争论的问题:这一逻辑在马克思、鲍德里亚那里出现的时候,是否仅仅一个托词?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否已经如此?
在《冷记忆Ⅱ》中,他从另一个角度为自己的策略选择作了更有趣的解释,因涉及对今天理论意义的看法,而较之上一个问题显然又大大深化了一步。他说:“所有的情境都是由对象、片断、在场的着迷而绝非由观念产生的。无处不产生观念,但它们是围绕客观的好奇、物质的起源和细节自我组织起来的。分析,就像魔术那样,发射出无穷小的能量。”[11]2 在此,他以类似结构主义的逻辑加上某种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论调陈述了一种独特的个体体验(《冷记忆》首先是一种个人体验的记录),同时亦精确地描述了他的写作战略的基本原因。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说,鲍德里亚思想历程中的逻辑转换并非由在其出发点上选择的支撑框架(如巴特、列斐伏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等人思想的复杂纠合)决定的自然深化,而是与其世界体验始终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亦看到,在其全部现实描述中都贯穿着一种深刻的异化体验,摆脱这种异化体验始终是他的理论目标。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始终使用异化这个术语。
四、“重复”,或能否从鲍德里亚到马克思?
革命成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强迫重复”,这当然是不可理喻的。不过,从激进理论的发展来看,我们又必须说:尽管战略是致命的,但并非荒谬的。这正是需要我们同情和深思之处。我们面对这种策略,并非试图赞扬其合理性,而只是出于理解它对批判理论自身提出的问题。
鲍德里亚不可能不遇到自己的难题,相反,他的每一步理论进展都是围绕自身理论难题发展出来的。因此,他说,革命将是象征的,或者将根本什么都不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主导“象征”交换中的是主体自身而非物,那么,在这种逻辑中,形式上的(量上的)等价性不仅不存在,而且形式本身不能作为目标出现。这一逻辑贯穿于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之中。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我们就不能通过对马克思的批评来拯救马克思主义之资本主义批判事业。
复杂的是,在揭示必须消灭形式才能实现内容这一主体诞生路径的时候,黑格尔传统的辩证法实际指向的是未来可能性——即一个等待着生成的全新主体,这也正是其突出强调“辩证扬弃”的基本原因,但是在今天这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在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中,我们早已听到了那一声叹息。当鲍德里亚从“68幻觉”中走出来的时候,他不是那声叹息的回声吗?(20) 特别是,当他进一步指认现代社会是形式战胜内容的时候(这也正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真正的问题就不是采取何种形式拯救马克思主义(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是我们能够从拯救行动中将获得什么。后一问题决定着前一问题。把“象征”交换作为一种策略行动托出水面的,正是在“象征”中蕴含的东西,这是一种永远无法被消灭的证明主体自身的欲望。在象征交换中被消灭的物,即在商品交换中相继出现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及符号价值,正是纠缠并威胁着主体的外部对象——黑格尔和马克思旨在打破的形式。所以,我们看到,即使鲍德里亚后来发展出“拟像”等一系列新概念来代替马克思的批判,他实际上仍然保留了后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判断。在这一点上,他以矛盾的方式获得了“象征交换=死亡”这种奇怪的平衡。在他看来,首先,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即现代资本主义之生命/死亡、主体/客体、能指/所指、男性/女性之间二元对立消失了;其次,革命本身不再如马尔库塞所批判的那样,表现为“在旧有链条破裂处锁上一把新锁”,而是通过彻底的主动的“强迫重复”来实现的欲望的复归(没有异化就没有复归)。在前一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是一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后一意义上,他又是一位彻底的前现代主义者。这种矛盾似乎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鲍德里亚反复解释过,自己是在一种螺旋运动中不断深化对现代社会内在对立揭示的,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学、生产、代码、体系、模拟、病毒;另一方面是夸富宴、耗费、牺牲、死亡、女性、诱惑以及最终死亡宿命。他对原始社会之深度的依赖正在于它实际上作为内容支撑着整个形式的批判。鲍德里亚实际上只是在理论内部维持着一种彻底性,他的意义不会超出这一点,因为世界从来都不是按照理论运行的。但,即使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他保持一份敬意,毕竟他以一种虔诚积极地探索着这个日益成问题的世界。让我们再一次倾听他的呐喊:“如果世界是毁灭性的,那让我们比它更加具有毁灭性。如果它是无情,那就让我们变得更加无情。我们必须战胜世界,通过一种至少与世界一样的无情来诱惑它。”[2]101
[收稿日期]2007-12-18
注释:
① 鲍德里亚曾用这个词来描述消费社会中人们面对汽车等消费品时的感觉。参阅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9页。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西语语境中,包括鲍德里亚、德里达等人在内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诞生的大师之所以往往以“妖怪”(médusée原来便是一个妖怪的名字)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与其理论之博采众长特点直接相关。鲍德里亚在其中最甚,他不仅方便地运用了许多本身在今天存在着理解困难和争论的理论观点,如,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那样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德波、巴特、拉康、福柯、巴塔耶、索绪尔、莫斯等人的观点在其不同理解阶段都起过作用,而且他最擅长“过河拆桥”,这些人也几乎都没有逃过他的批判。以此看来,鲍德里亚属于何种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多大理论意义。在汉语语境中,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因为,当我们按照传统一般研究的做法首先去问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时,恰恰不是打开了而是阻止了对话之门。在这一背景下,清理他的知识谱系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不过,如果抬高这种工作,把焦点集中于他受到了哪些理论思潮的影响以及他究竟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些理论资源,而不直接面对其为什么如此“出尔反尔”这个问题,我们亦不能摆脱那种奇异的“综合”所产生的理论眩晕而忽视了真正问题。实际上,鲍德里亚从来都不曾为既有理论(无论是来自他人的还是自己达到的)所累而始终试图把面对的问题追至底部。这不仅造成其身份离散的外部特征,亦形成其最终以碎片来对抗体系的知识恐怖主义逻辑。在此意义上,我们追溯其话语逻辑变迁,始终不是为了理解鲍德里亚本人,而是理解我们必须面对的消费社会和资本逻辑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它对鲍德里亚的折磨在何种意义上见证了既有理论的不足,反过来,鲍德里亚的炼狱经历是否有助于减缓我们经历炼狱之苦痛?
② “我们今天正在整体的生产系统层面上体验本雅明在法西斯主义中发现的那种政治的眩晕和美学的反常快乐,我们正在体验一种非政治化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眩晕——对事物进行理性管理的眩晕,目的性盲目狂热的眩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③ 参阅其对涂鸦例子的评论。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④ 参阅Douglas Kellner(ed),Baudrillard:Critical Reader.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1994,p12.鲍德里亚认为,在模拟逻辑中,“万物都躲避自身,万物都蔑视自身的真相”,因此。“真理的话语完全是不可能的”。(Jean Baudrillard,The Transparency of Evil: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Verso,1993,p73.)在这样的背景下,象征暴力是对模拟逻辑的真正挑战。
⑤ 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我们根本的命运不是“存在和生存”而是“露面和消失”。Jean Baudrillard,Fatal Strategies.New York:Semiotext(e),1990,p175.
⑥ “消失”在鲍德里亚那里并非传统“死亡”之意,相反,在现代社会,“通过增殖或污染、饱和或透明,或者因为衰减或灭绝,再或作为模仿流行病的结果,作为它们变成拟象之次级存在的结果,物才消失”。因此,他将之称为“致命的消失模式”。(Jean Baudrillard,The Transparency of Evil: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Verso,1993,p4.)与这种消失模式对应的战略是“致命的战略”。
⑦ 这种完美性并非指体系自身走到了尽头,相反,它表现为体系成为反体系目标的实现。鲍德里亚称之为“放纵之后”(after the orgy),这种“纵欲之后”是“现代性在我们身上的爆炸时刻”,这也就是他所言的“超—现实”,即过度的现实。在他看来,在模拟逻辑中,政治解放、性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破坏力的解放、妇女的解放、儿童的解放、无意识驱力的解放、艺术的解放等等全部解放都在表面上实现了,这种放纵之后,“我们今天能够做的是模仿放纵,模仿解放”。但是,“这种模仿只是假装沿着同一方向继续加速前进,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在一个空洞之中加速。因为,所有解放的目标都已落到我们身后,纠缠和困扰我们的东西都因此跑到了结果之前。拟真姿态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被迫对所有的剧本作出应答,正因为它们全部已经发生,无论实际地还是潜在地。全部的乌托邦都已实现,在其中,我们悖论性地继续生存,就好像它们并不存在。但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并且因此我们不再怀有实现它们的希望,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无限的模仿来‘过度地实现’(hyper- realize)它们。”(Jean Baudrillard,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Verso,1993.p3-4.)
⑧ 林志明对鲍德里亚与列斐伏尔之间的关系有详细的说明(参阅《物体系》之译后记)。值得进一步强调的是,鲍德里亚以《物体系》—《消费社会》揭开自己理论帷幕的时候,他与列斐伏尔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不只是这一点——他的理论方向在后者的预见之中,而且可以说《消费社会》旨在建构的那种消费社会学只是列斐伏尔长期而庞大的日常生活批判计划的一个方面。当然,他将自己的理论眼光更集中地锁定在列斐伏尔不愿意简单接受的消费社会之社会学探究之上的时候,最终也瓦解了后者那种不能实现的计划。但是,鲍德里亚的知识恐怖主义确实可以理解为列斐伏尔解读日常生活之恐怖主义的“永远的文化革命”的特殊形式,它义无反顾地走向后者防范的意义的零度,形成以恐怖主义对抗恐怖主义的理论思路。这种思路实际上亦是以结构反对结构,从而改变“结构不上街”之保守性。相对列斐伏尔那种持久的人本主义文化革命诉求来说,这是“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
⑨ 参阅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5-46页。译文有改动,“皮尔丹人颅骨”是一桩典型的学术造假案。英国考古学家陶逊称他于1911年在英国Sussex的Piltdown发现史前人化石,称“皮尔丹人”,后经鉴定系纯属伪造。
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鲍德里亚只是借用了一桩伪科学案件,但他所描述的关于“实在”消失的这种后现代主调恰恰是在由索卡尔揭起的“科学大战”中的争论焦点。因此,可以恰当地说,鲍德里亚在此仍然以一种隐喻回应了这场大战。只是他以80年代以来一贯的“知识恐怖主义”策略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论敌的目光和武器之外而专注于自己真正进攻的空白地形。
(11) 就如其评论的阿多诺那样,“狂喜宁愿自己破坏自身而不是看到它的概念的实现”。Cool Memories II.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84.
(12) 在假模假样的“冷静的回忆”中,他自己描述了这些身份。唯一改动的地方是,我只是把“横越各界面”(transversal)的潜台词“无所不能”给直接表述出来了,称其为TOE(Theory of Everything)分子。当然,鲍德里亚本人并不想把自己归入任何一个愿意接纳其为成员的俱乐部。参阅Cool Memories II.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83.
(13) 在定位“新资本主义”时,列斐伏尔逐一反驳了“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丰裕社会”、“休闲社会”、“消费社会”等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命名,而主张“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以期同时把握其理性特征(官僚性的)、组织原则(消费而非生产)及其基础(日常生活)。(Henri Lefeb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m World.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1971,p45-60.
(14) 这正是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结论部分所直接感觉到的难题。进一步,也正是这个难题推动着他随后关于符号政治经济批判的探索。这正是象征交换的基本逻辑与含义,亦是其面临的最深刻难题。在《消费社会》中,由于正面建构消费社会学理论的需要,鲍德里亚引入了莫斯的礼物(象征交换)逻辑,以此作为参照来说明现代消费是与之不同的逻辑,但他的全部批判却并非从象征交换出发的,他的批判主调仍然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的。这是因为,消费本身涉及的只是耗费或消灭,由它建立起来的本体论始终是自然水平上的循环,从而否定全部的人类文化创造。在接下来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也只是试图从形式上建立一种符号学的批判。只是在其后,在几乎全部的批判都流产了这个基本事实面前,他才把象征暴力作为最后的赌注。
(15) 前者把精神分析开辟的从意义角度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客观主义理论路线普及为常识,拉康及其他以符号或语言为中心的全部社会理论无不如此;后者以莫斯为突出代表的人类学理论为从象征交换角度展开对资产阶级话语批判奠定了新的基础。正如萨林斯等人的人类学所显示的那样,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相通的。因为,它们都把文化视为一种客观的意义构造(construction),即象征。这种从象征——客观意义结构——角度来解释社会文化和建构新型政治学的努力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普遍冲动,鲍德里亚、哈贝马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人也不例外,只是他们采取了复杂的理论变体。之所以形成这种普遍冲动,与马克思主义之经济决定论及其对之进行反驳的存在主义这两种主导思潮的失败直接相关。
(16) 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们可以提出许多不同意见,但争论显然不会有太大意义。因此,我们不会跟着他胡搅蛮缠,而把焦点放在那些区分背后的社会或文化定义问题上。这是真正的问题。鲍德里亚以“一般人类学”轻描淡写地打发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其后文本中始终没有给予正面讨论。说它是真正的问题,原因便在于,它正是鲍德里亚全部批判得以发生的范围,也是他所批判的假想的现实。说这个问题是文化定义问题,只是借助萨林斯——这位与鲍德里亚惺惺相惜的人类学家——的提法,因为他更清晰地把象征交换问题定义为文化(意义理性)问题。当然,在结构主义语境中,文化(理性)问题即是历史或社会问题,其焦点在于社会得以结构的框架,或用更传统的方式来说,即是关于社会历史本体的界定。
(17) 从鲍德里亚的理论发展看,《物体系》和《消费社会》讨论的是一种赝品的结构,这种赝品即符号。当然,这是在巴特水平上来讨论的,其中《物体系》是对体系本身的结构描述,《消费社会》是对这一结构的动因进行分析。在鲍德里亚看来,尽管在符号层面上的消费是一种元消费(meta consumption),但它亦是对社会本质的模拟(simulate the social essence)。只是,从异化的角度来说,符号消费较之先前的社会异化更深一步了,即达及彻底程度。这是因为,消费成为一种展现现代商品社会结构的元消费,即成为一个其本质功能在于维持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的体系,不再与个体的需要、欲望、目的有关。所以,借助于拉康的逻辑,鲍德里亚强调消费是围绕缺失(或空洞)运转的体系之自我展现活动,它展现的只是完全相同的东西之不同变体(the alterity of the selfsame),那个the selfsame也就是缺失(manque),那些the alterity则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差异(différence)。我们看到,鲍德里亚实际上借由巴特、拉康等人重述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思想。问题也出在这里,如果马尔库塞已经达及对消费社会本身逻辑的描述,那《消费社会》就不可能在逻辑上超出马尔库塞,并且更重要的,它也同样面临由1968年“革命”失败提出的批评。这正是《生产之镜》需要解决的问题。
(18) 今天,消费——如果不是在庸俗经济学给定的那种意义上讲——定义的恰恰是商品被作为一种符号、符号价值直接生产,以及符号(文化)被作为商品生产的阶段。Jean Baud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elos Press,1981,p147.
(19) “分形(fractal)”来自几何学。鲍德里亚大量地挪用科学术语或专业词汇,并由此形成特殊的比喻类型。一般比喻是用我们熟悉的东西来说明不熟悉的东西,但他总是相反,用一般读者不熟悉的专业术语来比喻我们熟悉的东西。由此,造成某种阅读的震惊,造成某种眩晕,从而达到他的战略目标。例如,他“政治晶体管机器的集成电路中的最低限度的通量”来比喻自由,用“非勒斯汇兑本位制”来比喻父权制等。
(20) “68”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并不需要证明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在1968年5月前夕出版《批判理论》文集的霍克海默在序言中说,“好心的人,想从批判理论中得出一些结论,以便采取革命政治行动。然而,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方法去促成这一点。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是: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责任有深刻的洞察。在变化繁复的历史环境下,不假思索地和教条地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实践,只能有助于批判理论旨在谴责的那个过程。这是那些严肃对待批判理论的人,包括同我一道发展它的阿多诺在内,都同意的”。参阅《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序言。我们不能说鲍德里亚是从这里入手的,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霍克海默在这里表达的逻辑和情绪在他那里得到了令人震惊的延续和深化。
标签:鲍德里亚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列斐伏尔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革命论文; 逻辑符号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象征交换与死亡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生产之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