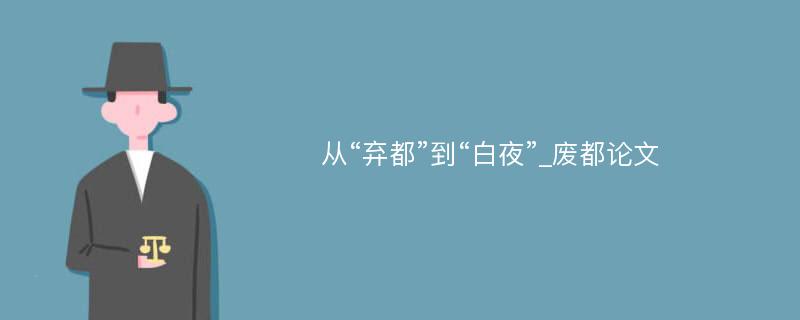
从《废都》到《白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夜论文,废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
在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中,贾平凹是一个文化姿态异常引人注目的成就卓然的作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作家主要不是靠作品来展示自己的文化立场,而是直接介入学术界的文化论争之中,以文化评论来制造轰动效应,或者发表一些远远不能说精湛的创作谈之类的文字,来树立自己的“杞人”形象。喋喋不休的话语,浮躁的心理,俱暴露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内养”之不足,气浮言浅。
相比之下,贾平凹可以说是安于职守,他完全是以一部部作品来表明自己的文化态度,他的文化心态,潜藏在他的作品之中,属于潜话语系统,而不是显话语系统,然而底蕴可能更加丰富些。反思世纪之交的文学,建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精神,贾平凹及其小说创作足以构成一个话题。无论对于哪一个杰出的作家及其作品,一味的赞扬终属赏析,简单的阐释无关痛痒,而批判的审视,才能发现其价值。这里作的讨论,虽然各人所见或有偏执,然共同的特点是不想隐讳什么。
90年代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年代。从文学创作上来说,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人——晚生代的进入写作。他们的写作——对于历史的逃亡与游戏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文学现象。可是,贾平凹写作《废都》的那一年,中国大地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文化颓败”的号咷之声不绝于耳。贾平凹在《废都》的“后记”里叙述了《废都》写作时的个人苦痛与困境。然而,仅仅他个人的痛苦与困境却并不能成为《废都》。而是整个时代鬼哭狼嚎的浓重氛围与巨大挤压产生了这部挽歌式的长篇小说。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践踏、折磨和侮辱的时刻,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惊慌失措,感觉到失去了生存的重量。他们的苦难经历恰好把他们自己推向了以色列先知般的神圣、光荣和崇高的位置,陶醉于一种受虐的快慰之情里。因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中,这个身份不明而被历史巨人一次又一次地戏弄的阶级形成了最为强烈,也最具有本质特点的性格——自虐与自恋。而今天,文化的崩溃和历史的失重使他们感觉到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足轻重与被弃之感。贾平凹呕心沥血地写作的《废都》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们——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尽管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这一曲传统文人的心灵挽歌已经失去了辉煌壮丽的历史叙事与装饰,甚至几乎连张爱玲所说的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也没有留下。它的节拍只是琐琐屑屑地敲打、铺张和伸缩,低徊于性爱的圈套之内。甚至也没有色彩丰富的情受,只剩下一种肉欲的恣放与失落,从而成为一种烂熟的末世的无名的悲哀。它不是象《红楼梦》一样可以吟唱的悲剧,而是《金瓶梅》式的无法言传的透骨悲凉。
在“《废都》热”——《废都》的阅读与评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对于《废都》的二度写作——两种完全不同的“《废都》滋味”。一种是庄之蝶的同代人对《废都》感伤的抚摸,一种是晚生代对它的愤怒的呵斥,以至认作是“一部嫖妓小说”。晚生代看到的是“《废都》热”中的浓厚的消费性与商业性,看到的是《废都》中鸳鸯蝴蝶的主题与圈套。而庄之蝶的同代人在对它的抚摸性阅读中深刻地体味到性爱死结后面强烈的挫折感、失败感、末世感和没落感,一种绵绵无尽的哀伤惨痛,在淋漓尽致的烂熟的肉欲铺陈后面隐含的精神颓败的命运感。萧夏林以“废都废谁”来标名《废都》的一部评论集,用一个最为简短的诘问语句揭示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在这部小说里陷落的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座城市,而是一个时代,是文化英雄的失败。他让一个最具有自恋性格的文化英雄——西京四大名人中的作家庄之蝶来面对历史所带给他的无可回避的破败和荒芜。
女性主义批评在《废都》中读出的是男性文化,看到的是对于女性的露骨玩弄。然而,她们没有看到庄之蝶在文化和权力的颓败中的紧张与焦虑,他脱尽了历史的衣裳,通过性的失败来淋漓尽致地渲泄他的失败之感。在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性上暴露了“名人”庄之蝶所遭受的致命挫折和彻底失败。他和景雪荫的往日旧情引起了一场纠缠不断的官司,为了消弥这场官司他将柳月作为一次交易送给了市长的残废儿子,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唐宛儿从他的身边被抢夺而去。因此,他和唐宛儿幽会的地方就称作“求缺屋”。西京四大名人之一的庄之蝶并不是由女人来衬托他的权力与光荣,而是经过对于他的女人的剥夺表现了他的残败与毁灭。无疑,这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悲剧之悲剧”,而只是无名的焦虑与悲怆。在某种意义上说,《废都》和激流岛上的“顾城事件”具有相同的意义。庄之蝶最终无法在性的梦幻王国里扮演着英雄的角色。他由西京的名人和被崇拜者变成了一个弃儿。
《废都》和《白夜》的书名都有着明显的寓意。废都西京是荒败了的皇城,是已经被取代了的权力中心。在《白夜》一开始,作者满怀惆怅地描写“废都”:“如果是两千年前,城墙上插满了猎猎的旗子,站着盔甲铁矛的兵士,日近暮色,粼粼水波的城河那边有人大声吆喝,开门的人发束高梳,穿了印有白色‘城卒’的短服,慢慢地摇动了盘着吊桥铁索的辘轳,两辆或三辆并排的车马开进来,铜铃喤喤,马蹄声脆,是何等气派!今日呢,白天里自行车和汽车在街上争抢路面,人行道上到处是卖服装,家具、珠宝、水果和各种各样小吃的摊位。戴着脏兮兮口罩的清洁工,挥着扫帚,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直扫得尘土飞扬”。贾平凹流露了对于现代性城市明显的反感与厌恶。在这种城市里,失去了令人神往的威严与秩序,只有盲目混乱、空虚荒芜的欲望。因此,当《白夜》的主人公夜郎面对这个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废都”时便产生了一种荒芜之感。“夜郎想到这里,一时万念复空,感觉到了头发、眉毛、胡须、身上的汗茸都变成了荒草,‘叭叭’地拔着节往上长,而且那四肢也开始竹鞭一样地伸延,一直到了尽梢就分开五个叉,又如须根。荒芜了,一切都荒芜了。”“废都”象征了秩序,权力和文化的颓败,在这种颓败中,夜郎感到古老而又空虚。他被这种颓败抽空了,无机化了,退化成为了植物。这种颓败和退化使庄之蝶内心积聚了巨大的紧张、压力、焦虑、失败和悲哀。
在《废都》的结尾,这种悲哀在一个象征中完成了最凝炼的表述。“废都”将要举办一个文化节,选择了大熊猫作为节徽,作家庄之蝶受命组织宣传材料。“庄之蝶最反感的就是大熊猫,它虽然在世上稀有,但那蠢笨、懒惰,幼稚,尤其那甜腻腻可笑的模样,怎么能象征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的文化呢?庄之蝶掷笔不改了。不改了,却又想,或许大熊猫作节徽是合适的吧,这个废都是活该这个大熊猫来象征了!”大熊猫不仅象征着在历史中被遗弃的文化古都,而且象征着在历史中被遗弃的文化英雄。他们象大熊猫一样稀少珍贵,也象大熊猫一样脆弱可悲。他们失去了现代社会中生存竞争的能力,甚至他们的生殖能力也可悲地退化了。在西京城里被当作名人供奉起来的自恋自怜的庄之蝶不正象大熊猫一样无奈地面对自然淘汰的命运吗?他们无法适应生存,只能悲怆地等待历史的毁灭。《废都》以庄之蝶的生命溃败和毁灭而结束。小说最后写道:“候车室门外,拉着铁轱辘架子车的老头正站在那以千百盆花草组装的一个大熊猫下,在喊:‘破烂喽——!破烂喽——!承包破烂喽——!’”庄之蝶没有丝毫悲壮、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只剩下大熊猫这个现代文明中的古老遗迹与怪物的象征物。老头的声音在书中不断地重复,就象一个主题在反复演奏。因此,《废都》完成了对庄之蝶及其文化英雄们无名的悲哀的历史表述,也是贾平凹献给他们以及自身的一曲悲怆的葬歌。而庄之蝶这个出自于《庄子》中的典故,在这里更主要地是暗示了作品深处的幻灭之感。说明了他对于历史以及自身的无法把把握与确证。
《废都》与《白夜》都是城市生活题材的小说。然而。贾平凹对于城市以及现代文明有着明显的反感。当贾平凹从《废都》的文化圈以及悲怆与自戕中挣扎出来面对市井俗世的城市之后,就有了《白夜》。“白夜”——一个既非白日也非黑夜的充满悖论无以名之的东西。由魔方、面具、霓红灯和化妆术组构而成的城市、人鬼不分,真假难辨,失去了历史,也没有了真实,没有了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城市就是抹去了白天和黑夜的界线的颠倒混乱的白夜。
在《废都》中,庄子蝶在徒劳地追求着尊严与真实,追求着完整的叙述。他是一个典型的自恋者。《废都》最终不仅是对庄之蝶的凭吊,也是对“真实”的否定。牛月清在知道了庄子蝶对他的背弃之后感觉到了“真实”的崩溃。“庄子蝶与唐宛儿的事发生后,她感到痛苦的是自己最爱的丈夫竟会这样;而现在,出了家的慧明也打胎,这世上还有什么是真的,还有什么让人可相信、可崇拜、可信仰呢?”于是,牛月清也终于认同了现代都市的生活,化妆美容,使她自己的母亲也认不出她来了。老太太惊道:“‘这不整个儿不是我女儿了?’从此就整日唠唠叨叨,说女儿不是她的女儿了,是假的。夜里睡下了,还要用手来摸摸牛月清的眉毛,鼻子和下巴,于是就怀疑了一切,今日说家里的电视不是原来的电视,是被人换了假的,明日又说锅不是从前的锅,谁也换了假的;凡是来家的亲戚邻居又总不相信是真正的亲戚邻居。后来就说她是不是她,逼着问牛月清。”化妆术是城市文明的代表。最具有戏剧性效果的化妆术是现代性和城市经验的核心内容。在《废都》里,柳月通过化妆术来涂改自己的农村身份;在《白夜》里,颜铭通过美容来修改自己的面目。城市化妆术改变了人们的物质世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甚至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感觉,摧毁了白天和黑夜的真实感觉,打乱了白天和黑夜的固定秩序。城市化妆术对于人们的心灵造成了奇异的震撼。在以化妆术为核心经验的变幻不定的城市里,一切固定的、永恒的、本质的和真实的东西都被破坏了。这给“后主们”带来了无限快乐的一切却使贾平凹感到无限的怅惆与悲哀。他甚至从不正面表现城市的生活经验,他恨城市。
然而,夜郎毕竟不同于庄之蝶,不是那个自恋性的男人,他有着夜的性格的一面。夜郎一开始就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小说这样描写他和颜铭第一次作爱之后的复杂心态。夜郎“醒来满窗阳光。穿衣起来,一夜间长成了一个丈夫。他在墙上的日历牌上寻查着这个日子。就想起颜铭不让他动的那块毛巾。毛巾是那时垫在床上的,从床下的盆里拉出来,红红的染了一片。夜郎并没有把毛巾放回盆里,却用报纸包了要带走,这是一个男人的得意之作,更是一个纯真处女的证明,他将要在他那个借居的大杂院里当院晾出,宣布在这个城市里,他什么也没有了,但他拥有了爱情,一切都肮脏了,而他的女人是干净的!”而当他发现毛巾上的血是颜铭以鱼泡灌红木以充处女之后,他因此“大失过望,极度悲哀”。于是他在这个城市里被抽掉了最后一点真实的感觉,成为无根无蒂,无以附着的状态。他多少摆脱了庄之蝶的自怜自恋的悲怆,多少带着夜的邪恶,成为一个有些恶作剧的喜剧演员。在《白夜》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某种移位变形,多少摆脱了《废都》宣叙调性的自叙性与感伤性。然而《白夜》同样表现了贾平凹内心深处无法化解的紧张、焦虑与忧愤。不论是对夜郎恶作剧的描写,以《精卫填海》作为结束,还是宽哥这个人物的塑造,都表现了他内在的压力与紧张。警察身份的宽哥在《白夜》里是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一个正直善良、尽职尽责的警察在维护合理秩序和履行正常职责之中的不合时宜和屡遭打击。贾平凹意在通过警察宽哥这个现代文明的象征来表现当代社会的悖谬感。
贾平凹努力通过写作去接近历史,甚至成为一种历史写作。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废都》中对于谣曲——这种中国社会历史中最具有神秘力量和阐释能力的语言的不断引用中。借用谣曲是中国历史写作中一种重要的策略。可是,《白夜》却以“再生人”的出现开始,再生人留下了一支曲子后来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贾平凹不仅在写作历史,而且企图抽象历史。也就是说,贾平凹企图表达他的某种“历史哲学”。换一种说法,贾平凹的创作实际上是在追求成为一种“寓言”。——尽管今天的理论批评家已经订下了规则,把我们的时代规定为“后寓言时代”了。
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一个非常暖昧的词语——“世纪”就开始象一首格律诗中的韵脚一样反复出现,有时叫做“世纪末”,有时却又下一转叫做什么“世纪之交”。尽管中国进入“世纪”还不到一个世纪,然而却又好象我们在世纪的轮盘里早已经转了几个轮回似的。不同的文化对于历史有不同的感受方式,一种特定的文化给人们带来特定的想象方式。由此,我知道了在五四的时候胡适等人为什么要打倒“名教”。我也因此知道了名教和文化对于人类的心灵生活有多大的塑造能力。构成贾平凹的生活世界和历史想象的是另一套符码:古镜古竽、禅佛卦卜、才子佳人,琴棋书画剑。是另一种历史另一种时空。在《白夜》的结尾,虞白要送给夜郎的《坐佛图》就体现了贾平凹的某种“哲学”。
“有人生了烦恼,去远方求佛,走呀走呀的,已经水尽粮绝将要死了,还寻不到佛。烦恼愈发浓重,又浮躁起来,就坐在一棵枯树下开始骂佛。这一骂,他成了佛。
三百年后,即冬季的一个白夜,□□徒步走过一个山脚,看见这棵树,枯身有洞,秃枝坚硬,树下有一块黑石,苔斑如钱。□□很累,卧于石上歇息,顿觉心旷神怡。从此秘而不宣,时常来卧。
再后,□□坐于椅,坐于墩,坐于厕,坐于椎,皆能身静思安。”贾平凹深深地沉浸于一种古老神秘的文化之中,企图以此找寻到抵挡现代文明混乱的“白夜”的智慧。我的一位朋友说,在贾平凹的小说里有一股鬼气,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半妖半仙的。贾平凹在古老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长久修炼已经“得道成仙”,因此构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构成了他自己的一个世界。
贾平凹生活在他所选择的文化中。他生活在“废都”深处,他反感“白夜”——现代性的城市,它的丑恶与混乱,变幻与虚伪。尽管他感觉到了城市气息的腐蚀,但是他抵抗城市——在他的小说中回避对于城市的体验。正如孟云房评论庄之蝶的:“别看庄之蝶在这个城市里几十年了,但他并没有城市现代思维,还整个价的乡下人意识。”贾平凹的小说在回避立交桥的现代景观的时候,几乎必然地转身面对古老的目连戏与民俗,去寻找另一种意味。同张承志一样,贾平凹也以他自己的“内力”,以他自己的文化想象方式来抵抗现代文明,并以此来化解他所承受的现代的丑陋、混乱、紧张与焦虑,将它们化作挽歌悠唱。
标签:废都论文; 白夜论文; 贾平凹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