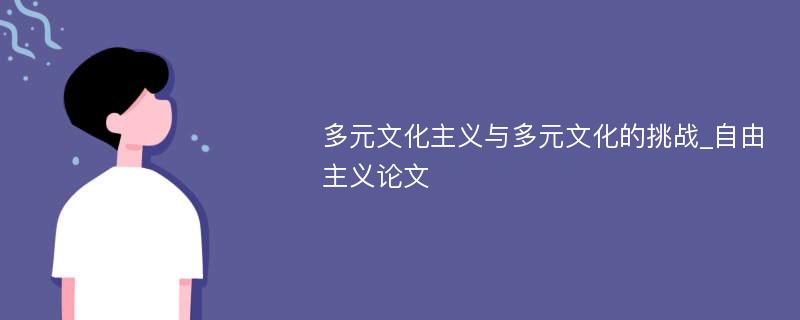
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广泛讨论的多元主义挑战的焦点问题。塞缪尔·亨廷顿对这一挑战进行了著名的总结,即“文明的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某些宗教、民族、种族之间,或者更为宽泛地说,那些有着不同文明背景的共同体(community)之间,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对于许多政治分析家来讲,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文化冲突是发生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用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的话来说,就是“伊斯兰圣战与麦当劳世界”之间的冲突。因此,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对话与宽容的可能性以及不同共同体如何才能和谐相处的问题,是当今多元文化主义研讨的核心内容。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对多元主义构成了挑战,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多元主义的挑战。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的巨大政治挑战涉及的是不同共同体之间多元主义的可能性,或者可称之为外部多元主义(external pluralism),那么多元文化主义自身还面临着共同体内部多元主义可能性的问题,或者可称之为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不同的共同体不仅会面临外部的冲突,也要应对内部冲突引发的分裂的挑战。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想家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与抨击,他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对那些以共同体价值观和理想为名压制政治反抗和离经叛道者以及使妇女屈从于男权的行为持宽容态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其合法化了。保罗·伯曼(Paul Berman)谴责了多元文化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采取宽容甚至辩护的立场。阿雅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指责西方国家借所谓的文化多样性之名对穆斯林文化中某些残酷的风俗——比如威胁到穆斯林妇女自由和生活的“贞洁文化”——采取了有意忽略的态度。 实际上,多元文化理论绝不想通过为专制的文化惯例辩护来达到同基本人权和个体自由大唱反调的目的。多元文化主义最初源于德国的浪漫主义,被构想为个体从与启蒙主义哲学相悖的思想束缚下获得解放,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将个体视为真实存在的人,而非纯粹理性意义上的人,他们有着特定的心理构成和社会构成。多元文化主义想要接触到人类的各种经验,“重视那些使人之所以成为人或者至少使人能够拥有人的生活的情感、道义和事业”。多元文化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它以每一个个体的真实性存在以及使之成为特定个体的特性为核心,该理论不以个体为敌,而是极其关注每个个体的繁荣发展。 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险,共同体的价值观当然能够无可非议地压倒那些对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后果持异议的个体的意见,但是在其他地方却证实了伯曼和阿里所说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梦魇。考虑到自我的经验主义构成的重要性,文化的、社会的或宗教的依附的向心性,以及对个体认同的信奉,致使个体无法与[他们自己的]特定的立场或观点相分离,或者说无法后退一步,站在局外来考虑和审视其立场或观点,“就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去考虑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但是,恰恰是因为那个原因,他们确定无疑地认为现实就是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个样子。”“他们拥有一种世界观,并不断地追求其真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认为,每一个共同体、文化或宗教都会要求其自身立场的客观性,并且都有着其自己的真理。这不仅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不同文明和文化发生冲突的潜在根源,而且还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成为引发某些严重的内部多元主义的正当理由。总之,多元文化主义需要直面伯曼和阿里提出的批评。 本文首先认为,外部挑战与内部挑战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两种挑战都源于一种共同体的认同观念,根据这种认同观念,我们的文化的、社会的或宗教的忠诚(commitment)才是我们的规范性(normativity)的源头。作为一种结果,不仅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有可能相互冲突,而且共同体同其个体成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当然会充分意识到这种双重困境,然而,由于这种理论的共同体主义思想根源,想要将一个共同体内部对多元主义的理解与不同共同体之间对多元主义的理解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最终结果是,解决外部多元主义的挑战似乎比协调内部多元主义更为可行。 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要介绍一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替代性理解,即认为我们的忠诚是个人或个体认同的一部分,这种理解不但可以使我们无差别地对待内部与外部的挑战,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多元主义挑战的更为合适的办法。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强调个体的自我建构中自主选择的作用以及个体对福祉和尊严的认知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思想家(理查德·罗蒂)以及更为普遍意义上的非认知主义的认同理论(伯纳德·威廉斯)则坚持认为,自我意识使我们意识到忠诚在历史上和社会中的偶然性和相对性特征。然而,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将个体而非共同体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因此,要想证明多元文化主义是共同体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十分困难的,也就是说,忠诚是被个体发现的,而不是被个体选择的,并且忠诚对个体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在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一种理论越具有多元性,就越不可能具有多元文化主义的特征,反之亦然。 因此,本文希望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规范性的描述,以便能应对多元主义的挑战。我希望对认同提出一种可能的见解,在充分珍视对共同体忠诚的道德观的同时,又不会剥夺对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忠诚进行有价值的批判性反思的任何可能性。我将提出与共同体主义观点相反的主张,指出我们的自我反思能力对于我们的自我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自我反思不必预设对于自由主义理论来说极其重要的自主的或笛卡尔式的“自我”,也不必暗示一种存在主义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缺乏任何最终的标准、原则或价值观。对我们的忠诚采取批判的立场并正确地看待它们,并不能使自我脱离其忠诚——无法剥夺自我应有的品质。我们的忠诚不会消失,即使我们能理解其真实的、纯粹偶然和相对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本质——它们仍然是我们的忠诚,并构成了我们的自我。但是,当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忠诚时,它们就不再以一种不经反思的和自发的方式驱使我们行动,它们就不再成为我们的规范性的源头;只有当我们希望它们成为我们行动的理由时,它们才会起作用,我们不得不接受和认同我们内心的忠诚。个体对其忠诚的被迫认同这一事实,会使共同体丧失其绝对的、无限的约束个体的规范性力量,由此便会产生出现内部多元主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一种依照个体忠诚所构建的认同理论——我们的社会、文化或宗教忠诚仅仅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正确的,而对其他人并非如此——同样为解决外部多元主义问题以及潜在的文化冲突提供了思路。 本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外部和内部挑战以及共同体主义为应对挑战所进行的各种努力。第二部分评述了自由主义的、非认知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观点,并指出,以自我认知为基础的认同观点可以应对多元主义的挑战。 一、多元文化主义及其面临的内部多元主义和外部多元主义的挑战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我们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习惯、品味和好恶是由我们所属的共同体形塑的。“我们的归属、关系、认同和志向是由现存的道德观所决定和表现出来的。”当拥有一种社会角色并归属于一个社会群体时,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对我们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的、文化的或宗教的忠诚,它们构成了我们的行动和生活,并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是谁的归属感。“那种道德观对我们来说具有权威性,因为恰恰是由于它的存在,我们才会成为有道德的人。”作为同一个社会群体中的成员,我们拥有共同的道德观念,通过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因此,不同的社会群体的特征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伦理构架。从这一意义上讲,多元文化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共同体内部一元论和共同体之间多元论的一种理论学说。正是由于这种内部一元论与外部多元论的相伴而生,才引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挑战:不同的共同体在国际关系中以及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只有达成政治上的契约才能和平共处,否则就会反复出现宗教的、文化的以及民族的冲突。一元论往往质疑共同体之间彼此宽容的可能性,即认为诸如共同体价值观一类的价值观念是合理的和绝对的,会产生有效性要求(validity-claims),这不仅仅是针对认同它的个体而言的,而且还具有普世性。一元论与多元论可能会产生激烈的交锋。 在《政治自由主义》(1994)和《万民法》(2001)两部著作中,约翰·罗尔斯试图协调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存在着相互宽容的可能性。罗尔斯并不想直接应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因为他并不把我们的普遍原则视为我们因对共同体拥有归属感而产生的忠诚,而是将其视为个体理性的结果:“理性的原则就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运用。”罗尔斯认为,应对普遍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方法大同小异。就这一点而言,罗尔斯指出,那些不可调和的但却合理的共同体原则并不具有帝国的或传教士的热忱,我们不能过多地依赖主流文化和宗教的框架来对待这些原则,但可以通过一种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找到共同的基础,认同一种独立的、宽容的政治构想。相比之下,尤尔根·哈贝马斯不相信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冲突。与罗尔斯不同,尽管哈贝马斯承认存在着共同体的忠诚及其向心性,但是他拒绝接受一元论。他认为,不同的共同体不会遵循一种独立的、合理的、理想化的宽容理念,只有通过共同参与对话和彼此的民主协商,才能找到共享的价值观。协商可以使共同体认同趋于民主化,使不同的共同体在保持各自差异的同时,走出自己的传统,分享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共同体的价值观不是被外部赋予的,而是协商的结果。同样,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倡导简单的共同体一元论思想,而是会考虑到各个共同体都存在内部的多元主义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并非一种使压制文化的和反对人类解放的实践活动合法化的保守理论。对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来讲,文化传统确实需要社会批判;他引用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大革命作为范例,以便使其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合法化。一种彻底的一元论观点的确暗含着一种客观化和具体化的文化观念,它难以符合社会学的观点,即认为共同体中的成员对于哪种价值观能够真正代表其共同体无法达成一致。正如麦金太尔(Alasdair McIntyre)写道:“充满生命力的传统总是包含着连续性的冲突。”或如沃尔泽所坚称的:“道德观……是我们不得不争辩的事物,共同拥有并不意味着达成一致。”但是,一旦我们承认一个共同体内部可能存在道德上的不一致性,多元文化主义就会面临多元主义的挑战。 实际上,共同体主义总是试图提供一种反一元论的观点。与我们自己的共同体保持一定的批判距离,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分裂或重复我们自己,在精神上退出那“复杂的、忠诚的、狭隘的”自我,以便能站在“超然的、公正的和中立的”自我的立场上,从而接受在道德意义上客观的观点;“如果没有某种特定的立场,我们无法正视自己。”“[忠诚]构成了我的既定生活,是我的道德观的源头。”然而,我们确实处于某种立场,并且不得不对各种社会规范的意义进行阐释。泰勒(Charles McArthur Ghankay Taylor)坚持认为:“确切地说,实践就是对规则的意义的连续性阐释和再阐释。”“阐释无法确保我们对现实存在的道德作出一种实证主义的解读”;规范“必须被解读、被提出、被分析、被注解、被阐明,而不是仅仅被描述”。因此,道德阐释就是一种在本质上具有批判性的事业,它完全内化于特定文化的传统之中,并且有可能潜在地挑战那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对社会规范进行阐释的范围必然是有限的——一种规范不可能被任意地阐释:“尽管我的整体认同在某些方面会具有开放性并且可以被不断地修正,但是它并非完全无法形塑。”但是,在某些限制下,我们可以自由地理解我们在一个共同体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尽管在一个共同体内,我们的社会认同不会呈现无限的多样性,但仍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通过强调我们的忠诚的动态和多元特征,共同体主义试图为一种反一元论的观点进行辩护。“但是,如果我是堂·吉诃德,手里拿着长矛,想要与风车作战,那么我遇到的并非势均力敌的对手,我将被打败。”因此,任何社会都只能承担有限的社会职责。然而,共同体主义者并不想回避堂·吉诃德的经验,并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指出:“应该总是为那些异常的社会成员留有生存的通道”,而且“我们必须尽我们的所能……去保护他们的权利”。然而,正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将一种厚重的道德理论与诸如抽象的个人权利等比较薄弱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导致理论上的不连贯性。考虑到这些困难,最近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层面上都有了许多尝试,认为文化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包含着个人的权利。但是,这一应对内部多元主义挑战的解决办法并非没有问题。毕竟,这种观点不得不假定一种文化是由不可改变的和固定的规则构成的,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是共同体主义者必须回避的文化观念。 尽管多元主义的内外部挑战都源于一种有关我们的价值观和认同的共同体主义观念,但是,由于共同体的向心性,因而共同体主义必须对外部多元主义与内部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加以区分,并用两套不同的理论加以应对。当罗尔斯和哈贝马斯试图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为我们提供解决外部挑战的办法时,共同体主义却遭遇了恰恰由内部多元主义引发的更多的问题,原因在于内部多元主义不像外部多元主义的挑战那么激进。共同体主义已经区分了内部多元主义与纯粹的个人主义,而这种区分虽然没有牺牲两者,却引起了一些麻烦。然而,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如果我们把实践认同(practical identity)作为一种替代性的观念加以考虑,将我们对共同体的忠诚理解为源于个体,就会将外部和内部多元主义的挑战还原为仅仅是一种挑战,那么我们有望找到一种更好地应对多元主义挑战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 二、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对多元主义的顺应 批评共同体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合理性并非因为共同体拥有独立的道德立场,或者共同体能够彻底地决定适合我们的理性和道德规范的模式,而仅仅是由于作为个体的我们关注我们的共同体,珍视我们对共同体的认同。事实上,自由主义者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立场,在倡导个人自主性和个体福祉及尊严的基础上为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辩护。克里斯蒂娜·克尔斯戈德(christine Korsgaard)发展了康德式的认同理论,认为我们的有自主权的自我是我们的忠诚的创造者,它自由地选择了我们的忠诚。然而,强调在共同体的各种限制下进行选择和自我建构的可能性,是没有有效地考虑到共同体主义深层的本能,即我们的忠诚与行为无关,而是关乎自我及其真实性的发现——我们拥有对共同体的忠诚,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拥有它们。正如克尔斯戈德所承认的,个体的选择会将主观随意的因素带入我们的忠诚,这会“对我们的深层责任设置一种真正的限制”。 其他理论家则强调文化与认知对个体的幸福和尊严所起的作用。个体拥有文化权(cultural rights),就这一点来说,共同体是自尊的重要源头,为个体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多元文化主义增进了对不同个体的平等的尊重。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成为反抗对某些少数族裔进行政治和社会歧视的有力工具。结果,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认为,我们对共同体的认同具有工具价值,而非内在价值;共同体被视为初级产品(primary goods),其在本质上与其他公共福利配给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身份认同只有成为个体幸福的来源,才能得到认知。但是,那些在共同体主义意义上不可或缺的忠诚,是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认真看待的忠诚,却在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中毫无立锥之地。自由主义的方法是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尊严,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多元主义的挑战,而是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进行正当的辩护。一旦我们放弃了共同体的建构性层面,多元文化主义有可能仅仅是社会变革的偶然产物,纠正政治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补救方法,但是却缺少任何进一步的规范性基础和必要性。 当伯纳德·威廉斯在一种认同观的视角下为个人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进行辩护时,他恰恰正是基于忠诚的理念。按照他的理解,忠诚不能被还原为对个人的有用性;与此相反,忠诚常常对个体幸福具有不利影响。与共同体主义的观点相似,与康德的理论相反,威廉斯坚持认为,我们的道德信念和忠诚并非源于我们的自由意志,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源于我们的社会背景。我们的价值观念起源于我们所居社会的结构,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它们是文化的产物。然而,与共同体主义者不同的是,他相信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忠诚采取一种反思的和批判的立场。我们可以“退出社会实践及其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不仅在我们的忠诚的道德范畴内进行思考,而且对这种道德范畴加以反思。对威廉斯来说,我们置身忠诚之外,以局外观察者的立场批判性地分析隐含在我们的忠诚之中的价值观:我们质疑“这是否是继续走下去的正确道路,是否是评判行动的好方法,其所获得的赞赏是否恰如其分”。我们用我们已有的关于价值观的知识来评价我们的道德观。“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伦理道德的知识。在伦理道德内部,通过同样的过程,我们可以获得相互谅解。”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人类的本性、历史以及什么是真实的世界的知识越多,对于我们的价值观就会有更清楚的理解。那些价值观不过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的偶然产物,它们是非客观性的,并且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联。但是,如果价值观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或宗教的基础,某些与我们拥有的有关人类本性和这个世界的科学知识完全对立的伦理观念就会变得不可接受。结果是,反思有可能会摧毁伦理道德观念,改变内在的伦理道德实践,尽管它没有产生一种客观的、普世的道德观。反思允许我们谴责并拒绝接受某些共同体的规范: 一旦我们将我们现在拥有的道德生活视为是真正历史性的和地方性的结构的产物时,尤其是一种有关其自身起源和潜能的特定的自我意识时,那么我们就不那么强烈地想要将其视为一种令人满意的功能性整体,那么我们将更有可能意识到这一道德生活中某些被广泛接受的部分实际上是对其他部分看似合理的推断而已,这样的推断应该受到批评。 此外,反思“要求一个人要过某种合乎道德的生活,同时要求他要意识到替代这种生活的其他生活不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业已存在,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周围也有可能存在着”。自由的制度“不仅对自由的探求而且对生活的多样化以及伦理道德的多样性”都是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似乎既解决了内部多元主义的问题,也解决了外部多元主义的问题,只要我们将认同理解为个人主义的认同的话,那么上述两种挑战不过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罢了。 不幸的是,威廉斯并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威廉斯反思理论的黑格尔式背景将历史构思为不断变得清晰的自我意识,使得这一理论在应对多元主义的问题时既具有相对主义的特征,又显得过于绝对化。首先,让我来分析威廉斯理论的相对主义问题。考虑到宽容和自由主义都是有关知识的问题,因而它们要成为可能,必须有待现代性的到来,即对世界具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对社会持有自然主义的观念。威廉斯被迫承认一种“距离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 of distance),即“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在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内考虑其道德生活”。尽管显得非常勉强,但威廉斯还是试图为早期社会的等级制度进行辩护,因为“他们认为其社会秩序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样的想法也许并没有什么错误”。因此,认为自由主义是合理的这种观点只是基于我们对世界的已有的知识而已,而且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运气”(moral luck)——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掌握了相对的知识罢了。另一方面,威廉斯的反思理论中的含义太过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t)。他应该坚称:“仅仅是空间距离上的相对主义在现代社会中是没有意义且无法应用的。”今天,道德实践必须将现代性的成就考虑在内。“尤其是当前伊斯兰势力正在试图颠覆这一过程……可是并不能表明这个过程是地方性的或可逆的,它只能引发绝望。”按照威廉斯的观点,人们一旦有了反现代的忠诚和态度,就应该立即改变。威廉斯想要避免得出下述结论:意识到我们的道德观的非客观性,要求我们“在遭遇到另一个共同体时要完全停止[我们的]道德回应”,因为“没有理由表明[我们]应该那样做”。在他的理论中,只有一类人不必得到这样的结果,那就是自由主义者。只有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有理由不去质疑并捍卫他们的忠诚,因为只有自由主义的立场才能汇聚关于人类本性和世界的真实知识。令人感到自相矛盾的是,威廉斯并没有如我们最初所希望的那样为多元文化的多种形式提供足够的空间,而且他本人也反对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认同政治应采取批判的态度的良好意愿。 威廉斯的基础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他不能认真对待下述共同体主义的要求,即忠诚是个人价值观的独立来源,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忠诚并不受我们的好恶、它们的对错及真假与否的影响。威廉斯的自我意识理论依赖于一种与历史哲学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知识理论,这使他不可能对忠诚进行一种非化约论的(non-reductionist)描述。对忠诚的规范性要求导致了强烈的认知局限。科学将最终决定你能成为谁以及你不能成为谁,因此也将最终决定多元文化主义的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与威廉斯的理论相比,反基础主义的非认知理论(我们可以将后现代主义以及大多数后殖民主义归入此种理论)对我们的基本忠诚更为敏感。例如,罗蒂像威廉斯一样,将自我意识建立在这样一种知识的基础上,即价值观的本质构成了我们的忠诚。然而,考虑到知识只是向我们表明,我们只能成为被历史塑造的我们,不存在任何关于世界的真理,真理只存在于各种道德观之中,因而自我意识不能要求我们去改变我们的忠诚。它仅仅告诉我们,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应采取自嘲的态度:“时刻意识到用来描述[我们自己]的术语是要发生变化的,时刻意识到[我们的]终极词汇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并因此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偶然性和脆弱性。”传统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应该将“忠诚与他们自己的忠诚的偶然性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并支持一种带有反讽性和自由主义希望的普世宽容的道德观。的确,这样的一种立场排斥认同政治,但是却有可能在缺乏真正的替代物的情况下使某种萎靡的、软弱的多元文化主义乘虚而入。 威廉斯与罗蒂都认为,自我意识具有认知主义的含义。他们在知识而非自我认知的意义上来对待自我意识。他们要求我们用自我意识的立场去分析我们的忠诚所包含的内容,去评判它们与现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基于他们各自关于知识的理论,他们要么摒弃了我们的忠诚中的某些内容,要么嘲笑忠诚本身。但是,他们不认为忠诚仅仅是属于我们的,它们就在那里,是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的必要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忠诚,我们就会成为我们希望成为的人。威廉斯与罗蒂对我们的忠诚进行了审判和批评。然而,脱离忠诚或对忠诚进行自我排斥都不能令忠诚消失。对忠诚的内容进行具体化的规定可能导致一个异化的自我的形成,从而致使自我表现的不连贯性,并且使自我发生根本性的、病态的分裂,最终分裂为一个善的自我和一个恶的自我。 应该在自我认知的意义上理解我们的忠诚——具有自我意识并不意味着对忠诚的内容采取某种立场,而只不过是知晓存在某种忠诚。一旦远离忠诚的规范性的观点去思考我们的忠诚,我们就不再因规范性的观点及其内容的束缚而觉得无助。这种远离使我们不受先验的、康德式的思想或者佛教意义上的一切皆空的思想的束缚——即除了自我,生活中别无他物。但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理解我们的忠诚,我们就是自主的,因为在一种忠诚驱使我们采取行动以前,我们就有可能去认同这种忠诚。一旦我们能够认同我们的忠诚,它们就真正成为“我们个人的”忠诚,而不再是我们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意识到,并非那些忠诚的相应的规范特征构成了我们的忠诚,而是具有个体特性的忠诚构成了我们的忠诚。一旦这些具有个体特性的忠诚被认可了,那么无论忠诚的内容如何,我们都不必改变或嘲笑我们自己。这种认知使我们不必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与我们有着不同价值观的其他个体。自我认知是个人认同的必要条件,因为它赋予我们一种自我的感觉,并且它的价值观能够将我们建构成为具有正确的和清晰可辨的意志力的自我。如果我们不能获得这种自我认知,那么大卫·休谟将我们设想为仅仅是一系列没有稳定认同的精神状态的存在物的观点可能就是正确的了。 一旦我们不再认为我们的社会、文化或宗教认同是必要的和基本的,就不再可能拥有一种自由的和超越忠诚的没有约束力的自我;自我意识不应变成对自我的拒绝,因为自我认知会正确地建构我们的认同和自由——一种已经被斯宾诺莎强调过的观点。其前提条件是,一种基于自我认知的特殊认同理论有助于我们解决这样的难题:如何才能在重视我们自身的同时在多元主义的情形下证明多元文化主义的合理性。考虑到认同是基于个体而非共同体主义之上,并且考虑到下述事实,即认同感才是我们的忠诚的规范性的来源,因而内部多元主义是可以得到保证的。正如保罗·伯曼和希尔西·阿里所主张的,不要空洞地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忠诚的共同体主义来源及其构建证明了多元文化事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一旦解决了内部多元主义的问题,那么就根本不必求助于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同样可以解决外部多元主义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共同体主义不得不区分内部多元主义与外部多元主义。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政治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自我认同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道德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