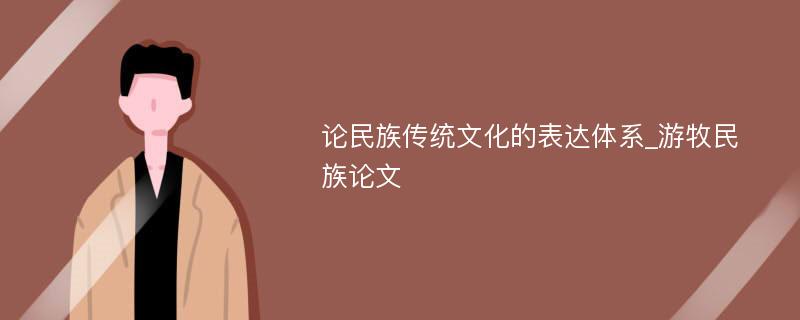
论民族传统文化表达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民族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0)04-0037-07
一、概念的提出
民族传统文化承传的集体强制性,使其拥有了特殊的品位与意义。一方面,尽管民族传统文化赖以产生的土壤已经弱化或消失,但其却顽强地沉淀于民族生命基因中,编织起一面迥异于其它民族,张扬民族个性的标帜;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民族,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承载与传承方式上,毫无例外地呈现出“双行道”的惯性表征:其一是以“物”的形式承载并馈遣子孙。这种“物”的遗存,差不多就构成了今天我们观念中“文物”这一概念的全部内容,姑且称之为“质化承载遗传系统”(简称“质化系统”);其二是以“非物”方式承载并惠于子孙,包括四季风尚、宗教信仰、传统节庆、娱乐游戏、工艺技术、婚姻习俗、家庭结构、亲属称谓、习俗约法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神话、传说故事等。这种不是以“物”或主要不是以“物”承传的方式,我们统称之为“非质化承载遗传系统”(简称“非质化系统”)。
把民族文化承传方式类分且强名为“质化系统”和“非质化系统”,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人类民族的普遍流行,它们一旦产生,便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格,并依照这一界定原则,演绎着承传的不同角色。
相对的独立性,表现于“非质化系统”,显著特性有二。其一,对人类文化观念的萌芽、变异,具有“第一时间”性质。人类的共同经验,是由氏族而部落而民族。氏族是以后所有演化的基石。这基石的确立,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源于外婚习俗。可以推敲一下这一习俗萌芽演化的流程。在此之前的一个进步,已排除了同一血源不同辈份之间的婚配,认可同一血源相同辈份的婚配。最初,肯定是个别人或部分人,对流行的同一血源相同辈份婚配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进而避免这一婚配行为。“非质化系统”首先开始反应并吸纳这种意识变异。当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或者已经打破这一传统时,“非质化系统”就完成了对这一反传统行为的肯定和沉淀。习俗开始形成,并通过“非质化系统”的进一步推进,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约法。于是,氏族外婚制度正式确立,氏族也就产生了,人类开始构建与氏族制度相联系的“质化系统”。“非质化系统”对于人类的文化观念,具有敏感的反应机制特性。其二,是人类行为的集体性。与“质化系统”人类参与行为的一过性不同,“非质化系统”承传内容和方式,自始至终无不蕴含融汇于人类的具体行为,并通过人类的具体行为方式而具备了表达功能。上述氏族外婚制度的产生、确立与流行,没有人类行为的参与,显而易见,不会产生更不会流行;参与的程度,不是个别或少数人,而是大部分甚至是整个集体人群。这是显别于“质化系统”带有根本性质的特征。
“质化系统”特征显而易见。物质性,即必须具备物质化的形态条件,才能完成其承传功能;直观性,即其承传功能要求具体的物化表现,历史文化内容,凭借具体的物化表现,获得了直观效果;不可再生性,即人类行为表现为一过性,即后的人类任何再生行为,均无法获得其原始的文化本质意义;等等。
“质化系统”与“非质化系统”的性格特征,规定了各自承传功能的实现方式,确立了完成功能的不同角色。一般而言,民族文化基因首先经过“非质化系统”的吸纳、整合、确认,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观念后,才将可以和应该物化的那部分内容,表达于“质化系统”。但这并不意味“质化系统”的依附和被动。当人类民族文化基因流注并凝固于“质化系统”时,“质化系统”把这种基因表达得更为有力,有着进一步强化和渲染作用。
内蒙古博物馆所藏“青铜阴阳短剑”是东胡族青铜文化的代表性器形,展示了东胡族特定时代的主流文化。该器形之所以择取如此物质化表现手法,概源于“非质化系统”对如下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反馈:母权已经衰微,但并未彻底失败;父权已经取代母权,但还没有强大到彻底剔除母权影响的程度。双方至少在文化观念领域处于平分特色的对峙状态。这种对峙,不是采取激烈的突变方式,而是一种渐进的和平演变。过去完全占据东胡人心灵的母系形象根本动摇,父系形象渐显明晰和重要。于是,把过去对于母系(或女性祖先)的认可和崇敬,悄然分出一半给父系。“非质化系统”确认了这一文化流变,但并未使这一流变仅停留于“非质化系统”,而是进一步将其表达于“质化系统”,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青铜短剑上比肩而立似乎完全平等的男女造型。这一文化流变,就“非质化系统”而言,久已湮没于厚重的历史烟尘中,无从感觉和把握;“质化系统”的这一遗留,则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东胡民族曾经经历的历史。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一个事实:并非“非质化系统”所有内容,皆可表达于“质化系统”。这种表达是有条件的,一曰应该,二曰可能。应该是主观上的意愿,可能是物质条件和表达手法的允许,二者缺一不可。这种条件行为,使“质化系统”对于“非质化系统”的表达不完全不充分。很多内容,截止于“非质化系统”层面。“非质化系统”又对这一层面的内容进行筛选和淘汰,仅把这一层面的部分内容遗传后世。这种筛选淘汰行为,使两套系统具有强烈的互补性。从其产生开始,碾转流化至今,以其相对独立性与强烈的互补性,呈现出永续化的相互“置换”、相互推动、互为表里的格局形态,共同促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
二、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传统文化表达的差异
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的中原民族,农耕经济的本质要求,规定了中原农耕民族长期囿守于特定区域。较为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使他们身心得以舒缓,仰观俯察,意驰八荒。辨物识事表现出冷静细腻的人文性格。这种民族性格,表现于“质化系统”,就衍生为一种执著:他们尽可能地创造或生产一件又一件令后人赞叹的质化器型。这并不完全出于实际的需要,另外的一个意愿非常明确,希望子孙因守这片热土,承嗣物质成果,永续他们的文化理念。中原农耕民族追求不朽而又注重现实,民族文化的物质化表达,成为二者之间的满意平衡。这种心态在较早进入农耕经济的民族中是普遍的。
农耕经济使土地人口的承载密度大为提高。人口的相对集中,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关系日趋错综。古典的习俗约法,在规范和调整这种复杂关系时,显得力不从心。源于这样的现实需要,中原农耕民族,就产生了专事人文秩序与文化构建的阶层——儒和士。他们聚精会神一生所为,就是把肇于远古的朴素文化遗传,予以提炼、加工。提炼的结果,使中原农耕民族的文化理念、人文秩序,要为系统精致,博大精深;加工的结果,使这一文化系统渗入斧凿烙痕,一定程度不免抹杀了古典人文理念深契自然宇宙的活泼天性,略失于僵化呆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争鸣局面,就是以儒士为主力进行的中原农耕民族文化体系、人文秩序的大规模构建工程。这种浩大的构建结果,使中原农耕民族传统文化的“质化系统”和“非质化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凭添了几份哲学化的韵味和儒士文人的理想。经过“有教无类”的努力,这种源于民间而又高于民间的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又以一种强制性渗归民间,对民心、民智、民俗,进行了一番卓有成效的洗礼。这种影响巨大而深远。随后的扩张力,绝不仅仅限于中原农耕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不容质疑的崇高地位。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生存地域深长阔大;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随时的迁徙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把他们磨砺得雄健而勇武,粗旷而率性。他们对客观事物的体认,有如草原远山的剪影轮廓,明晰而又疏达。大草原锤铸的民族性格,使他们对于物质化的构建没有过多奢求,也较少把文化理念物化于型的热情,即或有,也有很有节制的表达。我们熟知的东胡、匈奴族青铜文化以及草原民族的相似行为,就是这种节制表达的结果。他们把一切可以删除的东西,从观念和生活中全部删除掉了。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装武备、祭祀礼器、车舆毡帐等等,都表现出一种人为的刻意简化。在他们的文化理念中,唯一值得留于子孙的物质成果,就是脚下这片坦荡无涯的茫茫草原以及草原上游荡的牛羊。
草原游牧民族人口增长速度,长期以来远远落后于中原农耕民族。稀少的人口,阔大的地域,游牧的经济特点,使草原人口呈现出散点式布局特征。较为密集的人口聚居一无必要,二无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朗、单纯而又亲和。这样一种和睦的社会人际关系,使草原游牧民族没有需求产生专事人文秩序文化体系构建的阶层。他们规范调整、教化人际关系的文化传统和道德理念,就像草原的牧草,是自然而然地生成,并且足以调化滋养他们的社会机体。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把传统的文化理念更多地托寓了与这种文化几乎同时产生的“非质化系统”。换言之,“非质化系统”的风俗、习惯、约法乃至于神话、传说、故事等,成为草原游牧民族传统文化相对主要的载体和传承方式。中原农耕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骠悍的草原民族也曾几度入主中原,但这一切结果的最大所及,并没有使草原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的模式趋同,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游牧民族传统文化所恪守的发展轨道和承传方式,只是为草原游牧民族文化输入了某种弹性和张力。
中原农耕民族传统文化和草原游牧民族传统文化,各具特色,难比优劣。但从这两种文化体系的形成、演化、传承等方面考察,中原农耕民族传统文化,“质化系统”和“非质化系统”始终呈现左右互动,上下互融的演化格局,“质化系统”、“非质化系统”发育较为平衡,更多了一些谨严、细密和精致。与之相比,北方草原游牧文化“质化系统”发育滞缓。中原农耕民族,至晚在汴宋,研究“质化系统”的学科——金石学,渐臻成形。同时代的蒙古人,固然神勇昂扬,统一北方草原,递为雄长,继尔旋风般地横扫亚欧大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但留给我们的实物遗存少而又少,似乎与这惊心动魄的历史很不相称。有如前所分析,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质化系统”的表达不充分不完全,“非质化系统”担纲了相对主要的承传角色。这是北方游牧文化一个突出特征。
三、“非质化系统”承传文化表述历史的重要作用
“非质化系统”在历史演化中,不断循环着“吸纳——剥离——再吸纳——再剥离”的扬弃程序。其所承传内容,相当部分因剥离而失去承传载体支持,毫无声息地沉入历史“黑洞”。尽管如此,也有相当内容,在扬弃过程中稳定下来,在“非质化系统”中或多或少有了遗存。这些遗存,弥足珍贵,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质化系统”遗存。
追溯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进程,如何将“质化系统”、“非质化系统”、历史典籍的位置摆布准确恰当,各得其所,形成三者相互印证、相互支持的完整研究观念和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三者关系的失衡,会严重影响研究的进展和结果的真实。
事实上,“质化系统”相对弱化,“非质化系统”相对发达或者携载了更具本质意义的遗存,不为中国北方游牧文化所独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也存在。
长期以来,对于“非质化系统”这一珍贵社会历史化石,没有给予应有重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博物学家,面对许多民族流行的“非质化系统”内容,一脸茫然,继尔称之为“奇风异俗”,不屑一顾。使这种状况彻底改变的最具代表性人物,是一位律师出身的美国人。他发现,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实际存在的婚姻家庭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属关系,与流行的亲属称谓不相吻合。他没有轻易放过这一“奇风异俗”,而是以此契入,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终于廓清了笼罩在人类婚姻家庭史和古代社会史上的迷雾,重建了古代社会人类共同的顺序演进阶梯,第一次把古代社会史特别是婚姻家庭史的研究,置于了科学的基础上,创立了近代民族学。他就是被后人尊为“民族学之父”的亨利·路易斯·摩尔根,他是发现并成功运用“非质化系统”探素古代社会的第一人。摩尔根之后,人们改变了文化历史以“质化系统”为单系承传的观念,认识到人类文化历史还有另外一条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的承传系统——“非质化系统”。概因“非质化系统”曲折、隐晦的表达手法,实际的重视程度与其自身本具的重要功用,并未达致令人满意的契合,留下许多遗憾。
匈奴是具有较多“质化系统”遗存的游牧民族。内蒙古博物馆所藏著名的匈奴金冠饰,引人注目。金冠顶锤碟半球状,浮雕狼羊组合图形。狼四肢前屈,葡卧于地,尾部下垂,贴体前卷,目前方、嘴微合;羊强调头部,盘角镂空,硕大夸张,向后弯曲内旋。狼羊神态,均自然安和。雄鹰圆雕,展翼、俯视,爪粗劲,傲然挺立半球之上。下附带饰三件(似缺失一条),分别浮雕虎、羊、马,均卧踞。猛虎利齿贲张,羊马则蔼然温驯,头部对接。整个造型,拙朴明快,精美大气,威猛中流动着协谐平和。
匈奴人喜用善用动物特别是食肉类猛禽猛兽雕饰器形,自成一派,固然与生存环境关系是很大,但仅从这点解释,倘嫌不足。游牧其东的东胡,却喜用家畜和食草类动物为器形雕饰,风格不同。其实很多民族,都有以动物饰器习惯,而在动物类别的择取和表现手法上,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不完全源于生存环境的不同,也不是对动物自然属性认知的不同,而是不同的民族文化观念使然。把自然界某种因素提升为民族文化因素,即是用民族文化理念,对其自然属性进行引伸、演绎和开发,赋与其鲜明的民族文化意像,使之成为主要或第一层面内涵,自然属性弱化或隐于第二层面。特别是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进行的这种开发,大多与民族起源、图腾信仰直接相关。
崇天及天神,是人类原始文化第一层面主题。天高而渺,人莫能及,天地之间自由遨翔之禽鸟,使人产生联想、钦羡,进而崇敬,奉为神物,这是人类原始文化第二层面主题。“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故商族以玄鸟为崇拜[1];姜原践巨人迹生周后稷,以为不祥,“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周族以飞鸟为其保护神[2]。
匈奴称单于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意为天,“孤涂”意为子,即谓单于为“天之子”。匈奴人亦崇天。尽管匈奴神话传说存世很少,没有发现关于崇鸟内容,但许多专家认为,匈奴与突厥同俗,神话传说相同或有一致性。突厥语诸民族,广泛流传关于“鹰、天鹅等飞禽为神鸟,并被看作是灵魂显形”的神话[3]。匈奴崇天,次衍生崇鸟,似不成问题。近年发现的匈奴青铜器,动物雕饰主要有鹰、狼、虎、鹿、牛、羊、马等,其中鹰鹫图形就占三分之二左右[4]。可见,鹰在匈奴崇拜物类中的尊贵地位。
羊为匈奴人神兽,不必赘言。狼在许多民族中,形象恶劣,代表贪婪、凶残、狡猾。在匈奴人则不同了,《魏书·高车传》记载了匈奴人的一则神话传说:单于生二女,美丽惊俗,人视为神,单于筑高台,置二女于上,欲敬奉于天。越三年,天不至而狼来矣,二女遂“为狼妻而产子,后滋繁成国”。这个神话传说,应该是反映母氏族(部落),繁衍子氏族(部落)的过程。单于奉女于天,以天为崇信,分立的子氏族(部落),神狼为祖,在以天为崇信的同时,似以狼为宗奉了。公元前3世纪左右,匈奴氏族制度渐遭破坏。头曼单于时代,世袭权力已开始膨胀,但不为定制。公元前209年,昌顿单于时代,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等官职,世袭终成定制。氏族民主制度被彻底抛弃,但依然保留下来氏族外婚、公共墓地等基本因素。史载匈奴显族有虚连题氏、呼衍氏、须十氏、丘林氏以及后来的韩氏、当于氏、乔氏等,固然是匈奴世袭制造就的结果,同时也表明氏族制度躯壳的存在。
综上可以初步认为,匈奴金冠饰的动物造型,不应该是草原景象的自然摹描,也不大可能是弱肉强食理论直接截取,纯为艺术性装饰;应与匈奴氏族部落的源起、分立、联合历史以及图腾习俗密切相联。再明确说,在其出土的内蒙古阿鲁柴登地区,以鹰为图腾或族徽的氏族部落,是母族或强族;以狼、羊为图腾或族徽的氏族部落,是实行外婚的两个氏族部落,同时又是鹰族的庶族或属族。狼、羊和睦相处,构成内容同一的四组浮雕,雄鹰傲然挺立其上,正是这样一种关系的表征和注释。
自然,神话传说并非信史,本有局限。但人类任何民族,文字产生以前,利用神话传说,承传文化,表述历史,其实是一种必然而无奈的选择。剔除人类主观渲染和流转变异,神话传说的精神指向,是人类经验的坦白,绝非空穴来风。大多历史典籍都有传说索史传统。《史记》等辉煌典籍中的古史传说,屡屡被当代考古证明确为信史。正在进行的世人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即是以古史传说为线索,运用传统和当代高科技综合考古方法,求证中华文明的滥觞及其演化序列。
探幽索隐,“非质化系统”其它内容,同样不可忽视。以《蒙古秘史》为例。也速该临终托孤,蒙力克不负然诺,德薛禅顺达情理,于是,“蒙力克遂将帖木真来矣”[5]。帖木真称蒙力克为父,在《秘史》的其它地方还有记载。后世的研究者据此推说,也速该死后,帖木真之母再嫁蒙力克。除此之外,此说无其它依据。对古代蒙古族亲属称谓有精深研究的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对古代蒙古族“父亲”一词用法,有一精辟分析:“a表示亲生父亲,b称父亲的义兄弟(anda),c对年长者的尊称。”[6]联系《秘史》的其它内容,帖木真对蒙力克称呼的用法意义,应该是b或c,没有a的意思。古代蒙古人称谓系统,带有明显的分类或亲属称谓特点,b或c在用法意义上没有区别。至今,这样的称谓用法在蒙古人中依然流行。笔者曾经插队的乌珠穆沁一带,用“阿吉”一词称呼自己的亲生父亲,同时也可以用“阿吉”一词称呼与亲生父亲年龄相仿有血缘或无血缘的男性。
亲属称谓是“非质化系统”最为稳定的内容之一。比较《秘史》与现在流行的蒙古族亲属称谓系统,并无大异。蒙古族“父亲”一词的用法,无疑在指示这个民族久远之前的一种习俗,即氏族集体外婚原则。几乎人类的所有民族都有同样的经验,也有过相同的称谓系统,只不过现今保留这一遗存的民族,渐趋稀少。对“父亲”一词用法不详,衍生谬解,是对蒙古族“非质化系统”了解不够所致。
如上所述,“非质化系统”吸纳承传文化信息,具有直接、敏感的机制特性,相当一部分内容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同时也有表达手法曲折、隐晦和部分内容易失易变的局限,需要“质化系统”支持和历史典籍的补佐。但这并不能抹杀其承传文化历史信息的重要功能,以及其所承传信息对“质化系统”的补遗、注解和支持功用。“质化系统”被推为人类信史的指标器,某种程度也是名至实归,但“质化系统”也有断层、支离的局限,相当的遗存,用“质化系统”本身很难说清,需要另辟蹊径。过份注重“质化系统”常常使拥挤在这条“单行道”上的我们,发生阻滞和过失。疏导这种迷失,最好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双道行驶”。其实人类祖先,本来就是“双道行驶”而来。
四、结束语
第一,作为人类民族文化一个独立承传系统,“非质化系统”内容,分属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不同学科范畴。作为科学昌兴的细化结果,无可厚非。但这种结果使其本身自具的独立性,因学科之间范畴上的界定,呈支离状态,使“非质化系统”功用的完整性,若隐若现地被分割,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受到限制。因而“非质化系统”承传的独立性和功用的完整性、重要性,多少受到忽视。把“质化系统”和“非质化系统”作为一组相对观念提出,就是期指“非质化系统”的独立性、完整性有某种程度复归。
第二,中原农耕民族,历代都有设官治史传统,也都有专事文化构建的阶层。与此相对,民间的文化承传内容和形式被指称为“民俗”,这在中原农耕民族,自有道理。许多其他民族,包括北方游牧民族,没有设官治史传统和专事文化构建阶层,没有那样的相对观念。因此,中原农耕民族文化,“质化”和“非质化”系统又多了一层“官”与“民”的因素区别,传统上或多或少有重“官”轻“民”倾向。北方游牧民族,没有这样的区别因素,至少没有严格区别,这是北方游牧文化又一重要特征。应该重视这一特征,至少不能完全地沿用研究中原农耕民族文化的方法研究北方游牧文化;更不能简单地运用相对观念,将北方游牧文化承传特征归入“民俗”之类,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
第三,北方游牧民族“质化系统”发育不充分,中国历史典籍的记载,多为间接或粗粗涉猎,一无系统,二又零散,这是研究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困难。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深入挖掘现有的“质化系统”遗存,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佐证功用,二是对历史典籍进行系统整理,高质量地准确予以运用,三是依赖“非质化系统”支持。任何一个单线操作,都难达致圆满。
第四,50、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成果显著,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不足,特别是对民族文化“非质化系统”内容,深入不够。比如有的调查资料,对于亲属称谓,仅仅记载了称谓名词,没有进一步考察这些称谓在实际应用中的情况,使这些亲属称谓的科学性、完整性大打折扣,质量上留下很大缺憾。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迄今,没有再搞过成规模的调查。“非质化系统”的易变易失性,加之社会发展的巨大冲击,使许多珍贵的内容,遗憾而无奈地沉入历史烟尘,损失颇大。现在,对此再不予重视,则为将来留下更多遗憾!重视并着手这项意义不同一般的工程,无疑对于民族文化历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一个有质量的交待。国家目前推行的“抢救第一”方针,不但包括“质化系统”,也应该而且必须包括“非质化系统”。
[收稿日期]2000-05-11
标签:游牧民族论文; 文化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农耕文化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草原风格论文; 中原论文; 父亲论文; 秘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