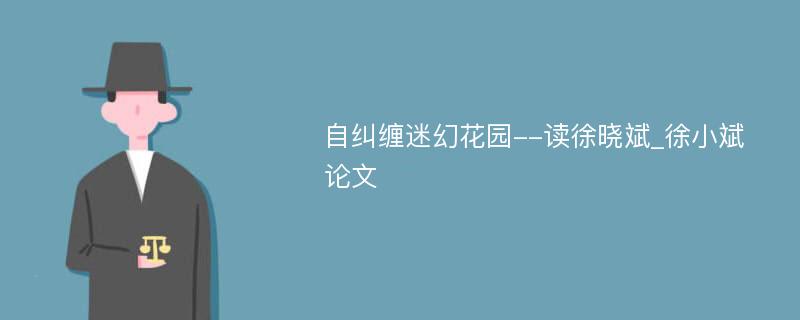
自我缠绕的迷幻花园——阅读徐小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幻论文,自我论文,花园论文,徐小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逃离与皈依
徐小斌曾以“逃离之路”为题,概括自己的创作与人生(注: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收入《徐小斌文集·折梦》,第372页。)。在一份渐趋清晰的自我指认中,她始终在逃离:逃离绝望,逃离创痛,逃离孤立无援;也许是——逃离“女人”:女人的不轨,女人“非法”的“真相”,女人的伤痛而无名孤寂的内心生存。因此,她的逃离始终是一种皈依。但她的逃离与皈依之途却不断地遭遇和撞击着那试图逃离之所。在徐小斌的作品序列中,到处可见的,是女性生命伤痛的涡旋,是不已之梦绝望而空洞的回声。那涡旋与回声彼此撞击、相互缠绕,显露出一处女性生命的迷幻花园。于是,她始终无法抵达她深深内在化的皈依之所,获取心的归属与庇护;或者说她在自己生命的体验与书写中不断发现,那如果不是一处语词的乌托邦,便是必需予以妥协、叛卖的现实的代名。但她也始终未能彻底摒弃对皈依与心灵宁谧的渴求。于是,她只能在皈依间拒绝皈依,在逃离中祈祷皈依的实现。在更多的时刻,她以逃离为皈依(“我的逃离是永生”(注:徐小斌:《逃离意识与我的创作》,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6期,收入《徐小斌文集·折梦》,366-374。)),为皈依而逃离。
在批评家的视野与作家的自我勾勒中,徐小斌颇为可观的作品序列与她几乎和新时期同龄的创作岁月,或许颇为清晰地分成两个段落,《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1985年)或生不逢时的长篇小说《海火》(1989年),成为这岔路口上的界标。但如果说,前次,她逃往一个美梦,一段梦想中的温馨与完满,那么,今次,她逃往魅影幢幢的梦魇。尽管在笔者看来,始自1981年的徐小斌的前期创作,与其说是梦的逃遁,不如说彼时彼地,一份理想主义的信念与图景尚能岌岌可危地托住缠绵飞动的少女情愫;我们尚且能为梦想找到一方天空,至少是一线缝隙。或者可以说,为变迁的时代和女性生命的体验所粉碎的理想,便只能被指认为轻飘的梦想。因此,我们与其说徐小斌前期创作所逃往的皈依与庇护之所是梦想,不如说是写作,是写作行为自身。相形之下,倒是徐小斌九十年代的作品序列更接近于逃离。一次再次地,她逃往异乡、异地、异时、异文化,她以一处处扑朔迷离的迷幻花园遮掩起女性/个人生命体验的裸脸,她以他乡和异地作为重演梦想的舞台,但却一次次因梦碎时分的绝望而泄露了心灵所经历的伤痛之旅。她在逃离中遭遇,以假面去裸露。不仅徐小斌笔下的异域奇观每每无从遮掩女人的宿命与绝望,而且在她异想天开的故事与光怪奇诡的文字下面,是一种现实与梦的剧烈撕扯与多重纠缠。她或许因此而迷恋那位不再时髦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的理论及其“说法”:面具人格(注:参见《“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角色冲突》,《徐小斌文集·折梦》,第355-365页。)。由前期到后期,与其说徐小斌抛弃了面具,不如说她更换了自己的选择。但徐小斌的作品序列不仅是所谓“假面的告白”——我们间或可以用这个字眼形容所有作家的创作;而且是诸多假面面面相觑的镜中天地。从镜象到镜象,徐小斌光影斑驳的神秘故事,绕开并显露了她真切且依然渗血的伤口;那流畅表达中悄然蔓延开去的细小纹路,事实上展露着一处拒绝言说、也许是恐惧或无从言说的巨大空白:一份女人生命之程必然遭遇、却多遭遗忘的伤痛,一段太过平常、却从未“合法”的生命遭遇。那是女人的成长之路,那是种种主流文化对女性的规范与女性生存空间有如天壤的沟壑。——为了活下去,女人或许比男人更多地“以遗忘和说谎为先导”(注:鲁迅:《伤逝》。),但这谎言更多地朝向自己;但如果不能成功地自欺,便只有遗忘,或一种并非自主选择的可能:疯狂。显而易见。徐小斌未曾遗忘。因此,她笔下的女主角,尤其是她自《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之后的作品,都多少带有几分疯狂。但那是一种太过“正常”者的疯狂,因为记忆而非遗忘,因为清醒而非恍惚,因为“理性”的逻辑而对着遭理性放逐的女性生存与生命的体验。徐小斌不断地以她的文字和故事填补着、遮蔽着这空白,那间或可以视为一份朝向自己的谎言;但她的故事却一次次地以种种痕迹和裂纹显露出那空白——溅染血色的空白的存在,那于是有成为一份固执的追问。有如自一幅足以乱真的画面顶端不断淌落殷红的油彩,徐小斌异域风情中的爱情或魔幻故事处处显露着阴霾、不宁与深深的伤痛和焦虑。
在皈依与逃离之间,在恐惧放逐与自我奔逃之中,徐小斌的作品充满了常数与异数的变奏。或许尚没有类似的例证:在为他乡故事所包裹着的自我厮杀之中,妥协于现实的诱惑是如此的频繁和巨大,但不甘与不已的挣扎又是如此的触目而剧烈。阅读徐小斌,因此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经验。
负重的纸鸢
在笔者看来,徐小斌数量颇巨的作品序列与其说展现了线性延伸的脉络,不如说它始终是为一处处重叠的旋涡与纵横的岔路所结构而成的空间。按照徐小斌自己的说法:
……我的作品大概有两类:一种是迷宫式、寓言式的写作,如《密钥的故事》、《迷幻花园》、《蓝毗尼城》、《蜂后》等等,这类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智力的挑战,让我迷恋;而从《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末日的阳光》到《双鱼星座》、《羽蛇》,则构成我的生命轨迹,可以从中窥见一个生命过程中深度的伤痛与隐秘,写这类作品是生命的需求,它是一种感官的写作,身体的写作,很疼痛,伤筋动骨。我很欣赏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苏珊·巴格的说法,她说“女性艺术家体验死(自我,身体)而后生(作品)的时刻,也正是她们以血作墨的时刻”。“以血作墨”实在是对女性写作的一个准确的界定,比所谓“个人化”要准确多了。(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原载《花城》1998年5期。为《徐小斌文集·折梦》代跋,第468页。)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作者划定的智性写作和身体/生命写作的脉络,一如创作前期、后期的划定,是太过清晰的边界。事实上,我们无疑可以在《迷幻花园》或《蜂后》中体味出那份生命和身体的痛感,而我们同样可以在《双鱼星座》、《羽蛇》里觅见那种智性的构架——尽管后者显然是徐小斌作品序列中动用了最多生命矿藏,最为伤筋动骨的一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所谓徐小斌前期创作中,她的基本叙事主题或曰生命创伤的区域便已然呈现,此后成了她的作品中不断回旋的女性的“初始情景”,成了挥之不去的迷惘与梦魇。那是一个个因此彼此重叠而显现出自我缠绕与纷繁萦回的涡旋。
《河两岸是生命之树》、《请收下这束鲜花》是伤痛间托举起的爱与温馨之梦。一个典型的空间:医院,一个现、当代女性写作中近乎症候性的角色:医生——以疗救生命为己任的理想且权威的男性人物,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负载者。如果说,这个被八十年代理想主义话语所支撑的人物、场景,或曰梦境已很快在徐小斌笔下坍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这个充当救赎者的角色已显现出他的孱弱、被动,并最终加入了叛卖者的行列;但类似的角色却再次复现于《敦煌遗梦》,就人物关系式而言,前者是年长的男人对年幼的女性的拯救;后者则不仅移向异地、异文化场景,而且成为年轻男性对年长、疲惫女人的抚慰。但一如贺桂梅君的发现(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原载《花城》1998年5期。为《徐小斌文集·折梦》代跋,第468页。):在徐小斌创作序列的起始点,她那些似乎吻合与时尚的书写方式,已悄然偏离了主流叙述提供解决方案的轨道;不仅社会解决并未成为人物命运的绝对转折,而且在那被乐观主义氢气球所托举的时代,爱情故事中远非完满的结局,生命不可弥补的伤残感已裂解了时尚或时代叙事的有效性。尽管这份朝向男性所提供的救赎的希冀,十分迅速地在徐小斌的故事世界中瓦解,但它仍不时在徐小斌的其他创作序列间闪现,但已多成了女性主人公生命中的又一份创伤与失落,有时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是一片宁静的海滩》中,出现了徐小斌作品主要的母题之一,在爱情与梦想中遭到重创的女性如何挣扎着舔净自己的伤口,在无法治愈的绝望中朝向生命。它的变奏形态,是《雾》中那个相逢非时,失之交臂的故事。此后,这母题继续在《玄机之死》、《蜂后》、《银盾》、《吉耶美与埃耶梅》、《羽蛇》中回旋。那是“痴情女子负心汉”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故事,但在徐小斌笔下,对于她敏感而备受创伤的女主人公说来,男性的叛卖、欺骗与懦弱,仍带有巨大的、无可免疫的杀伤力。事实上,在《这是一片宁静的海滩》中,徐小斌已更远地离开了八十年代前期的时代主题,而接近于青春故事的书写。那个关于女性成长的主题已然出现,而且因丁丁的死(尽管作为对时代书写方式的妥协,是一次昂扬而非凄凉的死)而呈现为断音。尽管成长故事是文学以及所有叙事艺术最古老的母题之一,但稍加细查,便不难发现整个关于成长的文化,是男性为主体、以男性生命为度量的。而女性的成长与成人,始终是一种含混,一份暧昧,一个定型化的女性形象序列间的断裂与匮乏。于是,“女孩”和“女人”的故事之间是文化的断裂带,除了作为生理与社会的阶段,其文化与心理的述说始终云隔雾障。而对于“女孩”和“女人”男性社会及其文化有着极端矛盾而对立的书写、标准与诉求。对于女性的生命与书写而言,作为一处巨大的、并不透明的文化空白,女性可能的选择是拒绝长大、或遭到成人世界永远的放逐,或丢弃自我、接受异化和改写。如果说,“女孩”和“女人”的故事始终是男性文化传统中两个彼此隔绝的系列(美妙的爱情故事永远在婚礼的盛宴中垂下帷幕;而女人的故事则始终缺乏其主体叙述的合法性,而更多地隔着不透明的种种间隔);那么,徐小斌的故事始终是“女孩”的故事(注:参见《逃离意识和我的创作》及《伊甸之光》。),尽管她的作品中很快出现那些生命与青春渐次枯萎的女性形象。但就徐小斌显然有所钟爱的人物序列说来(诸如《敦煌遗梦》中的星星,《双鱼星座》中的卜零,或《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尤其是《羽蛇》中的羽,等等),她们不曾“长大”或拒绝长大,她们始终有着一颗少女的心灵,她们始终以极度的敏感捕捉或编织新的梦境,以依托自己历经沧桑而不甘、不已的心灵。于是她们只能在一次再次的创伤与绝望中沉沦又浮起。于是,即使在一片《末日的阳光》下,她们仍与社会格格不入。但一个或许更为残酷的、女性的生存现实是,在男性/主流文化的表述中,女孩故事只能与青春共存;于是,它只能是一些短暂而辉光闪烁的时刻,只能是生命一个极端悭吝的施舍;而且在男性诗篇与书写中,尽管“丑八怪也有青春妙龄”,但那基本是美女——天生丽质的女人的特权。于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女人,一个自我放逐的姿态,势必被主流社会转换为货真价实的对离轨者的放逐:它将呈现为无视、轻蔑,乃至迫害。除却心灵的孤寂与肉体的饥渴(《迷幻花园》中,怡与“钢兰色”手枪和模拟生殖器相伴的岁月,显现出别一份狰狞,尽管芬嫁为人妇的生活同样被孤独、遗弃所毒化),尚有无尽的社会磨难。
笔者正是因此在某一层面上,将《迷幻花园》视为一个特殊的青春故事,那是围绕着一份少女的迷惘与绮想建构起来的故事:如果可能,你将在标识着青春、生命与灵魂的三张纸牌中选择哪两张?故事中两个才华过人的女性都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青春,在小说中,它亦即美丽的代名词;她们的不同在于对生命与灵魂的选择。小说无意间暴露出的是,如果说生命是具体而可观的存在,但灵魂之于女人却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或奢侈。如果我们参照在欧洲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出卖灵魂给魔鬼”的故事(浮士德、皮尔·金特或梅莫特),参照一个似乎十分相似的男性版本《道连·格雷的画像》;那么不难发现,在类似故事中,灵魂是必需的代价,而又是男性生命价值的所在;灵魂的争夺与救赎因此成了类似故事关键。而在始终作为表象、作为客体、作为人/非人间暧昧存在的女人,其版本却如此不同。此间,一个也许并不这样鲜明的差异是,男性出卖灵魂是为了浪迹天涯、追索人生或永远的感官或惟美享乐的盛筵;但在《迷幻花园》中,怡与芬则几乎是毫无“理由”地为了一个男人:金;她们在青春之泉中重生,却立刻去追寻那个曾背弃她们的男人——尽管那与其说是为了爱情,不如说是为了报复;而在徐小斌的作品中,这报复的对象究竟是那个背弃的男人,还是那个横刀夺爱的昔日女友,是最为有趣的症候点之一。因为她多数的小说中,居女性争夺客体位置上的男人,似乎显得并不重要,这场女人间的“战争”,似乎别有深意在其中(笔者下述)。尽管充满了繁复多端的表述与症候,徐小斌作品序列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一处女性反叛的不轨路,不如说,是一处女性文化的“鬼打墙”。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小斌是一个曾将男权文化深刻内在化的女性,由于对这一文化的信任与恪守,其中的种种暧昧伪善、诸多表里不一、双重标准——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成熟”者熟视无睹的林林总总,才会在徐小斌这里成了触目惊心、伤筋动骨的体验与伤痛。这体验与伤痛使她窥破而不能无视,憎恶却仍难于坦诚离轨者的宿命。徐小斌书写地形中的歧路,因此成了对女性文化别一样展露。她的精巧的、充满了“智性与诗情”(注:《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贺桂梅语。)的故事,因此有如一只负重的纸鸢。
歧路徘徊
徐小斌作品中的另外两个子序列,或许更为清晰地展现了这处女性文化的“鬼打墙”。一是自《得到的与失去的》那个十分“年轻”的“青春故事”始,徐小斌间或把自己的主人公或叙事人设置为男性(《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黑瀑》、《密钥的故事》、《蓝毗尼城》等等)。这或许是一种超越、战胜与治愈伤痛的绝望的尝试:其中最“年轻”的形态,是以男性为镜,以映照女性主人公的成功;以男性的愧疚与悔恨作为女性一份想像性的代偿与抚慰;最有趣的形态,是将女性的梦想赋予男性:对理想恋人/理想人格的不舍的追求,对梦想的固执,对现实的不妥协姿态;似乎是在希冀使自己的伤痛体验获得“人类的普遍困境”的超越价值,以男性故事为女性叙述争得“合法”依据;同时它间或出自推己及人,以期在自己的内心中获取一份原囿,一种治愈伤痛的可能。或许这些异时、异境、异乡的故事,在智性游戏的包装下,亦是想窥破男性生命“真相”的绝望努力。
构成其书写地形图最为繁复的迷宫段落的,是徐小斌作品中的女性场景。我们间或可以将其称之为女人间的“战争”。女人的猜忌、女人间的争夺(或者不如直白地说:争宠)、女人施之于女人的迫害、摧残——事实上,是男性书写中的古老故事。但在徐小斌这里,它却成了其女性书写中至为伤痛、迷人而又充满困窘的段落。我们可以将徐小斌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静悄悄》——对少女时代的挚友分道扬镳的故事,视为这一母题的发端,尽管这个故事无疑是一个稚拙、造作的时尚叙事。这一母题所包含的繁复斑驳、而又极端伤痛的经验表露,是在徐小斌的长篇处女作《海火》之中。支撑着这部长篇的,是双重主人公,一对女友:方菁和郗小雪。尽管在笔者看来,作者所设定的最初的文体与文字实验的目标:“把最虚幻的形而上空间与最现实的符码结合起来”(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并未达到,但作为一部颇为别致的青春故事(校园小说?),却凸现了徐小斌写作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情景:一个女人投向另一个女人的执著而又痴迷的注视,其间无疑有着皈依于姐妹之邦的渴望,有着同性恋情的幽隐;但这情同手足的姐妹情谊,却终因男人的闯入而跌得粉碎;因此成为一处或许终生不愈的伤口。如果说,“女子无真相”、“女人无友谊”,是至为牢固的男性话语,似乎女性间的至爱,只是男性登场前的情感热身;一经男性登场,“他”便成为君临的绝对主角,女人——甚至誓同生死的友人亦将为争夺男人而反目成仇。那么,在徐小斌貌似重述的类似故事中,这一“现实逻辑”,却呈现出远为繁复的脉络。毫无疑问,《海火》构成了徐小斌创作的转折点,由明媚、昂扬的时代基调,由“善”的场景,转向迷惘人生,转向“恶之花”,转向幽暗、间或险恶的心灵迷宫。在故事层面上,方菁和郗小雪构成了此时为徐小斌所迷恋的面具人生或双重人格的展现。所谓:“她们是一个人的两种形态”(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我是你的幻影,是从你心灵铁窗里越狱逃跑的囚徒”(注:《海火》。)。但这个一对至爱的女友最后成了角逐的对手与终生未了的仇家的场景,却不断在徐小斌的作品中复沓回旋:作者曾把《海火》故事缩写为一个中篇,略去了其中众多的情节、人物,只留下方菁与郗小雪的故事,取名《如影随形》;她们同时是《迷幻花园》中的芬和怡,是《吉耶美和埃耶梅》中的徐茵与吉耶美,是《羽蛇》中的羽和金乌,羽和安小桃,羽和亚丹。它复现得如此频繁,而这些篇章又无疑是徐小斌作品中颇为重要的篇什;于是,它便再度指向一种特殊的女性的伤痛经验,一份或许比来自男人的叛卖更为深切、更难释怀的记忆,一个血痕犹在的伤口与情结。在这些故事中,始终是以某一女主人公的视点出发,她通常是某种“理性”的指称(尽管在徐小斌的序列中,“她”渐次滑脱“理性”之轭),于是另一女主人公的神秘、不羁、魅力与阴险便呈现在前者那迷恋又不无恐惧的凝视/窥视之中。徐小斌自己曾以“镜象置换”来描述芬及怡的关系——这类故事确乎是女性投向同性、投向自我的痴迷注视,一种阐释在男权文化下无尽扭曲的女性心灵之谜的绝望尝试;但在笔者看来,它同时是经验层面为姐妹情谊所留下的创伤,是意识与潜意识中对姐妹之邦的向往与恐惧,一份欲罢不能的渴求。如果说,在徐小斌这里,姐妹之邦始终是一处逃离之所与庇护的天顶,那么它不仅为经验中的伤痛所隔膜,亦为对其间不轨之举的恐惧所断绝。关于《迷幻花园》,徐小斌写过如下的自陈,它在一份女性彻悟式的宣告同时,表达了女性的绝望与无奈:
更加可悲的是女性在选择中有着双重困境,因为她的命运需要借助男性的选择。父权强加给女性的被动品格由女性自身得以发展,女性的才华往往被描述为被男性“注入”或由男性塑造,而不是来自于和女性缪斯的感性交往。……芬和怡穷其一生变换纠缠于一个绝对的男性,到头来才发现维系他们一生命运的原来只是个“蓝田猿人”式的“活化石”。如果再给她们一次选择的机会呢?答案已经有了:她们依然会错。她们依然会掉入人生悖论的圈套之中。那是一次小女孩的纸牌游戏,这游戏的妙处就在于:选择的结果永远是错。
除非将来有一天,女性之神真正君临,创世纪的神话被彻底推翻,女性或许会完成父权制选择的某种颠覆。正如弗洛伦斯·南格尔丁胆大包天的预言:下一个基督也许将是一个女性。(注:徐小斌:《出错的纸牌》,原载《作家报》1995年,收入《徐小斌文集·折梦》第305-306页。)
其语词中充满“胆大包天”的僭越,但这僭越不仅充满了绝望的,而且潜在地认可着秩序的疆界与前提。在对父权制的异性恋婚姻制度潜在的认可之下,僭越的想像只能是负重的纸鸢;它如果不是“注定失败”、“以身试法”的悲情之战,便只能是朝向一个“女性之神”君临世界的未来梦想。再一次,类似故事与书写,是对男权话语“铁定逻辑”的颠覆,又是对其内在化程度的印证:女人/女友间的战争,是对女友叛卖的报复与想像性的占有,也是对男人——欲望客体的争夺。那既是一种不轨的欲望指向,是一份深切的结盟渴望,又是伤痛与失落的回声;那是生命的一岸,却一次再次地在登临时刻坍塌落水。因此,在一切之后,是郗小雪对方菁关闭的房门读出留别的诗句,是芬和怡共同注视着那个“活化石”样的男人,是金乌献身般的相助,也是羽/金乌/亚丹间的相弃与彼此永远的凝望。在此,对男人情爱,较之女性间的厮杀与战争,较之她们的纠缠、深恨(借用一句关于爱的套话:“恨无非是未尽的爱”),更接近于某种无妄与无奈。
尽管徐小斌的作品在令人目眩的泼洒的浓重色块、多向的丰富的知识(荣格、弗洛依德、海洋生物学、博弈论、密宗佛教或上古神话等等)与奇异的异地间回旋,但笔者倾向于将其读作关于现代女性、女性的生存与文化困境的寓言。毫无疑问,徐小斌的作品不仅仅关于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于现代社会、现代生存。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年,在那“理性”被供奉在圣坛之上的岁月,《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已经明确成为对理想/疯狂的质询,同时遭到质询与讥刺的,还有现代人的功利、冷酷、苍白与拜金;而出版于1989年的《海火》,则在“发展论”占据绝对主流的时代,提示着环境、生态与自然。徐小斌无疑是一个现代感极强的作家,尽管她的故事不断地转移着场景,不断更换着她“生活在别处”的叙述,但那些故事确乎因此而凸现一个现代都市人的经验和陈述。在她的笔下,都市是一处欲念浮动、却遍布饥渴的所在;她的异地、别处因此成为别一层面上的逃离,逃离文明的囚牢,逃离都市渊薮,逃往自然的生存。尽管佤寨(《双鱼星座》)、孟定(《缅甸玉》)、敦煌(《敦煌遗梦》)有着极端明确的乌托邦定位;而且异乡(《兰毗尼城》)、异时(《玄机之死》、《古典悲剧》)只是别样清晰地透露出文明社会的谜底与女性永远的悲哀。但是,与其说徐小斌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或者用她自己说法:“狭义的女性主义者”(注:徐小斌:《出错的纸牌》。)),不如说,她的性别书写出自不能自己的生命体验。当然,这份了犹未了的伤痛与不甘,已渐渐浮现为一份充满张力的自我意识,一个痛楚的女性的自指。《双鱼星座》因此成为徐小斌作品中一个异常重要的篇什。它十分明确的是一部关于女性、现代女性的寓言,小说的副题索性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徐小斌将故事的主人公卜零称为“菲勒斯中心社会”(注:徐小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徐小斌文集》第343-344页。)的逃离者。但她之逃离,却是逃往梦境,在梦中她极端冷静地依次杀死了徐小斌所谓代表“权力、金钱和性”的三个男人。梦醒之后,她再度逃往乌托邦式的边寨。
正是《双鱼星座》,显露出徐小斌作品中女性文化的一种深刻的潜意识形态:女性对于男性的深恨与复仇,永远只能在想像中表达、完成。卜零只是在梦境中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冷血杀手,而在现实中,她只能是一个脆弱、孤寂而饥渴的女人,她只有一次次逃离,而她又只能逃往乌有之乡(尽管现实中的男人会在卜零梦中袭击的部位感到疼痛,但那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伤害。如果我们将其比之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在《发条鸟年代记》中类似的描写,便会发现主人公的在别一空间维度中的袭击,会使被袭击者遭到致命重创)。一如芬朝向一个电影的拍摄场景射击,充其量是谋杀的表演。似乎惟一的女人的复仇,成功于《蜂后》,但不仅那个奇异女性是一个类人而非人的生命,而且那却多少是一次误杀。与此相反,男人对女人的侵害、叛卖却迫近、真实得多。它在《银盾》与《玄机之死》中,尤其惊心动魄的是在《吉尔的微笑》里。那是一个性别的记忆,又是一个性别的禁忌(这禁忌一直到《羽蛇》中,方始被打破。但羽却必需为对弟弟的谋杀付出她的毕生)。徐小斌不断地书写着这历史的空白之页,又不断恐惧着那空白显现出的字迹与血痕。她展示女性文化的一处歧路,一次或许难于终结与结论的徘徊。
《羽蛇》
从某种意义上说,徐小斌也是一个创作的潜伏期颇长的作家。尽管在一段创作的休眠期(1989-1991年)之后,她以《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等一系列作品的爆发式创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相对于她在不惑之年推出的长篇小说《羽蛇》(单行本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迷幻花园》及其她此前的创作,便只能算是热身赛。事实上,徐小斌是当代文坛上以自己的(尤其是九十年代的)作品而拥有自己的读者群的作家。如果说,她对巴赫赋格曲+埃舍尔怪圈的迷恋,使她着力于营造作品的迷宫式结构;她的充满伤痛感的女性生命体验,使她一步步接近禁区;那么她对于生存的“普遍命题”着魔般的固执,青春故事表层结构,以及她广泛涉猎的知识领域和她的异地场景,则使她的作品具有流畅迷人的可读性。在笔者看来,这种流畅与可读,与作品中迷宫路径式的营造,是徐小斌作品所呈现的另一份张力。它同样在冒犯与妥协之间,构成了徐小斌独特而难于定位的文坛位置。在另一层面上,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九十年代几乎成了一个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久违了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姑且将图书市场与纯粹意义上的商业操作存而不论,这种文体与社会变迁间的对位与错位本身,便是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命题。而许多其创作脉络始于八十年代的女作家此时不仅推出了她们的重要长篇,而且这些作品本身具有明确的自己的创作轨迹及生命线路上最赫然的界标的意义。《羽蛇》便是其中重要而有趣的一部。
事实上,《羽蛇》蔚为壮观的百年时间跨度,巨大的、尽管时常隐没在朦胧暗淡的背景中的历史画卷,与浮雕般地凸现其上的五代众多女人的故事,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一个创记录者。而且《羽蛇》无疑是九十年代女性写作中一个特殊的脉络“女性世序”/母系家族史的延伸。如果说,王安忆的长篇巨制《纪实与虚构》,是从母系的家族进入,以其建立起一个不同的“中华文明”及“民族记忆”的叙述;作品因此具有一个宏大的、僭越式的文化企图,它的副标题索性是“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那么,其中有趣而颇富深意的呈现,是一旦母系家族的故事脱离了生者的记忆与死者的口头传说而进入文字与书卷的历史,便成了母系家族中的父系故事;因此作为准自传式的个人生命史的书写线索与久远的家族(母系?父系?)史,亦即文明史的微缩本的追述间,便呈现出一份奇特的张力与参照。而在蒋韵的家族小说《栎树的囚徒》,则显现了另一个有趣的女性文化征候:那便是女性家族故事,事实上面临着女性的血脉与男性的世序间的巨大裂痕。于是她书写父系家族中的女性,那些因婚姻制度而偶然地连接在一起的女人的故事。这些女人的故事惊天动地、凄艳迷人,但她们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她们惟一能选择的便是死:死亡的方式与死亡的时间。
如果说,蒋韵的故事中充满奇诡缤纷的死亡;那么在徐小斌的故事中则充满了畸存。在扭曲、伤害与一次次地缝合之后,这些女人(包括故事中惟一一个重要的男人:圆光/烛龙)如同历史和岁月的遗物般苟活在人世间,直到历史变成了童话,而童话中的主人公却像是其中的残骸或污渍。有趣的是,尽管《羽蛇》中的诸多女人不无精彩刚烈的女性,但她们却无一在属于自己的剧目落下帷幕之后,退出生命,她们顽强地穿越岁月与历史的绝望和洗劫,直到死亡——自然的或非自然的死亡将她们带往“别处”。毫无疑问,这个女性世序的故事,同时是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不仅故事的主人公羽/羽蛇,那是“远古时代人类对太阳的别称”,而且“金乌、若木、玄溟……她们都是远古时代的太阳和海洋,她们与生俱来,与这片土地共存”(注:《羽蛇》中语。)。那不仅是生命,而且是生命的太阳。在笔者看来,如果说羽蛇、金乌或若木们,是太阳的象征;那么她们更近似于日蚀时刻的太阳:一种黑暗中的炽烈、一份幽冥间的灼伤。对于玄溟和若木,甚至羽,她们不仅灼伤自己与他人,而且彼此灼伤。她们甚或以自伤构成对他人的灼伤,而自伤又是她们惟一避免被他人灼伤的武器,因此,曾以《若木》为题先期发表的段落,无疑是小说中精彩的章节之一。那个在黑洞般的闺房里跪着的、如同“白纸剪成的少女”及她嘴角的那缕狞笑,无疑带有一份梦魇般的可怖回声。
如果说,在徐小斌作品中,女性间的场景,女性施之于同性的摧残,是一个繁复而强烈的情结式的常数;那么它在《羽蛇》中达到了极致。而且它不仅是女友间的亲昵救助与争夺、背叛;而且呈现为曾在《天籁》中初露端倪的另一“初始场景”:母女场景。徐小斌曾告白:
我用了很重的笔墨来写母女关系,当然主要是羽和若木的关系,若木和玄溟的关系,亚丹和孟静的关系……慈母爱女的画面很让人怀疑。只有金乌,因为没见过母亲,才把母亲想像成绝美的象征。母亲这一概念由于过于神圣而显得虚伪。实际上我写了母女之间一种真实的对峙关系,母女说到底是一对自我相关自我复制的矛盾体,在生存与死亡的严峻现实面前,她们其实有一种自己也无法正视的极为隐蔽的相互仇恨。广义的说,有些女人具有“母亲情结”,而另一些女人具有“女儿情结”,前者有一种权力欲,喜欢控制他人,而后者则是永远的女孩。“母爱”可以摧毁女儿青春、心智与爱情,因为“永恒的母亲”已经成为正确的象征,在彻底毁掉女儿之后在公众面前赢得掌声,因为她的原意是要使女儿成为一个“正常人”,这的确是一种滴着血的残酷,还在于,它表面上是以“女儿”获得幸福为前提的。(注:《伊甸之光》,见《徐小斌文集》第475页。)
在此,颇为有趣的是,类似书写和告白,除却明确展示了徐小斌的“女儿情结”、展示了她伤痛经验的核心之一:以健康、正常和爱心为名的摧残、压抑,乃至迫害,便是十分清晰地,作者于此尝试颠覆关于女人的“母爱天性”的神话。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女性书写的传统之一。张爱玲曾以她睿智、优美的笔墨,写到这种母亲对女儿的剥夺与践踏。然而,也正是在这里,那堵女性文化的鬼打墙再度显影:在《羽蛇》中母女相残的场景,始终以父亲的“缺席”为前提。在玄溟、若木的角逐之中,那位曾为革命党、而后堕落奢靡的父亲远在他乡;在若木、羽的冲突里,那位丈夫和父亲完全无奈而无助(事实上,那位父亲陆尘,正是玄溟、若木合谋的一场骗局的牺牲者;此后他便像是家庭悲、闹剧场景里的可有可无的道具和傀儡);在孟静、亚丹的关系式中,那位父亲已死于华年。于是,这些母亲们无血的暴行,便似乎是无因之果或互为因果的。它似乎在父权社会之外,而并非父权社会的造物与投影。而在这幕悲剧中,常常是男性成为乏力的正义者:是弟弟天成将若木从死亡的边缘救回,而羽则是父亲无力保护的“爱女”。
毫无疑问,《羽蛇》是徐小斌写作中最为着力并伤筋动骨的巨制。它不仅包含先期发表的、原本属于长篇中的片段《古典悲剧》、《若木》、《雪霁》,而且几乎重现了徐小斌创作中的大部分“初始情景”与叙事动机:母女场景与“姐妹”间的反目,羽和医生丹朱的故事再现了《河两岸是生命之树》与《请收下这束鲜花》中的温馨记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的冰湖,此时成了羽梦魂萦绕的林中蓝湖;《银盾》中的寻母主题再现于金乌的故事;而徐小斌的处女作中的故事,成了亚丹的第一部发表的作品;《末日的阳光》中的女性个人化的历史写作或曰“文化大革命”故事,此时贯穿了《羽蛇》的诸多篇章。《兰毗尼城》中的刺青,此时成了羽赎罪的“羽蛇”——显然,徐小斌对刺青这一象喻有一种特殊的迷恋,那是血肉的图画,它或许具有“以血代墨”的女性写作的象征意义;但同样有趣的是,在《羽蛇》中,那出自男性大师的手笔,而且羽穷其一生亦未曾目睹这幅神秘的图画。如果说,在故事中,它间或是羽的真身或前世;那么在其意义层面,它间或成了男性书写于女性(在故事中,它同时是法严与圆广——两位绝无仅有的理想男性——的双重或三重书写:背后、胸前的刺青及圆广和羽的“初夜”)的天谴或神宠的标记。事实上,无论是刺青/书写、还是男女性爱,或者蛇的形象,都可以读解为菲勒斯中心文化的象征。羽正是在此,以向男权文化的“血税”以赎救自己对男权文化的罪责:对弟弟、家族香火的延承者的谋杀。但,于笔者看来,也正是在这里徐小赋再度展露一个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核心的“情结”:秩序中的反叛者对秩序的嫉妒复杂的情感与剪不断,理还乱的牵系。
在此,一个极为重要的改写,是徐小斌不再将自我与身为女性的文化迷乱外化为他人,它不再将它们赋予郗小雪或景焕,而将自我躲藏在相对苍白的方菁们背后。我们可以说,在这部长篇中,徐小斌以裸脸面世,用王安忆的说法,便是:“现在我们对自己的挖掘到了深处,到了要使我们疼痛的地心了”,“将你心中最深刻、最私有的东西公开化,是一种牺牲”(注:王安忆:《神圣祭坛·自序》。);也可以说,她在裸露的同时,更深地躲入镜象的闪烁斑驳之中。在此,这份自我与女性的迷乱,构成了一组对称的形象:羽和亚丹。如果说,羽是一个飞扬的、神奇而蒙难的自我镜象;那么亚丹便是自我的现实漫画像。姑且搁置羽和亚丹故事中的种种曲折,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便是徐小斌九十年AI写作作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女性身体和欲望书写的浮现。类似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徐小斌毁誉并至。但它再度呈现一个颠覆与臣服、逃离与皈依式的表述。但有趣的是,在《羽蛇》中,真正的主角:羽,几乎是一个非肉身的存在(“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性”(注:《羽蛇》题词。)),她的身体仅仅用来承受伤害、自毁与苦难;她的欲望近乎激情,但那是一个无处附着的灵魂和饥渴与不宁;而肉体的、迹近疾患的欲望则被赋予/外化(?)给亚丹;尽管同样充满了创造力,但亚丹更接近与“原始”的女性:她的欲望,她的“沃土般”的身体,她为人母的身份。但欲望之于亚丹,同样是一份匮乏与磨难。只有金乌,这个无母(同时无父)的女儿,这个没有年龄、从容地穿行在时空中的女人似乎获取着一份精神与身体、思考与行动的平衡和完满,但她的中/M混血儿的“来历”似乎展露着徐小斌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另一种想像与潜意识的流露(作为一个注脚:故事中那羽最后的引渡者,那个驾帆船——诺亚方舟的男孩,那个乘大鸟而来的男孩,同样有着讲英语的M国形象)。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长篇小说《羽蛇》中最重要的一种尝试,在徐小斌近二十年的创作之途中,第一次显现徐小斌始终不曾暴露的一重“身份”,一个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份,一个身为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的参与者与亲历者的历史记忆。如果说,在此之前,徐小斌更多地书写闺房、密室,那么这一次,她的场景中出现了广场。这是出自对“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健忘”的痛悟,出自一个并不多见的感悟:“历史经验的断裂毁掉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人,每个目击者都会有一种深度的疼痛”。也正是在这一对当代中国历史的书写里,对逝去不远却已遭遗忘的悲剧撞击的记述中,徐小斌复现了一个已消失于她九十年AI写作作中的文化情境或曰文化情结:八十年代或曰对精英文化的尊崇与向往。一位理想男性烛龙/圆广藉此而得以复归。在这里,八十年代前期女性书写的一个重要的征候亦随之复现,构成别一类徐小斌的反叛与皈依,即,尽管毫无疑问,是徐小斌背负着这历史/政治的记忆,尽管是她体味着那份“深度疼痛”,但却始终是男性/烛龙贯穿在这宏大历史的场景中,并当然地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亚丹是一个一度追随在他身边的女人,而羽却只是一双投射着炽热的目击的影子。她只有爱,一份得自前世记忆式的不已之爱,一份小人鱼对王子式的献身与绝望。不错,徐小斌以异国他乡,烛龙卑微无言的死亡,为八十年代精英主义的文化举行了一次充满切肤之痛的送别与葬埋;但那个时代的遗产、记忆与身为知识分子与女性双重身份所构成的情结,却远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告离。
或许《羽蛇》作为徐小斌一部重要长篇的意义,不仅在于她书写了什么:五代女人的故事,或对男性精英主义文化的记述与薄奠;而且在于她如何书写。或许《羽蛇》自身的书写方式,比它的“内容”更清晰呈现了那个历史断裂、历史经验断裂的文化、文学命题。在这个徐小斌所谓以“威顿——桑特DLA簇”命名的神奇的树枝状的家族血缘图示的文字书写中,表现了徐小斌跨越断裂,至少在女性世序、女性记忆的意义上弥合四分五裂的历史/现实书写的企图。颇有深意的,是一如贺桂梅君所言:“《羽蛇》处理了百余年的历史,却没有形成断裂,这很不容易”(注:《伊甸之光》,见《徐小斌文集·折梦》第478页。);小说结构的精心建构的确弥合了巨大了的历史跨度与文化断裂,但这显现为传奇、谣曲、神话、不同时代的时尚叙事的拼贴画面,本身却不期然间印证了深刻的文化断裂的存在。徐小斌在时空跨度间的自主往返,在不同时代叙事风格间的轻松过渡,确乎显示了她的文字能量:在近、现代之交的叙事中,那种《红楼梦》、《金瓶梅》式的语调与场景、在现代故事中文艺青年书写的文笔、在当代叙事中的边缘的延安叙事、八十年代书写中特有的那种激情而痛楚、真挚而矫情的画面,以及在寻根文学及徐小斌九十年AI写作作中得到充分展开的魔幻笔调,它在构成一幅全景图的同时,显现了文化与记忆的纷乱与异质。
徐小斌说:“写作长篇是一种深度休眠”。她又说,写作《羽蛇》是她多年来的情结(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那么《羽蛇》作为徐小斌诸多女性的与文化的情结的展露,是否意味着一次新的僭越与治愈?前面,是未了之路。笔者仍在徐小斌的“出世”与“入世”间期待。再次借用贺桂梅颇为精当的话,作为此文的结语:“在九十年代的世俗与超越,拜金狂潮与人文情愫,众声聒噪与‘天籁之音’的冲突与对峙中,‘徐小斌现象’值得我们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她弥足珍贵。”(注:贺桂梅:《伊甸之光——徐小斌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