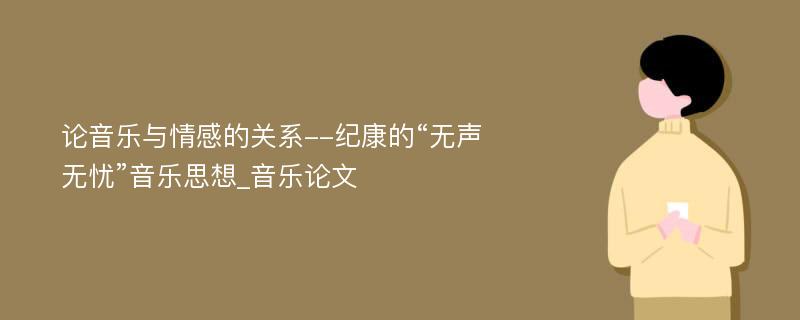
论音乐与感情关系——嵇康《声无哀乐论》的音乐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哀乐论文,音乐论文,感情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对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的认识直接涉及如何理解音乐作品的意义。音乐与情感各自独立,但是在对应的关系层面上两者产生了关系,这使得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出现多种不同的现象。在多种复杂的关系之中,声无哀乐和声有哀乐皆有其合理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到嵇康论述音乐与情感关系方面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 嵇康 声无哀乐论 音乐 情感 对应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一篇很有理论思维和价值的文章,重点论述的内容是音乐与人的情感之间的关系问题。大凡论及这篇文章的批评史或美学著作,都要指出嵇康思想的一点不足,便是嵇康把音乐与情感截然分开。李泽厚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也认为“这确实是嵇康的片面性所在”,同时又认为“在片面的形态中包含有深刻的真理”[①]。然而嵇康关于音乐与情感关系的理论恰恰不是那种所谓偏面的深刻真理,而是一种完整的科学描述。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否定嵇康理论,其原因是艺术为情感的表现,音乐自然也不除外,因而音乐必然是情感自身的表现,然而这是一般而论。否定嵇康的理论还有其历史的根源,那便是与嵇康思想完全对立的儒学音乐思想。儒学音乐理论历来极其重视音乐的作用,从孔子开始有很多关于音乐的论述。儒学重视音乐原因在于把音乐本身作为儒学的重要组成,强调音乐的社会感化、立身养性作用。概要言之,儒学以为“人而不仁,如乐何”[②],“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③],其理论根据无非是“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④],进而认为“乐不可以为伪”[⑤]。感物而动,情必摇荡,发为音声,声必真实,由此自然知道其时之政,其时之礼。嵇康反对儒家的这种理论,与毛诗大序针锋相对,他把音乐理论与玄学思想结合起来,提出音乐与情感之哀乐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提出应当是一种对应关系,认为音乐与感情没有必然关系。
嵇康在反对儒学的音乐理论时,出发点自然与反对儒学相关,但是嵇康也并不是完全反对儒家思想。在《声无哀乐论》之中也吸收了儒学思想,如“乐不至淫,哀不至伤”的美学原则,也不否定儒家对音乐的社会作用理论,仅仅是反对把音乐的作用夸大和神秘化。问题在于嵇康在反对儒学理论时,并不是仅仅依赖于儒道思想的分歧,而是结合音乐本身的美学特点进行辩驳的。嵇康的根据是:首先,音声自有善恶,与人的哀乐没有本质联系。嵇康提出“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⑤],“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⑥]。嵇康认为音乐他有自己的“自然之和”,乐音的组合有自己的规则,与人的感情无关。这里所谓的音声与情感的无关是指音乐与情感本为两物,音声本身并不传示什么情感,情感本身也并不与音声有关。乐音的变化如宇宙的阴阳五行运动,并不以人的情感而改变。然而人们总是把乐音与情感混为一谈。嵇康以酒为例说:“酒以甘苦为主,而酒者以喜怒为用。”[⑦]如果乐音喻为酒,那么可以知道酒本身并没有哀乐之情,只有酒味芳香与否,酒香可以使人情感变化,但酒香本身并不是情感。这一例子较为恰当,西方著名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也以类似的看法来说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玫瑰发出芳香,但它不是以‘芳香的表现’为它的内容的。”[⑧]花的芳香仅仅是一种香味而已,并没有更多的“味外之旨”,如果在香味之外表达什么东西,那便不是香味本身在表达什么,香味本身并不是情感现象。因此“从根本说,一首乐曲与它所引起的情感动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因果关系,我们的情调是跟我们的经验与印象的不断变化的观点而转变的。”[⑨]从总的理论上说是如此,如果具体去看音乐构成,则会发现嵇康理论的科学性。从最浅的层次上说,音乐是一个个的音构成,先从一个单音而论,只有物体振动之快慢,形成声音之高低,而物体振动之形式决定了音色变化的悦耳与否,也直接刺激着人的耳觉。另外音乐毕竟不是单音,由诸多单构成,是“五音之和”。这种自然之和是超越于人的情感,是“物之自然”所致,从而形成五声之善恶。从单音到“声比成音”,声音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自然规律,这种规律不会因为人的情感变化而变化。如嵇康所谓“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⑩]古代的五声音阶也好,现在的十二平均律也好,音与音之间的搭配和组合,有它自身的自然性和规律性。例如在以五声音阶为基础构成的乐曲之中,没有任何引入半音的准备,突然加入一个半音,就会破坏音与音彼此和谐连贯的特点,从而使整个乐句或乐曲变成“不善”。如果以135大三和弦为基础构成的乐曲之中,过多地使用246和声为基础的乐句,就会破坏整个乐曲自身存在的风格。每一乐曲的调式,都各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不是人为地可以变的。我国古代的戏曲音乐理论就有了以调性为基础的宫调理论,燕南芝庵的《唱论》中就说:“仙吕调唱,清新绵邈。南吕调唱,感叹伤悲。中吕宫唱,高下闪赚。黄钟宫唱,富贵缠绵。”[11]这里所说的宫调的特性正是嵇康所谓“其体自若”,每一宫调正是具有自身具有的特点。宫调的缠绵或富贵,非作曲家者给宫调以感情特色,是作曲家发现并利用了宫调的特点,因此可以说元曲的音乐理论不仅是进一步证明了嵇康的音乐思想和理论,也是进一步完善了音乐的情感理论。从节奏来看,快板易产生欢快、轻松,慢板易于抒情。这是音乐自身的规律性,虽然人的情感可以利用这些声音的规律性和自然性,达到表现内在情感的目的,但这不过是利用这些声音的规律,而不能创造声音的“自然之和”。“自然之和”正是汉斯立克所谓的音乐的独立性,“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12]
嵇康认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由此出发他反对因声知音的儒家理论,提出“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13]。这一问题直接又联系到言意问题,“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14]既然声音与人之心是彼此分立,没有必然联系,那么以声知心或以乐传情,都成了不可能的东西。因此嵇康批驳了葛卢闻鸡鸣,师旷吹律,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音乐既然不能表达人心,显然想从音乐的旋律确定音乐作品的主题或者某种思想的理论也是一种假定而已。汉斯立克也认为:“有些人声言音乐在人类精神的启示中占一个卓越的位置,可是音乐没有这个作用,也永远不会有这个作用,因为音乐没有传达思想信念的能力。”[15]这样就把诸多作曲家们宣扬的音乐作品具有深刻思想主题之说给否定了,音乐作品不仅本身没有情感,同时也是没有任何具体而深刻思想可言。汉斯立克进而认为“审美地接受音乐的最基本要求是:不管听什么乐曲,不管怎样理解,必须以乐曲本身为目的。要是把音乐只作为手段来加强我们的某些情调,或作为陪衬和装饰,那末它的作用就不再是纯艺术的。……数以百计的关于‘音乐艺术’的论断都与音乐无关,而只是牵涉到音乐原料所产生的感性效果而已。”[16]
其次,“声之与心,明为二物”,音乐自身没有情感,也没有思想,这是不是说音乐与情感之哀乐截然无关?嵇康没有简单地推进到这一步。他认为音乐与人的哀乐有关,但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对应关系基础上的,而不是必然的联系。嵇康就是在这一层次上谈了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曲度五音之会,“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比由声也”,“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17]。这几句话中都用到“应”字,这里的“应”字正是在对应的关系意义上讲。乐曲自有单复高埤等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决不是无关乎人的,乐曲的调式的高低、节奏的疾舒,都会给听者产生影响,听者的感情、心态为之而动。这种因声而动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应的,情感会躁静专散的反应。然而从这种对应的关系不能认为构成乐曲本身的内容与所反应的内容处在相同的层次,认为音乐作品本身含有情感意义。可以说反应的情感往往仅限于情感的基本形式,而不能具体、清晰地把握乐曲本身究竟表达的情感内容和意义。仅仅停留在对应关系的水平上,也就是“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意思是说在对应关系层次上,情感的反应只能是停留在模糊、基本的形式。汉斯立克也从音乐的节奏快慢强弱等形式论述了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问题,认为音乐“只能表现情感的‘力度’(dasDynamische)。音乐能摹仿物理运动的下列方面:快、慢、强、弱、升、降。但运动只是情感的一种属性,一个方面,而不是情感本身。”[18]嵇康也是在音乐的物理运动的层面上论述了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而不是认为音乐的物理运动本身就是情感的运动。比如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从它的主题音乐和副主题音乐的发展之中,情感会出现变化:当主题出现和发展时,情感变得有力和坚实,当副主题出现时则情感松弛而沉静。我们很难说这种基本的感情形式究竟表现怎样的具体情感。当然可以根据个人的生活经历加入很多内容,使抽象、基本的情感形式具体化。但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情感反应限度,不应认为是音乐作品本身寓含的。正因为音乐与接受的情感是一种对应关系,所以情感反应才会相当地抽象与模糊,而不是通过作品直接抵达作品自身的内容和作曲家创作时的情感。如果说音乐与情感关系为必然的本质联系,那么情感应该能够达到作品本身所含有的内容,或者是基本接近,也就是说音乐作品本身在内容上的限定性将会更为明确。当然这并不是说作曲家的情感完全传达到接受者的情感之中,作曲家以音乐的方式赋予情感以一定形式,使情感得到表现。但是接受者的情感只能在对应关系意义层次上抽象地接受而已。也正因为是这种音乐与情感对应关系,使音乐作品极其抽象。作曲家就在作品上经常写“富于表情地”、“哀伤地”、“沉痛地”等等名目繁多的感情要求,借此来规定作品的感情,也使演奏正确理解作曲家所要表达的情感。如果音乐作品自身完全可以靠自身表达这些感情规定内容,那么完全不必要作曲家写此类语言,只需要写上中板、快板等等之类的音乐术语便可以。
其三,嵇康还相当深刻地论述了音乐与情感在感情关系上的无常性问题,从另外一个层次,继续分析了声无哀乐的问题。因为情感与音乐处于一种对应关系,而不是必然关系,因此心志之应感而发是无常的。嵇康说:“曲用每珠,情随之变。”“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声音之无常哉?”[19]一方面由于音乐与情感的对应关系,基本在一定限度上会限定情感的形式,另一方面又由于对应关系会使同一乐曲出现全然不同的反应,听到快乐的曲子却哀伤,而听到苦闷的乐曲反而快乐。常常有人认为戏曲音乐具有相当程度的情感不确定性,以为这是戏曲音乐落后之故。戏曲音乐确实存在上述现象,同一个曲牌的曲子,似乎应当是表现相同或相近的内容,然而时常表现着完全不同的曲词内容。曲牌〈油葫芦〉在不同的戏曲作品之中表现着不同的内容,在尚仲贤《尉迟恭三夺槊》的第一折的〈油葫芦〉其内容是如下:“想当日背暗投明归大唐却须是真栋梁。划地厮提防。比及武官砌垒个元戎将、文官挣揣个头厅相。知他是几个死,知他是几处伤……”[20]又如郑德辉《钟离春智勇定齐》中第一折也用了〈油葫芦〉,其中唱道:“你着我针指匆匆居草堂,又着我攀绣床。不如我抚瑶琴学舞剑诵文章。……”[21]这里可以看到同一曲牌表现的意义和感情有相当大的差异。元杂剧的一折一般都一宫到底,虽然受宫调限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情感限制,但是也同时可以发现一折之中的宫调和曲牌大致相同,如第一折多用仙吕,曲牌用〈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等等。在这些相同的宫调和曲牌之中表现的却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情感,即不管戏曲作品内容有多大的差异,用的宫调或曲牌没有多大的差异。可见情感与宫调、曲牌之间具有相当大的距离。其实不只是古典戏曲音乐这样,现代音乐作品也是如此。一首怀念故土的歌曲《北国之春》可以把歌词改写为失恋或想念恋人的歌曲,并没有什么乐谱与歌词不和谐之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王启明在最悲痛的时候唱的竟然是歌唱毛主席的歌曲。音乐虽然基本给定了可能被唤起的情感,但因为这是一种对应关系,因此可能会出现“无常”。为何产生这样的无常现象?除了根本上是对应关系之外,还因为对音乐的理解往往与个人生活经历和当时的心情相关。这就嵇康所谓“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22]。实际上当体验音乐时,听者根据乐符的高低快慢,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投射于音乐之中。在这种投射之中,听者的体验把音乐构造成了心中的音乐,并把自己的生活经历与音乐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些联想,并以为这些联想正是作品所要描绘的情景,同时也以为其中的情感本身也是音乐作品内含的哀乐。然而听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已经在无意识之中把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投进了作品之中,却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美国著名音乐理论家伦纳德·迈尔说:“一个听众报告他感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时,他相信他正在描绘的那种情感,是这个乐段所真要表现的,而不是他自己体验过的任何情感。”[23]由于因音乐作品的促发,听者在重新经历过去体验过的情感之中接受了音乐,这样听者的感情和生活经常变化,因此在音乐与情感之间会出现“无常”现象。这种无常有时可能会出现“闻歌而哭”完全相反的情感反应现象,嵇康所举的例子似乎给人以片面的感觉。因为即使有这种现象,也仅仅是极端的例外现象,这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但是这种极端个例也说明了音乐与情感之间的关系,除这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之外,可能大多的情况是一定范围内的情感反应,也就是说情感反应出现一定的概率性。概率性不仅限定了情感反应定范围,同时也使情感反应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嵇康曾在《琴赋》中所说的“触类而长,所致非一”,最终的情感结果不是同一,但是由于相似之物的体验,终究还是有一定程度范围,从而产生概率性。
但是我们的确可以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首乐曲或歌曲,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感情基本是固定的,这似乎表明了音乐与感情之间的必然联系,其实非然。原因如下:1、从总体而言,一首乐曲无论是有标题音乐或无标题音乐,都以文化的积淀为基础。如小提琴协奏《梁山泊与祝英台》、钢琴协奏《黄河》等等,如果没有长时间的音乐之外的文化积淀,没有那些梁祝的传说,没有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知识背景,那么对这两个作品我们无法进行那么丰富的联想,从而帮助理解作品,也体验到作品所体现的感情。对一个完全陌生于中国文化和音乐的外国人来说,只能产生比较抽象模糊的感情形式而已。伦纳德·迈尔说:“在巴罗克作曲家作品中所发现的关于忧伤的、快乐的、愤怒的或失望的动机,或者在阿拉伯或印度‘拉格’(RAGAS)音乐中,那些特殊调式所属的感情的和道德的性质等,都是这种惯用的指示符号的例证。”[24]这里所谓的惯性便是文化积淀所构成的情感习惯,文化为音乐的情感产生了一定的情感规定性。2、嵇康所说的“先遘于心”虽然还没有仔细地分析上述的文化积淀,也没有说及人们对音乐旋律、和弦、配器、曲式、调式等等的积淀和体验,但是现代音乐理论已经从理论证明了嵇康理论的正确性。伦纳德·迈尔还分析说:“那种对我们来说,风格完全陌生的音乐,是无意义的。”[25]其原因是音乐需要一种指向,一种期待,但“期待主要是一种风格体验的产物”。某种旋律、和弦、调性被某些民族习惯性地赋予了一定的感情形式和内容,这正如狐狸在中国被认为是狡猾而奸邪的,而日本则认为是美好而聪明的象征。实际上狐狸被赋予的意义和感情与狐狸没有直接的关系,至多是对应了狐狸的某些习性而已,根本不可能认为是狐狸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情感。音乐的旋律、和弦也是“自然之和”的东西,与人的感情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人们习惯于以某一类型的旋律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感,因此一旦出现某一旋律时或者是与之相象的旋律时,必然会出现表达那种情感的期待。当那种期待被满足时便产生了音乐的快感,也会出现相应的想象,然而这些想象显然是曾经体验相类的旋律时产生过,或者说想象之间也具有某些类似性。但这显然需要一个前提,那便是对那些类型的旋律或和声的处理方式曾经体验过,甚至相当熟悉,这样才可能产生期待,否则是没有意义和情感的。3、既然“声之与心,明为二物”,那么感情和意义的传达似乎成了不可能,但也不尽如此。这里需要文化与音乐的某些固定模式,把某些感情和意义预先假定,并把假定的意义作为音乐作品本身的一种风格内容,再显现意义和确定意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交流和传达意义。迈尔曾指出:“‘假设的意义’(Hypot heticalmeanings)在那些期待行为的过程之中出现的。既然被设想的意义是一种作为风格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概率关系的产物,而这些概率关系总是包含着几种可供选择的结果的可能性,所以,一个特定的刺激物总是能引起几种可选择的假设意义。”[26]应当说他的理论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他所说的这种假定意义的前提,正是需要通过文化积淀来实现的。文化的积淀正是在假定的前提下不断积累,把假定的意义或情感模式进入日常生活之中,并且固定下来,使之成为难以分辨本体的混合之物,使人忘记原始的假定前提。嵇康音乐理论虽然没有达到现在的这种高度,但是在汉魏时期出现稽康这种理论高度的论文已经非常伟大了。
嵇康的思辩相当完整,而且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他并没有因为否定心声一元的观点,而否定音乐的移风易俗作用。这里似乎存在内在逻辑上的矛盾:既然心物明为二物,知音知世是错误的,言不足以证心,乐不足以达意,那么社会功能是如何产生的?他说音乐“使心与理相顺,和与声相应”[27]。这正是从对应关系讲到社会功能,节奏欢快的乐曲可能使人情不自禁地舞动,而那沉缓幽静的音乐则使心情平和。这与文学的作用不同,不是直接把明确的意义清楚地送进人的体验之中,使人的体验显现出较为可以明晰地把握的情感与意义,但是音乐仍然可以产生作用。音乐之体为和,和之虚静是音乐至境。在对应关系的作用上,嵇康主张音乐的教化作用,认为音乐不应扰乱人之平静心情,不应促发人的情欲,而应使人情与欲趋于虚静。应当说音乐确实可以有这些教化作用,因此“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之为体,心之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28]这里嵇康并不是完全为了说圆自己的观点,把各种理论硬凑在一起,而是具有相当完整严密的内在逻辑性作为其理论的基础的。
注释:
①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225。
② 《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本。
③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④ 《乐记·乐本篇》。
⑤ ⑥ ⑦ ⑩ [13] [14] [17] [19] [22] [27] [28] 均见于嵇康《声无哀乐论》,《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⑧ ⑨ [12] [15] [16] [18] 爱德华·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P13,P21,P49,P59,P94,P30。
[11] 燕南芝庵:《唱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卷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P160。
[20] [21]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59年版,P337,P500。
[23] [24] [25] [26] 伦纳德·迈尔:《音乐的情感和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22,P22,P53,P5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