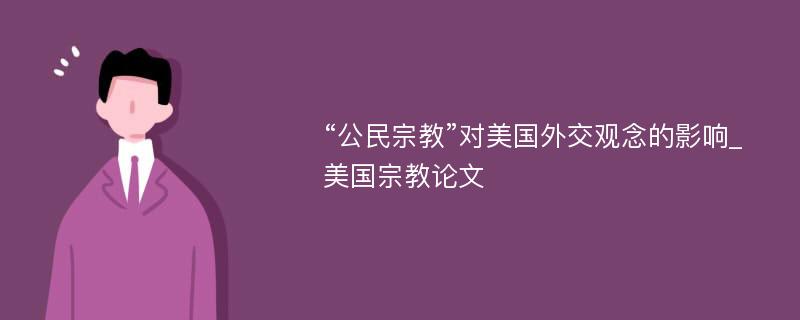
“公民宗教”对美国外交理念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公民论文,外交论文,宗教论文,理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53-05
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它有别于教会宗教或卢梭提倡的神权政治①。其基本性质如托克维尔所说:“宗教本身在美国主要是一种共同的见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条发生统治作用。”②美国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恩宠者”,形成一种“上帝恩宠论”,这便是美国“公民宗教”的逻辑起点。美国“公民宗教”还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宗教色彩的“国民宗教”,因为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它是一种文化的、神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派的复合模式③,显然,它与某一教派为主体的教会宗教或某种已经成为国教的宗教政治相区分。这种特质的美国“公民宗教”,是美国外交坚持“美国优先”基本理念并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
美国“公民宗教”所执守的“上帝恩宠论”,是一种通过“上帝”符号对美国立国理论进行了实用主义假设的泛宗教信仰。正因如此,美国“公民宗教”则有可能超越宪法原则之“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之墙,而对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外交政策的产生重要影响。换句话说,美国“公民宗教”在逻辑原点上能够含摄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支撑“美国至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建立其“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基准,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引导着当代美国教会宗教一种“政治宗教”的反世俗化走向。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美国外交中“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为地设定人类差别”④152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及其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超越“分离之墙”而影响外交
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其“不得确立国教条款”限制了国家以法律形式确立官方宗教;其“信教自由条款”保证了所有宗教派别的平等发展甚至竞争。1802年托马斯·杰斐逊进一步提出“建立一道教会与国家(机器)的分离之墙”⑤。由此,所谓“政教分离”成了美国国父们为在美国建立民主性质之“有限政府”的基本政治理念。就其内容来看,一方面,“政教分离”给予美国各教派以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教会势力乃至传统宗教意志对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之权力产生影响甚至干预。因此,“政教分离”之宪法原则,实质上是一个在限制政府干预教会之权力背后,同样限制教会干预政府之权力的“双面制约”之墙。但是,在实践中美国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教会势力的影响,却从未避免过宗教概念对它的影响。其原因在于,“政教分离”仅限于将国家机器与教会势力相分离,却没有也无法限制政治制度、外交策略与宗教概念之间长期相互依存的复杂联系。
美国历史上,马丁·路德·金以牧师身份领导民众争取自由的民权运动,开启了教会通过教会运动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先例。但是,这种努力并非一种对“分离之墙”的超越,而是对“分离之墙”的撞击或突破。从现象上看,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多元化美国新兴宗教的一系列社会参与活动,其目的无不为着企图影响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决策。这种现象显然是一种对美国“公民宗教”实然超越“分离之墙”的联动或附和。历来,美国国父们都努力将《旧约》中的“契约”精神引入美国,让美国人民能够充分相信美国是上帝唯一所选的至善之国、美国人都是上帝恩宠的选民。这种“公民宗教”的理论预设,造就了今天的“美国精神”,并在“分离之墙”之外一直对美国外交发挥着引导作用。美国外交也就此理直气壮地以“美国优先”这个基准去承担对全人类扬善抑恶的天赋权责。所以说,美国的“公民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与“分离之墙”并不相干,另一方面则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理念。
1976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N.Bellah)首先提出了“美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公民宗教’”⑥的断言。这是一种宗教现象学分析结论。实际上,“分离之墙”所限制的场域,总是远远小于“公民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场域。至于为什么要建立“分离之墙”,其中很大的潜在原因是为了让“公民宗教”不被混同于教会宗教并且不被教会宗教所利用,从而能够真正发挥“美国至上”精神对整个世界的辐射力量。这显然也是一种对于“基督教至上”或“天主教至上”的否定。因此,就美国外交的影响力而言,美国政府因为拥有“公民宗教”所提供的“美国精神”,便有可能回避“政教分离”宪法原则的约束,不至于对宗教思想统治下的整个西方世界失语。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教分离”之宪法原则原先是以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实现“双方限权”这个目的而产生的,当时人们没有也不会去追究它的“逻辑原点”。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问题。如同大多数社会现象那样,渐渐后续显现的一些理性观念,往往反而能够成为这些现象之所以如此这般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尽管“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出现很早,但其浮如中空,人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它的逻辑原点。晚些时候出现的美国“公民宗教”,实际上可以超越“政教分离”之宪法原则之前充当它的逻辑原点。这样一来,“政教分离”就自然地成了一种在“上帝观念”统摄之下的“形式分离”,而政府机构与教会组织之间表面对抗所形成的张力,反而反映出了美国政治与宗教之间从来就不曾断离过的实际依存关系,这甚至揭示了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早就存在的趋同性。这也许就是贝拉等一批美国“公民宗教”倡导者提升美国宪政及其外交影响力的希望与努力所在。
关于“公民宗教”的实质,董小川教授曾将“美国人共同信仰上帝”作为其灵魂,将“总统”作为其中心代表,将“美国民族文化”作为其主要内容,将“宗教民族主义”作为其有力支柱、将“学校”作为其特殊组织形式,将“社会政治”作为其根本任务,将“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作为其基本依托,将“超验公民宗教”作为其理想目标④141-149。当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同将白宫视为“公民宗教”的大教堂,将总统视为“公民宗教”的大牧师。若依本文的“逻辑原点”之说,这些剖析不无道理,其中,将“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作为其基本依托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在逻辑原点上对“政教分离”之宪法原则所体现的“各类宗教平等发展观”做出了一种新注解。而将超验性的“公民宗教”作为其理想目标这一条,则更能表现出美国宗教那种天然的政治参与性与社会道德性。
如果我们且将美国“公民宗教”视为一种“大宗教”并先置于逻辑原点由政府代表之,同时将各类教会之教派视为“小宗教”而由教会代表之,那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不确立国教条款”和“信教自由条款”显然就是为了表现美国政治的宗教宽容姿态而确立的。“公民宗教”的信仰执守与美国外交执行者——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甚至同体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分离之墙”表面上分离的是政府与教会,实质上却分离出了一个大宗教与多个小宗教。这样一来,分管美国“社会秩序”的政府机构,也就能够通过“公民宗教”从底线之处,回收或截断教会宗教对美国“精神秩序”之分管权的种种企图,从而造就了一种“大宗教统摄之小宗教平衡”的历史局面。
由于“公民宗教”是一个不设教会、不定教义、不拘形式、没有牧师甚至不限势力范围的一种“泛宗教体”,美国宗教便形成了一种“公民宗教”之大宗教与多种教会宗教之小宗教之间有机复合的生动局面。其表现,一方面是“公民宗教”的大而化之,另一方面是教会宗教的分而制之。因此,所谓“政教分离”实际上也被转化成了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民宗教”与体现教会意志的各类教会宗教之间的分权博弈式制衡。这种特别的政教关系之间的分权博弈式制衡,会因其原点对过程、全体对局部的直接统摄而最终演变成为一种不分之权、不博之弈、不制之衡。因为有了“美国至上”这个通过“公民宗教”所体现的“美国精神”,不同教会背景的美国人在外交方面便最终总能在“美国优先”这一点上趋向一致。
可见,“分离之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圆圈,将美国国内的教会宗教圈在了里面,其外围则是那个被“公民宗教”充分“赋权”的、能够对整个西方社会发挥其“美国至上”外交影响力的所谓“有限政府”。从这层意义上看,在美国“公民宗教”对“有限政府”的“赋权”之后,美国外交渐渐地显现出了一种“外交的‘公民宗教’化”与“‘公民宗教’化外交”之复合体。正如托克维尔那句“美国人把基督教的概念(即上帝观念)与自由的概念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概念不能单独地存在”之所言⑦,美国外交一直没有太多地遭受教会宗教的独立影响,其真正原因并非是“分离之墙”的隔离作用,而是“公民宗教”对这个围墙的超越。
美国外交的“公民宗教”化
上述浅析可见,美国意识形态对全球的扩张,其基础在于上述美国人的“公民宗教”意识。因此有理由认为,“美国外交的‘公民宗教’化”将会作为未来美国意识形态对外扩张的一种强势趋向。
在当今美国意识形态的对外扩张经验中,“新孤立主义”所主张的极端民族主义坚持以“美国优先”为其旗帜,它们渐渐扯下了左倾自由派曾经高举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的大旗。正如1941年创建《时代》、《财富》和《生活》三大杂志的亨利·卢斯鼓吹“美国例外论”而将20世纪称之为“美国的世纪”那样,美国人普遍认同“美国将作为仁慈的霸权或慈父般的权威来发挥作用”⑧。这种充满民族优越感的美国意识形态主流,不仅已经深入美国人心,而且具有强烈的对外影响力量,支撑它的便是“公民宗教”。
美国“公民宗教”的一个通俗表达式是“以上帝的名义”,这也是美国外交的一句广告语。在美国“公民宗教”史上,所谓“效忠誓词”曾在美国多次引起过风波。这些表面上的取舍往来,依然遮掩不住“公民宗教”对传统教会拥有上帝专属权这项文化遗产所进行的强势“掠夺”,由此,美国国内的传统教会首先品尝了美国意识形态那种“仁慈霸权”的滋味。
有趣的是,站在美国国界之外,人们不难发现美国的“公民宗教”正在与美国的传统教会以及诸多新兴教会争夺着国内的“教民”。这种“大宗教”式的含摄,显然希望美利坚民族能够“统一”(而不是“团结”)于建立在美国“公民宗教”基础之上的美国意识形态之下。这种趋势所隐含的对抗力,如今已经通过美国外交的“美国至上”的基准并对外释放而得到了转向,即美国国内这种特殊的宗教矛盾已经通过外交得以缓解。
“公民宗教”对美国外交理念的影响远非任何教会宗教所及。具有美国原创意义的“公民宗教”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其优势在于它能够向全球提出并赴履“美国优先”的外交战略甚至“美国至上”的强势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原先由英国等地“迁栖”到美国的其他传统宗教,则缺乏这种原创意义及其强势意识、气度和能力。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也是不得已而必须“挟上帝”才能“以令诸国”。这就是美国外交必须且必然走向“公民宗教化”道路的充分理由所在。也就是说,按照美国主义者甚至帝国主义者的设想,美国外交一旦走在了“公民宗教”化的道路上,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替天行道”了。
然而,问题在于“公民宗教”是以一种美国自封为“上帝之国”的虚拟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且不说这种无基之础上面的建筑总有一天将惟危可及,仅就“公民宗教”作为美利坚民族的一支强心剂或兴奋剂来说,它也已经因其原本的虚拟性而向世人预示了它的半衰期。也许,这将引发下面两种“外交突破”的趋向,即或者美国以其在未来世界事务中的超级强势而不再需要这支强心剂,或者“公民宗教”因为理论上能够迎合美国全球霸权的膨胀需求而铺设出一条“‘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大道,从而培育出一种新型的宗教政治国家。
这些令人悚然的揣度,源于长期以来美国在其外交政策背后一直张扬着一幅“上帝恩宠”的大旗,美国更以“上帝选民”的虚拟身份“行侠”于世界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可见,美国的“公民宗教”实际上已将原属神学的上帝涂上精神的颜色,而且直接培育出了如上所述的美国外交理念。显然,美国外交的基本理念已经被所谓的“公民宗教”化了。这就是“美国外交的‘公民宗教’化”的全过程或要结。
“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
本文所称谓的“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实际上是一种尚未成型的趋向。随着“美国精神”的全球推广,“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首先会表现出一些对抗传统意义上宗教世俗化的端倪。这种看似难以理解的判断,实际上不难被理解。所谓“宗教的世俗化”,从教会学角度看,指的是教会原来特有的功能渐渐地被世俗组织所替代、导致其社会影响正在下降的历史过程;从社会学角度看,指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些部分正在摆脱宗教制度和教条约束的现实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逆转的“过程”。
近年来,理论界对“世俗化论”的修正日益增多,比较突出的有“神圣化论”、“精英世俗化论”、“新世俗化论”、“去世俗化论”以及“文化转移分析”等,它们都分别承担了对这种逆转的理论分析。如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公民宗教”已经充分体现出对美国意志的强烈主导作用,并通过其外交向全球推广。对于这种旨在向着全球推行美国式强力意志的外交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显然,它应当就是“美国外交的‘公民宗教’化”接下去的一种定型。
作为只有信念与信仰、不设教会、不定教义、不拘形式甚至不限势力范围这种“泛宗教体”,美国的“公民宗教”实际上谈不上会有怎样的“世俗化”进程,或者说,美国“公民宗教”自它诞生起就深入并影响着世俗社会。基于这种判断,作为“大宗教”的美国“公民宗教”,实际上在含摄了诸多传统教会之“小宗教”的同时,也无疑产生了一种将他们“引向世俗”的基本导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公民宗教”深度地调和了美国宪法对于政府与教会的隔离,或者至少充当了教会宗教对政府机构发挥其影响之缺憾的替代品。
徐以骅教授所归纳的公民宗教诸多模式,按其功能分类则有:以维系一个社会团结的价值观念和情感为特点的民间宗教之文化模式、以作为一个超验的意义系统为特点的超越和普世的宗教之神学模式、以膜拜国家的至上神圣为特点的宗教国家主义之社会模式、以将美国的民主理想视为上帝的意志为特点的民族信仰之政治模式、以将道德主义、个人主义、行动主义、实用主义、工作伦理、向世界传教等(与天主教更重来世相比)偏重于现世利益的新教价值观作为自身内容为特点的“新教—国民信仰”之宗派模式③57-61。这些模式无不是不同程度地带有“盎格鲁—美利坚”种族优越感的深刻印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也成了“英—美外交联盟”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下来的一个基本原因。⑨
就美国的“公民宗教”的基因而言,正如菲利普·E·哈蒙德所发现的那样,“美国公民宗教中有一种对新教之过去的‘怀旧渴望’”。⑩而这种“新教之过去”,当指尚未彻底接受帝国主义改造而被美国本土化的原始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按照马克思·韦伯的话说,“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或不管将其称作什么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或也不应在任何意义上与启蒙意义上联系起来。”(11)从这个角度上看,尽管执守“上帝恩宠论”的美国“公民宗教”纯粹是一项“美国发明”,但因上帝并非仅是“美国的上帝”,所以,美国不愿也不可能放弃英国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宗教渊源”。
可见,所谓“‘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充满着“盎格鲁—美利坚”式的种族优越感。这种理念先置条件下的美国外交,其本身就充满着对上帝精神力量的极大崇拜和依赖,以“泛宗教”的形式所体现却又是隐形的这种反世俗化的基本导向,也成了“‘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的特质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去,长久以来无法得到解释的矛盾问题——即为什么美国现行外交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价值观、另一方面却又总是去人为地设定人类差别,也似乎因此能够得到一种明晰的答案了。
美国的“公民宗教”在客观上存在着“既极端神圣、又极端世俗”这种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两面性或普适性,这是产生上述矛盾问题的一个直接原因。这也就是说,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方面按其神圣性要求将人类视作平等无差,另一方面却因为世俗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差别社会”。如果美国外交不去适应、渗入、担待甚至掌控美国以外的一些客观存在的社会差别,那么,它就再也不能充分地或最大限度地施展“公民宗教”赋予美国意识形态的那种至上性、统摄性、基础性和导向性为特点的霸权力量,它也会就此失去“美国精神之体现者”或“美国精神之传播者”的起码资格。
因此,以“公民宗教”培育出来的“美国精神”作为基础的美国外交,特别是未来那种“公民宗教”化的美国外交,无疑是一个越发凸显其内在矛盾的矛盾体。其结果,要么美国外交被打造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对外扩张器,要么美国外交将会成为美国宗教次文化的全球传播器。不论这两个方面进展如何,美国都会以其“公民宗教”的力量去承付其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者在全球文化战争中的各种扩张,而全球范围内的宗教本色化(比如拉美福音派主义对美国宗教的摆脱),则更会越发成为抵抗这类扩张的基本力量。而且,这种趋向的必然性,则应当大于其偶然性。
收稿日期:2009.10.20
注释: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3:161-177
②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527
③徐以骅.美国的国民宗教及其国民宗教辩论.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一辑).时事出版社,2004
④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教文化.商务印书馆,1999
⑤即Thomas Jefferson在给浸信会教徒t的一封信中写道:“… should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thus building a wall of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收入Jefferson,Writing,Vol.XVI,pp.281-282,to the Danbury Baptist Association on January 1,1802
⑥Robert N.Bellah.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in Daedalus,winter 1967,96(1):1-12
⑦于歌(于彦智).美国的本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87
⑧周琪.宗教与自由精神并行不悖的美国.博雅旅游网http://www.bytravel.cn
⑨李琮,关于美国霸权问题论争的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2)
⑩Phillip E.Hammond.Varieyies of Civil Religion,San Francisco:Harper & Row,171
(11)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