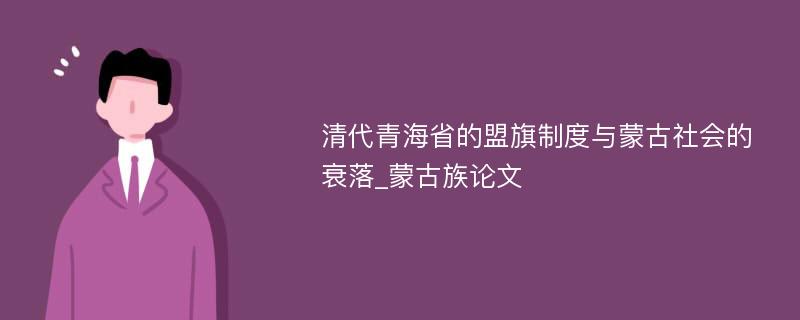
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盟旗论文,青海论文,清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雍正初年和硕特部贵族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青海厄鲁特蒙古被纳入了清王朝盟旗制度的统治体系,这一制度随之也成为清代青海地方行政制度的重要组成之一。尽管人们对于青海盟旗制度的基本内容有所了解,但对其中不少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有偏差,同时考察盟旗制度下青海蒙古族历史,呈出在我们面前的全然是一幅社会衰败的景象。对此进行学术上的探讨和反思,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历史启示。
一、有关旗的建置和会盟的几个问题
青海厄鲁特蒙古各札萨克旗是在平息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活动后,根据年羹尧《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请照依内札萨克编为佐领,以申约束”的建议,由理藩院侍郎鄂赉和副都统达鼐于雍正三年主持编设的。其编设原则是:“每百户编一佐领,其不满百户者为半佐领,将该管台吉俱授为札萨克,于伊等兄弟内拣选,授为协理台吉。每札萨克俱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员。每佐领俱设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四名。其一旗有十佐领以上者,添设副协领一员,佐领两员,酌添参领一员。”不过在实际编旗时每佐领以一百五十户为额。旗的编设尽管是以各王公台吉“原管部落”为基础,“查明青海蒙古乃二十九家,即分为二十九旗”(注:(乾隆)《西宁府新志》卷20,“武备·青海”。),而且所编各旗成为朝廷所确认的领地,但再也不能沿袭蒙古封建领主制对其领地任意进行分割或者再分封。旗与旗之间无论其实力和规模大小,“彼此不相统辖”(注:(清)素纳:《青海衙门纪略》,见(清)文孚著、魏明章标注:《青海事宜节略》“附录一”。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都是相互平等的行政单元。这样就打破了青海厄鲁特蒙古传统的兀鲁斯—鄂托克—爱玛克式的部落体制。所编二十九旗中,和硕特部二十旗、吐尔扈特部四旗、准噶尔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喀尔喀部一旗,另有一旗为察罕诺门汗喇嘛旗。但应该注意的是,在许多著述中和硕特部初编旗数都记为二十一旗,这是不准确的。由二十旗变为二十一旗,是因为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时新增添了由前左翼头旗中析出的前左翼次旗。据素纳所撰《青海衙门纪略》记载:是年,前左翼头旗札萨克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呈请“将伊第四子策令多尔济另放为一札萨克,于伊所管十佐领内拨给佐领四个管辖,经副都统众佛保据情转奏,允准添放,颁给印信,原日青海二十九旗,今添台吉策令多尔济一员,添成三十旗之数。”但南左翼次旗前后存在只有60年时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由于前左翼头旗札萨克郡王殁后无嗣,所遗爵职又由南左翼次旗札萨克台吉沙克都尔承袭,沙克都尔则鉴于“本管台吉旗内仅有属下人二十三户,请归并一旗”,“经部议准”(注:《青海事宜节略》,第21页。),和硕特部重又恢复到二十旗的原有格局。察罕诺门汗喇嘛旗是一个以察罕诺门汗(白佛,藏语谓“夏葺尕布”)转世活佛为札萨克、以其宗教领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特别旗。与一般札萨克旗的区别在于:其一,旗札萨克的职务是由历辈转世活佛担任,而不是依照普通的血缘关系世袭传承;其二,察罕诺门汗旗“不列诸札萨克盟”(注:《清史稿》卷522,“藩部五”。),即不参加各札萨克旗的会盟;其三,察罕诺门汗所属民户是长期以来由蒙藏王公贵族陆续赐赠所得,故该旗属民中包括有蒙古和藏两个民族,而不是单一的蒙古族。道光十二年(1832年)陕甘总督杨遇春和西宁办事大臣恒敬的奏折中称:“其属下四苏木,人户共有一千二百余户,计一万三千数百名口。内分二十八族,番子十六族,蒙古十二族,番子居其十分之七。”据此,则其属民中藏族占大多数。可见,该旗在内部组织形式上与其它札萨克旗也有所不同。
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札萨克旗内部实行的是世袭统治,当札萨克因故不能视事时则由协理台吉(即图萨拉克齐)代行其职,但也由清朝政府直接派员管理旗务的特例。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至三十二年(1767年)因和硕特前首旗札萨克亲王汪丹多尔济怕拉玛年幼,经西宁办事大臣舒明奏准,其旗务一直由理藩院差委司员一名前往办理(每届三年更换)。除此特例之外,其内部行政均处于一种自治状态。在札萨克旗之上设有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即西宁办事大臣衙门作为统一管理的机构,其职责一是组织和主持会盟,二是例行的年度查旗。会盟是盟旗制度当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会盟时“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意在使其充当会盟的召集人,但在道光之前“查西北沿边蒙古皆有盟长,惟青海蒙古向未设有管事盟长人等”(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8。)。会盟初为一年一次,至乾隆初年改为三年一次,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改为间年会盟一次。会盟之前首先要进行的是一项颇为隆重的“祭海”,即祭祀青海湖神活动,然后于次日“齐集各蒙古王公札萨克台吉等会盟,俱按品入筵,将承办绸缎袍褂衣料翎顶小刀茶封等物分别赏给”(注:吴丰培编:《豫师青海奏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会盟时还往往由办事大臣处理一些各旗之间刑民案件等等,乾隆中一度还曾有过办事大臣带领王公贵族进行的“打围”的活动。但会盟作为一种由朝廷封疆大臣亲自主持进行的隆重典仪,其重要意义显然并不在于处理和解决具体的事务,而是在于其强烈的政治象征功能。通过体现皇朝的“威仪”“威德”来强化地处边陲的蒙古族社会对于清朝封建国家的认同意识。因此这一制度对于维系边陲地方的国家秩序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查旗就是办事大臣(或差员)定期对各旗进行的巡视和监察,并对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奏请处理。查旗最初定为三年一次,乾隆十六年改为“遇不会盟之年,即奏明前往查旗”(注:《青海事宜节略》,第5页。)。
青海的盟旗制度到道光、咸丰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道光三年(1823年),奉旨在青海办理蒙藏事宜的陕甘总督那彦成和西宁办事大臣穆兰岱,奏请朝廷将游牧于青海黄河以北地区的全部二十四个札萨克旗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十二旗,各设盟长、副盟长一员。翼下每六旗设和硕札奇噜克齐一名,每三旗设梅楞一名,每旗设札兰一名。正副盟长设立后“各旗一切大小事件,令各旗呈报该盟长处,核明转呈该大臣(按即西宁办事大臣)办理。其操演蒙古兵丁,巡防卡伦等事,交该盟长等管理,以专责成”(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102页。)。盟长之设主要针对各旗缺乏自卫自保能力的情况,通过盟长的统一组织和协调起到一个联防的作用,意在改变长期以来蒙古各旗在遭到藏族部落攻击时“散漫无束,遇事各自规避”的消极被动局面,并无自行处理所属各札萨克旗务的权力,因而也没有相应的办事机构或衙门。两翼正副盟长人选由西宁办事大臣从各旗札萨克王公台吉中拣选并奏请朝廷批准任命,或者由各旗札萨克王公台吉推举后再由办事大臣转呈朝廷批准任命,任职可以终身但不能世袭。正副盟长之下的札奇噜克齐、梅楞及札兰等职都是分级负责兵丁训练和巡防事宜。另外,道光十八年,清廷允准察罕诺门汗旗移牧于黄河以北地区,虽然没有明令将该旗划归左右翼当中,但诸事皆由两翼盟长据情转呈,受其督率。若察罕诺门汗年幼或者出缺,清廷也往往授命左右翼盟长代理其旗务,左翼盟长车灵端多布和右翼副盟长拉旺多布吉就分别在道光和同治时代管过其札萨克“印务”。
青海盟旗制度的另一变化是会盟范围的扩大。自嘉庆以来,游牧于青海黄河以南地区的一部分藏族部落纷纷向黄河以北地区迁移,经过数十年反复之后,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年)获准在青海湖周围原属蒙旗的地界内划出一部分草原供其居牧,是为“环海八族”。为了能够控制和约束这些藏族游牧部落,清朝廷也规定“着其同蒙古一体来盟”(注:(清)徐松:《清稗类钞》第2册,“礼制类·青海蒙古会盟之礼”。中华书局1982年版。)。
二、盟旗制度下青海蒙古族社会的衰败
以和硕特部为主体的青海厄鲁特蒙古曾以青藏高原政治霸主的身份活跃于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然而当其社会被清王朝纳入到盟旗体制之后,其历史过程则完全是在一种带有强烈的民族悲剧的氛围中进行的:在政治上,当丧失了青藏地区统治民族的地位之后,又很快被清朝分割为数十个互相独立的行政单位,厄鲁特蒙古作为一个地区性的政治实体宣告解体,政治上的极度涣散使其最终沉沦为一个政治弱势的族群;在经济上,全社会都呈现出极度贫穷化的趋势,与此密切相关联的是人口大幅度的流失和损耗;在文化上,伴随政治经济上的极度衰败,使民族社会丧失了基本的内聚力,因而在族群成员中普遍出现了文化认同弱化的现象,最终造成民族认同的危机。在几近二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上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衰败互为因果,构成了青海蒙古族社会运行过程中一种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考察清代青海厄鲁特蒙古社会的衰败过程,显然与雍正初年因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反清而引发的战乱有着直接的关系。战乱尽管只持续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但给青海蒙古族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首当其冲的是人口和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在雍正元年十月清朝出兵之前,蒙古贵族中以罗卜藏丹津为首的反清派和以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为首的亲清派即因政见不同而发生内讧,双方兵戎相见。据《清世宗实录》卷八雍正元年六月壬戌条载,双方“交战四次,属下人多阵亡,其余亦行逃散,又将牲畜劫掠”;同书卷九雍正元年秋七月已丑条又载,“王(按即郡王额尔德尼厄尔克托克托鼐)之属下人等尽被抢掳,穷困投至甘州,朕闻之不胜侧然”。及至清朝大举出兵后,凡是反清部落都成为清军“诛锄”的对象,《清世宗实录》中屡屡出现清军将抵抗的蒙古军“尽皆杀灭”、“剿杀殆尽”、“攻杀殆尽”之类的记载。曾经随年羹尧西征青海而亲历其事的汪景祺在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中,对清军之滥杀与掳掠作了如下披露:“于是西夷大创,斩获无算。有掳其全部者,除贼首三人解京正罪外,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其功固亘古所未有,然其中岂无冤死乎?女子皆以赏军士,各省协剿官兵归伍者咸拥夷女而去,西安府驻防八旗回镇将士除自获外,年大将军复赏以夷女五百人。”汪景祺所记从年羹尧给雍正的奏折中得到了证实:“凡逆贼部落强悍者略已诛除,所存者虽留西海,经臣宣旨,分赏满汉官兵,共计男妇一万名口,以杀强暴之气。”(注:季永海等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年氏所奏说明清军大行杀戮的目的就在于“杀强暴之气”,也就是彻底摧毁青海厄鲁特蒙古所具有的能够与清王朝对抗的能量。一般估计清初时青海厄鲁特蒙古人口总数在20万以上,但经过战乱之后所余人口还不到二分之一。根据各种史料的一致记载,雍正三年编旗时青海蒙古二十八个札萨克旗共有佐领一百一十四个半。按定制每佐领150户计算,二十八旗总户数为17175户;另加察罕诺门汗旗四个佐领600户,则有17775户,以户均五口的通常算法,当时总人数应为88875口。在传统的游牧族社会中,人口的减少也就意味着经济的衰退,经济的衰退也必然导致人口的减少。战争结束时许多牧民都已“荡产失业”、“穷困流离,资生窘乏”。尽管清世宗下令予以赈济,但年羹尧等人仅仅发放一百万两白银就搪塞了事,根本没有解决什么大问题。
作为一个民族性的政治实体而言,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也就意味着其政治能量的萎缩;况且,原来隶属于和硕特蒙古贵族的“诸番”各部从雍正三年开始也由清朝直接统治,使其无法再象过去那样从“诸番”社会中获取政治与经济上的权益。为了彻底地从政治上将和硕特蒙古打垮,雍正三年编旗时,清廷将不足九万人的青海厄鲁特蒙古分散成为二十九个旗的行政单位,并使旗与旗之间各自独立,“恪守分地,不许强占”。这样,以和硕特部为主体的青海厄鲁特蒙古作为地方民族性政治实体便完全瓦解了。根据嘉庆中文孚所著《湟中杂记》的记载,二十九旗中人口超过千户的旗只有5个。其中人口最多的是和硕特部左翼前首旗,总共11个佐领,当有1650户、8250口;而人口最少的是南右旗和右翼东上旗,都只有半个佐领之数;另外,象西左后旗、西右旗、西右中旗以及右南旗也都只有一个佐领之数。平均而论,每旗还不足4个左领即600户之数,因此完全消除了每一单个的旗形成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盟旗制度在青海蒙古族地区的推行完成了清王朝所预定的双重任务:一是在这一地区国家秩序的建构;二是瓦解青海厄鲁特蒙古这个地方民族性的政治实体。
当然,盟旗制度在成为清王朝在青海蒙古族地区基本行政制度的同时,它也成为了青海蒙古族社会封建领主制新的外壳。除了传统的领主分封制遭到摒弃之外,领主制在盟旗制度这种国家秩序的框架内显然是得到了充分的确认。每一个札萨克旗就是一个该札萨克王公台吉世袭的封建领地,它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力。如果说雍正初年的战乱成为了青海蒙古族社会衰败的历史开端的话,以盟旗制为外壳的封建领主制则成为这种衰败持续的根本因素。作为游牧业经济,牲畜量的多少无疑是衡量社会贫富的最主要的指标,但乾隆时期青海蒙古各旗普遍都是“牲畜不甚充余”(注:《清高宗实录》卷1392。),有相当一部分牧民处在“毫无产业”的赤贫户地位(注:《清高宗实录》卷23。)。据《青海事宜节略》,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后,西宁办事大臣查旗、会盟及祭海等活动往往就因各旗无力提供差役(乌拉)而不能正常进行。乾隆之后,“各旗蒙古俱已贫困”(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5。),那些缺乏甚至丧失了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牧民们,或者“挖盐捉鱼,运往丹噶尔、西宁、大通等处售卖”(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71页。),或者在荒滩“寻割柴草,捡拾蘑菇,变卖度日”(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130页。);更为悲惨者“游牧则无牲畜,谋食又无手业”(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6。),只得以四处乞讨为生,很多人都因饥饿而死亡,而更多的贫困者则背井离乡、流徙他方。青海蒙古族人口流失的问题早在雍乾之际便已露出了端倪。《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元年九月癸巳条载,当时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因生计艰难”而“流移”到西宁府大通县口内。到嘉庆七年,青海蒙古和硕特前首旗札萨克郡王纳罕达尔济等给西宁办事大臣台布的报告中,称其属民“穷苦饿死的极多,逃窜漫散了的极多,与番子打仗打死的极多。……其余未死的许多百姓,在于西宁、丹噶尔、塔尔寺、拉卜楞寺等处,这里那里众寺庙里,并汉人番子地方去的极多”(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30页。)。从嘉庆和道光时期有关官员的各类奏折中所反映的情况看,蒙旗人口逃往“番地”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逃往番族之人多得便益,愿往番族者甚多”(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30页。),“蒙古王公等苦虐其下,多有投入番族之人”(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1。),“番族内蒙古甚多”(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1。)。由于人口的大幅度递减,到嘉庆十五年,青海二十九旗总户数只有6216户,总口数仅28963口,这分别比雍正三年初编时减少了65%和67%。其中,初编时拥有户口数最多的左翼前首旗仅存530户、1743口,分别比初编时减少了67.8%和78.8%;而不足百户的旗由初编时的两个增加到了8个。嘉庆以后,各旗人口流失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根据宣统元年清政府的统计,当时青海二十九旗总户数为1989户,口数为5139口,这比嘉庆十五年时分别减少了68%和82%;而与初编时相比,则分别减少了88.8%和94%。此时,不足百户的旗已经增加到24个,其中四五十户者有之,一二十户者有之,甚至有仅存一二户者。可见,从行政建置角度来看,大部分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对于青海蒙古民族而言,如此严重的经济衰败和人口流失,从过程看是一种苦难,从结果看则是一种灾难。显然,首先是满清统治者制造了这一民族悲剧,但这一民族悲剧之所以难有终结,在根本上则是蒙古族内部封建领主制的生产关系使然。大量的史料表明,在盟旗制度时代,各札萨克旗的封建领主们对旗民即阿勒巴图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榨取。嘉庆初年,陕甘总督松筠在其奏折中称青海各旗札萨克等“自图安逸,不能妥办旗务,差徭繁多”(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档,民族事务类,4全宗,137卷,《松筠奏折》。),时任西宁办事大臣的广厚亦奏称蒙旗领主“不知体恤属下,差徭派累日繁人心涣散”(注:《青海事宜节略》,第16页。),道光初年陕甘总督那彦成也指出各札萨克台吉等“任性贪残,不恤其下”(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6。)。惨重的经济压迫不但使牧民长期处在贫困之中,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人口流失的加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嘉庆初松筠就指出:“蒙古不能体恤属下,多方苦累,因而属下之人与番贼勾通,以图报复。或又携带妻子逃入番地以避诛求,甚且潜入番寨为之主谋。”(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18页。)道光初年陕甘总督长龄和西宁办事大臣松廷在所拟定的一份处置青海蒙藏事务的“善后章程”中称:“查(黄)河北各旗属下人户,从前本属众多,因该王公札萨克台吉罔知自检,任意需索,以致力不能支,或携眷逃亡乞食,或投入番族营生,亦有积怨已深,勾结野番抢掠本主财物者。”(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71页。)那彦成在其奏折中也一再提到:“自王公台吉虐其属下,其属下今更穷苦,反投野番谋生,因而导引野番抢掠其主”(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5。),“各旗蒙古属下苦其王公台吉等赋重政苛,勾引野番抢掠报复”(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6。)。当然,蒙旗牧民在经济上沉重的负担还不仅仅来自于旗内封建领主。旗作为清朝皇帝赐给蒙古王公台吉的世袭领地,自然要向封建国家提供必要的义务,因此诸如兵差、驿差及各种乌拉差等等也常常摊派到牧民头上,象西宁办事大臣例行的会盟、祭海、查旗以及过往旗界的官员差使等等都要向旗内征调乌拉。在经济衰敝的状态下,这些差役的频频派拨也往往使牧民不堪承受。
盟旗制度下青海蒙古族经济的持续衰退和人口的大幅度流失,过程又是和青海地区蒙藏民族之间此消彼长的族际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如前所述,经历了雍正初年战争的巨创,又经过了盟旗制度的整合,青海蒙古族在政治上仅仅变成了数十个各自为阵、人少势孤的行政单元而已,而经济衰败、人口流失和阶级矛盾尖锐,又进一步使每一个旗都变得极度孱弱。在古代游牧经济的特定环境中,像类似部落这样的社会组织单元是否强大,往往是它们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强大的部落可以有效地进行自保,从而避免外来势力的侵害。在清王朝所确定的国家体制当中,厄鲁特蒙古仍然处于一种“外藩”的地位,所以每一个行政单元需要具备基本的自保能力,但青海蒙古各旗武装自保能力是十分有限的。由于处在与藏族游牧部落毗邻交错的地理环境当中,缺乏有效自保能力的蒙古各旗就受到了藏族游牧部落的强大冲击,这又从外部加剧了其社会衰败的进程。
从雍正初年青海藏族各部摆脱蒙古贵族的奴役后,经过雍乾时期的休养生息,其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特别是黄河以南循化厅和贵德厅所属的各游牧部落,随着人口和牲畜的不断增多,“地窄人稠,不敷放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自发开展了向蒙古各旗争夺草原牧场的活动。而伴随这一自发无序过程的是频繁发生的各种命盗案件,不仅使蒙古各旗遭受了严重的人口财产损失,甚至基本的生产活动都难以维持,对于早已破败了的蒙古社会经济而言不啻雪上加霜。黄河南藏族各部对蒙旗的攻击活动在乾隆时期就已开始,最初主要限于黄河以南各旗,以后则扩大到河北各旗,并历经嘉庆、道光两朝,直到咸丰初年“环海八族”的格局形成后才得以缓解。面对藏族部落的攻掠,蒙古各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退缩的态势,像黄河南各旗因“常不能抵御”,致有“弃其旧游牧内徙”(注:《清高宗实录》卷1368。)之举;同时大量藏族部落开始进入蒙旗地界内游牧,乾嘉之际黄河南各族甚至一度被迫迁移到了黄河以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黄河南藏族各部大规模地发动了对黄河以北各旗的攻击和掠夺活动,“河北二十五旗遂致扰害”(注:《青海事宜节略》,第17页。)。“蒙古孱弱不能自卫,纷纷逃避”(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63页。)。先是在嘉庆之初,原来靠近黄河北岸一带游牧的六个旗相继退到环湖地区,随后又与环湖各旗退入口内西宁府属的丹噶尔、大通及河西各府县境内。嘉道之际,河北二十四旗中除远居柴达木地方的一旗之外,“其余二十三旗札萨克大半避入内地丹噶尔、大通一带;并有贫穷蒙古散处甘、凉、宁、肃边内插帐住牧及沿途乞食者”(注:《那彦成青海奏议》卷6。)总人数“不下二万余人”(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86页。),而“锅帐牲畜俱无”的赤贫就有4500多人(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87页。)。为了继续维持自雍正初年在青海蒙藏地区所确立的统治秩序,清王朝从嘉庆时期开始就开始“变通”所谓的“国家体制”,派出官军试图用武力阻止藏族部落对蒙古各旗的攻击,但措施不力、成效甚微。直到道光初年经陕甘总督那彦成“查办番案”时竭力处置,才迫使北进的藏族各部南返,退避口内的蒙古各旗也才算返归口外,但由于各旗原牧地方辽阔而人户凋零,经那彦成等人奏准,被安置在青海湖北岸琼科滩一隅,这样黄河以北、青海湖以南之间辽阔的草原上此后就几乎看不到蒙古包的踪影了,雍正初年所确立的以盟旗制度为内容的国家秩序也已经面目全非了。
那彦成“查办番案”虽然暂时缓和了藏族各部对蒙旗形成的强大压力,却并未解决黄河南藏族部落对草原的需求这一根本性问题,所以无论是在蒙旗中设立盟长进行联防也好,还是直接派驻官兵巡防震慑也好,河南藏族部落向河北地区的迁移以及对蒙旗的攻掠活动一直不曾停止。河北各旗每年派拨兵丁500名参加联防,自备粮草、器械和马匹,随同官军沿黄河北岸一带巡防,但经济的破败使这项措施不仅未能起到任何防卫作用,反而成为各旗的负担,“本欲护卫蒙古,转致蒙古坐困”。驻防官军也是疲于奔命。到咸丰初年,黄河南藏族各部大规模北进游牧于环湖地区,并最终迫使清廷认可了他们在环湖地区游牧,青海蒙古族最终丧失了他们环湖地区的优势地位。黄河南藏族各部对蒙古各旗反复不断的冲击使青海蒙古族社会长期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的冲击是与蒙古族社会内部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从而使其社会处在一种内外交困的格局之中。前述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在藏族部落对蒙古各旗频繁的攻掠活动中,普遍夹杂着那些不堪忍受残酷压迫和生活极端贫苦的蒙古牧民们对其王公台吉的“抢掠报复”的反压迫斗争。这种激烈的社会内部矛盾长期不能得到缓解,无疑在根本上窒息了青海蒙古族社会的活力。
盟旗制度下旗与旗之间的相互隔绝,特别是社会矛盾的尖锐以及经济上的凋敝所导致的社会生存状态的恶化,使青海蒙古族社会丧失了基本的内聚力,同时也产生了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逐渐淡化的趋势,突出反映在民族服饰和语言文字的藏化上。从服饰上看,蒙古族穿着藏式服装在嘉道时期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有鉴于此,嘉庆九年奉命到青海“查办番案”的理藩院侍郎贡楚克扎布就奏请朝廷“蒙古不准穿用番子服色”(注:《青海事宜节略》,第20页。);道光初陕甘总督长龄和西宁办事大臣松廷也指出:“查蒙古衣帽本有旧制,向与番子不同。此次奴才等带兵出口,见蒙古衣帽率皆照依番子式样制造”(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71页。),因此也奏请朝廷予以禁止。蒙古族穿着藏装,在当时“番强蒙弱”的情形下是无以自保的蒙旗牧民用以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穷苦牧民“意图假冒野番,抢夺蒙古牲畜,并可随同野番劫掠,俾人无从辨认”(注:《清代青海蒙古族档案史料辑编》第71页。)所致。从语言文字方面来看,黄河南四旗所属蒙古族逐渐放弃了本民族语言文字而全部转用藏语藏文。尽管从最终结局上看,藏化并未成为青海蒙古族整体的历史文化归宿,但黄河南四旗则进入了程度很深的藏化状态。就上述清末的人口统计来看,黄河南四旗共有1554口,几近各旗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民族文化藏化的现象应该说是多种因素所促成的,特别是对藏传佛教的信奉和处在藏族文化圈之中,都必然会给青海蒙古族文化造成深刻的影响。但就青海蒙古族的历史实际而论,其关键还在于该民族及其社会无论政治上的抑或经济上内聚力的严重缺乏。带有封闭和隔绝性质的旗的建置,对于民族内聚力就起着一种消解的作用;而各旗内领主制的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过度摧残和由此而长期激化不解的社会矛盾,则从根本上导致了民族和社会内聚力的丧失。
从盟旗制度下青海蒙古族社会衰败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丧失了内聚力的民族和社会是无法持久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而内聚力的保持在根本上要有赖于民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协调。易言之,一个长期经济衰退而且充满尖锐对立的社会矛盾又无以缓和的民族和社会是很难形成内聚力的,民族和社会文化的认同也必将趋于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