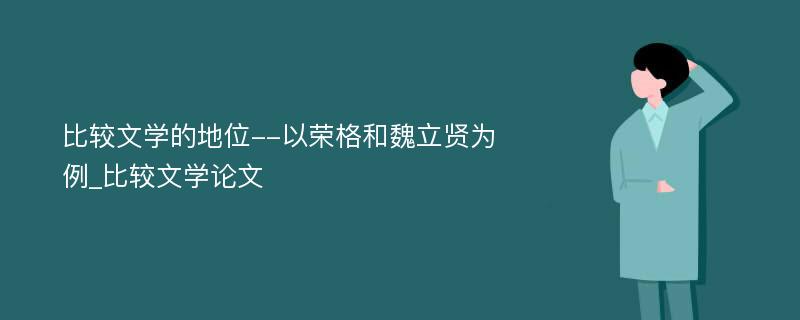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以荣格与卫礼贤的立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场论文,比较文学论文,为例论文,荣格论文,卫礼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历了后现代的解构大潮后,“立场”成了人们争议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立场’在今天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又十分晦暗。由‘立场’所启示的问题氛围不仅笼罩着全部的学术灵魂,也笼罩着当代人的日常生活。”①比较而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原本就立场不够坚定,在后现代和全球化语境下,其立场就更加飘忽不定,随风摇摆。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亟须重新思考和关注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并循此路线进一步探讨人文学者的立场问题。
所谓立场,就是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你的立场就是你所处的位置,你的位置决定了你的视角和眼光,决定了你的兴趣和态度,决定了你的“所见”和“不见”。立场决定视角,视角产生认知,认知影响判断。“立场问题其实是一个价值问题,而‘价值’,借尼采之言,乃是人类生存非此不可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人生就没有方向、目标和意义。”②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在新近发表的《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一文中指出:“视角的转换必然激发其观点的改变,但作为欧洲的学者,不能忘记我们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关系,这也很重要。”③作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时代“不能忘记我们的立场与我们自己的文学史的关系”,是否更为重要?
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与生俱来、鲜明突出,比较文学从创建之初就缺乏独立而稳固的位置。1995年,伯恩海姆在《比较的焦虑》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这个专业目标不清,方向不明,学生就业前景暗淡,陷入了焦虑重重的困境,亟待寻找出路。④“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界限和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⑤“它的研究对象的这种‘居间性’(inbetweeness)本身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显出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或不明确性,而且也使它从问世之初便没有一个确定的时空位置。”⑥任何比较都是有目的的:为什么比较?为谁比较?谁在比较?另外,任何“比较”如果可能,都会涉及以下问题:比较的基础、标准是什么?站在什么位置,以什么眼光,用什么方法比较?对以上问题的不同回答,比较的结果或结论就不会是相同的。比较文学学者如果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如何能拥有自己的立场?比较文学学者自身处在各种关系之中,他又如何能跨越这种关系?任何比较文学学者在文化身份上最终必然隶属于某一特定民族或国家,他们都会拥有各自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的文化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明断意味着要采取立场。”⑦
讨论比较文学立场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很多,最近笔者在认真研读了荣格撰写的纪念卫礼贤的文章之后,觉得或许可以通过荣格的立场来思考我们的立场,也就是说,通过西方人讨论东方文化的立场,来思考和探索中国人对待和研究西方文化的立场。荣格的文章名为《纪念理查·威廉》,写于1930年。文中荣格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立场或文化自觉,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一、比较学者的资格
比较文学学者的资格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谈论比较文学?荣格承认,谈论理查·威廉和他的工作,对他说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彼此的出发点相去甚远。具体地说,理查·威廉的毕生工作有相当一部分在荣格的研究范围之外。荣格说到底是一位医生,一个精神分析家,而理查·威廉却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神学家。荣格没有去过中国,也不熟悉汉语,但这些最终并没有成为他谈论理查·威廉的障碍。非但如此,荣格甚至觉得他们从一开始接触,就超越了学院的疆界,他们在人文研究领域相遇,“心灵的火花点燃了智慧的明灯,而这注定将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由此他发现了理查·威廉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把一种持续了数千年,也许注定要永远消逝的文化珍贵遗产,给予了西方”。⑧看来,经常能够切中肯綮地谈论比较文学或文化问题的学者,并不总是那些专业的比较文学学者,而常常是那些“业余爱好者”。
比较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跨学科,而跨学科这一特征自然需要跨学科的学者来使之成为现实。在论及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时,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异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⑨跨学科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类型,它也是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必然发展趋势。正是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的飞速发展,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与此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本身。这使得跨学科的研究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已经成为了比较文学学者所应当做和必须做的工作。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单就英国文学而言,哲学与科学跟许多伟大人物都是有关的,科学的间接影响尤其可观。”⑩英国文学如此,世界文学亦如此。对文学理论的贡献,并不总是来自文学理论家,反而常常来自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等。这一点对于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理查·威廉就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全名为理查德·威廉·青岛(Richard Wilhelm—Tsingtao,1873-1930)。卫礼贤原是德国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在德国占领青岛后到中国传教。在华期间,他曾创办礼贤书院,潜心研究中国儒家学说。他因为酷爱中国文化,便自取中文名字卫礼贤。从1903年起,卫礼贤开始发表有关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论文,并着手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他翻译出版了《论语》(1910)、《老子》、《列子》(1911)、《庄子》(1912)、《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和《易经》(1914)等。他通过办学、讲学、翻译中国经籍和解说中国文化,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荣格于1922年结识卫礼贤,随后成了好朋友。1925年荣格在远赴非洲旅行之前,决定请教《易经》,并为自己算了一卦。结果荣格得到了“渐卦第五十三的九三条”(11)。
作为医生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荣格,谈论作为汉学家的理查·威廉,这里就涉及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资格和身份的问题。谈论理查·威廉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并非仅限于那些汉学家,那些非汉学家的谈论也许更有创见和洞见,这也正是比较文学的意义和魅力所在。在许多情况下,具有真知灼见的探索和发现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狭窄领域内的专家和学者,某种跨学科的研究也许更能给人以启示并引发更多的思考。美国学者韦勒克曾经指出:“人们过分强调了专家的‘权威’,其实他们可能只是比较了解出版物的情况,或有一些文学以外的知识,却不一定具有非专门家的鉴赏力、敏感和眼界,而后者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完全可以弥补缺少多年专门研究的不足。”(12)就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而言,其先驱者是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宗白华等,他们中间没有一人是专门的比较文学研究者。
因此,荣格不仅能够,而且可以很好地谈论比较文学的问题。荣格认为自己是人类心灵的探索者。一旦他开始探索原始人的心理,便必定会探讨原始人的宗教和神话,这样他就必定会关注和研究东方古老的宗教和神话。荣格到过印度和锡兰,在那里他考察和研究了东方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神话原型,写出了大量有关东西方个性差异的著作。荣格正是通过与卫礼贤的交往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由此他认真研究了《易经》,这对于他日后写作《心理学与炼金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循此发展路向,荣格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心理分析学,走向了比较人类学和比较诗学。荣格曾经说过:“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纯粹的自在之黑暗中点燃光明之焰。”(13)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家与比较文学学者可谓殊途同归。
二、比较学者的目的和境界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比较学者所追求的目的和境界是什么?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进行比较?“比较文学研究现在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确定‘影响’,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精神力量所起的作用,集中于独特的、在文艺美学上可以把握的接受类型和方式,也就是说,集中于被接受了的促进因素所发生的变化。”(14)荣格发现:“所有平庸的精神接触到外来文化,不是夭折于自己的盲目企图,就是沉湎于不理解和批判的傲慢热情。他们仅仅以外来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自误,始终没有尝到它的真正好处,因而从未达到真正的心灵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昵的输入和相互渗透。”(15)这种心灵交流在巴赫金看来就是“对话”。“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相遇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涵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涵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就不可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这当然应是严肃而认真的问题)。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这种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仍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16)
我们今天对于外来文化,尤其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接触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呢?我们是否达到了“真正心灵的交流,那种产生新生命的最亲昵的输入和相互渗透”呢?是否实现了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呢?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接触、理解和认识,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早已不再是盲目地“跟风”,或一味地批判,但是,我们距离荣格所说的“真正心灵的交流”以及巴赫金所说的“对话”目标和境界还很遥远。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目前所做的,更多地是借鉴西方观念、术语、写作方法和形式,对于那些心灵交流的内容,因为其不易把握,不易认识、不易量化、不易表述而往往搁置一旁,或干脆弃之不顾。
在荣格看来,卫礼贤的工作是伟大的,“他把中国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种到我们身上,能够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一种根本变化。我们不再被降低为崇拜的或批评的旁观者,而是不仅参与到东方精神之中,而且还成功地体验到《易经》的生气盎然的力量。”(17)荣格继而赞誉卫礼贤在各种意义上都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仅使古代中国的文化宝藏能够为我们接受,而且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给我们带来了这种文化的已经存活了数千年的精神之根,并且将它种植在欧洲的土壤里。”(18)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荣格说:“我确实觉得他极大地丰富了我,以致在我看来仿佛我从他那儿接受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儿接受的都多。”(19)
卫礼贤将中国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种到西方人身上,并进而对西方人的世界观造成了根本变化;他将中国文化的数千年的精神之根,种植在欧洲的土壤里,从而改变或者丰富了西方文化的品质。荣格高度赞扬了卫礼贤的这种超越欧洲人的狭隘偏见的精神:“只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人性、一种洞察全体的博大精神,能够使他面对一种深相悖异的精神,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并通过以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为它服务来扩大其影响。”(20)卫礼贤昔日的成就显然就是今日比较学者的追求目标。中国文化之与卫礼贤,恰如中国的比较学者所面对西方文化。如果说,卫礼贤的这种追求和境界在我们的前辈学者中似乎还隐约可见。但到了今天,这些已成为明日黄花,随风而去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越来越专业化和专门化,而读者则越来越少,往往在专业之外便无人问津。所谓学术几乎成了学术圈内极少数人的自说自话。这样的学术研究究竟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呢?这样的学术文章如何“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比较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在荣格看来,就应该像卫礼贤那样,“他自由地、不带偏见地、不自以为是地对它加以考察;他向它敞开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他一任自己为它所掌握和塑造,因而当他返回欧洲,他就不仅以他的精神而且以他的整个存在,给我们带来了东方的真实形象。”(21)早在荣格的时代,“人们厌倦了学科的专业化,厌倦了唯理主义与唯智主义。他们希望听见真理的声音,这种真理不是束缚而是拓展他们,不是蒙蔽而是照亮他们,不是像水一样流过而是深入到他们的骨髓之中。”(22)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是否也应当“以他的精神而且以他的整个存在”给我们带来西方的或者外国的真实形象呢?是否也“希望听见真理的声音”,并使这种声音“不是像水一样流过而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之中”?这是否就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的最高研究境界呢?
三、比较学者的立足点
比较学者的立足点在哪里?任何比较都有比较的主体,比较的主体必须立足于某地,才有力量和能力进行比较。比较学者必须脚下有根,他的“比较”才能舒展自如、运斤成风、游刃有余,最后进入“比较”的最高境界。比较文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是跨文化的,当代已故的比较文学理论家迈纳在论及比较诗学时说:“只有当材料是跨文化的、而且取自某一可以算得上完整的历史范围,‘比较诗学’一词才具有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只不过是‘比较诗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23)比较诗学如此,比较文学同样如此。既然比较文学是跨文化的,而各种不同文化显然又存在着差异、矛盾、甚至对立,那么,我们该怎样评判这些不同的文化,我们以怎样的标准、理论或者观念去评价各种不同的文化?用荣格的话来说,就是当中国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科学原理”时,譬如说除因果原理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同步原理”(synchronistic principle)时,我们相信或者坚持什么样的原理是“科学”的?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显然是我们所反对的,东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也是我们应当担心和警惕的。比较文学在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以及传统思维习惯和定势之后,是否就不再有中心,甚至失去了立足之地呢?任何比较一旦失去了立足点,失去了根基,就不可能是稳固的、充分的、长久的。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比较学者比较的视野和方法时,是否将他们比较的立足点也一并横移过来?抑或是逐渐建立自己的比较文学的立足点,而真正领悟和掌握了比较文学的精髓?
卫礼贤钟情于中国文化,甚至酷爱中国文化,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中国人,他的立场仍然的西方的、欧洲的,“他始终仍是一个欧洲人,一个热爱青年人并对其寄予厚望的绝对的现代人”(24)。“卫礼贤到中国时是一位神学家和传教士,离开中国时却变成了儒家信徒。”他甚至说:“我作为传教士没有劝说任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对我是一个安慰。”(25)但这些只能说明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深入了,去除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固有的思维惯性和认识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立场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有时表现得几乎就像一个中国人,而他本人也常说,在中国就有人发现:他的思想和言谈举止比有些中国人还中国化。”但是,“他还是他,只是广博了,成熟了……他生来就注定要超越种族与民族的狭隘性而进入人类的层面。能够成为欧洲人的人很多,而能够把人类思想变为现实的人却很少。”(26)准确地说,卫礼贤是一个超越了种族与民族的狭隘性的欧洲人。正因为他超越的种族和民族的狭隘性,他才能如此热爱中国文化;正因为他是一个欧洲人,他对中国的翻译和解说才如此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欧洲人。
荣格自然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乞丐并不因为有人把手——无论是大是小——放在他手中而得到帮助,即便这可能正是他需要的。如果我们指点他怎样才能通过工作使自己永远摆脱乞讨,他得到的才是最好的帮助。我们时代的精神乞丐太容易接受东方人的手掌,不加考虑地模仿其种种方式……欧洲精神并不仅仅因各种新鲜感觉或一种神经的搔痒而得到帮助。中国花了几千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东西,不可能通过偷窃而获得。如果我们想占有它,我们就必须以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对它的权利。如果我们抛弃我们自己的基地,仿佛它们只是一些老掉了牙的错误,如果我们像无家可归的海盗,觊觎地栖身在异邦的海滩上,《奥义书》的智慧和中国瑜伽的顿悟,于我们又有何用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真实的问题置诸脑后,带着传统的偏见蹒跚前行,如果我们把我们真实的人性及其全部危险的潜流和黑暗遮蔽起来不让自己看见,东方的内省,特别是《易经》中的智慧,对我们也就没有任何意义。”(27)面对当今西方丰富的物质文化,我们许多人表现得就像是精神乞丐,太容易接受西方的手掌,将手掌上的东西不加分辨地尽可能地全盘照收。如果我们抛弃了我们自己的根基,西方文化于我们又有何用呢?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不至于沦落为文化乞丐呢?对于西方学者,荣格的忠告是:“我们需要有一种我们自己的根基稳固、丰富充实的生活,这样我们才能把东方智慧作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加以检验。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学习一点欧洲的有关我们自己的真理。我们的出发点是欧洲的现实而不是瑜伽的功夫,这种功夫只会蒙蔽我们使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现实。”(28)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我们首先应当有自己的根基稳固、丰富充实的生活,我们应当学习我们自己的真理和东方的智慧,这样才不至于被西方的文化大潮所蒙蔽而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现实。
其实,早在1907年,鲁迅在写作《摩罗诗力说》时就已经有了这种比较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他说:“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29)比较学者必须有自己的立足点,“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正是在审己与知人的过程中产生文化自觉意识,在这种文化自觉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有可能“清晰昭明,不同凡响”。杨周翰说:“我们的先辈学者如鲁迅等,他们的血液中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中国文化是其人格的一部分。这样他们一接触到外国文学就必然产生比较,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30)乐黛云继而指出:“杨周翰提出研究外国文学首先要有一中国人的灵魂,也就是强调首先要了解自己,要有深入的文化底蕴,才能使自己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中国特色,而中国文学也才能真正进入世界。”(31)当代法国后殖民理论家法农则从反面印证了鲁迅的观点:“一切被殖民的民族——即一切由于地方文化的独创性进入坟墓而内部产生自卑感的民族——都面对开化民族的语言,即面对宗主国的文化。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他越是抛弃自己的黑肤色、自己的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想当白人的安的列斯人尤其因为把语言这个文化工具当成了自己的而更像是白人了。”(32)即便是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描述和研究东方时也是有立足点的,这个立足点仍然是西方的,因为所谓“东方学”,其实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因而,任何人一旦在“比较”中失去了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真实的面孔,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只能是一副虚幻的面具。
当然,比较学者的立场并不总是固定不变的,也并不总是单一清晰的。1972年,德里达出版了一部访谈录,取名为《多重立场》(Positions),“它的多义性过多地表现在‘播撒性’的字母‘s’上?关于‘多重立场’,我要补充的是:撒播的实况、活动和样式”(33)。比较文学通常总是具有多重立场,这是由该学科的性质和特征决定的,但是,这并非是指每一个比较文学学者都具有多重立场,而是指每一个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应该有自己的立场,每一个学者的立场可以是不同的,甚至是变化的、矛盾的,这样才能够真正形成比较文学学科的多重立场。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强调比较文学的立场问题,并不是强调比较文学的先入为主,或比较学者的个人偏见和偏爱,以至于弱化或取消了比较文学学理上的普适性、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是警惕我们在比较研究中因为失去了立场而陷入一种失重的、飘忽不定的状态。
总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普遍和深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西方人对文学标准的选择、评定越来越限制,甚至规定着中国人对文学研究标准的认识和界定。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文学研究标准的认定也越来越接近,甚至趋于同一。这种情况固然意味着中国人对西方经典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认知水平的同步,但也隐藏着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和原创精神的弱化和丧失。因为这种“同一”基本上等同于“同西方”,尽管这里的西方可以是西方不同的国家。这样一来,西方学者对文学的“比较”标准就会成为唯一正确的标准,这也将成为衡量所有非西方学者学术眼光和水平的唯一标准。研究莎士比亚的非西方学者,最高目标和理想就是将来有朝一日能得到英国的莎士比亚专家的首肯和赞扬,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就得看俄罗斯人的脸色行事;研究福克纳的,自然就得唯美国学者的马首是瞻;至于研究歌德,当然就要看德国学者的眼神了……而那些西方汉学家,似乎并不太在意中国学者说了些什么,尤其不大在意中国学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说了些什么,有些西方汉学家甚至声称: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史只能由他们来撰写才是最公正、最客观、最真实的,因为他们最少顾忌和偏见。而事实上西方汉学家独特的视角和富有创见的成果的确曾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并因而改变了我们对某些中国文学作品的评价和看法。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叫“汉学”,中国人研究外国人的汉学叫“国际汉学”,国际汉学研究在今天已经成为国内一门蓬勃发达的学科,有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出了许多刊物、专著和丛书。中国人研究西方的学问,如果还有这样一种学问的话,叫“西学”,然而西方人对中国的“西学”似乎并不怎么关注,更谈不上有多少研究。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中国的“西学”缺乏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的“西学”如果只是对西方的“西学”的翻译和复制的话,自然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的“西学”学者缺乏自己观点和判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失去自己的学术立场。面对以上研究状态,如果我们不加以思考和警惕的话,最后中国比较学者发出的声音,便可能只是一味地重复西方、复制西方,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索然无味。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荣格曾告诫那些急于想学习和借鉴东方智慧的欧洲人:需要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根基稳固、丰富充实的生活,这样他们才能把东方智慧作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加以检验。巴赫金同样告诫我们:“存在着一种极为持久但却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于其中,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这别人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这种观念,如我所说是片面的。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别人文化之中,可以用别人文化的眼睛观照世界——这些都是理解这一文化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如果理解仅限于这一因素的话,那么理解也只不过是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不会起到丰富的作用。创造性的理解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己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摈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34)时至今日,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根基和立足点越来越摇晃不定、令人担忧。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太多的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出发点,失去了对我们自己的现实的关怀,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尽心尽力,我们离自己的目的地则会越来越远。
①②余虹:《立场·前言:虚无与立场》,余虹、徐行言主编:《立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③苏珊·巴斯奈特:《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黄德先译,《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
④Bernheimer Charles,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p.1-17.
⑤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⑥刘象愚:《比较文学“危机说”辨》,《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⑦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2页。
⑧(15)(17)(18)(19)(20)(21)(22)(27)(28)荣格:《纪念理查·威廉》,《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48页,第249页,第250页,第257页,第258页,第249页,第256页,第253页,第253-254页,第254页。
⑨(12)(14)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第29页,第20页。
⑩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74页。
(11)芭芭拉汉娜:《荣格的生活与工作》,李亦雄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66页。
(13)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荣格心理学纲要》,张月译,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页。
(16)(34)巴赫金:《巴赫金文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0-371页,第370页。
(23)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3-5.
(24)(26)W.F.奥托:《卫礼贤人格肖像》,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第6-7页。
(25)张君励;《卫礼贤——世界公民》,孙立新、蒋锐主编:《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29)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一百多年过去了,鲁迅的这篇有关比较文学或外国文学的论文仍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摩罗诗力说》在世界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双重背景中,以人类文明史和文化批判意识为视角,站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高度,以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系统评介了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并对中国诗歌发出了时代的呐喊。这就使《摩罗诗力说》当之无愧成为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和标志。”(见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比较而言,我们今天比较学者或外国文学学者撰写的论文,当下就鲜有人阅读,专业之外更是无人问津,何谈现实意义、百年之后?
(30)杨周翰:《镜子与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31)乐黛云:《后现代思潮的转型与文学研究的新平台》,《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11年第1期。
(32)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77-178、9、25页。
(33)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