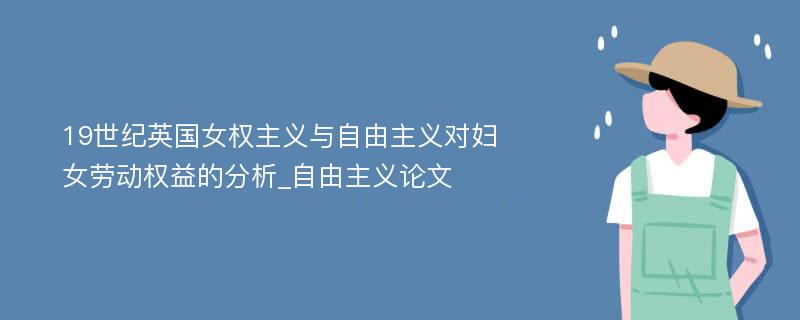
19世纪英国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妇女劳动权益思想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英国论文,妇女论文,权益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英国妇女的劳动权益问题是英国经济、社会现代化中产生的新问题。女性主义者把争取妇女劳动权益作为反对男权统治的基础,并在理论上、实践上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欧美学术界的许多学者把它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忽视了其自身的价值。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甚少。笔者通过对19世纪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妇女劳动权益思想的比较研究,阐明女性主义对此问题的贡献。
一、自由主义的探索与困惑
19世纪的英国是男权制社会,当时的社会观认为,两性自然本质不同,妇女较男人体质弱,经济上不能自立,也不需要自立,只有男性承担养活妻儿的责任。因此,妇女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任何保护。1851年英格兰、威尔士总人口17927609人,其中女性9146384人,20岁以上未婚女子1444556人。(注:Martha Victinus,Independent women 1850-192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P.27。)这些妇女分为工资劳动者和家庭妇女两种类型。1851年600万成年妇女有300万为生计而工作。(注:Pat Hudson and W.R.Lee,Women's work and the family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Manchester University 1990,P.125.)大部分劳动妇女就业于非熟练的、无组织、报酬很差的服务业和血汗行业。1851年,20岁以上的妇女18%受雇于家内服务业,16.3%在成衣业和鞋业,1.9%是教师,1.2%在丝织业,其余的是制造业部门工人、营业员、小商店店主,房东等。(注:Sally Alexander Becoming a Women and other Essays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Feminist History,Britain Mackays of Chatham P.L.C,Kent,P.15-16。)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妇女受教育机会的扩大,她们逐渐进入原属于男性的职业领域。但是妇女的工资始终低于男性,在同一部门,一般她们的工资是男性的1/3或一半,最高的也只有男性的2/3。(注:Sally Alexander Becoming a Women and other Essays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Feminist History,Britain Mackays of Chatham P.L.C,Kent,P.25。)家庭妇女只是无偿地管理家庭,操持家务,或者充当客厅里的装饰物。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都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承认这不平等的两性分工,否定妇女在公共领域的劳动权,否定妇女劳动的经济、社会价值,从而否认妇女的劳动权益。
亚当·斯密虽然意识到妇女劳动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他都强调家庭环境的重要性,但在讨论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时,他提出两性劳动力工资“两分法”:“最下级普通劳动者,为供养儿女二人,至少须取得倍于自身所需的生活费,而其妻子,由于需要照料儿女,其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己。”(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2页。)在他看来,两性对家庭承担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工资标准。女性的责任是照料儿女,从事家务劳动,不能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她们的最低工资只要能维持她本人生存,可以处于人类最低生存需要的微薄状态,而男性要供养本人、妻子、一定数量的孩子,他的工资即使在最激烈的竞争状态下,也不能与女性处于同等水平。
在讨论国民财富构成时,他否定妇女家务劳动价值,主张把妇女作为第二性来教育。他认为妇女为自己、为家庭劳动不能登记在公共生产的指数内,也不能包括在国民收入中。在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中,他排除了培养妇女的费用。他认为教育和培养劳动者的生产能力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组成部分。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两部分,家庭教育是自然机构,属于私人领域,公共教育只是培养有创造力的男人,而妇女不需要接受公共教育。他在《国富论》中明确指出:“对于女子教育的公家机构,是全然没有的,……女子所学的,或者是她的双亲或保护者判定她必需学习或者学了对她有用的课程,而别无其他东西。她所学的一切,无不明显地具有一定有用目的:增进她肉体上自然的丰姿,形成她内心的谨慎、谦逊、贞洁及节俭等美德;教以妇道,使她将来不愧为家庭主妇等等。”(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38页。)这就是说,妇女尤其是中上层妇女,唯一的经历是成为妻子和家庭主妇,她唯一可做的是让自己对男性具有媚力。在《道德情操论》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纯洁与谦恭是妇女必备的品格,妻子必须对丈夫关心、忠诚、诚实,而丈夫没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宪章运动高举的是当时激进的自由主义旗帜,但宪章主义经济学家R.J.理查德森同样否定妇女在公共领域的劳动权。他告诫妇女,“公共领域是男人的工作……你不应该去完成,你的位置在家庭,你的劳动就是你对家庭的责任,你的兴趣存在于你的家庭利益中,不要投入于别的,财富积累这样的服务看起来是你自愿的,但是你的耻辱!去寻找丈夫,没有丈夫,你会受累,有丈夫家庭,你回家去,管理家庭使它舒适……”(注:Sally Alexander Becoming a Women and other Essays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Feminist History,Britain Mackays of Chatham P.L.C,Kent,P.12。)《北极星报》甚至把抵制妇女外出工作作为维护男性高工资的手段:“让她们在家照顾家庭,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强制性地实现男性高工资的比例。”(注:Sally Alexander Becoming a Women and other Essays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Feminist History,Britain Mackays of Chatham P.L.C,Kent,P.124。)
穆勒是自由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中男女平等思想最为突出的一位。他在《妇女的屈从地位》、《政治经济学定义》等著作中,超越了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境界,鲜明地阐述了妇女劳动权益的思想。
首先他肯定男女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是社会环境导致女性屈从地位。“所谓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智力差别,不过是他们在教育和环境上差异的结果,并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别,更不必说极端低劣了”(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4页。)因为“妇女从最年轻的岁月起就被灌输一种信念,即,她们最理想的性格与男人截然相反:没有自己的意志,不是靠自我克制来管束,只有服从和顺从于旁人的控制。一切道德都告诉她们,女人的责任以及公认的多愁善感的天性都是为旁人活着,要完全克制自己。”(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8页。)社会拒绝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妇女受困于家庭,她没有时间、精力和自由的思想空间去进行生产和创造活动,大部分妇女没有获得特别技能。结果,她们长期在低技术行业就业。穆勒批判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力工资“两分法”的实质是男人运用市场权力、社会政治权力限制妇女的劳动权,加强他们对社会家庭的控制权。实际上,穆勒把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中对父权依赖关系与社会、伦理、法律上的受压迫结合在一起。他不仅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劳动力工资理论,而且肯定了两性平等的劳动权。
其次,穆勒从妇女的性别优势出发肯定妇女在公共领域的劳动权和经济上的自主权。他认为妇女的才能重实践,她们的直觉能力超过一般的男人,对现实敏感,并且有较快的理解力,这种能力使她们在工厂制生产中的生产能力不低于男人,这些都足以使妇女被当作自由的个体,而不是被当作受保护的对象。同时,他认识到妇女经济自立是婚姻平等的基础。“挣钱的权力对于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妇女来说是最根本的,她只有拥有独立的财产。才有平等的婚姻。”(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29。)他指责限制妇女择业自由的《工厂法》是改革家和慈善家最大的错误,是“承认不公正权力的结果,代替纠正不公正本身”。(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24。)所谓妇女的保护者实际上是妇女的压迫者。因为对于那些有独立谋生能力的妇女来说不需要被保护。他强调给妇女财产权、自由劳动权,并认为两性平等的劳动权不仅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唯一办法,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让妇女自由地选择职业,对其他人开放的同样职业领域及同样奖励和鼓励也向妇女开放,从而给予妇女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可以期待的第二个益处,就是可以双倍的智力才能为人类更好地服务。”(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4页。)
但是,穆勒的女性主义思想充满矛盾。在妇女劳动权益问题上,他在肯定妇女的社会、家庭能力,主张给妇女平等的自由择业权和财产自主权时,没有具体提出如何改变男人和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在他的思想深处还认为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道德价值对于充满竞争的公共领域是必要的解毒剂,妻子和母亲用全部的时间去教养子女,装饰美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他赞成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早在1832年穆勒曾说过:“妇女的伟大职业就是为生活添彩:在思想、灵魂、身体中播种所有令人快乐的力量,把美丽、高雅传播到每一个地方。”(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35。)这就是说,妇女的职业就是为别人点缀生活,为别人提供快乐。在此基础上,他在批判社会对妇女的奴性教育同时,又肯定把女性作为社会的第二性来教育,“教养妇女将对世界产生温柔的影响”。后来他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这种思想,但他还是坚持婚姻和雇用劳动对于妇女是不和谐的,“妇女的天性使她不能和男人一样谋职,她们能做的事并不是与男人竞争,竞争足以排斥她们”。(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36。)
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承认现存的两性分工,一定程度上否定已婚妇女公共领域的劳动权。他认为妇女除了承担家务劳动外,如果“她再承担家外劳动,也难以从原来部分解脱,只会妨碍她做好该做的事情。她自己不照料孩子和家务,就无人代替她。存活下来的孩子,他们可能很好地成长,然而家务管理很可能很糟,即使从经济上考虑,妻子赚钱,其实是得不偿失的。”(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0页。)因此,他主张已婚有孩子的年轻妇女可以专门照顾孩子,让丈夫在劳动力市场上挣钱。
在妇女家务劳动价值问题上,穆勒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它的经济价值。一方面他肯定妇女的家内劳动是经济活动的组成部份,“她不只是承担了她那一份义务,她为他们共同生存需要已付出体力上和精神上的努力”。(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30。)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了妇女生育孩子对增强社会生产能力的贡献。正如约瑟芬·多诺万所说:“穆勒并没有深入地探究已婚妇女作为家庭支撑者其作用何在”。(注: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这正是其女权主义理论不足之处。
可见,穆勒还是没有跨出其他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两性分工的思想框架,在他的理论中仍然承认家务劳动是妇女的第一责任,他从未想到家庭责任由男女共同负担,或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意味着外出工作的已婚妇女要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责任,妇女从根本上无法实现择业自由。
总之,穆勒的思想具有启蒙性,对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解释都不同于亚当·斯密和18、19世纪的经济、政治哲学家,他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妇女不平等的经济状况,但他不能提出可行的方案,因为他与同时代人一样,不能从本质上取消来自传统的两性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父权制的特权。正如女性主义者M.A.朴乔所说“穆勒没有完全超越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权制观点。”(注:Women's Agency in Classical Economic Thonght:Adam Smith,Harriet Taloy Mill,and J.S.Mill,Feminist Economics 1999.3 p.53.)
二、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19世纪英国的女性主义者,在反男权制传统中,从女性生活的现实体验出发,争取妇女劳动权益,对妇女的工资、劳动价值、社会经济角色等问题的认识,继承了穆勒的女权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穆勒思想中尊重妇女的劳动权与保护男性特权之间的矛盾,并提出超越时代的现实主义的女权观。
1、关于妇女劳动权和社会性别分工问题。首先,她们否定现存的两性分工,维护妇女劳动权。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像穆勒那样,肯定两性天生的能力、智力平等,强调妇女缺少技能是因为妇女没有劳动权,社会没有把她作为劳动力来训练。劳动权是解决妇女受歧视问题的前提。她们认为是男人“在有利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职业,高喊某些工作不适合女性,而剥夺她们的工作权利,并把她们驱逐到报酬最低,受苦的行业。”(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41。)巴巴拉批评“妇女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会夺走男工嘴里的面包”的观点是男性垄断主义精神的表现,从本质上是行使男权主义特权,把妇女排挤出工匠和技工的行列。女性主义者肯定给妇女劳动权有益于两性,将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越多的人工作,对生产的贡献也就越大,越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41。)另一方面,她们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劳动权是经济、婚姻、社会平等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促进妇女雇用协会”组织,明确指出“女神和政治经济学都告诉人们,地球由工作的人们拥有。”(注:Sally Alexander Becoming a Women and other Essays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Feminist History,Britain Mackays of Chatham P.L.C,Kent,P.139。)如果没有独立的劳动权,没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妇女在婚姻中不可能与男人平等。同时,她们把劳动权上升到人权高度,提出劳动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任何人不可剥夺。巴巴拉在1857年出版的《妇女和工作》一书中指出:“在各个领域妇女和男子平等,妇女是上帝的孩子可以享受与男子平等的各种权益。因为妇女要吃饭,要养活孩子,还有其他人要靠她生活,所有的男人希望工作的理由也正是妇女的工作理由。男人必须自立和工作,女人也应如此,否则她将堕落,立即处于男人之下,接受奴役的地位。”(注:Sally Alexander Becoming a Women and other Essays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Feminist History,Britain Mackays of Chatham P.L.C,Kent,P.37。)在此基础上,她们不仅在理论上借用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理论,鼓励两性在公共领域公平竞争,而且在实践上充满女性的自信,全方位挑战男权社会。19世纪50年代末,伯明翰一群年轻的未婚女子每周在俱乐部举行讨论会,讨论男人是否应该独自享受男性俱乐部,男性是否能胜任他们设想的工作等问题,试图以实际行动改变性别分工。
其次,她们向现存的女性标准挑战,重塑新女性形象。当时男人们的女性标准是妇女是否具有吸引力,男人最大数量被吸引,也是妇女最大的幸福。妇女依靠别人:丈夫、兄弟或其他英雄,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感情上愿意自我牺牲,体质上纤弱,妇女“如果与男性处于同一个工作标准,将威胁她们再生产的功能。”(注:Martha Victinus,Independent women 1850-192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P.22。)女性主义者批评这些观念是“让妇女更女性化,其实就是让她不明事理,愚味、虚弱、病态,是荒堂的。从本质来说,妇女越强壮,越具有女性化。”(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38。)劳动将使妇女更加健康美丽,更具女性化。如果妇女在任何场合生活的欢乐都依靠男人,这意味着她被迫接受有害于她的另类标准。“她们认识到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自由妇女,“不但要活得更幸福更有用,而且让自己比毫无色彩的服从更具有吸引力”。(注:H.M.Swanwick,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London 1913,in Dr Marie Mulvey Voberts Suffragists-towards the vote,P.138。)显然,女性主义树立的新女性标准对19世纪的性别分工是一种挑战,也是对正在成长的妇女家外就业的肯定,这与穆勒提出的提高女性素质,以便更好地充当男性伴侣的思想相比,女性主义者更强调妇女的独立性,与男性的平等权,对生活的自主权。
2、关于妇女的劳动报酬问题。女性主义者探讨妇女长期处于低薪状态的原因:一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M.G.福赛东等女性主义者援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工资取决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取决于大部分生产性工业的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雇主以较高的工资比例维持各个领域熟练工人的再生产。而她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妇女所面临婚姻生活中的分工使她们较少能继续工作,她的父母不愿意化更多的钱去训练她”。(注:H.M.Swanwick,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London 1913,in Dr Marie Mulvey Voberts Suffragists-towards the vote,P.72。)男性的工会组织和行业习惯都否定妇女直接参加行业,或当学徒接受技术训练。妇女从小就被剥夺了受技术培训的机会。结果,妇女几乎被排除在所有高工资的国内行业之外,大量的妇女集中在棉花纺织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而男人因为垄断了必要的技能训练,几乎垄断了机器制造业、银行等报酬优厚的行业。因此,只要存在对妇女劳动力技术限制,就会人为地增加妇女劳动力供给的限制,使妇女继续处于低工资状态。所以女性主义者指出,“不能说供给和需求是不受限制的,而是受多种人为限制”。“只要男人垄断报酬好的行业,妇女就会处于残酷的奴隶地位。”(注:H.M.Swanwick,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London 1913,in Dr Marie Mulvey Voberts Suffragists-towards the vote,P.74。)
二是社会偏见。因为,在传统的社会观念中,利他主义的男性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妇女儿童是自利成员,依附于男性,妇女可以依靠男性生活,她愿意接受低工资和比男人低的工资。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观念必然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男亲属愿意养活她们,她们的工资只是私房钱,二是男人养活她,她要讨他的欢心。而事实上,男性可以在不负责任的前提下获取所谓公平的工资,而就业在广阔的血汗行业的妇女成为受害者,即使她们与男子从事相同的工作,其报酬也低于男性。这样,妇女仅靠雇用劳动要在经济上独立非常困难,人格上也只能居于从属地位。
如何解决妇女不公平的工资待遇问题?女性主义者否定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劳动力工资理论,努力塑造经济自立、自尊、自强的现代女性形象。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是独立的个体,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应包括培养女性的生产能力。她们提出家庭社会应给妇女提供与男子平等的教育权利和职业训练的机会,让妇女有独立谋生的能力,给妇女打开更多的职业是防止妇女工资下降的主要手段。M.G.福赛东提出通过组织妇女工会和为妇女提供更多职业训练,提高妇女的就业能力,保障妇女公平工资。巴巴拉挑战父权制的思想,提出“父亲没有权力把对女儿的负担转嫁给另一男人,否则会降低妇女的价值,使她们沦为妓女,不管是合法的妻子还是大街上的妓女,只要父亲因为性别的理由没有教她如何为自由挣面包,妇女的身份就会降低。”(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38。)她劝告父亲们要给女儿经济自立的技能训练,并强调“给女孩子心灵上的财富,训练她们的工作技能比结婚更重要。”(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38。)这正是穆勒等男性思想家所无法认识到的。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者组织为提高妇女的工作技能而努力。“促进妇女雇用协会”的主要目标是训练妇女的工作技能和经济自立能力,协会领袖还组建“妇女生活互助团体”,设想通过该组织,妇女可以作为职员、代理人涉足多种专业,包括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等原属于男性职业的训练,她们还建立自己的合资公司,试图通过合作,用有限的资金建立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国民财富的再生产,获取与男性平等的工资。此外,女性主义者力图改善妇女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1897年“妇女工业委员会”召开代表大会,主要讨论妇女家内雇用的最低工资问题。代表们呼吁通过社会立法提高家庭雇用工作的卫生条件。会后还起草了“家内工作规则”,首次于1899年3月由约翰·布伦上交下院,力图使《工厂法》扩大到家庭车间。这样,女性主义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强制性地把原属于私人领域事务引入国家政治公共领域。“这意味着公共生活再也不能与家庭生活相分离,因为公共团体正在处理影响家庭的问题。”(注:Angela V.John,Unequal Opportunities,Basil Blackwell,1986,P.239。)
3、关于妇女家务劳动价值问题。第一,女性主义者肯定妇女家务劳动的重要性,把它列入国民财富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者把维持家庭生存的劳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家外劳动,即挣钱,提供足够的衣食住等生存条件;二是家内劳动,合理地安排家庭的饮食、起居,让家庭成员舒适地生活。妇女承担家务劳动时,牺牲了外出挣钱的机会,让男人有精力挣更多的钱。巴巴拉说:“妇女在家里象管家、护士,也象孩子的家庭教师,她象丈夫一样支撑家庭,这就是说男人养活妻儿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妇女放弃了合适的工作而操持家务时,她是自己养活自己。”(注:Ross Evans,Pujol Michelea,Feminism and anti-feminism in early economic thought U S A 1992,P.40。)男人选择了工作,他可以享受8小时工作后的成功快乐,把沉重的家务负担卸在妇女肩上。其实妇女比男人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一方面她们承担超负荷的家务劳动,心情不愉快。另一方面承受家庭、丈夫、孩子对她的依赖,她要照顾他们的生活,男人为此充满骄傲和希望,而妇女生病时没有人服侍她,帮助她避免病情恶化。因此,她们肯定“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单独为孩子创造世界,为世界创造孩子,而是他们共同创造。”(注:H.M.Swanwick,The Future of the women's movement,London 1913,in Dr Marie Mulvey Voberts Suffragists-towards the vote,P.154。)男人和女人构成了家庭共同体,两性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要充实知识,给予自由。妇女的劳动应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且应该与男人共同分享男人在公共领域的收入。把家务劳动作为劳动分工的组成部分,承认妇女在再生产领域的贡献,这正是现代女权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也是女性主义者对亚当·斯密等劳动价值观的超越。
第二,从权利与义务平等角度论证两性平等的经济权。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社会中妇女与男子共同承担着责任,许多单身妇女在经济上独立地养活自己,男女同样是国家的纳税人,为国家的富强出力。国家所支付的教育、食物、医疗、保健等费用都来自税收,“国家在危急时刻妇女与男子一样,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国家,包括为战争付出精力以及各种努力,冒种种风险,参与比直接参加战斗更多的服务,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注:Dr Marre Mulvey Roberts,the Suffragists-Towards the vote Female suffrage A.B.C)1995.P.10。)但是社会立法只肯定男性的工作,男人的税收利益三倍于妇女。从事理家——所谓的女性工作没有被列入享受疾病福利范围,几乎所有的妇女都没有享受失业福利待遇。她们从相同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有相应的权利的观念出发,重新构建两性关系模式,提出两性应享有平等的家庭财产权,为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等思想。她们建议,通过法律,强制性地给妻子固定部分收入,以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如保护怀孕的母亲健康和强壮,给妇女为家人的健康服务付服务费。有人提出建立国家母亲保证金。一些女性主义者吸收欧文主义互助合作、友爱的思想,设想家务劳动社会化来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
笔者认为在充满性别歧视的社会,女性主义者提出这一理论从主观上反映了她们要求社会承认妇女家内劳动的价值,以及对社会作出的独特贡献,保障妇女劳动权益,弥补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妇女劳动价值认识上的缺陷,为国家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政策提供思想理论基础,也为夫妻关系向伙伴关系发展打下理论基础。
总之,从亚当·斯密到穆勒,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否定妇女的独立存在,否定她们的劳动权益与劳动价值。穆勒虽然肯定两性在智力、能力上平等,肯定妇女劳动对家庭、社会的贡献,同时也看到了社会导致妇女屈从于男性,他批判现存性别分工对妇女的不公平,提出给妇女平等的劳动权、教育权、参政权以保障妇女独立的人权,但是,他没有完全否认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并赞同把家务劳动作为妇女的主要责任,也没有真正肯定妇女生育、教育子女等家务劳动对劳动力再生产、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女性主义从妇女的生活体验出发,继承穆勒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中对妇女智力、能力、劳动权益的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穆勒理论中维护女性权益与男性特权之间的矛盾,提出工作着是健康美丽的,独立生活技能比结婚更重要等新女性标准,主张通过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女性工作技能,通过社会立法实现两性公平竞争、公平劳动、公平工资。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肯定妇女家务劳动价值,两性权利与义务平等基础上,提出给妇女财产所有权,给妇女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以保障妇女的劳动权益等思想。显然,这是女性主义对自由主义妇女劳动权益理论的超越,也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我们从费尔斯通等人的理论中可见她们的思想缩影,这也是英国实施妇女劳动权益保障法的理论依据。然而,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来自于客厅,主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来自于中产阶级,她们主观上并不想挑战母亲的责任,很多人还是把妇女的家庭责任放在首位。她们也没有真正找到解决妇女劳动权与家庭责任、女性角色之间矛盾的途径。很多人的思想深处还没有真正想让女性摆脱第二性地位。她们反对限制已婚妇女工作,但有时又主张家庭能挣到足够的钱,妇女可以不工作,她们强调女孩得到训练,有能力养活自己,必要时,要培养她做母亲和侍候别人的技能。A.戴维称之为“理想的母性模式”(注:Angela V.John,Unequal Opportunities,Basil Blackwell,1986,P.224。)。尽管如此,19世纪的女性主义以顽强的力量逐渐改变社会的偏见,重塑公共观念,重塑妇女形象,为人的现代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M.维什纽斯所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为自己从家庭团体中独立和新女性形象而骄傲,她们通过努力工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世界上为自己开辟道路,她们坚信只要她们努力,其他人能做的事,她们也能做。”(注:Martha Victinus,Independent women 1850-192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P.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