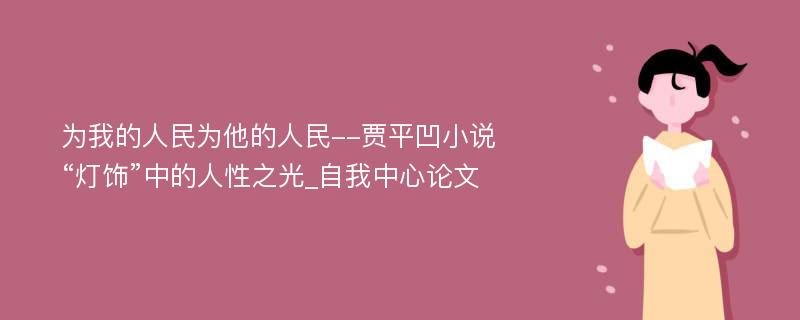
为我的人与为他的人——贾平凹小说《带灯》崭露的人性之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人论文,为他论文,人与论文,之光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9-0054-06
贾平凹的《带灯》写的是开放年代,也叫开发年代的乡土人生。在开放、开发之前,人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九百六十万土地都是社会主义江山,所谓“手心手背都是社会主义的肉,村前村后都是社会主义的田。”谁敢分离“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整体,分裂我们社会主义江山,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个容不得“他人”存在的时代,是一个只许“合”不许“分”的时代。开放、开发之后,中国进入一个“分”的时代,“我们”分裂为“你”“我”“他”,土地分割成“你”“我”“他”的责任田。不论你是谁,可以任意翻弄自己的手心手背,若是想动“他人”的手心手背,就得有个说法,还需征求“他人”同意,你才能动,没有说法或未经许可对“他人”的手下手,“他”就会骂“你”流氓,告你骚扰。也不论你是谁,可以在自家的地里随便下犁耕作,收获庄稼,但不能犁“他人”的地,收“他人”的庄稼,也不能不经“他人”同意,就在人家地里修路、盖房,否则,就会引发冲突,吃上官司。
“我们”分裂成“你”“我”“他”之后,各人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主。人与人之间不像之前那样“和气”了,变得越来越“生分”了。“你”跟“我”讲手心手背,“我”会警惕“你”别有用心,会问“你”说谁的手心手背,手心手背都是具体的有主的,不是之前那个属于一切人又不属于任何具体人的抽象概念。有主的手心手背是有生命有感觉的,你挠她,主人就会痒,你扎她,主人就会疼,因此,你动手之前,必须给主人交代一下,征求主人同意。抽象的手没有具体归属,没有生命感觉,因此,你随便摸揣任意折腾,并不会引起类似前述主体的反应,也不见得有人站出来跟你生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之后,田地有了它具体的主人,由主人负责这块田地的耕种与收获。同理,这块田地的耕种与收获关联着主人饭碗里的内容与稀稠,关联着主人身上的冷暖。因此,“你”要耕“他”的责任田,收“他”辛苦务劳的庄稼,就等于夺“他”的饭碗,剥“他”的衣服。往严重来说,“你”这种行为不仅剥夺“他”的生存权,而且羞辱了“他”的人格尊严,“他”怎能与“你”和气而不跟“你”生分!在这种场合,“你”不能光给“他”讲大道理,大道理“你”“我”“他”都懂,都知道这玩意儿好听不好用,它不能当田地,种不成庄稼收不了粮,织不成布匹盖不了房,饱不了肚子,暖不了身体。“你”可以把道理讲得比天高,但是,“你”“我”“他”都是地球人,都有一个沉重的肉体,都知道天太高,这不争气的肉体上不去。天上的道理营养太丰盛,需要高级的脾胃来消化,“你”“我”“他”的脾胃太粗鄙,消化不了,只适合消化地里种的粮食。人从乌托邦返回现实之后,首先提刀把那个要为“我们”所有人负责的“上帝”砍了,把那把许诺能打开所有人生之门的万能钥匙扔了,每个人都要自我做主,开自己的人生之门,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喊了几十年当家做主的主人被开发出来了,每个人都要主自个的事,过自个的日子,活自个的人。想稀里糊涂粘“他人”,人家不答应了。“你”“我”“他”之间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高筑墙。“我”生生地被从“我们”中分离出来了,被逼着要为自己做主了。“我们”开发成必须为自己做主的“你”“我”“他”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活得很具体,每件事都有了负责的主体,抽象混沌的“我们”开了七窍,混沌的“你”“我”“他”开了七窍。开始用自个的眼睛打量自个的生存位置,用自个的心体验自身生存的快乐与辛酸,用自个的嘴倾诉自个真切的生存要求。“你”“我”“他”只对自己的位置负责,行使自己位置的权力,完成自己位置的义务。“你”“我”“他”一方面相互在空间上划清生存位置间的界限,竭力捍卫已有位置的权益不受“他人”侵犯,另一方面相互比较不同位置尊卑高低的不同,拼命争取更高的生存位置,为自己储存更多的生存本钱。开了窍的人,从浪漫的“我们”回到了现实的“我”,由一心“为公”的人变成一意“为我”的人,“大我”变成“小我”了。做事的动力由遥远的理想变为当下的欲望,生存的动力实在了。操心的事情由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变为自己的前程,后辈儿孙的发展,活得更加靠谱了。“大我”以四海为家,以天下为己任,对自个没有也不能有具体的责任,是一种只有上半身的思考与想象,没有下半身的感受和体验的存在,即使腹中饥渴,衣衫破旧,依然会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小我”对自己负责,是一个看重下半身的感受与体验,看淡上半身的思想和想象的生存者,有了痛感他就骂,有了快感他就赞,“听说工资又涨了,心里觉得爱党了”。“小我”不喜欢究虚理,更不屑于建构乌托邦,遇到人用某某主义大道理解决“他人”的思想问题,就会骂假正经。听到谁用幸福的允诺应付“他人”现实的生活困难,就会指责他瞒和骗。“小我”讲实际,事事都动真格的,他要解决的都是生活中遇到的具体而微的小问题,让人觉得一地鸡毛不足挂齿,但是,要把这不足挂齿的一地鸡毛捡起来,却必须弯腰劳动,要把它们清理干净,也必须出力流汗。“小我”提出的所有问题,要解决都得刀下见菜,而且对菜的花色品种营养价值的要求很具体,你不能拿抽象的道理打发他,更不能用幸福的允诺糊弄他。且不说他根本不信你画饼充饥那一套,你自己也知道,在开发时代一切空洞的东西都很无力,别说拿它说服“他人”,首先它根本就不能说服自个。因此,当人由“大我”即“我们”,分裂为一个个“小我”即“你”“我”“他”的时候,人生问题也由抽象变得具体了,具体问题的解决需要实际的付出,比起耍嘴皮子,难度增加了。解决具体问题的主体出现了,主体必须对他解决的问题负责了,比起空里来雾里去,责任重大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是某个“小我”在自个特定位置上遇到的,基于自个特殊利益提出来的。“你”的位置上遇到的问题,在“我”这儿可能就不是问题,“你”的特殊位置的利益,可能对“我”非但无益,而且有害。“我”怎能为了解决“你”的问题,维护“你”的利益,负责任的伤害自己。“你”和“我”是不同的责任主体,是相互利害冲突的“他人”关系,人际关系比开窍之前紧张了。
“你”“我”“他”为自己负责了,人生自我做主的时代开始了,做人变得困难了。开发之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上帝,他替“我们”统一思想,指挥“我们”统一行动,为“我们”统一负责。“我们”只要听他的话,按他的指示办事,一切就都搞定了。“我们”只要心存这个上帝,目中可以无人。现在,这个上帝死了,“我们”分裂成“你”“我”“他”了,第一遭感受到“我”每时每刻都要遭遇到活生生的人,都要在现实的人群之中做人了。“我”在现实的人群中做人,每天都会面对形形色色与“我”不同的“他人”,这是“我”的宿命。因为,生“我”之前已生了“他人”,生“我”之时也在生“他人”,生“我”之后还在继续生“他人”。所以,“我”服膺先贤的说法,“人”由一撇一捺组成,一撇自我中心不是“人”,一捺坚决排他也不是“人”,两者相互接纳组合才能构成“人”。所以,做人从来都是在人群中,面对“他人”来做,让“他人”见证“我”的做人历程。古人说,做人就是在“相人偶”,就是说,“我”一定要在和“他人”相遇的过程中,扮演“我”的角色,承担“我”的责任,行使“我”的权力,完成“我”的义务,实现“我”的潜能,创造“我”的人生价值。但是,有些个人总是习惯于“自我中心”,不习惯与和“我”不一样的“他人”相处,总要想方设法把“他人”变成“我”的人,这个“他人”若是上级,“我”就奉迎拍马极尽贴、粘之术。这个“他人”若是下级,“我”就关心照顾让他自觉贴、粘上来。“我”的人是和“我”一心的人,是“我”的“哥们”“姐们”。变不成“我”的人,是和“我”二心的人,是“我”的“路人”甚至是“仇人”。“哥们”“姐们”的事就等于“我的事”,一定要办扎实,办彻底,办圆满。“路人”的事先放到一边,等有闲功夫再办,没有闲功夫了就不办。“仇人”的事一定要捣乱,做手脚,让他玩完。自我中心的人是绝对主义者,认定“我们”都是人,人和人都是一样的。“我”是“我们”的代表,是衡量“我们”人的标尺,和“我”一样的都是人,和“我”不一样的,要么是“非人”,要么是“病人”,总之,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对待不正常的人,就要使用非常手段,不然,“他”会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提出不着边际的要求。对“他”敲打敲打,有助于“他”头脑清醒。人际关系是相互对等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排他的同时,也受到了排挤对象的排挤,在打压“他人”的同时也受到打压对象的打压。于是,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社会环境越来越不稳定。社会不稳定,“你”“我”“他”为自己人生做主的权力都受到威胁,谁都缺乏安全感。底层百姓,地位卑微,势单力薄,生存权无法保障。基层干部职位太低,权力太小,想要做主,还需要往上爬许多台阶。人人都不满,人人都不安,为了争取生存权利,捍卫人生尊严,有门道的拉关系,没门道的用智角力,正所谓“鱼也争,虾也争,拼死争个水中雄,不争不是真性情。”竞争既是发挥潜能否定“旧我”,创造条件实现“新我”的过程。又是与各种竞争对手来往周旋,与这些“他人”繁忙烦神的过程。
樱镇人进入开发年代,每个人每一天都可能遭遇形形色色的“他人”,面对有形无形的竞争,日子过得都很忙乱。初遇这种情况,心里面都相当矛盾。一方面,“你”“我”“他”都认为,竞争给自己带来了机遇,让自己有了发挥潜力实现存在价值的环境与平台,因此,一旦自己遇到竞争升迁或者竞争发财的机会,就会由衷地感叹这样真好。另一方面看不惯别人与“我”竞争。一旦发现“他人”与“我”竞争升官加爵或者发财致富的事情,就会表现出厌恶烦躁和不爽。每个人都用新的伦理要求“我”自己,认为“我”应该如其所能的生活在竞争中,通过竞争否定没有出息的“旧我”,创造更有前途的“新我”,“我”若安守本分,就是不思进取。每个“我”都用古老的伦理要求“他人”,认为“他人”应该如其所是的生活,始终与自己的位置、身份保持一致,参与竞争就是越界越轨。尤其是镇政府领导和各村的负责人,他们根深蒂固的认为,“我”既是“我”自己,又是本地盘所有“他人”的代表。“我”领导和负责的地盘,一切都应当“我”做主。“我”心所想就代表本地盘所有“他人”之想,“我”嘴里所说就代表本地盘所有“他人”之说。“他人”应该一切行动听“我”指挥。安分守己作“我”的对象,装扮“我”的风景,凸显“我”的主体-主宰地位。如果与“我”竞争,就是给“我”制造麻烦,坏“我”的好事,威胁“我”的主体-主宰地位,要把“我”变成“他”的对象,“他”的风景,至少要分享“我”的主体-主宰地位,这种“他人”让“我”不安,让“我”心烦,逼“我”向“他”出手。“我”代表大局,向“我”挑战,就是破坏大局。“我”从大局出发,处理一切人和事,都要视其对“我”这个大局的利害关系而定。对“我”有利的就尽力推动,对“我”不利的就竭力阻挡,不关“我”痛痒的,视其为虚无。樱镇书记天天夜里去县城请客吃饭走门子,想方设法升位子。市委黄书记来检查工作,他觉得这是一个接近上司,讨好上司,为自己上升加分的机会,因此,带领镇长早早恭候迎接,而且全程陪同。认真准备汇报材料,亲自汇报。安排了丰盛的午餐,布置了最干净的午休房间。精心选择视察路线,布置视察地点。为黄书记访贫问苦提前准备好慰问品和慰问金。安排了黄书记与干部职工合影留念的照相事宜,叮嘱要多正面照、仰照,严禁俯拍。甚至安排好了书记每两小时要上一次的厕所。为了尽可能堵住一切漏洞,防止任何意外发生,规定樱镇所有干部不得在市委书记检查期间请假。为了在樱镇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村干部选举,他提出“要把和我们一心的人提拔上来,把和我们二心的人撸下去”。①所谓和我们一心的,实际就是和“我”一心的,就是能听“我”的话,按“我”的指示办事的人。元家兄弟和拉布换布听“我”的话,“我”就让前者当镇西街的领导,让后者当镇东街的头。提拔需要政绩,“我”想办法走门子,给樱镇争取到了建设大工厂的政绩工程,工程建设期间,天天到工地巡视,一天不去看,就吃不香睡不踏实。元家兄弟和拉布换布敲锣打鼓欢迎大工厂进镇,书记认为这是给“我”的脸上涂粉,身上贴金,就分别给他们承包一些能挣钱的生意。王后生提出大工厂有污染,影响当地环境和当地人民生活,书记认为这是给“我”伸腿使绊子,坏“我”的好事,就派人对其严刑拷打,逼其走街串巷宣传大工厂是循环经济,没有污染,对樱镇有好处,直到王后生人困马乏口干舌燥,非但不让他歇息不给他水喝,还要在他背上贴一条宣传大工厂好处的标语,才放他回家。
樱镇这些自我中心的领导,把自己当刀当案板,拿“他人”当肉,用镇书记的话说,“肉到了咱案子上,咱想怎么切就怎么切。”②这个“我”虽来自群众却脱离群众,只喜欢群众作“我”的人,听“我”一人独语,不喜欢群众做“他人”在“我”面前众声喧哗,更讨厌“他人”与“我”平等对话。喜欢外面的世界对“我”开放开发,却坚决对“我”地盘中的“他人”瓷化固化。在樱镇这块地盘上,“我”就喜欢做镇政府院子那棵独一无二的塔松,没有竞争,横枝邪股随意长,不愿做林中的树儿,受其它树的限制。镇上的主要领导从来说一不二,并且用行动告诉所有属下和群众,“我”是唯一的权威,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我”平权或者分权。镇书记和镇长下乡检查,书记停车解手,镇长的车走到了前面,书记转身掉头回家,用行动告诉镇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乱了规矩。书记热火朝天地抓大工厂建设,属下反映十三户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他马上推给镇长,让属下明白,“我”是抓大事掌控大局的,所有小事和局部问题,都不应该找“我”烦“我”,“我”是掌柜的,不能当伙计用。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拉布、换布改造旧街道,拆每一间旧房,这哥俩说值多少就值多少,房主不能讨价还价。元家兄弟负责大工厂修路盖房期间农民的树木赔偿费用,该不该陪,该赔多少,他哥俩说了算,谁要争辩和质疑就是犯上。樱镇这些大大小小的掌权派,生活在开发时代,只想利用手中权力吃光开发的肉,喝净开发的汤,不想出让任何好处与“他人”分享。开发时代的目的就是要开发每一个人当家做主的潜能,真正实现所有人当家做主的愿望。樱镇的当权派拒绝给予底层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力,坚决否认底层群众具有当家作主的资格。当权者认为,“我”让群众当家,就是让“我”当奴,让群众做主,就是让“我”做仆。那就把“我”从管理、管控的角色,转换为服务、服从的角色。“我”一旦失去管理、管控的权力,底下的人岂不忘了自己的身份,想入非非,人心不安,社会不稳。
上级要求维稳,本意是要求基层干部倾听群众呼声,解决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底层群众困难,让群众安心生产、生活。樱镇领导却认为,维稳就是要坚决堵截各种上访者,要求综治办防旱、防洪、防上访,把群众反映自身诉求,当成与天灾一样恐怖的人祸。堵截群众上访的腿,堵塞群众上访的嘴。要把樱镇的底层群众打压成开发之前那种沉默的大多数。然而,时代毕竟进步了,为自己当家做主的个体毕竟被开发出来了,即使与“我”书记一心的人,像元家兄弟与拉布换布两个大户,也必然分化成有各自利益诉求的不同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主体之间必然也会发生摩擦冲突。作为领导,面对这种情况,本应积极协调处理,书记却听从唐主任的建议,玩弄政治手腕,最终竟然酿成一死多伤的大祸,原想渔翁得利,却不料差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至于与“我”二心的人,像王后生等人,无论“我”用每个月送“他”几百元的利益诱惑,还是把镇政府变成渣滓洞③严刑威逼,“他”上访的心始终如死般坚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捍卫开发时代赋予自己的当家做主的权力,批判和控诉樱镇领导剥夺底层人民权利的强权。这种强权不但无视底层人民的呼声,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结果防洪工程把洪水堵到街道和村庄,淹了许多房子,死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大工厂还没建成,镇东街和镇西街两个大户产生群殴悲剧。最让人心悸的是,为了自保,书记伙同幕僚们采用金蝉脱壳之术,把责任推到忠于职守的两个下属身上,把带灯和竹子这两位维稳工作者,一个变成上访材料,一个变成上访材料的整理者。在樱镇演出了一场逆天惊人的大悲剧。它无情的控诉了樱镇当权者唯“我”独尊,以“我”排“他”的霸道行径,必然将樱镇再次引入退回到万众一心,只有“大我”。没有“小我”的人生暗夜。
《带灯》的目的,就是要划破黑暗,带来光明。它超越了经典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在批判之外,更展现希望。作品用大量的生活细节,向读者展示了被开发出来的个体自我,不满足独立,更追求相互尊重,互相承认。樱镇底层的生存者之所以要求承认和尊重,是因为樱镇传染着一种开发的时代病。独立的人还没有获得自由,还不能摆脱自己与自身位置的直接关系,还不能从容地站在“他人”的位置来看待、处理“我”与“他人”的关系。每一个“我”知道从“我们”中把“我”开发出来,让“我”独立有多么重要,都诅咒开放开发之前用“我们”遮蔽“我”,用“大我”挤压“小我”,把人生引向浪漫的“无我”之夜,让“我”无法割断与“大我”的脐带,无法摆脱对“大我”的依赖,是逼“我”在“为他”的崇高乌托邦中混沌一生,被奴役一生。开发时代,“我”从“我们”中分裂出来了,摆脱了“大我”的压迫,堂堂正正地做“我”了。然而,独立仅仅是当家做主的第一步,要真正当家作主,还必须自由。一个独立而不自由的人,往往会沾染用“我”代表“他人”,挤压“他人”的自我中心病。习惯于从本位出发观察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习惯于从本位出发要求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习惯于用“我”作尺子衡量“他人”,符合尺度的,是和“我”一样的人,“我”是“他”的代表,有“我”可以无“他”。不符合尺度的,和“我”不一样,“我”是人,“他”是非人,有“我”不能有“他”,“我”必须把“他”整垮。自我中心主义者习惯于把自己固定在特定的身份地位中,不能也不愿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拉开距离,外位于自身自由的观察天地自然,思考社会人生。所以,不能发展变化自己,这个“我”受到自身位置的限制,从生活的惯性出发,不能自由的做人,也不能包容和理解与“我”不同的“他人”,不愿承认“他人”做人的资格。受限制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整天面对人群,却总是无视“他人”,不想忍受与“他人”平等交往的各种烦恼,一心要享受唯我独尊的荣光。但是,社会是由“你”“我”“他”等众人组成的,众多“他人”不会因为自我中心者闭目塞听而消逝,自我中心主义者也需要在社会人群中做人,也必然要遭遇各种“他人”。“我”若不把“他人”当人,“他人”也不会认可“我”。互不认可的人相遇,要么互为敌人,要么互为路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就会产生悲剧冲突,后一种情况下必然形成相互隔膜。
带灯是一个能自觉摆脱生存惯性,自由生存发展的人。她在给元天亮的信中说:“我不想让某种生活方式成为生存惯性的,因为我要能随时地跳出来。”④惯性是惰性,在惯性中生存的人,没有自由。因此,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性,也不能真正的理解包容“他人”。职责要求他认真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加大防范打击整治力度,有效遏制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用竹子的话说,综治办是丑恶问题的集中营,整天跟带有各类丑恶问题的人打交道,真烦人。烦人的事领导都躲,干部都避。县信访局遇到上访者,就打电话通知各乡镇领导人;樱镇主要领导叮嘱门房堵截上访者,凡遇见上访者进镇政府大门就去门房问责。东沟村办公室门口写着:有困难找党员,有问题找支部。群众真正有了问题要解决,村干部就会推脱说,谁屙的谁擦。躲避不过推脱不掉的,就睁眉火眼,抡拳舞棒,与上访者不共戴天地干。带灯从不推卸责任,总是积极解决群众遇到的各类问题,群众称他是活菩萨。作为综治办主任,经常遇到自身职能与群众利益冲突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她绝不只是死板的从原则出发,僵化地按原则办事,而是尽量把政府的原则与群众利益兼顾起来,在原则里融入执行者的人性,让群众感受到政府的温暖。有时为了执行特殊的综合治理任务,不得不做一些对得起自身工作,却有可能伤害群众利益的事,事后她也会反省。比如为了让市委黄书记视察不受干扰,她教曹老八设牌局,诱使几位上访者赌钱,然后叫派出所警员去赌场抓现行。事后,她头脑十分清楚,知道人不可能时时自主自由,有时不得不像“做车子的人盼别人富贵,做刀子的人盼别人伤害,这不是爱憎问题,是技术本身的要求。”⑤
带灯自由自主做人的首要标志是,能够坚持群众立场,心存为底层群众排忧解难的服务意识。身为乡干部,却不拿自己的干部身份与乡民进行区隔,更不拿它吓唬乡民。把每一个村庄都当成自己的家乡,把每一位村民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她很享受一次次走村串乡,当它是一次次离家、回家,与亲人离别、重逢的过程。面对乡下的这些亲人,她从不空喊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寻问和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十三户农民在大矿区打工感染矽肺病,丧失了劳动力,生存遇到困难,她主动带领他们的家属,多方联系,想方设法忍辱负重解决他们的赔偿问题。冒着被领导批评的风险,领着十三个妇女到外乡找零活,解决他们生活中的燃眉之急。为了解除底层民众的病苦,她向陈大夫学医术,要用山里的奇苦之草,治疗山民的苦病。王后生经常上访,在许多镇干部眼中,就是眼中钉肉中刺,是阶级敌人,巴不得他早点从樱镇消失。带灯发现他糖尿病严重,依然给他开处方,要为他除病去痛。
带灯自由做人的第二个标志是,心存善念,爱做善事,经常善待“他人”。她与乡民接触,遇到家境可怜生活难以为继的,就尽力给予困难补助。遇到喜欢给“他人”挑刺,动辄上访闹事的,就用善心感染他,用善举打动他。她要让底层受苦人活得有尊严,让刺儿头逐渐变得和善。她喜欢大自然,常通过树木的成长获得做人的灵感。她的笔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一辈子去做自己转化的人吧,把虫子转化成蝶,把种子转化成大树。”⑥她一方面不断用善心、善行转化自己,让自己人格得到升华。另一方面,用善心感化他人,让他人不断变善。宋飞偷取仓库的炸药,把樱镇的所有领导惊出了一身冷汗,镇书记见他就用脚踹,马副镇长要求带灯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惩罚他。带灯见宋飞衣衫破烂,便送救济衣让他穿,不忍心他饥渴,送方便面给他吃,送矿泉水给他喝,感动得他答应以后决不再来樱镇搞破坏。善心就是包容心,带灯从“树能包容鸟”,⑦领悟到“我”能包容与“我”不同的人。她是镇政府干部,却在乡下村妇中结交了几十个老伙计;自己爱干净,却能理解身上爬满虱子的乡民;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截访、堵访,却能够体谅上访者的苦楚和辛酸;自己为人大方,却能够理解那些为了蝇头小利争执不休的人的可怜。在她看来,“你”“我”“他”有差别,却都是人,只有在人群中相互理解平等共生,每个人才能表现出端庄健康的人性,才能成就“你”“我”“他”独特的人生。一人独大,不受限制,他就会孤家寡人,唯“我”独尊,目中没有“他人”。就会生邪心,干斜事,把“他人”当非人排挤打压,让“他人”无法做人。假如“你”“我”“他”享有平等权利,就会相互认可,互相尊重。为“我”独尊的霸权者消失了,而千万个平等的主人则诞生了。
《带灯》告诉我们,人应该活的有尊严,“你”“我”“他”应该建立正确的伦理规范。每一个有尊严的“我”,既不需要上帝的启示,也不需要权威的引导,自己就能够辨别美丑善恶。“解放思想”的深意,就是要解放套在“你”“我”“他”身上的所有外在枷锁,只认同人性“自我”的价值伦理。而怀疑人性自主精神,放逐人性伦理规范,必然造成道德上的混乱。“我”如果既摆脱权威的指引,又抛开良知的呼唤,一味向外追求实惠,对己满足物欲,必然导致价值失序,道德沦陷。这是今日基层社会矛盾重重的深层伦理—社会动因。
正确的人性伦理规范只能由理性的“我”构成。理性的“我”是评判辨别善恶是非的唯一合法标尺。开放时代伦理思想的基本诉求,是要把人性的“我”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伦理。不理解人性伦理的本质,就不能理解“我”与“他人”的价值冲突,更不可能理解和包容“我”与“他人”在社会交往中的矛盾。开放时代精神领域的进步,并不在于要放逐集体式的“大我”,而在于让开发出来的“小我”传承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伟大传统,即从人的生存整体(物质—精神)上把握人,相信人是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为我”的人与“为他”的人彼此让渡、相互转化。人要实现自我,就必须首先做“为我”的人;人要完成自我,还要持续做“为他”的人。健全社会的伦理规范,应当在人性自我中反身叩求;和谐社会稳固的价值位序,以“你”“我”“他”完善的人格结构为基础。“你”“我”“他”人性成熟了,道德就健全了;人格健全了,社会就安稳了。“你”“我”“他”人性缺失了,道德就会沦丧;人格片面了,价值就会失序,进而造成人心不安,社会混乱。开放时代伦理道德的最高价值不是“自我”,也不是“他人”,而是像小说主人公带灯那样,“我”与“他人”彼此尊重与相互建构。这是樱镇的新生和希望,也是我们时代的新生和希望。
注释:
①②③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22、225、308、309页。
④⑤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202、262页。
⑥⑦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04、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