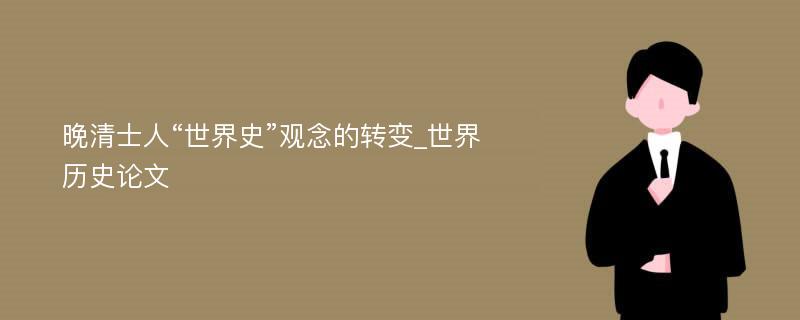
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学人论文,世界历史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历史”观念起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注:关于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可参见陈新:《论西方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观念》(《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5期)、《论西方近代的“世界历史”观念》(《学海》2001年第4期);叶险明:《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等文章;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正如时人所说:五洲未通以前,中国“极东孤立,庞然自大……并不知有亚洲,遑问世界?故世界史之著,亘古无闻焉”[1]。19世纪中叶起,中西碰撞日益加深,晚清学人逐渐关注外部世界,开始以传统史学的国别体撰写外国史;至20世纪初,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经由日本明治时代的万国史译著中转传入,深刻影响了晚清学人对这一概念的接纳和理解。就我所见,学界的相关讨论仅有:路则权的《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8期),林正珍的《世界史理念的建构及其相关论述》(《兴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9期)、《世界史视野的拓展与当代中国史学》(《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喜玛拉雅基金会2002年)等文章,而晚清学人接纳这一概念的整体过程及其所反映的史学体例变化、时人对“他者及自我”的认识与定位等等问题,并未见到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尝试在此层面上考察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
一
自从司马迁创设纪传体,成匈奴、西南夷诸传,历代正史都以“外国传”或“异域志”记载中央王朝以外的地区。起初,其立意甚好,“备远徼、筹边防,不可不讲之于平日”。但积久生弊,史家逐渐疏于世变,不屑悉心考核朔方异族。外史记载不仅统称之以“夷狄”,充满了自尊自大的意味,而且粗陋简略,道听途说、袭谬承讹之处甚多。王韬曾直斥昔日史官之陋:
欧罗巴列邦于明万历年间已来中国立埠通商……逮明史作传犹不能明法兰西之所在,几视与南洋诸岛国等是。其于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尚未寓目,况其他哉?宜其为远人所致诮也。[2](P3)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秩序日益受到西方的侵蚀,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世界史地著述以《海国图志》(1842年50卷本,1852年增至百卷)、《海国四说》(1846年)、《瀛寰志略》(1848年)等最具代表性。它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体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注:关于“国别体”体例与“封建”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史家重野安绎和晚清学者刘师培都曾谈到。重野安绎说:“史有数体而国别居其一。国别者,昉于《春秋外传》而终于《九州春秋》。盖自封建废,史统于一,于是编年、纪传盛行,而国别之体替已,魏晋以后是也。”参见重野安绎《万国史记·序》,见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又名《万国钢鉴易知录》),上海书局1902年夏。刘师培写道:“《左传》家者,列国史之祖也;《国语》家者,国别史之祖也……及封建既废,天下统一于一尊,断代之史兴而国别之史废矣,惟司马彪《九州春秋》,稍师国别史之成法,然范围甚狭,不过地方之志案已而。”参见刘师培《万国历史汇编·序》,见江子云等编《万国历史汇编》,上海官书局石印1903年。)尽可能详细地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史学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正是据此,刘师培称其为“中国之新史学”:“中儒著西史者,如徐氏《瀛寰志略》、魏氏《海国图志》,一改历代四裔传之例,以开国别史之先声,不可谓非中国之新史学也。”[3]
不过,上述诸书虽然遵循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重新发掘出“封建”时代的国别体,并且在空间范围上有所扩展,但是仍有两点局限值得注意。第一,它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日本史家重野安绎曾以此评估时人见识:“彼国虽大,而不过方数万里。寝处乎方数万里之内,目不接海波,而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以海国,而自称曰中土,是童观耳!井蛙之见耳!默深以达识著称,犹拘于素习而不自察,则其他可知已。”[4](重野安绎《序》)第二,王晴佳认为魏、徐等人的著述不把中国包括在内,是一种“洋外史”,表现出一种“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态,因而与日本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有重要不同。[5](p205~206)
《万国史记》初版于1879年,是近代日本较早受西方史学影响的世界通史性著作。一方面,它不仅发展了传统儒学的“国别体”,按地区、国别分别记述了几十个国家的历史沿革、风俗民情,而且将日本置于万国之中,表明日本与世界的联系。“日本记”开篇即言:“我国史乘甚备,不必赘言。然既题曰万国,则不得自异,提纲摭要,所以成公,看者亮之。”《万国史记》卷一的目次、内容如下:万国总说、亚细亚总记、日本记、日本记附录。“万国总说”综括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亚细亚总说”阐明亚洲历史现状,“昔时文物制度卓绝五洲,今则瞠然在欧罗巴之后”;“日本记”剖析国史短长;“日本记附录”译自西籍,虽“未免误谬,然亦未尝无反观之益也”。[4](p1~15)很明显,冈本监辅将日本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中,试图客观评价其传统的意义与不足。
另一方面,冈本监辅及其友人冈千仞已经受到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某些影响。在撰写每一卷,即各地区、各国历史时,冈本监辅没有使用传统的纪、传、表、志等形式,而是借鉴西洋史的综合叙述体,分上古、中古、近古三期叙事。冈千仞的序文专门讨论了西史分称三古的重要性,他说:“西史……分称三古,明古今明暗之别也……而东洋国俗,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辄曰风俗不古……东西两洋,明暗智愚,判然相殊,岂不以是故乎?”[4](冈千仞《序》)
上海申报馆最早翻刻《万国史记》,于1880年3月发售。(注:据光绪庚辰二月二十日(1880年3月30日)《申报》第一版头条“印售万国史记”的“本馆告白”。另,以国家图书馆的申报馆藏本推测,《万国史记》应印刷多次。)驻日外交人员何如璋、黄遵宪、曾经访日的王韬等与冈本监辅相识,也大约在这前后读到此书。不过,冈本监辅所受到的西方史学影响似乎并未引起他们的注意,如黄遵宪1880年发表对《万国史记》的看法:
余恨其无《志》、无《表》,不足考治乱兴衰之大者。……余从前亦欲作此书,自草条例,凡为《列国传》三十卷。为志十二:曰天文……为表十七:曰年表…曰铁道表。顾以其书浩博……卒未成书。[6](p154)
宋恕1887年在上海见到《万国史记》(注:宋恕(1862~1910)26岁(1887年)到上海时,“始见彼土书三种,则冈鹿门氏之《尊攘纪事》、《观光纪游》、冈本子博氏之《万国史记》是也。其后客南北,锐意求彼土书,所见日多……然弗敢忘冈氏、冈本氏之最先引我入胜也”。参见宋恕《亲灯余录·序》,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294页。),到1895年完稿《六字课斋津谈》时,仍然写到:
日本冈本子博撰《万国史记》,冠日本于万国之上,自以至公,然其体例实未为得。盖学者习史,外国不能不略,本国不可不详;若撰史者平列本国于外国,取齐篇帙,势不能详……或问:子撰外史,体例、题名若何?曰:体例仍魏、徐氏,而题曰外国史略,则正名言顺。[7](p63)
从以上对《万国史记》的评论可以看出,黄遵宪仍以传统纪传体的“志”、“表”等体例考求“治乱兴衰”,力求将各专史纳入列国传,不免陷入繁难之中;宋恕明确反对“撰史者平列本国与外国”,认为国史应另为一编,只作“外国史略”。王韬也基本持同样看法,他称赞冈本监辅游历广泛,博闻多识,“著有万国史略,搜罗颇广,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注:王韬所说的“万国史略”即为《万国史记》。王韬《扶桑游记》,明治庚辰年。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1974年,第130页。)他们都将《万国史记》看成是有关“列国史”或“泰西史”的掌故汇编,不曾注意到冈本监辅将本国史置于万国史之中,以“三古”分期强调进步,以“审万国形势”较“国史短长”的目的。
在甲午战前应对西方挑战的五十年间,清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始终是西方科学技艺,外史编译未成风气。虽然中西碰撞已经促使史家以国别体写作外国传,并且产生了诸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年完稿,但1895年才得以刊行)、王韬的《重订法国志略》(1890年刊行)等更为详实的外史著作,但是晚清学人尚不曾意识到世界历史的意义,还未能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其有限的外国历史知识,也不足以对人类历史进行整体性的观察。正如时人所叹“吾国数十年前局于闭关锁国之思想者,以为吾国以外无世界,即有人类亦等夷狄或如匈奴、突厥、回纥,故甲午以前,密迩东邻之日本犹未能察其国情,遑言其他世界各国哉”[8]。
二
甲午战败震醒了中国人天下之“中土”的长梦。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据谭汝谦统计,仅日文汉译世界史地著作在1896~1911年间就达到了175种,而1660~1895年间只有2种。(注: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表十一。据笔者所见,仍有部分日文汉译外国史地著作未收入,因而实际数目当不止于此。)随着留日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经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文本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由于西方理论学说,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说,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碰撞时,大都发生某些转变,因此,探究清末学人的“世界历史”观念,有必要首先考察明治日本人对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理解。
通过对基佐和博克尔“文明史”的研究,福泽渝吉是明治时代较早认同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中进步论、阶段论的启蒙学者之一。他在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写道:文明是“人类智德的进步”,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从野蛮到半开化、开化,现在的欧洲文明,是目前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其他仍然处于野蛮状态或半开化地位的国家,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但是,他坚决反对大多数西方史家坚持“西方文明永恒代表最高文明”的观点,认为:文明的发展又是无止境的,虽然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却并非尽善尽美,所以日本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9](p10~11,33)
至19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史学译著的大量出现和史学观念、方法的输入,有关世界史概念的阐述以及编纂学的实践,与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相比,都有明显的进步。较有代表性的两家同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的教员,一是经济学家、业余史家天野为之,二是历史学讲师松平康国。
天野为之的《万国通史》于1887年出版。它虽以“万国”为名,但“所载仅西方诸国,如朝鲜、支那、日本及其他东方之国,概不及焉”。对于为何“以西洋史为世界史”,天野为之解释说:万国史有两种,一种“普记万国,无所抉择”;另一种“总挈万国之大事,发明世界之全体”,“一国之形势虽具,征之世界之全体而不见其轻重”,则不予录之。他按后一种方式写作万国史,不得不放弃东方国家的历史。对比东西方文明,他不禁感慨叹息:
今夫欧洲诸国,其文明景象,实能周及寰瀛而发扬政治之进步者也。悲夫!东方之声教,东方之人民,其于世界之大,曾无毫末之关系,奈何于万国史中空留其名?……夫余岂不愿万国史中,赫然存日本之名,使日本之人为世间绝有关系之人,而余亦得取东方之事迹而详说之?虽然,此俟之一日千秋之想耳!嗟乎!此嘉运之固未至也。[10]
对比天野为之的类似“强势文明即为入万国史之资格”的简略理解,专业史家松平康国的阐述更加接近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之真意。在其讲义《世界近世史》中,他写道:
世界史者,视世界为一国,视人类为一族者也。考邦国如何成立,如何迁移,如何进化;考家族如何冲突,如何结合,如何而有性智,如何而营生活,如何而为归宿之方向,此世界史之本分也。先条举关系于世界全局之大事,然后于大事与大事之间,贯之以自然之法则,择一最当之体裁,然后可称为史之良也。但求得此自然之法则,属于历史哲学,而世界史之所叙述,即循此法则以为基础也。[11](绪论,p1)
松平康国注意到世界史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世界史关注人类整体的发展历程及其命运归宿,具有某种方向性;而此种方向性是由历史哲学求得的“自然法则”所规定的。因此,世界史的叙述,就要以此“自然法则”贯穿各种关系“世界全局之大事”,目的在于“泛识宇宙之大势,遍征人类之命运”,即指明人类发展的“理性大方向”。
近代西方探求此“自然法则”的最成熟理论由康德和黑格尔完成。康德假设人类历史是一个实践着大自然的隐蔽计划的总体,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形成一部完美的国家宪法,这部宪法将体现正义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以及天赋人权,撰写世界历史的线索就是描述这项大自然计划的展开与完成。康德意识到,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存在,虽然是人们以某种预想为线索进行撰述的结果,但有它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反之,如果我们不假定有一种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不用编撰世界历史的方式认识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并将它们概括成合目的的、合理的历史过程,我们就只能走向绝望[12](p15~21)。
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人类历史的合目的说,将其从康德的“一部完美的国家宪法”抽象到“精神”的领域。(注:英译者约翰·西布利曾经这样解释“精神”:“精神”的真髓在于自决,或者称为“自由”。在“精神”已经达到成熟的生长的时候,当一个人承认“良心”的制裁为绝对合法的时候,“个人”对于他自己便是法律,这种“自由”也便算是实现了。但是在道德和文明的较低阶段里面,他不知不觉地使这个立法原则成为“统治权”(一个的或数个的),服从它好像一个外界的外来的力量,而不像服从它自己(在这阶段虽然不完全)所混为一体的那种精神的声音。“历史哲学”揭示了他达到自觉的各个阶段,所谓自觉就是统治他的自己的最深的存在--也就是自决或者“自由”的一种觉悟。参加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注1。)他说: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即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世界历史所必需记载的,乃是各民族精神的行为。黑格尔将“自由的意识”视为世界历史的核心和最后目的,并以此衡量各民族、各国家以往和现在的历史在世界历史行程中的位置:没有自由意识的民族是非历史的民族,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各个民族、国家无论存在多大差异,最终都将被世界历史所统一,走到“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13](p1~117)
由于预设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无论是康德的“一部完美的国家宪法”还是黑格尔的“自由意识”,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具有了某种现代性的理想色彩。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本质的思考和人类未来的规划,对于“自由意识”的执著,成为近二百年西方变革的精神源泉。陈乐民先生谈到黑格尔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曾给他以莫大的启示:它无宁是“了解欧洲”的一把钥匙,而且可以从欧洲看到世界的前景,“欧洲的精神”或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14]。
不可否认,康德和黑格尔所求得的“自然法则”落实到世界历史编纂学,曾经诞生了风行十九世纪的单线进步的“普遍历史”和“欧洲中心论”。松平康国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不过,他认为此乃目前的历史事实:
舟车万里,广邦国之交际、原人类之关系者,西洋人为多焉;与异种之民族互相摩荡,互相激发,速世运之进化者,西洋人为多焉;学术技艺,致人生之幸福者,西洋人为多焉;政体法制,逐渐改良,循至于公理者,西洋人为多焉;干戈玉帛之利害,及于域外者,西洋人为多焉。虽以土地之广、人民之众论之,彼西洋人固未足以掩有世界也。若夫以实力摇撼地球,牵动来叶,则近世中孰有如西洋者乎?故历史家之以欧洲为世界史之主者,非于感情上主之,乃于事实上主之。[11](绪论,p2)
如果回顾世界文明从东方到希腊、罗马而至欧洲的盛衰转移过程,他认为世界史之中心未必不能移于东方:
夫世界文化发源于亚洲,横流于希腊,注入于罗马,泛滥于欧洲,今也激浪怒涛之势,复回向于东方,将来取西洋之文化,与东方旧时之文化相合,自成一种新文明,二十世纪之历史,其洋洋大观乎?虽然,今时机未至,犹未能以东方为世界史之中心也。读此书者,其奈之何哉
显然,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并非如西方某些史家所坚持的“西方文明永恒代表最高文明”。他们的看法既是自省的,也是自信的: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
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注:大多数学者都以1894年作为东洋史的开端,这一年那珂通世提议中学课程的世界史分为西方史和东方史。两年后,教育部采纳了这种划分。东洋史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东洋史的开拓者白鸟库吉写道:“回顾明治早期的历史,我国诚挚地模仿西方国家,迅速地输入它们的文化,却没有充足的时间消化?甚至历史课程也直接使用西方国家编写的课本。尽管这些书的名字是‘世界史’或‘全球史’,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欧洲国家兴衰史,东亚的事件完全被忽视。我们学校曾经使用过的课本,如威廉·斯顿(William Swinton)的《世界史纲》,都声称非白种人没有真正的历史。毫无疑问,这严重误导了我们的国民。”[15](p48)田中(Stefan Tanaka)曾分析白鸟库吉有关东洋史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他说:“东洋史作为整体历史的另一半被建构,与西洋史相对。它不只是要描述亚洲的事件和人民,正如白鸟的不满所表明的,东洋史的重要性也是意识形态的:它蕴含着日本的表现和理解。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能够展现日本也有‘真正的历史’”,而且“精确的东洋史叙述能够将日本从西方的阴影中解脱出来”。[15](p49)
王屏阐明了近代日本赋予“东洋”一词特殊含义的目的。他认为:作为日本在世界史或国际关系格局中的自我定位,“东洋”概念有两种性质。当面对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时,即“东洋”外指时,日本被包括在东洋之内,强调东洋的一致性,从而对抗西方;但当“东洋”内指时,即在东洋内部,日本却把自己排除在外,强调“日本=文明=西洋、中国=野蛮=东洋”,这时的“东洋”专指中国,“汉学”研究也变成了“东洋史”研究,日本从“远东”一员变成了“远西”一员,即所谓西方“文明世界”的一员。由此,日本对中国、朝鲜的扩张与干涉就可以在“文明”的名义下进行并在理论上得以正当化。这样,通过“东洋史”的构建,近代日本企图在亚洲及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中为自己重新定位,由此所产生的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及其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也规定了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16]
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和大批留学生赴日之时,适值日本上述诸种“世界历史”观念并存、而“东洋史学”悄然兴盛的时期。晚清学人在接触上述观念时,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反应?
清末舆论的重要人物梁启超表现出非常戏剧性的变化。1899年,梁启超在《文野三界之别》中,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与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中的进步论、阶段论联系起来,即野蛮、半开化、文明三阶段,提出了“我国民试一反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兴矣”的问题。[17](p9)1901年和1902年2月,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他认为:从过去、现在的历史来看,只有泰西民族“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所以“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然“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但那乃是“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18](《中国史叙论》,p2),而“世界史的人种”,必须具备“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的条件,以往世界史中能当此名者,“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识者同认也”。[18](《新史学》,p15)
郑匡民的研究表明了梁启超“世界历史”观念与日本启蒙学者福泽渝吉之间的深厚渊源。他认为:梁启超受到福泽渝吉的影响后,“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他开始拿起‘文明’这个尺子去衡量中国在文明进程中的位置”。梁启超的视点开始由戊戌时期“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的世界主义理想向“一国之存亡”转移,国家观念初步形成。[19](p65)
“文明三段论”和“世界史以泰西民族为中心点”的西方“世界历史”观念使福泽渝吉和梁启超认为“落后就要挨打”,并将后进民族被压制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其本身文明的落后。诚然,此种理论客观上使殖民扩张获得合法性依据,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为客观评价“自身”与“他者”提供了平台,促使二者更加关注国民“智、德”的进步。但是,不久之后,梁启超在《东籍月旦》(大约1902年5月~7月间发表)中,推翻前述观点,开始强烈谴责“以欧洲史为世界史”的做法:
日本人所谓世界史、万国史者,实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种族兴废存亡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无可以厕入于世界史中之价值。此在日本或犹可言,若吾中国,则安能忍此也?近年以来,知其谬者渐多,大率别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其真可称为世界史者,惟有最新出之一种:世界史上卷,坂本健一编……此书东洋西洋合编……冠绝此类同名之群著者矣。[18](《东籍月旦》,p91~93)
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梁启超发生实质性转向?他曾经谈道:日本人知道“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谬误,乃是近年以来的事,所以“别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于是,只有“东洋西洋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可以设想,梁启超最先读到的可能是福泽渝吉、天野为之、松平康国等人的著作,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了新的潮流,并且这一新版本的“世界历史”观念与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强烈的反侵略意识又非常合拍,(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基督教世界中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由一个文化圈内亚文化集团的竞争精神和危机感激发的,而中国从未在文化上感到低人一等,即使在军事上弱于那些“化外之民”,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天朝上国”而非亚文化集团做出回应,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文化中心主义”。参见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04~205页。)所以很容易就彻底改变观点,提出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最早批驳。与他的观点类似,留日学生团体湖北法政编辑社受日本文学士野村浩一的影响,也明确谈到“世界史名目应包东西洋而言,不宜隶入西洋史一部分”。[20](p2)
清末学人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批驳,除了梁启超的“东、西洋合编”说之外,还有一种是将世界历史看作“关系之历史”。由于东、西洋长期隔绝,发生联系的时间甚短,所以简单合编东、西洋史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史,目前还没有可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史。此种观点同样来自日本的东洋史学家。如王国维1898年起受教于东文学社,在日本教习藤田丰八的指导下,强调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和“系统”,认为“世界史者,述世界诸国历史上互相关系之事实。……古来西洋各国,自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今日西洋之文化;我东洋诸国亦白为一历史团体,以为东方数千年来固有之文化。至二者相受相拒、有密接之关系,不过最近事耳。故欲为完全之世界史,今日尚不能”[21]。汪荣宝以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为蓝本,综合浮田和民、久米邦武等人的著述,撰成《史学概论》。尽管他对“以欧洲史为世界史”表示理解,“是亦非有私于西洋,彼其境遇与实力足以左右世界之大势”,但也特别提出“自有始以来,人类之历史……不相关联”。“其万国交通,东西密接者,近百年来之事实耳。故于今日史学之程度,尚不足以为真成之世界史”。[22](p71)
二十世纪初,尽管明治初期“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书籍在中国流传很广,如天野为之的《万国通史》由吴启孙翻译,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松平康国的《世界近世史》更是出现商务、广智书局等多个译本。另外,也有持此相近观点的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万国史》。(注:服部宇之吉虽然也认为万国史是“国与国关系之历史”,但是他强调以“今日包涵世界文明诸国之大团体”形成为起点,进行回溯性的研究,即“研究此结合之团体,其始原于何时何地及如何事情,其后经如何变迁,至进今日之状况,是即万国史之宗旨”。这样的叙事结构实际必然以西洋史为中心。因笔者所见服部在京师大学堂的《万国史讲义》并不完整,故而尚不能尽窥其教学思想。服部宇之吉《京师大学堂万国史讲义》,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不过,他们的看法,即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应采取西洋史为世界史的编纂形式,未能在清末中国占据主流。明治中后期逐渐兴起的“东洋史学”影响更为深远,大量东洋史著作,如石村贞一的《东洋新史揽要》、小川银次郎的《东洋史要》、幸田成友的《东洋历史》、桑原骘藏的《东亚史课本》、市村瓒次郎《东洋史要》等输入中国,并且成为清末学堂教育的课本。虽然中国人未必认同东洋史为共同体,但以此反对“欧洲中心说”是确定无疑的,甚至直接影响民初学者的看法。曾经留日的王桐龄在《新著东洋史》中写道:“……世界史又分为二部:一东洋史……二西洋史。……西洋史学家,动谓西洋史为世界史,其说非也。……亚东民族,在历史上,绰有价值。欧人一笔抹杀之,大不可也。”“然则合东洋西洋各民族之历史,组织成一世界史可乎?曰:不可。世界史者,研究全世界国与国之关系者也。东洋各国,孤立东亚,与西洋各国关系绝少,或竟绝无焉,欲合一炉而陶铸之,恐无水乳交融之望也。”[23](p3~4)这样,曾经被梁启超称作近代日本惟一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著作——坂(阪)本健一的《世界史》受到了王桐龄的否定。
大致而言,无论是梁启超将世界历史视为“东西洋史的合编”,还是如王国维、王桐龄等人的东西洋史两部划分、进而否定现阶段世界历史的存在等看法,都未曾意识到东洋史的建构对于近代日本的意识形态意义。他们在东洋史中所见,乃是中华民族占据大部分历史,甚至将中华民族之地位自比为“世界史中阿利安民族之地位”,“日本近来著东洋史者,日增月盛,实则中国史之异名耳”。[18](《中国史叙论》,p2)
“世界历史”观念不仅关系着该国民如何认识“他者”,还关系着如何认识自己的过去,并且与该国民当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来的方向密切相关。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入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更为重要的是,晚清学人关于世界历史编纂体裁的诸多辩论,大都流于形式,而对于松平康国所留意到的世界史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贯穿世界史的“自然法则”,始终未见深入分析,这不能不影响着国人的自我认识及其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梁启超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