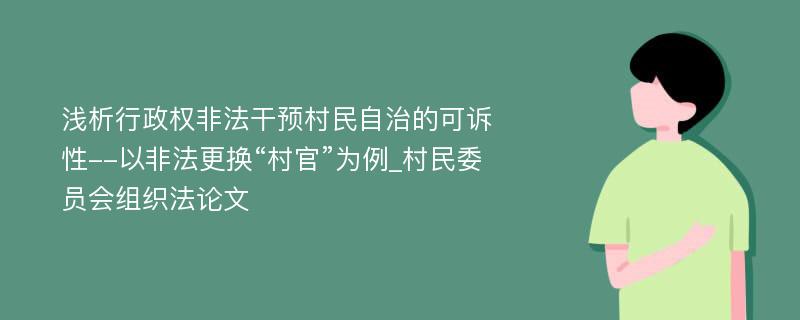
行政权非法干预村民自治权的可诉性分析——以非法撤换“村官”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治权论文,行政权论文,村官论文,为例论文,村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村民自治的行政干预
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的起点,也是解决困惑中国已久的“三农”问题的制度化出路。村民自治是否能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直接关系着中国农村的稳定和繁荣。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中国农村自治的基本形式——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罢免——却存在着种种问题。即便是合法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也得不到基层政府的尊重,例如有的基层组织不是依法组织村民罢免村委会干部,而是直接用行政命令撤换。据报道,在全国村民自治先进市——湖北省潜江市,自第四届村委会换届以来,被乡镇党委、政府非法撤换的村委会干部达619人,涉及269个村,占全市的82%,其中187个村的村主任被非法撤换,超过总数的一半。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违法干预,本来已十分艰难的村民自治势必将陷入困境。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村民自治必须是法治之下的自治,“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法治之必然结果。有规则而无完善的司法救济并不能够成就法治,所以必须让司法殿堂的阳光普照到权利存在的每一个角落。在目前的村民自治运行中,部分由于司法救济的缺失,国家在面对村民的权利诉求时显得有点捉襟见肘。由于权利受到侵犯时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权利的享有就成了纸面上的摆设,同时这也意味着权利侵害者事实上不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只有扩大现行司法救济的范围,才能真正体现“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适当的司法审查制度,将村民自治纳入行政诉讼的轨道。只有允许村民在法院直接挑战违法的地方干预,他们的合法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尽管中央还权于基层社区,但是中国下放的权力经常被乡镇基层政府截留,因为乡镇基层政府不甘于退出乡村社区,千方百计地扩展自己在村一级的权力触角。虽然法律规定了乡镇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没有具体规定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且诉讼渠道不畅通,缺少司法救济,从而使一些乡镇政府“替村民做主”,越权决定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这实际上是违法干涉村民自治事务,严重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乡镇政府非法撤换“村官”的行为。本文以此为例,分析乡镇政府干涉自治事务行为的可诉性。
行政诉讼:村民自治不可或缺的法治保障
村民自治中一个极具意义的重要举措是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当家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这条规定让村民们自主选择当家人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然而,在现实中,这项规定的实施并不总是那么有效。对于经常把村委会当作自己腿脚的乡镇政府来说,村委会组成人员的人选也是他们异常关心的人事。在此问题上,乡镇政府并不甘于作一个单纯的旁观者,而是要运用手中的权力在村委会的人选上体现他们的意愿,于是就出现了“村官”被乡镇政府免去职务的现象。村委会成员被撤换的问题不仅关系到被撤换者本身的权益,而且还关系到村民是否能正常行使民主自治权。
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显然超出了合法的权限范围,侵入了村民自治权的领地。为了保障自治权的有效行使,只在法律上确认其权限还远远不够;权限范围有了合法依据,司法救济便不可缺少,否则只能徒有虚名,权利的享有也就会有始无终。现实中就常常出现权利受到侵犯,可是受害者却处于告状无门的无助境地。以下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2年8月22日,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经大石窝镇镇政府研究决定,停止镇惠南庄村的村委会主任王华的工作,停发工资,并让他交出村委会的所有手续和任职证书。王华向镇政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是老百姓选的,应该由老百姓来罢免我们,你们没有这个权力。”虽然王华拒绝接受镇里的决定,不答应交出村委会的权力,但他还是被逐出了村委会。镇里重新调整了村里的班子,村委会的工作由镇里委派的其他人全权代理。镇里说,王华上任后很不称职,不仅没有为老百姓办什么实事,而且还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其中乱砍滥伐就是问题之一。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电费管理混乱,造成了10万多元的亏损。另外,王华还有越权审批宅基地以及与党支部不团结等问题。而王华却认为,这是镇里为撤他而找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工作方法不适合镇领导的胃口。
2003年1月,王华以大石窝镇党委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3个月后,房山区人民法院认为,只有人身权和财产权被侵犯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民主自治权利受到侵犯不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因此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王华又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但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村民自治权利的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驳回了上诉,维持了一审裁定。
在此案中,王华的法定权利显然被非法剥夺了,可是却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司法救济的缺失助长了乡镇政府的违法行为,使之无视国家法律的权威。长此下去,对于村民自治的前景将贻害无穷。既然存在一种权利,并且权利又被非法侵犯了,权利人必将寻求一种力量来恢复受侵犯的权利。在法治国家中,司法救济应当是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
乡镇政府罢免村官显然是一种不具合法授权的行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6条的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委会成员。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可见,只有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才能罢免村委会成员,乡镇政府的行为,实质上体现了行政权对自治权的侵犯。如果纳入到司法救济当中,目前的诉讼模式下,最适合的诉讼模式便是行政诉讼,因为在此种情形下,乡镇政府的罢免行为属于一种行使行政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该行为侵犯的自治权的享有主体是全体村民。因此,作为行政诉讼的适格原告的应当是全体村民。如果全体村民要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可以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并推选代表以全体村民的名义进行诉讼;如果村民会议讨论结果对于提起诉讼达不成一致意见,应当允许村民个人提起诉讼。这种诉讼类似于公益诉讼制度,即允许村民个人出于维护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考虑而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对于被罢免者本人来说,乡镇政府的违法行为还侵犯了其合法履行职责的权利,因而他仍然应当获得诉讼资格,而且这类诉讼最适宜的也仍然是行政诉讼。理论上说,只要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获得司法救济,但是由于中国行政诉讼法目前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制,只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样就将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权利救济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大门之外,村民自治权便是其中一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局限性,使得乡镇政府插手村民自治事务,干涉村民自治权行使,而受到侵犯的主体却没有司法救济的机会。这既不利于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对乡镇政府权力行使的监督,与法治精神极不相称。
通过法院实现村民自治的法治化
村民自治的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农村改革后,各种力量都登上舞台,但形成良性运行机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行政权淡出村民自治领域,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成为独立王国,因为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仍然受制于法治的约束。面对行政权的强制性、主动性和扩展性,要保障村民自治权的行使,必须创造权利行使的外部社会环境,培养权利主体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和自我组织能力,而司法权的介入则对于村民自治权而言发挥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1982年宪法以及中央的有关法律和法规为村民自治提供了诸多权利,但在实施过程中这些权利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按理说,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的法令对所有地方政府都有约束力,并应获得地方政府的无条件实施。但在实践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相当普遍,中央保护农民和村民自治的法律和政令往往得不到地方的有效落实。由此可见,如果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那么再好的中央意愿也得不到地方的执行。行政法的使命正是保证政府的法治以及法律体系的统一与完整。中国行政法治的任务是改善目前的诉讼体制,取消一些现在看来不符合社会需要的限制,以确保行政诉讼对于保障行政法治的重要作用。可以想见,如果允许村民在法院直接挑战违法的地方行政干预,那么他们的合法利益将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反之,如果我们仍然将村民自治排斥在诉讼范围之外,那么可以预料的是,村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还将继续受到各种形式的侵犯。
最近,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所长熊伟提出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就村委会成员被非法撤换、停职、诫免等能否提起行政诉讼做出司法解释》,而最高法院已经将此建议列入2007年司法解释的立项计划。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如果这项建议获得采纳,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突破《行政诉讼法》的字面理解,统一要求各级法院受理村民针对基层政府违法干预村民自治的行政诉讼,那么,村民自治就将被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村民自治获得司法保障之后,诸如王华案之类的纠纷又将是另一种解决方式。
标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论文; 法律论文; 法律救济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