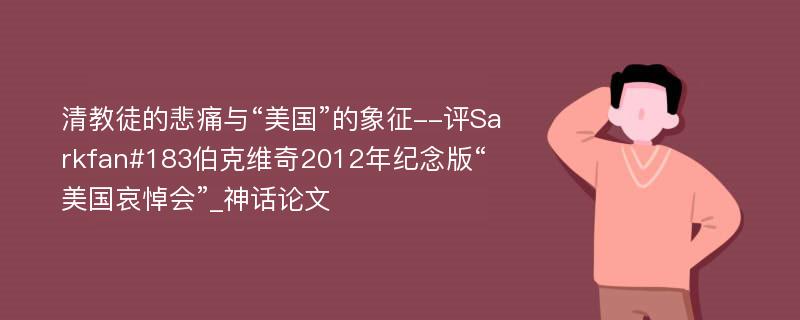
清教的哀诉与“美国”的象征——评萨克凡#183;伯克维奇的2012年纪念版《美国哀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维奇论文,萨克论文,象征论文,年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14)06-0087-05 萨克凡·伯克维奇(1933- ),哈佛大学鲍威尔·M.卡伯特美国文学教授、著名的美国文学、文化批评家。除了主编八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之外,伯克维奇还著有多部影响深厚的学术专著,如《美国自我的清教起源》(The Puritan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lf)、《美国哀诉》(American Jeremiad)、《惯于赞同》(Rites of Assent)、《红字的职责》(The Office of Scarlet Letter)。这几部著作奠定了伯克维奇的学术地位,使他成为继佩里·米勒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清教研究学者以及与亨利·奈什·史密斯、R.W.B.刘易斯、利奥·马克斯齐名的美国学研究学者。 《美国哀诉》初版于1978年,之后被列入美国高校文学、文化研究的必读经典。根据伯克维奇,哀诉发源于社会危机,却是社会再生之能动力。在二十一世纪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美国上下普遍要求改革之时,2012年再版《美国哀诉》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只要‘我们所相信的革新’在定义上等于‘确认体制基本信条的再生形式’,《美国哀诉》将永远活力四射、扣人心弦。”(Bercovitch,2012)伯克维奇为再版撰写了长达29页的序言,并在序言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包括研究的出发点、目的、方法以及最终的结论,还结合美国的历史与现状,赋予了哀诉以重要的时代意义。 哀诉,出自《圣经旧约》中先知耶利米书,文体以哀伤为主,后被普遍用于欧洲中世纪布道坛,作为谴责时代罪恶的一种表达方式。随后,该布道方式又随着大迁徙,从旧世界带到马萨诸塞。学术研究中的哀诉“不仅包括布道,还包括具有类似程式比喻的其它文本,如:俘获叙事、信件、契约的恢复、历史与传记”(Elliott,2002:102)。佩里·米勒在其《新英格兰思想:从殖民地到行省》中,详细分析了哀诉布道的起源、表现、形式、作用等,其阐释常成为后人认识的出发点。《美国哀诉》的思想也基于米勒的阐释,但与米勒思想存在分歧。 在起源上,米勒认为哀诉是第二、三代清教徒的产物,而伯克维奇提出那是第一代清教徒的产物。约翰·温斯罗普在“阿贝拉号”上的讲演就可视作这种哀诉的预演。在表现与用途上,米勒强调哀诉的谴责,而伯克维奇认为哀诉不仅用于指责,还体现了清教徒对其使命坚定不移的信念,具有“坚不可摧的乐观主义”。“诉而不哀”是清教哀诉的独特所在。在形式与功能上,伯克维奇提出清教哀诉不同于传统的欧洲哀诉,它着眼于未来,其终极意义在于“通过实施控制、维持过程……使控制合理化。”在语调与格调上,清教哀诉能乐观肯定地看待上帝的惩罚,认为上帝的惩罚证明了对他们的承诺”(Bercovitch,2012:7,24,8)。因此,哀诉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既含焦虑又具方向与目的。在辞令与历史关系上,伯克维奇也不认同米勒所认为的对立。他提出:“新英格兰正统,正是通过他们对清教理想的捍卫,成功地传承了一种神话,即使在神学统治消失,新英格兰本身失去其民族影响——从殖民地到行省、从行省到国家。……之后,这一神话依然处于文化之中心。”(2012:17) 辞令与历史并不对立。一方面,清教的想象传承了历史的神话;另一方面,清教徒对事实与理想间矛盾的哀叹常作为一种辞令方式在起作用,它常被用于敦促社群,“成为文化道德的工具”,并“经由共识进步的仪式、神圣-世俗象征体系以及公民宗教”,最终锻造成为强有力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具,在美国现代中产阶级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2012:61,28)。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离不开哀诉的另一个特征——对社会变化的适应能力。伯克维奇发现,面对社会发展,哀诉辞令会进行相应调整。尽管哀诉的本质是为了防范事实的侵袭,但其终极目标依然是使“新以色列”不受时代的危害。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危机成为哀诉的力量之源,之后,哀诉辞令不断在“十七世纪新英格兰的教义争执、印第安战争、巫术审判、特许状协商等一次次重大危机中,繁荣兴旺起来”,牧师们又“将正在衰退的一代融入历史考验的进步神话,并通过对救赎传承的大胆‘运用’,将父辈的传奇拓展成美国自身的故事”(2012:64,69)。 除此之外,哀诉者还依赖危机、颂扬危机,甚至还发明危机,为的是能从衰退中汲取勇气、将威胁变成维护、使苦难成为进步的保证,这样,危机既成了诉求的形式又成了内容。为了维护过去、捍卫过去的美好方式,一代代人从废弃的社会规范中抽象出一些更宏大的、更模糊的、也更灵活的象征与暗喻形式,如:新的拣选民族、山巅之城、应许之地、命定进步、新伊甸园、美国耶路撒冷等一些同质、同源术语,目的是为了“加快了从可见圣徒到美国爱国者、从神圣使命到显性天命、从殖民地到共和国到帝国力量的运动”(2012:91-92)。 这样一个逐渐运动的过程最终使“美国”①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共识的象征,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个地域的概念。 伯克维奇在《美国哀诉》中具体分析了这个演变的过程,并提出无论是在十八世纪、革命时期、乃至革命之后,种种时代辞令都可看作是清教辞令在仪式上的翻版。十九世纪之后,这种辞令的传承更是赫赫在目。各类思想,如:教育家所计划的使人类完善的“精神革命”,政治与道德改革家所宣传的“上帝计划的革命的圆满完成”,杰出思想家所敦促的技术将“革新土地”成为“人类神圣的天堂”,劳工领袖在革命中所发现的“工会主义后千禧年主义的合理性”,社会批判家对美国“在革命海洋中引领其他民族”的重申,政治家将合并与西进运动合理化为美国具有“向人类展现我们革命的神圣原则的杰出之处”的职责,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清教哀诉辞令的变异与体现(2012:142)。 重要的是,伯克维奇还发现,这样一个由辞令建构的“意识形态共识的象征”常以冲突的形式出现;共识不仅具有某种文化霸权的意味,而且冲突本身又是“一种控制方式,一种加快过程的手段,通过这一手段,过程成为社会化的辅助工具”(2012:161,160)。由此,伯克维奇提出:无论是在道德、宗教,还是经济、社会、思想方面,意识形态共识最成功、也最明显的体现依然在于哀诉赋予“美国”这个术语的象征意义: 只有在美国,民族主义才带有神圣的基督教意义。只有在美国,在所有民族称号中,结合了末世学与沙文主义的力量。……在所有现代意识形态中,只有美国方式,成功地结合了这些方法中固有的矛盾;在所有身份象征中,只有美国将民族性与普遍性、公民自我与精神自我、世俗历史与救赎历史、国家的过去与未来的天堂统一在一个综合的理想之中。(2012:176) 那么,“美国”这个象征在作家身上是如何展现的?伯克维奇以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为例提出:“美国”作为象征,既“是个现实”,又是个“自给自足的整体的两极体系”。尽管众作家间存有重大差异,但却具有令人惊叹的相似性:“我们所有的经典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神话,但又都在神话范围内写作。所有人都感到,至少在个人层面上,受美国主义的压迫,同时也受美国主义的释放。所有人,无论怎样受民族梦想的感染,都在用梦想去超越他们的文化范畴。”这种相似性恰恰就是美国哀诉之威力与影响力的显著证明:与新英格兰清教哀诉一样,这些作家在哀叹衰退的同时又在赞美民族梦想。“没有人比爱默生更宣称个体,更恶毒地指责美国的堕落,更热烈地捍卫美国体系的形而上学。”至于梭罗,“他在训斥邻居的同时,也在捍卫支撑他们生活方式的价值”。他认为美国是与“旧国家”相对立的“新国家”;他指责社会中的罪恶行径,认为那不是“美国方式的缺陷,而是偏离”。与爱默生一样,梭罗也同样屈从于美国的象征:“如果美国失败,那么宇宙本身——人、自然、历史的律法、英雄主义、远见与希望的基础将同样失败。”(2012:179-180,182,186,190) 除了哀诉,还存在一种相反的形式,伯克维奇称之为“反哀诉”(anti-jeremiad)。其出发点对立于爱默生与梭罗对美国的信念,即:出于对美国信念的否定。“反哀诉”指责所有的理想,无论是世俗的还是神圣的。在那些“反哀诉”作家手中,美国是个谎言,而非承诺。如果说哀诉致力于在美国的意义中发现人类的希望,那么“反哀诉”则致力于解释希望本身的徒劳与虚假。最佳例子是《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作品展现个人的失败是为了展现一切的失败,它暗喻的是一个“没有绝对标准”的世界的失败。因此,伯克维奇提出,所有经典作家都对文化适应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对于我们经典作家而言,成为美国人就是在定义上变得激进——反对过去、违反现状、成为变化的动因。同时,作为一位美国人,激进就是在某一基本意义上改变革命的冲动:使之精神化(像在《瓦尔登湖》中)、分散或扭曲它(像在《草叶集》中)、使之变成在亵渎与重生之间的选择(像在《白鲸》中)或使它普遍适应社会(像在“共和国的命运”中)。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通过调和个人、民族、文化间的理想,解决了价值间的冲突;……在任何情况下,可能提出基本社会选择的违抗行为变成了一种反对社会变化的基本力量。无论作家聚焦于个人还是社会,无论他要维护社会还是将社会注入自我,他所赞美的激进的能量是为了维护文化,因为释放那些能量的同些理想将激进主义本身变成文化凝聚与持续的方式。(2012:203-205) 至此,我们明白正是对清教哀诉及其所传递的“美国”象征的揭秘,《美国哀诉》才被誉为研究美国异议与文化形成的里程碑,其价值与贡献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美国思想研究的贡献。伯克维奇在《美国哀诉》中发现了蕴含在清教的哀诉与“美国”象征之间的“共识与异议”的文化本质。他提出清教的哀诉布道,作为一种社会凝聚力的礼仪模式,在确立以及维护文化主导意识形态中起着重要作用:哀诉辞令,以其能吸收对立面的兼收并蓄的强大能量,对“美国”的建构与“美国”的自我表达具有持久的塑造力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哀诉不仅“创造了一种焦虑的气氛,帮助释放事业成功所需的不安定的‘渐进主义’能量”,而且还能“将社会批评与精神重生、公共身份与个体身份、变化着的时代标志与某些传统的暗喻、主题与象征结合起来”,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作用于整个美国的历史进程(2012:xii-xix)。著名史学家埃德蒙·S.摩根认为“历史学家常感觉到大觉醒与革命、爱德华兹与爱默生,清教徒的山巅之城与美国扩张的‘显性天命’间存在某种关联,但都无法进行具体描述,伯克维奇提供了概念上的连接……[他]写的是最高层次的思想史”(2012)。 二,对美国辞令研究的贡献。《美国哀诉》是研究哀诉辞令的扛鼎之作。继米勒的清教研究之后,可以说,伯克维奇的成就无人超越。在迄今出版的两本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哀诉”研究专著中,伯克维奇的影响赫然醒目。一本是安德鲁·R.墨菲(Andrew R.Murphy)的《回头浪子:从新英格兰到9/11的道德滑坡与神圣惩罚》(Prodigal Son:Moral Decline and Divine Punishment from New England to 9/11);另一本是戴维·霍华德-皮特尼(David Howard-Pitney)的《非裔美国人的哀诉:呼吁美国的正义》(The African American Jeremiad:Appeals for Justice in America)。前者探寻了美国文化中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分析了从新英格兰到9/11美国文化中哀诉的形式、作用以及影响。墨菲坦言“美国哀诉”的研究一直处在“伯克维奇的长长的阴影”中,他在伯克维奇基础上提出了哀诉具有两种模式——传统的与进步的,并对比分析了两者的优劣,提出进步的哀诉优于传统的哀诉。后者,顾名思义,探索的是非裔作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思想中对哀诉的使用。霍华德-皮特尼一方面肯定黑人的哀诉辞令具有伯克维奇所谓的“保守的”与“激进的”双重因素;另一方面提出历史上哀诉一直是非裔美国人“表达不满与愤怒”、“呼唤改革”、“传递希望”、被广泛使用的“社会预言与批评辞令”以及“抗议辞令”(Murphy,2009:166,218)。这种认识与伯克维奇完全一致。另外,在作用与目的上,黑人哀诉与新英格兰清教哀诉也基本相似。两者唯一明显的差异在于源头,有不少学者就“上帝的选民”这一假定向伯克维奇提出过异议,②霍华德-皮特尼便是其中之一。 三,对美国文学研究的贡献。这既体现在研究方法又体现在思想洞见上。伯克维奇利用意识形态解读美国经典文学与美国文化,他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媒介,认为其本质是“交织进文化象征法中的观念体系”,是“共识的基础与实质”,其威力是它能将异议变成共识,使“美国的意识形态”成为由“一套独特的利害关系、权利结构以及自由社会的观念形态”的结合;使“美国”成为一个辞令的战场,一个被造就出来的象征,代表形形色色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世界观(Bercovitch,1993:355)。这种既非马克思主义又非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解读,不仅能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帮助人们充分理解作为时代文学的文本,而且能在多元主义的今天“认清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创造一个让冲突进行对话的空间,使对话保持在一种开放的状态”,最终“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达到使阐释不屈从于意识形态的目的(Bercovitch,1993:14)。为此,伯克维奇被赞为“作为美国文学研究中意识形态转向的主导人物以及跨学科实践的令人振奋之源”。(Hutner,2007:1)事实上,除了使用意识形态,伯克维奇还借用了雷蒙德·威廉斯与安东尼·葛兰西的社会与文化理论以及维克多·特纳与克里夫特·吉尔茨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等。这样的批评方法一方面适应了美国学研究快速变化的政治与机构局面,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学研究模式的方法论转向——从五六十年代的‘神话与象征’模式转向跨学科的‘新美国学’的研究”(张瑞华,2013:76-77)。 就其洞见而言,伯克维奇对美国文学研究者的影响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他向文学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为什么美国不同于其他移民国家(如:加拿大),相信自己是神授之国?为什么一代代移民接受并相信美国是“救赎者之国”?尽管有许多作家、诗人并不接受美国是世界的“弥赛亚”的说法(如:著名作家拉尔夫·艾里森、亨利·米勒、尤金·奥尼尔等并不认同哀诉的作用),但为什么其作品中人物的宗教经历依然在个人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有学者直言,因为伯克维奇,他“在教美国文学时与以往完全不同了”(Rosenmeier,1978:349)。1994年,作为对伯克维奇思想影响力的一个总结,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的内聚与异议》一书。编者在“引言”中明确表示:“这本论文集体现了伯克维奇思想在一代学者中的播撒……这些文章为美国文学与文化动力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考,这些思考源自与伯克维奇作品的思想交锋。”(Colatrella & Alkana,1994:xvii) 四,对由来已久的“美国”本质、美国身份之争的贡献。我们知道,美国文学史一直关注作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在伯克维奇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两者间的对立,即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文学中的“对立论”。③沃浓·帕灵顿从反抗传统权威的角度追溯“本土自由主义”的发展(Parrington,1927:vi),F.O.马西森宣称美国文艺复兴文本的共同点是“他们对民主可能性的探索”(Matthiessen,1968:ix)。与帕灵顿和马西森不同的是,伯克维奇也关注作家与社会间的关系,但他发现了迥异于他们的别样的东西,即:无论是对美国的批评还是对变革的呼唤,经典作家都基于同样的诉求:要求回归美国理想。因此,伯克维奇提出,经典作家的呼唤仅作为一种仪式(仪式化的哀诉)起作用,在他们那里“冲突本身变成了一种控制方式”(Bercovitch,2012:160)。毫无疑问,这一发现如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一方面,它对进一步“认识文学所履行的文化工作,了解某些文化张力是如何体现在文本中以及这些文本又是如何履行其自身的文化工作的”具有重大意义(Colatrella & Alkana,1994:xvii);另一方面,针对哀诉的意识形态共识性质,也有学者表示了担忧。他们担心这种文化模式对政治的影响,提出美国神话的那种“吸收矛盾以及调和紧张”的巨大威力可能会构成对人类潜在的危险(Zuckerman,1976:216);认为在意识形态批评家手中,“所有美国历史成了……一个个一成不变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版本”(Delbanco,1989:6)。有的甚至还批评伯克维奇的哀诉是“暴君式的辞令”,批评他的美国历史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历史(Harlan,1998:969)。 辩证地看,此类担心并非多余,因为美国的共识神话的确在伯克维奇那里得到了令人惊叹的表述与论证。而且就像伯克维奇在新版序言中所强调的,清教哀诉作为文化道德的工具以及意识形态共识的工具,不仅仅出现在文学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思想领域也随处可见。六十年代,黑人活动家利用哀诉倡导民权运动。二十一世纪,在美国遭受恐怖主义的袭击、面临重大经济危机之时,小布什要求美国“重整旗鼓,经历考验,更加坚强,取得自由事业上最伟大的胜利”。奥巴马呼吁“恢复繁荣……重申美国梦”、使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后的、最好的希望的形象”、“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面对危机,此类要求“恢复”、指向未来的哀诉辞令还出现在各类草根运动中,如:“茶党”爱国者在teapartypatriots.org 网站上以“追寻美国梦”这一愿景,宣告其核心原则是致力于“个人自由、经济自由以及没有债务的未来”;“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则以“我们是99%”的口号,强烈要求清除社会与经济中腐败与贪婪的影子,指责“1%”的有钱阶层不仅破坏了国家的价值,还破坏了美国梦。这些辞令在当今美国政治中的出现,绝非偶然,它们恰好印证了哀诉辞令对“美国”建构与“美国”自我表达的持久的影响力与作用力以及“美国”这个由象征建构的“神话”的巨大威力。从这一点看,我们似乎又不难理解美国学者们的担忧:共识的神话,作为美国例外主义话语的另一种表述,是把双刃剑,既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一方面,它为美国政治与生活中的对立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这种辞令又为美国的帝国构想提供了一个历史以及理论的支撑。 然而,不管美国的例外主义如何遭到追捧或批评,它一直是美国与美国人身份的一种表述。这已成不争的事实,就像一位英国学者所论定的:“美国的例外主义渗透在美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是在一系列有关美国身份与美国人身份的世纪争辩中传承下来的最强大的因素。”(Madsen,1998:1)在我们看来,神话与象征的创造既有其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伯克维奇的目的在于揭示这个创造与传承的过程,即他所谓的“‘美国’成为现代世界最强大的民族象征的过程”,而不是对其结果进行判断性的评说(伯克维奇,2005:1)。鉴于不少学者对他的误读,他声明这是“一位学者在试图传递某种创造性成就”,他的著作“既无意赞美‘清教思想’,也无意诋毁‘清教经历’。这既不是一位爱国者对‘美国例外主义’的高歌,也不是一位反对者对虚假神话的揭露”(Bercovitch,2011:14)。 伯克维奇的思想深邃,语言蕴意深厚,立论掷地有声,论述博古通今,再加上绵延复杂的句子结构,跨越宗教、历史、文学的学术语言以及时不时穿插的一些拉丁词汇,读者常需反复阅读、揣摩才能得其精髓,但瑕不掩瑜,语言结构的复杂掩盖不了一位学者的成就以及一部学术经典的普遍价值。尽管存在着异议,《美国哀诉》毫无疑问是我们认识、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乃至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注释: ①伯克维奇的“美国”(“America”)这一术语,既指美国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美利坚合众国,又指“美国”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宣言。“美国”的形成和维系既依赖一系列口头法则、道德法则、社会凝聚力、社会抗议召唤等,又依赖某个寓言、某个梦想、某种美学理想、某种现代的代名词(如:“进步”、“机会”、“创新”等)以及某些包罗万象的象征性说法(如:“大熔炉”、“大拼图”、“多民族之民族”等)。为此,伯克维奇提出:这样形成的一个国家不可避免会成为一个辞令(rhetoric)的战场。 ②这一点也可见他所主编的八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的编辑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