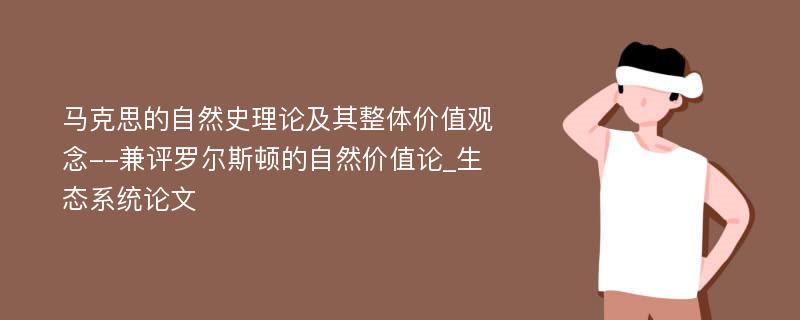
马克思的自然历史理论及其整体价值理念——兼评H.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自然论文,价值论论文,理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5-0606-06
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理论前提之一,其中统一的自然历史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解读似乎可以领悟到,在马克思自然历史观中含有一种人与自然的共同的普遍的价值理念,在这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都是不充分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虽然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与实践的重要意义,但其理论视野却是“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统一的自然历史体系的整体性、人与自然在其对象性与矛盾关系中趋于达到的“本质的统一”及其共同价值问题。
统一的自然历史观与“自然史”概念是马克思一贯坚持的学说。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第90页)他在论证“自然界的和人的存在”时又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第92页)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论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问题[2](第10页注②)。这里着重强调如下观点。第一,“自然史”与“人类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方面,“人类史”是通过自然演化和劳动的共同作用从“自然史”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在人类存在的条件下,“自然史”与“人类史”由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特别是人类的劳动实践而相互渗透、互为中介,从而延伸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共同系列,使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发展的自然历史系统。第二,“自然史”具有先在性与整体性,“人类史”是“自然史”的延伸与“现实部分”。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自然界由于人类的存在而发生怎样的变化,“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2](第21页),“人类史”本身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和更高阶段的延续。人的生活与生产、人对自然的工艺学改造与经济学占有依然是一种自然历史关系。第三,自然历史表现为“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首先,这一过程包括人从自然界的分化与提升,既包含“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历史,也包含人类的整个自然演化史,以及人类之前的自然演化史,因此当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之际,马克思才欢呼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3](第131页)。其次,这一过程包括人类通过劳动和主体意识的对象化活动所实现的对自然的人化,既包含的自然的人化,也包含人自身自然的人化。第四,自然历史表现为“自然史”与“人类史”,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矛盾与协调统一,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异化及其扬弃过程实现的。
以马克思的自然历史理论为出发点,从价值论的层面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应有其自身的价值,而统一的自然历史系统则是其共同的最高的价值承载者,在这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都是不充分的。这就意味着,在自然历史上“生成”的自然历史系统,包括其中各种形式的生命系统,人类系统,孕育各种生命的、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与人的生存活动息息相关的、为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所渗透的自然生态系统即人文—自然生态系统,都应有其局部的或整体的自身价值,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总体的自然历史的价值体系。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坚持康德的论证,认为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只有人才具有主体性、理性、意识、意志、目的、情感等,而其他自然存在物只是作为客体而为人存在的,它们只具有服从人的权力、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价值。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不仅有上面所说的主体意识的本质和其价值,更重要的是,人还具有劳动的本质和“类本质”及其价值;人不仅具有上述社会的人文的本质,而且还具有人的自然生命的本质,以及与这些本质相联系的目的与需求。因此,人是社会的“类存在物”与“自然存在物”的统一体,同时具有作为主体意识与劳动主体的内在价值和作为生命主体的内在价值,自身与他物在如何体现上述人文与自然的本质上、在如何满足其社会文化需求与自然生命需求上而具有工具价值的性质,这里的自身与他物包括人自身的行为和人之外的存在物提供的环境条件。
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则把自然目的性,特别是把生命系统的自然目的性,以及生命的存在与延续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否有客观的自然价值、包括其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重要标志和理由。罗尔斯顿为了证明“有机体的客观价值”,认为有机体具有“内在意向”和“追求特定目标的‘行为程序’”,认为“有机体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能够根据有关如何生存的信息……实现自我的维持、延续和再生。”[4](第133页)他还认为,甚至“在人类产生以前,有机体就从工具利用的角度来评判其他有机体和地球资源,有机体是具有选择能力的系统”[4](第253页)。因此他指出:“活着的个体是某种自在的内在价值。生命为了它自身而维护自己,其存在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对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4](第135页)。这里,罗尔斯顿肯定了生命个体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和他物相对于自身的工具价值,以及自身对他物所具有的工具价值。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所有生命系统都是“自然史”的产物,作为“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1](第104页),而分享自然历史的整体性价值,都具有自然的生命的本质与自然目的性。生命系统的自然目的性结构与功能都指向一个根本目的,即个体、物种与种群的自我维持与繁衍、自我生成与延续,都有这种内在的“自我需求”,从而可以表明生命系统应该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其自身行为与其生存环境在如何实现其满足“自我需求”的意义上,便具有工具价值的性质。这种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整合就构成了一种客观的自在的自然价值。
以上表明人与其他生命系统都承载自身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人除了具有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文价值或主观价值外,还有作为生命主体的自然价值或客观价值;而其他生命系统则只有作为生命主体的自然价值与客观价值;这种客观的自然价值应是人与各种生命系统共同的基础性的普遍价值。在自然历史系统包括生态系统中,人类显然处于最高的价值阶梯上,其他生命系统,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系统,都依次处于较低的价值等级上,并且作为不同的价值层次而构成生命“金字塔”的价值体系;同时上述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之间、不同局部的自然价值之间、人文价值与自然价值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过渡、互为条件、互为中介的,并且作为不同的价值环节而构成了生命链条与生态网的价值系统;所有这些价值实体在自然历史系统包括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重要的特定的地位、作用与意义。罗尔斯顿在讨论生命“金字塔”模型时,涉及了“人类主体”、“自然主体”,包括“人类文化系统”、“人类自然系统”、“动物自然系统”、“有机自然系统”等,指出:“处于上一层面的价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涵摄了、也需要处于下一层面的价值;上一层面的价值不是独立的或孤立的,而是需要下一层面的价值支持和维护的”[4](第 295页)。他还认为,其中“内在价值之结与工具价值之网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4](第254页)。
同时需要指出,上述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自然价值与人文价值、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等,既对整个自然历史系统及其整体价值的不断丰富与发展作出贡献,又要以这种共同的普遍的整体价值为基础,要分享具有自然历史性的整体性价值,就表明任何局部的自然价值与人文价值都是不完整的和有局限性的,都不是绝对的孤立的抽象的存在,它们不能从自然历史系统及生态体系的整体价值中剥离出来而赋有其充分的完整的意义。它们只有作为自然历史演化及其价值创造的积极成果,作为自然历史系统及生态体系整体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存在,才会具有其完满的自足的价值形态。对此,罗尔斯顿论述道:“在一个整体主义的环境网络中,‘自在自为’的个体的价值,即内在价值,是有些让人怀疑的。……如果把这些价值从生物的、公共的自然系统中剥离出来,那就是把价值看成了纯粹内在的和基元的,以致忘记了价值的联系性与外在性。……内在价值只是整体价值的一部分,不能把它割裂出来孤立地加以评价。”[4](第296页)这里罗尔斯顿坚持了生态价值整体性的主张。这种在自然历史上生成的生态系统整体价值对于各种局部价值具有基础性、主导性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与马克思“自然史”概念密切相关的是他的“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理论。正是“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自然历史的演化,才分化出和展现出了“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存在、对象性活动、对象性关系,以及自然历史体系包括生态系统之内在的本质联系、组织结构与统一关系;同时,正是由于“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才促成“自然史”向着更高阶段过渡与延续,促成了自然历史的不断丰富与全面发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在“自然史”上生成的各种生命系统,包括植物、动物和人,都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是“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1](第104页)。在他看来,“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1](第105页)。如果“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1](第106页)。如对植物来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1](第106页)同样,动物的饥饿的满足也需要自身之外的对象,以使它的生命的自然本质得以表现和确证。人直接作为有生命本质的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第105页)。
从价值论层面看,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含有如下思想。第一,一切“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都有一种“能动”的“自然力”、“生命力”,都有某种天赋的“欲望”存在于自身之内,因而都以生命的存在作为自己的内在本质或内在价值,而存在于自身之外的其他对象性存在物则具有“表现和确证”其本质力量的工具价值。第二,这种自然存在物在把其他自然存在物作为“表现和确证”其生命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与感性的对象时,又使自身成为其自身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表现和确证”其生命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与感性的对象,从而自身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相对于对方都具有工具价值的性质。第三,这种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都是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都是自然的生产与消费关系。对于这种生产与消费,马克思写道:“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5](第27-28页)。正是这种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物质变换、生产与消费关系,构筑了自然历史体系及其错综复杂的生态过程、生态关系与生态系统,构成了一切自然价值创造的内在动力与现实基础。第四,这种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关系,既包括自然存在物之间的相互区别与对立,也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创造或设定”,相互依赖与协调统一,其结果则是自然历史体系包括各种生态系统之组织化、有序化结构的形成,及其共同的整体的价值的形成。
上述自然历史的“生成”活动,以及自然历史上自然存在物之对象性关系、价值相关、物质变换、生产与消费的必然结果,则是自然历史系统的统一性与整体价值的形成,包括其中各种生态过程、生态关系与生态系统之统一性与整体价值的形成。这种统一性与整体价值一旦形成,对于各种自然存在物的对象性活动便会具有基础性、整体性、普遍性与压倒一切的地位。对于生态系统来说,罗尔斯顿曾指出:“生态系统所成就的最高级的价值,是那些有着其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存在于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灵长目动物、特别是人类之中——的处于生命金字塔上层的个体。这种个体是进化之箭所指向的最重要的目标。……即使是最有价值的构成部分,它的价值也不可能高过整体的价值。客体性的生态系统过程是某种压倒一切的价值”[4](第259页)。生态价值之所以有这种整体优势,是由于我们所谓的生态系统共同的整体价值,既包括处于生命“金字塔”与生态网中一切生命个体与种族之自然价值的统一整合,也包括与整个生态系统之内在的目的性与整体优化目标相联系的系统整体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这不同于罗尔斯顿对生态价值整体性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生态系统层面,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工具价值,……我们面临的也不是内在价值,……我们已接触到了某种需要用第三个术语——系统价值(Systemic Value)——来描述的事物。这个重要的价值……并没有完全浓缩在个体身上;它弥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但是,在生态系统中,这种系统价值并不仅仅是部分价值(Part Values)的总和。”[4](第255页)由于罗尔斯顿实际上否认了生态系统本身存在着整体性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因而他并未弄清楚这种不同于“部分价值的总和”的“系统价值”是什么。本文认为,生态系统的自然价值不仅应包括其中所有生命系统之“部分价值的总和”,以及在其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整合中所形成的总体价值,而且其核心应是与生态系统整体的演化与进化的目的性相联系的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与工具值,以及与生态系统自调节、自稳定、自适应、自组织的目的性与整体优化目标相联系的生态系统整体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而且,这两种目的性是相互联系、互为中介的,它们都指向一个更根本的目标,那就是更好地实现生态系统中诸生命形式的创造,生命形式多样性、复杂性、丰富性的展现,更好地实现各种生命种族的生存、延续、繁衍。这便是自然生态系统基本的核心的内在价值之所在,而系统自身及内部生态要素的行为,其外部环境条件的作用等,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而具有工具价值的性质。
人类一旦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便拥有其人文与社会历史的本质,开始创造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与自然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对象性关系:首先,人作为有生命本质的自然存在物,与自然界建立起了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自然性质的物质变换及生产与消费关系。其次,“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1](第107页)作为“类存在物”,人与自然建立的是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这“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第56页)这样建立起来的便是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主客体的“理论”关系,以及其他社会人文关系。
人作为“类存在物”,主要指人是作为劳动主体的存在物,具有劳动或生产实践的本质,人本身拥有区别于“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的“真正的劳动形式”及劳动的目的与需求,这是人最重要的内在价值之所在,人的劳动行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行为,在如何体现和确证人的劳动本质及实现劳动的目的的意义上便具有工具价值的性质。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第56页)人作为劳动实践的主体,具有自己生活与生产的目的,并通过劳动的对象化活动,而把自身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变成劳动的对象、劳动资料、劳动产品;自然界既是劳动的前提条件,又是劳动的对象化、外化、物化的结果,是对人的劳动之本质力量的展现和确证。这样确立起来的便是一种社会性质的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或生产与消费关系。
人作为“类存在物”,其次指人是有主体意识的存在物,而具有自我意识、意志、理性、思维、情感等内在本质,以及人的精神的目的与追求,这也是人的主要内在价值之所在,人自身的主体意识行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行为,在如何体现和确证人的主体意识的内在本质及实现其精神的目的的意义上也具有的工具价值的性质。由于人通过主体意识可“在理论上”把“自己本身的类”和“其他物的类”作为自己意识或“理论”的对象,因此“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第56页)。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有着精神的意向与目的,通过主体意识的对象性活动,而把自身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变为认知、评价与审美的对象,变成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及其作品。这种被人的自我意识所对象化的与人化的自然界,也是对人的精神或意识之内在本质力量的展现与确证。同时,人作为社会文化的主体,还有着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本质与目的,并以其特有的社会文化活动,创造着人类不断进步的社会历史、社会体制与社会生活,及其日益丰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些社会文化活动也会直接或间接地以自然界为对象,并渗透于自然界之中而改变着原生态,自然界则成为实现这些社会文化活动的基本条件与社会历史的产物。
在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中,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生态系统,包括诸多生态过程与生态关系,各种物种、种群与群落等,不仅会由于人类对象性活动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经受种种改变并不断被人化,而且作为自调节、自稳定、自组织系统,在一定限度之内会把这些人类的行为与扰动整合到自身之内,形成不断发展着的人文—自然生态系统这一统一整体及其共同的整体性的价值形态。
罗尔斯顿在谈到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时,主要强调的是“荒野”或原生态的总价值,他认为:“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学地位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是生态系统中的迟到者;而他们的文化行为(也许除了原始部落外)只能使生态系统退化”[4](第97页)。实际上,由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类活动已日益广泛与深入地渗透到了各种自然生态系统之生产与消费的生态过程中,及其各种相关的物种、种群、群落的组织结构与生态关系之中,各种局域自然生态系统和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几乎都受到了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的影响与改变,已不可避免地为人类社会历史所渗透,变成了由人类生活与生产技术活动,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活动所介入和延伸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时,我们所面对的已不是纯理想化的原生态或“荒野”,抽象地强调其“系统价值”已失去了现实意义。
应该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对象化,不仅导致了自然界的进一步人化与进化,而且也导致了自然与人的异化与对抗,以及生态系统的“退化”。工业社会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便是十分明显的证据。根据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类劳动本身及类本质的异化。人们通过历史的反思已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全球性问题的根源与严峻性,并在社会改革与进步中,通过社会生产、经济、政治、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协调发展,以及对人类自身行为的调整与控制,学会去逐步削减与扬弃这种自然界与人的异化与对抗。这当然是一个十分漫长的人与自然之双向调节与协调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论证了这种自然历史前景——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1](第81页),认为在此历史条件下,“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第83页)。这时,人才真正实现了自然界的人化与进化,自然才真正体现了人的“类本质”与人性,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自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与全面发展,都得到了进一步整合而协调统一起来。
相对于这样形成的人文—自然生态系统整体,人类生存与生产劳动,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才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与高级阶梯,人类特有的自然价值与人文价值,包括其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才成为它的组成要素而提升了这一整体价值;并且在人与自然的对象化、异化与协调统一中所创生的共同价值也汇入到了这一整体价值之中。同时,各种各样的、不同等级和层次的生命系统与生命维持系统及其自然价值,作为其低级阶梯,便构成这一系统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基本条件;生态系统演替与进化的目的性与合理性,其自稳定、自组织的目的性与合理性,仍然是其基本的核心的内在价值之所在,并且作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而指向一个更根本的目标,即实现地球上不同生命形式的创生、演变、分化、多样化、复杂化,以及诸生命系统的稳定、平衡、繁衍、完善,实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种族在各自生存空间中的全面发展与不断延续,展现包括人类生存在内的所有种族生命活动的丰富性、组织化、有序化、和谐与繁荣,实现地球上生命存在的永恒、美丽、完整与崇高。系统自身及内部自然与社会诸要素的行为,系统外部环境的作用,对此便具有工具价值的性质。
上述人文—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共同的普遍价值,既不是以人为中心,也不是以自然为中心,既不是纯粹的人文价值,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价值,而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价值,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共同的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利益与追求。
标签:生态系统论文; 内在价值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部分与整体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自然史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