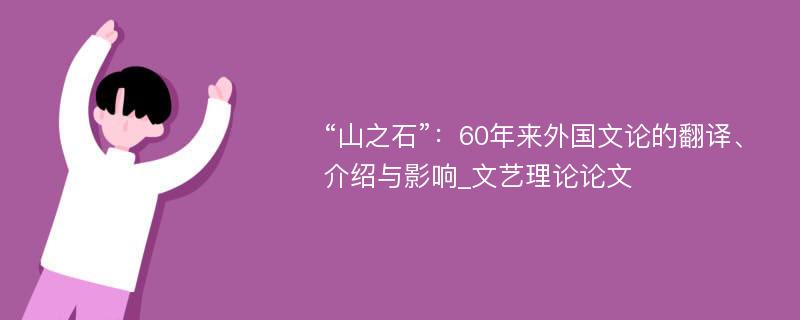
他山之石:60年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他山之石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12-0120-05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外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建国以来,文学理论的译介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以介绍苏联文论为主;80年代,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转向思想启蒙并以译介欧美西方文论为主;90年代,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把握中开始了与西方文论对话。经由这几个阶段,外国文艺理论进一步与传统文艺思想融合碰撞,这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和批评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50-60年代: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
20世纪50年代,出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构建新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需要,中国学界对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走上了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的道路。译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内容上,苏联文艺理论的译介都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
从苏联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国家领导人对文艺问题关心备至,常常以理论的形态或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作出直接指导。如列宁、斯大林等人都曾对文艺发展的方向作出过指示,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负责人卢那察尔斯基、日丹诺夫等人对文艺理论问题也多有论述。30-40年代,于苏联文艺界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的“日丹诺夫论断”。日丹诺夫时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联共中央书记,这样的政治地位意味着他的文艺主张实际上代表着苏联官方的指导思想。他强调艺术的思想性、人民性、阶级性、党性和社会意义,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上,极力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等思想理论流派一律概括为“资产阶级思想”,并通过一系列的大批判来清理这些观点,对国内持有类似观念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粗暴的打击。
苏联官方对待文艺理论的指导原则,对正在将苏联理论界思想原则奉为圭臬的中国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度政治化的苏联文论成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主要依据。这个时期,我国集中出版了以苏联专家编选为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如J·弗莱维勒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王道乾译,平明出版社,1951);米·里夫希茨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卷本)(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1966)①;索洛维耶夫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曹葆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曹葆华译,人民出版社,1954);尼·伊·克拉斯诺娃编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等等。这些经典论著的译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储备。同时,在这一时期,在苏联的举荐下,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论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高尔基、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理论著述,经过系统的翻译和有意识的推介,也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苏联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权威地位还体现在文艺理论教材方面的引进。仅50年代,就先后引进苏联文论教科书10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作为“苏联近年来唯一的一本大学文学理论教科书”[1](P1)的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柯尔尊的《文艺学概论》等。在此期间,中国也出版了一批自己的文艺学教科书,可基本上都是沿袭苏联理论界的框架体系和语言范式,其中比较权威的如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虽然这些著述可看到创造有中国特色文艺学教材的努力,但仍未跳出苏式框架,实际上是在文艺理论教材编写领域不断重复了“苏联模式”。
与苏联文论译介“一边倒”的局面相比,这一时期对西方文论的译介相对处于弱势。由于苏联对待西方现代理论的否定态度,欧美国家的文论一概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而遭到拒斥,中国学界同样效仿苏联,对西方的文艺理论译介不多,主要出版了一些古典和近代文论,有几套具有代表性的丛书或文选值得一提: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艺理论译丛》②;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科学院文学所西方文学组编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下),以及伍蠡甫主编的《西方文论选》(上、下)等等。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组织出版了一些西方古典美学著作,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吴献书译,1957)、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1961)、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1958),亚理士多德的《诗学》(罗念生译,1962)等等。以上这些西方古典译著在翻译质量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体现了编选者的学术勇气和非凡眼光,为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由于文本的选择也参照苏联模式,一味遵循政治标准和党性原则,使得学术译介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排他性,使得我们对于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仍然有着很深的隔膜,甚至闭目塞听,对国外学术界的动态和学科发展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
总体说来,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译介苏联文艺理论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流地位,并决定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理论构架、话语模式和评价标准。但由于我们是以俄苏为中介来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因而又陷入了一个误区,即认为苏俄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常常在苏联文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画等号,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苏联作家的阐释性论著不加分析地一概作为最高典范来译介和接受,对其顶礼膜拜。这种盲目崇信必然导致某些误解,例如,受弗里契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机械反映论的阐释,把一些苏联领导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奉为马克思主义来宣扬等等。而相形之下,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原著的钻研反而不够深入,甚至受苏联某些论著的影响,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理解存在偏差。这与特定的政治气候和特定的传播路径有直接关系,并且它直接导致中国学界对苏联文论几乎全面照搬,对苏联的文艺政策、文艺思想几乎全盘接受,缺乏批判性的审视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对除此之外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采取新然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这必然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制订产生深刻影响。同时,由于长期固守俄苏文论的指导思想、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均被排除在外,造成中国文艺学研究资源贫乏,话语单一,视野狭窄。随着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冷却,苏联文艺理论又被当成“修正主义”而受到批判,到了6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已阻断了与苏联等东欧国家的学术联系,只能通过“黄皮书”这样的内部参考资料来了解苏联文艺的发展。至此,中国文论界只能固守早期苏联文论的话语体系,苏联文论依然是中国文论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二、80年代:西方文论的大规模输入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革”的结束,政治和思想领域开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国门重新打开,文艺学和美学也在重大的历史机遇中谋求新的发展。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希冀驱动下,理论界越来越认识到,“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文艺理论建设也同样是这样。”[2](P1)通过译介外国文论,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以改变中国文论封闭的局面,成为时代之所趋。
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之后,我国文艺理论界思想空前解放,各项活动空前活跃,西方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工作逐步全面展开。最初,只是重新出版一些已经出版过的古典译著,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人们发现我们多年来奉行的文艺理论体系和模式,已经跟不上文艺发展的步伐,不能对新的文艺现象作出解释。为了满足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迫切要求,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得以迅速推进。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学界迎来了清末民初以来的又一次翻译热潮。据统计,“1978-1987年间,仅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译著,就达5000余种,大约是这之前30年的10倍。”[3](P275)“翻译热”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基于思想界的一个共识:中国社会各领域百废待兴,通过翻译引介来了解西方、认识西方,已成为第一要务。正因为如此,“翻译”的意义就不是语言的转换这么简单,而是指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即完成思想的启蒙,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半个世纪之前,鲁迅曾把翻译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的“窃火”,在中国社会经历冰封之后,搬运西方思想火种再次成为一条寻求突破的途径。在“睁眼看世界”的求知意识驱动下,中国的理论界迎来了新一轮的西学东渐。
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组织者们深信,自己所做的工作对于中国学术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将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如此宏大的目标和抱负,使得这场运动始终渗透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正如一位学者所言:80年代的翻译者们“既不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也不像1990年代许多人所主张的,从专业和学术建设的需要出发,而是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从他们对于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和历史使命的理解出发,投身到大规模的翻译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去。”[3](P278-279)因此,这场大规模译介西方理论的活动,是整个民族思想大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表征。在“翻译热”的席卷之下,大规模引进西方文论成为文艺理论界的重要学术活动,译介的力度和速度都是空前的,西方现当代各种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译文丛书主要有: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王春元、钱中文领衔编译小组所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文艺理论研究室所编的《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等。另外,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编选的《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文艺美学丛书》等等。
与50-60年代的外国文论翻译相比,这个时期的译介活动呈现出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思想更为解放,一些在以前属于研究禁区的著作陆续出版,所译范围覆盖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并努力提供介绍新思潮、新方法论、新理论学派的第一手资料,景象异常壮观。从接受范围和效果来看,这些译作、译著的影响力并不限于学术界和思想界,在普通读者中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中国社会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闭,几乎每个人都在尽可能迅速了解外来思潮的狂热气氛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美学译文丛书》最初的几部初版印数都在几万册,《艺术与视知觉》几个月内便卖出了6万册,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样一些专业人士都觉得晦涩难懂的哲学著作,也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册的销量。此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与这种繁荣的景象相对应的是,一些在西方学术界极受重视的重量级著作,翻译到中国来之后却似乎石沉大海,并未得到中国文艺学界的积极回应,如李普曼的《当代美学》、沃尔海姆的《艺术及其对象》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因为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涌入,乱花迷眼,泥沙俱下,表面的活跃背后隐藏一定程度上的喧闹,在读者中有一种跟风、一洪而起的效应;二是由于中国长期与国际学术界失去联系,对国外同行正在做的工作及讨论的话题还有些茫然无知;三是这个时期的人们迫切希望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因此钟爱更为宏大的叙事,而对于学术性较强、较为专业的著作缺乏兴趣。反映在外国文论的译介方面,这些现象也表现为某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比如,当时我们的理论界对于西方正红得发紫的分析美学重要代表作几乎没有引进,对于一些处于国际学术话题中心的重要理论也缺乏相应的关注。
1980年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外国文论译介工作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取得巨大功绩的同时也造成了某些方面的缺憾,它们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无法割裂开来。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总体上讲,通过翻译引入大量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使得中国文艺理论界和思想界逐渐摆脱了狭隘的意识形态模式的禁锢。而大规模输入西方文论本身是基于对一种美好前景的预设,即通过引进西方文论,改变苏联文论一统天下的局面,输入新的理论资源,的中国文论迎来一个繁荣的春天。但是,在操作层面,这样一种缺乏时间顺序的进入难免使人心浮气躁、眼花缭乱,一时难以理顺各种思潮之间的关系,对各个理论体系的发展逻辑线索缺乏清晰的认知。
第二,理论资源的调整,带来了研究范式的转型。西方文论的特点是有着严密的逻辑层次,富于独创性,重视个体的价值,充满人文关怀等,这对于习惯苏联文论高头讲章式的批评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感悟式批评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然而,80年代的理论界对于纷繁的西方文论基本采取一种完全“拿来主义”的态度,刚开始还把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当作某种教材引进,供国内学界研究、批判,但很快就转变立场和姿态,主要以“学习”和“补课”为目的。这种态度也造成了另一个误区,即从照搬俄苏模式转向套用西方模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对西方文论的理论崇拜,对外国文论缺乏认真的审视和有效的鉴别,致使生搬硬套、囫囵吞枣。
第三,由于时间紧迫,为了使中国读者以最快的速度了解西方文艺理论,翻译组织者大都非常重视翻译的速度。因此很多丛书的翻译较为粗疏,甚至存在一些错漏和不合规范的地方,如“编译和摘译盛行;随意删去注释和参考书目;不注明原作的版本和出版时间;搬用台湾或20、30年代的陈旧译本,等等”[4]。不过,这种情况随着90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及中国社会和法制建设进程的推进而基本告一段落。
20世纪80年代外国文论译介工作的意义,在于重新建立起与世界文艺理论之间的联系,为新时期的文艺理论建设输入了新的活力。由于选择翻译的文本本身大部分都是名著,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影响巨大,而这些译著所引发的话题,以及在这些译本的影响下产生的各种阐释、批判性的论著和论战的推波助澜,引起更多的人对原著的关注和研读。这就造成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力和辐射范围越来越大,日渐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中国学术界似乎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缺乏批判性的反思和独到见解。到了199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对西方的话语霸权甚至“文化殖民”提出质疑,虽然这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在西方的理论话语熏染下形成的思维模式,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自觉意识,不再愿意继续做西方文论的附庸。面对中国文论的输出和西方文论的引进之间的严重逆差,中国文论界开始了重建中国文论体系的努力。
三、新世纪:走向多元对话
这里所谓的“新世纪”,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时间概念,并不严格局限于21世纪,更确切地说,它指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文论译介和中西文论对话的趋势。经过近一个世纪,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积累,引进了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为健康的沟通和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入新世纪,西方文论翻译工作呈现出“共时”的特点,正在逐渐缩小译介的时间距离,如周宪、高建平主编的《新世纪美学译丛》,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金惠敏主编的《国际美学前沿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王逢振和希利斯·米勒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0世纪西方学术思想译丛》等等,都致力于介绍最新的国际理论动态,使中外文艺理论界的关系由单向传播走向多元对话。
这个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译介工作更加理性,也更加系统,以梳理、阐释、辨析为主,带有更强的时代感和学术性。这一时期对外国文论的接受不仅仅是停留在方法论、术语等表层,而是向纵深发展,对各种流派和思想的产生语境作更深入的考察,进行系统的研究、清理、深化和拓展,同时竭力探求新的研究方向,有着更明确的学科发展意识。具体说来,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美学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紧密结合。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现代性理论、后现代思潮、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译著数量迅猛增长,伴随中国社会的急遽转型,市民社会中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的显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译著陆续出版。这些译介活动反映了新世纪外国文论译介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和理论需求,以学术诉求为基本驱动力去做有意识的推动,努力在学术层面回应当代社会思潮的变化。
第二,在已完成文论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查漏补缺,填补空白,把一些重要的、但仍未译成中文的学术著作引介进来。如杜威的《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阿多诺的《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门罗·比厄斯利的《西方美学简史》(高建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等,都相继翻译出版。另外,像在当代西方美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像分析美学代表人物阿瑟·丹托等人的以前未受到我们重视、但在国际美学界广为人知甚至成为话语中心的一些著作,也译成了中文。
第三,努力与西方保持同步,形成对话。这既是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世界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的一种自觉的转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信息技术的进展,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都拥有同样的信息平台,各种交流日益紧密和频繁。外国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的新进展随时都能被中国学者获知,当代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思潮几乎能够同步进入中国,并引起反响。不少译著的中文版和外文版的出版时间相隔很短,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差,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西方学者讨论的前沿问题反应迅速,学术译介呈现同步的特征。中国学者通过国际会议、学术访问、讲学、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或出版论著、邀请西方同行来我国参加国际会议、讲学等活动,主动加强与国外的学术联系,增进外国同行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进展的了解。而在中国文论界有意识着手建构自己的美学和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同时,很多西方学者也开始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转向东方,从中寻找新的灵感和发展契机。当代著名美国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桥”。他说:希望能在中国和美国哲学之间搭建起一座桥,加强彼此之间的互动。作为实用主义美学在新时代的传承者,舒斯特曼自身也努力地从亚洲思想中寻求启示[5]。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认识到,新世纪美学的发展需要中西方学者通力合作,以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在其中寻找共鸣。
在新世纪,有几套具有代表性的丛书尤其反映了这样一种寻求双向交流的努力:一是周宪、高建平主编的《新世纪美学译丛》。该译丛的目的是“了解国际美学发展的现状,以我们自身的理论资源,参加到国际美学对话中去,这是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必由之路。”[6](P2)可见,国外美学新的发展动向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进入世界体系提供了契机,一种美学上的“国际主义”呼之欲出。二是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该译丛的立意同样非常清楚:“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7](P2)强调新时代的中国文论不应再跟在西方后面奋力追赶,而是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立足自身的实际,同时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个更高、更宽的平台上来思考。三是由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合编的一套《国际美学前沿译丛》。这套丛书带有某种象征意味,表明中外美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并倡导一种“球域”美学,即兼具经验的普遍性和不同传统的个性的美学。丛书的编者相信,这将是未来美学发展的方向。
从以上这些翻译活动我们可以看出,新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采用了一种双向的视角,套用文化学的一个术语即“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的话语崇拜,导致对自身学科发展的忽视,有学者非常犀利地指出:“近百年来,中国人几乎总是跟随在外国人的理论创新之后,翻译介绍,来往奔走,疲于奔命,而这种跟随与模仿,又往往变为一种时髦与招摇[8](P3)。的确,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要思考的不应再是引渡和挪用的问题,而是怎样不再让自己的理论园地成为外国文论的“跑马场”,怎样利用传统资源构造有独特学术个性的理论格局,在新一轮对话中掌握话语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因此,在新世纪,我们应该积极巩固既有成果,在有选择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构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形态,在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中发掘中国文论的当代价值,为世界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注释:
①米·里夫希茨所编的这套《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是当时最权威的选本,其中的某些部分在此之前已经翻译介绍过来,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曹葆华、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等。
②该译丛1958年12月第六期出版后停刊,1961年复刊时改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
标签:文艺理论论文; 美学论文; 文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西方文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