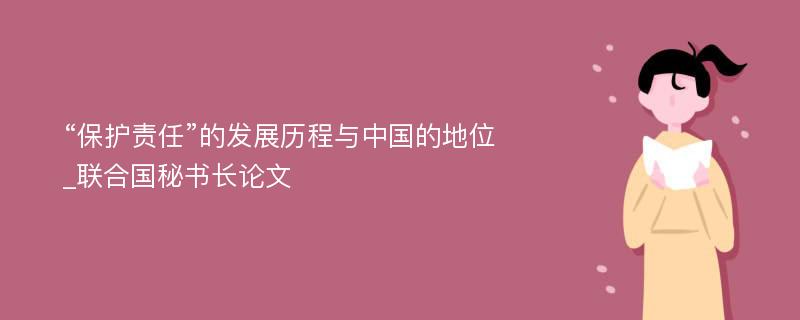
“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历程论文,立场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就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及相关的人道主义干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概念也应运而生。这一概念在2001年被正式提出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不仅被联合国秘书长所采用,而且被写入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更在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被实施。这一概念从产生到实施,进程发展之快实属罕见。虽然国际社会对其仍然存在分歧且在其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但“保护的责任”作为保护人权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探索仍然备受瞩目。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大国,其对“保护的责任”所持的立场也是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 一、“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 从2001年“保护的责任”概念正式提出到现在已经有近13年时间了,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保护的责任”概念的萌芽和酝酿(2001年12月以前) 为了解决冷战后频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人们已经开始探索联合国维和这一传统方式之外的新的更有效的途径,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干涉的权利”“人的安全”“个人主权”“负责任主权”等,这些概念都对“保护的责任”概念的提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0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国际社会就人道主义干预的相关问题达成共识。为了响应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一倡议,加拿大政府提议成立“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简称ICISS)作为解决相关问题的国际协调机构。2000年9月,在联合国的千年首脑会议上,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宣布该委员会成立。“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是专门为促进“保护人权”与“尊重主权”两种概念之间的沟通而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旨在促进世界各国就干预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展开全面辩论,帮助联合国消除内部在军事干预与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分歧。①加拿大政府任命了澳大利亚前外长、时任国际危机小组主席兼行政首长的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和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曾任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的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萨努恩(Mohamed Sahnoun)为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另有10名成员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德国、南非、菲律宾、瑞士、危地马拉和印度。他们当中既有知名学者,也有一些前政界人士。该委员会的经费由加拿大政府和一些重要的国际基金会提供。2001年1—7月,该委员会在北京、开罗、日内瓦、伦敦、马普托、新德里、纽约、渥太华、巴黎、圣彼得堡、圣地亚哥和华盛顿举行了一系列圆桌会议和讨论会,与各国的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代表共200多人进行了广泛研讨,征求了大量意见,最终形成了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保护的责任》报告。 (二)“保护的责任”概念逐步进入政治议程并被确认(2001年12月—2006年) 2001年12月,该委员会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了一份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②正式提出了“保护的责任”的概念。③根据这一报告,“保护的责任”的核心含义是一个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国民免受可以避免的灾难,具体说就是免遭大规模屠杀、强奸和饥饿。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履行它的这种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对此进行干预,从而代替其履行这种保护的责任。这是国际社会首次明确提出“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面阐释。 此后关于该概念的讨论日益增多,“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④的报告、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都对它做了阐释,不断推动这一概念向前发展。在2005年9月召开的世界首脑会议上,这一概念被写进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意味着它被正式提上了联合国的议事日程。 2004年12月,“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向安南提交了名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的报告。它明确阐述了新时代“主权和责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表达了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应该承担“保护的责任”。报告指出,主权概念“显然含有一国保护本国人民福祉的义务,以及向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履行义务之义务。但是,历史极为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能假设每个国家总是能够或者愿意履行其保护本国人民和避免伤害自己邻国的责任。而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集体安全原则意味着上述责任的某些部分应当由国际社会予以承担”。⑤该报告在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多次人道主义灾难后指出,“问题并不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干预,而是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保护那些身陷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的人,那些面临大规模屠杀和强奸、采用强行驱逐和恐吓方式进行的族裔清洗、蓄意制造的饥馑和故意传播的疾病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虽然主权政府负有使自己的人民免受这些灾难的主要责任,但是,如果它们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这样做,广大国际社会就应承担起这一责任”。⑥“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的报告及时呼应了“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新概念,使“保护的责任”被纳入联合国秘书长的考虑范围。 2005年3月21日,在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上安南秘书长做了题为《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的报告,对上述两份报告进行了肯定,并认为需要为此行动起来。报告第四部分指出:“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和最近由来自世界各地16名成员组成的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都赞同‘新的规范即集体负有提供保护的责任’(见A/59/565,第203段)。虽然我清楚这一问题的敏感性,但我坚决赞同这种做法。我认为,我们必须承担起保护的责任,并且在必要时采取行动。这一责任首先在于每个国家,因为国家存在的首要理由及职责就是保护本国人民。但如果一国当局不能或不愿保护本国公民,那么这一责任就落到国际社会肩上,由国际社会利用外交、人道主义及其他方法,帮助维护平民的人权和福祉。如果发现这些方法仍然不够,安全理事会可能不得不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行动,包括必要时采取强制行动。”⑦这是联合国秘书长首次正式将“保护的责任”的基本含义传达给各国,并请各国给予认真的考虑。 经过艰苦谈判,2005年10月24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该成果第四部分“民主与法治”特别强调了“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并以两段文字对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其中,第138段指出:“每一个国家均有责任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这一责任意味着通过适当、必要的手段,预防这类罪行的发生,包括预防煽动这类犯罪。我们接受这一责任,并将据此采取行动。国际社会应酌情鼓励并帮助各国履行这一责任,支持联合国建立预警能力。”第139段指出:“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也有责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使用适当的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帮助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在这方面,如果和平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有关国家当局显然无法保护其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我们随时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通过安全理事会逐案处理,并酌情与相关区域组织合作,及时、果断地采取集体行动。我们强调,大会需要继续审议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及所涉问题,要考虑到《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相关原则。我们还打算视需要酌情做出承诺,帮助各国建设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能力,并在危机和冲突爆发前协助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⑧这是联合国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表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原则上接受国际社会整体对陷入特定情势的人民负有保护的责任。2006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问题时通过的一项决议再次确认了《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中提到的“保护的责任”。该决议指出,安理会“重申《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138段和139段关于保护平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的规定”。⑨ (三)围绕如何实施“保护的责任”的大辩论(2006年—2011年3月) 这一阶段关于“保护的责任”的大量学术成果得以涌现,焦点逐渐转向如何将其付诸实施。此外,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人们在给予该概念高度赞扬的同时,也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国际社会也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对这一概念如何履行进行了激烈的公开辩论。 2009年7月23日、24日及28日,第63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了讨论秘书长关于《履行保护的责任》报告的辩论会,94个国家代表发言阐述了本国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及其关切的重点。绝大多数国家都对此报告表示欢迎,并支持报告为实施“保护的责任”所提出的“三大支柱”⑩的建议,认为前两个支柱尤其重要。多数国家认为“保护的责任”源于《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条约和国际人道法等已经存在的约束之中,赞同将该概念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四项罪行。很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都承认非洲联盟在实施该概念发展上的开创性作用。 但忧虑和分歧也是存在的。部分国家担心“保护的责任”在实施中会出现选择性适用或双重标准,从而导致其被大国滥用。约1/3的国家呼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涉及“保护的责任”议题上不使用否决权,有少数国家提出改革安理会是实施“保护的责任”的先决条件。在安理会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时,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处于何种关系的问题上各国没有达成一致。这是各国首次在联合国框架下对“保护的责任”进行正式的专题讨论,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 (四)对“保护的责任”进行实施并产生重大分歧(2011年3月至今) 2011年3月19日,以北约为首的多国部队在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后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这次行动被西方称为“保护的责任”的首次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这次干涉行动之前,国际社会的很多表态和反应都是从“保护的责任”角度出发的。例如,2011年2月23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阿什顿代表欧盟就利比亚问题发表谈话时,谴责了利比亚当局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表示欢迎联合国安理会22日呼吁利比亚政府承担保护人民的责任与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法的声明。(11)2月23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发表公报,强烈谴责对和平示威者不加选择和过度地使用武力,认为这是对人权和国际人道法的粗暴践踏,造成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号召利比亚政府承担保护的责任,保证人民的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的到位。(12)因此可以说,“保护的责任”是利比亚军事干涉行动的重要动因。 2月26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第1970号决议,对利比亚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决定对利比亚实施严厉制裁。3月17日,安理会通过了第1973号决议,决定对利比亚实施禁飞,要求卡扎菲政权立即停火,并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根据这一授权,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局势进行了军事干预。但这次干预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多国部队的行动被认为滥用了安理会授权,直接进行了政权更迭,这违背了安理会决议的初衷。 利比亚危机一波未平,叙利亚危机又接踵而至。西方一些国家在利用“保护的责任”成功干预利比亚危机并实现预期目标后,又想以同样的方式干预叙利亚危机。而在国际社会,“保护的责任”确实也成为观察叙利亚危机的重要视角。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2年1月18日就明确指出,叙利亚问题将是对“保护的责任”的一次检验。(13)事态的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国际社会在处理叙利亚危机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分歧,中国与俄罗斯联手在安理会多次否决了针对叙利亚的提案,在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多次相关投票中,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明确表达了反对的立场。国际社会的严重分歧表明叙利亚危机已经不太可能复制“利比亚模式”,“保护的责任”在叙利亚危机中似乎已经陷入困境。 二、“保护的责任”在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保护的责任”概念产生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到2005年的世界首脑会议已经在国际社会达成了某种共识,但在如何实施的问题上却一直存在诸多分歧。这也表明“保护的责任”在实施中会面临多方面的问题。 (一)日趋缩小并被严格限定的适用范围 从“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来看,原则上“保护的责任”已经在联合国得到了确认,但其最终的适用范围已经与最初报告的设想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初的“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对“保护的责任”适用的范围界定较为宽泛。然而,随着该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逐渐被提上政治日程,在人们期待它能够在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时,却发现它的适用范围在逐渐缩小。 “干预和国家主权委员会”的报告和“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的报告均采用列举式来定义保护的范围。它们都认为“保护的责任”是“保护本国国民免受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的责任,但前者列举的是“大规模屠杀、强奸、饥饿、种族清洗”,(14)后者列举的是“大规模屠杀和强奸、采用强行驱逐和恐吓方式进行的族裔清洗、蓄意制造的饥馑和故意传播疾病”。(15)安南秘书长在其报告的附件中将其限定为“灭绝种族罪、族裔清洗、危害人类罪”。(16)《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直接将“保护责任”定义为“保护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相比较秘书长的报告,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将“战争罪”也纳入保护的范围,但相比较“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和“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的报告,显然是缩小了“保护责任”的适用范围:饥饿和故意传播疾病被排除在外,灭绝种族、族裔清洗的范围也比大规模屠杀要小。“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和“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的报告使用的是描述性语言,而秘书长的报告和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是以现有国际法和条约所确定的罪名为基础的,便于在实践中进行判断和应对。一方面是由于文件的制定者在性质上存在差别,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对“保护的责任”问题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得以通过是妥协的结果。 由自然灾害引起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否应纳入“保护的责任”,各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法国、克罗地亚、斯洛伐克等少数国家对此表示支持。《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表述中没有对引起四种罪行的情势做出规定,它是从“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传承而来的,该报告将引起四种罪行的情势表述为“内战、叛乱、镇压或国家陷入瘫痪”,但这种界定显然过于宽泛。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把“保护的责任”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这四种罪行,并被认为是关于“保护的责任”现已达成的国际共识和权威解读。 (二)关于如何行动的不同提法 在如何履行“保护的责任”方面,国际社会所达成的共识是:国家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只有在国家因主观或客观原因无法承担这一责任时才有义务行动;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在行动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需采取行动,应该从非强制性措施逐渐过渡到强制性措施,军事手段应该作为最后手段而使用。 “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报告提出了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三个阶段“预防—反应—重建”。预防措施包括政治和外交、经济、法律、军事;(17)反应则“可以包括像禁运、国际公诉和在极端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等强制性措施”。(18)“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指出的行动路径是“开展预防工作,在必要时对暴力行为做出反应,和重建四分五裂的社会。应该主要注重通过调解和其他途径协助制止暴力,和通过派遣人道主义特派团、人权特派团和警察特派团等措施来保护人民。如果需要使用武力,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19)安南认为,应当“由国际社会利用外交、人道主义及其他方法,帮助维护平民的人权和福祉。如果发现这些方法仍然不够,安全理事会可能不得不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行动,包括必要时采取强制行动”。(20)《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遵循了秘书长的看法并将其具体化。首先使用和平手段,动用强制手段时要和区域性组织合作,安理会并不制定一般规则,而是逐案处理。 (三)国际社会对“保护的责任”的不同立场 虽然经过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和2009年联大的几次辩论,国际社会已经在原则上就“保护的责任”达成某种共识,但并不表明所有国家都对“保护的责任”拥有了完全相同的看法。事实上,不同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看法不尽相同。 在2011年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根据不同国家的立场,可以把世界各国的态度大致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非常支持的国家。这些国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等规模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德国、北欧各国;第二种情况是非洲政局比较稳定的国家。这部分非洲国家适应了非洲联盟主导的或者非洲联盟与联合国合作的干预模式,对“保护的责任”态度积极。 第二类是持保留态度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可以归为这一类,有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也有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尼。它们对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等推动“保护的责任”并不反对,但是它们表达了自己的合理关切,认为该概念尚不成熟,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并有合理的制度做保障之后才能付诸实施。 第三类是极力反对的国家。这类国家并不多,仅古巴、委内瑞拉、苏丹、尼加拉瓜、斯里兰卡等少数国家。 这三类国家的构成表明,发达国家阵营内部态度不统一,发展中国家阵营也不是一个声音说话。但随着利比亚危机的发生和依据“保护的责任”对其实施的军事行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国际社会在实施“保护的责任”问题上重新进行了分化和组合。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二类持保留态度并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国家之中。其中一些国家如美国由于积极主张军事干涉被认为加入到了第一类非常支持的国家的阵营。而一些国家由于看到利比亚危机中安理会的授权被滥用,进而对继续干预叙利亚危机坚决反对,被认为加入到了第三类反对国家的行列。 (四)如何解决和规避利比亚军事行动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 多国部队对利比亚危机的军事干预行动让国际社会看到“保护的责任”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如安理会的授权被滥用的问题,实施行动国家的政治偏好和政治意愿的影响,如何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的问题等,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将会影响“保护的责任”在未来的发展走向。 三、中国关于“保护的责任”的立场 “保护的责任”强调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不能或不愿履行它保护本国国民的责任,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进行干预,从而代替该国履行这种保护的责任。这是国际社会试图处理人权与主权关系的最新进展。这种理念从根本上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构成了挑战,因为它允许在特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可以突破主权国家的界限对其进行干涉。而这与中国传统的外交理念是冲突的。 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强烈捍卫国家主权传统原则的少数国家之一,中国反对大部分针对国家内部事务的外国干预。中国的主权观念非常传统。(21)因此,中国是国家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坚定捍卫者,坚决反对外来力量对一国内政的直接干涉,特别是外来的武力干涉。中国一贯支持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对于西方主张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中国是反对的,认为国际人权保护应建立在坚定维护各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之上。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主权观念,中国对那些冲击或挑战主权原则的概念和理念都表现出一定的疑虑,持非常审慎的态度。这一情况不仅体现在“保护的责任”的酝酿阶段,在此后的几个阶段也有所表现。 (一)在“保护的责任”的酝酿阶段,中国参与到了对这一新概念的讨论过程之中,但态度谨慎,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准备起草《保护的责任》报告的阶段,“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曾专程来北京座谈,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讨论会,希望讨论以下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讨论外部的武力干涉,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干涉,武力干涉以外的途径是什么,以及武力干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在中方与会人员中,只有一位前任大使,其余均为学术机构和大学的研究人员。这与在巴黎和新德里召开的讨论会相比,规格明显要低。中国学者的发言基本以“人道主义干预”为主,重点批判西方主导的相关行动。中国学者认为,应当将联合国主导的“人道主义救援”(humanitarian assistance)与西方国家强调的“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进行严格区分,并且在地区冲突中,推动前者而非后者。中国学者并没有直接讨论“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提议的“保护的责任”问题,也没有涉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武力的问题。(22)从参与这一讨论会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对这一议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在当时情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没有明确在这一议题上表达立场。 (二)在“保护的责任”概念逐步进入政治议程并被确认的阶段,中国明确表达了官方立场,认为国际社会对于“保护的责任”应持慎重态度 作为该理念的主要支持者,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提议组建“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讨论“保护的责任”及联合国改革问题。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应邀参加了该名人小组的工作。对此,中国政府在公开场合表示欢迎该小组的成立,赞赏安南秘书长为此所做的努力,期待该小组尽早启动,并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保护的责任”则未提及。(23) 在这一阶段,中国对“保护的责任”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目前各国并未就此达成一致,因而应重在进一步讨论而不是匆忙将其运用于实践。若非要适用,则应恪守基本的国际准则。中国2005年6月发布的《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在第三部分“法治、人权与民主”标题下单列了一小节,明确阐明了中国对“保护的责任”的立场。其中指出,“各国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一国内乱往往起因复杂,对判定一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保护其国民应慎重,不应动辄加以干预。在出现大规模人道危机时,缓和与制止危机是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有关行动须严格遵守《宪章》的有关规定,尊重有关当事国及其所在地区组织的意见,在联合国框架下由安理会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和处置,尽可能使用和平方式。在涉及强制性行动时,更应慎重行事,逐案处理”。(24)这和中国此前的立场一致。(25)中国赞同不结盟集团关于“保护的责任”的意见。(26) 在2005年9月世界首脑会议期间,中国代表的发言重申国际社会应当慎重对待“保护的责任”。王光亚大使在联大磋商9月首脑会成果文件草案时的发言中指出:“‘保护的责任’概念涉及国家主权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各方目前仍有不同认识,需进一步协商。草案对该问题的表述应慎重……各国政府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对如何判定一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和意愿保护其公民,应研拟国际社会普遍同意的综合评定标准,不应由少数国家或机构自行制定。”(27)而在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不论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大和安理会上的发言,还是外交部长李肇星和大使张义山的公开发言,则都未直接提及“保护的责任”。(28) 在世界首脑会议文件正式通过后,中国又对其官方立场进行了补充。中国强调对“保护的责任”概念的界定应以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的规定为准。中国认为第1674号决议及世界首脑会议文件关于“‘保护人民免受大屠杀、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责任’的表述”不同于“单纯的‘保护的责任’概念”。(29)“不能对‘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做扩大或任意解释,更要避免滥用……各方仍应以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中的内容为准来解释和适用该概念。”(30) (三)在对“保护的责任”如何实施进行大辩论的时期,中国积极参与了各种国际场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明确表明自己对讨论持开放态度,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立场 中国认可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对“保护的责任”的界定,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于四种严重的国际罪行,认为履行“保护的责任”不能违背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安理会要慎重行事,防止“保护的责任”被滥用。在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中国立场的是2009年7月中国时任联合国大使刘振民在联大关于“保护的责任”问题辩论会上的发言。(31)其中认为“保护的责任”是21世纪初出现的一个新概念。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对“保护的责任”做了非常谨慎的描述。成果文件将“保护的责任”的适用范围严格限于“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反人类罪”等四种严重的国际罪行。但几年来,各方对此概念的内涵和适用性仍存在争议。 根据这一发言,可以看出中国关于“保护的责任”的立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各国政府负有保护本国公民的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协助,但保护其民众归根结底还要靠有关国家政府。这与主权原则是一致的。因此,“保护的责任”的履行不应违背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尽管世界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能动摇。 第二,“保护的责任”概念只适用于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等四种国际罪行。各国均不应对该概念做扩大或任意解释,更要避免滥用。要防止将“保护的责任”用做“人道主义干涉”的另一种翻版。在出现上述四大类危机时,缓解和制止危机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正当要求。但有关行动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尊重当事国政府和所在地区组织的意见,要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处理,并用尽一切和平手段。 第三,当发生上述四大类危机且需要联合国做出反应时,安理会可发挥一定作用。但安理会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和处置,并应慎重行事。需要指出的是,《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其采取行动的前提是发生了构成“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及侵略行为”。安理会应将“保护的责任”放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框架内一并考虑,应防止滥用。 第四,在联合国及区域组织范围内,应将正常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履行“保护的责任”时的国际援助相区别,以保持人道主义援助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并避免“保护的责任”的滥用。 中国认为“保护的责任”自提出到大辩论时期都还只是一个概念,尚不构成一项国际法规则,因此,各国应避免将“保护的责任”作为向他国施压的外交手段。“保护的责任”能否得到各国一致接受、能否真正有效履行,还需要在联合国或有关区域组织内进一步探讨。 此外,中国还明确反对将“保护的责任”适用于自然灾害引发的人道危机中。(32)中国认为要保护平民,必须从源头上解决冲突产生的根源。(33) (四)在多国部队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导致国际社会对“保护的责任”产生重大分歧的阶段,中国的态度逐渐由温和转为强硬 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中国并不是从“保护的责任”的视角来看待利比亚危机的处理,而是强调“逐案处理”的原则,不希望国际社会干预利比亚危机成为惯例。针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明显出现背离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中国明确表示反对,并在后来针对叙利亚危机的表决中,多次使用否决票来表达自己坚决反对的立场。在处理利比亚危机的前期,中国政府基本支持了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行动,对1970号决议投赞成票,对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投弃权票事实上是默许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干预行动。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反应十分关注,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多次提问涉及这两次投票,例如,弃权票是否表明中国相对放弃了“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一贯立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非常含糊。 但与西方干预利比亚危机基于“保护的责任”不同,中国并不是从“保护的责任”的角度来解释自己的行动。在联合国安理会就1970号决议和1973号决议投票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保东在解释性发言中明确将“利比亚局势的特殊情况”(34)而不是“保护的责任”作为中国在1973号决议表决中投弃权票的原因。对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该事件与“保护的责任”的应用相联系的论述,中国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此外,在利比亚危机中,中国强调了在《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中规定的“在涉及强制性行动时,更应慎重行事,逐案处理”的原则。通过强调利比亚事件的特殊性,中国政府表达了不以该事件为未来国际相关机构采取行动时的依据的基本立场。(35) 对于多国部队滥用安理会授权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了不满。“中方呼吁各方严格、准确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不做任意解读,不采取超出授权的行动……”(36)“保护平民属于人道主义范畴,不能夹杂任何政治动机和目的,包括进行政权更迭……选择性的做法或采取双重标准只会损害安理会的作用和权威。”(37)中国也质疑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是否符合保护平民的原则。 在“利比亚事件”没有完全结束而叙利亚危机已现端倪时,中国提前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中国政府不希望类似于利比亚的干涉事件再次发生。(38)由于在利比亚危机中成功实现了军事干预,西方国家希望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叙利亚危机。安理会在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和2012年7月19日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与俄罗斯采取一致立场,联手否决了这三个意在谴责叙利亚并可能为军事干预铺路的决议草案。(39)中国不仅在安理会上否决了有关草案,在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涉叙问题上也多次投了否决票。 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涉叙问题上的投票表明国际社会在实施“保护的责任”干预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这似乎使得“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前景变得不确定起来。这其中,中国的立场备受瞩目。有观点认为,中国从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接受“保护的责任”到在涉叙问题上多次投反对票,似乎关于“保护的责任”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但经过对中国立场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保护的责任”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是传统的主权原则的坚定捍卫者。从一开始中国就对这一概念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中国也希望国际社会持谨慎态度。在2005年在世界首脑会议上就这一概念达成一定共识之后,中国本着合作的态度接受了这一概念,但接受是有前提的。中国只认可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对“保护的责任”的界定,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于四种严重的国际罪行,并坚持履行“保护的责任”不能违背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对于利比亚危机的处理,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并不是从“保护的责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对利比亚危机的军事干预使中国看到一些国家在利用“保护的责任”的概念滥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进行政权更迭,这完全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违背了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是中国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中国采取了坚决的反对行动。但中国的反对行动本身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反对“保护的责任”的理念,中国反对的是一些国家在“保护的责任”的大旗下突破现有国际法准则、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行动。 综上所述,“保护的责任”概念自2001年12月诞生至今已经以惊人的速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虽然国际社会就此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分歧也一直存在。由于其在利比亚的实施暴露出了新的问题,导致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分歧,从而没有在叙利亚危机中得以复制。中国对“保护的责任”的立场也经历了回避、表明立场、有条件支持、坚决反对其滥用等几个阶段的变化。“保护的责任”在实施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表明“保护的责任”概念目前还不尽完善,有待进一步规范。 注释: ①魏宗雷、邱桂荣、孙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②"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http://www.dfait-maeci.gc.ca/iciss-ciise/report2-en.asp; 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保护的责任》报告(中文版),见http://www.iciss.ca/pdf/chinese-report.pdf。 ③该报告除前言和提要外,分八章对“保护的责任”进行了阐述,说明了它的基本原则、责任基础、构成要素(预防责任、做出反应的责任、重建的责任),以及军事干预的原则。详见http://www.iciss.ca/pdf/Chinese-report.pdf,该委员会还发布了报告的补充卷(共398页),详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文献资料、争论的主要问题等。 ④“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3年9月召开的第58届联大上宣布成立的,目的是就联合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载理想、为所有人提供集体安全向他提供意见。 ⑤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U.N.Doc.A/59/565,第29段。 ⑥同上,第201段。 ⑦[加纳]科菲·安南:《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U.N.Doc.A/59/2005,第135段。联合国网站: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5/270/77/PDF/N0527077.pdf,Open Element,2010-07-07;另可参见http://www.r2pasiapacific.org/docs/R2P% 20Key% 20Documents/In%20Larger%20Freedom%20Towards%20Development.pdf,2014-06-01。 ⑧《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U.N.Doc.A/Res/60/1,第138、139段。 ⑨联合国安理会第1674号决议,2006年4月28日安全理事会第5430次会议通过,U.N.Doc.S/RES/1674(2006)。 ⑩这三个支柱依次分别为:国家的保护责任、国际援助和能力建设、及时果断的反应。 (11)刘衡:《欧盟在利比亚危机中的行动大事记(2011年2—11月)》,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网站,http://ies.cass.cn/Article/dsj/dsj/dsj2011/201111/4328.asp,2014-02-25。 (12)COMMUNIQUE OF THE 261 ST MEETING OF THE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http://au.int/en/dp/ps/sites/default/files/2011_feb_23_psc_261stmeeting_libya_communique_en.pdf,2014-05-03。 (13)《潘基文称叙利亚问题是对落实“保护的责任”的一次检验》,联合国电台,2012年1月18日,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archives/161466/,2014-02-28。 (14)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保护的责任》报告(中文版),分别见前言和第52页,http://www.iciss.ca/pdf/Chinese-report.pdf,2002-01-03;报告全文也可参见http://www.r2pasiapacific.org/docs/R2P%20Key%20Documents/ICISS%20Report.pdf,2014-05-20。 (15)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U.N.Doc.A/59/565,第201段。 (16)[加纳]科菲·安南:《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U.N.Doc.A/59/2005,附件。他敦促各国元首“接受‘保护责任’,作为对灭绝种族行为、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采取集体行动的基础,并同意将这项责任诉诸行动”。 (17)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保护的责任》报告(中文版),第17页,http://www.iciss.ca/pdf/Chinese-report.pdf,2002-01-03;报告全文也可参见http://www.r2pasiapacific.org/docs/R2P% 20Key%20Documents/ICISS%20Report.pdf,2014-05-20。 (18)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保护的责任》报告(中文版),提要部分,http://www.iciss.ca/pdf/chinese-report.pdf,2002-01-03;报告全文也可参见http://www.r2pasiapacific.org/docs/R2P%20Key%20Documents/ICISS%20Report.pdf,2014-05-20。 (19)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U.N.Doc.A/59/565,第201段。 (20)[加纳]科菲·安南:《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U.N.Doc.A/59/2005,第135段。 (21)楚树龙:《中国、亚洲及主权和干预问题》,改革开放论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编纂:《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9—42页。 (22)Thomas G.Weiss,DonHubert,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search,Bibliography,Background:Supplementary Volume to th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December 2001. (23)2003年11月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就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应邀参加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工作答记者问,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fyrbt_602243/dhdw_602249/t40234.shtml,2013-05-24。 (24)《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2005年6月7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lhg_609678/zywj_609690/t199083.shtml,2014-03-02。 (25)2004年4月19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谢波华参赞在秘书长改革报告《法治、人权与民主》部分非正式磋商中的发言,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fyywj/wn/fy2005/t192894.htm,2009-07-26。 (26)“在制定使用武力标准、‘保护的责任’、人的安全等问题上,中方已明确阐明了立场,理解和支持不结盟集团的有关主张。”参见2005年7月2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张义山大使在联大磋商9月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草案时的发言,http://www.china-un.org/chn/zt/gg/t06050.htm,2009-08-01。 (27)《王光亚大使在联大磋商9月首脑会成果文件草案时的发言》,2005年6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200843.shtml,2013-05-03。 (28)胡锦涛:《维护安理会权威,加强集体安全机制》,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安理会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9月14日,纽约,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t/snhy/t212128.htm;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9月15日,纽约,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t/snhy/t214187.htm;李肇星:《走和平、和谐、共同发展之路》,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2005年9月19日,纽约,http://www.china-un.org/chn/lhghvwj/ldhy/yw/ld60/t212849.htm;《张义山大使在第60届联大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的工作报告时的发言》,2005年9月29日,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ldhy/yw/ld60/t214652.htm,2013-08-03。 (29)《刘振民大使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2006年6月28日,http://www.china-un.org/chn/xw/t260631.htm,2009-07-26。 (30)《刘振民大使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2006年12月4日,http://www.china-un.org/chn/hyyfy/t282527.htm,2009-07-27。 (31)《刘振民大使在联大关于“保护的责任”问题全会上的发言》,2009年7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lhghywj/ldhy/63rd_ga/t575179.htm,2014-03-02。 (32)“将这一概念引入救灾领域,不仅无助于国际社会对这一概念达成一致,还可能导致更多的混乱。”2008年11月3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刘振民大使在第63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60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的发言,http://www.china-un.org/chn/dbtxx/czfdblzm/zyhd/t29985.htm,2009-07-27。 (33)“安理会既应重视遵守国际人道法问题,还应设法解决产生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实现标本兼治。”2009年1月29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刘振民大使在安理会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尊重国际人道法”问题非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http://www.china-un.org/chn/zgylhg/jsyfz/rdzysw/t534474.htm。另外,2005年12月9日,张义山大使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辩论会上的发言,http://www.china-un.org/chn/xw/t25607.htm,以及2008年5月27日刘振民大使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辩论会上的发言都强调了这一点,http://www.china-un.org/chn/lhghywj/fyywj/2008/t459182.htm,2009-07-26。 (34)《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在安理会通过利比亚局势决议后的解释性发言》,2011年3月17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zwbd_611281/t808039.shtml,2013-05-05。 (35)《王群大使在人权理事会利比亚人权状况特别会议上的发言》,2011年2月25日,http://www.china-un.ch/chn/hyyfy/t802369.htm,2013-05-06。 (36)《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在安理会关于利比亚问题会议上的发言》,2011年6月16日,http://www.china-un.org/chn/hyyfy/t831410.htm,2013-06-06。 (37)《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在安理会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的发言》,2011年11月9日,http://www.china-un.org/chn/hyyfy/t875607.htm,2013-05-07。 (38)杨洁篪:《共迎挑战共同发展: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2011年09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862501.shtml,2013-05-06。 (39)联合国网站,“关注北非局势”“叙利亚”部分,http://www.un.org/zh/focus/northafrica/syria.shtml,2014-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