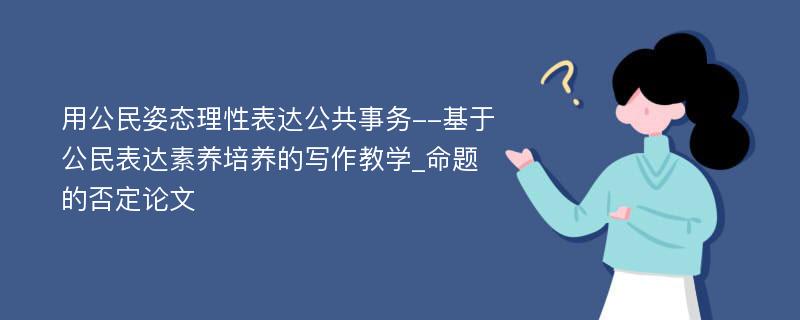
以公民姿态,就公共事务,做理性表达——基于“公民表达素养”培育的写作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素养论文,姿态论文,公共事务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社会的建设,对于当今中国的价值与意义,正在从少数思想者的卓识,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给我们的教育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语文教育与人的精神养育和文化构建息息相关,理所当然应该关注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公民素养的培育。不仅如此,语文教育还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参与公民素养的培育,在我看来,作为一门将语言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科,语文教育更应关注“公民表达素养”的培育。其中,写作教育更应发挥其专业性的独特作用。
公民社会是个表达社会。公民的表达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力量。但这个力量能否发挥和发挥到怎样的程度,则取决于公民的表达素养,包括表达的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表达的立场与态度、表达的能力与技术等等。如同公民社会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社会一样,公民表达也有着新的内涵与内容。写作即表达,写作教育应该关注这些新的内涵与内容,并且以此作为反思和改进当前写作教育的重要维度。
基于“公民表达素养”培育的写作教育,我将其基本内涵与内容概括为“以公民姿态,就公共事务,做理性表达”。
以公民姿态
公民的姿态,也就是写作者的公民身份与写作者的公民立场。
“代圣人立言”是传统写作教育的基本模式,写作者将自己虚拟为居高临下的圣人和绝对理念的占有者,以宣讲和布道的姿态阐发义理,抒发情怀,最典型的如科举写作。科举写作其实是主体缺席的写作,强势的选拔功能与专制的话语环境不由分说地遮蔽了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文化选择,一把生硬冰冷的标尺切割了千万个生机勃勃的生命。表达者义正词严,表达的内容却空洞无物,因为他说的都是别人的话。但也正是凭借了这种空洞,表达者往往以真理自居,以权威自居。鲁迅说中国少有“个人的自大”,而多了“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从表达的角度看,正是因为他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意志、情感与思想,他把自己淹没在“合群的自大”中,主体的缺席反过来增加了他虚张声势的底气。空话、套话、正确的废话、不用负责的话等等,与此不无关系。
价值绝对,主体缺席,以及由此造成的创造错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写作教育基本上延续了这个套路。革命政治的现实需要,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短缺的教育资源和急功近利的教育追求,都使得科举写作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检视一下几十年来的高考命题及写作,不难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一套高考写作,其实还隐约拖着一条科举写作的尾巴。即便到了今天,高考已经褪去了神圣与神秘的色彩,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国民教育的一个环节,而不再具备先前身份遴选与社会界定的功能,但科举“应制”的那一套作文模式依然能够大行其道,备受恩宠。一年一度的高考命题百花斗艳,但也有个别命题还依稀散发出科举写作和旧文化的酸腐味道,与高考在目前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意义与特殊地位很不相称,与新课改的先进理念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样的命题,批判名利思想,却消解了公民的权利意识;礼赞道德典范,却淡化了公民的自我意识;吟诵山林情怀,却消解了公民的社会意识;鼓吹隐忍与逍遥,却泯灭了公民的批判意识。命题的疏漏一经学生在写作中放大,其消极效应也就随之放大了。某高考作文《包容》的结尾,作者在分析了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要取包容之姿态后,这样写道:
其实天很蓝,阴云终要散;其实海不远,此岸连彼岸;其实草很绿,万物皆自然。其实,你不必担心太阳的光亮被遮住,你也不必担心人间有太多不平,包容那些阴郁,心中便有阳光,我们终将收获全部的美丽……
“其实……”这样的语气,是十八岁高中生的口吻吗?看破红尘,看透人生,看穿人世,这是世外高人的指点,还是得道高僧的说教?显然,这不符合中学生的人生体验与认知,本质上也不合乎公民社会对“包容”的理解。文章充满诗意和浪漫,唯独缺乏真实与理性。究其根源,在于身份意识(主体意识)的缺乏或错位。
作为表达主体,公民的表达应该独立而平等。公民不是群氓中无差别的“份子”,群氓的声音宏大,但却空洞、虚假,因为群氓的“万岁”与“打倒”都靠不住。公民表达意味着价值的独立判断与担当。表达的价值在于真实,说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真心实意(意志)、真情实感(情感)和真知灼见(思想),并为自己的表达负责。“真”是“公民表达素养”的基石,要做到“真”,就必须摆脱传统的“代圣人立言”的表达模式,将价值的选择权利交给学生,将生命的体验空间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写作中真正享受自我创造的乐趣,这是培养“公民表达素养”的第一步。
传统社会总是存在着圣人与愚民、暴民与顺民、臣民与逸民的鸿沟,因此,居高临下的说教,置身事外的逍遥,制造仇恨与暴戾的煽动,看破红尘的清高与超脱,甘为庸奴的宣誓与表忠,是那个语境的必然产物。站在公民的立场看,陶潜们的挂冠而去、弄臣们的小丑笔墨、士大夫们的天下情怀、黄巢们的“我花开后百花杀”,尽管都能在不同的侧面得到合理的历史解释,但无论怎样,都与公民社会的生活与精神存在着冲突。培养学生以公民身份表达,对于这些司空见惯的“中国式表达”,应该加以辨析和扬弃。。公民的表达,是独立自主的表达,是平等沟通的表达,是身在其中的表达,是自负其责的表达。
公民的身份意味着应按照公民的是非标准来表达。在写作教育中,我们常常鼓励学生“我手写我口”,抒写性灵,表现生命。但“性灵”这类常用概念太诗意、太抽象、太玄妙,似乎无所不包,似乎又空空如也,太难理解和把握。若问,违背道德的情怀是否也可直抒胸臆?很难作答。公民是人基本的社会身份,中小学教育“育”的那个“人”,首先便是“公民”,而写作教育的首要任务,便是培养学生以公民的身份按照公民社会的法则进行有效表达的素养。换句话说,这里的“人”,已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基于公民身份的具体生命。公民的底线在哪里,写作的底线就在哪里;公民的边界在哪里,表达的边界就在哪里。遵守法律、恪守道德、尊重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些都是公民的基本素质,也是我们写作与表达的是非标准。公民的标准,比起“圣人”、“接班人”之类的目标,要具体得多、明晰得多,也可行得多。
就公共事务
公民的立场意味着对公共空间与社会事务的介入姿态。以公民身份写作,首先要关注自己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关注现实的社会生活,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时代的脉动中发现表达的灵感与素材,在社会的矛盾中抒写真我的感受与思考。
传统中国是以家族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在国家和百姓之间,缺乏一个公共的社会空间,百姓们也缺乏公共生活的经验与意识,这导致了百姓对公共事务的淡漠,也导致了公民精神的缺失。传统的写作教学,总体上倾向于皓首穷经,在阅读与冥思中寻找写作的题材与主题。而到了八股文,则干脆在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彻底堕入了脱离社会、脱离生活的无物之阵。
当下的“写作教育”,在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的驱动下,越来越狭隘化为“作文教学”,写一篇文章,甚至是“应制”一篇中考高考作文,似乎成了写作教育的唯一主题。这样的写作教育,有意无意地隔绝了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切断了写作与实践的通道,它培养的只能是“酸文人”、“笔杆子”,或者“文曲星”,而不可能是一个关注社会且能对社会事务独立发言的现代公民。当下的高考命题,有意回避现实的社会问题而热衷于抽象的道德高论,回避真实的人生而作玄妙的哲理辨析,回避具体的问题而发宏大无用的议论,几乎是在逼使考生写空话,说假话,编废话。而回避现实、疏于实践的文章应制模式,催生了一大批“伪文学”、“伪文化”、“伪情感”、“伪议论”,矫揉造作、晦涩玄虚的文风大行其道。
现代公民的成长,只有在公共生活空间中才能实现。在当下文化环境中,试图将学生封闭在一个应试的环境中,将他们与真实的生活和生动的现实隔绝开来,事实上已不可能。教育不应该回避社会矛盾,回避阴暗,因为你在回避矛盾与阴暗的同时,将真实与真相也遮蔽了。恰恰相反,应该正视当下多元与开放的文化环境,并从这个环境中发现新的教育资源。若将现实的、充满矛盾与激情的生活引入写作教学,将真实的、复杂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纳入写作教学,将具体的甚至惨淡的生命聚焦于写作教学,一定能引导和激发学生的思考、辨析,学生也能做出理性的判断与选择。我相信,经过理性思考的道德才是真实的,经过自主选择的人生才是无悔的。
“就公共事务”发言,基本的教学思路应该是引导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就现实的社会事务,表达具体的态度与意见。对一切空洞、抽象、浮泛、大而化之的毛病,“具体”是一剂良药。近年来,有少数高考命题探索将现实的社会事务纳入写作范畴,这个尝试是值得赞赏的,尽管其中也有不少纰漏。这也在提醒我们,其实,单从命题的角度看,比起那些空洞的宏论或虚假的抒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难度相对更高,需要命题者更广更周全的知识与思想背景。比如2009年某省将蔡铭超高价拍得圆明园文物却拒绝付款造成流拍的事情作为议论的对象。这个命题将当下的社会事件纳入考察,要求对蔡铭超的具体行为作出具体判断。显然,这就不能靠空谈政治教条和道德教义来解决问题了,你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赞成还是反对;还需要一个具体的理由——为什么赞成或反对。
不过,这个题目值得商榷之处颇多。对于近代的屈辱,中国人有着特别深刻的记忆,对于拍卖这些文物表现出的朴素的民族情感与激愤,也事出有因。加上社会与教育的种种相关影响,我想,以一个中学生的思维和眼光,难免有人要赞美蔡铭超的赖账行径。题目中还刻意提到“有人称其为民族英雄”,这句话是不是有所“暗示”呢?这就容易让考生陷人情感与理性的两难境地。赞美蔡铭超,无异于赞美“恶意破坏规则”;否定蔡铭超,似乎又与朴素的民族情感相抵触。若命题者认为可多角度看待此问题,则命题者的立意出了偏差,因为蔡铭超的行为显然是非理性的。若命题者本来就意欲否定蔡氏的行为,似乎题目的开放度又不够。
提倡“就公共事务”发言,并不是漠视学生的私人空间和作为私人的写作。但对私人写作的关注,应该在公民生活的原则下进行。首先,私人写作毕竟是个人的事情,教育的介入要有分寸,这就如同父母不能偷看孩子的日记一样。另外,将私人化的写作纳入公共考察,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比如像“提篮春光看妈妈”这样的高考命题,个性色彩和情感倾向很浓,是个很私人化的话题。一旦置于公共视野,则感情的真伪难以判断,写作的真实性也难以甄别,以这样的命题来考察众多考生的写作能力,水准高低难以确定,公平难以保证,导向也就消极了。
做理性表达
“做理性表达”,既是公民表达的身份要求,也是“就公共事务”发言的态度要求。理性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也是公民素养的基本内容。
“理性表达”包括理性精神与理性思维两个层面的内容。理性精神,首先是独立思考,不迷信任何权威,包括书本、教条、经验、领袖、导师、救世主等等,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判断与选择;同时,质疑与判断要实事求是,要合乎规律与逻辑。在以博客、微博、BBS为代表的网络表达兴起之后,理性精神的欠缺已成人所共知的公害。非此即彼式的绝对化,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武断片面,随意推断,歪曲事实,以偏概全,上纲上线等等,无不昭示我们理性精神的启蒙是多么迫切。理性的缺失导致思辨力的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思维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见宋怀常《中国人的思维危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
理性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逻辑思维。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理有效。中国传统思维重感悟、重灵性、重混沌,可以说是“诗化的文明”,与重实证、重思辨、重逻辑的西方思维方式不同,这个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随着公共生活空间的不断扩大,传统的思维方式日益显示出自身的局限,需要加强逻辑思维的普及和教育。
当下的写作教学中,非理性表达很突出,集中表现在五个“效应”上。
1.权威效应。所谓“名人开会,名言荟萃”就属此类,这是典型的非理性表达。传统文化有浓重的圣人情结和偶像崇拜,似乎他们的言行举止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与意义。有外国学者称中国为“格言社会”,意谓中国人喜欢依照格言、标语、口号的教导来行事,喜欢模仿偶像来安排自己的人生。名言警句的泛滥成灾,显示出思想的惰性与思维的僵化,也反映了主体意识的欠缺和自我价值的矮化。
2.大众效应。“大家一致认为……”,“众多事实证明……”,“众所周知……”,使用类似的语句,无非是想借“人多势众”的习惯心理来回避对问题的正面讨论,本质上这是一种“愚民的专制”、“大众的压迫”。借群众的名义与借权威的名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非理性的表现。
3.事实效应。人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却不曾想到,那些堆砌材料与事例的文章,可能是最缺乏说服力的文章。人类社会之复杂,就算是最荒谬的论点,或许都可找到相应的事实来呼应和印证。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理解,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迷恋事实,单靠事实雄辩而缺乏明晰的理论辨析,这样的结论是靠不住的。
4.诡辩效应。一种庸俗的辩证法在我们社会生活中颇为流行。这样的诡辩可用“虽然……但是”来概括。比如关于“汶川大地震”的一段诡辩:
“汶川大地震”在一瞬间夺取了数万同胞的生命,让数万家庭妻离子散,让多少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这是一件多么让人伤痛的事情!可是,这也给落后的西部带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崭新的医院、学校和住房将会在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一个崭新的西部将会崛起。(典型的“虽然……但是”式表达。“可是”后面的内容,似乎是在赞美地震:地震来得真好!)
5.眼球效应。已故学者王元化说他“最怕读两种文章,一种是‘惊听回视的翻案文章’,一种是‘意在求胜的商榷文章’”。“惊听回视”的文章如果货真价实,倒也振聋发聩;但若虚张声势,则费力也是枉然。这种追求轰动与惊悚效应的表达颇有市场。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歪曲事实,戏说历史,水煮经典,玩弄辞藻,这样的表达对写作教育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觑。
将此类非理性的表达及恶劣文风与社会生活做一些深层次的联系,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很多深层次的有意味的联系吗?非理性的社会思潮、非理性的社会行为、非理性的公共表达,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是司空见惯。在一波又一波的非理性浪潮中,我们需要确认一个共识:理性表达,绝不止是写作的需要,从更深层次和更长远看,更是公民社会的需要。
写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关涉人的价值观和精神取向;写作是一种认知活动,关涉人的实践与思维;写作是一种创造活动,关涉人的多种能力与素养。“以公民姿态,就公共事务,做理性表达”,强调在写作中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在写作中培养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与能力,在写作中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思维能力。如今的写作教育,可谓积重难返,以“公民社会”的建设来促推写作教育的革新,也算是一种思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