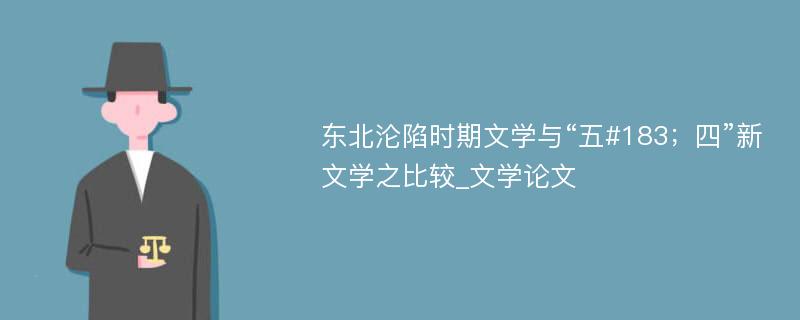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与“五#183;四”新文学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时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虽然比“五·四”新文学迟了十二年时间,但其所走过的道路却大体上是相同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同之处。把它和“五·四”新文学做一些比较,会使我们从中看出一些新的问题。
继承不是单纯的承接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从性质上看二者是相同的。那么,这之前的文学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文学中有一些现象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
一是,从1919年到1930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东北新文学没有很快地发展起来?当时,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开始兴起,如启明学会在《新民意报》办副刊《启明旬刊》、白杨社创办《白杨文坛》等;安怀音的文章《文学与时势》和《文学家与革命家》等文,都提倡了文学革命。这些,虽然对东北的新文学有一些影响和推动,但终因当时的文学形势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以新文学革命还是中途夭折了。
二是,来东北宣传新文学革命的人不少,其中有党派到东北来做地下宣传工作的,如陈凝秋(塞克)、安怀音、李震赢、韩乐然、楚图南、冯至等;有到东北讲学的,如徐玉诺、穆木天等;还有来东北宣传文化工作的,如恽代英、萧楚女、叶圣陶等;有专门来东北办报的,如关向英到铁岭创办《铁岭日报》;甚至瞿秋白、胡适等人物也来过东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讲述新文学运动。这些对东北新文学革命不能没有影响,但都没有使东北新文学很快地走上正途。
三是,在这段时间里有些文学创作也出现新的文学成果。如赵鲜文的《昭陵红叶》(小说散文集)、宋树人的《樱花第一枝》(创作集)、凭汝的《风纹》(小说集)、张露薇的《情曲》(诗歌集)、周飘渺的《落寞之笑》(诗歌集)等。这些文学是否是新文学,是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当然这些文学作品属于东北新文学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们不但承接了“五·四”新文学,而且也确实改变了旧文学中那种文言和八股气。但是,我们却不能认为它们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由于它们不仅脱胎于东北文化基础比较落后的现状,而且其本身的社会功能和导向人生的作用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没有真正成为人民所必需的。
而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学有着相同之处。“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时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且人们尤其知识阶层的人们有着强烈的要求,他们从1918年就有了实际的创作。东北的新文学,初时除了一般的响应外,整个的文学界没有文学要革命的迫切感,因此创作出来的只不过是些应景的文章,只要看一看发表新文学作品较早和较好的《盛京时报》副刊上的一些文艺作品,就会知道它们的成色了。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不甚关心,多数人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东北的文化层次本来就低,这样,对文学感兴趣的就不多了。可是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情形就绝然的不同了。不要说知识分子关注着文学,就连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对此也另眼相看。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主要原因是人们切身感到文学是一种需要。在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当时,东北的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起来抵抗,而敢于站出来第一个进行抵抗的却是文学。在“九·一八”之夜我们的记者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枪声进行采访,记下了沈阳沦陷的真实情形,揭露了日军的罪恶。并把写好的稿件当即寄出,寄往关内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发表,接下去还有十几篇散文也登在这个刊物上。这样,首先是文学这种形式冲破了不抵抗主义的牢笼,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并改变了人们以往的印象,真正的成为了人民的文学。也就是说,文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真正代表了人民同日寇进行斗争。
在关内《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散文有《讣闻》(徒然著),是叙写沈阳沦陷的情景;《铁蹄下的吉林》(绿波著,即姜椿芳),是写吉林为什么沦陷得那么快。此外还有写日本强占东北土地的,在东北设赌场开烟馆的,伪满洲国内部你争我夺的,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的,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的。杜重远的《别后》(收入《锦绣河山》)特别提到马占山领导东北人民进行的威名远扬的江桥之战。马占山原系国民政府任命的黑龙江省主席,在日军进犯之时,他通电全国,表示“大敌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宁可丢掉官职与人民一起同日军进行斗争。他的行为感染了许多人。四川万县一位苦力工人,每月工资只有两元钱,但他每月拿出一元资助马占山抗日。这表明东北的抗日斗争已经超越了东北的界限,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
如果说《生活周刊》因发表了东北的文学作品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的话,那么,东北的报刊发表反日的作品更引起了东北三千万人民的欢欣。在伪国务院办的《大同报》上,中共地下党员创办了《夜哨》副刊,发表的作品大都具有进步倾向。作品中有反映日军占领齐齐哈尔时的全城人民的逃难(《山沟杂记》),有描写机关车在哈尔滨市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压死城市居民的情景(《臭雾中》),有表现在日伪高压下纱厂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象与猫》),还有高唱着《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吼声(《两个阵营的对峙》)……然后是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文艺》和齐齐哈尔《黑龙江民报》文艺副刊《芜田》上发表的文艺作品,都具有强烈的反满抗日的内容。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赞颂了抗联战士英勇杀敌的情景,萧红的小说《看风筝》描写了农民领袖刘成的形象,其他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也都锋芒毕露,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日本侵略者。这时,东北人民成了历史的主宰,也成了文学的主人,他们创造着反侵略战争的历史,也演绎着文学的兴衰。也就是说,这时的文学真正成为了人民的文学,人民文学才谈得上继承光荣传统的问题。
综上,明确了一点,即继承不是单纯的承接。文学的继承只有当文学真正成为人民文学的时候,后一代文学才能继承前一代文学的光荣传统。“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九·一八”前的东北文学是一个过渡时期,即由一般的文学转变为人民的文学的过程,这里包括作家世界观的转变,包括社会对文学的影响而使它逐渐成熟为人民的文学。东北新文学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很快地成为了民族的抗战的文学,因此可以说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光荣传统。
相似不是简单的重复
世界万物有许多是有相似之处的,但不管如何相似都不是简单的重复,文学之道也同此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就文学革命而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又各有其独特性。
(一)社团和流派。当新文学革命即将到来之际,文学社团的创办是相当多的,这预示着新文学革命就要开始了,“五·四”新文学革命是这样,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也是这样。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首先诞生的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接着是语丝、莽原和未名社,还有弥洒社和沉钟社,这以后文学社团就更多了。充分的表明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由青年组成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物也在全国各地蓬勃地滋生起来。茅盾先生曾经统计过,从1922年到1925年之间,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多种,他说:“我未尝有意地去搜集,因此实际上从民国十一年到十五年这时期内全国各地新生的文学团体和刊物,也许还要多上一倍。”(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这种狂猛的文学大活动是随着民主革命的高潮而来的,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但尽到了当时文学的战斗任务,而且为以后的新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社团,大体上也和“五·四”时期的文学社团相似,在1932年围绕着哈尔滨“牵牛房”的一伙文学青年,虽未正式起名文学社团,但确实具有文学社团的性质。主要成员有金剑啸、萧军、萧红、罗烽、白朗、舒群等。他们先后创办的文学副刊《夜哨》、《文艺》和《芜田》都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文学作品。如果说“牵牛房”成为第一个文学社团的话,那么1933年初成立的冷雾、飘零、新社和白光这四大文学社团,就是第二个层面了。据《满洲报》于大同二年十一月三日统计,除以上四大社团外,还有二十多个文学社团的成立。这些文学社团,不仅使日本侵略东北时遭到破坏的新文学得以迅速恢复,而且为东北新文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自1936年以后,由于日伪对文化统治的加强,金剑啸被杀害,萧军萧红等人的逃离东北,使得大多数文学社团不能生存,有的自消自灭,有的隐姓埋名。
就在这种情形下,“艺术研究会”(《明明》前身)成立, 并于1937年创刊了《明明》杂志, 使得即将毁灭于日伪之手的东北新文学又重新亮出了自己的旗帜。《明明》不但顶着日伪的刺刀诞生,而且从一卷四期起成为东北第一个纯文艺刊物。发表的一些文学作品,更是大放异彩,其中有纪念鲁迅逝世的专辑,使鲁迅首次在国破家亡的沦陷了的东北与世人见面;还有酷似鲁迅杂文的作品的出现。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流派也与“五·四”新文学差不多。“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开始是互相对立的,创造社中大部分人外语甚好,受外国文学影响很大,因而对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敏感,文学研究会则抱着“文学是人学”的现实主义理论同创造社争论。东北文坛当时有艺文志派、文选派、文丛派、作风派和学艺派。文选、文丛合二而一统称文选派。在当时,艺文志派和文选派是两大派别,而且对立尖锐,斗争激烈。因为艺文志派的主要人物古丁被文选派的主要人物山丁说成是“奸细”之后,于1941年辞去了伪国务院的官职(统计局事务官),办起了艺文书房,专事于文化工作。两派争论的结果虽然没有平和,但到后来却因文化统治的高压而逐渐的冲淡了对立的气氛。这两派和“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是有相似点的。开始都是由社团兴起,中间因为抗日方法有别而展开争论,艺文志派成员大多精通日语,与创造社极相似,后来两派因各种原因趋于缓和而殊途同归了。
社团和流派的相似是外在的现象,其实质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因为“五·四”时期有当时的历史环境,那时虽然也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问题,但整个国家还没有象东北那样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民族斗争就不那么明显,反封建是当时的主要任务。而“九·一八”以后的东北却不同,只有舍生忘死地同日伪斗争,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失去的江山,因此沦陷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民族斗争。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是社团还是流派,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大局。因此相似也是有区别的。
(二)由文言向白话过渡和文艺大众化。这个问题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重要问题。用现代人的语言表现现代人思想的文学就是新文学,反对用旧思想和死文字的封建文学,这其中的死文字就是指的文言文。鲁迅先生针对反白话的人为“现在的屠杀者”,说他们“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注:《热风·现在的屠杀者》。)陈独秀对待白话文有明确的态度,他在回答胡适的信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因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注:答胡适之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这种坚决的态度, 也就使白话为正宗的文学得以顺利的发展起来。陈独秀一方面以《新青年》主编的身份极力倡导,另一方面他全力团结象鲁迅、钱玄同那样的革命先驱者,所以白话文学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的杂文《热风》和《坟》,小说《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等,郭沫若的《女神》等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是新文学的结晶,也是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重要成果。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不仅是发展新文学的要求,同时也是进一步地由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简而言之,文艺大众化就是文艺的普及问题,而普及文艺首要的是语言,文艺的大众化要求语言不仅是白话的,而且是通俗易懂的。
东北沦陷以前文学由文言向白话的过渡是比较缓慢的,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文学作品,半文半白的语句,残缺不全的标点符号,空洞无物的思想内容,比比皆是。可是到了东北沦陷以后,文学作品中除了标点符号有的不太符合标准外,其他均一改往日的容颜,白话是真正的白话了,内容因多半是反映东北人民的苦难和对日本侵略的反抗而不再空洞无物了。就是使用的方言和行话也都有注明。如《大同报·夜哨》副刊发表的小说《路》,是写东北各地山林土匪纷纷奔赴抗联进行抗日的故事,其中用了许多土匪的行话,但因都有很好的注明,所以读起来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到了东北沦陷时止,由文言变白话已基本完成了。按照鲁迅的说法:“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这文艺大众化的提倡,不仅要文言变成白话,而且更要语言大众化。东北沦陷时期的一些作家,在大众语的运用上没有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底层,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所以对使用大众语没有隔离的感觉。翻阅金剑啸的作品,再看萧军和萧红合著的小说集《跋涉》,就会了解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已经初步的形成了大众化。
但是,二者除了相似之外,还有不同之处。“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的文言变白话,是开山始祖,万事开头难,这是东北沦陷时期文学革命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它毕竟是受“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影响,有了前车之鉴走起来容易得多。文艺大众化问题,在东北沦陷时期主要是解决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五·四”时期的作家,要解决深入生活,转变感情,改造世界观的问题。两个时期各有侧重,并不重复。有关这方面的文学成果也是很丰富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除了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外,叶绍钧的《倪焕之》,茅盾的《子夜》、《春蚕》,王统照的《春花》和《山雨》等,都是当时的重要成果。东北沦陷时期金剑啸的长诗《兴安岭的风雪》,山丁的小说集《山风》,古丁的杂文集《一知半解集》和《谭》等,也都是很有成绩的。
(三)描写黑暗。“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以后,在中国的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描写黑暗的风气。作家选取的题材,确定的主题,运用的方法和使用的语言,都与描写黑暗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叶绍钧曾说过:“现在的创作家,人生观在水平线以上的,撰著的作品可以说有一个一致的普遍的倾向,就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反抗,最多见的是写出家庭的惨状,社会的悲剧,和兵乱的灾难,而表示反抗的意思。”(注:《创作的要素》。)茅盾则更强调“新文学描写社会黑暗”要“使人读后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注:《什么是文学》。)。要求年青的文学工作者,要注视社会问题,创作出反映痛苦社会背景的新文学作品,因为这是“五·四”新文学的主潮,所以当时的文学工作者都特别关心并努力实践着。
无独有偶。与“五·四”新文学革命相对应的第三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也有个描写黑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张“描写真实”与“暴露真实”的作家山丁说:“‘暗’——这是在满日系批评家一致对满系作品的观念批评。我们读了人家的评文仿佛有许多话要辩驳,其实辩驳也无益处。八不主义(即《艺文指导要纲》发布之后日伪当局对文艺提出的种种要求,其中就有不准写黑暗——笔者)不是明晃晃的颁在那里吗?有时也自己解剖自己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明朗起来呢?我们是活在以写穷人为可耻的土地吗?秋萤的作品是刻画暗的。这暗则是‘明’的希求,是‘明’的征候,我们的作家仿佛是一辞送葬的歌手,倘能唤出新的,相信也会奏出健康的明朗的声调的。”(注:《〈去故集〉的作者》,摘自《满洲作家论集》。)看了山丁的评文就会明白,日本侵略者是很反感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描写黑暗的,山丁所说的日人评论家指的是大内隆雄。他翻译了山丁、古丁等东北沦陷时期作家的许多作品。同时他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指手划脚。山丁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给以无情的讽刺,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沦陷时期的作家。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在描写黑暗上虽有相似,但也有不同。“五·四”新文学的描写黑暗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而且要求青年文学作者要深入到工农中去,来一个脱胎换骨的世界观改造,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描写黑暗是自发的,作家们自觉地把描写黑暗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去揭露日伪,打击敌人。只是有的作品把现实描写的更严重,以显露民族斗争的艰巨性;有些作品在行文中,暗指“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的特征,如机关车、仁丹胡等,以表明其抗日倾向。
相同并不雷同
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和“五·四”新文学宏观上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从两个不同时期产生的作品可以看出。
“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产生了一些宏篇巨著,如茅盾的《子夜》是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揭示封建社会的垮台和农村的破产的主题,震撼了几代作家,作品巧妙的构思和精心的设计也令人惊叹不已。作品中民族资本家丝厂老板吴荪甫是个中心人物,其他人物围绕他而写。吴老太爷由农村进入城市后的死亡,象征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投机市场使民族工业的倒闭和农村的破产,又使人民的生活没有了着落。赵伯韬是当时的金融巨头,他靠帝国主义发家,当然也就操纵了上海的经济命脉。吴荪甫的一败涂地有力地实现了作品的主题。除《子夜》外,短篇小说《春蚕》影响也比较大。
东北沦陷时期作家山丁的短篇小说集《山风》中的一些作品,描写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后的农村破产的情景。其中《织机》是写手工业的织布作坊的破产。日本入侵东北后,仰仗工业之先进,挤垮了中国的民族手工业,日本的资本家垄断了市场,使东北落后的手工业陷入了破产的困境,于是抵制日货的运动使这场危机更加突现出来。“无数个机房,就集聚了约摸五千多只笨木机,六千多机匠”,现在是帮散机亡。“机房仅仅剩不到二百”。而且在这不到二百的机房中,日人开办的洋行不供给线,也只好停产。这时日人的洋行又趁火打劫,最后使机房倒闭,机匠改行,手工业工人失业,民族工业破产,工人不得不在死亡线上挣扎。这篇作品比不上《子夜》的构思庞大,但民族工业的破产还是传达出来了。作品中字面上虽然没有提到日本的入侵东北,但读后是能够心领神会的。另一部描写民族工业破产的是长篇小说《绿色的谷》。它写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在东北搞垮民族工业进行了大量地掠夺。往深山密林处开设铁路,而且是用机枪和电网保护着。铁路开通之后,从东山里大量地拉出煤炭木材,然后运往日本,这样大肆的经济掠夺使东北的民族经济遭到破坏,而且掠走了东北的丰富的资源。作品中有一段话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这段话是:“火车从广漠的大平原上滚进这个充满了烟雾的市街,它以怪兽一般的吼叫震碎了这市街的春梦。谁都知道,使这市街繁荣的脉管,便是一年比一年更年青更喜悦的火车,它从这里带走了千万吨土地上收获的成果和发掘出来的宝藏,回头捎来‘亲善’、‘合作’、‘共荣’、‘携手’……”这段话在作品出版时被扯页处理。这一长篇没有《子夜》的恢宏,但它所反映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是逼真的。
另一作家古丁的作品也有与“五·四”新文学时期相同的地方。如小说《玻璃叶》与《春蚕》颇有相同。《玻璃叶》写蚕村农民盛衰的历史。霍家峪自到东北开荒占草以来,就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世道,“但是他们似乎都记得,他们的祖宗并没喝过糊涂,也没吃过树叶子”,可是如今,放了四十七年蚕的霍有金,却因连糊涂和树叶子都填不饱肚子而凄惨地死去。对于他的死,妻子和儿子“两人都没有眼泪”,为什么呢,是不是有点不尽人情?不是的。“因为山上山下,天天不知有多少人这样死掉,并无人掩埋”,而他霍有金毕竟还有妻子和儿子埋葬,这也就是万幸的了!这种毁灭人性和人的感情的灾难,不是比毁灭人的肉体更深重吗?这一点是《春蚕》中老通宝的时代所不能比的。尸骨遍野的惨景,连树叶子都吃不上的境况,不正是日本侵略东北后的农村写照吗?作家古丁不仅在小说的深层背景上展现了中国东北的民族灾难,而且还通过杂文把矛头指向日伪政权。在1936至1937年间,正是东北文坛大饥馑时期。古丁在《明明》和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杂文,并于1938年出版了第一本杂文集《一知半解集》,给当时死寂般的东北文坛以莫大的鼓舞和活力。这本杂文有两大特点:一是言别人之不敢言。日伪的文化统治是相当严酷的,颂歌可以唱,真言不能说,轻者关进监牢,重者杀头示众。在这种情况下,古丁赞扬了鲁迅的战斗精神,批评了日伪当局。说在伪满洲国要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首先就要象鲁迅那样成为不容于当局的大战士,唯其成了大战士才能成为鲁迅似的大作家。而伪满洲国“连买《辞源》都犯罪”,上哪去谈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呢?“满洲倘还需要文艺,至少得给予作家预备军(读书人)以读书和思索的自由”,那种“只许堆笑颜不准做哭脸,只许发赞声不准泄叹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表现了古丁的无畏精神。二是尖刻、辛辣的讽刺。连买辞书都犯罪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尖刻、辛辣的讽刺,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配谈产不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呢?讽刺的尖刻和辛辣,主要是在语言上。鲁迅杂文的语言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他自己也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注:《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在东北沦陷时期,古丁是学习鲁迅杂文的最好作家之一,他不但语言学的象,就是风格也酷似鲁迅。请看《鹦鹉和文人》一段:
有所欲言,才有所写,所谓“言”并非学鹦鹉;鹦鹉虽言,只是出于口未尝发自心。因为她的言,句句是主人传授的,其声音虽比主人清脆而娇媚,而脖颈上却系着一条精致而华美的丝带和银链。因此她的风彩和态度也许会漂亮而高傲,但至多不过是早晨说“早安”晚上道“晚安”,顺应着时辰说几句吉利话而已。
我们的文学,自从官也招标商也收买的风气起来,这“吉利话”跟着洋溢四野,文坛也吉利,天下也吉利,宇宙也吉利……这种文学给她创作个名称,曰:“吉利文学”;这种贩卖“吉利文学”的文士给他创作个名称,曰:“吉利文贩”。
文士因为金钱有时会成为鹦鹉的同类,文士的言因为金钱有时会发出和鹦鹉一样的声调。
这一段文字,把个为日伪政权唱颂歌的文人讽刺得体无完肤。鹦鹉学舌,不管她怎么会说也只能是“学舌”,没有一句话是她自己想说的。在伪满洲国的一些御用文人中,象鹦鹉学舌一样的文人还少吗?日伪说“一德一心”、“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他也跟着学说一遍,象这样的“吉利文贩”跟鹦鹉学舌有什么两样呢?有人说古丁具有“强烈古丁杂文风格”。我以为,若是没有鲁迅的杂文,也未必会有古丁杂文风格,古丁杂文的风格,完全是学习鲁迅的结果。
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里,文学创作与“五·四”新文学相同的不只山丁和古丁两位作家,其他如金剑啸、王秋萤等的作品也有与“五·四”新文学相同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即或是有相同之处,因东北是沦陷了的国土,特殊的环境也会造就出来一种全新的文学,沦陷文学的本身实质上就是殖民地文学,在这一点上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最大的不同。这种殖民地的环境和地位,就使得在东北很难产生“五·四”时期那样的伟大作家和作品。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鲁迅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子夜论文; 散文论文; 杂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