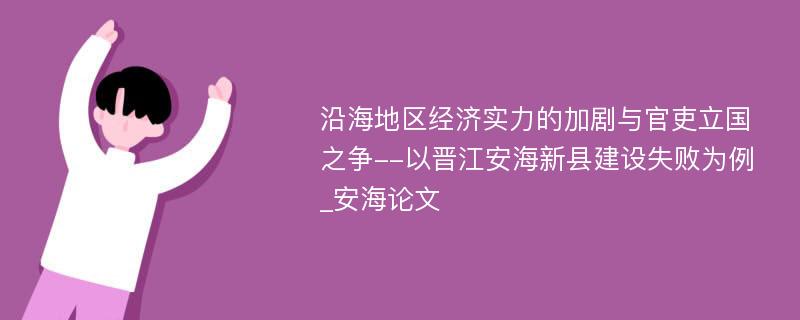
海疆经济分量加重与设县中的官、私较量——以明晋江安海新县设置失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县论文,海疆论文,晋江论文,为例论文,分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5)05-0170-11 DOI:10.13718/j.cnki.xdsk.2015.05.023 一、明安海海港兴起与海疆经济分量的加重 民间海商的海上贸易活动驱动着安海港的兴盛。早在宋代,商贾们造船出海,将“唐货”换成“番货”,转销国内。因此,宋代泉州市舶司已派官吏来管理安海港市贸易事务,“州遣吏榷税于此,号石井津”[1]。安海与石井隔海相望,近在咫尺。“斯时,海港千帆百舸,乘风顺流,出入海门之间。渡头帆樯林立,客商云集,转输货物山积,镇市店肆罗列,百货杂陈,举凡越裳翡翠,南海明珠,无所不有,丝绵锦绮,氇毛靴袜,无所不备。镇市之繁荣,不亚于一大邑。”[2]明代,泉州港衰落,安海港更进入其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它逐渐发展成跟漳州月港齐名的私人海外贸易中心之一,其地位于泉州平原的南侧,北靠厦门湾。苏琰说:“安海距泉郡五十里而遥,其地北阻府会,南控漳潮,乘风破浪,诸岛夷仅在襟带间。”[3]174其地理位置对发展海外贸易有一定的优势。《安海志》中说安海的形势为: 安平,泉南一大都会也。上接郡垣,下达漳、粤;西扼九溪、黄冈之险,南通金、厦、台、澎之舶。 其地势远自三峰、毫光,转东北十里为六都内坑、熊山,迤逦南行为七都桐林、前埔、曹店;自是而东曰佳坂、庵前,接以内市、浦边,障安平之左臂。而由内市南行则有庄头、井林、萧下,南至东石,以踞海门之东。其西曰古田、后萧接以曾庄、曾埭,障安平之右臂。而由曾庄南行,则有南安之朴兜、江崎至石井,以踞海门之西。是则东石、石井,实安平之二巨螯也。 其水道则由晋江东南隅诸溪流,南汇于石井江以达大海:其南安诸水则自九溪东折于大盈桥入溪尾、曾埭而注于海,与晋江水大会于海门,以通天下之商舶。[2]卷二,山川,p10 安海港居围头湾内。循围头澳而西,经丙洲、塔头、潘径,即达安海港。入港处有白沙、石井两澳东西对峙,是为海门。舟入海门,海面豁然开阔,港岸弯深,随处有避风良坞。旧有后垵湾者,在镇东里许,为天然避风港。海舶遇风,恒趋此避险。……安海江海流平,出入无风涛之险,较之泉州湾口江海争流,风高浪急,舟行有横风逆流之险,安海港尤为航海者所欣所向。[2]卷十二,海港,p118 但在明初的时候,江夏侯汤和整饬海域,安海不算冲要之地,还将元代设于该地的巡检司移往浯屿水寨:“洪武二十年丁卯(1387),江夏侯整饬海域,以安平不系冲要,乃移本巡检司往浯州屿水寨,而以同安陈坑巡检司兼守本处。初未设官,随时以指挥、检校、县丞,千户等宫委镇。”[2]卷一,沿革,p3明政府在此处缺乏直接管辖的机构,却为私人海上贸易兴起提供了方便。《闽书》说:“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贾夷,差强赀用。”[4]也有“晋江人文甲于诸邑,石湖、安平番舶去处,大半市易上国及诸岛夷,稍习机利,不能如山谷淳朴矣。然好礼相先,轻财能施,曷可少也”[5]。迄至嘉靖年间,安海已有了一定的规模:“本都数千人家,粟帛之聚,甲于乡邑。”[2]卷十二,海港,p127又有文献称安海是“东南巨镇,朋比阗联,万有余家”的大镇[6]。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7]这些史料都说明安平是嘉靖年间福建主要走私港口之一。 万历年间,安平镇经济进一步繁荣,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民)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8]显然属于跨国贸易,安海商人采购来浙江丝绸、江西瓷器、四川药材和本省府县的山货、海味、手工业品、土特产,汇聚之后,浮海“贸夷”,安海成了海商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从安平港载运出去的货物包含了丝、绸缎、锦绮、陶瓷、药材、铁器、糖品、果品等,运销到柬埔寨、占城、暹罗、渤泥、三佛齐、吕宋和日本等国。安平商人常驾船到三佛齐与阿拉伯商人进行交易。换来的钱再买成胡椒、香药、犀角、象牙、珠贝等,运回安海再销往各地,安海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8]。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安平镇已是“室家鳞次,阛阓栉比,肩摩毂击,骈骈阗阗,昔村落而今粤区矣”[3]174-175。 因为明政府推行“海禁”,故导致安平镇繁荣的主因是海上走私,由此而形成的安海商人集团渐渐闻名于全国。“福地素通番舡,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盖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此皆海澳僻远之处,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明代朱纨曾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获窝家之利。”[9]私人海上贸易几乎都控制在地方的强宗大族手中。他们从明中叶至明末不断发展,对外开拓,势力越显强大。李光缙说:“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兄伯十二,遂从人入粤。尠少有诚壹辐辏之术。粤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贷,用是致资。时为下贾。已,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言,收息倍于他氏,以故益饶,为中贾。吕宋澳开,募中国人市,鲜应者,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10]223这一段文字很实在地描写了一个安平商人发财的经历。李光缙感慨地说:“吾温陵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锋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壶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概也。”[10]225去吕宋贸易很快在安海形成一股风气:“自吕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如《安海志》中所记叙: 嘉靖间,安平商人李寓西,即曾徙南澳与夷市,因长期与夷人交,能夷言,乃倍获其利。甚有富豪贾商,勾结官吏,私造海船,自雇船工,满载货物,迳自往日本、吕宋、交趾等地,其瞒天过海,各有妙法:或就海港附近小港澳,轻舟分散出海,以就海舶转运;或贿赂官吏,假给文引以渡关卡;或借官许通贸之琉球为转口再运往日本或南洋各地,以牟厚利者。更有大者:集帮伙,结船队,置武装,载私货,窜行海上。官称之为寇,却莫能制。若郑芝龙者,曾以安海港内之石井澳为踞点,集海船千百艘,纵行海上,成为东南海上之一大海商。安平商人,或乞其符令,或借其庇护,乃得畅行海上而无阻。其始,仅船数十,至天启六年丙寅(1626)而有一百二十艘,次年突增至七百艘,崇祯间竟达千余艘。明朝对其发展之快,自叹为:“彼以恤贫诱人,我以禁粟驱民。”[2]卷十二,海港,p122-123 众多的番商亦有驾船前来贸易的。嘉靖年间,“番舶连翩径至,近地装卸货物。”[11]黄堪《海患呈》说:日本商船一来就有数十艘,碇泊安海港海门白沙。“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云集于市。”本地人民“亦有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2]卷十二,《海港》附文,黄堪《海患呈》另据《同安县志》记载:“碇于晋南之白沙头,与漳、泉人互市”的日本船,最多曾达“数千艘”。隆庆间(1567-1572)吕宋开洋,募集华人为市。安海商人李寓西、陈斗岩首航吕宋贸易,获得巨利而归。从此,包括安海在内的沿海居民纷纷下海去南洋,有的便定居下来,成为华侨。到明末安海的地方社会差不多已被郑芝龙海商势力完全把控,郑氏拥有庞大的商船队,此时,安海“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省城”[12]。外国人称其为“著名的商业城市”。一些强宗大族链接官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科举多有斩获。安海作为晋江的一个重镇,有明一代,登进士者21人,登乡榜者71人,蔚为大观。[2]卷一,沿革,p8安海的地方士绅与海外贸易存在深刻的联系,他们积极谋求跟官方合作以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走私港口勃兴,具有科举功名的士绅阶层参与到海外走私贸易活动中,逐渐形成巨大的经济力量,他们试图与地方官府形成联盟,从而在地方社会控制中掌握主动权。提出设县动议并谋求占据主导权是许多有着海外走私贸易背景的士绅们试图达到的目标。 二、嘉靖年间安海设县之官私较量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安海地方出现了倭患的冲击,这种外来力量加剧了安海地方社会的混乱状况。嘉靖年间黄堪的《海患呈》说: 本年(嘉靖二十四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有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始则两愿交易,向后渐见侵夺。后蒙本府严禁接济,是以海沙罢市。番众绝粮,遂肆剽掠,劫杀居民。鸣锣击鼓,打铳射箭,昼夜攻劫,殆无虚日。去海二十里乡村,挈妻提子,山谷逃生。灶无烟火,门绝鸡犬。……至本月十九日,夷船闻风逃去,居民复业。[2]卷十二,《海港》附文,黄堪《海患呈》 在黄堪眼里,嘉靖年间安海地方因为港口走私贸易的发达,商品汇聚,人口增殖,市井繁华,但他认为这里地方社会秩序混乱,一方面私人海商集团坐大,不服政府管理,另一方面是地方富庶引起山海流寇的觊觎。 迩来生齿浩繁,众志难一,流寓杂处,机巧居多。况县治去远,刁豪便于为奸;政教未流,愚民易于梗化。况本都数千人家,粟帛之聚,甲于乡邑。山海寇贼,素来染指,实可寒心。又有奸民诡告良民为番徒,以塞清议;又有把寨妄申良民为番徒,以图需索。鹿马不分,玉石俱焚,是皆海寇致害良民。[2]卷十二,《海港》附文,黄堪《海患呈》 黄堪并不敌视安海经济的发达,但他觉得这时的山贼和海寇严重危害了当地的正常秩序,奸民诬告良民,贪官诬陷良民的现象均存在,理应设置相应的政府机构,对此做细致的处理。这一认识得到了此时负责福建军政事务的朱纨的积极呼应,并首次提出在安海设县的主张。《甓余杂集》中记载: 臣惟安海地方,虽属晋江、同安二县,而离县太远,政令不行。南安一县,迨近府郊,又无城池,人不数姓,不成县治。……若以南安官司移置安海,而以南安附近晋江、同安都图割附该县,以安海都图割入南安,不过转移之劳、营建之费,而一府之经画伟矣。[13] 明代南安县城在丰州,离泉州府城不过十里,且无城池防守,人口亦不多。所以朱纨提出可撤销南安县,重新分割里图另立安海县,并在原南安县内设府通判以控制安溪、同安、晋江各县。“或以安溪离府太远,不可无南安。然有南安,安溪固自远也。南安数姓,惟黄族为巨,为守望谋,亦不过移一腹里冗设巡司。使该府巡捕通判在往住札,则南安、安溪等处皆有控制矣。”[13]《明世宗实录》中亦记载了中央政府所理解的朱纨的主张:“国初海禁甚严,地方宁谧,迩年豪民藉势通夷,当事者莫敢诘难,动为掣肘,惟庙堂烛其奸欺,不为摇动,然后法禁可立,一明宪体,言都御史职在总宪,比御史周亮奏言:城池、仓库、钱谷、甲兵、刑名、狱讼及官吏臧否,利病兴革,皆不得与。则所谓宪职者安在?请申明之一定法守。言浙福守巡诸臣既有专官,继又设粮储、屯田、巡海等道,职守参差,互相推诿,今宜檄分巡各道:按地分驻,兼综诸务。专事者惟理其绪而稽成焉,苟一道不治,专事者乃躬督之一定要害,闽之要害若月港,首宜创邑。安海原属晋江、同安二县,离县太远,南安迫近府郊,地偏民寡,宜移治安海,割其地近晋江同安者附之,二县而以安海割入南安,似为两利。桐山、梅岭,闽之尽境,行部罕至,宜增置漳州通判一员,专驻梅岭,置福宁州同知一员,专驻桐山,一除恶本,言通盗势家往往窃发文移,预泄事机,及有捕获,又巧昡真赝,此恶本之难除也。请自今地方失事即重创守土所司,俾知惩戒。一重决断,言规画多方,奉行者鲜甚。或持异论以阻挠之,宜令各守臣持议坚确,凡事果行,无惑两可。”下兵部覆议,纨所陈多忠愤激切,其言定法守,欲以专事者受成,似非分职之意。至于海滨立县增官亦嫌更扰。然其议守巡分驻要害,禁诘海滨,实有益也。[14]考察史料,还发现嘉靖年间江苏昆山人俞允文对朱纨的主张也持基本赞同的意见: 访得贼中谙水道及操舟善斗者,多漳州、泉州、福宁人。漳州属县诏安有梅岭,龙溪有海沧、月港,泉州署县晋江、同安连界有安海,福宁有桐山,皆负海阻,民甚桀逆,专以勾引番人杀掠为命。梅岭在闽中极南,尽界邻走马溪、下湾二澳,接广东潮州。走马溪下湾有两山障蔽,无风涛险害。贼舡每收泊于此。桐山东北尽界,接浙江。……今漳州、福宁多阻桀逆,于闽中又为最。即欲诛之,不能尽诛。拟合漳州添设通判官一员,专住箚梅岭;福宁州添设同知官一员,专住箚桐山,照依海沧安边馆事例。其月港、安海,可各添设一县。或谓,泉州南安县去府甚近,民又稀少,无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鄙附近晋江同安者,即割隶晋江、同安。安海都鄙即割隶南安,不必另立县为省。此议前已经福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诚为甚便。乞即下吏部议处,选择贤能官员知其俗者,讽喻和辑之,又守候诚谨,则民既近有所属而威德宣行,自消其凶悖之心矣。[15] 这则史料可被看作是对当时朱纨主张的主要立论之补充,俞允文的主张大概来自朱纨的上议,而俞允文的父亲俞璋,正德辛未(1511年)进士,曾任官泉州府,是为俞允文关注安海设县的原因。 作为安海地方士绅一员的黄堪自然积极支持朱纨的建议,黄堪认为:“且宋石井镇之制,近有朱都堂移县之请,伏望明台为本都造万古不磨之功。乞赐申请设官永镇,使地方有备,则盗寇无窥伺之心;政令申严,则奸顽无交接之患。地方安靖,民生乐业,实为万代阴骘。”[6]文中的朱都堂即指朱纨。朱纨提议安海设县主要看重安海地理位置适中,处于南安、晋江、同安、安溪四县之交,在此立县易于控制这几个县。但朱纨也意识到安海若立县则与南安县存在辖区重叠,腹地变小的问题。因而他的主张是设安海而撤南安。理由是南安县治丰州离泉州府城太近,不到十里,人口不多,又无城池。而当时反对设县者表面的理由仍为新县设置扰民费财等,而我们可以推断深层次的原因还有泉州一府在宋代已经几乎开发完成,拥有较长历史的南安县在地方士绅的眼中还具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识,故地方士绅没有明说但在内心应该是反对裁撤南安县的。而如果新立安海,并保留南安,则在经济上、政治上、地理区划上都不容易协调。因而这一主张在当时存在较大的争议,加上朱纨严格海禁导致闽浙士绅反对,最后朱纨设县计划终于搁浅。 三、万历时期安海筑城之官、私较量 朱纨在设立安海新县的建议中没有明确提到安海在防卫上的便利之处,但安海当地的士绅则看得更清楚。安海作为海港远离外海,拥有曲折的海湾,便于防御来自海上的威胁,同时陆上腹地周边都有山岭拱卫,易守难攻。如果在安海设立城池则诚为一良好的防御所在。如《安海志》卷四城池记载: 迨元入明,治属晋江,图依旧,都名八,班四十。……其后生齿繁而文物盛,产籍多而赋税足,为晋江之上都也。郡邑视为富饶,宫府赖其急办;两盗贼亦缘此而流涎,故广贼入者二,海寇涎望者屡。但阻于港汊之险,难于兵舰之用耳。[2]卷四,城池,p29 同卷城濠中亦说明: (安海)南城面海,目穷处海门也。潮一日夜两次起落,潮退港底水尽,如船入,必乘潮头初动时即随潮而入,至波平方得到岸。去必潮大平时即转船头,亦随汐渐出,汐尽得到海门,若稍缓则两头俱不得到,必须停流,盖港汊多曲湾,微不由道,必搁浅败船。此海寇不得到岸一也。 石井、东石乃安海之二巨螫,两边到海,内宽外窄,春秋二汛,海上汛船如麻;收汛则捕盗船亦多,如寇一入,则兵船把汊口,盗船不能脱,此海盗不能到城二也。 自古海寇何此百千至。杰黠势大如温文进,岂曾不垂涎安海,亦不敢窥其门墙者,以此二险也。此固天堑百二之险不能过也,东西二埭,水泽泥淖,东埭到东门以上,接皇恩坑;西埭到西门以上,接福埔坑,是皆易防守。所可虑者东北一隅耳,守城者须用力于此,自古贼至安海者,按高谱载:宋景炎之世,天下大乱,奸民挟漳贼二次而入,获进士高大章以去。自后至明朝正德二年丁卯(1507)十月十三,广贼远袭,剽掠甚惨。五年庚午十月廿四,广贼又至,皆山寇也。直至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四月初三倭寇由海而来,然皆从他处弃船登陆,行有十里而后至安海,非直抵也。[2]卷四,城池,p36 这样的地理形势对于明代官方防倭来说是很便利的。所以明代官方与地方士绅在嘉靖年间开始有筑城的动议。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时任晋江县令卢仲佃和安海地方士绅为防倭始有筑城之举。而这一筑城的行动则充满了波折和地方势力之间激烈的斗争。倡导筑城的为泉州知府熊汝达和晋江知县卢仲佃,负责筑城的是曾任池州知府当时已经致仕在乡的乡宦柯实卿。安海筑城的过程在《安海志》作如下记载: 嘉靖之末,东阳卢公以本县父母,垂慈怜而废政:闾里贵宦以邻乡狡官,生忮求以成谋;父母有爱子之真心,而彼以爱兄之道乘,诚信而喜之,不虞其有他计也。乃于三十六年丁巳(1557)卜日,运五十之工,驱东海之石以成建,功未及半,而柯宦实卿因取植木为基,被乡恶颜钦夫殴死。戊午(1558)四月,宦仆挟倭以来报宦仇,焚其尸,火其庐,祸延居民。其岁城亦卒成之,己未年(1559)雨大城圯,倭奴大至。自是六七年间,漳贼、倭寇流祸不已,城随圯随修。[2]卷四,城池,p29 在这则史料中,将负责修城的柯实卿称为闾里贵宦,并指出他有私心,并擅自在修城时取公用木料为基础,导致被“乡恶”颜钦夫殴死。同时这则史料认为修城完毕的第二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倭患是柯实卿的仆人勾引倭寇来为其报仇,结果反而“焚其尸,火其庐,祸延居民。” 再参考《安平志》对安海修城的考证,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柯实卿修城却罹奇祸的始末。在《安平志》卷二地理志城池一节中,1957年编者考证:建设安平城之时间,明、清官修府县志,皆作嘉靖三十七年,先由县令卢仲佃倡建,后由乡绅柯实卿完成,隐去三十六年卢侯倡建,柯绅以自修一百丈为响应,功及半,柯绅因取木为基,被乡凶殴死等事实。但何乔远之《闽书,建置志,安平镇》对此有如下记述:“(安平城)令卢仲佃与乡绅柯实卿甓石拓之。实卿为池州守,为镇人成功,其坚果任怨如其治官,竟为凶徒所戕”。证实卢侯、柯绅共同建城,及柯绅确被凶杀于建城中,而非最后完成安平城之建设者。可知城池篇所述建设安平城之曲折经过,及起讫时间为实录。即城始建于嘉靖三十六年,完成于嘉靖三十七年。柯绅之死,似应在三十七年四月倭寇由龟湖突至安平掠杀之前,因此之后,安平城也告成。[16]卷二,地理志,p44又据同书第47页编者的考证,说明柯实卿在修城时存在损公利己的行为,同时由于他家是地方势宦,与地方其他大族等存在较深的矛盾,所以导致了被殴身死及来年奴仆挟倭报复的闹剧。下面将编者按转引如下: [原编者按]:清抄本有“安平城池”一篇,系将明抄本“城池志”删去柯仆挟倭以来之记载,而加以称颂柯实卿语词之作品,或者系出于清道咸间新街人柯琮璜之手笔。而明抄本“城池”篇中,柯宦因取木为基被乡恶颜钦夫殴死乃涂改原文,而宦以忮求死之句,当时造城派工派捐,众人埋怨者,盖亦以柯宦之兄系大商人,柯府广有田园财产,造城首先为保护豪富,柯自造百丈石城而拆东桥石,又擅取他人之木,乃损人利己之行为耳。当时黄菊山在文中即特别指出:安海筑城出于民之醵金,是否认柯对筑城之功也。卢侯城记即高元宾之作,观明抄本“小序”有“高元宾曰”等语,似高亦系修编安海志人之一,其文中亦有兴作重役不能无生得失之句。可见当时筑城与防倭,以及贾夷问题与人民生活之关。至于“安海旧城”一篇,乃黄其琛作于清光绪十年上巳辰后三日,尽去旧案。[16]卷二,地理志,p47 而《安平志》在义烈一目“黄仰”条下的记载也与《安海志》大不一样,详细记载了柯实卿家族及黄仰家族在嘉靖年间的斗争及柯宦死事的始末。义烈黄仰条下首先说明了嘉靖年间安海的廪生黄仰为维护位于安海的石井书院的祠产,与当时福建督学浙江人田汝成的斗争。这一事迹与《安海志》所载基本相同。然后史料详细说明了黄氏家族与柯氏家族在筑城前后的争斗。《安平志》记载: 有乡太守柯实卿者,杰黠狡猾,凌驾寒门,吞渔大姓,又欲以力制吾宗,遣其仆募永春之教头,令其弟诱五澳之海贼,三道入攻,意在残捣掳掠,公乃率我族众,督我家僮败山海之贼而推擒其首。柯知力不敌,乃复以势以贿而构之于官,两下俱伤,狱久未决。既而实卿毒害于人,无远不披,岂虑其所以自毒也,寓泉被刺而未遂,居家侄弟谋杀而不就,钦夫杀之如拉朽。[16]卷七,人物志,p228 说明黄氏与柯氏两族在地方控制上存在巨大的矛盾,黄仰史料的编写者甚至认为柯实卿是嘉靖年间安海倭患的幕后主使,而柯家陷构黄仰入狱,双方在修安海城时处于缠讼之中,而以柯实卿被颜钦夫所杀告一段落。 而第二年(嘉靖三十七年)倭寇入犯安海则是柯家世仆所为:“继之戊午之年,有被害者林五与逝仔、童仔挟倭而来,冀复其仇,盖未知实卿之已死也。至则赭其室,焚其棺,俘其人,纵余毒而后去。”[16]卷七,人物志义烈,p228-229当时黄仰还被押在狱中, 时公在狱,倭寇狼藉,乡邦莫之能御,公素有用武之志,而筹略亦素闻于人,阖郡咸推郡守豫章熊公汝达,出之于狱,礼而遣之,公誓不与贼俱生,发家僮为兵,守洛阳桥,当贼北来之冲,贼首有跛脚番者,最杰黠用事,公以计获之,于是不敢渡,沿山道而去南安潘山直抵磁灶,与其乡千长吴君范战杀之。公策其必至安海,乃率众追及磁灶破之,遂直趋至堡时,堡新筑未就,以四月初三败罢役,公至,率家兵子弟,调拨守御,贼闻之不敢□堡者数日,公料其已沿山路出境矣,因暂安之,且值端午,遂各解严回家。有为贼响导者,以□□□□意,公兵犹在堡,又以西桥为绝□,可托险而破也。乃诱贼沿堡城边俘掠人民,出西桥南趋,意欲□□以自脱也,既而乡之避贼者二万余人,亦欲出西桥以奔,贼于后追逐甚急,海潮又涨,西桥一时拥塞,而公兵未集,望救者转切,公按剑誓曰:‘捍贼救民吾之分也,见贼扼人于险而舍之,将焉用戎为。’即率其现有之兵二十人,据险以拒贼,杀贼十余徒,而二万逃生之众,乃不得脱险焉。既而人渡尽,贼大至,以二十人抗三千,势不可支矣。而潮水涨满,人劝之曰:‘众寡不敌,尚可逃也,谨避之,以图后计。’公曰:‘逃,非匹夫事也,辱人也,逃遁贱行也。以一身活二万人之命,丈夫责也。余廪膳也,食君之禄矣,纵不敌而死,亦从王事之忠也。忠,素志也,死不以罪,而以功得死所也,夫复何恨哉。悲夫!纵毒而死于匹夫之手者,何啻祥鸾之于□鼠也’,遂擒战力尽,与其从弟廷英死之。嘉靖戊午岁之五月初五日也。事闻官给葬。巡按御史斗山范献科上其功而祭之以文,钦赠州同知,赐一子冠带云。[16]卷七,人物志 义烈,p228-229 从这则材料中可知,当柯实卿筑城之时,黄氏性格刚烈的代表人黄仰因与柯家的诉讼还被押在狱中。而柯氏死后,直至嘉靖三十七年春,柯家仆人挟倭来攻时,府县官员因安海地方有城而无守城之有力领导人,柯实卿已死,乱亦由柯氏内部的人导致。此时官方才将在地方上另一有影响力的大族领袖黄仰放出领导城防。这一事例颇像之前章节所说的正统年间,诏安镇涂膺领导的诏安镇城的保卫战,也是地方士绅领导群众抗御本地武装流寇骚扰的例子,只是涂膺守城成功而安海黄仰则不幸身亡。 再看《安海志》中记载黄仰死后其一子获得封荫的情况。黄仰死后,袭冠带的儿子名叫黄回青。《安海志》转引《泉州府志》中的记载说:“父仰遭齮齕,絷圈土十年。回青亦坐累落籍,荼苦备尝。值倭乱,父自狱中上书请讨贼,死难赠官。回青袭冠带,州同治。”[2]卷三十,义勇,p360可见安海柯氏与黄氏因对地方把控问题导致的诉讼居然长达十年之久,而黄仰本人因为在此前得罪了省督学田汝成,在诉讼中处于下风,被絷狱中达十年之久,亦不能为筑城的领导人物。但在嘉靖三十七年的倭乱中却成为了城防的地方领导,死后其子回青及黄仰的兄长黄伯善共同领导了之后的守城及抗倭,黄氏宗族亦在之后的安海社会中取得了发展和地方影响力。再看《安海志》转载黄仰族兄黄伯善条的记载: (伯善)领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乡荐历任昌化教谕、衢州府同知,后罢官归家,益思行其德于乡,数为乡人排难解纷,尤急于宗族;族中指以七八千,为纪纲约束之,奖其贤者,周其贫者,诫斥其傥荡不类者,族人多化焉。[2]卷二十七,文苑,p339-340 黄伯善的儿子黄宪清后也为举人,黄宪清之子黄汝良(伯善之孙)中明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会元进士,另一儿子黄汝为中万历四十六年(1618)乙卯科乡举人。汝良二子庆增、庆华分别再中天启四年(1624)、崇祯六年(1633)举人,黄庆华后官至山东监察御史。从这些资料可知,黄氏家族为安海地方科举极发达的大族,族众达到七八千人之多。而黄氏与负责筑城的柯氏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明代安海地方社会强族相争,把持地方事务的复杂历史面貌。双方对地方的把持与斗争也都依赖于官方的支持与调停,但实际上有点凌驾于官方之上了。而明清时期的地方史志的书写者由于出身与立场的不同,多少受到了地方强宗的影响,也对这一公案作出了不同的阐释,导致我们今日看到这样复杂不清、语焉不详的记载。 上述史料说明明嘉靖年间,安海地方社会的大族之间围绕着筑城与海外贸易问题存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但无论斗争如何激烈,安海镇城修筑对安海的地方防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嘉靖三十年代大倭寇侵袭福建沿海的冲击中巍然不倒。而柯实卿被刺杀这一事件,柯氏族众必然谋求官方对行凶者予以处置。《安海志》卷三十一笃行下列柯实卿之弟柯奇卿条目中记载了柯氏代表对柯实卿被杀案件的追诉。这则转引自《泉州府志》的材料是这么说明的: 柯奇卿,字特季,号鳌桥,为郡诸生,有文名。兄实卿为池州守,归,为乡人所齮齕。奇卿亦因是坐累铲籍。实卿议城安平,奇卿实助其画,复部署族人为捍御计。比倭至,率以登陴,兼治糜以哺保者,与众共守,城卒以完。后倭复至,野剽无所得,乃发冢责赎,乃冒死从间道以父柩归。……实卿之殁,以建城采木为凶徒所戕,事极冤酷。奇卿徒跣控诉两台,累岁倾资殆尽,不为辍。凶人卒伏辜。[2]卷三十一,笃行,p362 从这则史料来看,刺死实卿的颜钦夫被官方处死而告终。但在明代当时,如若发生民刺官的事件,则官府将极为严厉和果断地予以惩处。但从材料来看,制裁刺杀柯实卿的凶手居然要花费如此周折,可见期间充满了大族斗争的矛盾,柯家在官方眼里似乎是把持地方的另一乡霸,也是需要惩治的,地方舆论也分为矛盾对立的双方。如上引黄仰的史料,说到“柯知力不敌,乃复以势以贿而构之于官,两下俱伤,狱久未决”,说明明代泉州官方处理柯、黄两族的争端,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除将黄仰系狱外,也革除了柯氏中柯奇卿的生员身份。这样才能说“两下俱伤”。 而当时的地方舆论对柯宦被刺事件分为同情与讨伐二派,如何乔远就同情柯氏被刺,并认同柯氏造城之功。但官方文献中《泉州府志》《晋江县志》都对争端的深刻内因避而不录,而历代私修安海志的作者对这一事件则有自己的看法,《安平志》中在还记录了数条补充资料: [附二]城池志门楼四,以后有窝铺连城楼二十八个,及稍广之。立甲长副以居民。配上中下户。家产有千者为上户,出银三十两中,下出银二十两,柯宦署笔自担一百。丈柯功何不大哉。宦之死莫之记者何也?后乡绅御史苏琰志其墓,深为太息。柯宦死于嘉靖丁巳,至崇祯甲戌八十有余,其孙胤贤乃葬之。 [附三]东桥名曰“东洋桥”。宋绍兴二十二年,安平桥成,二十三年权泉州军赵令衿偕进士临漳户椽史进建之,不半载而成。长六百十余丈,广一丈二尺。分为二百四十二间,东西二亭,赵令衿撰碑记。明嘉靖三十六年,倭寇频扰,急议筑城保障里人。知府柯实卿乃拆东桥石筑城,而桥废焉。 [附四]明嘉靖丁巳年,邑尹卢公讳仲佃,乡绅柯公讳实卿,虑安平士民之众,无城廓之卫,于是申请各宪议建石城以为之备。因为乏石,乃拆斯桥之石以筑城,功未及半,而柯公身受意外之祸死矣。后之往来者,冒风雨之阻,多归怨于柯公,厥后,石城完就,而安平之众,无有颂柯公之德者。呜呼!桥城二便,不知孰是孰非,惜哉![16]卷二,地理志,p48 附二与附四为柯实卿抱不平,同情柯氏之死。而附三则谴责柯实卿修城擅自拆安平桥的罪过。这些都反映了明代地方社会复杂的面貌。而所谓柯氏家仆勾引倭寇为柯复仇劫掠安海,估计是其家仆乘着柯氏死后图谋对主家的劫掠,所以倭寇攻安海反而将在安海城外的柯家烧毁,劫掠一空。如此解释,则安海筑城的曲折历史可以让我们稍有清晰的认识。而安海镇城修好后,“倭寇”多次进攻,都未能下,地方赖以安全。“三十八年倭寇两攻安平,四十三年后自仙游来攻,皆不能陷。”[17]卷九十九,p4522 嘉靖三十年代末倭寇冲击风波过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漳泉地方社会处于一种较宁静的状态中。漳州海澄设县,月港开港之后,漳州沿海获得海外贸易的合法地位,安海的海外贸易实际上从属于月港。而万历三十年代,安海设县之议再起。而在此之前,相邻地方先有将驿站移置安海的主张。如若安海设驿站,则是安海地方的一种负担,故引起地方士绅强烈反对。黄氏家族的乡绅黄伯善也给我们留下了反对筑城的文献。黄伯善认为安海筑城没有花费官方的经费: 安海筑城出于民之醵金,不烦库藏;守城本予土著编户,不动官兵,钥锁自由,盘诘不懈。而相邻南安县康店的驿夫居然想把原属南安的驿站移到属于晋江的安海来,这对安海和晋江都是一笔额外的负担。为逃避此负担则安海居民只有逃亡一条路可走,而安海居民逃散,此处地理位置重要将为贼所占据。近有南安县康店驿夫,保捏呈欲寄驿于兹土。……其奸人乘传,托以皇华为名,而非肺急呼于外,党与伏匿,假以驿卒为名,两观衅待变于内。方此之时,若拒之而不纳,是无王命也。纳之则万家之命坐受其缚,幸而不死,仅有鸟迁兽徙而走耳,奚暇顾其家室哉。是城反为贼寇之堡,而驿为奸宄之资,数万金之费,委于草芥;数百雉之险,鞠为丘墟,城既不为民有,驿亦安得独存,云霄驿之近事一鉴也。且晋江濒海,村落靡有孑遗,独安海一城,伤残之民以供里旅之役,而安海亦何负于官府哉。兹复使为贼有,则安海之人民土地,一时俱尽,宁复可为县乎。贼得安海城以为巢穴,聚而不散,谋而不轨,羡鱼盐之利,通山海之货,游途隘隔,数县声息不通。东断永宁之臂,西折武荣之肢,南拊南安之背,北扼清源之咽,是事不十费支吾耶。缘系议处应否徙驿,书生愚昧,以为不相应,大不便云。[18] 因此地方士绅强烈反对将南安的负担转嫁于晋江和安海。这一动议也就搁浅了。从材料来看,南安方面主张移驿,似乎是作为安海设县主张的一个附加条件来谈的,而黄伯善为首的地方士绅反对,说如果移驿,而人民逃亡,“安海之人民土地,一时俱尽,宁复可为县乎。 而黄伯善之孙万历十四年会元黄汝良给我们留下了万历年间地方士绅推动设县的重要史料。根据《安平志》说明,1984年安海镇政府在朱文公祠西侧建镇政府办公楼时,出土有关明代设驻镇馆石碑二方,其碑文对万历年间割地设县未果,以及后设驻镇馆的复杂曲折历程,有详细的记述。同时碑文出土明确说明了《安海新设驻镇馆记》一文的作者为明万历年间安海黄氏进士黄汝良,而不是乾隆府志所收入同名文章所说的作者为苏谈,而府志收入此文删节过多,篇幅仅为碑文的三分之一,且碑文字迹剥落难辨者亦不少。从该碑文来看,万历年间安海重提设县的动议,是地方士绅受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海澄设县成功的鼓舞。“列圣以来,益谨绸缪,泉漳兴福之间,时增式廓,若竹崎、云霄、海澄诸处,大者为邑,小者为镇,犬牙错而虎落周,良以巨浸浩淼,风飖飘忽,不备不虞,易启戒心,盖庙谟宏远矣。”漳州府在明代至此已经新设五县,同时云霄作为镇城,也以设官管辖,直属于府。而安海自嘉靖年间设县动议未成之后,虽已筑城,但没有官方常驻机构管辖。碑文中对嘉靖万历以来安海的局面作了以下描述: (安海)承平日久,生聚渐繁,室家鳞次,阛阓栉比,肩摩□击,骈骈阗阗,昔村落而今粤区矣。物力既盛,巧故萌生,曩时奸民往遥阑出、交关岛夷,输我虚实,自洋禁开,互市之舶往来□□,我以彼为外,□彼□□□为兀脔,□陀涎垂何所不有。昔内地而今夷□□。嘉靖之季,倭讧突发,磨□吮血,万室为墟,当事者乃始料民醵赀,筑为城堡,保聚捍御,民用稍有宁志。其后夷棼既憩,经久虑疏□间,镇以武弁桑梓□□□□□□□□复经则委□□□□□吏早□□褥徙规浚削。无事如蚁慕膻,有事则如□遗迹,非惟无益又滋害焉,何则城非公创,不领于职方。守无专官,罔虑于民社居平,犹或探充无忌,杆鼓时鸣,一旦有儆,其□剪为寇,雠者几何,夫时至则事起,以高皇帝加意海邦,推之讵于今日,不为之所哉。[19] 在这种情形下,地方士绅联合向上官建议设县,“于是堡之缙绅父老,走控上官”。 时任晋江县令顾士琦对于新设安海县的建议是:“安海置邑,如海澄诚便,然必割晋南同之界。版籍既定,纷更为难,又必设官,办建学,必多创公署,必措处舆台,一切廪禄经费,猝未经办。宜略仿云霄竹崎故事,建设分府,即以现在府倅一员充之,无增官之扰,有保障之安,计无便此者。”[2]卷五,公署,p41而碑文中对安海分设府通判常驻的始末是这样记载的: 监司上其议,直指方公深韪之。为请于朝,给印章,文曰驻镇安海,用示专守。堡人闻命欢欣鼓舞,输将帛币,□走恐后,乃始揆日蠲吉,饬材庀工,即城之西北而建署焉。统以周垣,拱以重门,有堂有皇,有寝有房,宾馆廨舍,罔不毕备,盖不烦官帑一钱,而隆栋岿然矣。经始于别驾汪公,殷公继之,趋事益敏,起丙午四月,越戊申四月落成。[19]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因安海设县存在较大的行政难度,故模仿漳州云霄镇的例子,设立泉州府督粮馆分镇安海,并派遣新任府通判殷光彦莅临安海专驻管辖。安海的府属督粮馆实际上是作为晋江的分县常驻该地处理的。 道光《晋江县志》中为当时推动设镇的县官顾士琦和首任督粮官(府通判兼任)的殷光彦都有列传。 顾士琦,字二韩,太仓人。万历戊戌进士,二十九年由崇安令调知晋江县。不为伉强开敏喜事好功,一以恺悌为政。值旱蝗相继,极意拊循催科,不事鞭扑,与为期会,民无逋者。两造之讼,徐出片言,轻者立遣,重者量惩,无株连,亦无久系。校士严加防范,邑无留良,即在彀外者亦帖息无哗。兴一事必惟其终,革一事必思其后。居己于瘠而予民以肥,居己于拙而予民以静。门无暮金,吏皆奉法。造请贤士大夫咨询利弊,不厌谆复。秩满,念岁祲,民艰于食,报绩独迟。[20]卷之三十五,政绩志 顾士琦的施政风格是严于律己,加强管理,颇有政声,在任晋江令后升迁而去,因而他的主张得到上司的首肯,也得到地方士绅的认可和支持。 而首任安海镇官的通判殷光彦也有较好的政绩: 值安平新设镇,移驻于斯,是时疆理方殷,庶务草创,光彦至未数月,顾吩咄嗟,百务具举,镇去郡稍远,邪侠恶少,博塞呼卢,探丸击剑,恣睢莫何。光彦摘其尤桀黠者,重惩之。诸风渐息。镇素殷富名,奸人虎视,始而鸡狗窃关,继且萑苻思逞。为慎管钥,严街鼓,明保伍,饬游击。于是夜犬不吠,闾阎安堵。镇城数圮,外隍曾无衣带之限,创谋缮陴,塞港以壮金汤。……俗嚣讼难诘,光彦干局精敏,才谞练明,片言立折,两造输诚。钩金既省,桁杨罕用,惠同之民咸赤质成。其他善政,难以枚举。郡人歌颂,万口一词。[16]卷七,人物志,名宦,p202 万历三十五年虽设县不成,而终于有了官方常驻的文官予以管辖,安海地方社会也经历了一段安靖发展的局面。但好景不长,天启、崇祯时期随着郑芝龙海上力量的崛起,安海很快成为郑氏海上商业与军事集团的基地,基本脱离了官方的直接控制,为郑氏海上集团直接把控了。根据廖渊泉的研究,天启、崇祯年间,安海港是郑芝龙对外贸易的基地,郑芝龙海商贸易的发展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壮大,必然促进安海港的极盛。郑芝龙以其煊赫的权柄和雄厚的资财,调动大批的人力、物力,采取很多措施,对安平镇进行大规模的整治与建设,如首先继续修筑安海城池。“筑城安平镇”,“开府其间”。他还在安海镇内大兴土木,建筑有“亭榭楼台,雕梁画栋,极尽豪华”的府第,其“巧工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并兴建仓库和军营,“积财宝甲兵,充实其中,人物丽盛,专务丰殖,”更重要的是郑芝龙还整治安海港,在安海“开通海道,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竞达海。”而郑芝龙降清之后,郑成功继续利用安海为基地,展开对清政府的斗争。[21]这都使得安海成为明清福建历史上一个特例,因为战争的破坏,安海港开始衰落下去。入清以后,虽再有设县的动议,基本不能获得官方的支持,因为这时安海的经济地位已不像明末呈顶峰状态,厦门崛起之脚步已渐近。 由上文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安海设县跟海澄设县的情况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两处地方在明中叶私人海上贸易发展起来之后,都是地方海上贸易的中心地,经济发展迅速。都与当地原有的政治中心距离较远。一旦设县都能够控制地方重要的港口地域,而且地理上都有利于地方的军事防御。两地在明代都产生大量科举士绅阶层,这些阶层都力图推动对地方有利的设县运动。但安海与海澄设县一成一败,又分别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和不同的历史背景。 从地方士绅对地方事务的把持来说,安海的士绅集团更加深入介入地方事务。嘉靖年间的设县及之后的筑城运动,可以看到地方大族对地方控制权的斗争的情况。海澄在设县之前,不像安海出现能够强力把控地方政务并能跟政府合作的科举式大族,海澄地方秩序更加混乱,倡乱的民间力量与官方合作的程度更低,如前面对海澄设县的详细考察中,海澄设县后地方民众对官方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明代官方如若不在海澄设县,地方治安及将来放开合法的海外贸易基本不可控制。 此外安海所处的泉州经济发展的周期与漳州不同。泉州的开发早于漳州,宋元时期其行政区划的格局基本稳定,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而漳州开发的黄金时期和经济发展的高峰在明中叶以后,漳州地方的县份原本就较少,各县的辖区过大,海澄在地理上具有更完整的成县的条件,面朝九龙江入海处,腹地内有完整的水系沟通,山区与沿海地形复杂。安海的成县条件则相对不足,腹地狭小,所在的晋江、南安两县之间再划出一县,势必导致三县的地域都过于狭小,所以明代倡导设县的主张是撤南安,让安海、晋江两县并立。这势必引起南安地方的反对。同时,在私人海外贸易港口的功能和地位上,安海一直不如海澄。海澄在明代中叶以后已经成为可以联系全中国沿海的贸易中心地,全国的财货要纳入海外贸易往往先转运至海澄,再分批发出去。而安海的贸易货物,尤其是纺织品往往从海澄转批发。这些都导致海澄设县势在必行,而安海的设县却存在种种的阻挠。 最后看安海历史最特殊的一面。在于明代崇祯年间郑芝龙海上力量崛起之后,完全把持了沿海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安海成为郑氏海上力量的总后方和大本营,这样特殊的历史更使得安海设县的可能性化为乌有。明清易代时期,郑成功与清政府与福建沿海的争夺更集中在诏安、海澄、厦门岛、安海这几个重要据点。至郑氏力量离开福建沿海后,沿海的海上贸易衰退,地方治安趋于长期稳定,安海设县的内在动力几乎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