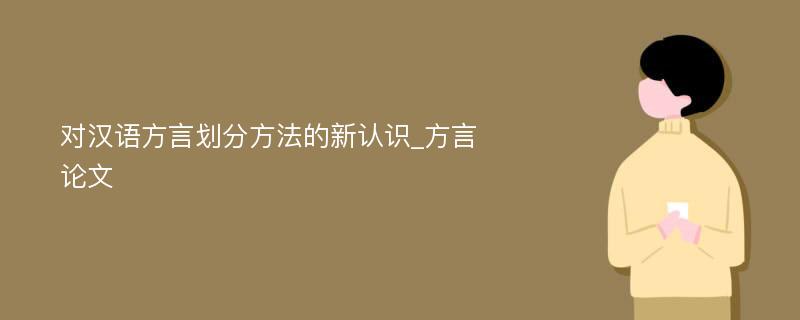
汉语方言分区方法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汉语论文,方言论文,分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作出新的分区以来,关于方言分区问题的讨论就成为引人关注的学术焦点,一直持续至今。讨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区的方案,二是分区的方法。前者主要是讨论某些方言区的分合,后者主要是讨论分区标准。这两个问题都跟分区方法有关,本文试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审视汉语方言分区问题。
一 事物分类和方言分区
方言分区本质上是语言的分类,既然是分类,就必须遵守事物分类的一般逻辑,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方言分区不同于一般事物分类的特殊性。
人类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本能,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进行分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必由之路。在科学研究领域,分类更是建立学科体系的基础,对于生物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来说,这种分类显得尤其重要,方言学也属于这样的学科。
分类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观需要,而且是有客观依据的。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这就是分类的依据。根据共同性,可以将若干事物归为同一个类;根据差异性,可以将一个事物划分为若干个类。逻辑学将前者称为归类,后者称为划分。归类是从种到属,划分是从属到种,二者的逻辑出发点相反,思维过程也不同,但结果应该一致。也就是说,一方面,将属划分为种所依据的差异性标准和将种归类为属所依据的共同性标准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操作的规则也是一致的:(1)同一级的种与种之间必须互不相容,(2)同一级的种必须穷尽最邻近的属,(3)每一次操作必须采用相同的标准,(4)每一次操作都不能越级。
就一般事物而言,划分和归类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有一个包含100 个多边形的几何图集,我们可以从整体出发,根据多边形的边或角的数量,将它们划分为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等等;然后再根据边长或角度将三角形进一步划分为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将四边形进一步划分为正方形,长方形、梯形、平行四边形,如此等等。反之,我们也可以从个体图形出发,同样根据每一个多边形的边长或角度将其归类为正方形、长方形、梯形、平行四边形,以及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等等;然后再根据边或角的数量进一步归类为三角形、四边形、五边形,等等。
但是,对于连续性事物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连续性事物内部同样存在差异,因此也是可以分类的,但在分类之前,整个事物呈未被切分的连续状态,根本无法确定其内部包含多少个体,因此很难从个体出发逐层向上归类,那就只能从整体出发逐层向下划分。例如,要对一条连续的曲线进行分类,只能从整体上去划分。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即使可以从整体出发对连续性事物进行逐层划分,并最终将所有的个体从连续体中切分出来,但这样分出来的不同的类中的个体,并不都像离散性事物那样泾渭分明,靠近切分部位的个体,往往既像这一类,又像那一类,或者既不太像这一类,也不太像那一类。例如颜色的划分,究竟有多少种就是不确定的。16世纪时牛顿将颜色分为7类,这是近代色轮的原型。此后, 人们又提出过许多不同的标色方法。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国际照明委员会1964年修订的CIE色度系统, 该系统只分红、绿、蓝三原色,然后任取三原色中的两种按不同的量进行机械的混合,就可以得到远远多于七色的各种色调。
这样看来,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连续性事物的分类具有较大的难度。从分类的逻辑起点来说,从整体出发向下逐层划分,其适用面要宽于从个体出发逐层向上归类。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使不是连续性事物,假如个体项目数量庞大并且很复杂,要逐一考察后再逐层归类,其效率也不如从整体出发逐层向下划分。因此,对于复杂事物来说,划分不仅比归类适用面更宽,而且更易于操作。
方言既是分布广袤的共时现象,又是绵延不断的历时现象,因而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具有连续性。汉语是世界上母语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方言最复杂的语言。汉语方言即便以县为个体单位,其数量也超过两千,其中还有不少地点的方言情况尚不清楚。综上所述,汉语方言分区作为一种语言的分类,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因此,汉语方言分区也应该走划分的思维路线。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汉语方言分区走上科学的道路时起,就采取了以确定的标准划分汉语方言的做法。这些标准起初带有工作假设的性质,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尽管没有一条标准是完美无缺的,但其中的核心标准至今仍不可取代。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对这些最初带有工作假设性质的朴素的真理加以更加深刻的重新认识。
二 汉语方言分区的两个步骤:划类和鉴别
汉语方言分区,当然要遵循事物分类的一般逻辑。以往的分区工作在这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没有严格贯彻从全局出发逐层划分,每一层划分采用同一种标准的原则。例如,争议最大的“晋语”问题,就是因为在同一层次的划分中没有坚持同一标准。为了解释由此产生的矛盾,有一种意见认为,划分方言区和确定方言区的层次应该加以区分,二者不能采用同一个标准,前者只能用语言标准,最好是单一的语音标准,后者的标准则复杂得多。这显然是违背分类的一般性原理的,因为方言区的划分只能用同一个标准在同一层次上进行。依据这一原理划分出来的方言区当然处于同一层次,假如用另外的标准将其解释为不同层次,这就不合逻辑了。
尽管在遵循一般分类原则方面有不够严格之处,但汉语方言分区至今不能取得一致的主要原因还是汉语方言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在于各方言特别是交界地区的方言长期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使得原有的差异渐渐磨损,新的区域性特征则不断产生,尤其是随着方言调查的密度不断增大,某些重要的区别性特征的覆盖面反而相对缩小。例如,就连保留全浊声母系统这一似乎没有争议的吴语鉴别特征今天在一些边缘地区也已经磨损了。人们从实践中逐渐意识到,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仅仅按照一般的分类原理是难以全面解决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于是,很多学者试图寻找和添加新的分区标准,随之又发生了语言标准和人文历史标准、语音标准和词汇语法标准、单项标准和多项标准、共时标准和历时标准的一系列争论。迄今为止,先后提出的分区标准日益增多,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陷入了各执一端,僵持不下的困境。本文不打算提出新的分区标准,而是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以往的标准。
我们认为,汉语方言分区不妨借鉴系统工程的方法,即面对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人们的工作目标常常难以一步到位,此时可以设法将这个大系统分解为若干子系统,使问题的复杂性有所分散,以便于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分别予以解决,同时从总体上加以综合、调控。这种做法运用于复杂的连续性事物的分类是有成功先例可循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关于颜色的CIE分类系统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此外,上文批评将划分方言区和确定方言区的层次加以区分并采用不同标准是违背分类的一般逻辑的,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意见中也含有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相对单纯的问题,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加以解决的合理因素,这是富有启发性的。事实上,汉语方言学界近年来根据以往方言分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也逐渐产生了将方言分区分解为两件不同工作的思路。詹伯慧(2002)认为:“方言分区决不是地理上方言区界的划分”,“方言的地理划界只能说明说不同方言的人所处的地域区界,跟方言分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李小凡(2003)提出“方言的分区与划界是相关而又不同的两项工作,分区是从语言学角度划分出几类特征鲜明的典型方言,划界是从地理学角度划定每一个区域的方言归属。分区必须先行,划界则以分区方案为出发点和归宿。”
按照以上思路,汉语方言的分区可以分解为划类和鉴别两件相关而并不等同的工作。首先是从汉语方言的整体出发,划分出几类特征鲜明的方言区;划类完成后,再从个体出发,将方言点一一归入既定的方言区中。前一项是严格意义上的划分类别,后一项工作则是鉴别类属。划类与一般事物从属到种的划分完全一致,鉴别则不同于一般事物从种到属的归类。其差别在于:鉴别时,类是事先确定好了的,是工作的出发点;归类时,类是有待确定的,是工作的目标。也就是说,鉴别是一种对号入座的工作,是划分的后续工作;归类则是与划分同一层次但方向相反的归纳工作。汉语方言的划类和鉴别工作前后相继,操作时互不干扰,结果互不矛盾。两项工作综合起来就是汉语方言分区的全部内容。
第一步划类工作要严格按照分类的一般原理,用同一个特征在同一层次上作穷尽性划分。这样划分的结果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
(a)能划入某一类的都是特征鲜明的典型方言,典型方言区即使互相毗连, 由于特征鲜明,边界并不模糊。
(b)典型方言区之间往往存在既难以划入这一类, 也难以划入那一类的或大或小的方言过渡区。典型区与过渡区互相交错,呈网状分布。
(c)就典型区而言,原先在地域上的连续性分布便转化成了离散性分布,这就使典型方言区变得明确而不再模糊了,典型区中方言点的归属也就同时得到了确认(方言岛除外)。
(d)就过渡区而言,其方言归属尚未确定,须留待第二步的鉴别工作去完成。
(e)地处典型方言区边缘的某些方言点, 虽因具备该方言区的划类特征而被划入该方言区,仍须在第二步鉴别工作中加以检验,假如它同时又具有相邻的典型方言的特征,其归属还需要综合考虑。
第二步鉴别工作的范围限于划类时未能确定类属的剩余区域。这些区域分别处于几个典型方言之间,远离典型方言的中心地带,是不同方言之间的过渡区。方言区中心地带的语言特点扩散到这里已经变得模糊起来,有的甚至完全消失。所以过渡区的方言常常既不具备甲方言的全部特点,也不具备乙方言的全部特点;同时又既具有甲方言的某些特点,也具有乙方言的某些特点;有的甚至具有某方言的众多特点却没有该方言的划类特征。对于过渡区的方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区别对待。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1)将过渡区各方言点的语言特点分别与邻近的典型方言的代表点相比较,对号入座,与哪个典型方言的共同性大就归入那个方言。需要注意的是,共同性不仅要看共同点的多少,更要看共同点的重要性。
(2)对于难以判断究竟与哪一个典型方言共同性更大的过渡性方言,可以采用不一定适用于整体划分,但对区别邻近的典型方言十分有效的鉴别特征来判断。例如,某些古老的、罕见的语音特征,还有特征词、特字,以及某些特殊的语法形式等都可以充当这样的鉴别特征。
(3)对于很难用纯粹的语言特征来判断的过渡性方言,可以参考其人文历史和地域文化与邻近的典型方言区的异同来确定其归属。
(4)以上三种方法都不能确定其归属的过渡性方言,不一定非要归入某一个典型方言,可以径称为“过渡方言”。
(5)如果过渡区的地域比较大,其内部分歧也比较复杂,在人文历史和地域文化上又有过比较长期的共同发展历程,而且难以认定它正在或将要向某个典型方言靠拢,也可以单立为混合方言。混合方言不是在第一步的划类中根据划类特征从整体上划分出来的,其性质与整体划分的典型方言不同。承认混合方言有利于稳定分类格局,可以说是对汉语方言分区的合理的综合调控。混合方言不完全是自身演变的结果,也是方言接触的产物。方言接触的理论意义今天已经得到了充分揭示,将其应用于方言分区应该是合理的。
以上讨论都是就一级方言区而言的,一级方言区以下的各级次方言,理论上也应该依照上述原理自上而下层层划分。但实际操作时,每一级次方言的划分难度都不亚于一级方言区的划分,都需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找出最佳分类标准,统一划分出若干典型次方言,然后再对剩余地区加以鉴别,归入恰当的典型次方言。划分次方言的研究总的说来远不如一级方言,因此,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不过,次方言的层级越低,进一步划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越低。因此,不妨先集中力量解决一级方言区的划分和鉴别问题,而将各级次方言的划分留待条件成熟时水到渠成地分别予以解决,在此之前,可以先维持现有的次方言格局,暂且视之为工作假设。
令人欣慰的是,在次方言划分方面,实际上已经有了十分成功的范例可资仿效,这就是李荣(1985)对官话次方言的划分。它采用中古入声调在官话方言中的分派这条音韵标准从整体上将官话方言统一划分为北京、东北、冀鲁、胶辽、江淮、中原、兰银、西南等8个次方言。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由此也使我们相信:第一,其他次方言的科学划分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第二,用单一标准划分汉语方言区并非不可能;第三,入声的分派既然已成功地用作划分官话次方言的标准,就不能同时再用来划分一级方言,也不宜与其它标准共用。
三 汉语方言分区的两类标准:划类标准和鉴别标准
按上文划分和归类两步走的思路,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也应该分为两类,一类用来对汉语进行整体划分,另一类用来将方言点归入既定的类别。前者可以称为“划类标准”,后者可以称为“鉴别标准”。这两类标准不仅操作顺序不同,性质也不必相同。划类标准要从科学性、逻辑性出发,尽可能反映方言的本质特点,并对各方言具有普遍性;鉴别标准则要从实用性、便捷性出发,不必刻意追求普遍性。
划类标准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语言标准,最好是单一标准。过去认为这是难以做到的,所以分区标准才会越提越多。但是,将方言分区分解为划类和鉴别两件不同的工作后,在第一步划类工作中就有可能做到了。
鉴别一个方言点的归属时,通常只需考虑该方言点邻近的两三个典型方言,因此,鉴别标准不必具有普遍性。即可以用某些标准来鉴别某过渡区的某方言点属于典型方言甲还是典型方言乙,而用其它标准来鉴别另一过渡区的某方言点属于典型方言丙还是典型方言丁。还可以采用多项标准,甚至可以借助某些人文历史、地域文化标准。由于归类是在分类框架已定的基础上进行的,采用若干不同的鉴别标准不会反过来影响划类。
以上两类标准不能互相替代。划类标准无法用来鉴别过渡方言的归属,因为方言过渡区本来就是用划类标准对汉语方言进行整体划分后的剩余区域。鉴别标准不一定能用来划类,因为它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以往关于汉语方言分区标准的讨论将两类标准混为一谈,结果既不能有效地解决整体划分问题,也不能有效地解决个体归类问题。
汉语方言分区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较早明确提出比较系统的分区标准的是王力(1936)。他将汉语方音划分为五大系,不仅对各大系的分布区域作了详细说明,而且每一系都“择定一个都市的方音”作为代表,逐一列举其语音特征。这些语音特征就是划分五大系的标准。这在汉语方言分区的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王力采用的标准是若干项具有普遍性的语音特征。其中,古全浊声母的今读是首要标准。迄今为止,用来进行整体划类的语音特征,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丁邦新(1982)将这些语音特征称为“历史性条件”,朱德熙(1986)则加以修正:“说是历史标准,是因为用了古音类的名目。其实我们可以完全不提古音类,直接选择某些字在现代方言里的实际读音作为分类标准。事实上历史标准是无法直接施之于现代语的,我们能够利用的只是它在现代方言上的投影。”方言表现为共时分布,却又反映了历时演变,方言分区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分区标准也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否则,分出来的就不是具有空间和时间双重连续性的方言区了。
但还是有人在方言分区问题上将共时和历时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认为:“要追溯历史,对方言进行历时分析,就应该选择能反映方言间亲缘关系的语言特征为标准;要反映现代方言间的共时差异,就应该以方言的类型特征为依据,而不必考虑这些特征是否反映亲缘关系。根据亲缘关系给方言分类属谱系分类法,根据类型特征给方言分类属类型分类法,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薛才德1991)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须知选择关键性的演变特征并非仅仅为了追溯历史,更是为了反映变化或发展中的事物在共时层面上的深层差异。在这一点上,方言分区类似于生物分类,生物分类就是用遗传学特征来进行的。正如朱德熙(1986)所言:“方言区实质上是方言亲缘关系在地理上的分布。划分方言区是给现代方言分类,可是分出来的类要能反映亲缘关系的远近。因此这种研究实质上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范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目的固然是为了追溯历史,重现语言的历史面貌,但所采用的历史比较法却是从共时出发,以共时现象为依据的。方言分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今天的方言分类,但也不排除它在方法上可以而且必须采用具有历史内涵的分区标准。纯粹的类型学分类的确可以不考虑历史,但分出来的类就不是具有空间和时间双重连续性的方言区,而是类似于孤立语、屈折语、粘着语,或者分析语、综合语,甚至SVO型语言、SOV型语言那种结构类型了。
按照分类的一般原理,划类标准应该是越少越好,最好只用一条标准,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兼类。这一点在理论上没有人反对,但是在实践上会遇到重重困难。正如张振兴(1997)所说,“确实很难只用一个标准,特别是用一个绝对排他性的标准,对方言进行自始至终的划分。当然,也很难设想可以采用多种标准,对方言分区产生相同的效果。”既然难以做到只用一个标准,只好迫不得已地采用多项标准。从王力一直到《中国语言地图集》,采用的都是多项语音特征。罗杰瑞(1995)则采用了一套“包括有音韵、词汇、语法三方面”的多项标准。此后,李如龙(2001)认为,“方言特征词可以为方言分区提供依据”,“只根据语音特征来区分方言是不可能做到不偏颇的”。詹伯慧(2002)认为,“毫无疑义,在考虑以方言特征来区分不同方言时,语音、词汇和语法理应受到同样的重视”。然而,即便增加词汇语法标准,恐怕也难以真正做到全面。若用这种思路来指导分类,一旦发现按原先的标准分出来的方言区有不尽全面之处,必然会设法增加新的标准以求全面,那么,标准就会越来越多,而且从理论上来说将会没有止境。这是与上述分类标准越少越好的原理相悖的。采用尽可能少的分类特征并不意味着抹杀众多的其他特征,过去对方言词汇、语法重视不足、研究不够也不是由方言分区造成的。
朱德熙(1986)对这个问题的精辟分析很值得重视:“给方言分区时,原则也是这样:最好能只用一条同言线来规定方言之间的界限。有人觉得根据一条简单的标准划分方言太轻率。不知道标准多了,要是划出来的同言线完全重合,那么任选其中一条就够了,其余的都是多余的。要是不重合,那么根据不同的同言线划分出来的方言区就不相同,彼此打架。此时必须确定这些标准之间是逻辑上的合取关系,还是析取关系,把几项标准合并成一项,这样才能使划分出来的方言区有比较明确的范围。”朱先生强调通过合取和析取关系可以把几项语言特征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单一的划类标准,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同言线的分歧。然而,连单纯根据语音特征画出来的同言线都难以重合,再增加词汇、语法特征只能徒然增加整合和统一标准的困难。因此,在第一步划类工作中,同时采用语音、词汇、语法三种不同质的标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容易造成更大的混乱。
那么,三类标准中哪一种最适合充当划类标准呢?显然应选择处于语言结构中更深层次者。加拿大学者J.K.Chambers、Peter Trudgill(2001)在分析各类同言线的重要性时,在对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的六项因素进行分析后,曾经尝试按照它们的抽象程度由浅入深作了如下排列:
词汇:1、词汇(lexical),2、发音(pronunciation);
音系:3、语音(phonetic),4、音位(phonemic);
语法:5、形态(morphological),6、句法(syntactic)。
在以上六项因素中,最深层的是句法。我们相信,这一概括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用作选择汉语方言分区标准的参考。不过,就汉语而言,目前对方言句法的研究水平显然还不足以提出有效的划类标准,汉语又缺乏形态标志,因此可以用来划类的抽象程度最高的结构特征就是音位了。事实上,迄今为止汉语方言分区的主要依据恰恰都是音位性的音韵标准,例如浊声母的有无及其不同的演变途径、入声韵的有无及其不同的归并方式、鼻音韵尾的多少、调类的多少及其不同分并方式等。
以上几种音韵标准中,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里的映射最具系统性和规律性。系统性表现为对共时音系的控制面广,规律性表现为对音韵演变的解释力强。前者即李荣(1985)所说的“代表性”和“频率”,也就是统辖的字多,控制面越广的要素管的字就越多。后者即丁邦新(1982)所说的“历史性”和“普遍性”,经受漫长的历史冲刷而不被湮没,而且在各地方音中均留有痕迹的要素对音韵演变的解释力最强。显然,在上述几种音韵特征中,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里的映射是管字最多、历史最久的。这从《方言调查字表》便可窥见,在该表所收三千多字中,古全浊声母字将近一千,而入声字只有六百,闭口韵字三百,浊上字一百多。浊声母不仅字数最多,而且能和各个韵摄、各个声调相配合,因此对音系的控制面最广。相比之下,入声不涉及阴声韵摄,闭口韵只涉及咸深二摄,控制面都不如全浊声母。同时,全浊声母开始清化的时间也早于入声和闭口韵的消失,波及的方言也最多,因而对音韵演变的解释力最强。综上所述,假如要挑出一项音韵特征来给汉语方言分类,根据目前的认识水平,恐怕只能是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中的映射,尽管这条标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最终选择。严格地说,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里的映射实际上是一条合取特征,王力在列举客家音系特点时就将其列为两条:(1)无浊音[b d g v z];(2)古浊声母字无论平仄,今皆读为吐气音。
依据中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里的映射这条标准对汉语方言进行整体划分,可以得到以下6类典型方言:
1、系统地保留全浊声母——吴方言。
2、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逢舒声保留浊声母或并入不送气清声母,逢促声并入送气清声母多于不送气清声母——湘方言。
3、全浊塞音、塞擦音全部并入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客赣方言。
4、全浊塞音、塞擦音多数并入不送气清塞音、塞擦音——闽方言。
5、全浊塞音、塞擦音逢平声并入送气清塞音、塞擦音, 逢去声和入声并入不送气清塞音、塞擦音;若逢上声,保持阳上调的并入送气清音,归入阳去调的并入不送气清音——粤方言。
6、全浊塞音、塞擦音逢平声并入送气清塞音、塞擦音, 逢上去入三声并入不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官话方言。
除了以上六种类型之外,山西晋中一些地区中古全浊声母字今白读音无论平仄均为不送气清声母,但这些白读音字数有限,表明白读系统已走向衰亡,而占优势的文读系统则属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官话类型。因此,尽管该类型与以上6种类型都不相同,仍不宜在整体划分的层次上划为一类独立的方言。
标签:方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