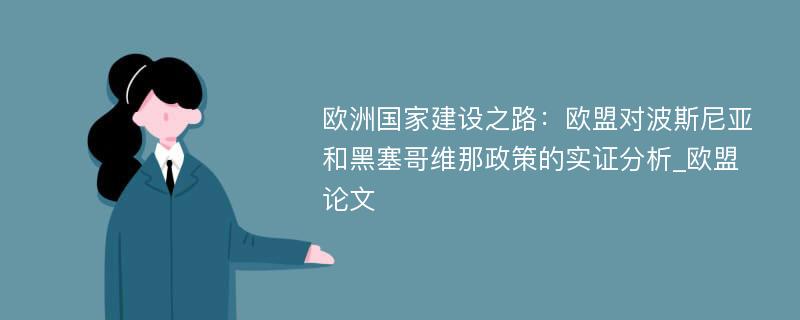
国家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波黑政策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黑论文,欧洲论文,实证论文,欧盟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①及国际社会在波黑的实践
国家构建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在不同背景下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就本文而言,笔者对其的定义就是一个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或外来行为体的帮助和支持,运用多种手段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统治核心,该统治核心有能力出台一系列国家得以运行的法律制度,实行一系列国家发展的重大计划,主要包括市场经济和货币政策在内的诸多公共政策,用于支持民主发展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等。
笔者认为,目前存在三种对国家构建的解读角度,一种从国家自主发展和自身建设的角度来看,国家构建就是国家通过制度化建设调整自己与市场、社会以及社会与市场之间的三重关系,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存在、维持和强大的过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是这一派的代表,他认为“理性化”和“合理性”居于国家构建的核心位置。②第二种观点则是探讨一些特殊行为体如欧盟的“国家构建”过程。我国学者周弘对此进行了研究。众所周知,欧洲联盟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特殊的政体(sui generis),但一些学者尝试在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中寻找对于欧洲联盟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周弘通过自己的分析认为,民族国家中的经济和法律等机制来自于国家构建历程,它们遵照功能性规律向欧盟层面转移;民族国家中的社会文化等机制来自于民族构建历史,它们根据民族性逻辑而滞留在民族国家层面;受到民族和国家两种力量双重推动的经济社会机制则在民族和国家“错位”的情况下被置于肢解的状态,向欧盟转移的只是其中功能性的部分。欧洲一体化因此表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国家转型”进程。③第三种观点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他更多地从国际秩序、全球治理或者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待国家构建问题。他认为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是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④他认为,贫困国家缺乏国家能力的问题已经直接困扰着发达国家。冷战的结束在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中东、中亚和南亚等地区留下了一群失败的、软弱无能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索马里、海地、柬埔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东帝汶,国家的崩溃或弱化,引发了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灾难。⑤福山所理解的国家构建就是指一些国家因为民族、宗教或者经济等原因无法完成国家正常的功能建设,导致国家功能的衰弱或者混乱,引起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并向国际社会外溢。
无论从哪种角度出发⑥,这些国际学者无疑都把国家构建作为研究相关对象的基本出发点,都充分认识到国家构建对国家自主发展、欧盟自身建设和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的关键性作用。由于探讨的对象不同,笔者这里只关注第一和第三种观点。这两种观点是互相借用和补充的,都是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国家性”的重要性。他们对弱国家(弱功能性国家)以及好国家(完全功能性国家)的认识都是一致的,无论在内部和外部,弱国家总会造成不稳定。笔者认为,欧盟对波黑的国家构建更多的是基于福山的观点,即无论从战略利益考量,还是从弱功能性国家溢出效应考察,波黑的弱国家性都是欧盟必须解决的问题。那么,波黑到底是怎样一种弱功能性国家呢?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黑因种族矛盾而爆发战争,国家开始分裂和解体(1991-1995年)。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1995年11月21日,国际社会代表与波黑签署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总体框架协议》(也称《代顿协议》)。它规定了波黑共和国官方称呼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国际法上作为一个国家而合法存在。但这个国家由两个实体组成:波黑联邦和色普斯卡共和国。协议强调“致力于和平、正义、容忍和协调”。⑦地方分权化、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以及确保种族平等是其基本特征。两个实体在坚持波黑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可以与邻国平等地建立关系。《代顿协议》旨在向塞族、穆族和克族三个种族共同体提供最大限度的平等保证来阻止冲突的发生,避免某个种族在国家框架内居于支配地位。协议出台许多制度机制来保证各选区民族的利益,诸如在议会的投票权,一院制立法制度和共同的国家总统等。⑧
《代顿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波黑塞族、穆族和克族之间的冲突,但它在很多方面是不完善和矛盾的。根据协议建立的波黑国家是一个权力极端分散化的弱功能性国家,两个实体都有自己的议会、政府、警察和军队,行使各自领土权限内国家运行的大部分功能。它是一个混合体,大约有80%的权力掌握在各实体手中。⑨国家中心层面的功能混乱而复杂——色普斯卡共和国集权化,而波黑联邦则权力分散化。总之,波黑包含了一个国家(波黑共和国)、两个实体(色普斯卡共和国、波黑联邦)、三个主体民族(塞族、穆族、克族)、四百万居民和五个层次的统治方式(国家、共和国、联邦、州和市)。这就造成了一个规模庞大而效率低下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决策过程非常拖沓和低效,在遇到涉及种族和实体核心利益时便陷入无法运转的境地。《代顿协议》设计者的想法是好的,希望通过协议的执行逐渐克服实体和种族之间的分离状态。他们乐观地认为波黑种族矛盾将消退,一个更西方化的政党制度将发展起来。事实上,直到今天波黑的政治生活仍旧受到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两个实体彼此猜忌,这种情绪构成了创建和巩固共同制度和多党制的主要障碍。波黑至今仍需要在国际社会支持下运行,一些国家甚至认为波黑作为一个国家缺乏合法性,而且该国有很多人(塞族和克族)并不“真心”支持这个国家的存在。⑩
二 欧盟构建波黑功能性国家的方案
《代顿协议》虽在波黑确立了和平并成功促成了政府的政治选举,但在帮助其建立一个有效的、一体化的政府上却是不成功的。这跟当时的情况有关,协议刚签署波黑国内百废待兴,国际社会当务之急是建立国内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为追求这些目标而暂时容忍了各实体和各市区政府在各自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容忍了在政府层面各种制度功能的交叉和决策的低效率。自“9·11”事件促成美国从巴尔干地区淡出后,欧盟开始全面接管国际社会对波黑的重建使命。欧盟面临的新挑战就是在波黑稳定之后如何把它建设成决策有效、功能一体的波斯尼亚人国家。实际上,欧盟构建波黑国家的动机与其对西巴尔干其他国家的动机相同,就是把它建成一个和平稳定区和完全功能性国家,并使其最终加入欧盟。其手段和方案充分体现欧盟的特色,即条件限制和制度改革。
欧盟自2000年开启了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谈判,它对西巴尔干各国使用的政策模式基本相同,通过给予相关国家欧盟成员国资格来实施条件限制,此外还引入了社会学习的过程。通过这两种方式,欧盟促进这些国家基于民主、法治和人权观念的改革。在此过程中,欧盟明确规定了这些国家入盟首要的政治和经济标准,并且强调必须达标。(11)从这种模式可以看出,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构建的方式是基于利益核算的理性选择逻辑。赋予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好处将使包括波黑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努力按照欧盟设定的条件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则是把自身构建成一个完全功能性国家,直至最终加入欧盟。欧盟明确告知波黑,只有主权和拥有自治能力的国家才能进入欧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正是具备独立的国家性这一要件才得以成功入盟的。保加利亚社会学家伊万·克拉斯托夫(Ivan Krastev)曾深刻地指出: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谜团中有一个清晰可见的线索:“只有真正的民族国家才能在欧洲一体化计划中成功。”(12)
欧盟的制度改革则以2002年对“代顿协议”的修正为标志。2002年3月27日,(欧盟)高级代表(13)与波斯尼亚政治家一道做出了重大的宪法修正并缔结了《莫拉克维卡—萨拉热窝协议》(Mrakovica-Sarajevo Agreement)。该协议赋予波斯尼亚所有选区的民族和市民相同的地位,确保维护每个共同体的利益以及它们在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欧盟还针对波黑设计出一种功能性的治理模式,鉴于实体层面的总统有太多的权力,宪法要求他们把权力让渡到国家政府层面而组成一个有效的国家政府。协议强调国家构建的首要问题是加强国家层面的立法。(14)但由于欧盟的制度框架主要是强调先保持民族的平等与融合,并通过发展和完善经济领域的问题来解决政治问题,因此建立真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加强经济竞争力、打击腐败和黑市成为首要目标。也就是说,欧盟对波黑制度构建的举措仍然是比较温和的,没有强迫各实体和民族尽快将权力让渡到一个统一的国家权力核心,而是希望通过发展彼此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合作逐渐实现权力让渡——这一点与欧洲一体化早期发展采用的模式是一致的。
三 欧盟对波黑国家构建政策的具体实施
欧盟在形成了对波黑国家构建的总体框架和计划前后,已经逐渐动用各种制度和工具开展国家构建活动。这种行动是漫长的,而且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总结起来就是,首先实行规范性影响,力图改造波黑制度结构。随着形势发展又辅以技术性影响,力图培育波黑的自主发展能力;而欧盟在实行这些政策过程中,也逐渐完善了其在规范和技术层面(15)的国家构建方式。
1.欧盟对波黑施加规范性影响,这一工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从1991年前南冲突爆发到1995年《代顿协议》签署,这一阶段是欧盟/欧共体对波黑的初步介入。欧盟的政策是把自身打造成一种民事力量,通过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和民主价值观来影响甚至是改造波黑。
在参与波黑重建的众多国际行为体当中,欧盟首先强调自己作为一种“民事力量”的作用,即在国际舞台上动用外交和经济工具而不是军事工具来发挥自身影响力。这一概念是弗朗索瓦·迪歇纳(Francois Duchene)在20世纪70年代在谈到欧共体未来角色时所阐述的。迪歇纳认为,国际关系日益相互依赖使得民事工具(经济关系、合作和外交)比军事工具更重要。他并不认为欧共体通过发展核能力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重要影响。在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的背景下,欧共体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发展成一支超级军事力量。它唯一可能的前景是作为一个经济力量出现,动用合作和外交工具来促进其利益与价值。(16)
欧盟朝着增强软实力方向发展也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跨大西洋安全机构的保护、自身的制度障碍(比如政府间主义的影响而无法组建统一军事力量)以及上述提到的思想家的影响。因此它在发展方向上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第一支柱——经济领域发展比较迅速且成熟,而第二支柱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则相对缓慢。
欧盟发挥规范影响力这种战略初登国际舞台并没有出彩。在前南斯拉夫危机发生前,欧盟对前南冲突的调解效率低下,最终只能看着冲突的爆发。一些分析家也认为,当前南危机不可避免时,欧共体传统的工具(经济援助和制裁、外交斡旋)无法发挥作用。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危机初期也无法达成共同立场。对自身力量的吸引力过分自信和对前南情况缺乏足够的信息造成欧盟政策的最初失败。随着波黑冲突的加剧,欧盟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等国际行为体的干预而被边缘化。1994年,应对波黑危机的联络小组(Contact Group)成立,该小组主要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代表组成,欧盟的作用开始大大降低。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联络小组是欧盟联合其他国际行为体发出声音的一个渠道,但难以听到欧盟作为一个行为体的声音。
(2)从1996年到1999年,这一阶段是欧盟在北约和联合国框架下发挥民事作用的时期。随着《代顿协议》的签署,欧盟承担了战后重建的任务。欧委会人道主义援助部(ECHO)开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1996年开始,欧盟出台了“法尔计划”和“奥波诺瓦(OBMONA)计划”,向波黑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实行贸易特惠。1997年,欧盟首次确立了政治和经济条件限制。经济援助受益国要尊重人权、民主、自由和法制等条件。具体到波黑来说,就是不断完善国家层面的建设,形成统一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主的政治制度。
欧盟虽然在波黑的经济重建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欧盟采用的民事办法缺乏清晰的战略,欧盟没有表明与波黑的长期关系是什么——没有提供给波黑明确的入盟前景。尽管它付出很多努力,但仍没有在波黑占据主导地位。美国采取的强势干预政策使得欧盟的影响力相形见绌,欧盟对波黑提出的限制条件因为缺乏强制性而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
(3)从1999年到现在,是欧盟对波黑政策的第三个阶段。从这一阶段开始,欧盟不断把自身的国家构建理念输入到波黑的和平重建当中。在这一阶段,欧盟不断调整和定位自己在波黑的角色和作用。这种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逐步完善自身作为“民事力量”的内涵,这种内涵在欧盟东扩过程中得以强化,即把自身打造成“规范性的力量”或者说是“改造性力量”——利用欧共体的贸易政策和对外援助实现外交和战略目标——把欧盟周边(包括波黑)打造成安全稳定区;借助扩大过程,促使相关国家(包括巴尔干国家)改变国内制度,使其成为稳定的功能性国家;通过把自身建设成和平稳定区,发挥榜样的规范性影响。这一时期,由于欧盟经济力量的逐渐强大,其民事影响力和规范性效应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从1999年开始,欧盟在扮演波黑地区第一大国际捐助者角色的同时,(17)它也采取了长期性的结构性冲突预防办法,旨在清除引起冲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它进一步明确了与波黑未来的关系——成为欧盟的一员。在此思想指导下,1999年欧盟相继发起了稳定和联系进程、《东南欧稳定公约》,倡导在巴尔干地区的长期战略,勾画了巴尔干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的清晰前景。2000年欧盟陆续与西巴尔干国家开始了稳定和联系进程的谈判,该进程针对的是制度建设、经济重建和区域合作,为最终加入欧盟作准备。借助这些手段欧盟确立了在西巴尔干的主导地位。西巴尔干包括波黑加入欧盟的前景由欧盟理事会在2000年6月的费拉和2003年6月的萨洛尼卡峰会上得到批准和确认。其标准和进程与中东欧的东扩是一致的:本土化或“赛舟原则”(“regatta principle”:候选国加入欧盟的先后顺序与它们的努力程度有关)和条件限制。入盟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标准由1993年哥本哈根理事会确立(即民主、人权、法制等完善的制度,信奉市场经济以及履行欧盟的义务等)。针对西巴尔干地区,欧盟又增加了一些具体的标准:与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全面合作、为难民返回家园创造机会、参与区域合作等。经历2002年的宪法修正后,欧盟加大与波黑合作力度,在新的欧共体“援助重建、发展和稳定计划”(CARDS)下实行了更多的经济援助,帮助进行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市民社会建设。
2.欧盟发挥技术性影响力。国际社会毕竟是讲究现实政治的舞台,这一点欧盟的政治家们很清楚。在发展民事力量的同时,欧盟逐渐开始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力求两条腿走路,从而在国际社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由此,以波黑问题为平台,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也明显开始向“技术化”方向转型,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提升共同安全和防卫政策的作用。
前南解体以及随后的冲突告诉欧盟,如果它想要成为一个可信和有效的国际行为体及周边区域规范的促动者,就应该用军事手段支持其行动。从1999年欧盟理事会科隆会议开始,动用军事力量就包含在欧盟的工具箱中。波黑也成为欧盟检验其安全与防卫政策的第一个试验场。欧盟在波黑开展了广泛的军事行动,它由两种专业力量组成:欧盟驻波黑军队(EUFOR)(18)和欧盟驻波黑警务使团(EUPM)(19)。
2003年1月1日,欧盟派遣的首个警务使团从联合国领导的国际警察小组(IPTF)(20)手中接管了在波黑的任务。欧盟警务使团是欧盟安全和防卫政策框架下的第一次行动,因此它带有学习和尝试的味道。欧盟警务使团对欧盟高级代表负责并密切协调与北约关系。欧盟警务使团包括近500名警官,他们通过担任顾问、监督和审查波黑警察来提高波斯尼亚警务水平,同时也承担着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重建警务力量的使命。最终,欧盟技术性影响的目的是要培育波黑独立和一体的警务力量,用以维持波黑自身的社会运行。2004年12月,欧盟又从联合国稳定部队(SFOR)处接管维稳使命并开展了欧盟建立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EUFOR Althea),共有6300名士兵部署在波黑的三个区域:西北部——由英国人指挥;北部——由芬兰人指挥;东南部——由西班牙人指挥。大约有14%被部署的人不是来自于欧盟国家,主要来自土耳其。(21)欧盟在波黑的安全和防卫政策目标是强化欧盟在波黑的地位并有效地促进欧盟的规范和价值。尤其是支持法治(由EUPM实现)并帮助维持国家稳定(由EUFOR实现),以此来增强民主和尊重人权。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对此也多次重申:“欧盟已随时准备动用军事手段和资源。当情况需要时,我们就会部署军队。要想具备综合的全面的危机应对能力,就必须在欧盟层面建设军事上的危机管理能力。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好的捍卫我们的价值和原则。”(22)
四 波黑的弱国家性成为国家构建的障碍
实际上,无论是规范性影响还是技术性影响都在波黑取得了效果,同时,由于波黑的弱国家性,通往完全功能性国家的道路仍是漫长的。
从规范性角度看,在经济层面,波黑国家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安全层面,波黑的准军事组织已被解散,被起诉的战争罪犯已经从政治生活中被排除,普遍安全得到保障,言论和流动自由得以恢复。在难民返回上也取得巨大进步——2004年末,超过100万难民返回家园。同时,在与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合作上也取得进展,2008年7月卡拉季奇被捕并送交前南法庭审判。正因为取得上述进展,2008年6月16日欧盟正式与波黑签署了《稳定与联系协议》,波黑在入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如果以建立完全功能性国家的标准来看波黑的进展,则情况不容乐观。波黑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之路仍然是漫长的。在面对经济利益的时候,各个实体很难达成一致,这就使得国家层面的政治和经济运行功能仍很弱。2003年欧盟委员会出版了关于波黑改革的年度审查报告,结果显示为“进展缓慢和不明显”。(23)在随后三年,欧盟的进展报告指出同样的问题:尽管大多数波黑人意识到并支持建设一个功能性国家,但“宪法框架提供的改革目标至今仍未实现。2006年4月波黑议会拒绝由部分政党所支持的一揽子改革。这一揽子改革包括增强国家层面的管制能力,提高和简化决策程序以及少数民族在国家议会的代表性。”(24)
从理性选择逻辑分析当前波黑现状,则更有说服力。在欧盟提供的宪法改革制度框架下,两个实体以及塞族、穆族和克族主导群体将会考虑它们是否从这种安排中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尽管波黑加入欧盟的前景对每个群体都有诱惑力,但如果为了这个暂时无法实现的前景而让出自身现有的实质利益,则是各实体不愿意接受的。尽管波黑内战结束了,但在波黑政治中,仍顽固地存在着庇护制度。(25)庇护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波黑种族利益集团所形成的统治格局,脆弱的国家性无法从法律上保障制度和政策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学者米兰·斯库里克作了相关研究并指出,在波斯尼亚,各利益群体的代表控制着绝大多数地方市长职位。《代顿协议》签订前后所延续的特权继承制确保了庇护制度的生存和受益者链条的牢固性。庇护制度决定了财产的分配和获取各种利益的机会,利益政党和有权势的财产继承人自上而下控制着波黑的企业,他们联合垄断着波黑的饭店、娱乐场所、餐馆、银行、烟草、森林、电讯、能源和自来水公司等(26)。这些获利者组成重要的国家政党,并且每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政党都形成了自己的庇护人来维持各种各样的利益。这种利益关系在国家结构中是纵横交错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塞、穆和克族的领袖是各个族的最大经济利益代表,它们每一族都组成了庞大的族际利益链条维护者,彼此之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难以妥协;从微观层面来看,在三大族下面又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彼此为控制各种资源而互相争夺,这些复杂交错的网络分割了波黑整个国家的经济,难以形成功能性的市场。欧盟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对于这种顽固体制的干预软弱无力。财富分配和获取权利的机会是极端不平等的,经济活动的私有化无法规范化,非法和非正式的经济剥夺了政府的税收,据估计每年的数目约为5亿美元(27)。灰色和黑色经济盛行导致了腐败。
与此同时,欧盟施加技术影响的目标也未取得进展。其目标是建立波黑独立和一体的警务力量,这一目标也因脆弱的国家性而举步维艰。对一个国家来说,警务力量在国内政治中最具代表性,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功能之一。但对波黑各种族来说,却是最敏感的问题。欧盟高级代表帕蒂·埃施多恩(Paddy Ashdown)从2003年开始集中进行警务改革。2004年,欧盟确定了改革的三条原则:(1)波黑政府在所有警务事务上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威;(2)各实体不能有干预警务改革的行为;(3)应以技术性而不是政治性的标准对各地区警务整合做出安排部署。(28)这些原则立即遭到抵制。波斯尼亚人认为,如果采用这三项原则,色普斯卡共和国将不会再有法律意义上的警务。基于此,色普斯卡共和国领导人强烈反对。2004年7月,埃施多恩建立了一个警务重建委员会,组建关于在波黑政府控制下的多民族统一警务力量。2005年10月,埃施多恩向色普斯卡共和国国民大会表示,应尽快接受三项改革原则并同意建立警务改革指导小组来实施这些原则。(29)警务改革不久,欧盟另一位高级代表谢林(Christian Schwarz-Schilling)于2006年2月接替埃施多恩的职位。谢林支持埃施多恩的警务改革建议,但反对对警务改革不服从的政客采取解雇等激进办法。2006年末,警务改革进入关键时期,色普斯卡共和国政客们在总理多迪奇(Milorad Dodik)领导下,反对该项计划,多次声称警务改革会威胁到色普斯卡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存在。多迪奇强调,他接受国家层面的警务力量,但色普斯卡共和国要保留独立的警务区。(30)欧盟实行的波黑警务一体化目标仍遥遥无期。
五 欧盟国家构建的特色和启示
通过欧盟在波黑进行国家构建的案例分析,笔者总结出欧盟国家构建的特点,它在波黑国家构建上的成败经验无疑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深刻的启示。
1.欧盟国家构建方式以规范影响为主、技术影响为辅。尽管欧盟已经意识到技术性手段(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鉴于欧盟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特点,借助规范影响力成为其主要手段,而技术性手段影响力还需要漫长的建设过程。
发展规范性影响也与欧盟国际观密切相关。欧盟对当今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假设前提是一个行为体无法解决问题,需要多边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形成,每个行为体的治理风格都会得到承认和确立,比如联合国(确立事件议程、冲突和危机调解的框架)、北约和欧安组织(防止冲突、危机处理、监督和构建安全体系等)、世界银行(对国家构建进行贷款或资金支持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经济情况、维持金融和货币稳定等)等,欧盟在这场国际分工中主要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规范的领导者,另一个是国际规则的倡议者和构建者。欧盟一直努力构建一个适合于后冷战世界实际状况的真正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欧盟从事的各种对外行动(包括对外援助、冲突调解、战略对话与合作等),也主要是想获得更多的国际道义支持和合法性,借此引领世界,重拾欧洲昔日引领世界的梦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的软实力的确已经得到举世公认,部分实现了其战略目标。而作为硬实力的军事力量建设则要服从软实力建设这一至高无上的目标的。
2.与美国、北约和联合国等从事国家构建的主要行为体相比,欧盟的国家构建方式既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从而也体现出欧盟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1)从提供冲突调解和国家构建的工具和手段来看,欧盟已经成为可以动员的资源最为丰富、最具吸引力也最具长期良性影响的行为体。这不但包括迄今为止最让人着迷的成员国资格的巨大诱惑力,而且欧盟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入盟机制来解决周边国家冲突和它们的国家构建,这套机制的严谨程度和稳定性是其他行为体无可比拟的,而且通过五轮成功的东扩后,这些机制还表现出很强的弹性。这种构建国家的欧洲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具有极高的合法性和强大的约束力——其设定的标准是申请入盟国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另外,在双边关系其他四个层次中,欧盟也体现出很强的规范辐射力和制度改造能力。(31)
从具体数据统计看,欧盟每年用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预算,2004年是6300万欧元,如果将用于对外发展合作援助、人道主义援助、促进民主与人权项目、与不同地区的合作(这些都是国家构建的主要手段)等预算加在一起的话,这个数字高达50多亿欧元,超过联合国的总体预算。(32)以国家构建最重要的手段对外援助来说,欧盟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力量,它所提供的对外发展援助占全球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总数的52%(2005年)。欧盟对外发展援助的绝对值在不断增长,2004年为350亿欧元,2006年高达480亿欧元,约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42%。同期,美国的对外发展援助仅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17%,日本占0.25%。欧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国。(33)除了自身资源之外,欧盟还可以利用其成员国(英、法、德等大国)的资源,如果考虑到欧盟还可以充分利用跨大西洋安全机制(北约)来发挥其国家构建的物质动员能力,它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国家构建可利用资源最丰富厚实、动员能量最大的行为体。
(2)联合国执行军事上的冲突调解(国家构建的第一步)的经验最为丰富和成熟。它拥有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国际制裁力,也拥有直接的决策工具、武装力量以及统一的指挥系统,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拥有几百名军事和民事工作人员来运筹帷幄。联合国安理会名义上每六个月要针对具体问题或行动做出决定,在这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可以相对不受限制地执行军事使命。可以说,联合国是唯一平衡地兼具国家构建军事和民事资源(但比起欧盟,其民事资源相对有限)的行为体。北约和美国(美国通常是借助北约开展行动)则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部署大规模军事行动,能运用军队介入到世界上任何想进入的地方。在美国主导下,北约的军事资源的动员堪称是大手笔的,是它者无法匹敌的。北约(和美国)的军事行动具有全球战略考虑,并且具有强制性,甚至某些时候宁愿采取单边手段来达到国家构建目的。但北约没有能力执行民事行动,它需要依靠联合国、欧盟和其他国际机构来开展民事行动。在军事行动决策上,北约采取一致决议的办法,但它也会采取“寡头政治”,美国可以在其中发挥巨大影响力,推动北约决策获得通过。与北约和联合国相比,欧盟的军事资源动员能力则是短板。与在规范上强调全球影响力相比,欧盟在军事上则追求区域影响力,并且都是试验性的,即使正在建设的“欧洲军”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民用机器。欧盟对军事行动采取的决策是一致同意原则,由于没有一个支配性的国家,决策效率非常低下。欧盟在承担领导责任的领域仅限于已经被北约或联合国等组织缔造出和平的区域。如果说欧盟在军事领域有何成就的话,那就是与北约、联合国等国际行为体形成了很好的分工配合。
3.欧盟的国家构建实践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同时也面临巨大考验。欧盟对波黑等国家构建的过程也是自身政策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欧盟塑造“规范性力量”的过程。在摸索建立这种力量过程中,其政策的实施经历了从失败到成功、不成熟到成熟、不断地自我定位和修正的过程。但国家构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其进程也可能是逆向的。而实践恰恰证明,欧盟在西巴尔干国家构建也有失败的案例。比如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分裂、科索沃的独立都是欧盟国家构建不成功的例证。因此,巨大的国家构建资源的投入与成功是不能画等号的。事实证明,在欧盟付出巨大努力的情况下,种族矛盾的顽固性程度最终决定国家构建的结果,这是西巴尔干给欧盟带来的最大经验和教训。(34)而欧盟的努力如果不断失败也可能逐渐消解自身国家构建方式的影响力,对欧盟及其当事国的信心都可能是一种打击,因此欧盟国家构建的模式需要根据新形势而不断调整。
注释:
①“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在汉语文献中有“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形成”、“国家建设”等几种译法。笔者选择“国家构建”这种译法。
②[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③详见周弘:“民族建设、国家转型和欧洲一体化”,《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
⑤[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序言”。
⑥当然这种分法只是笔者根据文章主题而形成的一家之言,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的分析角度,但与本文所讨论的核心内容不直接相关,参见慕良泽、高秉雄:“现代国家构建:多维视角的述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⑦"Dayton Peace Accords on Bosnia",Annex 4,Constitution,US Department of State,1996-03-30.
⑧European Commiss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Law(Venice Commission),"Opinion on the Constitutional Situation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nd the Powers of the High Representative",11 March 2005,CDL-AD(2005)004.
⑨Christophe Soloiz,Turning-Points in Post-War Bosnia,Ownership Proces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Baden-Baden:Nomos,2007,p.87.
⑩Sumantra Bose,Bosnia after Dayton,National Par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London:Hurst & Co.,2002,p.4.
(11)Bruno Coppieters et al.,Europeaniz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Case Studies from the European Periphery,Academia Press,2004.
(12)Judy Batt,"The Question of Serbia",Chaillot Paper,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of European Union,No.81,August 2005,p.30.
(13)这里并不是指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欧盟驻波黑高级代表是《代顿协议》签署后于1995年由波黑高级代表局设立,用来监督协议的民事执行情况。高级代表局则是国际社会共同组建的。后来随着欧盟在波黑地位的上升,国际社会的高级代表就是欧盟的特别代表。“9·11”之后,高级代表不但代表国际共同体也代表欧盟,它受欧盟指派并为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服务。
(14)Gergana Noutcheva,"EU Conditionality and Balkan Compliance:Does Sovereignty Matter?",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2006,p.60.
(15)规范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国家构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这是笔者根据欧盟特色进行的划分。一般而言,规范性影响是指欧盟在民事方面的影响,而技术性影响则指在硬实力(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影响,但欧盟很多军事行动只是从技术细节方面辅助民事行动的实施,并无采取武力行动干预冲突的目的,因此称为技术性影响较为妥帖。
(16)Francois Duchene,"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Interdependence",in Max Kohnstamm and Wolfgang Hager eds.,A Nation Writ Larg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before the European Community,Basingstoke:Macmillan,1974,pp.1-21.
(17)比如从1991年到2004年欧共体共向波黑捐助了250亿欧元,来自成员国的捐助达180亿欧元,参见欧盟官方网站http://europa.eu/.
(18)http://www.euforbih.org/,Accessed on April1,2009.
(19)http://www.eupm.org/OurMandate.aspx; http://www.eupm.org/OurObjectives.aspx,Accessed on April 1,2009.
(20)全称为“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ce Task Force”,该部队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97年的1103号决议组建。
(21)这是很有趣的现象,欧盟的行动当中竟然有欧盟非成员国,不过它们的行动代表欧盟。Stefano Recchia,"Beyond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EU Peace-building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Occasional Paper,No.66,Paris:EU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February 2007,pp.13-14.
(22)Javier Solana,"Reflections on a Year in Office",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Central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er,26 July 2000,Dublin.
(23)European Commission,"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on the Preparedness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to Negotiate a 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EU"(Feasibility Study),18.11.2003,COM(2003)692 final.
(24)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Bosnia and Herzegovina 2006 Progress Report",COM(2006)649 final,p.6.
(25)有关对庇护制度和庇护主义的论述,参见陈尧:“政治研究中的庇护主义——一种分析的范式”,《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6)Michael Pugh,"Postwar Political Economy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The Spoils of Peace",Global Governance,Vol.8,2002,pp.470-471.
(27)Peter van Walsum(OHR Economics Division),cited in "UN Envoy Says Officials Involved in Corruption",UN wire,17 August 2000.
(28)Timothy Donais,"The Limits of Post-Conflict Police Reform”,in Michael A.Innes ed.,Bosnian Security After Dayton:New Perspectives,New York:Routledge,2006,p.183.
(29)Timothy Donais,"The Limits of Post-Conflict Police Reform"; Gearoid O Tuathail,John O' Loughlin and Dino Djipa,"Bosnia-Herzegovina Ten Years After Dayton:Co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ublic Opinion",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47,No.1,January-February 2006,pp.63-66.
(30)James Dobbins,Europe's Role in Nation-Building:From the Balkans to the Congo,Santa Monica,USA:Rand Corporation,2008,p.160.
(31)从欧盟(多以欧共体名义或与其成员国一起)与第三国缔约的实践看,根据协定的内容多寡、范围大小和构建双方关系的紧密程度,大致有五个基本类型和层次:最紧密的是联系协定,俗称为“准成员国资格协定”;加强式协定或欧洲邻居协定次之;再次之是伙伴关系协定或合作协定;接下去是贸易协定或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这种合作协定最为常见;再就是专门性的或技术性的合作协定。参见曾令良:“中欧伙伴与合作协定:谈判、问题、建议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124-125页。
(32)朱立群:“欧盟是个什么样的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33)同上。
(34)See Liu Zuokui,"EU's Conflict Resolution Policy in the Balkans",Working Paper Series on European Studies,Vol.1,No.6,2007.
